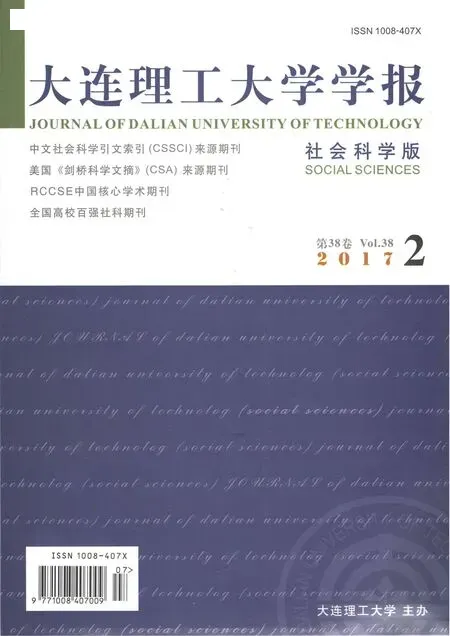环境谈判:解决环境冲突的另一方式
赵 闯, 黄 粹
(1.大连海事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6;2.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辽宁 大连 116024)
环境谈判:解决环境冲突的另一方式
赵 闯1, 黄 粹2
(1.大连海事大学 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6;2.大连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辽宁 大连 116024)
环境冲突已经成为国内环境治理中需要面对的经常性问题,环境谈判或许可以为此提供一种合适的解决方式。现实中的环境冲突主要基于对环境利益与需求的认知差异,面对环境事实,人们表现出不同的信念、偏好与评价。解决环境冲突,有两种正规的方法:环境诉讼和环境谈判。环境诉讼有其优势,但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而环境谈判在解决环境冲突问题实质方面,则具有其自身优势。为使环境谈判顺利进行,需要重视和处理好其中的原则性关键点,即确定谈判的参与者、明确激励因素、营造合作意愿与基础、引入第三方调解和对协议的遵守。而为促使环境谈判成为解决环境冲突的惯常手段,政府需提供必要支持。
环境;冲突;谈判;诉讼;调解
伴随环境污染的加剧,在逐渐增多的环境治理、环境资源管理等领域的讨论中,一些分析和研究涉及环境冲突及其解决。“冲突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1]环境冲突也是正在发展的环境治理和管理中需要面对的经常性问题。目前,对于环境冲突现象,人们可以使用的正规解决途径有:法律诉讼方式和非诉讼方式,而后一种方式主要是指环境谈判。在应对环境冲突的过程中,人们对这两种解决方式存有争论,特别对环境谈判在解决环境冲突中的优势保持怀疑。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明确环境冲突的现实问题,涉及环境冲突从何而来,这会直接影响解决方式的选择;其次,对环境诉讼与环境谈判的差异进行讨论,探究环境谈判在实质上解决环境冲突的可能性;再次,讨论环境谈判的技巧,如果选择这种解决方式,如何进行谈判才能达成一致协议;最后,探讨环境谈判常态化问题,政府能否对此有所支持和保障。
一、环境冲突的现实
从某个视角来看,环境冲突是以环境资源为媒介,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其中涉及到不同类型环境利益的冲突[2]、广大民众权利困境[3]和政府职能缺失[4],也关涉世界观的差异[5]、以及价值冲突与抵牾[6]等。在这个意义上,环境冲突可以被理解为:至少有两个行为人或群体在同一时间努力获取某种环境资源的社会情形之下,在交互过程中造成的利益、需求和目标上的分歧状态。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分歧状态主要表现为,当事者对某一个项目、决定或政策对环境资源状况的影响所持有的不同看法,即基于对环境利益与需求的认知差异。
地方政府意图建设对二甲苯(PX)化工项目,但当地居民普遍对此项目持反对立场;公共事业部门建议建设垃圾焚烧厂,但当地居民表现出几乎一致的抵制态度;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出台严厉的惩治举措和规章,被影响的企业、地方政府对此颇有微词,而环境保护群体和公众也心存不满。那么,是否应该引进对二甲苯化工项目?是否应该建设垃圾焚烧厂,或哪里才是合适的建设位置?环保部门的规章措施是有效的吗?可以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衡量吗?显然,人们对此看法不一,对什么是合适的政策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在这些例子中,环境冲突真正表现在人们对现实问题的不同认识上。地方政府认为化工项目对经济有巨大推动作用并符合环保标准,但当地居民普遍对此项目可能带来的环境危害感到恐慌[7];公共事业部门认为垃圾焚烧厂的环保功能巨大,但民众认为焚烧飞灰会对自然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8];受到环境政策所影响的企业、地方政府也许会认为其太过严格,成本代价太高,而环境保护群体、公众可能认为这些做法仍旧力度不够,不足以改善环境质量。若要解决环境冲突,就要更多地认识和理解这种背后的认知差异。
现实中的环境冲突有多种来源。由于一件事情的结果会对当事者带来不同的影响,产生不同的利害关系,所以,当事者经常对一件事情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场。如果打算兴建水电站,有些人会为发展清洁能源来增加能源供应并缓解减排压力而选择支持,有些人则因为担心造成地质变化而表示反对;有些人因为防洪和获得更充足的供水量而趋向赞同,有些人则因为对河中渔业资源的影响而持否定态度;居于上游的居民也许会同意,居于下游的民众可能会抵制,或者相反[9]。当事者对分配结果的简单计算,对谁受益和谁损失的估计,会为认识环境争议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当获益大于损失的时候,一些合适的补偿也许会使那些承受损失而持否定看法的人们,放弃反对立场。然而,在许多环境冲突或环境争议中,谁将有所得和谁将有所失,并非显而易见,环境决策经常要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例如,临海而建的核电站是否可能发生事故而威胁人体健康,这应取决于包括污染处理设备在内的整个核电机组设施正常、有效地运转。虽然理论上事故概率非常小,但因为新的技术或复杂的地质情况,没有人能够完全断言结果[10]。同样,建造核电站会带来更多的税收和就业,但也可能对市政管理带来很多额外要求和风险,也许不利影响最后会变成有害后果。所以,类似的建设项目究竟是好是坏,我们无法准确判断,这也许最终取决于我们无法精确预测项目发展的各种条件与趋势。
不确定性是导致很多环境冲突的重要问题,但很多时候,环境冲突并非仅仅来自于环境事实本身的不确定,也在于当事者对环境事实的不同认知。环境事实本身只是影响因素之一,数据与论证有可能起作用,但也有可能用处不大。认知的差异使当事者对环境风险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对机会和可能性进行不同的判断,做出不同的决定。假设某个城市面对不断增加的垃圾量,必须决定如何有效地处理固体废物问题。现今,有两个选择摆在面前:一是建立一个垃圾填埋场,另一个是建造一个垃圾焚烧厂。事实上,这两个选择都可能产生环境污染,具有环境风险。填埋场,如果不能得到良好的建设和维护,渗滤液是其最大隐患,污染地下水;焚烧厂,如果不能得到严格地建造,二噁英气体是其最大危害,污染空气。在所有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该城市会偏向于选择对环境威胁最小的选项。这种威胁与两个因素的作用正相关:环境污染的概率及其产生影响的程度。
从技术条件上来说,我们可以对两者产生环境污染的可能性进行估计,给出概率。假定:填埋场产生污染的概率是x,无污染的概率就相应为1-x;焚烧厂产生污染的概率为y,无污染的概率就相应为1-y。但人们经常会对此有截然不同的估计,一些人相信某个设施十分安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非常危险。有时候,这种差异来自于各自掌握的信息不同。在环境冲突中,反对者和支持者因为仅仅拥有或了解片面的信息而产生巨大分歧,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但很多情形却是:即使人们面对同样的信息和数据,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概率的不同估计会产生环境冲突,但当人们对概率达成一致的时候,冲突仍可能发生。相对来说,填埋场发生污染的概率很低,而焚烧厂则很高。设想人们同意x为1%,y为99%。但发生污染概率高不等于对环境的威胁大,发生污染概率低不等于对环境的威胁小,还取决于其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对于发生污染后的影响程度有多少,人们又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会认为水源受到污染更不可接受,另一些人则认为空气污染更无法忍受。假设人们对影响程度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样发生1次污染,填埋场造成100万元的损失,焚烧厂造成5万元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居民也许会支持填埋场建设,看重了概率,而不是影响程度;有的居民也许会支持焚烧厂建设,看重了它的影响程度,而不是概率。当然,还可以将概率和影响程度相乘,算出二者的环境成本分别是:填埋场1万(1%×100万);焚烧厂4.95万(99%×5万)。但金钱不是唯一的问题,相对来说,地下水对有的市民更重要,而不是空气。这毕竟不是纯粹的数学计算,这是人性化的认知。知晓环境成本,也无法避免认知与偏好的差异。
我们对这个“垃圾处理项目”的例子作了很多简化,逐步弱化其中的不确定性,但认知差异致使环境冲突始终存在。简言之,即使在一个概率和影响都为人所知的假想世界中,对风险的不同认知与态度仍将酿成冲突。而在现实事件中,如果还要分析利益相关者的范围[11]、如何选址[12]等诸多问题,将会面对更多的认知差异,也因此会导致更多环节的环境冲突。尽管科学与社会都在不断发展,但对使用自然资源的后果,我们仍旧有许多无从所知的地方,它的长期影响带有不确定性。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同样的事实,人们表现出不同的偏好、价值观和态度,而这一切又并非完全不合情理,我们也没有理由简单地给出评判:哪一方的认知更正确、更重要。那么,面对充满认知差异的环境冲突,采取哪种解决方式才是合适和有效的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二、两种正规解决方式的比较
环境冲突复杂而棘手,面对环境冲突及其带来的纠纷,有两种正规解决方式可供选择,一个是提起诉讼,另一个是展开谈判和进行调解。由于面临严峻的环境治理形势,中国正在加紧修订和制定相关法律,如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对希望以法律途径来解决环境冲突和纠纷的民众、专家、环保组织给予了一些回应,拓宽了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虽然,中国环境立法进程还面临诸多争议[13],但以诉讼方式来解决环境冲突仍存在有利之处。因此,许多环保支持者主张和提倡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诉求。
那么,以诉讼方式来解决环境冲突具有哪些优势?第一,诉讼可以提供法定授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获得法律权威的支持,一个小群体,甚至民众个体(虽然新颁布的《环境保护法》并不支持,但已有成功案例[14]),得以有可能与大型财团或强大的政府机构进行较量,并且,有时也有取胜的机会。诉讼之所以吸引人,也在于其具有强制力,可以强制做出行动。当一方提起诉讼和做出指控,另一方必须应诉和回应。诉讼过程在高度建构的规则下进行,这种规则也为当事者所事先知晓。即使法官无法摆脱外部环境影响,但他们也许是最有能力将这种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的群体。第二,诉讼会产生重要影响力。即使在最终是否胜诉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仅仅是提起诉讼都会使被侵害方对实施侵害的一方获得重要优势,虽然这种优势或许是短暂的。在由环境污染造成侵害的案例中,即使污染企业或公司对最后的判决结果有合理的信心,但只要足够理性,如果对方肯撤诉,该企业或公司通常也会选择减少对环境的破坏。第三,诉讼也是教育公众和激发公开讨论的方式之一。通过走进法院来制止污染环境的行为,这样的诉讼案有可能获得社会各界关注,如果经过广泛宣传,也有望促进立法进程,催生更为严格的立法规范。当环境事件进入诉讼程序,对环境质量的抽象关注会变得更为具体,也会增强环境保护的公共信念。环境诉讼是一种公共性实践,体现公共性精神[15]。
然而,由于其自身特点,诉讼方式有其无法克服的制约。除了公认的成本过高(这其中不仅包括金钱意义上的费用支出,也包括诉讼付出的时间和人力资源成本[16])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环境诉讼对解决环境冲突中的多重认知差异问题有其固有的限制。第一,从性质上来说,诉讼方式是一种对抗模式。控辩双方在法庭上都将对方看成是对手或敌手,一方的胜诉建立在另一方的败诉基础之上,这是零和博弈。一方认真听取另一方陈述的目的,不是为了倾听和理解,而是为了找到其中的弱点而予以攻击。而复杂的法定程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息的可获取性及其相关讨论,这也限定了法官看待环境冲突的方式。第二,法庭裁决有着单一焦点,范围相对狭窄。裁决关注的是权利,关注如果侵害了环境权益,如何进行纠正、惩罚和补偿才是合适的。这种对权利的聚焦并无不好,只是法庭裁决不可能更多考虑税收、激励措施、各种补贴、市场调节等相关替代手段可能对解决环境冲突具有的作用,而这些方面对人们的认知差异(特别是对政策的不同认知)却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第三,诉讼以事实和程序为导向,无关预防与未来谋划。解决环境冲突重在预防,这是缓解所有环境难题的最佳选择,而且,环境冲突涉及很多影响未来的复杂因素,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后果持有不同看法和各异估计,认知差异不仅指向当下,也指向未来。但法院只能就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调查(司法确定事实的过程决定了这会是一个困难重重的事后调查[17]),适合纠正过去和正在发生的不公正,而不适合对未来发生的变化给出谋划。对法庭裁决来说,有关预防和未来规划的意图本身就是陌生的。
上述局限是诉讼本身特点和法官权限所致,法院不能篡夺行政决策权威,这正是环境诉讼面对环境冲突中认知差异的无奈之处。环境诉讼不能对政策和决定做好坏的判断,只能就是否符合程序来给出裁判。所以,诉讼很难触及深层的环境决策及其认知差异问题。如果过度依赖法院的特性与司法制度,往往会带来司法资源浪费或超出其能力所及[18]。寻求诉讼方式来解决环境冲突是法治社会的表现,但环境冲突是否只能或都要依靠环境诉讼来解决。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所有环境冲突都在法院走完全部法律程序,法院系统将处于瘫痪状态。在有组织的社会中,法律并不是唯一的社会调节器[19]。我们需要一种非诉讼方式使之与诉讼方式相配合,这种方式能够聚焦于当事者对某一个政策、项目或决定的认知差异和利益纠葛,充分考虑政府、社会、市场等多种影响因素,在规则下寻求共识和达成协议,对未来变化和发展给出规划。而环境谈判(包括调解)这种非诉讼方式,或许可以成为解决环境冲突的另一途径。
在国外,如美国,早在20世纪已经开始鼓励使用谈判等类似方式来解决环境领域的冲突,由第三方协调当事者就环境问题进行协商,尽可能实现最佳的互惠结果[20]。有学者从公共参与、政策制定和规则制定的角度来探讨环境冲突解决中的谈判和调解问题[21];有的利用“转化型理论”[22],以转化型调解的方式来讨论环境冲突解决中的复杂情况[23];还有的专注于结果评价和促成因素[20],以及这种解决方式所面临的挑战[24]。而在我国,从2002年开始国家日益重视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重新强调调解的意义[25]。如今面对不断加剧的环境冲突与纠纷,人们主要从行政调解[26]和诉讼调解[27]来探讨其中的问题与解决机制,也有从博弈论角度来分析环境规制谈判的模型[28]。本文要讨论的环境谈判是一种在当事者中进行的非诉讼谈判。
环境谈判的优势在于:第一,环境谈判是以谋求共识的方式来解决当事者之间的冲突,相对于对抗方式,这种方式表现出一些自身的优势。在当事者自愿条件下进行的环境谈判,就是为了让各方对各自的认知差异有更全面的了解。各方在谈判桌前所展开的讨价还价过程是各方不同想法的直接呈现,由此产生的结果更可能准确反映当事各方的偏好。谈判的处境使拥有不同价值观和实际利益的各方更可能完整表达自己的认知、观点与评价,因为谈判更关注的是如何共同解决问题,而不是维护强制性的法庭秩序。在这里,一种致力于解决共同问题的期望将得到提升。第二,面对面的商谈使各方有更好的条件考虑不同的解决方案和分析由此产生的不同结果,对环境问题的技术与制度维度有更好地理解。在谈判中,不但涉及相关法律,还会涉及对环境科学、环境政策以及相关的行政职能、经济手段和市场条件,甚至对道德、习惯与风俗等也有所关照。这些因素在多个层面构成了认知差异产生的原因,也是利益分歧的根源。对多种因素、方式和结果的全面讨论和商谈,更可能使实质问题得到解决。第三,环境谈判是一种避免环境冲突激化或环境诉讼唯一化或暴力冲突产生的方式,是对可能造成的环境损害的预防手段。最后达成的一致协议会基于环境问题的特点,对未来的变化做出说明,即使之后还会有问题出现,早期的谈判将会提供迅速有效的解决模式。环境谈判不会只注意过去和现在,还会关注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因为环境谈判所促成的协议更像是一个共同决策,而不是一个判例。
环境谈判的好处是具有吸引力的,但作为一种通过达成一致协议来解决环境冲突的方式,它也有弱点。一些弱点内在于共识过程中,而另一些则可以克服。如果一些障碍得到清除或减少,环境谈判的道路会变得更加通畅。
三、环境谈判的关键:如何开展谈判
无论在私人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谈判都是解决冲突的基本方式。环境冲突通常带有社会性与公共性,这种冲突未必就会导向暴力行为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环境谈判会为此提供一个缓冲和解决手段。而环境调解基本上可以被看成是需要第三方协助进行的环境谈判。环境谈判通常会涉及多方当事者,要处理认知、观念和利益等多种冲突。为了顺利开展谈判,必须确定谈判的参与者,激发和维持人们的谈判意愿,营造合作氛围以达成共识目标,视情况引入第三方调解,并落实协议要求。这些是环境谈判的关键。
1.确定谁应该参加谈判
在环境谈判中,确定参与谈判的当事方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例如,对于一个石油化工厂的兴建所引发的环境冲突或纠纷,应该有哪些人可以参加谈判。开发企业很明显是当事方,相关负责的当地政府机构也是当事方,当地民众的生活会受到影响,也应该参与谈判。那么,与这个工厂兴建相关的周边经济实体及其顾客、员工是否也应该参加谈判;如果这个建设也可能影响到外省市的空气、水源等环境质量,是否他们也要有代表参与谈判;基于对自然环境状况的关切,民间环保组织和团体是否也可以坐在谈判桌前;对此感兴趣的大众传媒和专家,是否可以加入谈判。一般来说,那些在结果上有着重要利害关系的当事者应该得到考虑和确认,这其中就包括所达成协议直接影响的人,成功执行协议所需要的人,以及如果不参与进来就会削弱谈判的人[29]。同时,谈判也要为其他公众提供参与机会。但谈判者的数量需要予以限制,谈判桌前的人数越多,谈判越难以协调,彼此的信任越难以建立。必须存在一个准入制度,确认谈判当事方的资格,以及谁能够代表当事方参与谈判。所以,经过筛选后,上面例子中的谈判者可以包括:直接利益相关方代表,如开发企业代表、直接明显受到影响的居民和经济实体代表;负责的政府机构代表;民间环保组织代表(如果基于濒危物种保护、湿地保护、保护区维护等公益目的,可以参与谈判);调解人(如果引入第三方调解)。谈判进程和阶段性成果应该适时对外公布,举行发布会或听证会,确保其他关注者可以获得相关谈判信息,并有机会提出疑问。解决谁可以成为谈判者,无疑是环境谈判的首要和关键问题。
2.明确激励因素
只有当事各方愿意,谈判才能开启。但同意谈判,并不意味着就会达成一致协议。谈判过程由一系列选择所构成:考虑在什么时间和地点会面,如何设计议程,提出意见的恰当时机,如何对要求进行回应,是否确定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否执行全部协议,是继续谈判还是离开谈判桌。这些选择具有连锁效应,要促进谈判进程顺利开展,就必须明确其中的激励因素。激励因素也许会被认为就是成本收益问题,尽快开展谈判和达成协议,最能节约成本,可以减少由于冲突继续而产生的成本消耗,也可避免成本花费更高的解决方式,甚至能使成本转化为收益。但环境谈判的结果并非仅仅取决于金钱,环境谈判的进展更与人类的基本需求相关。谈判立场背后的人的基本需求,如安全感、经济利益、归属感、认同感和生活自主性,不应该被忽略,只要一方认为自己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谈判就不会取得进展[30]47。在环境谈判中,这些基本需求似乎也与金钱有关,但认可认知差异的存在,换位思考另一方的处境和利益,感受另一方的情感寄托,才是谈判力量的更好体现。谈判中的情绪具有信息传递和激励功能[31],应尝试去理解自己和对方的情绪。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信任关系,而谈判的许多好处都来自信任的氛围。不仅要尝试信任别人,也要知道如何让对方信任自己。公平对待、理解和信任、以及情感慰藉,是促成人们达成共识的重要因素。
3.营造合作意愿与基础
环境谈判之所以具有自身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以各方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环境冲突。它的博弈论根据是非零和博弈,而不是零和博弈。环境冲突各方之所以同意谈判,仍旧是主要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但重视自己的利益,并不等于置对方利益于不顾。一旦对方发现你在认真考虑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开始重视你的想法,协作的意愿就会增加,而这种意愿是实现最终合作所必须的[32]。最后达成的协议不是为了实现某一方的利益,而是在各方利益中寻求平衡。环境谈判既为减轻环境风险或污染,也为尽可能降低处置成本;既重视保护环境,也创造就业与税收。如果最终的结果是,项目不能开工建设,或发生污染,或补偿不被接受,各方都不能从此脱身,没有哪一方完全没有损失,还会带来更多的误解和敌意。创造合作解决问题的氛围,需要找到利益共同点或利益相容点。在谈判时,可以给出多个解决方案以供选择,目的不是一定要找到其中哪一个是正确的方案,而是为谈判打开一个开放的空间,为合作寻求一个共同利益的基础。寻找利益相容意味着:寻找对你代价最小,对对方好处最大的方案,反之亦然[30]75。环境谈判的关键就在于将冲突对抗转化为合作共赢。
4.引入第三方调解
调解是一种推进谈判的方式,介入谈判的第三方既无决策权威,也无权力强加解决办法,但精于调解并不偏不倚,能够协助谈判各方对所有或部分纠纷议题达成自愿、一致同意的决议[33]。以重要谈判经验看,借助调解人来开展环境谈判,是实用和明智的选择。调解人对谈判的作用,是谈判各方不能替代的。调解的基本过程是:调解人确定各层面的问题和各方自己无法达成协议的原因;然后,给出谈判如何继续的建议,如果各方和调解人都同意以引入第三方调解的方式进行谈判,调解人可分别约见谈判各方,探求他们最想保护的利益是什么,以及为保护这些利益希望其他各方做些什么;随后,就是发挥创造力的阶段,针对各层面的问题举行一系列单独或联合会议,讨论和评价尽可能多的解决办法,直到穷尽所有的可选办法;最后,调解人提供协议草案,供谈判各方审查和修改,这种修改会重复下去,直到最终达成协议。所以,环境调解的核心特性就是能够创造性地帮助环境谈判各方找到形成共识与妥协的领域,促使他们以新的、分享的视角看待彼此的认知、价值观和态度,从而缓和情绪和改变态度。相对于诉讼和决策过程,环境调解在程序上拥有更多灵活性,调解人具有与环境谈判各方进行私下沟通的行动自由,并可以适时提出实质性的解决建议,这是环境谈判成功的基础。调解人必须知道谈判各方的要求、愿望、工作程序、认识局限和行业限制,将各方的提议表述得更加清楚,并容易接受。例如,由于项目施工产生的噪声污染而引发的环境冲突,居民提出项目施工不能在20:00-07:00之间进行,而经过调解人转述变为:建议在07:00-20:00之间进行项目施工。调解可以利用调解人的信誉、谈判经验、专业知识、沟通管理能力来发挥影响力,但最终还是要依赖于谈判各方的信赖和满意。
5.对协议的遵守
当各方离开谈判桌后,谈判并没有结束,遵守协议是环境谈判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如果不能确保遵守协议,协议甚至不会得到签署。协议达成与履行协议同时发生,或者,彼此承诺之后同时履行协议,这两种情况相对简单。而复杂的情况是:各方承诺履行协议,但非同时履行。很多时候,环境谈判面临着这种复杂、长期的履约承诺,如水坝、化工厂、垃圾焚烧厂等项目的建设,项目建设的许可在前,而履行环境保护、环境资源分配的承诺在后,并且,间隔时间长,这就会给先履行承诺的当事方带来很大风险。为尽可能规避违约风险,需要采用一些必要手段。例如,设立仲裁条款。如果对协议条文的解释出现纠纷,以仲裁方式解决;设立或有条款和第三方管理账户,为今后设置必要的污染控制设施提供资金,并与监控手段配合使用,当发现排放超标,便启动污染控制设施的建设活动;设立保证金,提供违约补偿;设立惩罚条款,明确细致地说明如何取得罚金。而面对多方履约者,可以建立对各方履约行为的结构性约束,将一个大的协议履行框架拆分成由多个阶段、多个部分组成的形式,由各方交叉执行与行动,每一方的一个阶段的履约行为都会得到某一方或多方的相应履约行为的回应,“连续违规不仅要招致名誉损失和非正式的制裁,而且很可能要招致法律制裁,”[34]从而在各方之间建立起持续的履约关系与习惯,保证对协议的遵守。
总之,确定谈判的参与者,以及准入和退出条件;发现和调动激励因素,推动谈判积极进行;寻找合作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方案;适时引入第三方调解,打破僵局;保证对协议的履行。这些都是成功开展环境谈判需要遵循的原则性关键点,直接关系到谈判中实质性结果的取得。尽管环境谈判的过程不能循规蹈矩,协议的达成不会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从谈判中获得全部好处。但谁也无法忽视:“不论双方的相对实力是否悬殊,你如何谈判(以及你如何准备谈判)会对谈判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30]173。即使最终无法达成一致协议,对这些谈判关键点的良好处理,也会为各方之间建立良好的商谈与合作关系奠定基础。
四、结 语
在国内,环境谈判还不是一种解决环境冲突的常规方式。人们并不熟悉这种争端解决过程,相对来说,他们更熟悉使用对抗性策略来实现利益。实际上,与环境谈判相比,通过直接冲突和对抗来解决环境冲突与纠纷,是最易操作的。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召集人们坐在一起对某个问题进行谈判与协商,找出共同的解决办法,要比直接诉诸冲突和对抗困难得多。试想将一群对具体环境问题的各个层面都带有不同偏好和优先性考虑的人们聚在一起理性商谈、寻求共识容易,还是在他们之间激化冲突与争端容易,答案显而易见。当前,为使环境谈判成为应对环境冲突的惯常手段,必须做出改变,而这种改变主要在于政府主体的行动。
1.政府主动推行环境谈判
在可预见的未来,环境冲突会伴随有限资源的分配、公共优先权的设定、环境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等继续呈现多发态势。如果想让环境谈判成为可被接受的环境冲突的解决方式,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面对环境冲突,政府既是治理主体,也可能成为当事方。政府应以环境谈判作为首选应对手段,推动谈判规则设计和订立,积极促成各方坐到谈判桌前,展开谈判,并在必要时,帮助引入合适的第三方进行调解。
2.环境保护负责机构的形象重塑和能力延伸
在谈判中,环境保护负责机构是大企业、大公司、地方利益的制衡力量。环境保护负责机构应更新观念,塑造平等的管理者、监督者形象,拓展谈判能力与经验,但在适用环境法规和标准的时候,应体现和维护环境保护的公共性。环境保护负责机构应向各方表明,在不违反环境法规与标准的情况下,会努力在各方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冲突解决方法,使环境冲突各方预期有所收获或相信可以避免更大损失,否则,他们便不会真心实意地进行谈判。事实上,在某些环境谈判中,调解人可以由来自环境保护负责机构的人员来担任,比起一个来自私人机构的调解人,环境保护负责机构的人员也许更容易赢得信任。环境保护负责机构不仅仅是环境违法行为的惩罚者,也应该是环境冲突的协调人,而政府还可以为培养更多的专业环境冲突调解人提供资金支持和认证服务。
3.善用媒体在环境谈判中的作用
整体来说,媒体可以监督和确认谈判信息,可以让局外人知晓自己的利益未被损害或被包含其中,甚至,也可以给予当事方施加压力,促使各方最终达成具有公共利益考量的谈判协议。政府机构也许担心由于自己对环境谈判的参与,一旦谈判结果不理想或谈判破裂,政府便会成为众矢之的,而与被管理者进行谈判,也容易招致“幕后交易”、“利益输送”的怀疑与诟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借助媒体在谈判中的特殊作用,阐明其在谈判中的观点、要求和行动,进行必要的公共宣传与传播。当然,要尊重谈判规则,只对各方同意公开的阶段性信息进行公开,不能使媒体成为谈判中的负面因素。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最好能够提升新闻媒体在谈判中的作用,而不是削弱它。
4.必要的法治环境和伦理责任约束
当人们拒绝谈判的时候,不是拒绝谈判本身,而是拒绝极易被滥用或非法利用的谈判方式。良好的法治环境是环境谈判得以普遍施行的必要条件,环境谈判需要在法律的庇护下来进行。在环境谈判中,当事方的强弱对比通常十分明显,如果没有法律的威慑,强者与弱者很难坐在谈判桌前开始谈判,而即使展开谈判,这种谈判也会在实质上成为受操纵的胁迫游戏。在某种意义上,环境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将会促进环境谈判的可行性。同时,环境谈判应该受到环境伦理和公共责任的约束。对一般谈判中当事各方的伦理责任做扩大解释也许并不合适,但鉴于环境谈判的公共性影响,即对生态资源、环境资源的影响,谈判各方不能无视环境伦理和公共责任,此种约束将增进谈判协议的公正性和稳定性。
强调政府在环境谈判中的作用,我们意图探讨的是政府应当在其中担负的责任。环境谈判不能取代环境诉讼,但环境冲突不能仅仅通过环境诉讼来予以解决,负责的行政机构、政策制定者必须要承担解决环境冲突的职责,具有环境谈判的能力,扫除环境谈判的障碍,适应并习惯于公开的环境谈判活动。在解决环境冲突过程中,环境谈判未必都带有时间和成本优势,但环境谈判的真正长处在于它更有潜力促成那些为相关利益人更易接受并付诸实施的决定。我们将环境诉讼与环境谈判进行对比,不是要在二者之间做优劣选择,或二选一的取舍,而是想要找到能够予以补充或配合的方式,在面对环境冲突的时候,存在更多的解决途径。也许人们还需要时间来适应环境谈判的方式来积累环境谈判经验与技巧,但有理由相信以协调合作与共识决策为基础的环境谈判,会为解决环境冲突贡献更好的实践形式与策略选择。
[1] CARPENTER S,KENNEDY W. Environmental conflict management: new ways to solve problems [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1981,1(1):65-70.
[2] 刘莉. 邻避冲突中环境利益衡平的法治进路[J]. 法学论坛,2015,(6):39-46.
[3] 孙旭友. 邻避冲突治理:权利困境及其超越[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81-86.
[4] 谭爽,胡象明. 环境污染型邻避冲突管理中的政府职能缺失与对策分析[J]. 北京社会科学,2014,(5):37-42.
[5] ABRAHAM E. Towards a shared system model of stakeholders in environmental conflict[J].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8,15(2):239-253.
[6] 李启家. 环境法领域利益冲突的识别与衡平[J]. 法学评论,2015,(6):134-140.
[7] 李永正,王李霞.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实例分析[J]. 人民论坛,2014,(2):55-57.
[8] 杨长江. 重视垃圾焚烧超常规发展引发的环境与健康风险[A]. 刘鉴强.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4[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09-117.
[9] 鲍志恒. 长江水电开发再现危局[A]. 刘鉴强.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3[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48-58.
[10] 王作元,马卫东. 从日本福岛核事故影响看中国的核安全[A]. 杨东平.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2[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69-78.
[11] ABRAHAM E. A system dynamics model for stakeholder analysis in environmental conflic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2012,55(3):387-406.
[12] 杨长江. 垃圾危机[A]. 杨东平.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1[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212-214.
[13] 郄建荣. 2014年中国环境立法进程[A]. 刘鉴强.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5[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62-70.
[14] 郑世红. 全国首例公民个人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A]. 王灿发. 中国环境诉讼典型案例与评析:律师版[C].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259-281.
[15] 高冠宇,江国华. 公共性视野下的环境公益诉讼:一个理论框架的建构[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0-15.
[16] 王灿发,冯嘉. 中国环境诉讼的现状与未来展望[A]. 王灿发.中国环境诉讼典型案例与评析:律师版[C].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6-7.
[17] 夏锦文,徐英荣. 现实与理想的偏差:论司法的限度[J]. 中外法学,2004,(1):33-46.
[18] 考默萨. 法律的限度[M]. 申卫星,王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
[19] 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69.
[20] EMERSON K. Environmental conflict resolution:evaluating performance outcomes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J]. Conflict Resolution Quarterly,2010,27(27):27-64.
[21] BEIERLE T C,CAYFORD J,Dispute resolution as a method of public participation[A]. O’LEARY R,BINGHAM L B(Eds.). The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of Environmental Conflict Resolution[C]. Washington,DC: RFF Press,2003.
[22] ROBERT A. The Promise of Mediation: the Transformative Approach to Conflict[M].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2005.
[23] CAMPBELL M C. Intractable Conflict[A].O’LEARY R,BINGHAM L B. The Promise and Performance of Environmental Conflict Resolution[C].Washington,DC: RFF Press,2003.
[24] BLACKBURN J W,BRUCE W M. Mediating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Theory and Practice[M].West,CT: Quorum Books,1995.
[25] 吴英姿. “大调解”的功能及限度——纠纷解决的制度供给与社会自治[J]. 中外法学,2008,(2):309-319.
[26] 周健宇. 环境纠纷行政调解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 生态经济,2016,(1):201-206.
[27] 裘实. 两造合意与环境保护的平衡[J]. 福建法学,2015,(1):3-5.
[28] 姜涛,薛红燕,张光. 基于合作博弈的环境规制谈判模型研究[J]. 管理世界,2011,(3):17-18,38.
[29] DALE C. Building consensu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putting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C]. Ottawa,Ontario: National Round Tabl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1996:23.
[30] 罗杰·费希尔. 谈判力[M]. 王燕,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31] OLEKALNS M,DRUCKMAN D. With feeling: how emotions shape negotiation[A]. MARTINOVSKY B. Emotion in Group Decision and Negotiation[C].Springer Netherlands,2015:32.
[32] 托马斯·谢林. 冲突的战略[M]. 赵华,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62.
[33] O’LEARY R. Assessment and improving conflict resolution in multiparty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Behavior,2005,8(2):181-209.
[34]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 于逊达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50.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 An Alternative Form of Resolving Environmental Conflict
ZHAO Chuang, HUANG Cui
( 1.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Humanities,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116026, China;2.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
Environmental conflict is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faced constantly in domestic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 may provide an alternative form for environmental conflict resolution. In fact, environmental conflict results mainly from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and environmental demands. When faced with environmental facts, people may show distinctive beliefs, preferences and judgement.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may be resolved through two appraoches-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and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 has some merits, but it is not without limitations. However,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 has its own strengths in resolving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To guarantee smooth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s, several key points need to be cleared: participants identification, incentive confirmation, joint problem-solving, third party mediation and compliance with the agreements. It is advisable that governments adapt to changes and provide essential support to make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 a habitual form of environmental conflict resolution.
environment; conflict; negotiation; litigation; mediation
10.19525/j.issn1008-407x.2017.02.019
2016-08-08;
2017-02-26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我国环境群体性冲突及其治理机制研究”(14BZZ084);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我国环境冲突应对中的公众参与问题研究”(W201407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环境正义视角下的环境伤害问题研究”(3132016365)
赵闯(1978-),男,辽宁营口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政治与政策研究,E-mail:zhaochuang2008@163.com;黄粹(1979-),女,辽宁鞍山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社会性别与社会组织研究。
D089
A
1008-407X(2017)02-01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