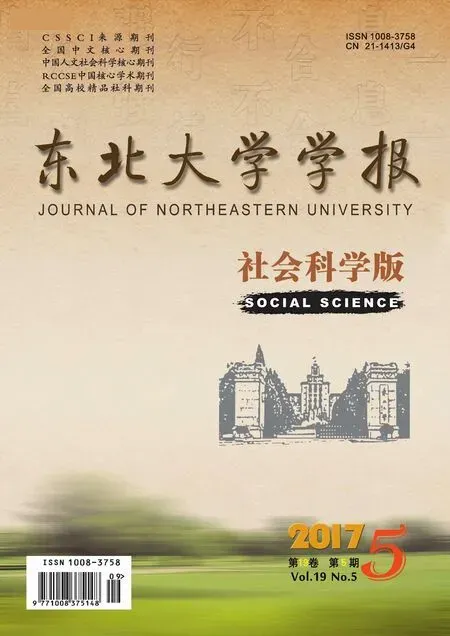后现代生态思想的构建
——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再审视
王 小 会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2)
后现代生态思想的构建
——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再审视
王 小 会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872)
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当代文学批评中又一重要理论贡献,它源于对后工业社会中人类命运与生存状况的省思,深刻批判了积弊良久的现代性思维模式,主张建立生态整体思想和真实的世界观,传承拯救人类的共同体精神。它试图重构一种和谐、民主和生命之间相互关爱的生态社会,恢复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不仅构建了一种崭新的后现代生态思想体系,丰富和推进了后现代文学理论,而且对于生命共同体“共同福祉”蓝图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后现代主义; 文学批评; 生态思想; 生态社会
Abstract: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Originating from the reflection on the state of human existence in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t criticizes the modern thinking pattern resulting in the maladies of age and advocates establishing the ecological holism, the real worldview and the community spirit. It tries to reconstruct an ecological society that is harmonious, democratic and full of mutual love and restores a mutual interconnectedness between humans themselve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world.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not only constructs a new postmodernist ecological thinking system,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 but also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lize the “common well-being” in the life community.
Keywords: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literary criticism; ecological thinking; ecological society
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涌起,继之而来的是各种文艺理论的诞生,20世纪后半叶俨然成为一个文艺理论层出不穷的时代,而每一种理论的诞生都有其繁杂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背景。“如果说生态批评源于人们对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的担忧和焦虑”[1],那么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后现代生态观,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则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层内在联系,并旨在解决后工业社会中的人类生存危机,开辟一条以生态思想救赎人类社会的独特之道。生态环境危机确实是当下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但归根结底,生态环境危机是人类精神世界危机的外在表征,因此,缓解生态危机必须革新陈旧的思维范式和传统的生活方式。毋庸置疑,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社会,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难以摆脱的困境,有目共睹的生态环境恶化,技术成为控制人类意识形态的新形式,物质主义滋生精神文明塌陷,消费主义文化导致人性异化,现代性思维模式引发的生存危机促使人们探索新的生存理念,“寻找另外的生存方式的动力孵育了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产生”[2]。
一、生态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学理基础与现实危机
生态后现代主义(ecological postmodernism)这一术语,最早由美国生态批评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提出,在她的扛鼎之作《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TheResurgenceoftheReal:Body,Nature,andPlaceinaHypermodernWorld)中,她深入分析了现代性危机的深层根源,敦促人们重建真实的世界观,该著作也被誉为理论界“重要的杰作”和“思想的灯塔”。斯普瑞特奈克曾主修英美文学和哲学,她将坚实的理论功底融入对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建构,陆续出版了大量富含哲理的著作,发表了许多洞见深刻的文章、演讲和访谈录,并且为之付诸实践活动。正是基于她的不懈努力,生态后现代主义逐渐融入文学、哲学、社会学和绿色运动等多个领域,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世界范围内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注入勃勃生机。
诚然,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复杂的哲学根源和理论基础。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要哲学基础是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夫·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创立的过程哲学。过程哲学又称关系哲学或者有机哲学,其核心观点是抛弃实体思维,建立以相互联系为特征的关系思维。“所谓实体思维,就是强调世间存在着独立不依的、永恒不变的终极实在。这种‘独立不依的,永恒不变的终极实在就是‘实体’。从实体出发看待事物,也就是把事物看作独立自足,不假外求的。”[3]自苏格拉底以来,“实体”概念一直在西方传统哲学思想中根深蒂固,近代以来深受机械论世界观的影响,它将个人视为孤立于社会和他人的“单子”,从而为偏狭的个人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成为解构“实体”思维的有力思想武器,它强调世界即为过程,过程是指“有机体各个因子之间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活动,因而整个世界就表现为一种活动的过程”[4]136,这种“相互内在”*相互内在(mutual immanence),是过程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揭示的是一种“亦此亦彼”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存在与存在是相互联系,时间与时间、空间与空间、时间与空间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生成了关系思维方式。过程哲学的有机联系观颠覆了现代科学机械论,它主张宇宙间万物绝非孤立地存在,而是一条有机联系的生命链,所有存在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彼此影响,最终汇入宇宙这一系统的整体之中。美国著名过程哲学思想家玛约丽·苏哈克(Marjorie Suchocki)也认为,“相互依赖是生命的内容”,并且“我们并不是偶然地相互依赖,而是必然如此”[5]。现实世界变得日益相互联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此启发了生态后现代主义对真实世界观的认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相互联系世界观提供了哲学依据。
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根植于生态批评的肥沃土壤之中,两者有与生俱来的不解之缘。空前的生态危机使得生态批评如燎原之势在全球理论界高涨,并迅速蔓延至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个领域,其跨学科能力和不凡的生命力可见一斑。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认为,生态批评的第一阶段以“自然书写”为中心,主旨是在文学作品中重新发现、评估自然的价值。在第二阶段,生态批评的重心由平静的田野转向城市景观,环境正义和人类福祉成为核心主题。第三阶段由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乔尼·亚当逊(Joni Adamson)和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创始人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两位学者提出,其主要特征为生态批评的多元化发展,即“在肯定种族和国家特殊性的基础上,超越种族、国家及民族之间的界限,第三阶段从环境视角出发探索人类生活经验的方方面面”[6]。正是在第三阶段,生态批评开始认同后现代话语的现实关怀指向,发生后现代转向。相映成趣的是,后现代世界观也要求我们将对人类福祉的特别关注与对生态的考虑真正地融为一体,因为“真正的后现代是彻底的‘生态的’”[7]。生态批评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开始发生交融,在斯普瑞特奈克的推动下应运而生。
生态后现代主义是对生态批评和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继承与超越。首先,与生态批评反思现代性的立场一致,生态后现代主义明确指出,现代性思维模式的根源为长期禁锢西方哲学界的二元对立思想和近代机械论世界观。二元对立思维是“非此即彼”的排他性思维,它导致文化与自然、物质与精神、情感与理性,以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对立,非但如此,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视自然为一个“物质堆”,否认自然具有主体性和神秘之处,它将身体看做是物质的、机械的,甚至是身心分离的。在二元论和机械论精神枷锁的束缚下,现代性思维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自然被过度开发、技术被滥用、人类生存意义的失落和对地球共同体中其他生命漠然置之。生态后现代主义归纳了现代性思维模式在现代文明中的表现形态,“经济人假设”是最核心的表现,工业主义、客观主义、理性主义、机械论世界观、科学主义、标准化、官僚政治和集中、人类中心论、与自然对立和轻视乡下人、分隔化、逃离宗教和宇宙论背景的缩小,以及极度男性价值观,这些都是现代性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这一系列危机使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反思现代性弊端,那么地球上的生命都难以逃脱消亡的命运。其次,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致力于消解单一的现代性,以“非中心”解构了长期以来统治西方哲学界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打破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范式,使一切权威和等级思想都黯然失色,但其过分强调差异,认为世界由碎片组成,根本不存在真实,这无疑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也“未提出建设性主张”[4]139。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囿于语言和文本的虚构世界,将话语视为权力游戏,未对社会实践发生任何真正的行动,也未能跳出现代性思维模式的囹圄。生态后现代主义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坚持的世界观迥然相异,它是一种崭新的、积极的后现代生态思想,追求一种重“生存”而非“占有”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要发出真实的声音颠覆现代性思维模式,完善后现代生态思想体系。
二、 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内涵
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建构和谐生态环境为本,坚持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主张重建人类自身、自然和地方,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理想,有力地回应了生态文学创作主题。自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SlientSpring)的出版至今,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一直是文学作品探索的议题。斯普瑞特奈克认为,文学作品中描写的生态环境恶化皆归因于人类身心分裂,人与自然、地方关系的破裂,因为,当人类痴迷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忽视自然和地方的存在,生态环境的恶化必然成为生死攸关之大事。斯普瑞特奈克首先以相互联系的关系思维拓展了生命与物质之间的动态关系。她认为:“在地球共同体上,每一个宇宙生命的形式都是以它自己的方式来到世上,然而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孤立地到来的。无论有生命,没有生命的,都是我们的亲戚,都在我们周围存在。”[8]233她的生态整体观超越生命与非生命界限,谋求建立人与自然、与非自然、与宇宙之间的亲戚关系,坚信“宇宙/地球/大陆/民族/生物圈/社区/邻里/家庭/个人,这些都是自我的扩展了的界限。我们的场、我们的根基、我们的存在就是宇宙”[8]85。其次,她以“生态自我观”颠覆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自我的成长目标是对地球的道德责任感,就像我们对他人的道德责任感一样”[9],生态后现代主义将“自我”概念延伸到环境和地球层面旨在表明,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主人,而是宇宙的一部分。人类应该对自己传统的思维定式进行反省,担负起地球守护神的职责,彰显人类对地球的责任感。它呼吁应该从身体、自然和地方出发,与现代性意识形态做斗争。这里的“身体”是指统一的身心,具有认知能力、能够与周围的整体环境相协调,并且为生存做积极的抗争;“自然”是孕育、滋养生命,陪伴人类成长的自然,是具有主体性的“返魅”的自然,应该将人类社会放到更大的自然背景中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地方”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实现情感依附的物理背景,因为“人是嵌入在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的存在物,人与‘地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作为相关的生态和社会文化背景对人产生着微妙的影响”[8]5。生态后现代主义呼吁人类回归真实的自我,建构一种人与自然、地方相融的和谐生态环境。这一理论将生态批评中单纯的对环境的关注扩展至人类自身和地方,是对生态文学批评的重要补充。
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第二个维度指向技术,它积极引导技术的道德化、生态化和人性化发展。在当今的文学批评理论中,将技术发展纳入批评视野中的理论并不多见。面对技术风险日益增多的现实背景,将技术应用的责任规范融入文学批评范式已迫在眉睫。斯普瑞特奈克批判了对技术的一味膜拜导致的人性异化,在她看来,技术的应用永远不是价值中立的,“每种新技术的目的和设计都反映了我们的文化,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技术发明把现代价值观带入了极度现代的形式中”[8]147。现代文明中人类对技术的盲目乐观助长了三个误区:技术的复杂即是“幸福生活”;技术革新即是“社会进步”;技术应用等同于“发展完善”。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技术革新的伦理立场的模糊性”[10]。在《绿色政治》(GreenPolitics)一书中,斯普瑞特奈克严厉谴责了技术与军国主义的联姻,“五万枚核弹头散布在苍穹,隐藏在海底核弹发射井,令人不寒而栗。核武器在不断地被电脑自动控制系统‘改进’,导致在任何时刻都可能源于机制错误而出现意外。每一项技术的突破与升级都使对方更不安全、更加戒备与担心,造成局势愈发紧张。因此,如若我们对核武器情况进行严肃审视,人类借日子活命的说法并不夸张”[11]57。核武器的存在非但没有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反而强烈加剧了我们的内心恐慌,何况武装冲突在局部地区频频发生。由此可见,技术的应用缺失了伦理约束和道德规范,必然走向异化,演绎为人类永难填满的欲壑的附庸、笼罩时代进程的阴霾。在现代医学技术问题上,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人过度依赖医学技术的态度是极不理性的,它鼓励“生态医学”思想,与中医疗法极其相似,全面综合地治疗疾病,唤起身体内部系统的修复能力,避免滥用医学药物、医学手术。此外,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媒介技术不仅带着有色眼镜炮制新闻,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而且遮蔽了其他观点,“将人们的价值观‘均一化’”[12]。久而久之,媒介技术转移了人们对真实生活的关注,压制了人们真实情感的流露。生态后现代主义从核技术、医学和媒介技术三方面阐释了当代文学中的技术异化的深层原因,同时也提出了理想的技术发展愿景,即罢黜技术的统治地位,引导技术沿着富含人文情怀、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
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和谐社会维度涵盖政治、经济和生活层面,它将批评视野拓展至文学作品中的社会正义、和谐和生态经济主题。斯普瑞特奈克积极推进生态政府的建设,她批判基于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为标准的衡量政府执政能力的误区,认为生态政府应该以生态普遍联系性为指导思想,全面拒绝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战略。生态政府的完善还有赖于草根民主建设,因为草根阶层比政府更关注切身利益和环境变化,他们自发地形成绿色社团,自觉地对他人、社会和环境形成一种责任感。因此,“草根组织、草根民主和草根运动促进政府很好地为生态经济、生态社区服务的作用”[13],他们的存在对政府管理能力形成一种鞭策。生态政府还应该承担对社会和对人民的责任,关照各个阶层的利益。她的绿色经济思想旨在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抵制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缓解生态环境危机的紧迫压力。当今经济学家仅以高效、生产率和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这是以牺牲人类幸福和生态环境成本为代价的。社区型经济属非营利性质,有利于减少经济全球化对地方经济的掠夺与伤害,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也维系了社区关系纽带,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指数。在社会生活层面,生态后现代主义批判单面男性价值观,支持女权主义运动,反对父权制对女性发展的羁绊及各种形式的暴力。生态后现代主义建构和谐社会原则是对绿色政治运动核心价值观的借鉴,这十大价值观是:“生态智慧、草根民主、个人与社会的责任、非暴力、非中心、以社团为基础的经济学、后父权制价值观、尊重差异、全球责任和未来发展”[14]。
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维度是它的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它提倡弘扬传统文化来实现对人类的精神救赎,敦促人们追寻后现代时期的生存意义。这种对生存意义的追寻正是当代文学作品中关注的重点,在消费主义刺激下,文化消费趋向商品化和娱乐化,将文化本身的道德教诲、艺术审美功能抹去,这无疑阻断了人们对真实文化精神的追寻,正如斯普瑞特奈克所言,“每个人都以一种孤独的个体身份消融在大众文化之中,并接受着大众传媒的哺养,他们的生活成了实现‘进步’和满足国家对经济无尽头的、绝对的增长要求的工具”[15]。因此,在文化层面上,它高度肯定传统文化对抵制消费文化侵蚀的积极作用。经典传统文化不同于大众文化,它不仅是一种精神积淀,更具一种救赎力量。当前全球化环境下回归传统经典文化,除却陶冶心灵的意义,更主要是培养人们的历史纵深感和思辨意识,引导人们走出文化迷途。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也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在很大程度上与老子关注自然的精妙过程,与孔子强调培养道德领袖及人类对更大的生命共同体的责任感有共同之处”[8]5。生态后现代主义将真实世界观视为后现代时期的生存意义。它坚信“正像由多种多样的有机物和无生命物质之间的互动组成的整体性生态系统,这种整体性特征也存在于社会系统——如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共同体”[11]31。有鉴于此,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唯一真正的安康是由繁荣富足和个人的健康关系组成的:有与家族的关系、也有与各种社会共同体的关系、还有与生物区和生物圈的关系”[16]。实践生活也一再证明,关爱他人的人会延年益寿,呵护周围环境会降低人的患病几率。因此,人们只有恢复生存意义,回归共同体的怀抱,才能涤荡心灵、提升理念,获得真正的幸福。生态后现代主义以生态原则为基石的思想并未局限于生态系统,也拓展至人类社会内部,因为人是一种深刻的关系性存在,必须处理好人与周围世界的真实联系,以一种关系思维来维护自我与他人、社会、环境,以及与各种共同体的关系,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维度蕴含的是人类既完善自身,又为整个地球共同体负责的积极使命感,与文学作品的终极精神归旨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
生态后现代主义从生态、技术、社会和精神维度四个层面,建构了一个理想的生态社会模式,是生态批评视野由自然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问题的延伸,体现出生态批评向生命共同体的“共同福祉”目标进军的重要转折,在此意义上,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生态批评理论的发展。生态后现代主义构建的可持续发展的后现代生态文明思想体系,彰显出生态后现代主义强大的理论张力与现实关怀,标志着人类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不仅如此,“由于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物质自身具有内在经验性、施实创造力和活力”[17],以及它对整体自然的独到见解,颠覆了现代科学中的机械物质观,为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它与新物质主义一起“作为主要力量推动了物质生态批评新领域的开拓”[18]。
生态后现代主义强大的跨学科理论体系和现实价值促进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由于它在文学文本与后现代社会文化之间建立了一座理论桥梁,它与文学的深度的精神默契为解读当代文学作品提供了与时俱进的视角,许多当代英美知名作家谱写了如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般的时代强音。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在作品中反复强调她的世界观,“人类应该懂得自身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有植物、动物、鸟类、昆虫、爬虫类一起构成了宇宙和谐的和弦”[19],这无疑是在说明,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美国后现代人道主义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多部作品中都蕴含强烈的生态后现代主义精神,他一直试图重构一种生态社会意识形态、一个亲戚社会来救赎人类。在他的小说《滑稽戏》(Slapstick)中,他明确提出了建构一个人类大家庭的理想。蜚声文坛的美国作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在他的获奖作品《回声制造者》(TheEchoMaker)中,呼吁重建身体、自然和地方之真实,藉此构建和谐的、物种间平等的生态社会。英国文坛巨擘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都市小说中,对“后自然”世界的批判,对人与自然、地方和谐相融关系的追寻,对媒介现实的批判,对真实的世界观的呼吁,正是他的生态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积极体现。他们在文学空间构建了一个乌托邦的理想生态社会,倡导以生态后现代主义精神来消除现代性危机,无疑与生态后现代主义形成一种深度的契合。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生态后现代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贡献还有待继续深入地探讨。
在现实意义上,生态后现代主义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种种生存困境的剖析、对后现代生态思想的诉求和对生态社会的希冀,道出了真正眷注人类未来和民族命运的睿智之士的心语。在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的时代背景下,人类浸淫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中,沦为“消费机器”和金钱的奴隶,造成身心发展的严重断裂,从而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向度,对生存危机置若罔闻。生态后现代主义明确了人类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时代责任,呼吁人们对陈旧的生活理念改弦易辙,回归和谐的身心,从而肩负起对整个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责任。它勾勒的人与自然、地方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对宇宙的创造力和活力再现的肯定,独辟蹊径地拓展了人类的世界观,为人类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生态后现代主义将生态和谐意识渗透在教育理念中,提升了人类精神层次上的追求,开创了一种人类与地球共同体联系的新方式。在高科技的后现代社会,它提出的富含人文主义情怀的科技伦理观,有助于科技朝着利益之善、事实之真的造福人类方向发展。它构建的生态社会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模式,不仅是超越现代性等级制度、真正维护群众利益的理想社会,而且是全面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焕然一新的工程。当然,蓝图的规划不等于理想的实现,但蓝图的规划必定有助于托起人类的希望、翻开地球美丽生态的新篇章。
四、 结 语
生态后现代主义是对深受时代诟病的现代性思维模式的全方位审视与拷问,它构建了一种新型、和谐的后现代生态思想体系,也促进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新发展。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阵营中的一支生力军,它超越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弊端,以真实的联系性世界观来建构和谐社会。与此同时,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开放性实践还强调超越差异,超越民族和国家范畴,呼吁在未来的生态社会建构中进行全球范围的对话与合作,共建全球美好的生态、精神家园。生态后现代主义理论高举有机主义整体生态观,坚持真实的后现代精神,努力将人类从危机四伏的现代性困境带入全面和谐的理想佳境。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和谐发展的内在理论体系和外在推动力。
[ 1 ] 刘岩. 生态女性主义的学理基础和批评范式反思[J]. 国外文学, 2016(1):10-18.
[ 2 ] Spretnak C. States of Grace: The Recovery of Meaning in the Postmodern Age[M]. San Franciso: Harper Collins, 1991:12.
[ 3 ] 王治河. 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20.
[ 4 ] 乐黛云. 生态文明与后现代主义[J]. 中国比较文学, 2010(4):136-140.
[ 5 ] Suchocki M.The Fall to Violence: Original Sin in Relational Theology[M].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99:69.
[ 6 ] Adamson J, Slovic S. The Shoulders We Stand on: An Introduction to Ethnicity and Ecocriticism[J].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S., 2009,34(2):5-24.
[ 7 ] 大卫·格里芬. 后现代精神[M]. 王成兵,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23.
[ 8 ] 查伦·斯普瑞特奈克. 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M]. 张妮妮,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9 ] Roszak T. The Voice of the Earth[M].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321.
[10] 默里·布克金. 自由生态学:等级制度的出现与消解[M]. 郇庆治,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8:252.
[11] Capra F, Spretnak C. Green Politics[M]. New York: E.P.Dutton, Inc., 1984.
[12] 王治河. 斯普瑞特奈克和她的生态后现代主义[J]. 国外社会科学,1997(6):49-55.
[13] 陈世丹. 后现代人道主义小说家冯内古特[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294.
[14] Spretnak C.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of Green Politics[M]. Santa Fe: Bear & Company, Inc., 1986:77-82.
[15] Spretnak C. Postmodern Directions[M]∥ Griffin D R.Spirituality and Society: Postmodern Vision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33.
[16] 查伦·斯普瑞特奈克. 生态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J]. 张妮妮,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2):63.
[17] Oppermann S. From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to Material Ecocriticism[M]∥Iovino S, Oppermann S. Material Ecocritic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21.
[18] 唐建南. 物质生态批评——生态批评的物质转向[J]. 当代外国文学, 2016,37(2):114-121.
[19] Doris L. 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M]. New York:Bantam Books Inc.,1972:120.
(责任编辑: 李新根)
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Ecological Thought—— Re-examination of Ecological Postmodernism
WANGXiao-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I 06
A
1008-3758(2017)05-0545-06
10.15936/j.cnki.1008-3758.2017.05.016
2017-01-15
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资助项目(16XNLG01);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HB15WX031)。
王小会(1979- ),女,河北邯郸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河北师范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英美后现代主义文学及西方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