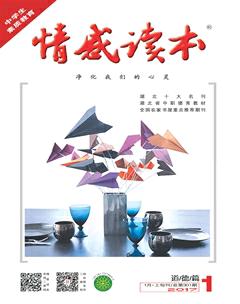因为我是姐姐
连翘
原来这些年过去,我们之间依然有些微妙而神秘的心灵感应,我疼,她也会疼。
一
妈妈说,怀孕时我们成天在她肚子里打闹,她原以为是两个坏小子,所幸老天怜悯她,赐予她一个女孩。那时我不懂,为什么生了个女孩就是老天怜悯,妈妈笑笑:“你看你总是那么调皮,姐姐却很乖巧很懂事,你说是不是老天怜悯我?”
姐姐刚满月,就被送到了乡下奶奶家。理由现实而残酷:爸爸和妈妈两地分居,妈妈一个人无法同时带两个孩子。
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有过年过节才可以看到姐姐。奇怪的是,虽然相隔那么远,我们竟会心意相通,我有个头疼脑热,姐姐那边也不会太舒服;而姐姐如果生病了,我也会又哭又闹。家人都觉得很神奇,我和姐姐却因为年纪小对此未知未觉。一直到上学前班姐姐才被接回来,她个子比我要矮,一点也不像六岁孩子的身高,又黑又瘦,从外貌上很难分辨出我们是双胞胎。
我和姐姐住了同一个卧室,为了谁睡上铺谁睡下铺,我们竟然打了起来。最后妈妈一句“姐姐要让着弟弟”,决定了她睡上铺的命运。可即使被她让着,我也抗拒叫她姐姐,理由很多,我们才差了一个小时,我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小时叫她姐姐呢?更何况我个子比她高,个儿高的怎么能叫个儿矮的姐姐呢?
那时她会隔着床板对我进行“思想教育”:“早一分钟你也得叫姐姐。”可她得到的通常是一声“嘁”。教育无果,她就进行利诱:“叫我姐姐,我就给你讲故事。”
六七岁是最爱听故事的年纪,这个诱惑真的很大,于是我叫了一声姐姐。
二
六七岁的她,已经懂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她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叠好自己的被子,然后帮我叠被子,之后她会扫地、摆好碗筷。
我心安理得地看着姐姐做这一切,从来不觉得自己应当帮把手。妈妈经常夸她勤快懂事,那些赞美让她很受用,于是更卖力更有眼力见儿地帮妈妈分担家务。见她被夸奖,我却不那么心安理得了,我嫉妒她总被夸乖孩子,于是坏坏地压在被子上让她叠不成,或者藏起扫把让她无法扫地。妈妈向来只看结果不追究原因,便婉转地批评她:“翘翘,今天的地有点脏哟!翘翘,你们的房间不是很整洁哟!”
姐姐便十分委屈地申辩:“是弟弟……”“你是姐姐,要哄着弟弟,不要凡事都拿弟弟做借口。”姐姐便不再说什么,她受了委屈通常会选择沉默。
邻居朋友来串门,看到姐姐总要猛夸,啧啧,真是个懂事的孩子。也有替姐姐鸣不平的:“你使唤这闺女使唤得也太狠了,锦葵什么也不做吧?”
“她是老大嘛,老大当然应该多做一些。”妈妈说。
彼时姐姐在厨房择韭菜,我则坐在客厅吃西瓜,这一切,我听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
三
小学五年级时,班里很多同学参加了兴趣班,我想参加篮球班,就吵着让妈妈同意我报篮球班。
“成!成!给你报。”妈妈捏捏我的脸蛋。
一会儿,姐姐放学回来了,她问妈妈可不可以参加兴趣班。
“什么兴趣班?”妈妈可能没想到姐姐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老师说我作文不错,让我报写作班。”姐姐的声音充满了渴求。“要活动多久?”“每周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不就是写作文吗?在家写成不成?你爸不在家,你知道妈妈工作忙,有时还要值夜班,你要是一周参加两次兴趣班,你弟弟肯定会饿肚子的。”
姐姐紧紧咬着下唇,想说什么,最终只是默默地走进卧室。
更糟糕的是,不懂事的我偏偏要刺激她,我得意地炫耀:“妈妈同意让我报篮球班了。”本来低头写作业的姐姐抬起头,想了一会儿,像是下定决心似的走进客厅,说:“为什么弟弟可以,我不可以?”“因为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当我和姐姐发生矛盾,妈妈无法或者没有耐心调停时,就拿这句话做结束语。
那个晚上,姐姐一直在小声呜咽。我说:“翘翘,你别哭了。”她不理我,继续哭。我又说:“如果爸爸能调回来,你就可以上兴趣班了。”最后没辙了,我说:“要不,你教我做饭吧,这样你就可以去上兴趣班了,我在家给咱做饭。”
“妈妈说得对,我是姐姐,应当让着你。”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句话其实是她心理平衡的法宝,她唯有让自己更加坚信,才会少一些失落,少一些难过。
四
中考那年,因为过多地操心家里的事,姐姐只考上了技校,我则考上了重点高中。
学校很烂,离家又远,妈妈希望姐姐可以离家近一点儿。我清楚地记得,当妈妈提出掏些钱让姐姐上一所好一点儿的中学时,她很生硬地说:“离家近是为了让我继续给你们做牛做马吗?”
“怎么和妈妈说话呢?”爸爸大声地呵斥她。妈妈却没反驳,只是呆怔了半晌。那时爸爸调回了本市,可能出于惯性,姐姐依然分担了很多家务。
“你就按妈妈的意思,读离家近一点儿的中学吧,你考的那个学校风气不好。”爸爸说完,就和妈妈一起出去散步了,只剩下我和姐姐在家。
“如果我是妹妹,很多事情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姐姐说这话时,两眼含着泪水。
姐姐最终违背了妈妈的意愿读了技校。后来她就变得像个叛逆少女,涂很重的眼影,穿爸爸妈妈看不惯的衣服,甚至偷偷吸烟。最让妈妈烦心的是,姐姐谈恋爱了,而她的男友,是所谓的待业青年。
五
就在这时,家里一个惊天阴谋被姐姐发现了。
那时我读高三了,犹记得我正在解一道数学题,姐姐来到了学校,她递给我两张发黄的纸,我好奇地打开,发现是两张出生证明。
一张是我的,一张是她的。她的出生证明写的出生时间是14点05分,而我的出生证明,写的是13点01分。她说:“你以前知道这事吗?”
我摇头。然后她的眼睛就红了,可是她没哭,她说:“如果医院没弄错,就是他们骗了我,我不是姐姐,我是妹妹才对。他们骗了我18年,我受那么多委屈,原来都不应当是我受的。”
我傻了,姐姐很激动,她那天说了很多话,而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她恨我们,是我们——爸爸,妈妈,还有我,甚至奶奶。
然后她说她要走了,我紧紧拉住她的手,问她去哪儿,她说不知道,也许回学校。我不敢放手,我总觉得我这一放手,就会永远把她弄丢。她试图挣脱我的手,无果,然后噼里啪啦打我,我不躲。
我只有抱着她,抱着为这个家牺牲了18年的翘翘。
一直到晚上我才弄清真相,翘翘的确是我妹妹,当年奶奶出于重男轻女的思想,认为女孩儿懂事,让翘翘做姐姐可以多帮帮妈妈,在她看来,只差一个小时的时间,谁做老大谁做老二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可实际上,他们区别对待了。
妈妈去学校找过姐姐好几次,姐姐却不肯原谅她,甚至干脆不回家了。
六
姐姐毕业后做了导游,开始在全国各地东奔西跑。那一年,我考上了大学。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翘翘,妈妈提起她便哭。妈妈开始后悔,可妈妈忏悔的言辞,姐姐无法听到。
我们就这么疏离了四五年,我清楚地记得我阑尾炎发作那天,一阵剧烈的疼痛包裹了我,然后我稀里糊涂被送到医院,醒来的时候,手机里有一条短信:我在长途车上,突然一陣头晕目眩,你好吗?
原来这些年过去,我们之间依然有些微妙而神秘的心灵感应,我疼,她也会疼。
我好开心自己病了,可以作为要挟她来看我的条件。我回复:我在医院,刚做完手术。
她是第二天出现在医院里的,妈妈和爸爸见到她,只是不住地抹眼泪。我说:“姐,其实我们都很想你,别不要我们,别一去不回,没了你,我们该多寂寞。”
现在,我还是叫她姐姐,因为一直以来,姐姐该做的和不该做的,她都做了,她配得上这个称呼。
固然摘自《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