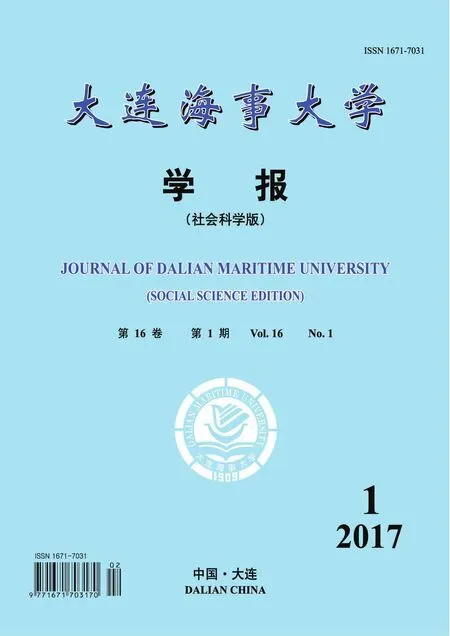英国海事案件管辖权冲突之历史考察
——以18世纪英国走私案件管辖的两院冲突为焦点
熊 孜
英国海事案件管辖权冲突之历史考察
——以18世纪英国走私案件管辖的两院冲突为焦点
熊 孜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1)
英国海事法院自创建之始便面临着来自普通法法院对其海事案件管辖权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包括法律理论的争执,也包括司法实践中的相互争夺。该冲突存在的历史源流以及在法律理论冲突的背后所隐藏的动因是海洋法领域研究中鲜有人关注却难以回避的问题。发生在18世纪英国关于走私案件在北美殖民地的两院之争是该争端的最典型范本,法官、律师团体与法学家们通过法律语言论证本院管辖权的正当性,但在此冲突背后的政治与经济因素才是更为重要的考量。
英国;海事法院;海事案件管辖权;走私案件
1784年7月的一个夏日午后,有一位名叫乔治·库姆斯(George Coombes)的英国走私贩子正与自己的同伴们一起,试图用两艘四角小帆船将自己的走私货物偷运到位于南安普敦郡的克里斯彻奇港去。哪知时运不济,他们在沿岸寻找靠港机会的过程中引起了皇家缉私船“厄瑞忒弥斯”号的注意,为此库姆斯等人只有拼命向岸边驶去,以期能够逃避惩罚。“厄瑞忒弥斯”号上的税务官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见状则立刻指挥舰船全速追击。乔治·库姆斯在自己的小船触到沙滩的一刻立刻与几名同伴一块弃船逃命,与此同时,为了阻挠身后距沙滩仅有一百码之远的“厄瑞忒弥斯”号顺利靠岸追击,他掏出身上已上膛的手枪,朝“厄瑞忒弥斯”号胡乱开了几枪。而其中一枪,不偏不倚正好命中船上的威廉·艾伦,后者最终不治身亡。
案发后,乔治·库姆斯被送往海事法庭接受审判。尽管乔治·库姆斯一直辩称自己没有开枪而是同伴开的枪,但在没有陪审团参加庭审的情况下,他仍然被海事法院认为有罪。两年后,在伦敦老贝利街的高等海事法院上,法官詹姆斯·马略特爵士(Sir James Marriot)在此案经历两次上诉之后最终一锤定音,宣判乔治·库姆斯有罪,并随后执行了他的绞刑。*R. v. Coombes (1785) 1 Leach 388. See The English Reports, Vol. CLXIII, Crown Cases I, NEIL AND CO., 1925, pp. 296-297.尽管此案判决已尘埃落定,但关于此案的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走私贩子在岸上开枪杀死了尚身在海上的一名税务官员,这一看似简单的案情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复杂的法律技术争议。海事法院对此案的管辖是否正确?为何采用犯罪行为实行地而不采犯罪结果发生地管辖,从而转至南安普顿郡普通法法院进行审判?该案中的走私犯罪情节是否可被援引为是海事法院管辖的一个理由?关于此案,如是问题还有很多,[1]170-171它就像一根导火索,再次引燃了关于海事法院与普通法法院管辖权争议的火药桶,但它绝非绝无仅有。在18世纪,大英帝国货船在世界范围内乘风破浪的背景下,诸如此类的争议,特别是对走私犯罪的管辖争议不绝于耳,而其中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发生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两院之争,而它也正是本文试图去聚焦的范本。对于这一范本的关注,并非仅存在于法院与律师会馆内的争吵,而将更加关注法律争议之下的利益驱动。
一、海事法院与普通法法院管辖权争端之缘起
海事法院与普通法法院管辖之争来源已久,这一争端在海事法院创设之时就已见端倪。早在12世纪的英国,“五港同盟”(Cinque Ports)在组建之时得到了某些皇家特权,其中包括组建船队为皇家海军服务,而这便是海事法院的前身。海军上将(即admiral,海事法院为courts of admiralty)一职直到1295年才首次出现,而该职位最初并没有将听讼等司法权能纳入囊中。最初的海事案件,尤其是涉及海盗的犯罪案件的审判,是由普通法法官完成的。直到1340年,海军开始拥有自己的法院,这得益于爱德华三世意欲扩大海军权力的举动。值得注意的是,海事法院最初的设立便与王国岁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走私犯罪尚未像后世一样普遍的中世纪,海军乃至之后的海事法院的重要职责除了打击海盗,还在于实施禁运,对海洋中沉船残骸的打捞以及对皇室渔业进行管理,这都与王室岁入有极大的关联。*这部分王室岁入并非来自于议会的批准,这就是后世布莱克斯通所谓的国王的普通收入,相对于源于税收的特别收入。参见文献[2]。而在15世纪,海事法院的官员开始对海事案件相关的法律进行汇编,于是便有了《海事黑皮书》(TheBlackBookoftheAdmiralty)的出现。此法律汇编事无巨细地囊括了当时海事法院审判实践中的规则,其内容很明显地体现出欧陆民法实践的影响,其来源是西北欧地区早于12世纪就已经开始通行的海商规则“奥利伦法”(Laws of Oleron)。海事法院的建立与发展是一种海军为自己的权力寻找一种组织机构形式的过程,[1]30而这一过程,也同时伴随着普通法法院的压力。
对海事法院权力的质疑,首见1371年。时年议会收到了一份关于海军腐败以及海员与商人不满的请愿报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海事法院没有陪审团参与庭审。据《海事黑皮书》记载,1375年曾有所谓的“昆伯勒调查”(the inquisition of Queenborough),试图对海事法院管辖的事务进行确定。而在1389年与1391年,理查二世为了回应对海事法院的不满,对海事法院权限做了两次严格的立法限制。其中重要的内容在于确定海事法院无管辖王国内部案件(包括河流)的权力,将其权力牢牢绑在了公海上,并且,在陆地上签订的契约、产生的纠纷与诉讼请求(毫无疑问,这是绝大部分海事案件的案源),海事法院也无权力审理。这种限制使得海事法院在整个15世纪里显得微不足道,它甚至失去了完成自己主要目标的能力。这种情形直到亨利八世时期才有所改变,因为在这名对海上贸易与探索有着强烈兴趣的君主看来,海事法院是一个绝好的工具。它不仅是一个司法机构而已,更是一面以海事法律为装饰,以妥善解决与外国王公之间存在的海上纠纷的盾牌,可以很好地将自己的政治意图隐藏其后。也正是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确定海事法院刑事管辖权的法令得以发布。*28 Hen. 8, C. 15.
在都铎王朝统治的16世纪英格兰,海事法院权力在王朝的鼓励态度下发展至极盛。其权限明确为三个领域:民事或称普通海事审判、刑事审判以及捕获案件审判。由于16世纪英国海洋力量的全球拓展以及大规模殖民活动的开始,海事案件的数量陡增。随之而来的则是专门的律师团体,他们的诞生是为了适应海事案件的需要,其所学都是罗马法而非英国普通法。罗马法律师团体垄断了海事案件的辩护,由此也引来了普通法律师们的敌意。在整个17世纪,两者之间的冲突不断。为此,普通法律师们做了很多限制前者权力的尝试,比如向大法官法院申请中止令状(supersedeas)与调案令状(certiorari)以阻挠海事法院审判等,但却收效甚微。海事法院不采用陪审团审判是普通法律师们诟病的焦点,但在1535年与1536年的两条法令中,这种情形仍在继续。*27 Hen. 8, C. 4; 28 Hen. 8, C. 15.在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伊丽莎白一世那里,由于其放任自由的航海政策,海事法院的权力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在这名击败过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女王看来,海事法院通过捕获案件所得的收入是滋润海军以及王室岁入的重要渠道,故普通法律师们限制其权力的抗争想要取得成果确实不易。
在革命爆发的17世纪,由于王权的衰弱与司法实务的新变化,两者间斗争的格局又有了新的变化。在著名法学家爱德华·柯克等多位在大法官法院任职的法官们的努力之下,于1633年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两派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协定。根据此协定,海事法院的管辖权被紧紧地约束在三类案件中:一是涉案契约或其他相关法律行为是在海上或海外达成的案件;二是在海上航行时发生的船员薪资以及租船契约纠纷;三是与建造、修理、装配以及救助船只相关的对物诉讼。作为大幅削弱海事法庭权力的妥协,普通法法官同意不得用人身保护令状(writs of habeas corpus)释放海事法院根据协议逮捕的嫌疑人。这一协议订立之后,两者的争端很大程度上得到缓和,但都铎王朝时期海事法院之强力权柄也一去不复返了,之后查理二世与詹姆斯二世执政时期,试图复兴海事法院的努力再也未取得成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罗马法学家们发现他们依靠的王权已经不再强力,而议会则远在他们的把握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海事法院的管辖权即便被大大缩小,但其重要性在实践中从未被忽略。举例而言,在王权土崩瓦解、极端清教主义盛行的大空位时期,海事法院并未被忽视。相反,其职能得到克伦威尔很好的照顾。毕竟,随着英国海上贸易以及殖民地事务的大幅增长,海事法院在处理这些事务上的便利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它与普通法职业者的争端,在大英第一帝国在18世纪的海外扩张活动中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下文关注的焦点。*上述海事法庭发展史参见文献[3]和文献[4]。
二、18世纪英帝国的走私案件管辖权问题
(一)走私活动之猖獗与司法惩处之无力
18世纪是海事法院管辖权争议最为激烈的一段时期,而关于殖民地走私犯罪的讨论则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这一焦点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出了狭窄的学理讨论,进而延伸到国家财政乃至宪政原则层面。之所以有如此巨大影响,首先是与当时走私活动的空前猖獗分不开的。这种猖獗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走私活动影响之大。尽管走私贸易仅占整个贸易份额的很小一部分,*该观点参见劳伦斯·哈伯关于英帝国走私贸易的著名研究,参见文献[5]第263页。但其对国家税收与走私目标地的经济活动仍有很大的影响。走私活动在某些地域足以冲破航海法体系所设置的帝国贸易垄断,甚至于给议会带来调税压力,影响不容小觑。*比如对华茶叶贸易的垄断就因为大量的走私活动而被打破,这也是汤申德意图对美推行茶税的动机之一。参见文献[6]。其次是走私犯罪规模与手段的升级。走私犯罪在18世纪初已具备集团化、武装化的特征,并且辅以陆地武装帮派为接应。在1723—1733年间,有256名海关官员因缉私而殉职,[7]10走私犯罪打击的困难可见一斑,这也使得海关税务官常常要借助海军的力量。[7]13-17即便如此,呼吁以更严厉的手段来打击走私活动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因为在某些地方由于缉私力量的缺乏,甚至出现了官员故意放纵犯罪的情形。[7]36-37最后则是面对增长迅速的走私犯罪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国家立法。18世纪的大量关于走私的立法可以很好地说明当时的现状。其中较为重要的有1709年“海岸检查法”(hovering acts),为对在海岸卸货的走私行为进行打击提供了依据。*8 Anne, c. 7.1736年法案,为对在港口界线内以及海岸两里格远的走私船只货物进行检查及罚没开创了先河,而这之后,法院的判决更将这一范围扩大到四里格。*9 Geo. II, c. 35.1763—1765年间发布的三条议会法案,则有了对滞留殖民地海岸船只进行捕获的条款。*3 Geo. III, c. 22. & 4 Geo. III, c. 15. & 5. Geo. III, c. 63.除诸多立法之外,还有很多法院判决与海关署的命令,但尽管这是一个不断在修修补补的过程,在实践中却仍然难以应对需要。
在走私泛滥的当时,司法体系又能否满足打击走私的需要呢?在漫长的18世纪上半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受限制的海事法院管辖权。18世纪60年代,威廉布莱克斯通在《普通法释义》论述侵犯私人的危害行为这一章中将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如果契约或者行为的原因,一部分发生在海上而一部分发生在陆地上,那么普通法便得排除海事法院的管辖权。因为在两者都有权管辖的情况下,一般或者普遍的法律便要取代特殊的法律。”[8]106他还提到,普通法法院对海事法院所管辖的绝大多数案件有一种并存的(concurrent)审判权,海事法院所能管辖的案件并不能排除普通法法院的管辖权。[8]107这种表述不是纯粹的理论说教,在18世纪上半叶,海事法院的权限确实遭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限制。上文已经叙述过,海事法院职能范围内有三个重要领域。其中民事诉讼案件范围极大地缩小了,明确归于海事法院的只有涉及船员薪资的案件,其他能被海事法院管辖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普通法律师的观点,都是普通法法院吃剩下的残羹冷炙。[3]30捕获案件虽然不可能由普通法法院管辖,可捕获案件上诉法官群体中,却有很多普通法法官当值,这对捕获法律本身,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3]27-28而本文所关注的海事刑事审判,由于受到普通法法院的限制,仅限于公海上的重罪案件(根据上文所述的亨利八世时期发布的法案之规定),在1763年改革之前,这类案件的数量则极其有限。[3]29
将走私案件交由普通法法院审判,为何就起不到很好的打击犯罪效果呢?这需要综合走私案件的性质与两种不同法院的审判形式来进行分析。首先,在采用证据的形式与标准上海事法院显然要宽松得多。与普通法法院不同,海事法院在实践中广泛采用宣誓证词,书写的问答笔录不但可被认定有效,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相对于普通法法院庭审时对证人的口头询问,这种形式显然更契合海事案件中从事海洋贸易相关行业的证人们居无定所、随传随到确有困难的特点。[5]184-185其次,上文已经提到,海军在缉私活动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对海事案件的发现以及之后的抓捕、传唤、扣押等一系列法律行为的完成,都与海军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故海事法院实践上通常是首先受理的法院,审理上具有很大的便利性。再次,海事法院与普通法法院的审判形式不同,最重要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是否采用陪审团审判这一问题上,陪审团参与审判使得整个案件审理过程变得更加耗时。而且,尤其是在英帝国殖民地地区,陪审团由于涉及自身利益的缘故常常放纵案犯,成为人们广为诟病的弊端。[5]194最后,由于海洋贸易本身的特点,很多时候走私案件审理的速度要比精确性更重要。举例而言,迟而未决的商品会腐烂掉,这对诉讼的任何一方来说都绝不是什么好事情。[5]200
(二)七年战争带来的改革变局
从1756年打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改变了上述海事法院对走私案件管辖无力的情形。究其原因,则需要从这场战争本身说起。七年战争虽是欧陆群雄争霸之战,但主战场却在远离欧陆的北美、加勒比海与印度等地,其中北美大陆是英、法两国交锋的主战场。在这场战争之前,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管束是相对松散的,在这段埃德蒙·伯克口中的“有益的忽略”时期里,*“有益的忽略”作为埃德蒙·伯克极负盛名的论断之一,首次出现是在著名的《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一文,参见文献[9]。北美大陆的海事案件审判也呈现出较为混乱的图景。早期的北美殖民地严讼倾向严重,*即便在洛克为卡罗莱纳写的宪法文件中,都能很明显地看到这种倾向,在文中,洛克称“辩护是一种为牟利而存在的下三滥事务”,参见文献[10]。这种倾向直至18世纪中叶仍然存在。[5]182直至美国革命时期,法官与律师队伍中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人数都很少。[5]183在这种原本法治就很不发达的情况下,海上走私案件交由普通法法院或财政法院审判远没有交由海事法院管辖来的便利,因为后者对整套海事案件办理程序的熟悉程度远胜于前者。[5]184-185但实践中,海事法院并没有在北美占据对走私案件审判管辖的优势,以北卡罗来纳地区海事法院为例,从1729—1759年这30年间,海事法院仅仅受理了60起案件。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样一个清水衙门的法官职位甚至不值得去争取。[11]521事实上,北美各殖民地司法状况极其不统一,分散、混乱、无统一的上诉机关是海事案件的司法实践状况。普通法法院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海事案件审判权,甚至于出现已经在海事法院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为感到自己将要输掉官司,转而向普通法法院申请诉讼中止令的情况发生。[12]但这种混乱的司法实践,在七年战争之前并没有引起英帝国中心的足够重视,但在战争在北美打响的时候,走私问题就成了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
在北美英属殖民地作战的英军,原本认为自己占据了人和,但事实却让他们大跌眼镜。北美殖民者非但没有显示出多少犒军的热情,反倒开始借此战事大发其财。七年战争期间,大量的北美殖民者因为从事走私、私掠、放贷以及军需供应积累了巨额财富,这些人日后便是反抗英国税改的中坚力量。[13]561这些北美殖民者的行为,尤其是走私行为,引起了英国军方的关注。这是因为北美殖民者与加勒比海的法属西印度群岛通商甚至走私,其危害远不止侵犯国家财政岁入征收而已,还等于给法军从海上活生生地拉出了一条补给线路,这对英军的作战是极其不利的。[14]401761年的一个司法判例已经允许政府通过协助令状来打击美洲殖民地走私者,[15]但效果并不理想。故当消息传到威斯敏斯特时,立刻引起了议会中的轩然大波,在以格伦维尔为代表的英国政客的努力下,议会于1763年决定,由殖民地附属海事法院(vice-admiralty courts)管辖原本由普通法法院管辖的关于商贸与税收的案件,主要是违反航海法的刑事案件。[16]此举的根本依据仍然是亨利八世的那条著名的关于海事法院刑事管辖权的法律,其中提到海事法院对海上发生的叛国、海盗、重罪、抢劫、谋杀以及其他海上犯罪有管辖权。*28 Hen. 8, C. 15.这一法令是老生常谈,但走私这一犯罪行为本是违反航海法的行为,原不属上述海上重罪,故想要明确宣称海事法院对走私的管辖权,就只有将它解释为是叛国罪,[16]因为战时通敌的走私行为的存在,这一逻辑并不难理解。
这一变革迅速在殖民地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现依次来看争论两方面的观点。支持海事法院管辖走私案件的人们,主要是英帝国中心的那些希望加强殖民地管控的政客认为,破坏航海法体系的案件原本就应由海事法院管辖,1696年的一个法案要求所有涉及《航海法》的案件均不设陪审团,由海事法院审理。但因为殖民地的分散、混乱司法实践以及广泛的不合作态度,帝国的法令得不到很好的执行,[17]1139所以1763年之改革无异于一次重新宣示,一次对帝国法令执行力的强调。但在反对这一变革的北美殖民者们看来,它毫无疑问是一种僭越。违反航海法的案件由殖民地普通法法院把持了多年,这种突然的改变使得殖民地本土很多走私行为利益相关者受到损害,这些人开始不吝于重燃起冷寂已久的两院之争的战火,并将它与18世纪60年代的税收制度改革一块予以抨击,乃至扩大成了独立的战火。*关于对美国革命前由于糖法、印花税法等法令引发的财税-宪政问题的争议概述,参见文献[18]和文献[13]第631页。在这种冲突之中,两方运用了大量的政治与法律的语言,但在这种语言之后,还隐藏着宏观与微观的利益冲突。通过叙述这一冲突将这种隐藏在这一历史已久的冲突之后的事实揭示出来,则是下文将要完成的工作。
三、对北美殖民地两院之争的分析
(一)法律的语言:普通法与罗马法之争
法律技术的争议,从此争端发源之时就已存在。但对此首次进行详细限定的,当属17世纪著名法学家爱德华·柯克。柯克在此争端中引领着普通法法院阵营,其观点成为普通法律师们关于此问题的经典论述,为后世所不断援引。[3]17他从两个法院的地域管辖界限说起,海事法院管辖权限于契约订立于海上的案件,任何在英格兰各郡内订立契约的案件,包括海湾与河流,皆属郡普通法法院管辖。而在外国订立契约的案件,也不能归属海事法院管辖,这是在地域上对海事法院进行最严格限制的表述。[19]另外,他提到的一点便是海事法院的资格问题。由于海事法院并不属于存卷法院(court of record),仅仅属于较低级别的非存卷法院(court not of record)中的一种,*关于英国法中存卷法庭与非存卷法庭的具体区别,参见文献[20]。其中非存卷法庭词条参见第339页,存卷法庭词条参见第344~345页。故无资格对藐视法院的诉讼当事人处罚没以及监禁。按照柯克的说法,海事法院由于资格的缺失,甚至无权没收保证金,[19]而这对于海事法院的司法权力需求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同属普通法阵营的法学家,还有18世纪的布莱克斯通。上文已经提到,他通过一般法得以排除特殊法的原则,以及“共有管辖权”的概念进一步发展了对海事法院权力的限制,并且在柯克的基础上提出,海事法院不是存卷法院,无权保存盖印合约。[8]107他的学说也是当时争议惯用的法律语言之一。
然而,站在海事法院阵营的法学家们也不甘示弱。其中重要代表是两位著名的海事法院法官、罗马法专家理查·祖齐(Richard Zouch,1590—1661)与约翰·戈多尔芬(John Godolphin,1617—1678),他们也是当时对爱德华·柯克论断的反驳者。在他俩看来,海事案件的审判权应当根据诉讼的性质而定,柯克那种将海事案件案由完全限制在公海上的说法是极其荒谬的,管辖权应当归于契约执行所在地法院而不是订立所在地法院。这就对爱德华·柯克的地域管辖表述做了另一极端的表述。[3]21-23
对普通法学说发出最有力挑战的人,并不是上述两位法官,而是莱昂莱恩·詹金斯爵士(Sir Leoline Jenkins,1625—1685),他的成就来源于他外交家的身份与在国际法方面的造诣。他对两院之争的观点表述如下:海事管辖权的要点在于海事案件的性质而非地点。对其进行法令上的限制并不会灭绝其实际上的管辖权,因与海事案件相关的各项行为均为皇家海军所监管,这种联系是不会消亡的。为其审判设置如此之多的立法障碍只会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审判的拖延与不确定性,而这对于负有契约在身的海事案件当事人来说是最为致命的。他不但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并根据自身的海事案件审判实践列举了许多普通法法院在海事审判上相对无力的证明。[3]24-25只可惜,在17世纪,如詹金斯一般的罗马法学家并没有将自己的学说变为现实,即使在制度层面而非实践层面,普通法法院也由于把持着对立法的最终解释权,在地域管辖问题上并没有退让一步。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争论中持温和立场的马修·黑尔爵士。虽然他的言论并未在论战中为人广为引用,但这名著有《英格兰普通法的历史》的知名法学家对这场争论有着一针见血的洞察力。在他看来,这场普通法与罗马法之间的争议其实无实质意义,因不同的法律之间不能比较优劣,只有何时何地何者较优之说。他承认,采用罗马法的三种特别法院(即军警法院、海事法院与教会法院),特别是海事法院,常常会对议会立法做扩大解释,或利用自己在受案上的便利性来扩大自己的权力。但由于其事实上存在军事与司法两个面向,故看待其管辖权力必然要区分法律(de jure)与事实(de facto)两个方面,不能一以概之。虽然他也认为,国王的普通法是范围更广的一般法律,应由普通法来确定特殊法之适用范围,特别是要让特别法院尊重王国习惯,但比起其他普通法学者来说,黑尔爵士的区分论断已经具有很大程度上的调和性。[1]4-12
(二)学理论说的背后:政治与利益之考量
波斯纳曾在他的著作《法官如何思考》中向人们展现了经验理解法官行为的方式,其中法官的职位、升迁与薪金等因素显然是值得人们去思考的。[21]这一思路用来考察本文所关注的这一问题也必不可少。之所以有1763年之改革,就是因为英国议会看到了普通法法院审判走私犯罪中的一个重大弊病,那就是殖民地官员,包括普通法法院法官,甚至是陪审团团员的偏袒犯罪问题。18世纪是大英帝国官僚机构急速膨胀的时期,殖民地官员多从帝国中心选派,甚至在庇护制的腐败政治环境下,通过卖官鬻爵的方式派任到殖民地。但却无法将他们的薪酬问题解决,因其是对本身就因战事而负债累累的帝国的一个巨大的负担。在此背景之下,包括普通法法官的薪酬被本土化,长期处于殖民地本土精英的控制之下,而殖民地本土的有产者不乏投资走私贸易之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帝国官僚制度效率之低下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14]28-34上文已经提及,普通法法院由于其诉讼程序的特殊性,对走私案件的惩处力度自然不及海事法院,更何况由于陪审团成员不乏走私案件利益相关者,往往有意放纵犯罪,故大英帝国1763年之改革针对的正是这一弊端。*也有学者称这一问题被历史学家们给夸大了,数据显示,在有陪审团审判的46起走私案件中,定罪率仍有54.4%之多,参见文献[5]第195页。
在普通法法院把持海事案件审判的时代,海事法院难以为继,由于它是隶属皇家海军之下的一个兼具司法与行政性质的机构,其法官薪金并不由政府支出,而是由海军部划拨。在实践中,它的收入主要来源是海上通行税、港口停泊费以及出售捕鱼许可证等。[22]33而即便是上述收入,也于18世纪50年代在普通法法院陷入诉讼,最终被普通法法院的判决宣布非法。[22]33-40上文已提到北卡罗来纳海事法院经济上的窘迫状况,事实上这种境况在各地附属海事法院都很常见。海事法院原本不必如此窘迫,因为海事案件的判罚,特别是捕获案件,由于17至18世纪海上战事的频发,其实是颇具利润的。民事案件诉讼费自不待言,事实上捕获、遇难、弃船中所有,以及漂浮、抛弃和系有浮标的投海货物,由海事法院判给海军部,这其中归于海事法院的不在少数。这一份厚利直到1894《商船法》的出现,才真正由国王收回。[17]27拍卖罚没货物则更加有利可图。[11]522故普通法法院与海事法院之争背后的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有利可图的案源的争夺。
海事法院自诞生以来,在英国语境下就具备政治争议的可能性,这跟它的“出身”很有关系。正如黑尔爵士所言,海事法院具有军事与司法两个面向,故不能将它看作单纯的司法机关来考察。在法院人员配置上,法官、登记官员及执行官都是由国王特许状任命的。[17]28而在实践中,海事法院法官权力还往往由海军部临时授予,然后才向王室权力寻求追认其有效性。[5]192从法官的教育背景来说,他们并不是律师会馆训练出来的普通法律师,而是在大学里寒窗苦读的罗马法博士,比起英国法律传统,不如说他们是欧陆的法学-神学家传统的追随者。由于大学与王室关系之紧密,其中多存在人员庇护之关联。这些罗马法博士,也就是日后的海事法院法官们,在成长起来之后成为天然的绝对君权拥护者。[3]12-13以著名的法官威廉·斯科特(Sir William Scott)为例,他于1798—1828年任高等海事法庭法官,其人出身于牛津大学,接受的是罗马法教育,并强烈地支持国王的政府、托利党与教会,同样也接受了来自后者的很多恩惠,在政治立场上对法国大革命问题表示不安。[3]38-41在17世纪,像斯科特这样的海事法庭法官成为普通法律师与清教徒的天敌,而在18世纪,他们则成为殖民地革命者们的天敌。对两者冲突的考察,还需观察他们之间的政治背景以及法官派系归属,[11]518才能真正理解其冲突的本质。
四、结 语
在追溯完这段关于走私案件的两院之争历史之后,文首所提及的关于库姆斯案的争议便有了新的诠释视角。海事法庭的审判便利与身为一名英国人应当享有陪审团审判的自由之间的争执,也许并非仅是虚构的权力与权利之争那么简单。海事案件产生于人们的航海实践,对海事案件管辖权制度的构建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商业实践需要和对海事活动性质认识的影响。但不难发现,如果从实践需要或海事活动性质本身出发,普通法法院扩大自身权力范围的努力是完全与之相悖的。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是制度的形成、学说的提出还是司法实践状况,都很难说能够完全按照实践需要与海事活动特性而定,真正的动因毋宁说是来自人们政治与经济层面上的需求。分析本文所聚焦的例子也许能够给法律人带来一点启示,那就是当我们对制度、理论或实践中的法律冲突感到不解时,全景式地考察它或许能带来某些助益。
[1]PRICHARD M J, YALE D E C. Hale and Fleetwood on admiralty jurisdiction[M]. London: Selden Society, 1993.
[2]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M].李红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279.
[3]BOURGUIGNON H J. Sir William Scott, Lord Stowell, Judge of the High Court of Admiralty, 1798-1828, Chap I[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4]LAING L H. Historic origins of admiralty jurisdiction in England[J]. Michigan Law Review, 1946, 45(2): 163-182.
[5]HARPER L A.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6]BOWEN H V. Revenue and reform: the Indian problem in British politics 1757-1773[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8-109.
[7]MASTERSON W E. Jurisdiction in marginal seas[M]. Lond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
[8]BLACKSTONE W.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in four books, Vol. II[M].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893.
[9]伯克.美洲三书[M].缪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6.
[10]GOLDIE M. Locke: political essay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4.
[11]UBBELOHDE C W, Jr. The Vice-Admiralty Court of Royal North Carolina[J]. The 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1954, 31(4): 518-522.
[12]STECKLEY G F. Merchants and the admiralty court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1978, 22(2): 137-175.
[13]RABUSHKA A. Taxation in colonial America[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DICKINSON H T.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M]. London: Longman, 1998.
[15]HERTZ G B. The old colonial system[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05: 74.
[16]LAWSON P. George Grenville: a political lif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189.
[17]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李双元,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8]DOUGLAS R. Taxation in Britain since 1660[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31.
[19]COKE E. The fourth part of the 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M]. London: E. and R. Brooke, 1797: 134.
[20]薛波.元照英美法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1]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M].苏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2]COSTELLO K. The Court of Admiralty of Ireland, 1745-1756[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2008-2010, 50(1): 33-40.
2016-09-06 作者简介:熊 孜(1987-),男,博士研究生;E-mail:1401110989@pku.edu.cn
1671-7031(2017)01-0037-07
DF961.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