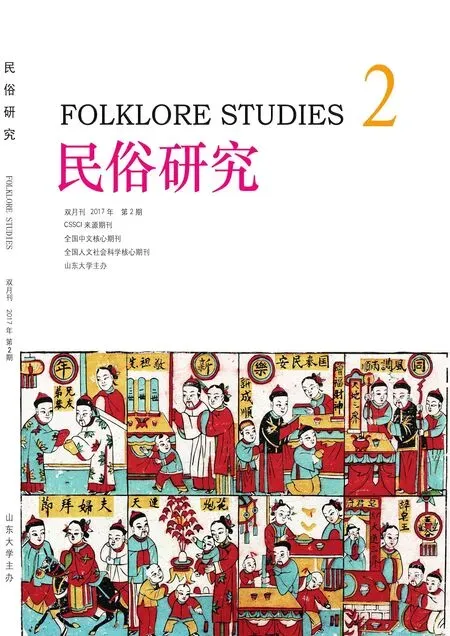西南地区发现的石敢当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
赵川 王丽君 张科
西南地区发现的石敢当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
赵川 王丽君 张科
西南地区目前所发现与公布的石敢当遗存可大致分为三类,各类别在外观形态、制作时间、安放地点和功能意义上存在差异。其中第一类A型石敢当具有典型的道教正一派因素,第三类则不具有明显的道教因素,这种差别可能跟道教正一派在该地区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结合文献与相关拓片资料,泰山石敢当开始出现并流行的年代应不早于明代。
石敢当;泰山石敢当;正一道;天师;民俗
一、西南地区发现的石敢当遗存

图1 剑阁“天师石敢当”碑拓片
根据文献记载,制作石敢当立于路口或宅院门口以镇鬼辟邪在宋元以来一直较为流行。但保存至今的古代石敢当遗存却寥寥可数,仅在个别区域或省份有为数不多的发现,其年代以清代为主。以西南地区为例,加上剑阁新发现的1例,目前已经公布材料的石敢当共计12例,分布在川南、川东和黔北等地。根据石刻形态和所刻内容的差异,这些遗存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3件。石刻主体呈竖长方形,石面竖刻楷书文字和道教符箓,字数多少不等,但均带有“石敢当”字样。按有无榫头以及道符和“石敢当”文字的位置关系,分为两型。
A型:2件。石刻下有榫头,碑面正中竖刻的“石敢当”之前均冠以“天师”等字样,其两侧分刻道符。
2015年10月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与剑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在剑阁县老君庙遗址新发现1件“天师石敢当”碑(见图1)。*关于该碑的详细情况,可参见白彬、赵川、王丽君:《四川剑阁县“天师石敢当”碑研究》(待刊)。图1拓片由王丽君、赵川制作。
碑首上部左、右各刻一圆环,环内分刻“日”“月”二字。中间从左至右分别竖刻“经宝”“道宝”“师宝”,即道教的道、经、师“三宝”。碑身上端正中刻符一道,符下大字竖刻“玉(?)帝敕五灵老君天师石敢当”,另有四列形体较小的符形和文字从上往下分置两侧。碑身下部竖刻文字10行,行间用阴线隔栏分开,从右向左读。右侧:“天师立放(教?)真武收魔断除痨瘵咒曰:/天符无碍,众百鬼□(尽?)消。魔走化徙他乡外,/个个恼(脑)门破。入(?)粉碎□万(?),莫恼诸仙子。/□天食诸众生,闻吾一咒□,速速远他方。/海外无藏处,□(收?)□(留?)地狱间。永为□鬼精斩绝。”左侧:“人安万代,正(镇)宅安宁。誓断冤痨,万鬼消亡。/女青律令,不得留停。一立已后,万古传名。急!急!/正德三年戊辰九月十六日都司官□陈纪雅识□/上清大洞回车道宝箓断冤真师刘/三天掌教正一降魔护道天师张。”
贵州遵义市汇川区泗渡镇石敢当碑,碑身呈竖长方形,露表通高80厘米、宽47厘米、厚10厘米。碑额上端抹角,左右分别刻“日”“月”二字,中间刻一笔画稍有变形的“敕”字,每两字之间各刻一道符。碑身用阴线分为五列,中间竖刻“天师誓鬼石敢当”,左右各刻一大型道符,最左侧刻“大明成化二十年甲辰岁五月十五日立”16字,最右侧刻“誓以绝咒□□□冤讼玉清三洞五雷经……”等字(见图2)。*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主编:《遵义历史文化》(内部刊物)2015年第4期,第34页。该材料由政协遵义县文史委员会刘永书先生惠示,特此致谢!
该碑带有明确纪年,立碑时间为成化二十年(1484)。类似的材料,在遵义地区的古代方志中也有著录。如道光《遵义府志》记载:“成化誓鬼符刻。按,刻在府城南七十里庙林,古藤缠抱,不著地,俗因呼‘飞来碑’。上刻日、月、符篆,下一行书‘成化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立’,中行书‘敕天师誓鬼石敢当’,末行书‘誓以绝咒除炼解冤讼’等字。城北六十里道旁阜上亦有此刻。”*郑珍、莫友芝编纂:《遵义府志》(点校本),巴蜀书社,2013年,第185、186页。又民国《续遵义府志》记载:“景泰符刻,在城西南穆家寺右半里,石碣上刻日、月、符篆,中行‘勅天师誓鬼制邪石敢当’,左行‘天运景泰六年乙亥岁十一月初九庚戌午时立’,末行‘誓以绝迹除炼解散魔讼’等字。”*民国十八年(1929)《桐梓县志》亦对此石有著录:“景泰符刻,在城西穆家寺右半里。石碣上中行刻‘勅天师誓鬼制邪石敢当位’,左行‘天运景泰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誓’。”两书所记的个别释文略有差异,或因碑文漫漶所致。周恭寿修,赵恺、杨恩元纂:《续遵义府志》,巴蜀书社,2014年,第251页;李世祚修,犹海龙纂:《桐梓县志》卷八《舆地志下》,民国十九年(1929)铅印本。两碑分别刻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景泰六年(1455),均早于汇川区所发现的石敢当碑,目前尚未发现其原石。但据方志著录文字来看,其与汇川的石敢当碑在形制与内容上较为接近,均可归入第一类A型石敢当碑讨论。尤其是道光《遵义府志》所收之石敢当碑的立碑时间仅比汇川区泗渡镇石敢当碑早1年,碑身中间均刻“敕天师誓鬼石敢当”,后者右侧所刻文字已经部分漶泐,但可据前者补为“誓以绝咒除炼解冤讼玉清三洞五雷经……”。像这样年代、内容极为相似的两块碑,安立在不同的地方,绝非偶然所致,而是有意为之,应是有一定规模和组织的行为所致,也说明这种类型的石敢当碑在当时应非某地、某户人家单独出资或者主持刻立。虽然其背后的相关历史背景难以准确追寻,但笔者相信若进行仔细搜寻,在播州(今遵义)地区应该还会有类似遗存的发现。
B型:无榫头,道符位于石敢当上部,占据石面大部分位置,下刻“石敢当”三字。目前发现仅1件。1990年,通江县广纳乡出土1件带道符的石刻*重庆市博物馆编:《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二册,四川·重庆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8页。,上部已残,下部无榫头,石面左右两边缘饰卷草纹,残高60厘米、宽43厘米。上部刻三道道符,右侧竖刻“……历三十八年七月吉日法师李”,下部中间刻一椭圆形的后天八卦图,卦图内、上部分别刻“永镇山”“石敢当”,卦图左、右侧各竖刻两列文字,左侧为“五雷镇宅保家堂,人口清吉鬼消亡”,右侧为“五百雄兵灭蟒怪,千年万载守门方”(见图3)。据所刻文字,知石刻年代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
第二类:石刻大体呈横长方形,上端抹角,石面无道教符箓,仅刻有文字。《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收录1件僧智明买地券(见图4)*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下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090-1092页。,该券现藏于都江堰文物管理局,石刻宽44.8厘米、高41.4厘米,立劵年代为崇祯十二年(1639)十二月初二日,券文与一般成都地区明代墓葬出土买地券并无殊异,惟券额横向阴刻“石感(敢)当”三字,不见于其它类似材料。

图2 贵州遵义市汇川区泗渡镇石敢当碑

图3 四川通江县广纳乡石敢当碑拓片

图4 崇祯十二年(1640)僧智明买地券券文拓片
第三类,石刻上部圆雕怪兽头像或将军像,其下或旁边阴刻文字的内容简单,仅刻“泰山石敢当”“石敢当”“泰山不当位”等寥寥数字,无道教符箓。该类石敢当在四川宜宾*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下)》,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807页。、简阳*该碑现存于简阳市奎星阁摩崖造像旁的大路边。承蒙简阳文管所所长陈军先生惠示,特此致谢!,重庆*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重庆分册(下)》,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41、275、316页。,贵州遵义*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贵州分册》待出。等地共发现有8件。如贵州遵义赤水市大同镇黄金村四洞沟石敢当,高1.2米、宽0.6米,碑身圆雕将军像,头戴盔甲,怒目圆睁,张口吐舌,手捉小鬼,其年代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川宜宾屏山县新安镇金鸭村石敢当,立于大路右侧石滩青杠林内,碑身呈竖长方形,高1.6米、宽0.27米,上部浮雕怪兽头像,其下竖排阴刻“泰山石敢当”五字,侧面刻“大汉民国元年(1911)五月十五日立”。
上述不同型别的三种石敢当遗存,第一类3件(不含道光《遵义府志》和民国《续遵义府志》所著录的两件),第二类型1件,第三类型有8件。从刻石年代来看,其中第一类A型石刻年代最早,贵州遵义汇川区石敢当立于成化二十年(1484),四川广元剑阁县石敢当立于正德三年(1508)。此外,道光《遵义府志》和民国《续遵义府志》所著录的两碑年代更早。第一类B型石敢当年代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第二类石敢当僧智明买地券刻于崇祯十二年(1639)十二月初二日,稍晚于第一类B型。第三类石敢当《中国文物地图集》所公布的资料中,有的并未提及石刻准确的纪年,但根据类似材料可大致推定其主要流行于清代至民国时期,年代均晚于第一类和第二类。
二、原生环境与性质功能
第一类石敢当均刻于明代中晚期,石刻内容为文字与道教符箓相结合,其中第一类A型年代早于第一类B型。除此之外,两者之间在使用方式上也应该存在一定的差别,第一类A型有榫头,带座,应系安放于人来人往的道路当口或者宅院附近,以为当地居民断除复连,镇鬼辟邪;第一类B型无榫头,体量较小,不大可能立放于地面上的某处。据石刻文字内容,刻石的目的在于安镇宅舍,故而第一类B型这1件石刻极有可能埋于生人宅院附近。
第二类材料乃为墓葬出土的买地券,只是在券额刻以“石感(敢)当”三字,与该地券形制较为相似的成都出土明代买地券材料中,券额内本就没有固定的刻字内容,有刻表示石刻用途的“墓券”*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中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575、576页。“券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中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653、654页。“大朝券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中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674、676页。“地契之照”*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中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585、586页。“立幽堂券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中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703、704页。“立券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中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709、710页。等,有刻“南无地藏王菩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中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573、574页。,有刻寓意吉祥的“阴阳开太(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下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093、1094页。,有刻纪年的“下元己丑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中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577、578页。“上元岁君庚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中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693、694页。,也有留白不刻文字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博物院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中册,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668、669页。,诸此种种,不一例举。与第一类、第三类石敢当护祐生人、断除复连而有所不同的是,第二类石敢当置于墓中,显然是为埋于地下的死者服务的,其意义应如一般买地券一样,在于冢墓安稳,保护亡魂不被邪精干犯。僧智明买地券制作精细,字迹工整,刻写之人当具一定的知识水平,而券额却将“石敢当”之“敢”刻为“感”,或乃字音相同之讹写。第二类石敢当材料虽然仅此1件,但却反映了石敢当在功能、意义上的转变,这是值得加以重视的。
第三类石敢当均系笔者从《中国文物地图集》的西南地区相关分册搜集而来,书中未附照片或拓片图版,故无法得知碑刻的具体形态。但从其描述性文字来看,第三类石敢当在外观形态上与第一类、第二类均存在极大的差异,其石面上刻写“石敢当”等字样以显示其镇鬼辟邪的功能,更在石刻重要位置圆雕怪兽或捉鬼的将军像,显示出其具有捉鬼、食鬼的能力,形象上具有直观性。第三类石敢当多立于古道路口,不大可能埋于地下。目前此型别的石敢当发现数量最多,一方面可能与年代距今不远,保存较好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以来石敢当信仰在民间的流行和深入状况。
划入第一类A型的2件石敢当碑,碑面中间竖刻的“石敢当”三字前均带有“天师”二字,剑阁石敢当碑更是三次出现“天师”字样。江西龙虎山张道陵后嗣的天师乃道教正一派的领袖,但天师不可能真正地参与这些石敢当碑的制作与安放过程。石碑冠以天师名号,乃系民间道士打着天师的旗号,假借天师的名义,突出石碑的法力,以便更有效地震慑邪鬼。类似的情况,在考古发掘成果中亦偶有所见,如江西南城县益宣王朱翊鈏及其二妃合葬墓的李英姑墓室(嘉靖三十五年,1556)中出土纸质冥途路引,文末署有“三天扶教辅元体道大法天师张证盟”。*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张勋燎:《江西、四川明墓出土的道教冥途路引之研究》,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第五册,线装书局,2006年,第1352-1354页。江西玉山县广西参政夏浚墓(嘉靖四十年,1561年)出土纸质冥途路引,文末署有“祖师三天扶教辅元体道大法天师张证盟”。*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玉山、临川和永修县明墓》,《考古》1973年第5期;张勋燎:《江西、四川明墓出土的道教冥途路引之研究》,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第五册,线装书局,2006年,第1350、1351页。两件冥途路引均为批量生产制作的木版印刷纸品,文末署之天师名号系事先印刷上去,并不表明当时的天师曾去为益宣王妃李英姑和广西参政夏浚“证盟”。湖北秭归县西陵峡归州镇庙坪明墓出土的部分契砖正面券文末署“祖师三天扶教(命)大法师张在天判给”*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湖北省三峡工程移民局编:《秭归庙坪》,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41、244、271页。张勋燎:《重庆、四川成都和湖北秭归新发现的河图洛书遗迹》,《中国历史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73-479页。,强调说明该契券是由张天师颁发给死者的有效证件。明前中期诸帝大都崇道*曾召南:《明代前中期诸帝崇道浅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正一派尤受尊崇,到明中期发展到极为贵盛的局面,正一天师见重于朝廷,屡蒙召见赐封,常命设醮建斋,可谓荣耀已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3-439页;赵玉玲:《从正一道的贵盛看明代道教的世俗化》,《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道教正一派以斋醮祈禳和符箓法术见长,信众极多,正一系统的符箓法术在民间社会有广泛的流布。四川剑阁和贵州遵义所发现的明代石敢当碑均带“天师”名号,应与当地正一派的流行有直接的关系。*关于明代道教正一派在播州(遵义)地区的流行情况,可参见赵川、韦松恒:《贵州遵义县鹤鸣洞道教铭刻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编:《南方民族考古》,待刊。第三类石敢当中多名为“泰山石敢当”“石敢当”“泰山不当位”等,不见“天师”字样,碑身也不再刻划道教符箓,取而代之的是凶猛的怪兽和将军形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以来安放石敢当的行为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民俗活动,正一道因素的影响逐渐衰退和没落。
以上三种型别的材料不仅存在外观形态的差异,在制作时间、安放地点和功能意义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当然,由于石敢当遗存多立于道路当口,容易遭受风雨侵蚀和人为损坏,完好保存至今的不多,加之此类铭刻材料本身数量较多,年代较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相信目前西南地区保存下来的石敢当数量当远不止上述几件,类型也应更多,均有待作进一步田野调查。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而言,虽不一定能完全反映西南各地区石敢当材料的准确分布比例和数量,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南地区石敢当遗存的大致面貌。
三、“泰山石敢当”起源再探讨
本文所讨论的西南地区目前公布材料的12件石敢当材料均带自名,或为“石感(敢)当”“天师石敢当”“泰山石敢当”,但就分类情况而言,自名为“泰山石敢当”者均属第三类石敢当,年代皆不早于清代,与之相应的是,文献记载“泰山石敢当”也多集中在明清时期。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再新县治,得一石铭,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今人家用碑石,书曰‘石敢当’三字于门,亦此风也。”*王象之:《舆地纪胜》第七册,李勇先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65页。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七,“石敢当”条记载:“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则世之用此,亦欲以为保障之意。”*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第206页。以上两则材料记载石上所书或所刻文字均为“石敢当”,而非“泰山石敢当”。杨慎《升庵集》卷四十四,“钟馗即终葵”条:“俗立石于门,书‘泰山石敢当’。”*杨慎:《升庵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5页。《灵驱解法洞明真言秘书》,“泰山石敢当”条记载“凡有巷道来冲者,用此石敢当。”*午荣编,李峰注解:《新镌京版工师雕斫正式鲁班经匠家镜》,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306页。表明“泰山石敢当”出现年代应该晚于“石敢当”年代,不大可能早到宋元时期,或不早于明代。*蒋铁生先生亦曾指出“在明代以后,随着泰山信仰的发展,在各地石敢当的石刻中,有的加上了‘泰山’二字。在传播中,‘石敢当’和‘泰山石敢当’同时存在”。蒋铁生:《泰山石敢当论纲》,《民俗研究》2005年第4期。
笔者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有幸拜读叶涛先生《泰山石敢当源流考》一文*叶涛:《泰山石敢当源流考》,《民俗研究》2006年第4期。,文章许多见解精辟独到,对笔者有颇多启发。文中提到三方宋金时期的石敢当碑,其中一方立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一方为金代“如意院尼道一首座幢记”,具体年份不具;另一方为金熙宗完颜亶皇统六年(1146)“金泰山石敢当蒙古文”。作者据此指出宋金时代已经出现“泰山石敢当”。文中公布了两方金代碑刻拓片,“如意院尼道一首座幢记”两幅拓片的宽、高尺寸一致,知原石应不少于两个碑面。两幅拓片图版中,只有其中一幅带“泰山石敢当”字样。该幅拓片文字可分为三部分,一是横书的梵文经文,共7行;二是经文下的楷书题记,记载了尼道一立此经幢的缘由和经过;三是在梵文行间间隙双线阴刻楷书文字,上部竖刻“泰山石敢当”五个大字,下部刻“安镇大吉”。另一方皇统六年碑刻的情况大致与“如意院尼道一首座幢记”相近,所公布的两方拓片显示碑已残损,其中一幅上部为一行梵文经文,下为三列楷书题记:“言:矧命三复,敢用直书云耳。维/皇统六年岁次丙寅十二月丙申朔二十/五日乙时建”;另外一幅拓片较宽,左侧上部从左至右横书“元亨利贞”,下为六行梵文经文,行间双线阴刻楷书“太山石敢当”五个大字,右侧部分仅刻5行梵文经文,且位置明显低于左侧经文,表明这幅拓片所拓乃两个不同的石面,系拓工先对左侧部分上纸后再顺时针将剩余的纸张上至右侧部分,因而制作出来的拓片明显宽于另一幅。笔者细审拓片图版,将两碑拓片的拓墨残痕与字迹笔画仔细对比,发现竟能完全重合一致,只是拓片长短尺寸不一,盖此二碑实乃一碑无疑。原来所谓的两碑各两幅拓片,实际上是同一多边形经幢的其中四个石面的拓片,只是所拓范围各不相同及拓墨颜色深浅略有差异,遂被误以为是不同石碑的拓片。从字与字之间的关系来看,碑文中的梵文经文与其下楷书题记布局谨严,字体规整,原为一体。“泰山石敢当”中的“泰”“当”,均分别打破了原来的梵文经文。从残存题记来看,“泰山石敢当”与原梵文经文和题记没有任何内容之间的关联,也不大可能是同时期规划的。笔者推测其极有可能是经幢所在寺院衰落荒芜之后,经幢尚立,后世之人为取材便利,遂直接在其文字空白处刻“泰山石敢当”等字加以重新利用。实际上,明清时期在前代所立经幢上刻“泰山石敢当”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乾隆《孟县志》卷七,“唐开元间尊胜幢”:“右幢但存尺许,经文剥落,村人于其上刻‘太山石敢当’五字,惟正面‘尊胜幢上为开元圣文神’十字尚存。”*仇汝瑚:《孟县志》卷七上《金石》,乾隆五十五年(1790)刻本。叶昌炽《语石》卷九:“妄人题字一则”:“又一残幢,有‘泰山石敢当’五字,此皆所谓毁瓦画墁也。”*叶昌炽:《语石》,中华书局,1994年,第526页。因此,如意院尼道一首座幢记上面的“泰山石敢当”五字的绝对年代应明显晚于经幢的制作时间,不可能早至皇统六年(1146),极有可能为明清之作。显然,利用此碑来证明不晚于金皇统六年就已经出现“泰山石敢当”碑,是站不住脚的。*崔广庆先生曾就年号、文字关系、“幢”字意义等方面对此碑的年代提出质疑,并推测其“被翻刻的可能性很大。”笔者赞同其对年代的判定。但根据“泰山石敢当”与梵文经文间的打破关系,可知该碑应非翻刻,而是明清时人对该石碑进行重新利用,直接在经幢上文字空白处补刻“泰山石敢当”。崔光庆:《泰山石敢当起源研究》,《泰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另一件南宋绍兴年间的碑刻*关于该碑的详细情况,可参看林国平、彭文宇:《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8页;周星:《中国和日本的石敢当》,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编:《民族学研究所资料汇编》第8期,第88、89页。本文系转引自叶涛:《泰山石敢当源流考》,《民俗研究》2006年第4期。,叶先生在文中未公布其拓片图片或照片,但附有形制及内容示意图。石碑高约80厘米、宽53厘米*林国平、彭文宇:《福建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8页。,上部从右至左横书“石敢当”三字,其下竖刻四列题记,释文为:“奉佛弟子林进晖,/时维绍兴载,/命工砌石路一条,/求资考妣生天界。”记载了该碑原立于绍兴年间,系奉佛弟子林超晖为超度其父母亡魂而出资修路所立。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修路的功德碑,那么其原先所立位置也应在路边显眼处。从示意图上,看不出碑文上部“石敢当”和下部的题记之间是否存在打破关系。但既然是记述修路的功德,又何必在题记上方刻与题记主题毫无关联的“石敢当”三字。笔者姑且也认为“石敢当”三字系后来补刻上去,不属于林超晖在南宋绍兴年间立碑时的原刻文字内容。因此,该碑始立年代为南宋无疑,但于碑身上部刻“石敢当”三字的时间应晚于林超晖立碑年代。所以,如果将此碑作为“石敢当”遗存来研究,在没有其他充足证据或材料佐证的情况下,是不能断然将其年代定为南宋时期的。
综上,西南地区发现并公布材料的石敢当遗存不多,其年代均不早于明代,目前笔者亦尚未见到其他地区有年代确切早于明代的石敢当遗存公布发表。而碑身明确出现“泰山石敢当”字样的石敢当的年代不早于明代,均为清代至民国时期的遗存。联系文献记载,至明代中晚期,泰山石敢当才始见诸时人之记载,其开始出现并流行的年代应不早于明代。
[责任编辑 龙 圣]
赵川、王丽君、张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6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项目编号:13ZD&101)的阶段性成果。 拙作草成之后,承蒙四川大学张勋燎教授、白彬教授及同门葛林杰、余靖、干倩倩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