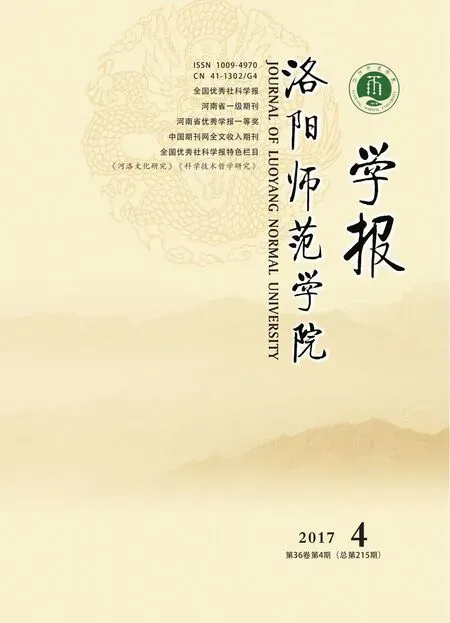数字时代记忆研究与哲学的出场
杨庆峰
(上海大学哲学系, 上海 200444)
数字时代记忆研究与哲学的出场
杨庆峰
(上海大学哲学系, 上海 200444)
每一个体都有其生命的特殊时刻, 如出生、 成人、 婚姻、 生子以及死亡; 每一对夫妇、 每一个家庭同样拥有这样的时刻, 结婚纪念日、 孩子的出生; 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如建国日、 传统的节日等等。 这些时刻就成为一个个体、 一个群体、 一个家庭、 一个国家存在的合理基础、 价值所在以及发展的重要见证, 纪念这些时刻对于个体、 群体以及国家来说显得异常重要。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 记忆实践的快速发展与理论滞后之间的矛盾亟待人们加以回应。
面对上述现象, 古代哲学家曾经给予过极大的关注, 这是哲学的伟大之处, 但是也正是因为此, 中西方哲学传统对记忆现象的关注同时也导致了不可忽视的忽略或者遗忘。 中国文化传统中就存在着这种忽略。 “忆”在文献中出现的很少。 在《说文解字》中并没有“忆”字的注释说明, 仅仅在一些偏僻文献中略有点到, 如《释名.释言语》中做出“忆, 意也, 恒在意也。 ”可以看出, 中国文化传统中用“意”来解释“记忆、 回忆”。 这个阐述是将记忆放到意的范畴中加以解释, 相对贫乏而且过于局限(相比拉丁语对记忆概念的10种解释就显得贫乏, 此外更是将记忆限制在心的领域中)。 后来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明显。 尽管人们使用着“记忆”“回忆”之类的概念, 但是基本上不做区分。 在古代西方, 情况稍微好一些。 我们在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 可以找到相当丰富的论述。 柏拉图的记忆描述多是体现在对话录中, 如《斐利布斯篇》《泰阿泰德篇》、 《费德罗篇》和《智者篇》等四篇目中, 主要以蜡块、 戒指印等比喻形式说明记忆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的记忆分析主要集中在《论记忆与回忆》、 《论灵魂》等篇目中, 主要探讨记忆与回忆的区分、 记忆与时间、 记忆主体等问题, 这些成为了整个西方记忆研究的源泉。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在那个自然科学极度落后的时代, 哲学家的阐述成为时代理解记忆现象的重要根据。 可惜的是, 由于记忆现象被放入到心理学的体系之中以及认识论体系中, 更由于记忆研究方法显现出浓厚思辨性的特征使得记忆并没有成为真正的问题。 随着西方进入黑暗时代, 尽管古代希腊哲学家的记忆文本被保留了下来, 但是记忆与哲学一道沦落为宗教的奴婢, 完全被遗忘, 如同阿拉丁神灯中的妖灵等待着重新被唤醒的时刻。
14世纪以来, 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人类对于记忆现象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数学、 物理学、 生物学保持着其自有的发展速度, 更为重要的是, 心理学借助实验方法摆脱了思辩方法的束缚, 真正从哲学领地中独立出来。 20世纪50年代以后, 神经科学与技术给各个自然科学领域的带来了福音, 如同吹响了集结号一般, 各个领域在记忆现象联合起来, 迅速推进着记忆研究, 从记忆内容、 记忆位置、 记忆存储到记忆取回等问题不停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甚至MIT的研究员们正在给小老鼠植入错误记忆、 寻找帕金森症导致的失落记忆。 在当前时期, 人类记忆科学研究的知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当年恩格斯提到老黑格尔应该高兴, 因为他有足够的自然科学材料来为他的自然观做出辩护。 今天, 哲学家除了高兴之外, 还要意识到自身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如何面对当代记忆研究的新情况以及如何认识以及复兴当年记忆哲学研究的繁荣气象?
当代记忆理论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内取得了共同的突破。 自从哲学中记忆火焰的熄灭, 历史学、 文学与社会学在记忆研究领域迅速推进, 并且提出了颇有影响力的记忆理论, 如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 诺拉的记忆之场和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等。 这些理论有力地支撑起上述领域中的经验研究。 然而关于记忆的本质、 记忆主体等阐述一直停留在古希腊水平, 遵循着希腊哲学家划定的问题, 并没有多大进展, 甚至他们将记忆理解建立在心理学与生物学的基础之上。 而记忆的科学研究由于实验方法以及新的技术的运用唤醒了所有自然科学的研究, 正在进入一个记忆知识迅速积累但也是被学科高度分化的阶段。 20世纪之前的记忆研究一直徘徊不前, 20世纪初的记忆科学研究发端于生物学, 德国生物学家赫林(Ewald Hering)、 理查德.萨门(Richard Semon)等从“生物印痕”的角度阐述了记忆与遗传的关联, 这使得记忆研究与生物有机体完全结合; 同代的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用实验方法将记忆与心理的关系加以阐明。 后来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布兰德.米勒(Brenda Milner)将心理学引入与神经科学结合的领域, 通过研究失忆的、 精神分裂的病人继续推进着记忆研究。 也正是因为这样做, 她终于找到了记忆之家——海马体。 后来的神经生物学、 神经心理学都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继续探索, 不同的是, 更多是借助最新的技术(如光遗传学(optogentics))对记忆细胞做着相应的研究。 这些胜利令人高兴, 因为人类关于记忆的知识更加完备, 改造记忆的技术也初具规模。 但是, 这些知识却是在自然科学高度分化与融合的基础上获得的。 即便出现的学科融合, 也只是方法的融合与知识类别的融合, 无法改变记忆本质被分割的状况。 这一点是由现代科学的本性决定的。 自然科学越发展, 越是从不同细部研究对象, 所给出的知识也越加显示出被分割的本质特性。
当代记忆实践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现象。 一方面, 自然科学家如何借助新的技术改造着人类记忆、 植入错误记忆、 删除不良记忆以及找回失落的记忆, 这样做已经给人类自身带来了震惊, 我们无法在原有的知识框架中去理解“我是谁?他是谁”的基本问题。 另一方面不同个体、 社会群体、 国家都在以不同的形式明确着属于自己的重要时刻, 如生日、 诞辰日、 忌日和建立日等待。 “第一次”成为日常生活记忆中熟知的概念, 也正是在这样的概念之上, 生成了个体、 集体的记忆与认同。 在记忆实践中, 记忆的使用与滥用、 过去的建构与解构、 历史与身份的认同等等都如同待嗷嗷哺乳的婴孩等待着奶汁一样, 等待着记忆理论的援手。 很显然, 科学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 甚至他自身也需要理论的孵育。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哲学必然要出场, 显示自身。 哲学出场之前预备性的说明需要实现一个目的, 说明哲学对记忆现象的关注之必然性与必要性。 从根本上来说, 从哲学角度关注记忆问题不是为了解决其他学科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而是数字时代哲学自我反思的必然要求。 “因为哲学首先要做的工作, 就是要证明它的对象的必然性”(《小逻辑》, 第414页。 )。 所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哲学关注记忆现象必然性。
首先, 从哲学角度切入记忆是哲学的应有之意, 然而记忆在哲学自身发展中被遮蔽和遗忘。 记忆现象本是哲学的传统研究对象。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探讨灵魂问题的时候, 就将记忆视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并围绕记忆的本质、 记忆与认识、 记忆与技术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讨论。 但是由于哲学自身强大的认识论传统, 记忆被认识、 知觉和认知问题遮蔽, 从而造成“哲学遗忘记忆”的历史。 此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发展与突破。
其次, 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记忆成为各个学科的对象, 而加剧了记忆在哲学中的缺席。 19世纪70年代, 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使得记忆现象的思辨解释获得了可靠的经验支撑。 实验心理学揭示了记忆现象的心理机制; 实验生物学揭示了记忆的生物学机制(如印痕), 并给出了经验证据。 对比之下, 记忆的哲学观点显得老旧不堪, 相形见拙; 自然科学的观点逐渐被接受并且获得广泛认可。 尽管当时一些极具反思和创新精神的哲学家有效地利用了自然科学记忆研究的成果对记忆现象展开进一步反思, 但是自然科学发展遇到的技术障碍使得上述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 由于缺乏实验和必要技术的支撑, 自然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有机体层面, 而无法进入到更基本的构成单元:自然科学研究由于自身的障碍而停止下来。 这种限制使得对记忆的哲学反思无法再获得新的材料和观点突破, 继而也完全停滞下来。 但是记忆研究的极度专业化、 分割化特征已经形成。
最后, 哲学重新关注记忆是哲学在数字时代自我反思的必然要求。 数字时代中虚拟现实技术、 数字技术等新兴体验技术形式的出现, 成为刺破哲学内在反思记忆现象研究障碍的力量。 数字技术的出现, 不仅赋予古老的哲学问题以新的形式, 而且带来了新的问题有待于回答。 当然, 哲学再次关注记忆并非偶然的、 外在因素推动的结果, 而是其内在必然性的要求。 20世纪初出现了哲学终结的现象, 即哲学的话题逐渐消散在生物学、 心理学、 神经科学、 社会学、 历史学和文学等不同学科中。 作为古老哲学对象的记忆现象也不能除外:记忆逐渐成为上述学科的研究对象, 在不同的学科中被分裂研究, 从局部的、 分析的角度得到解释。 尽管提出了一些具有价值的观点和命题,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整体意义模糊不清、 本体论承诺互相冲突、 记忆本质界定矛盾和记忆概念所指与能指不明等。
综上所述, 当前记忆研究急需哲学的出场。 但是, 哲学的出场并非是给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记忆现象, 古希腊哲学家的理论框架已经存续了千年, 提出的问题等待着时代重新回应; 哲学的出场并非是仅仅表现为伦理学的关切。 伦理学的关切充其量是道德情怀的表现, 如同黑格尔说的“良善道德的义愤”, 而是需要直达理性的层面。 哲学的出场从根本上说真理精神的展现, 至少表现为如下层面:(1)在知识获取层面上至少表现为对断裂的、 被分割的知识的一种综合过程, 需要反思记忆消散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状况, 从综合的角度概括不同学科记忆研究的内在逻辑、 特征和局限, 从而消融当代记忆研究中的模糊和矛盾之处; (2)在成果指向上至少要把记忆研究成果、 观点放入“人的问题”这一整体语境中, 从整体的角度反思数字时代记忆研究对于“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等问题的解决程度, 反思数字技术凸显出的新问题; (3)在本体层面上需要为解决当代哲学中的身体与心灵、 认知与认同以及主体与他者等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最终有效呈现哲学之于当代记忆研究的真正价值; (4)更为重要的是, 哲学的出场需要改变看待记忆的传统视角, 摆脱知识与真理的阴影, 需要克服认知科学的影响, 将记忆从一种介于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泥潭中拔离出来, 从认识与认知的阴影之下解放出来, 真正回到记忆本身。
(杨庆峰,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
[责任编辑 尚东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