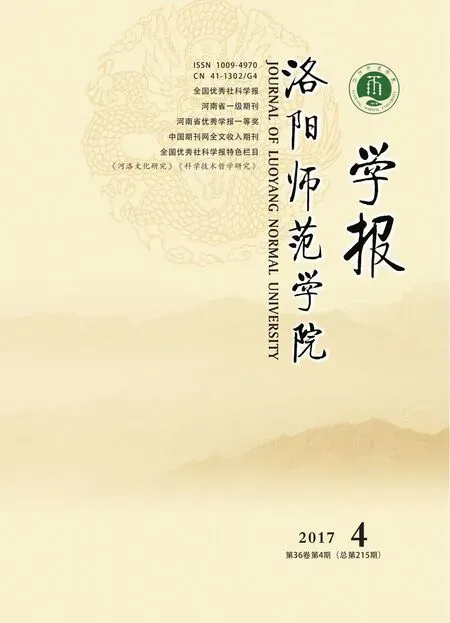曾德昭《大中国志》中的汉字字体名称研究
刘亚辉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曾德昭《大中国志》中的汉字字体名称研究
刘亚辉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汉学名著《大中国志》介绍了汉字的四种字体, 因只标了注音, 未写汉字, 引发后人诸多猜测, 特别是第二和第三种字体, 争议颇大。 何高济认为第二种字体为行书, 孟德卫、 计翔翔、 陈辉、 董海樱等学者认为第二种为楷书, 第三种为隶书。 但大量资料证明第三种不应为隶书, 而是行书。 《大中国志》介绍的汉字四种字体应分别为篆书、 楷书、 行书、 草书。 关键词: 曾德昭; 《大中国志》; 字体; 隶书; 行书
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 1585—1658)于1641年完成的《大中国志》(RelaçãodaGrandeMonarquiadaChina)是汉学史上的名著, 全面深入地描述了中国明末的社会和文化, 在欧洲广为人知, 影响极大。
曾德昭1613年来华, 1637年从澳门返欧, 开始撰写《大中国志》, 1641年完成*关于书稿完成时间, 何高济认为是1638年(何高济译:《大中国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计翔翔认为是1641年(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笔者赞同后者。。 原稿为葡萄牙文手稿本, 未刊印*关于《大中国志》的葡萄牙文原稿当时是否出版, 有两种意见: 一是认为当时出版过, 如美国汉学家孟德卫(D. E. Mungello)认为1641和1642年分别于葡萄牙的马德里和里斯本出版(孟德卫著, 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65页); 另一种意见是当时并未出版, 如何高济认为当时手稿并未出版, 首次出版的是1642年的西班牙译本(见《大中国志》“中译者序”), 计翔翔也写出了这两种意见(见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笔者赞同后者。。 1642年苏查(Manuel de Faria I Sousa)将其译为西班牙语出版, 1643年原稿译成意大利文刊行。 1645年和1667年有两种法文译本, 1655年有英文译本, 可见当时其在欧洲的广泛影响。 后又于1956年出版了译自意大利语的葡萄牙文本(1994年再版)。 1998年何高济将其译为中文。
《大中国志》用了整整一章介绍中国的语言文字, 介绍了汉字的产生年代、 汉字总数、 笔画构成、 造字法、 字体等, 后世学者对其介绍的内容产生了很多误解和争议。 如曾德昭在书中展示了5个汉字以及它们的书写过程, “一”加一竖为“十”; 再加一横为“土”, 意思是土地; 上面再加一横为“王”, 意思是国王; 在它右上侧, 头两横之间加一点为“玊”, 意思是一种珍贵的石头。[1]33曾德昭以此表明汉字的形体是由笔画组合而成的。 董海樱认为这是表明汉字造字法的著名例子[2]123, 我们认为这不是说明汉字的造字法, 而是讲了汉字的笔画构成, 与造字无关。 例如“十”从造字来说, 是个象形字, 结绳记事, 表示一个终结的数字, 汉字构形系统发展到西周以后, 所有字形中的块形成分都取消了, 大多数变成了一横。 对《大中国志》中介绍的字体, 误解和争议更大, 本文仅对此作出研究。
一、 曾德昭对汉字字体的介绍
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向欧洲介绍了四种汉字字体, 但未写出汉字, 只标出注音, 引发后人的种种猜测和讨论。 曾德昭是如何介绍的?因为没有找到其葡萄牙文手稿, 我们只能根据译文来了解。 为便于读者比较, 笔者摘取了《大中国志》英文译本中的以下部分*当时的英语与现代英语有区别。:
“This variety in making of their letters hath caused foure kinds of them. First theAncient, which remaineth still in their Libraries, and is understood of all theLitterati, although it be no longer in use, except in fome titles and feales, which they put instead of Armes. The second is calledChincù, and is the most current, as well in manuscript, as printed books. The third they callTaipie, and answereth to the running hand used among our publick Notaries, not much in use, unlesse it be in bills, contracts, pleadings, policies, and such like things. The fourth is so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as well for the Abbrebiations, (which are many,)as also for the different stroakes and shape of the letters, that it requireth a particular study to understand them. This wordSie, which signifieth to give thanks, is written after three most different manners.”[1]33
何高济将上述英文翻译成了中文:
“造字的这种变化, 使字体有四种不同。 首先是古文(Ancient), 这种文字仍保留在他们的图书馆, 知识分子认识它, 尽管除了用作代替纹章的印玺和题名外, 不再使用。 第二种叫做行书(Chincù), 最通用, 用于文献和书籍印刷。 第三种叫做拓白(Taipie), 相当于我们书记的手书, 不怎么使用, 仅用于告示、 协约、 申请、 票据等等。 第四种和其他的很不相同, 既是缩写(这很多), 也有字体的不同笔划和形状, 需要特别研究才能认识。 ‘谢’(Sie)这个字, 意思是谢谢, 有三种极不相同的写法。 ”[3]40-41
何高济的中文译本影响很大, 引用者众。 如张西平引用说:“曾德昭还介绍了汉字的三种书写形式, 即‘古文’, 指印玺上的形式; ‘行书’, 指通用文献和印刷的形式; ‘搨白’(Taipie), 指仅用于告示等的书写形式。”[4]8张西平在引用时只说曾德昭介绍了汉字的三种字体, 不知为何没有注意到第四种。
二、 学界对曾德昭所述字体的讨论
学术界对四种字体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二种和第三种上。 何高济在中文译本中认为第二种是行书, 但其他学者普遍认为是楷书。 何高济并未推测第三种是什么, 后世学者多认为是隶书。
对这“四体”, 计翔翔认为:第一种“显指篆书”, “曾德昭称其为古文(Ancient), 是很得当的”; 第二种“应是真书或正书(Chen-shu)的对音, 即正楷(字体方正, 可作楷模)、 楷书(Chiao-shu)”[5]; 第三种“据推测是‘拓片’或‘拓本’的音写”, “汉语中对书体并无‘拓本’‘拓白’之说, 唯一的可能是, 曾德昭在华时常在‘拓本’上看到这种字体, 因此有此误称。 但是‘拓本’上的字是隶体或魏碑体都有可能。 由于曾德昭还说‘相当于我们书记员的手书, 仅用于告示、 协约、 申请、 票据等’, 当指隶书(Li-shu)无疑”; 第四种“显然可推测为‘草书’(Tsao-shu, Running-grass)。 曾德昭把它称作Sie, 可能是‘写’的音写”。 “但曾德昭把‘写’又与同音字‘谢’相混淆, 说‘意思是谢谢’, 表明他对某些汉字还是掌握得不够。 ”计翔翔还认为曾德昭说草书“有三种极不相同的写法”, 应是指章草、 今草和狂草。[5]147-148
孟德卫(D.E.Mungello)在《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字的起源》中也专门谈到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所说的汉字字体:“第一种字体最为古老, 保存在古代的书籍中, 只有文人认识, 并仅在印玺和徽章上作装饰性文字之用。 这里指的其实是篆书, 在四种字体中, 篆书最显著地保留了汉字最早的象形文字特征。 第二种字体叫‘Chincu’, 据说是书写和印刷中最通用的。 这里指的其实是真书, 也叫楷书, 从公元前约200年起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颁布简化字体为止, 它就一直是最为常用的印刷体。 第三种字体是‘Taipre’, 据说仅用于法律文书和告示, 实际上指的是字形方正清楚的隶书。 第四种字体是‘Sie’, 曾德昭将它描述为一种简化的书写方式, 变化形式极多, 需要特别的研究才能理解。 这里指的实际上是草书, 是文人使用的一种书法艺术形式。 曾德昭描述的是汉字的四种传统字体‘四体’, 可是他的这些译音却让笔者无法辨认。 可能他用的是汉语的一种方音。 不过, 他的汉语口语能力既然这么好, 却总是不能正确地为这些汉字进行音译, 这显然让人不解, 也许语言学水平更高的人能对这些明显的矛盾作出解释。 ”[6]68
张国刚基本采用孟德卫的观点, 认为第一种显然指篆书; 第二种是真书; 第三种或许是“拓本”或“台阁”的音译, 据曾德昭说只用于法律文件和文告上, 可能指隶书; 第四种被称为“Sie”, 或许是“写”或“行”的音译, 曾德昭描述它是一种汉字的缩写形式, 由于变形严重, 需要特别研究才能理解, 指的应当是草书或行书。[7]286陈辉梳理了几位传教士对汉字字体的认识, 认为曾德昭所说的四种字体分别为“篆、 真、 隶、 草”。[8]88-89董海樱认为计翔翔与孟德卫观点相似, 认为他们的分析和推断很有道理, 但第三种字体, 董海樱译为“代笔”[2]119-120。 张海英介绍了何高济、 计翔翔、 董海樱等对这几种字体的研究, 谈到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定这四种字体应该是篆书、 楷书、 隶书和草书。[9]66
讨论者众, 恕不一一列举。 综合各家观点, 目前大多认为曾德昭《大中国志》中介绍的四种字体分别为篆书、 楷书、 隶书、 草书。
三、 对曾德昭所述字体的考证
(一)第一种字体为篆书, 应译为“古字”
曾德昭说的第一种字体英文翻译为“Ancient”*各版本中, 只有英文版本将该词斜体, 首字母大写。[1]33, 西班牙文本为“antigua”[10]51, 意大利文本为“antica”[11]45, 法文译本为“ancienne”[12]48, [13]51, 葡萄牙文本为“antiga”[14]76。 何高济将其译为“古文”, 未见其他学者对此提出异议。 我们认为, 用“古文”来翻译“Ancient”是不准确的, 因为“古文”在汉字学中有专门的含义, 一般指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 译为“古字”更为合理。 各位学者认为这种字体指篆书, 笔者也持相同意见。
(二)第二种字体为楷书, 据《西字奇迹》注音推断
第二种字体“chincu”, 何高济译为“行书”, 孟德卫、 计翔翔、 陈辉、 董海樱等都认为这是“真书”的对音, 即指楷书。 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以语音为线索查阅相关文献。
第二种和第三种的注音, 各版本不尽相同(参见表1)。

表1 《大中国志》所述第二种和第三种字体注音各版本对照表
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没有列出完整的汉字音节表或是对音表, 只是有一些零星的汉字注音。 笔者根据中文译本统计了曾德昭的汉字注音, 仅找到“臣”字注音为“chin”, 未发现“真”或“行”字的注音。 在曾德昭的注音系统(以下简称“曾氏注音”)中, “h”常为送气标志, 如“蒲州(phucheu)”曾氏注音中的“ch”与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的“zh”和“ch”对应, 如“州(cheu)、 察(cha)、 主(chiu)”等。 由此推断“chin”不可能是“行书”之“行”的对音。
根据曾德昭的生平, 1613年到达南京, 最初学习汉语就在南京, 在南京生活三年后到达澳门, 后来在杭州、 嘉定、 上海、 南京等地生活了很长时间。 再从时间上看, 《大中国志》的撰写时间为1637—1641年。 罗明坚-利玛窦注音系统的代表《西字奇迹》完成于1605年, 更加成熟的金尼阁《西儒耳目资》第一版于1626年出版, 因此推测曾氏所用注音系统应与金尼阁系统相似。
但查阅《西儒耳目资》之后, 我们发现曾德昭所用注音系统与其并不一致。 如“日”的注音, 《西儒耳目资》[15]中为“je”, 而《大中国志》中为“gè”。 因此董海樱和陈辉用《西儒耳目资》来查阅曾德昭的注音是不合适的。[2]119, [8]89再比较《大中国志》与利玛窦《西字奇迹》[16]中的注音, 发现两者相似度极高(参见表2)。

表2 《大中国志》注音与《西字奇迹》注音对照表
注:表中《西字奇迹》截图所标页码均出自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三)第三种字体为行书, 而非隶书
第三种字体, 何高济译为“拓白”, 并加注解:“对音不明, 或指摹写古碑字, 用于告示等。 ”[3]43计翔翔推测是“拓片”或“拓本”的对音, 认为是隶书无疑。 孟德卫认为指隶书。 张国刚推测为“拓本”或“台阁”的音译, 认为可能指隶书。 陈辉认为应译为“代笔”, 指隶书。 董海樱“基本认定”可译为“代笔”, 并认为学界基本认定第三种字体是隶书。
我们认为曾德昭所述的第三种字体应为行书, 而非隶书, 在此与各位学者商榷。
首先, 根据原文的翻译(主要使用英文译本, 参照其他各种译本): “第三种他们称为‘taipie’, 相当于我们公证员使用的草体字, 不太常用, 主要用于告示、 契约、 诉状、 政策等类似之物。 ”本段英文译本的第一句为:“The third they callTaipie, and answereth to the running hand used among our publick Notaries.”[1]33这句话英文译本中的“running hand”, 何高济译为“手书”。 这个“running hand”在西班牙文本中为“cursiva”[10]51, 葡萄牙文本中为“cursiva”[14]76, 意大利文本中为“corsiua”[11]45, 均可译为“草写体手书”。 法文本没有与之对应的词。 其实以上各种语言中这个词的意思都是写得很快的字体, 那在汉语中就是行书或草书了, 不可能是隶书。 告示、 契约、 诉状、 政府文书等正式文件也不可能用草书, 那就只能是行书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 曾德昭所述的第四种字体已基本得到公认为草书, 那么第三种就不可能是草书, 而应为行书。 总之, 根据这段话的意思, 第三种不可能是“隶书”。


但这些都不能说明问题。 我们根据民间有称行书为“带笔字”推测“taipie”可能是“带笔”的对音。
再从另一方面来分析这也不可能是隶书。 因为隶书存在于南北朝以前, 在明代时已基本不使用, 告示、 契约、 诉状、 政府文书等一般都不会用隶书。
陈辉认为曾德昭将“隶书”称为“代笔”, “代笔”就是替别人书写文书, 古代最高级的是替皇帝起草文书。 并举例说《无罪获胜》中有十份康熙的御旨是用隶书写的。[8]89那么, 替所有人书写文书都用隶书吗?还是替皇帝写用隶书, 替别人写的可以用其他字体?从这个角度来看, 认为曾德昭将“隶书”称为“代笔”这个证据本身就有问题。
由此, 我们认为, 第三种应为行书。
(四)第四种字体为草书, 作者举“谢”为例
第四种字体, 笔者同意大多数学者的看法, 认为是草书。 关于其中的“sie”, 笔者同意何高济等学者的看法, 认为曾德昭是用“谢”字来举例说明草书有三种极不相同的写法, 但孟德卫和计翔翔都误将“Sie”当作字体名称了。 计翔翔认为曾德昭混淆了“写”与“谢”, 应是对曾德昭的误解。
[1] SEMEDO A.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M].London: E. Tyler for I. Crook,1655.
[2] 董海樱.16世纪至19世纪初西人汉语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 曾德昭.大中国志[M]. 何高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 张西平.16—19世纪西方人的中国语言观[J].汉学研究通讯,2003(1):7-17.
[5] 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 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字的起源[M]. 陈怡,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7]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8] 陈辉.《无罪获胜》语言学探微[J].浙江大学学报,2009(1):85-91.
[9] 张海英.英国来华传教士艾约瑟的汉语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
[10] SEMMEDO A.Imperio de la China[M].Madrid,1642.
[11] SEMEDO A,Relatione Della Grande Monarchia Della Cina[M].Roma,1643.
[12] SEMEDO A.Histoire Vniverselle dv Grand Royavme de la Chine[M].Paris,1645.
[13] SEMEDO A.Histoire Vniverselle de la Chine[M].Lyon,1667.
[14] SEMEDO A.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M].Macau:Dri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1994.
[15]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16] 利玛窦.西字奇迹[M]∥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47-288.
[17] 黄笑山.利玛窦所记的明末官话声母系统[J].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3):100-107.
[责任编辑 湛贵成]
A Study on the Chinese Typeface Names inRelaodaGrandeMonarquiadaChina
LIU Ya-hui
(SchoolofHumanitiesandCommunication,Zhejiang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Hangzhou310018,China)
As a very famous book in the history of Sinology,RelaodaGrandeMonarquiadaChinaby Alvaro Semedo has been of great influence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book introduces four different kinds of Chinese typefaces, but it does not present the written form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only their phonetic symbols are given, which has led to many speculations and discussions, especially to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kinds of typefaces. HE Gao-ji sees the second kind as the running script (Xingshu), but D. E. Mungello, JI Xiangxiang, Cheng Hui, and Dong Haiying see that as the regular script (Kaishu) and the third kind is regarded as clerical script (Lishu). All of these opinions have been widely quoted in academic circles. Based on careful studies, the author, however, argues that the third one should not be the clerical script (Lishu) but instead the running script (Xingshu). The four kinds of Chinese typefaces of Semedo should be the seal script (Zhuanshu), the regular script (Kaishu), the running script (Xingshu), and the cursive hand (Caoshu) respectively.
Alvaro Semedo;RelaodaGrandeMonarquiadaChina; Chinese typefaces; the clerical script (Lishu); the running script (Xingshu)
2017-03-27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6—20世纪初汉字西方传播研究”(15BYY051)
刘亚辉(1976—), 女, 河南洛阳人, 博士, 副教授。
J292
A
1009-4970(2017)04-0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