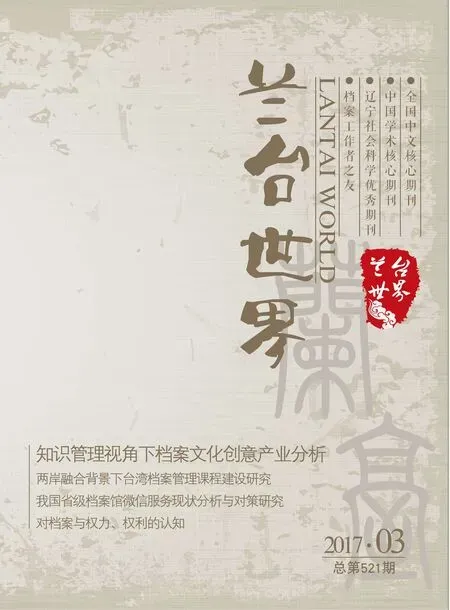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出版事业的特点及其影响
包广宽
(云南民族大学 昆明 650500)
DANG'ANCHUNQIU 〉〉〉档案春秋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出版事业的特点及其影响
包广宽
(云南民族大学 昆明 650500)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出版事业异军突破,发展尤为迅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既促进了云南出版事业的飞速发展,也为中国出版文化事业提供了环境和文化基础。云南出版事业不仅出现了许多较之以前不同的特点特征,更重要的是其在抗战特殊年代所形成的出版文化,对宣扬战时先进思想和文化,呼吁抗日救亡、争取民主思想的运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促进抗战取得胜利获得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出版事业 抗日战争 云南
一、抗战时期云南出版事业的特点
1.官办与民办共举繁荣。抗日战争之前,云南民间已经出现了图书发行机构,如:书堂、书坊、书铺等,但图书发行与出版的主要力量大多隶属于政府机构,民办机构数量有限,出版行业虽然也具有一定规模,但是,这些民办出版机构集出版、编辑、发行工作为一体,分工并不明确,出版事业力量总体还是很薄弱[1]。抗日战争以后,云南的出版事业蒸蒸日上,尤其繁荣,出版机构、政府部门、机关团体、学术机构和个人的出版都蔚为壮观。
据统计,抗战期间,云南共发行图书270种,大约占了民国时期全部滇版图书的51%,官方出版的书籍大约占了44%,而非官方独立出版系统出版的图书大约在37%左右,有20%的为私人自费或者委托待印的书籍。不同的群体和个人,纷纷著书立说,从而改变了云南一直以来的官方出版在出版上的一手遮天而独占鳌头的局面,增强了社会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性,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全面性发展。
2.出版数量巨大,报刊寿命较短。抗日战争时期的出版,无论是期刊、报纸、图书杂志的发行数量,都超过以前。在抗战八年的时间里,仅仅在昆明出现过的期刊就多达150多种,平均每年约有20种新期刊产生,不仅有综合性的期刊,还有专业期刊、行业期刊等等;在报纸方面,昆明的报纸也发行了10多种,超过了以前云南的报纸总数,图书出版也多达270多种。其中,官方出版的关于省情调查、规划和研究的图书就多达108种,占战时云南出版图书的40%左右[2]。然而,虽然出版的数量和规模都较为巨大,但是由于战争和国民政府的审查,其寿命期限却比较短暂,在报纸和期刊上表现得比较突出。抗战时期,战线的移动和转移,报刊事业也为保存实力的需要,很多都是由外地迁入云南地区,或者从外地转到云南重新创办,但是随着抗战的胜利,来滇机构又一次向外迁移,重新转向原来的出版发行地,报刊的出版发行也随着转移。如:《益世报》于1938年12月从天津迁来,在昆明复刊。抗战胜利后,又于1945年12月,返迁到天津。
然而,国民政府严厉的审查制度,致使很多报刊负责人遭到迫害,出版机构遭到破坏,这也是报刊寿命较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个旧的《曙光日报》,由于在1940年6月的副刊《锡花》上发表了《一个不被重视的女人》,一个排字工人在文中加排了“董广希太太偷人”等字,被国民党个旧县长董广希借机搜查报社,最终报社被迫停刊。
据统计,能够查询到其创刊和停刊时间,或者迁移外出时间的报刊中,总共大约100家,存留时间仅为一年的大约就有50家,占了总期刊数量的50%;存留时间在两年以上的大约有27家,所占比例约为27%;存留时间在5年以上的大约9家,占9%。由此可以看出,期刊寿命时间的短暂,可算是历史之最。
3.出版机构与社会机构的互动性增强。抗日战争以前,云南出版的书刊报纸,目的比较单一,或进行单纯的学术研究,或者就仅仅对当前社会信息和问题做简单的发布和社评,或就某一领域和学科阐述自己的观点,出版机构与其他部门各为其利而扮演着自身的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出版事业相关部门和人员,把自己置身于争取民族独立,抗拒外敌的社会浪潮之中,把抗日救亡、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的发展等紧密联合起来,增加与文化教育机构、政府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互动性交流与合作。面对抗战时期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与阶级斗争激烈的情况,他们把出版物作为社会交流和思想宣传的工具,积极宣传抗日活动,介绍和传播先进文化思想,针砭时弊,痛骂国民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汪伪政权的投敌卖国政策等等。出版事业部门积极与文化教育机构相互交流与合作,采取形式多样的方式,进行着阶级斗争与抗日活动。出版机构与社会机构互动性的增强,尤其表现在出版物的来源广、范围宽这一点上。从出版专业机构来看,不仅出版系统在出书,其他的机关团体、教育科研部门和私人自己也都在出书。
另外,还有出版机构与高等学校协作发行书刊。据记载“自大学研究机构相继西移后,除重庆成都之外,昆明实为学术中心”[3],为了训练高级社会学研究工作人才,视云南省社会情形起见,国立云南大学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合组社会学研究室。后来,刊物中的部分文章被翻译为英文,编入《太平洋学会报告》、《哈佛大学社会丛书中》。此外,在云南地方政府资助下,还成立的“西南文化研究室”,开展西南民族、历史、政治的调查研究工作,出版了两种学报、六种丛书和许多的专门调查报告[4]。最后,作家、教师办报刊,也是抗战时期出版事业与社会互动中的一大特点。如1943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昆明建立了第一个省支部后,为了打开舆论新局面,发挥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作用,出版了《民主周刊》,而民主周刊的委员当中,绝大部分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授,其中包括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等等。这些,不仅促进了教师、作家与时代的联系,也促进了出版与文化、教育文化机构的结合,活跃了报刊的版面。
二、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出版事业的影响和作用
经过数年的洗礼和磨砺,抗战时期的出版事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出版系统,对宣传战时先进思想和文化,呼吁抗日救亡、争取民主思想的运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促进抗战取得胜利获得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1.宣传先进文化思想,抵制国民政府的文化专制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云南的出版发行事业,采取了公开、秘密、合法与“非法”的众多手段对国民政府的法西斯文化专制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斗争,对赢得民主的最终胜利和争取出版自由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宣传进步文化,在云南传播马列主义思想,这是云南出版事业在一个特殊年代给云南文化建设和革命发展做出的特别贡献。在云南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后,积极开展活动,一些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创办了众多的书店和教育出版社等等。如:邹韬奋的生活书店,艾思奇、黄洛峰的读书出版社,钱俊瑞的新知书店及华侨书店,孙起孟的进修教育出版社,李公朴的北门书屋等。他们都宣传团结御辱、抗日救国等进步思想,传播民主爱国思想,宣传进步的文化,以弘扬民主革命为目的,他们出版发行的以及销售的出版刊物,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很多学生、工人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在读过这些书刊之后,树立了先进的思想与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他们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在昆明发行的《新华日报》、《群众》等革命进步报刊,直接推动了革命思想的进步发展。这些先进报刊和书籍出版,受到了云南各界人士的欢迎和重视,他们积极寻求购买这些书刊,从中汲取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的知识。
特别是在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会议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还连续发表了演讲,直接攻击共产主义,他要实行不限“军事”而付诸武力的“军法之治”下的“军政”,还强调要国民政府来管理一切,达到“以党治国”和“以党建国”的最终目的。所以,在这种“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下的国民政府,在文化思想领域直接实行了专制性的法西斯统治。
除了实施这些“反共”文化专制政策以外,国民政府还直接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进攻,要求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更为严重的是,在昆明地区,也出现了陈铨、林同济等人的“战国派”,以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和斯宾格勒·汤比的历史形态学为理论依据来否定历史的发展规律,来鼓吹人类的历史永远是战争的历史,歌颂权利的意志和英雄豪杰与天才[5]。面对如此严厉的顽固政策和思想,《云南日报》《南风》等都组织了文章,对这些言论给以有力回击,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判,在持续而广泛的声讨中,《夜玫瑰》被迫停演,《战国策》也停刊。中央南方局派遣马子卿来到昆明,向云南党组织传达党的精神,并指示在国统区开展宣传工作的活动,比如:利用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总理遗嘱》,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言论,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宣传党的主张。
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要求下,地下共产党员在《云南日报》和其他的报刊上,利用合法的形式,宣传反法西斯活动。这些反对国民政府的出版言论和舆论的发表,不仅仅使得出版事业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还批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文化统制政策,从而壮大了文化战线的队伍和力量。
2.宣传积极抗战,争取扩大民主战线和抗日战争的阵容。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宣传问题上,要实行《总理遗嘱》,唤起民众,一致抗日。实行民族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达到国民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把宣传抗日战争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抗战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对抗战的宣传,不仅鼓动了人民的抗日士气,对团结大批的革命人士起了信息输送和革命宣传的纽带作用,同时也给日本侵略者制造了思想和舆论压力,打击了日本侵华的嚣张气焰。
早在抗战爆发前期,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就在《云南民国日报》发表讲话:“凡我国在此安危绝续之守,务须无远无近,无老无幼,应以最大的决心,准备为祖国牺牲,以求我国家民族五千年之历史”,动员云南人民的抗战士气,把全部的精力和力量贡献给中央,贡献给国家,与日军作战。也有的把宣传抗日战争,救亡图存作为办报的唯一理念和目标,如龚自知为《人民日报》写社论《唤起民众与打开出路》的时候就说:“我们的革命导师中山先生的遗教,便是我们出路的指南。唤起广大民众,共同一致向前奋斗才会有出路,中国才会得救,这是我们的信念,这是本报致力的唯一目标。”
后来,还发表了社评做了更明确的说明,把传达地方消息,疏通国内声气,结合学术思想,转移社会习俗作为当前的新任务。他们在传达各地消息的同时,来扩充人民的见闻,从而增进人民对抗战的认识,达到沟通人民意志,活泼人民见闻和思想的目的。
除了对抗战的鼓舞外,还有对战争情况的详细报道,以便让云南人民及时掌握最新的战况,适时调整抗战策略。正如《中央日报》昆明版在发刊词中所说:“在争取最后抗战胜利的阶段中,我们认为消极悲观和盲目乐观,同是病态现象,我们的报刊一方面报道了解的一些真实敌情,养成健全的抗战心情;另一方面想将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介绍给国人,期待对抗战工作聊尽绵力,以求心之所安。”
3.促进了云南出版事业近代化的进程。抗战爆发以前,云南的出版事业开始步入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出现了最早的报纸《滇南抄报》和铅印机构“云南铅印处”。然而,云南的现代化起步,却要比内地发达地区晚了八十多年。在抗战之前,云南的报纸也只剩下《云南民国日报》《云南日报》《云南新商报》几家,新闻事业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在所有的数十家印书馆中,设备简陋,大多拥有的是石印技术,出版事业工作人员数量较少,最多的一家“文雅堂”的工作人员也只有十多人。况且发行单位还分散,实力良莠不齐,不成规模。抗战爆发后,云南昆明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大量的高等院校、印刷厂、技术专家、著名学者等迁到昆明。顿时,云南的出版事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而发展起来。出版社、书店、书摊,聚集增长,云集在昆明的大街小巷。出版发行机构中,有百家的印刷厂,已经普遍使用了铅印技术、石印技术和铜锌版技术,甚至还出现了胶印设备和技术。
在图书期刊的出版上,出版单位众多,出现了股份公司、合资经营、独资经营和国民党官办等性质的出版机构和单位;在出版的层次上,有出版系统、机关团体、教育机构和私人等,形成了多渠道、多途径的出版方式。经过抗战八年的努力,云南的出版事业,用几十年的时间,经过了跨越式的发展之后,逐步赶上了国内发达地区历时130年的现代化进程[6]。
[1]宣勤.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历程:1900—1950年代,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2]宣勤.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历程:1900—1950年代,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3]刘兴育.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史略,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4]毛立红.抗战时期国家高等教育与云南地方互动研究,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5]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6]宣勤.云南出版业的早期现代化历程:1900—1950年代,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G239.29
A
2016-10-15
10.16565/j.cnki.1006-7744.2017.03.27
包广宽,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出版事业、信息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