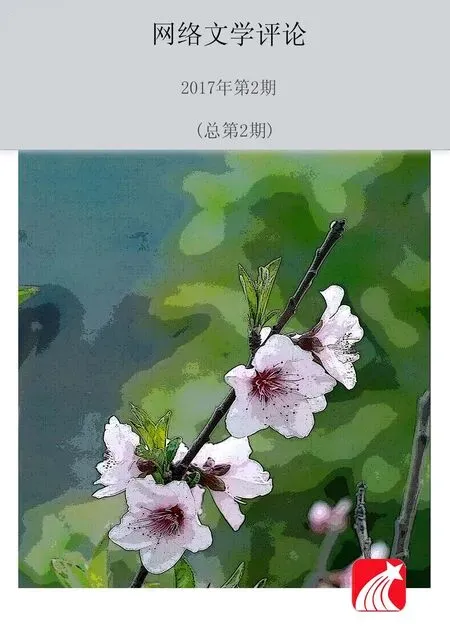既无所欢,何乐可颂?
——评阿耐的《欢乐颂》
文/唐小祥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目前围绕阿耐网络小说《欢乐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种趋向:一种把它理解为青春励志小说,另一种视之为“现实主义的颂歌”或者“新自由主义的讴歌”[1],还有一种把它看作折射“中产阶层”焦虑的可视化文本[2]。第一种观点在豆瓣读书上颇为流行,后两种观点则主要源自学术界。我的讨论也就从这三种流行的观点入手。具体来说,它包括这样一些质询:《欢乐颂》通过描写五位都市女性的职场和情场经历,“激励”着怎样的人生“志向”?《欢乐颂》里“一地鸡毛”式的现象学白描,是否抵达了“现实主义”(既是原始意义上也是经典意义上)的高度?《欢乐颂》里连自身温饱尚未解决的樊胜美、邱莹莹和关雎尔能否归属“中产”之列?如果说它讲述了一个中产阶层的成长史、辛酸史、暧昧史,那么最吸引读者目光的安迪和曲筱绡,除了作为中产渴慕的物质范型或者资本批判的靶子,是否还有别的叙事功能?经由此番层层追问,从而参与进作为方法的“现象主义”“自由”“平等”等现代社会性道德的自然化与幻象化,未完成的“现代性”与“人的文学”等一系列意味深长的议题,展示网络小说承载历史经验与复杂现实的丰富可能性。
一、作为“方法”的“现象主义”
从一个小细节谈起。小说叙事伊始,安排了两场具有楔子功能的“谈判”:谭宗明劝安迪回国,曲母劝曲筱绡回国,这才有了五位都市丽人在欢乐颂小区的比邻而居,从而给叙事提供了一个公共的生活场景。安迪回国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弟弟,换言之,是为了“亲情”,曲筱绡回国是担心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败光家产,也是因为“亲情”。如此情节安排,很可能隐藏了某种叙事玄机。叙述者使出“中国式谈判”中最重也是最后的筹码——亲情——来关联两个原本互不相干人物的意图,既反证出现实中两类人“老死不相往来”的真相,也透露出小说叙事潜在的无奈和危机:正是这个细节,规定着《欢乐颂》是一部“现象主义”而非“现实主义”小说的性质。
从叙事内容或者要件来看,《欢乐颂》几乎囊括了网络小说的所有重要符码,既有痞子蔡《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桃色事件,也有李可《杜拉拉升职记》的商界风云;既有石康《奋斗》的青春迷惘和混乱爱情,也有郭敬明《小时代》的物欲狂欢和消费盛宴;既有权力与资本的共谋双赢,也有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问题群集;既有“居,大不易”的流行话题,也有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因此,“接地气”“富有时代感”“很犀利很现实”“一语戳中”,是网友最直观的阅读感受,也是它现实主义品格的文本依据。我的疑问在于,小说中人物、事件和场景的现实性,在叙事逻辑上必然会导向一种“现实主义”的叙事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不能不回到常识,回到现实主义的源头。
经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发展,人们头脑中的物质观念越来越浓,金钱成为人的唯一尺度甚至宗教,形成对人的新一轮压迫;而启蒙运动所承诺的价值(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等等)却迟迟不临,浪漫主义式的美化和逃避又无济于事,因此只有用更冷静的眼光去探照社会,从更现实的角度去思考人的命运和改善人的处境。所以,除了恩格斯所说的“细节的真实和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以外,现实主义小说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的批判性,在于它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上下求索的坚毅。人们所熟知的经典现实主义作家,比如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无一不是如此。《欢乐颂》对五位都市女性的描写,既未赋予一种批判的眼光,也没有对她们命运遭际的根源作深入的考察与反思,只是停留在“现相”的平面呈示上,停留在对流行话语的通俗注释上。人们读完后,不外乎是感叹海市有那样的五个女性,她们各自的经历都是那样的亲切,宛如身边的同学同事,感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4];不外乎是进一步确信社会已经板结,阶层已经固化,确信没有金钱的爱情必将无所附丽,无论是职场还是情场都铺满着规则与套路等等。除此之外,还能收获些别的什么呢?
从文学史上看,这种毫无深度的零度叙事,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只不过,《欢乐颂》在这条路上越滑越远,毕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和池莉的《不谈爱情》还带着反讽与自嘲,方方的《风景》和刘恒的《狗日的粮食》还带着生存的沉重与荒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坚持认为《欢乐颂》根本不具备现实主义小说的品格,充其量只是一种“现象主义”的展览。在这里,现象不仅是叙事的主要内容,而且是叙事唯一的方法和动力,并以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据不完全统计,“对话”占小说篇幅90%以上)。与绝大部分网络小说一样,小说也采用了线性顺序的结构框架,从安迪、樊胜美的回国,樊胜美、邱莹莹、关雎尔爱情和事业的双面困窘,经过互相启蒙或贵人相助,到结局时安迪不负众望嫁给了包亦凡,曲筱绡花落赵医生,樊胜美的家境好转兼事业有成,邱莹莹淘宝店的生意有了起色,关雎尔的文艺范渐褪且日益成熟,每个角色的命运都有了转机,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了一份安排,艰难漫长的“苦斗”终于迎来了“光明的尾巴”。我想,作为商界女强人兼财经作家的阿耐,作为拿过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而且懂政策又懂生活的流行小说作家,恐怕不至于如此地天真和乐观,她自己对这个传统小说大团圆的结局恐怕也不会太满意;但既然无法把叙事引向一种深入思考,又不能出示一种纵深的远景想象,除了交代表面浮游着的层出不穷的现象以外,还能如何煞笔呢?
二、现代社会性道德的自然化与幻象化
所谓“现代社会性道德”是与“宗教性道德”相区分而言的,它不同于后者超越人类的上帝(基督教)、理性(黑格尔)、天理(朱熹)或良知(王阳明),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历时古今而不变的绝对总体性,而是指在现代社会人际交往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标准,“平等”“自由”是其最主要的范畴[5],也是《欢乐颂》涉及的两种主要价值观念。
小说将五位女性共居于欢乐颂小区,实际上先在地预设了一个价值判断,那就是她们都是平等的,都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和自由,尽管从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到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明显存在轻易不可弥补的鸿沟。这在今天几乎已经成为公认的价值观念,在实践过程中也充满着正能量和召唤力,甚至还占据着道德的高地。所谓“再贫瘠的土地也渴望生长,再底层的人生也有梦想”,很少会有人站出来质疑它。我这样表述,并不是要否定平等、自由这样一些基本价值的公共性或普世性,也不是要人为地制造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和隔阂,更不是否定普通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的追梦权利,而是想要指出它们的被自然化和非历史化。
历史地看,“平等”“自由”这类价值绝不是先验地存在或者从天而降的,而是经过启蒙运动以来持续不断的斗争才最终获得其合法性的。所谓的“天赋人权”“人生来平等而自由”,并非真的有什么超验的“天”在赋予经验的“人”以现实的“权利”,并非每一个人一出生便在形式、程序和实质上都是“平等而自由”的,它只是启蒙思想家出于对理想社会的想象而“人为”规定和建构起来的基本契约,宛如儒家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假设它们存在,而不是现实地已然存在。而在《欢乐颂》里,它们被自然化和非历史化了,缺乏起码的自觉和自省,这也是当前文学创作(不仅仅是网络文学)在价值判断上呈现的普遍误区。邱莹莹、樊胜美和关雎尔首先要把自己设定为与安迪、曲筱绡是平等的存在,并且自信通过个体的不懈奋斗,一定能够鲤鱼跃龙门,然后才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将后者设定为追求的榜样与启蒙的导师。但经过现实的敲打和磨炼,即使再乐观的人,恐怕也不可避免地要觉悟到这种平等和自由的虚妄。
英国作家哲斯脱敦的小说《布朗神父的天真》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引用在这里,颇能道出平等问题的实质:“一位年老的夫人带领二十名仆人住在一所寨堡里。另外一位夫人来拜访她,她对这位来客说:——我始终是孤零零地一个人在这里,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医生来告诉她,这个地区发现了鼠疫,有传染的危险等等。这时她又这样说:——可是我们这儿的人很多呀!”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也引用了这段话,并且加以发挥,得出了两个结论,认为人们的平等感根源于宗教和生物学的错觉,前者的思路是:上帝是父亲,而人都是他的子女,因此人人平等;后者的逻辑是:在生下来的时候,人人都是赤身露体,因此人生而平等。[6]由此观之,平等并非永恒的范畴,它有时仅仅是一类话语策略。而所谓自由的泛滥在今天所带来的混乱,人们已看得比较真切了。比如“新闻自由”变成媒体霸权和宰制,多元并存变成了同质单一,个人自由变成了人际冷漠。
正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也有自己追求平等与自由的反抗和求索之路,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已然实现的价值事实去“拿来”,也不是把它当成一种“天之经,地之义”的神圣原则来信仰,最终通向一种规定好的“奴役之路”。也就是说,只有首先自觉到这种不平等、不自由,才会产生清醒的自我意识和规划,才能避免因创伤性经验过密而坠入迷失和虚无之谷。《欢乐颂》有意缓和了不同阶层在平等和自由等价值维度上的差距,这突出地表现在空间设置上:在社会公共空间中,樊胜美、关雎尔和邱莹莹与安迪、曲筱绡分属于现代公司这种新的科层制中的不同层级,几乎难以产生交集,更别说友谊;但只要一回到“欢乐颂”这个日常生活空间,她们彼此之间的各种区隔便瞬间瓦解,外在身份和地位的标签在其乐融融的人伦和身体话语面前似乎完全失效。叙述者甚至不惜借安迪和曲筱绡在爱情上的缺失,来营造一种虚幻的平等感。不过这种平等感的生成却遮蔽了两个空间事实,一个是住房的分配,樊胜美、关雎尔和邱莹莹合租一间房,安迪与曲筱绡却各自住着一套房;另一个是工作空间差距的抹平,在小说描写中,5位女主人公都出入于海市摩登的办公大楼,重要的是“摩登”,至于樊胜美特别是关雎尔和邱莹莹,与安迪、曲筱绡工作环境和待遇的天壤之别,至于那些真正的生产空间,比如一线工厂昏暗嘈杂的车间,偏远郊区荒芜萧瑟的工地,等等,都被刻意淡化、隐形和拉远了。人们不知道牛仔裤和打火机是怎样做出来的,不知道特仑苏和蛋黄派在流水线上是怎样压榨着打工仔的身心,甚至连包亦凡带安迪去考察他的家族企业,参观的也是高大上的现代化研发中心。哪怕是意识到日常生活对政治的强大侵蚀力,也免不了不敢“直面惨淡人生”的嫌疑。作者据说是宁波某企业的高管,此刻眼里自然看不见基层员工的挣扎和血泪,但“高管”不是生下来就“高管”(部分家族企业的高管除外)的,也曾体验过“基层生活”,自然也深谙那种辛酸和卑微。
那为什么在文学想象中要千方百计地隐去这些辛酸的经验呢?是因为在特别讲究出身的文化传统中,害怕不光彩的过去,有损此刻的颜面,耽误将来的路途?还是因为要制造一轮平等自由的幻象,来迎合大众文化的消费逻辑,契合流行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欲望投射,好抚慰那些在现实生存中失落的魂灵?进而言之,如果过去(历史)可以背叛,初心(自我)可以遗忘,那么未来又植根于何种地基之上?退而言之,“出身”在何种范围、意义和程度上足够“决定”人的命运,过去是否可能或应该被彻底遗忘,如何才能保证它不像个定时炸弹一样,于瞬间引爆今天的“美好生活”?安迪即使经过美国文明的“漂白”,也仍然难忘儿童时代在福利院的屈辱经历,难忘失踪的弟弟、发疯的母亲和一去不返的父亲,樊胜美经过现代都市文明的“调教”,还是摆脱不掉老家(自己的过去)的牵绊,这种对历史的焦虑,恐怕不仅仅是作者个人尚未解开的心结,也是当代文学长期以来的某种存在命运吧?
三、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者“人的文学”
回到本文开篇提及的质询。《欢乐颂》激励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志向”,是席不暇暖、宵衣旰食以便当上主管乃至高管那样的CEO,还是如《厚黑学》或者《职场女性成长指南》所“教诲”的那样,善于抓住每一个“上位”的机会,不惮于使出一切有益于“往上爬”的伎俩,最后跻身安迪、曲筱绡之列。无论是哪一种,恐怕都算不上真正的“志向”吧?我的立意不在批判作者的价值观迷思,更不想也无权指责有的人把它们奉为生存圭臬和人生追求,而是要从《欢乐颂》文本内部的罅隙,来检讨文学的“现代性”或者“人的文学”这样一些宏大到无边无际、令很多人一听到就“反胃”的老掉牙的问题。
从五位女主人公的职场和情场遭际看,人们可能会自然联想到两个观点:经济决定论和出身论。前者至少有两层内涵,一层是什么人跟什么人交往,樊胜美与王柏川,邱莹莹与白主管,关雎尔与应勤,安迪与奇点,包亦凡,曲筱绡与赵医生,五对门当户对的情侣搭配,说明一个人的经济条件先在地决定他/她的恋爱和婚姻对象,折射出不同阶层间的交往成本和“翻身”的难度。另外一层是什么人过什么生活,樊胜美、邱莹莹和关雎尔的收入除开衣食住行就所剩无几,因此周末和假期只能蜗居在逼仄的合租公寓,靠睡觉、斗嘴,玩游戏、看电影来打发,而安迪和曲筱绡的周末不是约会就是出差,不是在豪华酒店觥筹交错就是在商业招待上翩跹起舞,显然分属“两个世界”。“出身论”的意思是,任凭樊胜美、邱莹莹和关雎尔怎么拼命奋斗,怎么坚持不懈,也无法过上安迪和曲筱绡二人那样的物质生活。
真是一个绝妙的反讽:最传统的观念和命题,最古老的价值和判断,竟然重又在后现代的都市空间里上演,人们竟然不以为奇反以为常!这就是我马上要谈到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者“人的文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中国当代读书人耳熟能详的命题,人们原本以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洗礼,早已被从各个侧面受到了攻击和颠覆,流行和非主流的话语也早已弃之如敝屣,却在今天再次成为大众“主流”的观念,冥冥之中似乎回答了特里·伊格尔顿的那个设问:“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7]。“出身论”在某些时期曾经让某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今天却从人们的脑袋和口齿间,像一句口头禅那样随意冒了出来。当反思现代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在全球人文学院成为最显赫话语的时候,当“历史决定论”和“客观规律性”像一场“瘟疫”那样,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欢乐颂》里的主人公又在重新演绎着存在与意识的辩证法,人的价值和尊严、个体的主体性和精神自由,在攀比炫耀的“消费社会”里重又被密封于坚硬的黑箱之中。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设计”[8],周作人在“五四”时代力倡的“人的文学”[9]。之未完成之不彻底,在《欢乐颂》里是多么的触目惊心。
那么《欢乐颂》文本内部的矛盾和罅隙,也就显而易见了:一方面主人公享受着最现代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一方面他们的脑子里又在运转着最“封建”最陈旧的思想观念,行动和思想相处两端互相掣肘,形成一种奇怪的混合,更诡异的是她们自己连同叙述者在内,都没有自觉到这种“奇怪”所在,反而继续着这场没有地图、不知所终的旅行。即使聪明、富有如安迪、曲筱绡者,在这场人生之旅上,也是一样的迷惘而盲目,根本无力去启蒙或者引领樊胜美、邱莹莹和关雎尔之流,“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不过是梦醒时分偶尔发出的叹息。从这点看,《欢乐颂》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一样,也是一种“失败者叙事”,实在毫无“欢乐”可“颂”。由此也引发出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在“人活着”大于“如何活”“为什么活”“活得怎样”的文化境遇中,身处“便无风雨也摧残”的“艰难时世”,启蒙文学还是否必要,何以可能?现代性是否过早终结,又如何往前推进?后现代是资本的解毒剂和装饰品,还是一种历史的回光返照,或者如张曙光所说,是我们“在痛苦中进行的构想”?(《岁月的遗照》)20世纪以来的文学教育包括新世纪以来的素质教育是否有效,文学是否需要重新规划和描述?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得到仔细梳理,远非本文所能承担。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用“现实主义”“现代性”和“人的文学”等一套似乎已经“老掉牙”的批评范畴来讨论作为网络类型小说的《欢乐颂》,并不是没有充分考虑到网络小说与传统纸媒小说在生产和传播方式以及话语和想象方式上的深刻分歧,而是这些概念依然有效。《欢乐颂》仍然是欲望的象征性补偿和想象性实现,仍然深深地嵌入历史与现实之中,内蕴着丰富的时代信息,远不是单纯的“娱乐”“消费”所能涵盖。我们既没有必要固守现代文学以来的那一套“文学知识”,也没有必要为了分歧而分歧,因为它构成了当下小说创作版图的很大一个区域,因为它吸引了很大一部分青少年或中老年读者,就刻意引入另一套读解的符码系统,搞什么网络小说特殊化。说破天,网络小说还是“小说”,不过是类型小说罢了。这既是本文讨论《欢乐颂》的方法论前提,也是笔者对某些过于强调网络小说特殊性的批评的一个回应。
注释:
[1]张慧瑜:《一曲中产的“欢乐颂”》,《南风窗》2016年第12期。
[2]吴畅畅:《欢乐颂:一阙现实主义的颂歌》,《上海艺术评论》2016年第4期。
[3][德]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
[4][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成仿吾译,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页。
[5]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7页。
[6][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7][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8][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9]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号。
——观电视剧《欢乐颂》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