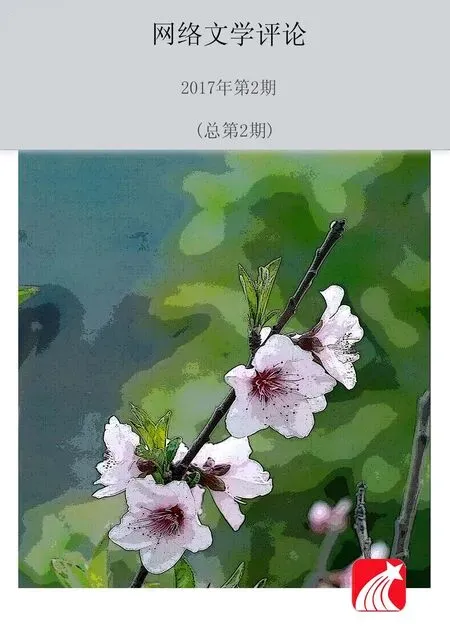语言的幻觉
——《明朝那些事儿》第1部论析
文/黎保荣 张佳丽
《明朝那些事儿》是中国明史学会会员、青年历史学者当年明月创作的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因其拥有专业性和创新性书写的优点,且迎合了当下读者对“国学热”“历史热”的认可和追崇,自2009年完稿出版后,该书先后斩获当当网“终身五星级最佳图书”、“卓越亚马逊畅销书大奖”、2007年—2011年度系列畅销书第一名,并多次获得“新浪图书风云榜”最佳图书等荣誉。小说亦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引起诸多学者从语言特色、思想艺术、小说笔法等方面对文本进行研究。本文尝试以文史交错的“文史互证”理论为切入点,论析《明朝那些事儿》第1部中的语言幻觉。
一、历史的文学性与文学的历史性
“对历史而言,文学不是次等的被动存在物,而是彰显历史真正面目的活生生的意义存在体。”[1]182新历史主义将文学视作一个符号象征系统,这一系统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来解读历史,并赋予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事件观念层面上的意义。蒙特洛斯把这种文史的互相交错分为“历史的文学性”与“文学的历史性”两个方面,“历史的文学性”即历史需要被文学选择性地阐释,“批评主体根本不可能接触到一个所谓全面而真实的历史,或在生活中体验到历史的连贯性,如果没有社会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作为解读媒介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进入历史奥秘的可能性。”[1]185“文学的历史性”即“个人体验的文学表达总是具有特殊的历史性,总是能表现出社会与物质之间的某种矛盾现象。这些现象见诸所有的书写模式中,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作品,而且也包括研究作品的文本环境。书写模式中的历史的、社会的、物质的情景,构成了所谓的文学的历史性氛围。”[1]185《明朝那些事儿》作为兼备明史的文学性和小说的历史性的文本,正身陷这种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幻觉中。当年明月是明史研究者,创作时坚持“忠于历史”的原则,他在“引子”中这样写道,“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是描写正史的,资料来源包括《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余种明代史料和笔记杂谈,虽然用了很多流行文学的描写手法和表现手法,但文中绝大部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甚至人物的对话都是有史料来源的。”[2]7他甚至在文中好几处对话后面附上“注意,这个是实数”[2]47“深入漠北,无所得,遽班师,何以复命。”[2]244“诏内外狱无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2]273之类的说明或原句来标示文本的“正史”属性。除了以真实的史料为原料外,当年明月的创作亦辅之以小说的笔法和对人物心理的主观分析,由此又产生种种想象和虚构。这种将历史考据与小说的审美想象结合起来的写作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梁启超所提倡的“以小说来证史”的“文史互证”的研究范畴。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提出,“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3]如神话小说《山海经》虽有荒诞虚妄之嫌,其真实的历史性却不容小觑,史学家们确能从中挖掘许多贵重而神秘的史料;再如曹雪芹的《红楼梦》文本故事虽属虚构,但却能反映康雍乾盛世及当时上层社会的文化生活状态,其对贵族官僚大家庭盛衰历史的描写,也揭示了封建社会日趋腐败和衰落的危机。明史学家出身的当年明月亦将《明朝那些事儿》定位为“意义增殖”的文本,欲通过小说的笔调来满足读者阅读的审美体验,进而让读者达到接近历史本相的目的:了解明朝重要人物的命运、揭露官场政治谜团、理清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变等。《百家讲坛》主讲人毛佩琦更是在小说的序中给予了文本很高的评价:“明月的写作不仅笔锋活泼幽默,而且加进了自己的感悟,这就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也拉近了古人与今人的距离。布帛菽粟,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古人原无异于今人,真能深入古人的情境和内心,历史就活了起来。”[2]5
客观而言,当年明月确实兼备文史皆通的学术修养和文史沟通的研究能力,然而《明朝那些事儿》中文史互证的写作模式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历史与文学的范式差异,从而使文本陷入了语言的幻觉中。正如王阳提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视角关系在性质上属不同类型,不可互相转换。历史叙事要求在实证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建立史实‘真实性’的分辨尺度, 而文学仅在形象性和直观感性的前提下谈论‘本质’的‘真实性’标准。两者之间关于‘真实’概念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因而在使用范式方面不可通约。”[4]文学中所阐释的历史情境往往不是历史真相,这亦是文史互证方法的局限所在。私以为,最好的方式或许是让历史的归历史,让文学的归文学,如将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看作历史读本,将元末明初罗贯中以其为史料支撑所著的《三国演义》看作文学读本。
毕竟历史言说与言说历史不同。人们言说历史,千言万语,各持己见,滔滔不绝,文学言说历史,故事与人物粉墨登场,最终却不过是语言的狂欢与语言后的空虚。如中国原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最初都只是在人们劳动的过程中口头流传,多因时代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内容或形式的变异,最终经过漫长的时间用文字记下的一鳞半爪已经难以认定为其原貌。所以,只有建立在史实与史笔(实事求是的笔法)的基础上的史识,才能真正洞察历史。然而,当所有历史都成为文学之后,文学也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属于历史的文学部分。文学想超越历史,最终亦超越不了历史。此外,历史本身的言说就是不言说,大音希声,以历史事件与人物来展示,以沉默来默默承认,或者以沉默来冷冷嘲笑。
二、想以戏谑化的语言来重建历史,但历史拒绝重建
与正襟危坐、刻板庄重的史书典籍不同,当年明月在对明朝近三百年历史的书写中投入了不少个人的心灵体验,同时赋予诙谐风趣的笔法,迎合了网络文学的趣味性,亦成就了文本:《明朝那些事儿》最初在天涯社区“煮酒论史”板块连载时就颇受读者喜爱,曾创下2000万的点击率纪录,出版后又销量过千万,几年间成为人尽皆知的“时髦书”(所获荣誉在此不再赘述)。然而,当年明月对历史本相如此通俗化的解读,却不可避免地使文本出现语言的幻觉的第二个方面:想以戏谑化的语言来重建历史,但历史拒绝重建。
其一,语言口语化改变不了历史的沉重。在《明朝那些事儿》中,当年明月采用了许多趣味横生的口语化语言,以此来消除文本的庄重,可这样的书写却仅仅能够拉近与读者的阅读距离,根本无法改变文字背后沉重的历史。如“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小伙子身体棒,精神劲儿足,饭量大,一顿能扒好几碗,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在他看来,把丞相赶回家,也不过是多干点活,自己累点,也没什么。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2]194乍一看是作者对朱元璋心系国家的调侃式赞美,其实却是朱元璋为了独揽政权,步步为营,最终废除丞相制度后不得不啃的“苦果”。而这一皇帝和丞相之间权利制衡关系的解除,又是以诸多生命的牺牲为代价的。除了处死胡惟庸三族以外,朱元璋还利用“胡惟庸案件”,将专横跋扈或对专制制度有威胁的文武官员、士族地主都陆续列为胡党处死或抄家。朱元璋甚至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诛杀曾功居第一的韩国公李善长三族七十余人。“从洪武十三年(1380)案发,连续查了好几年,被杀者超过一万人。”[2]191
再如“那举人怎么才能当官呢?很简单,当官的人死了,你就有机会了。所以你如果在明朝去参加某位官员的追悼会,看到某些人在门口探头探脑,面露喜色,要不是和这家有仇,那一般就都是举人。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范进同志考中举人后会发疯吧,换了你也可能会疯的。”[2]164“在说下一关之前,我们要介绍一下科举考试的考场,当时的考场可不是今天光线明亮的教室,还有一大堆家长在外面抱着西瓜等你。明代考试的考场叫做贡院,其实从结构环境来看,可以称其为牢房。贡院里有上万间房间(大家可以估计一下录取率),都是单间。有人可能觉得单间很好,别忙,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单间,这种单间叫做号房,长五尺,宽四尺,高八尺……考生在进去前要先搜身,只能带书具和灯具进去,每人发给三支蜡烛,进去后,号门马上关闭上锁,考生就在里面答题,晚上也在里面休息,但由于房间太小,考生只能蜷缩着睡觉,真是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2]164这两段话出现在作者介绍明朝科举制度的部分,虽以诙谐幽默的口语化语言呈现,却也掩盖不了读书人为仕途备考之枯燥,生存之艰辛,条件之恶劣等史实。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分别是院试、乡试和会试,通过会试的精英有机会参与殿试,最后榜上有名的三甲才会被派任低级的官职。然而历经千辛万苦走到这一步,后来朱元璋又给学子们设置了一道最困难的关卡:八股。八股文拥有三大限制:形式限制、思想限制、出题限制,书写难度极高。诸多弊端亦导致许多选出来的英才都只是于现实社会无用的“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2]171八股文的推行甚至是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就曾痛斥:“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5]
其二,语言现代化改变不了历史的过去。《明朝那些事儿》中不乏用现代的文化诠释古代的内容,首先是现代表格的运用,如小说开头用档案和漫画的形式介绍主人公朱元璋的血型、学历、家庭出生、生卒年、社会关系、座右铭等基本信息,有趣的是朱元璋生平的主要事迹以他在大山之下俯视一只小狮子的模样为背景图,似乎象征着他的神威英武和对皇权的志在必得;第106页,作者用图表从起因、阵营、结果三个方面来对鄱阳湖之战进行战况分析。如此,朱元璋和陈友谅为何决战,朱营为何以区区二十万兵力导致拥有六十万兵力的陈营全面崩溃,以及朱元璋在军事领导上有什么天赋等问题的答案便一目了然;再如第151页,作者附上六幅图,分别对应六个年级来标明“名将是怎样炼成的”,从理论学习到实操训练再到心智的锻炼,最终得出了“所以名将之路是一条艰苦的道路,非大智大勇、大吉大利之人不能为”[2]154的结论;还有第166页,作者用表格介绍明朝严苛的科举制度、第195页用图表对比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各大机构权力的变化、第257页用表格概述蓝玉案的始末等等。这些以图表进行说明的写作形式使读者在阅读时能更为直观地联想起文字背后的历史形象和情境,同时更易理解小说中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给读者的阅读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此外,小说中还有不少现代语言的运用,加强了历史的现场感。如“在游方的生活中,朱重八只能走路,没有顺风车可搭,是名副其实的旅行”[2]18,“顺风车”“旅行”等现代用语有助于读者体会朱重八化缘之艰辛;再如作者在介绍朱元璋废除丞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一职时,“他们无孔不入,无所不管,他们不但管理国家大事,还管理皇帝的私事,他们不准皇帝随意骑马游玩(正德),不准皇帝吃伟哥(隆庆),不准皇帝选择自己的继承人(万历)……朱元璋来到历史的商店,想要买一块肥皂,历史辩证法却强行搭配给他一卷手纸。”[2]196在这段话中,作者将皇帝出巡改为“骑马游玩”,热衷春药说成“吃伟哥”,“商店”“肥皂”“卷手纸”等今词古用的写作策略更是直接拉近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令人在忍俊不禁中读懂历史;还有“在战斗电影中,到这个时候,经常会出现以下的场景:一个战士满脸愤怒的表情,对部队的指挥官(一般是排长或连长)喊道:‘连长,打吧!’另一个战士也跑上来,喊道:‘打吧!连长!’众人合:‘连长,下命令吧!’这时镜头推向连长的脸,给出特写,连长的脸上显现出沉着的表情,然后在房间里踱了几个圈,用沉稳的语气说道:‘同志们,不能打!’剧情的发展告诉我们,连长总是对的。这并不是开玩笑,当时的蓝玉就面临着连长的选择。”[2]243当年明月在此直接采用战斗电影中会出现的桥段,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蓝玉在粮食缺乏和水源殆尽的困境下思考军队是否前进的痛苦和犹豫。另,小说中还融入了“公务员”[2]33、“股份”[2]35、“黄金旅游景点”[2]39、“城市户口”[2]281等充满语言张力的现代用语,代替了古代晦涩难懂的词语或事物,使得文本更显活泼和通俗易懂。
然而,历史作为形而上的存在,是无法复制或改变的。《明朝那些事儿》固然通过许多现代化色彩语言的运用来破除历史的神秘性,亦呈现了一定的历史真相,或历史的“再创造”,但这仅仅停留在“描写”历史的表层,而非回到过去“改变”或“重建”历史。
三、想把历史写得好看,但历史本身并不好看
“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2]7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的“序”中写了自己的创作愿望:将历史写得好看。现今学者们对这部小说的解读也多从“好看”入手,如赵勇的《“好看”的秘密——〈明朝那些事儿〉的文本分析》指出,小说“好看”的秘密正在于它“以化重为轻、化难为易、化陈腐典籍为话语奇观等方式制造出一种名副其实的‘悦’读‘笑’果”[6];孙小超的《〈明朝那些事儿〉幽默风格成因探析》提出“小说的幽默风格,主要是通过情节选择和修辞手段的运用实现的,而这种尝试,使历史有了更好的表现形式,为人们轻松获取知识提供了方便”[7];万昭莹、叶玉的《通俗史论中的小说笔法——以〈明朝那些事儿〉为例》[8]从“现代诙谐历史”“通俗平民写史”和“心灵成长写史”三个方面分析当年明月将文本写得好看和精彩的原因。然而笔者认为,《明朝那些事儿》既然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我们在关注其小说笔调的“文学性”是否精彩之余,也不应该忽略文本背后的历史本身并不好看的事实。
首先,《明朝那些事儿》并不和平,文本中穿插着许多血腥残暴的战争。这些战争作为权力拥有者争夺江山的筹码,产生的频率和规模可谓是“丧心病狂”,由此导致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又有多少士兵命丧黄泉?答案自然是数不胜数。回到文本:嗜好杀戮的常遇春在打败陈友谅的军队后,大开杀戒,竟连夜将三千俘虏活埋;龙湾之战后,“汉军在战场上留下了两万具尸体、七千名俘虏”[2]71;在鄱阳湖之战中,作者对作战中的士兵的描写充满无奈与凄凉之感,他们本是无辜的普通人,却被迫蹚进统治者设计的尸山血河中冒险拼命,“数十万人手持刀剑,拼死厮杀。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也谈不上有多大仇恨,但此刻,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死神牢牢抓住了每一个人,士兵的惨叫声和哀号声让人闻之胆寒”[2]104;在捕鱼儿战役后,蓝玉彻底击溃北元,“此战彻底歼灭了北元的武装力量,俘获北元皇帝次子地保奴、太子妃并公主内眷等一百余人、王公贵族三千余人、士兵七万余人,牛羊十余万头……”[2]248此外,“尸体堆成山”“拼死厮杀”“全军覆没”“损失惨重”“屠城”“十万大军仅剩十人”等语句在小说中随处可见,由此,文字背后血流成河的历史确实不忍卒读。
其次,《明朝那些事儿》充满着贪官们自私贪婪和欺诈谋权的丑恶嘴脸。作者在小说第204页介绍了官员贪污的方法:折色火耗与淋尖踢斛。“折色火耗”即官府打着熔锻碎银的损耗的名义多征赋税;“淋尖踢斛”即官吏通过踹斛,将倒在地上的谷粒纳为粮食运输中的损耗并当作自己的合法收入的行为。这两种方法将贪官们绞尽脑汁压榨钱财的奸诈模样描绘得淋漓尽致,尽显人性之险恶。此外,文本还记述了许多贪官腐败的具体事例:如元至正四年(1344),黄河泛滥,沿岸山东河南几十万人沦为难民,除此之外淮河沿岸又遭遇着严重瘟疫和旱灾,然而面临这些天灾,却因为政局腐化,赈灾物资遭到层层盘剥克扣,“皇帝(元顺帝)要下诏赈灾,中书省的高级官员们要联系粮食和银两,当然了,自己趁机拿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赈灾物品拨到各路(元代地方行政单位),地方长官们再留下点,之后是州、县,一层一层下来,到老百姓手中就只剩谷壳了。”[2]15导致伏尸处处、饿殍遍野、民众易子而食的悲惨局面;再如元朝命令沿岸十七万劳工修河堤时,各级官吏丝毫没有“父母官”的良善之道,异常兴奋的原因居然是“皇帝拨给的修河工钱是可以克扣的,民工的口粮是可以克扣的,反正他们不吃不喝也事不关己,这就是一大笔收入;工程的费用也是可以克扣的,反正黄河泛滥也淹不死这些当官的。”[2]23更为讽刺的是,朱元璋虽然严厉打击官场的贪污腐败现象,并实施了许多刑罚,如凌迟、抽肠、刷洗、阉割、挖膝盖等,“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官员们仍然前‘腐’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自明朝开国以后,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2]213官员们“朝获派,夕腐败”的人生信条实在令人不解。
再者,朱元璋巩固皇权的目的,是在诸多杀戮残暴的冤案辅助之下逐渐达成的。如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的空印案,朱元璋将地方计吏持空印文册至户部报告财政账目的做法视作藐视自己皇室权威的行为,竟把所有主印官员处死,副手打一百杖充军,除此之外,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因“监管不力”而获罪;再如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桓贪污案,在朱元璋编的《大诰》中,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最后算出总账,他和同党一共贪污了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2]221“经过朱元璋的追查,六部的大多数官员都成为郭桓的同党!”[2]221此案以三万余人的死亡告终。然而如此触目惊心的贪污数量和人数背后却存在着许多疑点:其一,当年明朝一年的收入也只有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且“胡惟庸案件”刚刚消停,朱元璋又设立了锦衣卫,郭桓区区一个侍郎从何来的胆量贪污明朝一年的收入?其二,郭桓贪污的同党之多为何涉及礼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实在令人费解。另,朱元璋的心性越发极端,就连在“胡惟庸案件”和肃贪的背后,也附带了许多错杀和冤枉的案例,导致“很多人就此给朱元璋安上了‘屠夫’‘杀人狂’的名字。”[2]225
故此,即使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一反传统历史小说的枯燥无味,致力于在没有背离史实的基础上把明朝历史书写得绘声绘色,却始终无法掩盖精彩的文本背后人物和历史事件本身并不好看的事实,这便是语言的幻觉的第三个方面。
结 语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作为网络小说,试图以通俗化的现代语言和大众化的时尚思维来书写明朝的故事,进而达到还原明朝历史原貌的效果,并激活读者了解历史的兴趣。其初衷固然是好的,然而“文学”与“历史”间的沟通却是不易的。在诸多史料的充实下,小说虽然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但这并不代表文本内的虚拟世界已经与历史的现实世界完全融合。文本内“文史互证”的局限,“想以戏谑化的语言来重建历史,但历史拒绝重建”的尴尬,以及“想把历史写得好看,但历史本身并不好看”的沉重,都是语言的幻觉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