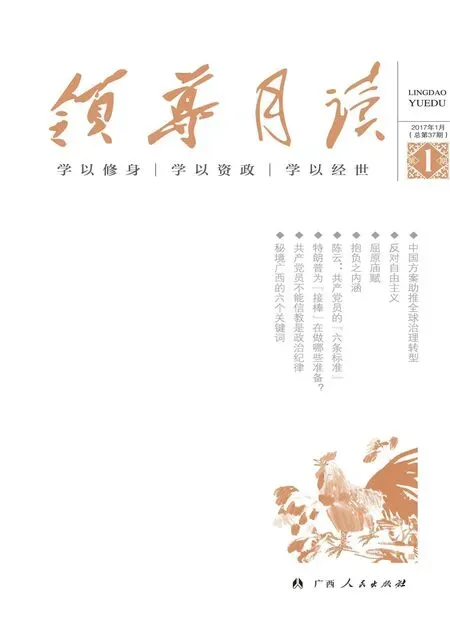它们多么美好
[俄]普里什文
它们多么美好
[俄]普里什文
乌鸦
我试枪的时候,打伤了一只乌鸦——它飞了几步路,落在一棵树上。其余的乌鸦在它上空盘旋一阵,都飞走了,但有一只降了下来,和它停在一起。我走近,近得一定会把那只乌鸦惊走。但是那一只仍然留着。这该如何解释呢?莫非那乌鸦留在伤者身旁,是出于彼此有某种关系的感情吗?就好像我们人常说的,出于友谊或者同情?也许,这受伤的乌鸦是女儿,所以为娘的就照例飞来保护孩子,正像屠格涅夫所描写的那只母麻雀奔来救它那小麻雀。这种感人的事情,在鹑鸡目动物中是屡见不鲜的。
可是转念一想,眼前是食肉的乌鸦呀,我脑子里不禁又有了这样不愉快的想法:那停落在伤者身边的第二只乌鸦,也许是嗅到了血腥味,醺醺然一心妄想马上能饱餐一顿血食,所以就挨近死定了的乌鸦,强烈的私心使它丢不开垂危的同类。
如果第一个想法有“拟人观”,也就有把人类感情搬到乌鸦身上去的危险,那么第二个想法就有“拟鸦观”的危险,也就是说,既然是乌鸦,就一定是食肉者无疑了。
松鼠的记性
我在想着松鼠:如果有大量储备,自然是不难记住的,但据我们此刻寻踪觅迹来看,有一只松鼠却在这儿的雪地上钻进苔藓,从里面取出两颗去年秋天藏的榛子,就地吃了,接着再跑十米路,又复钻下去,在雪地上留下两三个榛子壳,然后又再跑几米路,钻了第三次。绝不能认为它隔着一层融化的冰雪,能嗅到榛子的香味。显然它是从去年秋天起,就记得离云杉树几厘米远的苔藓中藏着两颗榛子的……而且它记得那么准确,用不着仔细估计,单用目力就肯定了原来的地方,钻了进去,马上取了出来。
梭鱼
一条梭鱼落进我们安设的网里,吓呆了,一动也不动,像根树枝。一只青蛙蹲在它背上,贴得那么紧,连用小木棒去拨,半天也拨不下来。
梭鱼果然是灵活、有力、厉害的东西,可是只要停下来,青蛙就立刻爬了上去。因此,大概作恶的家伙是从来也不肯停手的。
田鼠
田鼠打了一个洞,把眼睛交还给了大地,并且为了便于挖土,把脚掌翻转过来,开始享受地下居民的一切权利,按着大地的规矩过起日子来。可是水悄悄地流过来,淹没了田鼠的家园。
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它根据什么规矩和权利可以偷偷逼近和平的居民,而把它赶到地面上去呢?
田鼠筑了一道横堤,但在水的压力下,横堤崩溃了,田鼠筑了第二次,又筑了第三次;第四次没有筑成,水就一涌而至了,于是它费了好大的劲,爬到阳光普照的世界上来,全身发黑,双目失明。它在广阔的水面上游着,自然,没有想到抗议,也不可能想到什么抗议,不可能对水喊道“看你”,像叶甫盖尼对青铜骑士喊的那样。那田鼠只恐惧地游着,没有抗议;不是它,而是我这个人,火种盗取者的儿子,为它反对奸恶的水的力量。
是我这个人,动手筑防水堤。我们人汇集来很多,我们的防水堤筑得又大,又坚固。
我那田鼠换了一个主人,从今不依赖于水,而依赖于人了。
啄木鸟
我看见一只啄木鸟,它衔着一颗大云杉球果飞着,身子显得很短(它那尾巴本来就生得短小)。它落在白桦树上,那儿有它剥云杉球果壳的作坊。它啃衔云杉球果,顺着树干向下跳到了熟悉的地方。可是用来夹云杉球果的树枝叉处还有一颗吃空了的云杉球果没有扔掉,以致新衔来的那颗就没有地方可放了,而且它又无法把旧的扔掉,因为嘴并没闲着。
这时候,啄木鸟完全像人处在它的地位应该做的那样,把新的云杉球果夹在胸脯和树之间,用腾出来的嘴迅速地扔掉旧的,然后再把新的搬进作坊,操作了起来。
它是这么聪明,始终精神勃勃,活跃而能干。
(摘自《文苑》2009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