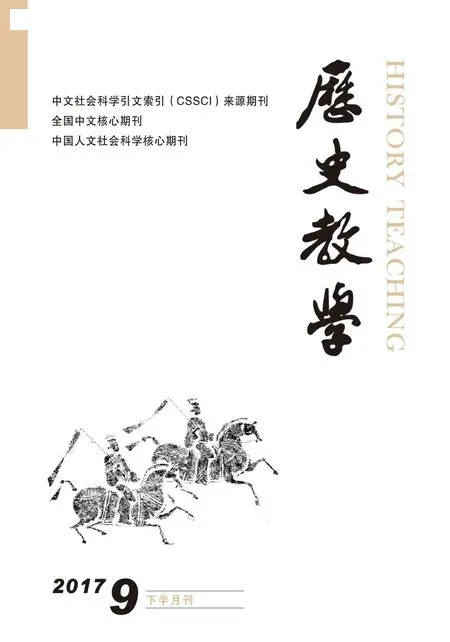论北宋阿云案的流变及影响
陈立军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
论北宋阿云案的流变及影响
陈立军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
熙宁初年,阿云案历经三次转变,由个案的量刑之争转变为改订国家法的立法之争、由按问欲举自首法之争转向谋杀法之争以及由法律之争转变为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政争。这些转变对宋代按问欲举自首法、谋杀法以及熙宁变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阿云案,按问欲举自首,谋杀法,熙宁变法
治平四年(1067年),登州民妇阿云在服母丧时与韦阿大订婚。成亲后,阿云嫌韦阿大丑陋,于是乘夜间韦阿大在田舍中熟睡时想用刀砍死他,但在砍中十余刀后仅砍断他一根手指。县尉在追查此案时怀疑是阿云所为,经用刑恐吓后阿云具实招供,是为阿云之狱。
目前学界对阿云案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尤其是关于案件性质的讨论最为集中且深入。但是囿于《文献通考》和《宋史·刑法志》的记载,这些成果对案件过程的描述缺乏具体的分析,影响了我们对本案更深入的认识。而且在考察此案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时,学人仅看到变法和反变法的冲突,未注意到对变法的影响。因此,本文试从阿云案的流变入手,分析本案对王安石变法的意义。
一、阿云案的既有研究
关于阿云案的记载主要见于《文献通考·刑考九》《宋史·许遵传》《宋史·刑法志》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司马光文集》、韩维《南阳集》保留不少当时的奏状,亦是可资参考的重要史料。
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上史料展开讨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1)案件史实。苏基朗对详载阿云案的史书《文献通考》所述每一个历史环节进行了考辨。①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阿云案属于凡人关系的谋杀;司马光《体要疏》是针对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一日诏而奏。但仍有一些关键细节失考。如戴建国指出《宋史·许遵传》所载“诏以赎论”,不是阿云纳钱赎罪,而是许遵议法不当受罚;②戴建国:《宋代刑法史研究》第六章《自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1页;《阿云案与宋代的自首制度》,林明、马建红主编:《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变迁与社会进步》,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2~229页。该文与《宋代刑法史研究》第六章《自首》在内容和观点上没有太大变化。又如苏基朗推论“许遵在登州任内已奏请付两制覆议此案”,事实上许遵在判大理寺后才奏请两制之议。
(2)敕律之争。已有学者指出它是学人对明代丘浚评论的一种误解。③李勤通:《法律事件抑或政治事件:从法律解释方法看阿云之狱的定性》,《法律方法》(第16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8页。丘浚认为造成阿云案聚讼的原因是“争律敕之文”,但其落脚点在“国家制为刑书,当有一定之制”,不可因人而改。④(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08,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933页。后人不察,据此以为阿云案是一场以敕律之争为核心的新、旧党争。⑤郭成伟:《从阿云狱的审理看宋神宗年间的“敕律之争”》,《政法论坛》1985年第4期。郭东旭又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敕律之争的背后,还潜伏着更深一层的变法与反变法的真实目的”,⑥郭东旭:《论阿云之狱》,《河北学刊》1989年第6期;《论熙宁初年刑名之争》,《宋朝法律史论》,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从而将敕律之争的内涵发挥至极致。但苏基朗指出,阿云案仅是一场法律纷争,不存在新、旧党争,随着变法的实施,才染上党争的色彩。戴建国赞同此说。苏基朗的结论是通过分析王安石在熙宁初年与司马光、韩维等人物关系以及变法举措和阿云案之争依次展开的时间而得出,虽然纠正了郭东旭的偏颇,但由于不是基于案件本身发展路径的考察,故仍有不少问题。但戴建国未完全放弃郭东旭的观点,认为此案是王安石从法律上拉开改革的序幕。①戴建国:《宋代刑法史研究》,第270页。《宋史·许遵传》载,“执政许以判大理寺”,“未几,果判大理”。其中“执政”指曾公亮。理由有三:(1)此时中书省内曾公亮独相,不仅有权选拔官员,还专享审阅刑狱奏状的权力;(2)曾公亮和许遵在断案议法时所持义理相近,许遵常怀“好生之义”,而曾公亮则“主于平恕”;(3)在随后的议法中曾公亮支持许遵。这点值得肯定。
(3)按问欲举自首法。苏辙认为,阿云案的“贡献”在于“谋杀遂立按问”。②(宋)苏辙:《龙川略志》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页。 司马光:《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司马光文集》卷38,第878页。据此,季怀银指出阿云案扩大了按问欲举自首的适用范围,抓住了本案的关键。③王云海:《宋代司法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3页。 (元)脱脱:《宋史》卷330《许遵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628页。至晚清,著名法史学家沈家本开始质疑阿云按问欲举自首是否成立。他指出,已被捕至官府的阿云“未有悔过情形,按律不成首”,“许遵删去欲举二字,谓被问即为按问”。④(清)沈家本:《寄簃文存》卷4,《历代刑法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62页。徐道邻沿用了这一说法。⑤徐道邻:《阿云之狱》,《中国法制史论略》卷7,台北:中正书局,1959年,第74页。但此观点有误。巨焕武指出沈家本不仅误解了“按问欲举”,还忽略了宋律存在犯罪未发和犯罪已发的两种自首情形。巨焕武认为阿云自首符合犯罪已发的要件,但不满足“所因之罪”的要件,故不能成立谋杀已伤的自首,王安石“怙势而胜”。⑥巨焕武:《犯罪自首成立与否的大争论——宋代的阿云之狱》,《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95年第70期。苗苗、赵晓耕持与之相似的看法。⑦苗苗、赵晓耕:《从阿云之狱看宋代刑法中的自首制度》,《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而戴建国则未区分成立自首与放宽自首的不同,认为“许遵把狭义的坦白纳入自首范围,放宽了自首成立的条件”。⑧戴建国:《宋代刑法史研究》,第264页。这或是受苏辙《龙川略志》的误导。苏辙在指出阿云案使“谋杀遂有按问”后,又说道“时欲广其事”,出现“虽累问不承,亦为按问”的状况。故此说有待考论。
(4)礼法之争。它主要源于司马光《体要疏》。阿云与韦阿大虽然违律为婚,但毕竟已有夫妻之实。据此,司马光从儒家伦理纲常的角度提出以“礼”决阿云案的主张,⑨(宋)司马光:《体要疏》,《司马光文集》卷40,李文泽、霞绍辉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97页。明代丘浚又推衍其义。这被不少法史学者接受,如陈煜、罗大乐等,就认为在敕律之争的背后还有礼法之争。⑩罗大乐:《中国法律文化萃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4页;陈煜:《皇帝如何断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这虽然是认识阿云案的一个取向,但是司马光的观点未被神宗采纳成为主流。
二、阿云案的流变
从治平四年到熙宁二年八月一日,阿云案历经三次流变,分别由个案量刑之争转向带有改订国家法性质的立法之争、由按问欲举自首法之争转向谋杀法之争以及由法律之争转向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政争。这三次转变对理解阿云案的性质、熙宁初年变法与反变法冲突的缘起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梳理史料可知,许遵在两制之议前曾针对阿云案四次进奏。在知登州时,他不仅将阿云案依法奏裁,还疏驳了审刑院、大理寺的绞刑。但刑部在覆议后认为许遵妄断,故神宗诏令许遵纳铜赎罪。至熙宁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在宰相曾公亮的支持下,许遵由知登州改判大理,①戴建国:《宋代刑法史研究》,第270页。《宋史·许遵传》载,“执政许以判大理寺”,“未几,果判大理”。其中“执政”指曾公亮。理由有三:(1)此时中书省内曾公亮独相,不仅有权选拔官员,还专享审阅刑狱奏状的权力;(2)曾公亮和许遵在断案议法时所持义理相近,许遵常怀“好生之义”,而曾公亮则“主于平恕”;(3)在随后的议法中曾公亮支持许遵。成为大理寺的主判官,使他拥有了断案和议法的权力。于是,他一面稽留阿云案不断,一面上奏神宗请求将此后天下所有谋杀已伤自首的案件都作减二等断遣,②(宋)苏辙:《龙川略志》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页。 司马光:《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司马光文集》卷38,第878页。从而使阿云案由个案的量刑之争转变为带有改订国家法性质的立法之争。这是阿云案的第一次转变。
这次转变与许遵有直接的关联。《宋史》认为这是明法科出身的许遵“立奇以自鬻”。③王云海:《宋代司法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23页。 (元)脱脱:《宋史》卷330《许遵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628页。一些学者认为许遵是受到雪活奖励制度的驱使。但从王安石的书信看,许遵怀有“好生之义”并深受传统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①(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73《答许朝议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77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乙丑”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094页。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两制之议迭起,御史中丞滕甫起到关键作用。这次转变引发御史台不满。②《宋史·刑法志》载:“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戴建国认为《刑法志》不可据,在许遵纳铜赎罪后御史台已无理由再弹劾他,而是许遵主动要求重审阿云案。此观点有误。许遵提议改法的奏疏是触发御史台弹劾的诱因。许遵进呈奏疏事,可见于两制之议结束后司马光进奏神宗的《议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而自首状》。据此可知,许遵进奏在两制之议前。《宋史·钱顗传》:“治平末,以金部员外郎为殿中侍御史里行。许遵议谋杀案问刑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顗以为:一人偏词,不可以汩天下法,遵所见迂执,不可当刑法之任。”可知,《刑法志》所述可信。御史钱顗弹劾许遵“所见迂执”,要求罢免许遵,并获滕甫支持。③《宋史》卷321《钱顗传》,第10434页。这不仅使大理寺出现主判官因断案议法频遭言官弹劾的现象,还牵连出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安石。④治平四年十一月,中书原委任祝谘判大理,但因谏官刘庠弹劾旋即被罢。见《宋会要辑稿》刑法4之75,刘琳、刁忠民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486页。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后备受神宗青睐,威胁到滕甫的地位。苏轼代张方平为滕甫撰写的墓志铭首段文字,就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两人对神宗政治影响的转换。⑤(宋)苏轼:《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苏轼文集》卷15,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59页。其实早在嘉祐任职馆阁时两人就已结怨。⑥(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6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86页。这些因素加剧了滕甫的紧张和不满,所以他反对神宗诏从王安石所议,强烈要求复议。这才有了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和知制诰钱公辅的合议。
众所周知,阿云案聚讼的焦点在于“谋是否为伤之因”,但这仅限于熙宁元年的两次两制之议。至熙宁二年初,这个焦点发生改变。据韩维所述,由于法官不满吕公著、韩维所议,又有了两次王安石和法官的集议。集议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谋杀已死是否允许自首、“谋杀首从颠倒”和“谋是否为伤之因”。前两个议题是法官在“谋为伤之因”的基础上作推论解释衍生的。
据《宋刑统》谋杀法,依犯罪行为程度,谋杀分三类,谋杀未伤、谋杀已伤和谋杀已死。据此,法官指出,既然谋杀已伤许自首,那么谋杀已死是否亦允许自首?这是法官的第一个推论。许遵将“谋杀已伤”分离为谋罪和杀伤罪,认为谋罪是杀伤罪的所因之罪,依据自首获免,但杀伤罪仍科。这是“谋为伤之因”的观点。它使法律规范由谋杀之“谋”转向“杀伤”。据此,法官指出,如果“谋为伤之因”成立,从故杀法定断,那么对犯罪人数在两人及以上的谋杀而言,“造意者”的谋罪就会被获免,成为从犯;“加功者”的杀伤罪仍科,则为首犯,从而造成“谋杀首从颠倒”。这是法官的第二个推论。⑦(宋)韩维:《南阳集》卷26《论谋杀人已死刑名当再议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23页。
根据《宋刑统》规定:“造意者,谓元谋屠杀,其计已成,身虽已行,仍为首罪,合斩。余加功者,绞。”⑧(宋)窦仪等详定,岳纯之校正:《宋刑统校证》卷17《贼盗律·谋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6页。可知,“谋杀首从颠倒”背离了《宋刑统》的规定。
这两个新议题使争论焦点由按问欲举自首法转向谋杀法。熙宁二年二月三日(庚子)诏、王安石复奏以及熙宁二年二月十七日(甲寅)诏,都是为解决这两个议题而发布的。⑨王安石复奏:“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70《刑考九》,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099页。这是阿云案的第二次转变。这次转变除了受许遵“谋为伤之因”的观点、法官作推论解释影响以外,还与王安石在两制之议时提出谋杀从故杀伤法定断有关。它造成谋杀与故杀伤法相混淆。
熙宁二年初,这场集议仍是一场法律之争。因为除了新议题出现之外,与议者多是专门从事司法实务的官员。所谓“法官”指审刑院、大理寺的官员,分别有知审刑院齐恢、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大理少卿蔡冠卿⑩《文献通考》卷170《刑考九》,第5099页。和大理寺详断官韩晋卿,不包括刑部。刑部在这次集议的背后扮演了支持王安石的角色,如刑部详覆官朱温其为王安石检法。①(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73《答许朝议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77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乙丑”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094页。这次法律之议之所以会成为吕诲攻击王安石变法的口实,①(宋)吕诲:《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09,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81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9“治平四年闰三月乙丑”条,第5085页。是因为除了与议的韩晋卿在嘉祐末年与时任纠察司的王安石就一宗由鹌鹑引发的命案起过争执以外,②《宋史》卷426《韩晋卿传》,第12706页。 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第170页。还为王安石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提供了契机。
由于王安石与法官争议,形成不利于王安石的舆论氛围。③(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3页。 《宋史》卷331《郑獬传》,第10419页。为保护王安石,神宗于熙宁二年二月三日(庚子),既颁布了一道支持法官关于谋杀已死的诏令,又令王安石由翰林学士改参知政事,以折中的方式中断了集议。这引起与议双方各自支持者极大的非议。御史中丞吕诲不仅严厉抨击法官,还暗指王安石改法;④吕诲:《论重辟数多奏》,《宋朝诸臣奏议》卷99,第1065页。翰林学士韩维上奏指责庚子诏律意不明,⑤《南阳集》卷26《乞更议谋杀自首刑名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721页。刑部则直接将庚子诏“封还中书”。⑥《文献通考》卷170《刑考九》,第5100页。如何妥善处理谋杀刑名问题成为困扰神宗和大臣的难题。为此,韩维建请“群臣博议”,欲以公论厌人心。但神宗拒绝了自己这位东宫旧臣的建议,选择王安石复议,从而引发王安石和唐介的廷议之争。《唐介传》载:
初,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服,以律案问欲举法坐之,得免所因之罪。(唐)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安石曰:“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也。”⑦(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15《唐参政介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0册),第778页。
苏基朗认为,唐介是想借机推翻熙宁元年七月三日(癸酉)敕“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⑧《宋史》卷14《神宗本纪》,第268页。的规定。此推论是合理的,但他忽略了中书宰辅分立的面相。“朋党”一语揭示赵抃支持挟情反对王安石的唐介。因为这时中书只有宰相曾公亮,参知政事赵抃、唐介和王安石,富弼虽已拜相,但尚未入朝。故以为正是宰执间的对立令刑名之议染上一层“党争”的色彩。
这使阿云案由法律之争转变为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政争,成为阿云案的第三次转变。所谓“党争”,只是王安石为反驳唐介而贴的政治标签,既不具派系的争斗,也没有变法的内容,但却出现公论与私议的矛盾。而且唐介、赵抃原本就极力反对王安石进入中书任执政。于是,神宗在熙宁二年二月十七日(甲寅)下诏将王安石复奏法令化。由于刑部处于国家法令颁布的关键环节,判刑部刘述、丁讽不仅将此由中书下发省部的甲寅诏视作颁行全国的条法,认为这“误引刑(部)一司敕”,还以此作为借口要求中书省和枢密院合议。⑨按律法颁降程序,法条分两种:一、诸州敕,或由刑部翻录行下,或由进奏院发送诸路;一、省部条贯,由中书省直接行下。根据律条颁降程序以及刘述奏疏所列诸司可知,甲寅诏并非颁行全国的诏令,而是由中书直接下发省部的条法。参戴建国:《宋代法律制定、公布的信息渠道》,《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其目的是为了探求朝廷的动向。⑩《宋会要辑稿》职官65之34,第4816页。这获得御史台吕诲、钱顗、刘琦和宰相曾公亮的支持,形成一股“公论”的舆论态势。
一般判刑部须由侍御史知杂以上的朝官充任。治平四年闰三月,刘述改官御史知杂就是中书宰辅主导的结果。①(宋)吕诲:《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09,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81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9“治平四年闰三月乙丑”条,第5085页。宰相曾公亮支持刑部的举动,使神宗以为御史成为了宰辅的肘腋,故反对复议,造成中书省不与议,仅由枢密院合议。这方使阿云案由法律之争演变成“治理国家应采用什么司法原则的大问题”。②《宋史》卷426《韩晋卿传》,第12706页。 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第170页。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主张维持“旧法”,新晋枢密副使韩绛、知枢密院事陈升之赞成王安石之说。至三月十五日,富弼入相,神宗令富弼与王安石复议,但富弼反对王安石之说,拒绝合议。可见,谋杀刑名之议不仅未取得进展,还导致二府大臣分裂。
五月,御史中丞吕诲连续上奏,认定不以新法断谋杀案的权知开封府郑獬、知制诰钱公辅和宣徽使王拱辰出外是王安石所为,指责他专权。③(清)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4,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3页。 《宋史》卷331《郑獬传》,第10419页。郑獬等人属于侍从以上的高级官员,他们的差除由神宗决定,中书无权干涉,那么吕诲是如何获知这次差除与王安石有关呢?因为这时中书门下运行失序。曾公亮出使西京,唐介已死,王安石与富弼、赵抃不合,以致中书出现“每欲主张亲知,但只先同议论,后至签敕时,别作回避”的现象。①范纯仁:《上神宗论刘琦等责降》,《宋朝诸臣奏议》卷109,第1190页。(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6页。故宰执间的对立为吕诲探知消息创造了机会。神宗在诘问吕诲后清楚地指出,吕诲“为人所使”,“此必是中书有人与如此说”。②(宋)杨仲良:《宋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58“吕诲弹劾王安石”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87页。表明吕诲弹劾王安石的背后是中书省宰执与御史联手谋求扳倒王安石。这成为熙宁变法史上王安石首次因为政争而离开中书省。
在考察熙丰变法之初变法派和反变法派冲突的缘起时,罗家祥指出,王安石非议司马光、吕诲等人论谏濮王之议导致吕诲进奏《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③罗家祥:《熙宁变法之初两派纷争缘起新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事实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间接原因。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五月三十日重返中书,才是导致这封著名奏状出现的直接原由。④将吕诲奏疏所论十事依时间次序罗列可知,最晚的事件在熙宁二年五月十九日,即郑獬、王拱辰和钱公辅三人出外但宰相不书敕。其中论章辟光献岐王迁外事,《宋史·吕诲传》已指出它是吕诲造谣生事,和王安石无关,其他九事都有实迹。据此可知,吕诲仍是针对差除不明的问题进奏。之前,吕诲已有两封奏疏,均认定人事调动是王安石所为,迫使王安石辞去执政,故吕诲《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疏》仍与王安石重入中书省有关。熙宁五年六月,王安石在觐见神宗回忆初任执政时指出,“及蒙陛下拔擢,曾未及一两月,初未曾有施为,吕诲乃便以方卢杞”。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4“熙宁五年六月辛未”条,第5684页。唐代宰相卢杞在宋人眼中是党同伐异的代表。可知吕诲早已将王安石视为政治隐患。而《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仍是针对郑獬等人的差除问题,只是站在反变法的立场上,扩大了攻击范围,将自熙宁元年七月三日以来颁布的一系列谋杀敕视为王安石“挟情坏法,外报私怨”。⑥吕诲:《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状》,《宋朝诸臣奏议》卷109,第1180页。神宗最忌御史谗说殄行,不仅罢免吕诲,改变御史任命方式,还将参与阿云案之争的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和孙昌龄等贬降出外,御史台几乎为之一空。⑦参熊本崇:《权监察御史里行李定——关于王安石的对御史台政策》,〔日〕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王铿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1页。这不仅改变了嘉祐末年以来言官恣意弹劾大臣的局面,还造成宋代政治史上变法与反变法的冲突。
三、阿云案与按问欲举自首法
宋代自首法分两类:一犯罪未发的自首,即主动投案承认罪行;一犯罪已发的自首,即被捕或被告发后经审问后承认罪行,即“按问欲举自首”。阿云案扩大了按问欲举自首适用范围,使“谋杀遂有按问”。这既是许遵的目的,也是宋人的看法,更是目前学界的共识,但并未牵涉自首认定条件的问题,那么为何还会出现《宋史·许遵传》所述“虽累问不承者,亦得为按问”,以及劫盗案“或两人同为盗劫,吏先问左,则按问在左;先问右,则按问在右。狱之生死,在问之先后,而非盗之情”的状况?⑧《宋史》卷330《许遵传》,第10628页。巨焕武认为,“这不是《嘉祐编敕》对按问欲举所作宽广的解释造成的,更不是许遵个人的过错,而是执法者不当”。不少学者持与之相似的看法。⑨如《宋代司法制度研究》第三章《犯罪人自首》,第124页。但巨焕武对自己的观点抱有疑虑,其后言:“因为旧法一问不承,后虽为自言,皆不得为按问,为何此时,虽累问不承者,亦得为按问呢?”⑩巨焕武:《犯罪自首成立与否的大争论——宋代的阿云之狱》,《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95年第70期。那么这个问题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文献记载看,最早将阿云案与按问欲举自首认定出现的问题相关联的记载始于苏辙《龙川略志》。成书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的《邵氏闻见后录》卷21又转述了苏辙的记载。①范纯仁:《上神宗论刘琦等责降》,《宋朝诸臣奏议》卷109,第1190页。(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6页。《龙川略志》卷4载:
知润州许遵尝为法官,奏谳妇人阿云谋杀夫不死狱,以按问欲举乞减死。旧说,斗杀、劫杀,斗与劫皆为杀因,故按问欲举可以减。谋而杀,则谋非因,故不可减。士大夫皆知遵之妄也。时介甫在翰苑,本不晓法,而好议法,乃主遵议。自公卿以下争之,皆不能得,自是谋杀遂有按问。然旧法,一问不承,后虽犯者自言,皆不得为按问。时欲广其事,虽累问不承,亦为按问,天下皆厌其说。予至齐,齐多劫盗,而人知法有按问,则未有盗而非按问者。二人同劫,先问其左,则按问在左,先问其右,则按问在右。故狱之死生,在问之先后,而非盗之情。又有甚者,捕人类多盗之邻里,所欲活者,辄先问之,则死生又出于用情。予见而叹曰:“惜哉,始议按问者之未究此弊也!因以语齐守李诚之。”①(宋)苏辙:《龙川略志》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页。
据此可知:(1)《龙川略志》是《宋史·许遵传》的一个史源;(2)按问欲举自首的认定出现问题在熙宁六年。因为《龙川略志》所言“予至齐”,指熙宁六年苏辙任齐州掌书记,②孔凡礼:《苏辙年谱》,北京:文苑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时知齐州为李师中;(3)苏辙认为朝廷又在谋杀允许自首的基础上扩大了范围,方出现“虽累问不承,亦为按问”的现象。可知,苏辙混淆了扩大按问欲举自首的适用范围和放宽按问欲举自首条件的区别。因为扩大适用范围只需要改变不适用自首的刑名的解释即可,许遵正是将“谋杀已伤”解释为“谋为伤之因”才使得“谋杀已伤”允许自首,而放宽按问欲举自首则要改变按问欲举自首原有的构成条件,是故苏辙的说法有误;(4)“虽累问不承,亦为按问”,实际是神宗熙宁年间发布的一道放宽按问欲举自首法的敕令。它是认识阿云案向放宽按问欲举自首法转变的关键。
这道敕全文不可见,仅在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四日大臣奏疏中存有节文。其内容为“因疑被执之人,虽有可疑之迹,赃证既未分明,则必无按之理。若不因其自服,所犯无由显露”,“虽累讳后招,终因自服,依按问自首”,“合从减等”。③《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39,第8253页。
神宗何时颁发的这道敕?史无明文,仅知在“熙宁年间”。我们以为,它很可能颁布于熙宁三年八月以后不久。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范纯仁奏:“熙宁后来,用按问欲举条,虽曾隐讳,终因罪人说出并得减等。”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0“元祐元年闰二月壬子”条,第8940页。这与上述敕的节文大意相同,可证它确实颁于熙宁年间。据时人刘鸣玉所言,“介甫申明按问欲举之法,曰:虽经拷掠,终是本人自道,皆应减二等。由是劫贼盗无死者”⑤(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5,邓广铭、张希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06页。可知,这道敕是由王安石在申奏以后颁行,影响了劫贼盗案的定断。这与苏辙的观察一致。齐州、登州均属京东东路,历来是劫盗贼案的频发地。以此推知,上述敕当是针对劫盗贼猖獗的问题而颁行。
熙宁二年八月一日,神宗降诏“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结束了阿云案之争。⑥《文献通考》卷170《刑考九》,第5100页。此诏牵涉的仍是谋杀问题,那么放宽按问欲举自首法应在此之后。熙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中书门下针对现行刑罚过重的问题提出五条意见。其中,第一条指:
至如强劫盗并有死法,其间情状轻重有绝相远者,使之一例抵死,良亦可哀。若据为从轻之人,特议贷命,别立刑等……自余凶盗,杀之无赦。禁军非在边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宽首身日限,以活壮夫之命,收其勇力之效。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戊寅”条,第5211页。
这条意见表明放宽情状较轻的强劫盗贼的刑罚成为改革的方向,而放宽逃卒自首的日限为其指明出路。熙宁五年十一月,编敕所驳斥大理寺、审刑院所断军贼李则案,认为李则“合依条,于斩刑上从按问欲举自首减二等”。⑧《宋会要辑稿》刑法4之77,第8487页。可知,新的按问欲举自首法已开始适用贼盗案。故以为上述敕当颁于熙宁三年八月中书门下提议后不久。
综上所述,造成“狱之死生,在问之先后”的直接原因是上述敕,间接原因才是阿云案。苏辙所言“虽累问不承,亦为按问”有问题,缺少是否“自服”这一最关键的环节。这种表述与苏辙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因为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具有苏辙回忆录性质的《龙川略志》成书时间又恰在绍圣四年(1097年)哲宗亲政起用新党而苏辙被贬循州之际。⑨李致忠:《宋刻龙川略志六卷别志四卷》,《收藏家》2012年第2期。
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改革了按问欲举自首法。其表现为犯罪已发的自首从“一问不承,后虽犯者自言,皆不得按问”,转变为“虽累讳后招,终因自服,依按问自首”,更改了按问的要件。《嘉祐编敕》规定“因疑被执,但诘问便承”,按问欲举自首便得以成立,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0元祐元年闰二月壬子”条,第8941页。但未明确“诘问”的次数和时限,故有“一问不承”不为按问的实践。熙宁年间的这道敕,则直接将按问欲举自首的要件由按问的次数与时限转向了犯人是否“自服”,使“自服”成为决定按问欲举自首是否成立的关键。新法还规定:“凡杀之人,虽已死,其为从者被执,虽经拷掠,苟能先引服,皆从按问欲举律减二等。”②《涑水记闻》卷16,第326页。按:原作“四等”,据上述敕以及熙宁二年七月三日敕改为“二等”。这与上述敕共同构成新的按问自首法的内容,是熙宁变法在刑政方面取得突破进展的重要表征,反映了韩维在两制之议时提出的圣人制法之意在于“原首以开善”的主张。
这道敕还与王安石的执政理念有关。放宽按问欲举自首法带来的弊病在熙宁六年全面显现。不仅造成劫盗“狱之死生,在按之先后”,还使配隶犯流放地沙门岛人满为患。神宗指出“案问欲举法宽,故致多如此”,但王安石却以为只有继续放宽自首法才能使沙门岛无罪人。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6熙宁六年七月己未”条,第5983页。可知,王安石抱持儒家“刑期无刑”的理念,反映了他对先王之政的追求。
四、阿云案与谋杀法
以往对阿云案的研究多将注意力放在自首法上,忽略了本案对谋杀法的影响。这与学界对阿云案的第二次转变以及宋代谋杀法的认识不足有关。④闵冬芳虽然对我国古代“谋杀”概念的形成和演变作了细致的考察,但失于对宋代的考察。参氏著:《中国古代谋杀概念的形成与演变》,《法学》2009年第2期。针对法官的第一个推论,谋杀已死是否允许自首,熙宁二年二月三日(庚子)敕规定:“谋杀人已死,自首及按问欲举,并奏取敕裁。”⑤《文献通考》卷170《刑法考九》,第5099页。这道敕虽然被神宗于二月十七日收回,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发挥着效力。关于法官的第二个推论,“谋杀首从颠倒”,熙宁二年二月十七日(甲寅)敕规定:“其谋杀人已死,为从者虽当首减,依《嘉祐敕》凶恶之人情理巨蠹及谋杀人伤与不伤奏裁。”⑥《文献通考》卷170《刑法考九》,第5099页。这道敕并未解决“谋杀首从颠倒”的问题,导致“谋杀首从颠倒”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被运用到司法实践中。据《长编》载:“大理寺断潞州民王德与弟亮妇程奸,造意与程谋杀亮死。程案问从故杀处死,德减死流二千里刺配。”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0元丰七年十一月辛丑”条,第8383页。按《宋刑统》规定,王德为造意者,程某为加功者。大理寺以程某为首犯、王德为从犯的定断,说明大理寺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了“谋杀首从颠倒”的推定解释。该案由尚书省于元丰七年(1084年)十月上奏疏驳改正,表明“谋杀首从颠倒”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被贯彻执行了。
熙宁二年二月十七日(甲寅)敕,不仅相较沿用《唐律》的《宋刑统》谋杀已死从犯绞刑的规定,在刑罚上减轻,还使谋杀从犯也适用按问欲举自首,而且相较《嘉祐编敕》规定“谋杀人伤与不伤奏裁”,在适用范围上又有了扩展,谋杀已死从犯亦许奏裁。这顺应了北宋立国以来对谋杀量刑放宽的趋势。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七月庚午诏,“诸谋杀人不至伤杀,而情理凶恶,不可留本处者,具狱以闻”,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景德二年七月庚午”条,第1351页。要求情节恶劣的谋杀未伤的案件奏裁。至天禧三年(1019年)八月壬寅诏:“谋杀、故杀、劫罪至死,因丁亥赦原者,诸州并依强劫贼例刺配本城。情重不可宥者,部送京师。自今著为定式”,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4“天禧三年八月壬午”条,第2165页。又进一步将谋杀死罪情节严重者纳入中央决断的范围。《嘉祐编敕》“谋杀人伤与不伤奏裁”的规定正是这两道敕令的综合。熙宁二年初的那两道敕又在《嘉祐编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奏裁范围。表明在不断放宽谋杀刑罚的背后是北宋皇帝逐渐加强对谋杀犯罪的处决权。
而在法律实践中,司法部门较皇帝在处理谋杀案时更倾向扩大宽刑的范围。熙宁变法时,审刑院、大理寺不仅将熙宁二年初的那两道敕适用于谋杀已死的案件,还将其适用范围由凡人关系的谋杀扩展至夫妻关系的谋杀。审刑院、大理寺对通奸谋杀夫死案中的奸妻,用“按问自首变从故杀法”,足以说明这点。⑩《涑水记闻》卷16“相州狱”,第324页。但出于封建礼法的需要,审刑院、大理寺又据《宋刑统·名例律》“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将身为从犯的奸妻断入恶逆斩刑。以此推知,当不触及名分等礼法问题时对谋杀伤的犯罪处罚会更轻。而且即便存在夫妻身份,谋杀的量刑亦呈现出放宽的态势。
元丰三年,备受王安石器重的中书堂后官周清改变了上述案件中奸妻的量刑。在许遵“谋为伤之因”观点的基础上,周清重申谋杀首犯与从犯构成所因关系。他指出:“妻谋杀夫已杀,合入恶逆,以按问自首变从故杀法,合用妻殴夫死法定罪。缘妻殴夫死者斩,不言皆斩,乃系相因为首从,合依首从法减死,止科以流刑。”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2“元丰三年正月丙子”条,第7345页。可见,周清是针对《宋刑统》等法条的漏洞“不言皆斩”的规定对通奸谋杀案中的首从关系进行了解释。据此,周清将通奸谋杀夫死案中奸妻的量刑由恶逆斩刑改为“止入不睦”“依敕当决杖处死”,使奸妻可以根据新按问欲举自首法由死刑转化为生刑。这既是将不定期赦免谋杀死罪的规范化,也是对熙宁二年二月十七日诏谋杀从犯奏裁的具体化,更是南宋《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犯奸而奸人缘奸杀其夫,妻不知情者,奏裁”条款的法条渊源。②《庆元条法事类》卷80“诸色犯奸”之“贼盗敕”,戴建国点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21页。崔碧茹:《宋代奏裁环境下的法律论争:如何处罚“因与人奸致夫于死”的“奸妻”》,《宋史研究论丛》(第14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1~82页。崔氏虽然注意到凡人之间的谋杀法在元丰时也适用夫妻关系以及由唐律“与同罪”到《庆元条法事类》“妻不知情者,奏裁”的变化,但对这种转变的原因以及周清在其中的作用失考。
南宋理学兴起,虽然加强了对三纲五常的教化,但仍沿用了周清之法。如,淳熙六年(1179年)阿梁和叶胜谋杀夫案,妻子阿梁为从犯,还是“加功者”,但在奏裁后,仅断作贷命决脊杖二十、二千里编管,而不是绞刑或恶逆斩刑。③《宋会要辑稿》刑法6之40,第8552页。明、清以后,理学成为统治思想,奸妻的量刑方倒退至《唐律》的法律规范。但神宗对凡人关系的谋杀从犯量刑为明清律条所吸收。明代著名律学家雷梦麟指出:“若谋杀人,伤而不死,造意者,绞;从而加功者,杖一百,死亦少宽之也”;“其同谋而为从之人”,“已杀则杖一百,徒三年”,足以说明这点。④(明)雷梦麟:《读律琐言》卷19,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45页。《大清律》延续了《明律》的规定。可知,由阿云案确立的有关凡人关系的谋杀法,不仅改变了由《唐律》结构成的《宋刑统》的法律规范,还影响了明清时代的律法。
五、阿云案与熙宁变法
王安石变法崇尚法治。戴建国指出王安石是以阿云案为突破口,“首先从法律上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就可以说明这点。但阿云案是如何与王安石变法相衔接的?戴建国已注意到王安石主政采用放宽自首法与实施重法地分相结合以瓦解罪犯的一面,⑤戴建国:《宋代刑法史研究》,第269~270页。但这不全面。
熙宁元年,阿云案由量刑之争转向立法之争。各方虽然争论“谋杀已伤是否许自首”,但是在讨论使用何种法律形式议法时却形成鲜明的对立。许遵在奏请两制之议时谴责刑部“弃敕不用,但引断例”。这段文字是学者将阿云案视作敕律之争的重要证据。⑥郭东旭:《论阿云之狱》,《河北学刊》1989年第6期。但已有学者指出,其中“敕”,指《嘉祐编敕》有关按问欲举自首的规定,而非神宗颁布的敕令,不能说明司马光等人反对神宗有关谋杀敕的问题。⑦李勤通:《法律事件抑或政治事件:从法律解释方法看阿云之狱的定性》,《法律方法》(第16辑),第58页。故以为与其说这是一场“敕律之争”,不如说它是北宋中期掀起的一场大规模抵制以例破法的开端。
虽然许遵指责刑部只用断例议法,但已任大理主判的他提出“谋为伤之因”的主要法律依据仍然是断例。⑧据司马光《议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而自首状》,许遵在论证“谋杀已伤许自首”时使用了苏州洪祚断例、《嘉祐编敕》“谋杀人伤与不伤,罪不至死者,并取敕裁”以及《律疏问答》“谋杀凡人,乃云是舅”等。可知,“谋为伤之因”的观点脱胎自洪祚断例。因为仅有它存在所因之罪和杀伤罪二分的原则。王安石指出“法寺、刑部所以自来用例断谋杀已伤不许首免”。⑨《文献通考》卷170《刑考九》,第5098页。可见,断例早已成为司法部门断案议法的重要根据。王安石、司马光在两制之议时虽然在观念上存在分歧,但是一致反对司法部门用例议法。王安石认为“盗与杀伤为二事,与谋杀伤类例不同”,有司职在守法无权议法,否则紊乱行政秩序;⑩《文献通考》卷170《刑考九》,第5098页。司马光则认为这是“以例破条”,损坏了正常的法律秩序。①司马光:《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司马光文集》卷38,第875页。 《宋史》卷201《刑法三》,第5007页。故两人改用《刑统》总则《名例律》阐释谋杀已伤是否允许自首。《名例律》“规定全律通用的刑名和法例”,②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1“元祐元年十一月丙子”条,第9520页。是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而大量断例的出现与运用破坏了《名例律》在断案议法时的基础地位。
王安石、司马光在主政后落实了上述政见。王安石为“变风俗、立法度”,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看详编修中书条例司等,就采用编例为条、纳例入法的方式,改革人事制度和行政制度。之后,又将此举由中书省延伸至枢密院乃至中央机构各部门,以摆脱“政出胥吏之手”的局面。③李国强:《论北宋熙宁变法的实质》,《史林》2011年第2期。哲宗即位,高太后执政柄,起用司马光主政。司马光虽然反对熙丰变法,但是在处理政务运作中出现“以例破法”时延续了王安石的政策。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乞不贷强盗白札子》和《乞不贷故、斗杀札子》强烈反对断案“用例破条”,要求刑部举驳并加强门下省在疑狱奏谳中的审核权,④《司马光文集》卷48,第1024~1028页。次年,又在《乞令三省诸司无条方用例白札子》中提出“渐除弊例”的建议。⑤《司马光文集》卷55,第1142页。两人连续性的举措实现了宋代例由法的对立物向例为法条的制度性转变。
阿云案还是熙宁变法检讨现行刑罚过重的开端。韩维、吕公著在两制之议时较王安石、司马光更进一步,他们将《名例律》背后的“圣人”推到法律思想的前台,彰显其权威性,用圣人制法之意批判国家现行刑罚过重的问题。⑥《南阳集》卷26《议谋杀法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721~723页。这一思路与王安石援释、道义理入儒学并以此作“经术”经理世务相得益彰,⑦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成为了熙宁变法改革现行刑名问题的一个发展方向。熙宁三年,中书门下上奏,将五条包括劫盗、逃卒在内刑名义理过重的条例要求刑部重新删定;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戊寅”条,第5211页。枢密使文彦博更是提出“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要求检讨“自五代以来,于朝廷见用刑名,重于旧律”,又将检讨的事项扩展至伪造符印等犯罪,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7“熙宁三年十一月戊申”条,第5280页。而且神宗在王安石要求下还令曾布刊定《宋刑统》刑名义理不便的内容,⑩《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8,第8219页以使之适应北宋中期社会发展的需要,均是以儒家义理为本位批判现行刑罚问题的思路的延续。不仅改变了北宋中期对强劫盗、逃卒以及伪造符印等以往被赦令、灾异等排除在减刑之外的刑名的刑罚,还反映了北宋中期兴起的以经学义理决断政务的潮流。
通过对阿云案的总结,王安石获得一条政治经验:“有司用刑不当,则审刑、大理当论正;审刑、大理用刑不当,即差官定议;议既不当,即中书自宜论奏,取决人主,此所谓国体。”①司马光:《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司马光文集》卷38,第875页。 《宋史》卷201《刑法三》,第5007页。这套说辞虽然是熙宁三年王安石针对曾公亮“中书论正刑名为非”的观点有感而发,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国体”,是因为有阿云案的前车之鉴使它具有了合法性。它所代表的不仅是一套已行或可行的行政程序,还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渗透到行政体系中,成为中书宰辅干涉司法复审、加强中书司法权的名义。元祐元年十一月,门下侍郎韩维就是以此作为借口,要求加强门下省对大理寺所上奏裁案件的审核权。②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1“元祐元年十一月丙子”条,第9520页。
综上所述,从政治层面看,阿云案历经三次转变,揭开了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冲突。而从法史的角度看,这不仅扩大了按问欲举自首法的适用范围,使谋杀已伤和谋杀从犯亦许按问,还改变了谋杀从犯的量刑以及按问成立的要件,从而扩大并放宽了按问欲举自首法。这是熙宁变法在刑政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另外,阿云案还顺应了自真宗以来放宽对谋杀犯量刑的趋势,影响了宋代通奸谋杀案中奸妻的刑罚,改变了由《唐律》结构成的《刑统》对谋杀从犯绞刑的规定,并为明清律条所吸收,体现了北宋皇帝逐渐强化对谋杀犯罪的处决权的面相。而在阿云案之争中形成的一些政治理念,成为熙宁变法时期解决以例破法的问题、检讨现行刑罚过重和加强中书司法权的滥觞。因此,阿云案不论是对宋代的按问欲举法,还是谋杀法,甚至是熙宁变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是熙宁变法在刑政方面进行变革的开端。
The Discu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Case of A-yun
The early years of XiNing,the case of A-yun go undergo three times trasformation,from the argumentof sentence to the legislation revising national law,from the law of voluntary surrender to the law ofmurder,and from the legaldispute to the politicalargumentsof fighting againstWang Anshi reform.These trasformation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f the law ofmurder,the law of voluntary surrenderand the reform ofXiNing.
the Case of A-yun,the Law of Voluntary Surrender,the Law ofMurder,the Reform of Xi Ning
K24
A
0457-6241(2017)18-0020-10
2017-07-05
① 苏基朗:《神宗朝阿云案辨正》,《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149页。
陈立军,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