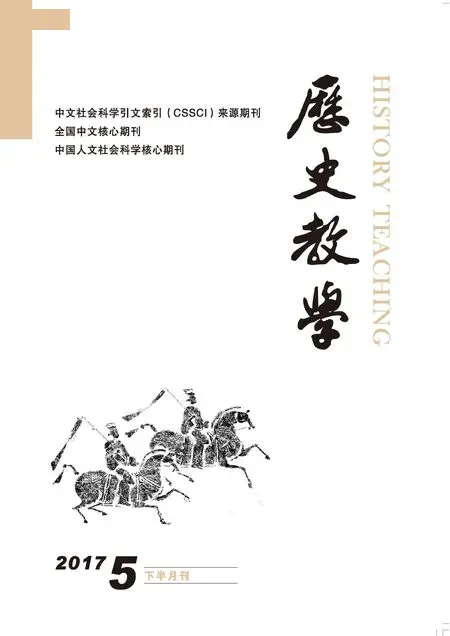日本二二六事变后中国舆论的反应*
赵晓红
(浙江大学历史系,浙江杭州310028)
日本二二六事变后中国舆论的反应*
赵晓红
(浙江大学历史系,浙江杭州310028)
日本军部内的皇道派与统制派在内政、外交等方面的矛盾,导致了1936年2月26日的空前大政变。二二六事变不仅关乎日本内政,而且对外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则首当其冲,因此中国朝野对此事变均分外关心。政变发生后,中国各大媒体即对该事变持续进行大幅度报道,对其发生背景、原因、影响、政局变动及善后处理情况等进行了分析探讨。在此基础上,中国舆论更关心由该事变而引发的中日关系变化、日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等问题。以民间舆论为代表的国民外交与政府外交相辅相成,起到了相互配合和促进作用。
二二六事变,中国舆论,少壮派,元老派
1936年2月26日清晨,日本少壮派①少壮派与元老派,亦称皇道派与统制派;急进派与稳健派或维持现状派与打破现状派等。军人因不满元老重臣、政阀和财阀的政策,由驻扎在东京即将调往中国东北的陆军第一师团一些青年军官发动叛乱,占领首相、陆相官邸和警视厅,并刺杀刺伤元老大臣多人,此次事件被称为二二六事变。震惊世界的二二六事变是日本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叛乱,也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于日本的政治走向具有深远历史影响。此次政变不仅影响了日本内政,且对远东局势和世界秩序,特别是对中、苏两国均有重大影响,因此,在相关研究中多会涉及该事件。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针对二二六事变后中国朝野的反应及具体应对等则尚无过多聚焦和分析。本文试从当时媒体舆论的角度,考察国人对此事件的反应,从而管窥时人的日本观及对国际问题的认知,探讨舆论在政府外交和国民外交中的作用。
一、对二二六事变本身的关注
2月26日晨五点多,日本爆发了二二六事变,南京方面于十时左右,即已接到简略之报告。27日,中国的晨报迅即以头版头条、大篇幅及醒目标题的形式进行了报道。此后,许多报刊发出号外或连续辟出专栏或刊出特辑来专门讨论此次政变,标题大多以“空前政变”或“惨变”来形容此事件。由于东京实行戒严,封锁电讯,其经过详情、善后办法均因日本检扣新闻,而无法得到确切消息。中国各方面对此极为关注,南京各方颇多赴外交部探听详情者,但外交部亦因电讯断绝,到27日晚为止仍未接到驻日大使馆之详细报告,日本驻京使馆及其他各国使馆亦均未接到报告,因此,更使人们相信东京事态当极为严重。②《我国注视发表》,《申报》1936年2月27日,第2版。由于消息受限,态势不明,最初各报的消息难免有误,例如叛军人数、各大重臣生死状况等均有不确之处。
对于日本重臣多人被害,中国舆论既表同情,同时又不失时机以此来回击日本。
“吾人闻此凶变,惟有代为抱惜。”③《社评:日本之暴力政变》,《大公报》1936年2月27日,第2版。“我们对于邻国发生这样大不幸的事件,当然表示很深厚的同情;对于遭难死伤的几位政治家,尤其表示哀悼的同情。”④胡适:《东京的兵变》,《独立评论》第191号,1936年3月8日。80多岁的藏相也未能幸免,“即使抛开政治道德国家纪纲不论,单从人道上讲也太残忍了”。①芸生:《日本暴变的由来》,《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9期。另一方面,国人一般认为被害的元老重臣是日本的稳健派,相对急进的皇道派而言,稳健派的对华侵略以及对外政策相对温和一些。因此,国人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胡适即认为:“他们和我们同是一种狂热的暴力的牺牲者,所以我们不能不同情于他们的不幸。”②胡适:《东京的兵变》,《独立评论》第191号,1936年3月8日。
二二六事变前,中日关系因华北问题日趋紧张与恶化。“当东京事变的消息传来,举国惶恐,以为中日关系的前途总是凶多吉少”,但亦有人认为“我们的敌人家里有了内乱,虽不敢说于我们一定有何种益处,但总不致有多大的害处”。③皮名举:《对东京事变的感想》,《独立评论》第192号,1936年3月15日。对此想法,有学者警示称:
对于此次事变不可做乐观,切勿以为日本内部既发生裂痕,今后将难以全力侵略中国,此则大谬!④胡恭先:《二二六事变之里因》,《日本二二六大政变及中日问题》,成都:统一评论社,1936年,第17页。
日本的大陆政策和向外发展,都是传统的和一贯的。在元老重臣与少壮军人之间,只有缓急的分别,所以无论谁当国,日本的对外政策是不会大变的。因此我们对于这次东京政变,除同情死难的人以外,无所用其哀乐。⑤徐庆誉:《日本政变之前因后果》,《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第8号。
在国际政治宣传中,借重大事件之机会打击对手,拉拢争取潜在的同盟者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此种手段历来为各国所普遍采用。⑥李云峰、叶扬兵:《西安事变中苏联和日本态度之比较》,《文博》1997年第1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占领东北的原因,归责于“中国连年内乱,不成体统,支那政府人民没有纪律,不能自治,应当受别人的管理”。⑦皮名举:《对东京事变的感想》,《独立评论》第192号,1936年3月15日。并在日内瓦国联开会的时候公然侮辱中国,“不是一个国家,乃是一个地理名词”。⑧皮名举:《对东京事变的感想》,《独立评论》第192号,1936年3月15日。二二六事变后,中国学者趁此回击:
日本时常向世界宣布说她是远东最文明的国家,中国是最无秩序的国家,这一次政变残酷的情形足以证明这种宣传是不合事实的。恐怕一般国际政论家要说远东最无秩序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日本。⑨崔书琴:《日本政变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政问周刊》1936年3月4日,第10号。
更有学者辛辣地忠告和讽刺日本:
认清自己的地位和能力,从此以后好生管理自己,少管别人的闲事。须知日本的祸乱是在内而不在外……一个不能保护他自己元老重臣性命的国家想来管理旁人,实在有点太不自量了。⑩皮名举:《对东京事变的感想》,《独立评论》第192号,1936年3月15日。
对于事变的性质,叛变初发时,陆军省当局发表谈话说:
青年将校此次袭击之目的,系以当前内外严重时局之下,元老、重臣、财阀、官僚及政党等,将从事破坏团体,故拟申明大义,以图完成拥护国体之本旨。⑪又荪:《日本政变的观察》,《独立评论》第191号,1936年3月8日。
叛变的青年将校们也自称是“无上之忠君者”。⑫又荪:《日本政变的观察》,《独立评论》第191号,1936年3月8日。叛变平定后,陆军省当局发表谈话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29日,川岛陆相声明:“此次军内发生未曾有之叛乱,致紊乱军纪……对于国内外显然有污国家及国军之名誉,指贻昭和圣代历史以不可拂拭之玷。”⑬又荪:《日本政变的观察》,《独立评论》第191号,1936年3月8日。在中国,绝大部分人认为此次事件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空前未有的大政变,但并非革命。⑭又荪:《日本政变的观察》,《独立评论》第191号,1936年3月8日。例如《大公报》认为:“本事件性质与五一五相类而重大过之。……无论昨早暴动之人数及规模若何,其行动目的,即在制造政变,而非叛乱性质。”⑮《社评:日本之暴力政变》,《大公报》1936年2月27日,第2版。《申报》也同样认为“此次政变,其严重性迥非五一五事件所可比拟”。⑯《时评:日本大政变之观测》,《申报》1936年2月27日,第5版。“二二六政变,实为日本法西斯蒂运动迈进中必然产生的结果,而且也表现这次政变实为法西斯运动与议会政治最后之决战”。⑰炳琦:《日本二二六政变之回顾与前瞻》,《创进月刊》1936年第3卷第7期。
关于事变的原因,论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分析阐述。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的朱显祯总结了中外人士关于暴动原因的观察,大致有:1.不满现政府外交政策之软弱;2.未能达到扩张军费预算之目的;3.总选举结果,政府派胜利,少壮派军人以现政府命运延长,扩张军费无望;4.近来日俄两国缔结不侵犯公约之风说,甚嚣尘上,因此惹起少壮派军人的愤懑不平;5.苏联两次五年计划成功,军备渐渐完整,日本少壮派军人感觉恐慌;6.世界法西斯蒂思潮之刺激。①朱显祯:《日本二二六事变之剖视》,《日本二二六大政变及中日问题》,第12~13、15页。但朱显祯认为这些或许可以说是间接原因,却不是直接原因。朱认为事变的根本原因是民族性中的“大和魂”精神,即武士道的结晶。因为这次暴动是有背景和有组织的日本整个少壮军人派之暴动,一般日本人不但不非难他,诅咒他,还颂扬他,称他们为“无上之忠君者”。②朱显祯:《日本二二六事变之剖视》,《日本二二六大政变及中日问题》,第12~13、15页。
总之,对于二二六事件爆发的原因,舆论从各角度进行了讨论,但对于事变的根本原因,大家则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日本经济结构的问题,有人归结为政治派别的矛盾斗争,有人认为是民族性的根源。一方面说明了该事变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亦可以看出,即使自诩最了解日本的中国人,对日本国内复杂现象还是有一种雾里看花,看似明白却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二、对事态走向及影响的分析探讨
日本如何善后,可反映其日后政局和外交的走向,所以各国朝野甚为关心。最初日本呼声最高的是由近卫、荒木、真崎合作组阁。“西人一闻荒木之名,或即目为极端派之胜利”。③《社评:东京凶变之国际观》,《大公报》1936年2月8日,第2版。相对西方人对荒木等急进派组阁的疑惧,中国舆论显得相对较为淡定,认为:
欲收拾时局,恐实有荒木登台之必要,荒木受一般青年军官之同情,恐尤不可少。要言之,日本乃支配于一种大势,军事领袖,不过顺大势而推行,是则较一般激烈军官信仰之人,反较易于驾驭矣。④《社评:东京凶变之国际观》,《大公报》1936年2月8日,第2版。
对于已经饱受日本侵虐的国人来说,“所谓积极强硬,已惯闻惯受”,而因应之道应为“自守一定限度,并不问对方内部如何变迁也”。⑤《社评:东京凶变之国际观》,《大公报》1936年2月8日,第2版。对于日本此后的对华政策“为缓为急,为硬为软,倒可不必过分重视,因为日本对华早有一个固定的‘国策’,无论哪一派当政,都是一条路线,只于是缓急软硬之差而已”。⑥《社评:日本暴变的由来》,《大公报》1936年3月2日,第3版。
对于事变后日本政府的善后,大部分中国学者分析不外乎三条出路。其一,严厉处分叛兵,并肃清其根源,以振纲纪,维持元老重臣的路线,仍由维持现状派组阁。其二,不敢对叛兵作严正处分,且为易得少壮军人的信赖计,索性任命真崎、荒木、平沼等打破现状派组阁。⑦《社评:日本暴变的由来》,《大公报》1936年3月2日,第3版;《短评:东局鳞爪》,《大公报》1936年3月4日,第4版。其三,两派之间相互妥协,形成调和内阁,但更多体现军部意志。但舆论分析认为,由于“日本政党内阁已名存实亡,沦为军阀官僚的附庸”,⑧张逸如:《日本政权的解剖及政变后的趋向》,《国闻周报》1936年13卷9期。所以第一种方式难以实行。另外,由于政府与急进派的矛盾以及急进派法西斯自身没有一致的政纲,各法西斯团体间不能形成统一的战线,且政变未必能获得一般国民之同情。因此军部独裁或者与急进派之联立内阁也难以实现。所以,第三种缓冲调和内阁最有可能。至于事变后,由荒木、真崎、平沼等单独或联立内阁的传说,有舆论认为“这不是激进改革论者之企望故意宣传,就是政府为了防止事件扩大所放之烟幕弹”。⑨张逸如:《日本政权的解剖及政变后的趋向》,《国闻周报》1936年13卷9期。并且元老重臣方面之“有力人才内阁”与海陆军方面之“强力的举国一致内阁”的呼声已经频频由东京传出。所以有学者断言:“继任内阁,不拘何人出马,其所受军部之影响将更大,法西斯化的程度也必更为加强。”⑩张逸如:《日本政权的解剖及政变后的趋向》,《国闻周报》1936年13卷9期。
最初呼声很高的荒木、真崎、平沼等人并未得到组阁机会,近卫文磨以健康为托辞拒绝了组阁任命。在此危难时刻,原外相广田弘毅被推到了幕前,对于广田组阁,各方有着不同的认识。一般中国人“一闻此次日本事变,则惶然惧,若恐大祸之将至,闻广田拜受大命组阁,则色然喜,以为今后可高枕而卧,因为广田是主张和平政策,而不是主张焦土政策的重要分子”。⑪《谈言:不要希望人家》,《申报》1936年3月10日,增刊第1版。有评论认为:“西园寺之推荐广田,实为意外英断,揣其用意,当为侧重调整外交,勿令恶化。”⑫《社评:日本政局之形势》,《大公报》1936年3月7日,第2版。国际社会的反响亦大抵和国人相似:
广田任命一传,英美即有欢迎之反响,而广田对俄,向主张缓和,是新阁若成,日俄关系亦暂纾。且外相拟任吉田茂,吉田为牧野之女婿,亦老练之外交家。是以广田内阁之色彩,自国际的观点论,将认为日本较稳健的文治派之政府也。⑬《社评:日本政局之形势》,《大公报》1936年3月7日,第2版。
也正因为如此,广田内阁遭到军部反对而搁浅。国人“又不免忒忒然而惧之”。⑭炳琦:《日本“二二六”政变之回顾与前瞻》,《创进月刊》1936年第3卷第7期。在和军部妥协,更换阁员名单的基础上,广田新内阁终于成立。中国舆论绝大部分对此持消极评价:
他是军部的傀儡,他之所以能成立新阁,是因为接受了军部的条件而变更了原定阁员的三分之一,以替代军部和接近军部的份子,他更是忍痛地接受了军部提出的膨胀军费,扩大军备,对外强化政策,对内消灭财阀势力的苛求,他更接受了军部的要求将政变责任之一部分而归之于政党。由此可知,广田内阁的特质,完全是仰承军部鼻息的……必对中国施其一元政策,秉承军部意旨,向中国加紧掠夺。①炳琦:《日本“二二六”政变之回顾与前瞻》,《创进月刊》1936年第3卷第7期。
亦有人持相反观点,认为:
广田内阁成立的经过,表面上似乎是改革派的胜利,实质上则为维持派的成功。……从阁员人选而观,找不出一个改革派的人物,就是新陆海军大臣寺内和永野二人,也不是改革派所拥戴的领袖,由此可知广田内阁的出现,依然是维持派把持政权的成功。②林云谷:《广田内阁成立经过之内幕》,《日本评论》第8卷第3期,1936年4月15日。
事变发生后,情况虽尚未完全明了,但中国舆论已意识到此次事变的重大影响问题。
中国舆论主要从军界、政界和经济界三方面分析了事变对于日本国内的影响。日本军部因对此次政变既不能采取高压手段,彻底肃军,亦不能完全听从于少壮军人的跋扈,所以两派只能妥协,而结果则会导致军部内“下克上”趋势增进,酿成日后的祸根。政界方面,元老重臣政党官僚势力虽大受打击,但日本的社会机构经济组织没有根本推翻,他们的势力不致一无所有,所以不论今后内阁的首脑是谁,恐不至于有“飞跃”。不过日本军部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自然要比以前更进一步了。财政界,因为公债的消化力有限,民众的租税负担力亦难再予增加。所以增税政策虽较为可能,但其负担客体或将由财阀让步。③参见《日本政变聚谈会》中邵玉麐的观点,《日本评论》第8卷第2期,1936年3月15日。
日本政变对外影响,关系最密切者为苏联与中国。日本政变对于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为何要重视此次政变,《东方杂志》做了如下一针见血之分析:
首当其冲者就是我国,其次为苏联与英国的殖民地。但是苏联的国力强于日本,进攻苏联虽是日本法西斯所愿意的事,但他因为有种种关系常常表示犹豫,至于觊觎英国的殖民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英国现在虽是困于欧洲势力的束缚,不能用全力以阻止日本,但是因为美国对日本的嫉妒心甚重,若日本进占英国殖民地,则英国有与美国联合的可能。英美如联合攻日,则日本的胜利就很无把握。所以在这样的国际阵势之下,恐怕日本向外发展的目标最后将更集中于我国,这不是夸大推测之词,东京事变对于我国实有严重的关系,希望吾国人士万勿以此为内变而忽视了其严重的对外影响。④陈开夫:《日本惨变的社会背景与其影响》,《东方杂志》第33卷第7号,1936年4月1日。
二二六事变后,中国舆论普遍认为:
不论谁继任内阁,必须以积极的外交政策相号召。故对华即将加紧侵略,对俄更将强硬,实为不可避免之事实。⑤邓石士:《日本大政变的考察》,《日本二二六大政变及中日问题》,第11页。
因为,“一般日本军阀,不问其稳健还是急进,莫不欲孚民望,欲孚民望,唯有侵略中国”。⑥胡恭先:《二二六事变之里因》,《日本二二六大政变及中日问题》,第18页。在一片悲观声中,也有学者安抚国民:
日本政变之后增加我中华民族实际上之自信力量。政变后为缓冲时局,强有力内阁必求中日问题之痛快解决,结果中日一战难免,可促进中国内部之团结,未必不为中华民族之福音。⑦徐敦璋:《我对于二二六政变的感想》,《日本二二六大政变及中日问题》,第23页。
更有学者从国际视角出发,认为此次政变对中国亦有有利的地方:
第一,日本对外强化,可使中国外交当局,认清日本的要求究在何处,认清之后,自易对付。我们最怕的是,是她那种蚕食式的侵华政策。第二,日本对华强化的结果,会使英美俄合作更易实现,使日本更形孤立。⑧《日本政变聚谈会》中袁道丰的观点,《日本评论》第8卷第2期,1936年3月15日。
“大政变发生后,有许多国家都已感觉忧虑不安,英美俄各国对日的戒备更要增加,只有德意两国对日似乎还表同情”,所以,“日本在国际的地位将因这次大政变而恶化;以后我国对日交涉时能够获得更大的国际同情”。⑨崔书琴:《日本政变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政问周刊》1936年3月4日,第10号。更有人认为少壮派对曾立殊勋的元老“杀人如鸡豕”,“日本元老几无毅力足以阻拦狂澜”,“我国如能抵抗此辈虎狼暴徒,则必能博得全世界之同情”。①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1页。
三、关于日苏战争可能性的认识分歧
中、日、苏三国关系就像一个连环锁,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苏联为战争目标的少壮派所发动的此次政变,是否会加速日苏战争,成为中国朝野热议的话题。西方各国亦关心日苏开战的可能性,因为它与世界局势密切相关。
东京事变以后,“各国论者,多虑日本此后,对外更强硬化,极端化,尤推料对俄战争之迫近,俄京观察,亦倾于悲观”。②《社评:东京凶变之国际观》,《大公报》1936年2月8日,第2版。中国舆论分析日苏关系时,认为二者不管从意识形态还是利益冲突来讲,二者的矛盾不可调和,日苏之间战争最终无法避免。但日苏是否会马上开战,则看法各异。有学者认为:
日俄战争,即快要爆发。我们从日本屡次拒绝与苏俄签订互不侵犯公约一事,即可察知日本对俄作战的决心,已非一日。日俄战争,究在何时虽不能断定,而此次政变结果,必促进爆发的机会,当无可疑。③《日本政变聚谈会》,《日本评论》第8卷第2期,1936年3月15日。
不少学者则持相反看法。例如1936年3月3日由《日本评论》主编刘百闵招聚的《日本政变聚谈会》中,大多学者都认为日苏战争不会马上爆发。
日俄战争尚非其时。在过去两年来,苏俄曾对日本一再退让……而日本在未巩固它在内蒙和华北的地位以前,也决不会向外蒙或苏俄进攻,所以在最近的将来,日俄关系是不会紧张的。④《日本政变聚谈会》,《日本评论》第8卷第2期,1936年3月15日。
更有部分学者指出日苏战争“实在是日本的烟幕弹,或者也可说是日本的骗局。……日俄战争的发生,迟早终有实现的一日,不过照现在的情形,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或者可以假定至少在一年以内,是决不会发生的。……日本对俄作战是较远的目的,对中国控制——尤其是对华北控制是最近的目的,而宣传防俄或对俄作战是其手段。关于这一点,日本政变不政变都不会改变”。⑤《日本政变聚谈会》,《日本评论》第8卷第2期,1936年3月15日。
为了证明日本暂时无意对苏开战,中国舆论界转载了日本著名专家学者及权威媒体的观点。例如,记者兼俄国研究专家布施胜治在大阪《每日新闻》经济旬刊载《俄国有战意乎》一文,其结论亦谓:
俄国之强化军备,乃以日德为假想敌,而其主要正面,实在西方,他所以忧虑的是怕东西双方的夹攻,如果东方的威胁能缓和,则俄国当然会集中其实力于正面的西方,如在背面的刺激加重,则必移其全力以对后方。⑥子修:《动荡中之日俄关系》及《日苏空气之缓和》,《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17期。
《东京日日新闻》亦忠告政府,不可给予俄国以决心开战的机会,甚至且有主张(如海军方面及室伏高信等人)南向发展,以避免与俄冲突的。所以由这种消息看来,日本目前绝对没有对俄开战的决心。⑦子修:《动荡中之日俄关系》,《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17期。
针对国人对日苏战争抱有过分期待与依赖心理,有学者敲响了警钟。
对日本最有利益的政策,乃是先执行独占中国的计划,而非对苏俄开战。……日苏战争也许不可避免,但在日本未完成他独占中国的计划之前,是不会进攻苏联的。事实上,日本自己常夸大日苏战争的危机,借此而进一步的占领中国的土地,其作用一方面可向欧美国家表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乃为进攻苏俄的准备,并无排斥他们的意思,另一方面可罪责中国又趁日俄战争而攻击日本的心迹,因此提出更严厉的要求,使中国为日本的附庸,永无复苏之日。……有一部分人常常设想解脱日本侵略与压迫的惟一机会,是在日苏战争的爆发,因有此一种观念存在,所以其期待日苏战争的心理,有时候反而把抵抗日本侵略的心理遮掩住了,这是一种很不幸的设想,因为我们自己若不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不待日苏战争爆发,我们早已成为牺牲品了。⑧戴尔卿:《日本推出海会后之外交动向与中国》,《日本评论》第8卷第2期,1936年3月15日。
既然日苏一时不会开战,又怎么解释两国边境上不断发生的武装冲突呢?有不少学者认为:“这实为日本欲笼罩一般人士的耳目所放的烟幕弹。”⑨林金墉:《紧张中之日苏战争问题》,《日本评论》第8卷第4期,1936年5月15日。其真实用意大致为:以反苏联宣传为取得国际间同情而加强对华侵略;以反苏联宣传为破坏法苏互助公约缔结的工具;以反苏联战争空气来收买国内议会的选举票。①林金墉:《紧张中之日苏战争问题》,《日本评论》第8卷第4期,1936年5月15日。
假如日苏开战,中国是否真的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呢?林金墉的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
日本对苏备战,其势必图控制华北的一切,使其能完全俯首听命而后已……日苏关系愈险恶,而日本对华的高压手段则愈加强,而中日交涉,愈形紧张。②林金墉:《紧张中之日苏战争问题》,《日本评论》第8卷第4期,1936年5月15日。
日苏一旦发生战事,中国究应如何自处呢?中国舆论界认为,不外有三条路线可选:“(一)联甲抗乙(二)联乙抗甲(三)局外中立。但事实上中立只有吃亏,且必牵入漩涡,故第三条线是走不通的。……总之,我们不应苟安,不能躲避,目前只是备战求和。”③《日本政变聚谈会》中周志由的观点,《日本评论》第8卷第2期,1936年3月15日。“中立虽是一个稳健的政策,但事实上决不可能。将来我国恐终于被逼卷入漩涡。我们希望敌友的取舍,能决于我们自己。取舍的标准,现在当然言之过早,但决不能离开‘两害之间,取其轻,两利之间,取其重’的原则。”④崔书琴:《苏蒙议定书之政治意义》,《政问周刊》1936年4月15日,第16号。可见,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对于大众期盼日苏开战,中立渔利的思想持反对态度,认为其不仅有害且不可能实现。
四、媒体舆论与政府的态度及决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政界、学界各派竞逐,杂志业十分兴盛,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更是中国期刊创办的一个高潮期。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强,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国人对日本的兴趣大涨,不得不加强对日本研究。因此该时期,在众多杂志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专门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性期刊。1930~1947年,中国主要日本研究杂志达31种之多,全国性杂志一下子增加到13家。这些杂志针对性强,价格便宜,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普及性,使得日本研究“从少数人写少数人看,变成大家写大家看,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研究的普及和深入”,日本研究杂志真正地走向了普通民众之中。⑤王坤:《试论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以〈日本评论〉为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2卷第6期。
一方面,报纸杂志等媒体越来越发达,日本研究越来越普遍深入。随着国人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国事的关心日增,相当多的国人都养成了通过报刊了解国内外时事的习惯,《大公报》《申报》等有影响力的报纸发行量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政府也日益认识到舆论宣传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对媒体的利用和控制。例如,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后每天必读《大公报》,且非常重视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蒋甚至亲自过问《中央日报》问题。另外,国民政府亦非常重视与学界名流间的联系和互动。例如,专门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杂志《日本评论》,在研究日本的问题上具有广泛的影响。《日本评论》的几任主编都是国民党政府的上层人物或是高级知识分子。主编刘百闵曾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又曾被聘为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教授。刘百闵被称为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笔杆子”之一,所以《日本评论》似乎又有着国民政府官方的背景。⑥王坤:《试论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以〈日本评论〉为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2卷第6期。
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局势向来甚为注意。二二六事变后,蒋日记中连续几个月都有相关记载,一方面关注其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不断考虑如何利用此事件处理中、日、苏间的关系。⑦关于蒋介石的态度及应对,参见赵晓红:《二二六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因应及其困境》,《民国档案》2017年第1期。蒋介石一方面希望对日“以少壮派为对象”,要想法设法“离倭挑倭”,⑧周琇环编注:《事略稿本》36,1936年3月4日,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64页。促成日本内讧,争取中国国防准备的时间。另一方面,蒋希望挑起日苏之战,而使中国得以“鹬蚌相争”之利。对于国人认为日苏开战时机尚非其时,蒋介石并不认同。实际上蒋对日苏开战抱有很大期待,认为:
夫倭俄之战争以理测之犹两虎食人而斗,当迫在眉睫矣。而有人犹以为欧洲无事,则倭俄不至战争,此固亦有一部分理由,殊不知倭寇迫不及待,正欲以东方之战而挑起世界大战,惟俄阴险尤甚,其心意可知,其行动则不易测,吾中国更宜慎之又慎也。⑨周琇环编注:《事略稿本》36,1936年4月8日,第319~320页。
如果日苏战争爆发,中国应采何种因应之道,一直是蒋介石为之殚精竭虑的重要问题。蒋介石对日本国防政策长年观测的结论是,日本陆军是以对苏作战为目标,海军以对美作战为布局。①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12年,第203页。二二六事变后,蒋介石认为日本军部矛头必首先指向苏联,因此“俄方或亦更为着急”。②蔡盛琦编注:《事略稿本》35,1936年2月27日,台北:“国史馆”,2009年,第666页。因为日本的目的在于“攻俄而制华”,从这个意义上,中苏为共命运体,显然有联合的可能,但是蒋担忧中苏联手的不利后果,而且中苏关于签订互助协定的商议并不顺利,在处理共产党问题方面,两方亦分歧明显,所以蒋介石决定:“俄共态度在晋匪未受打击以前不与之商讨一切。”③周琇环编注:《事略稿本》36,1936年4月8日,第76页。蒋介石不断比较日、苏态度,认为“俄之狡猾恶毒甚于倭寇”。④蒋介石日记手稿,1936年3月20日。蒋研究日、苏利害关系,批判那些主张联苏者:“一般书生文人以为非联俄不能生存,青年无智者多从而附和之,非痛加惩创,不足以使生觉悟也。”⑤周琇环编注:《事略稿本》36,1936年3月21日,167页。
总体而言,中国朝野对事变的背景、原因、事态动向和善后处理等方面的分析和看法上大致相似,但在日苏是否会立马开战以及日苏开战后中国的立场等问题上,舆论、外交部及蒋介石等国民政府上层之间的看法则有较大的分歧。对于具有个人独裁性质的国民政府政权来说,蒋介石的看法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更显其重要性。二二六事变前,中日关系因华北危机不断恶化,面对艰难处境,蒋介石在积极联苏的同时,更希望全面改善中日关系,并为此做了不断努力。蒋介石希望游走在日、苏之间,可让中国有更多的自由选择,这也与舆论所倡导的取舍敌友的标准不谋而合。与舆论所分析的中立对中国不利的观点相反,蒋介石一直希望促使日苏先战,中国尽可能中立。如中立不成,蒋倾向亲日,而国人大多偏向联苏。蒋曾在日记中感叹:
何以华人如此亲俄而恨倭,何以不能使华人亲倭如亲俄,此其故实多由倭人侵略之暴而急,俄人态度之阴而柔乎?只可惜倭人不自知其弱点而欲外交上实现根本之方针难矣。⑥高素兰编注:《事略稿本》38,1936年10月6日,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571页。
而在联日方面,蒋又不能不顾虑国内强烈的反日情绪。事实上,蒋介石所期望的中立亦因日本要求中国对苏强硬,苏联要求中国对日强硬而无法实现,这也正中了舆论所谓中立事实上绝不可能的预言和分析。
五、结论
二二六事变后,日本国内形成所谓“全国一致”内阁,皇道派势力被肃清,并从此没落,但掌权的统制派却继承了皇道派的大多观点,因为二者在实质上本来就没有根本性分歧。此后,日本发动了全面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最终把日本引向了战争的深渊。因此,有人把二二六事变称为日本亚洲侵略战略上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开始。当时国人对此重大事件的关注也反映出国人对时事的关心和敏感度。并且当时中国舆论所分析的日本政局善后和走向以及对中国的危害也基本与史实相符。虽然国人对中国因应之道多有建言,但在国际形势尚未成熟之前,作为孤立无援的弱国,多有无奈和无力回天之处。但时人对此政变的关注与讨论却并不是全无用处。
首先,通过对该事件的探讨,中国人再次深刻意识到培养“日本通”以及“俄国通”的重要性。
甲午战败,国人上下对日本不得不刮目相看,掀起一股学习日本、了解日本的风潮。但是直到民国初年,中日间认知仍非常不平衡,戴季陶曾尖锐地批评道:
“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都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不愿意听,日本人不愿意见,这真叫“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⑦戴季陶:《日本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9页。
日本二二六事变发生以后,国人颇感对日本的无知与日本通之缺乏。“我们承认中国有‘日本通’,但是太少了,与日本的中国通比较,差太远了。”⑧张云伏:《卷头语》,《日本二二六大政变及中日问题》,第2页。直到1940年,竺可桢阅毕英国驻德大使亨德森所著《出使辱命记》后,仍感叹:“何以吾国有许多日本通,而竟无一本关于日本内幕之书?戴季陶之《日本论》亦卑卑不足道也。”①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7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33页。面对眼前的困境与教训,有学者建言:
中国教育系统中之外国语,是以英文为主的,政府应该另设一个外国语学校,这个学校目前不妨以日文和俄文为主,一早就研究日俄两国宗教、文学、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的基本人才;同时,这个学校亦可作为对日、对俄外交人才的摇篮。今日大家急着找“日本通”,此后我想必有更着急找“俄国通”的一天(虽然意义也许不同)。这种学校,似乎是中国的百年大计之一。②陶陶:《从日本政变说起》,《独立评论》第197号,1936年4月19日。
在政府层面,抗战期间确实有对留日人员的培训。另外,以蒋经国为中心,确实也有一批专门研究苏联的专家学者及活动。
其次,该事件亦体现出近代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的相互配合与促进作用。
二二六事变发生后,相较苏联政府的机关报中对日本政变的报道、评论和批判,作为国民政府机关报的《中央日报》仅注重报道政变本身进展情况,而未作过多评论。这也体现出国民政府在处理涉及中日苏关系问题上,小心谨慎的态度。就连《大公报》等大报“所载者皆日本公式发表之事,凡关日本政治之流言蜚语,虽闻之亦不载,此非中国报业之全无消息也,徒以因重视国交及对日本国民表示友谊故耳”。③《社评:读中央社驻日记者第一电》,《大公报》1936年7月18日,第1张第1版。
相对官方或半官方的言论克制,中国民间舆论则对日本政变展开了各种评论,甚至利用日本政变,趁机打击对手,宣传在亚洲失序的国家,不安定的因素是日本,而不是日本向世界所宣传的中国等,有力地促进了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的相互配合。1936年5月,日本第69次帝国会议上,男爵园田武彦质疑广田:五一五及此次二二六事件在国际上使日本信用失坠,甚至被他国称作劣等国,总理是如何考虑的。广田答称:当初此事件对于外国有很大刺激,外国人会认为这是真正的日本,外国人不怎么知道日本的事情,随意想象,对日本有所误会,有关官厅应该找机会对日本的建国精神及将来应如何进取的日本国魂等进行充分说明。④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1421300、帝国議会関係雑件/質問答弁関係/外交関係質疑応答要旨第一巻(A-5-2-05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本所面临的这种国际舆论困境不能说和中国的宣传不无关系。
然而,中国媒体舆论与政府决策之间既有一致的地方亦有分歧所在,政府注重对媒体的利用及导引的同时,亦不能不受媒体舆论的影响,在作决策时不得不考虑舆论所代表的民心民意。但我们应注意的是,政府一些举措,多大程度是受舆论的影响,仍需审慎考察而得出结论。因为在民国时期,我们确实不能忽略舆论的发展及其影响力。但另一方面,亦有大势所趋,政府和舆论的思路不谋而合的一面。
再者,中日双方以新闻报纸为阵地,展开外交、舆论与情报信息等之间的攻守战。20世纪的战争已不仅仅是武器之间的比拼,更是外交、舆论、情报信息之间的一个综合较量。各国之间除了利用间谍、截获对方电信情报信息、通过驻外使馆和武官收集情报以外,也非常注意收集和利用他国的新闻报纸信息,并利用己方的新闻报纸做相应宣传。例如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日本非常注意收集英美苏中等国的舆论信息,并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消除外国人对其之“误解”。对于中国新闻舆论,日本尤其重视《大公报》,认为《大公报》原来就是关于中日关系的中国第一评论,现在说是中国舆论界的代表也不为过。大公报的一些社评不仅是对中国人进行开导,同时窥其真实意图又有使日本广知之意,故应加以参考。⑤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140400、日、支外交関係雑纂/輿論並ニ新聞論調第五巻(A-1-1-08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大公报》在中国政府中央社向东京派驻正式记者驻日,并发表第一电之后,以社评的形式肯定了其重要意义。并呼吁:
日本朝野各方此后充分利用中国中央社在东京新设之特派组织,藉向中国国民宣布意见,或辩论事实,中国社会定将充分倾听。⑥《社评:读中央社驻日记者第一电》,《大公报》1936年7月18日,第1张第1版。
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将此文翻译并呈交给了有田外务大臣。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140100、日、支外交関係雑纂/輿論並ニ新聞論調第五巻(A-1-1-08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由此可以看出,新闻报纸在中日之间的外交辅助、舆论导向与情报信息获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February 26 Incident and the Reactions of Chinese Public Opinion
Bythe early1930s,officers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split into two main informal groups: the Kōdō-ha“Imperial Way”faction and the Tōsei-ha“Control”faction.The two factions have different notions 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diplomacy,which lead to the February 26 Incident.This Incident had not only caused panic in Japanese society,but had also aroused worldwide attention.Since China would be the first to be affected,Chines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were concerned about this incident.Chinese media made extensive coverage of the incident,especially the background,cause and impacts,especially it’s influence on the movements ofSino-Japanese relations and the possibilityofJapanese-Soviet warfare.
February26 Incident,Chinese Public Opinion,the Kōdō-ha“Imperial Way”Faction,the Tōsei-ha“Control”Faction
K26
A
0457-6241(2017)10-0057-09
赵晓红,浙江大学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2017-03-26
*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人文社科类)重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Y2014315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蒋介石资料数据建设》(项目编号:15ZDB048)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