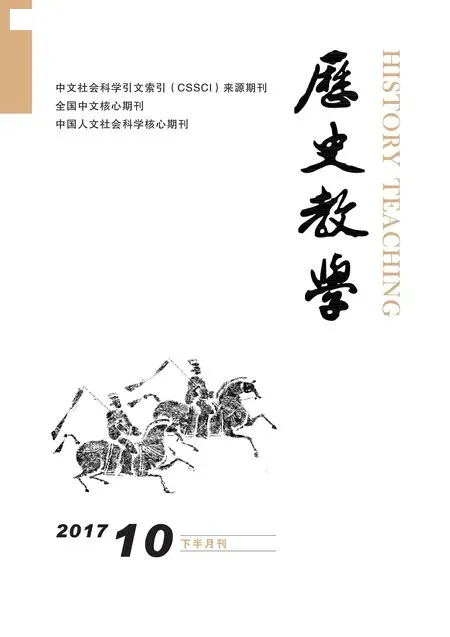A B团与富田事变新探
——兼与戴向青先生商榷
王承庆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210008)
A B团与富田事变新探
——兼与戴向青先生商榷
王承庆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江苏南京210008)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前夕,苏区最高领导层围绕反“围剿”战略方针产生严重分歧,并对根据地反“围剿”准备造成直接负面影响,如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将可能造成反“围剿”作战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反AB团扩大化就具有了某种可理解的“合理性”,并成为引发富田事变的导火索。为确保反“围剿”作战全局胜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富田事变作出果断处置,无异于“壮士断腕”。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AB团,富田事变,戴向青
发生于1930年12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的富田事变,当时即被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先后定性为“A 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之后,关于富田事变的讨论基本上是个学术禁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术界开始拨乱反正。1979年,江西省委党校的戴向青先生发表《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一文,标志着学界对富田事变的研究开始打破坚冰。①刘海飞:《富田事变研究述评》,《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随后,海内外围绕富田事变陆续发表论文数十篇,还出版了专著。②论文主要有:戴向青的《富田事变考》[《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79年第4期]、《关于论富田事变问题》(《江西社会科学》1980年专刊)、《论AB团和富田事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必须以严肃态度对待肃AB团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AB团灭亡后共产党为何还反AB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5期)等;罗惠兰的《论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中对肃AB团错误的抵制》(《求实》1989年第1期)、《中央苏区肃AB团述评》(《求实》2000年第2期)、《再评罗坊会议》(《历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4期)、《毛泽东与富田事变及肃AB团责任问题考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5期)等;戴向青、罗惠兰的《论毛泽东在肃AB团问题上发生错误的原因》(《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阎中恒的《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79年第4期];梁尚贤的《对〈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的一点质疑》[《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0年第2期];陈铁健的《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读〈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札记》(《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李维民的《从共产国际档案看反“AB团”斗争》(《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景玉川的《富田事变时刘敌给中央的信》(《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马社香的《驳高华“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经济导刊》2014年第8期),等。专著有戴向青、罗惠兰的《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及台湾学者陈永发的《中共早期肃反的检讨:AB团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上册)。关于富田事变的起因、定性和影响,成了各方争论的焦点。③赵金平:《近三十年肃“AB团”和“富田事变”研究》,《淮阴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学界大多认为,富田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反A B团的扩大化。而进一步研究发现,所谓“A B团领导的”的说法“证据不足”。于是就有学者得出“富田事变是历史错案”的结论,并据此提出“应彻底平反”的要求。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富田事变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有着复杂的深层原因,这一原因在当时被掩盖,后来也被学界所忽视。本文就此谈些看法。
一、总前委与省行委的冲突
富田事变发生不久,邓小平率红七军团于1931年4月进入中央苏区,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 B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变之爆发。”①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9~20页。这即是说,所谓“右倾”,所谓“A B团的作用”,主要还是认识问题;富田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这种冲突大致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二七”会议上的土地政策之争。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陂头召开的“二七”会议,是关系中央苏区建设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激烈争论。赣西南党的领导刘士奇和曾山等主张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并承认土地私有。而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等则坚持土地应归国有,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乃废除私有制,如果土地按人口重新分配,势必强化农民的私有财产观念,这“简直是开历史倒车”;支持江汉波的李文林更担心土地很快分给贫农,可能会对富农和小地主冲击过大,一旦主力红军离开,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农民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②陈永发:《中共早期肃反的检讨:AB团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上册,第207~208页。这一顾虑不无道理,但也反映了江汉波、李文林等或多或少已站在“富农和小地主”的立场考虑问题,它必然不能完全调动农民(贫农、雇农和佃农)参与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其进一步的结果将是革命的不彻底性。主持会议的毛泽东表明了支持刘士奇、反对江汉波的鲜明态度,指出:“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与男女老幼平分,应该采取后者,这是为了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所不可忽略的紧要策略。”强调“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③《前委通告第一号——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1930年2月16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9页。但这次会议由于受到中央关于开展反对取消派斗争指示的影响,错误地做出了开除江汉波党籍的决定。这就进一步激化了赣西南苏区的党内斗争。
二是“二全”会议后赣西南地方党的集体“左”转。1930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派李文林、段良弼、曾山为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全国苏区代表大会。李文林和段良弼在了解了上海中央的具体意旨之后,从此成为立三路线的坚定执行者。这年8月,二人回到江西苏区后,立即召集中共赣西南第二次全体会议(即“二全”会议),彻底修正毛泽东的土地政策。同时严厉批评和打击支持毛泽东的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指责刘士奇:“消极反抗中央、省上的正确政治路线,曲解党的民主集中制……多次拒绝出席二全会议,破坏二全会的政治斗争意义。”④《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决议案之二——党对政治斗争问题决议案》(1930年8月27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央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9页。会议还指责赣西南“过去的党是种波浪式的推进、傍着发展的方式,这都是农民意识的反映,没有积极猛力前进的精神”。⑤《赣西南特委(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9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28页。李文林对刘士奇的这些批评之词,与中央立三路线批评毛泽东的说辞如出一辙。“二全”会议后,中共赣西南特委全面执行李立三“左”倾路线,领导机关“集体左转”。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欧阳钦后来报告说:江西地方党部“自‘二全’会议之后到富田事变,完全接受了立三路线,经过A B团的利用,疯狂的执行”。⑥《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65页。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也认为:“二全会议,就是立三路线领导的会议,实际上是A B团操纵向党进攻。二全会议后立三路线便完全统治了江西的党,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把地方武装完全集中到二十军卅五军,抛弃苏区的巩固工作,冒进的攻打中心城市,攻赣。……立三路线这样的发狂,结果做了A B团一面好旗子,造成反革命的富田事变。”⑦《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号》(1931年4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302页。这些都表明,“二全”会议后赣西南地方党执行的路线方针与毛泽东正确路线渐行渐远,也反映了江西苏区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相当尖锐和复杂。
三是反A B团的扩大化。A B团,原本是江西省内一个秘密反共组织,于1926年底或1927年初由段锡朋、程天放和周利生等人创立。A、B原本是指A B团内部的两个次级组织,A团为核心,B团为外围。其后因缘附会,A B变成了反布尔什维克(Anti-B olshevik)的缩写。1927年4月国共分裂后,江西省的军政大权落入滇军将领朱培德之手,A B团则控制了地方党部,主要在赣西南活动,以段锡朋老家吉安县城为大本营。但戴向青先生认为,1927年“四二暴动”后,①AB团成立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篡夺了江西省党部的领导权,中共党组织联合国民党左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共产党员邓鹤鸣等10余人于3月中旬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揭露AB团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得到左派国民党中央的大力支持,并于3月20日作出改造江西省政府的决定,由朱培德接替李烈钧任省主席,一些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任委员和厅长。江西人民受此鼓舞,趁势于4月2日组织大暴动,一举摧毁AB团把持的江西省党部,并于4月3日在南昌公共体育场举行3万人集会,庆祝反AB团斗争胜利,将捉到的30余名AB团骨干进行了公开批斗。从此,AB团组织彻底崩溃。史称“四二暴动”。A B团的组织彻底崩溃,“寿命仅三个月”,其后“既未恢复也未重建”;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投靠蒋介石之后,于6月5日“礼送共产党人出境”,并释放了被抓的30多名A B团分子,A B团团员遂作鸟兽散,各自在政治上寻找依附。②戴向青:《论AB团和富田事变》,《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不可否认的是,A B团组织虽然被摧毁,A B团分子却大量存在,其反共活动仍可能死灰复燃。赣西南中共党组织从“红五月”开始破获A B团,到8月“二全”会议时,已破获A B团大批组织。在反A B团问题上,李文林比刘士奇有过之而无不及。反A B团的方法包括:“扩大宣传”“组织秘密侦探队”“派人监视行动”“对狡猾而不真实者杀无赦”“对A B团严密调查”“审查A B团要注意供出其组织”等。③《赣西南特委政权工作报告》(1930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114~115页。但到10月4日红军夺取吉安以后,总前委调查发现,李文林领导的许多地方土地未彻底分配、强迫扩大红军、严重脱离群众等问题表现严重,并将这些问题同样定性为“A B团问题”。这表明,这时的A B团已经不是段锡朋、程天放当初成立的A B团组织,而已被异化为“富农反革命分子”的代名词了。“因为A B团是反革命分子,人们也习以为常的把凡是反革命分子均称为A B团”了。④戴向青:《关于论富田事变问题》,《江西社会科学》1980年专刊。反A B团的扩大化,不仅仅是肃反对象、范围的扩大化,更重要的是概念的泛化、扩大化。
四是围绕“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分歧和斗争。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与以李文林为首的江西省行委的分歧和冲突,其源头是中央立三“左”倾路线在江西苏区的反映。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他是在与中央“左”倾错误路线作斗争;而在李文林等人看来,他是在忠实执行党中央的决策指示。第一次反“围剿”前期,毛泽东根据当时敌情变化,在罗坊会议上明确提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把敌人放进根据地内部加以消灭;而李文林、袁国平等人却不赞成这个主张,甚至上升到“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的政治高度,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是保守主义的表现。⑤陈正人:《回忆罗坊会议》(1967年12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1988年,第260~261页。朱德、周以栗、罗荣桓、曾山、陈正人等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滕代远等则“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也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⑥滕代远:《谈有关罗坊会议的情况》(1967年),《江西党史资料》(第6辑),第254页。为了不激化矛盾,罗坊会议并没有把“诱敌深入”方针写入会议决议,而是在会议结束后的10月30日总前委紧急会议上,正式确定“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这个“总前委紧急会议”并没有李文林等省行委的代表参加,红三军团领导人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后,红三军团也有人反对东渡赣江,主张一、三军团分家,夹江而阵。彭德怀坚决支持总前委的正确决定。但李文林却对“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根本不予认可。罗坊会议后,李文林仍四处游说,极力反对诱敌深入,“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彭德怀回忆说:“他们始则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继则散发传单,发表什么告同志书,写出大字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这就不简单是党内路线斗争,而是分裂党,分裂红军了;由党内路线斗争,转移为敌我斗争了,这当然会为A B团所利用。大敌当前,如不打破这种危险局面,就不易战胜敌人。”⑦《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3页。
总前委与省行委的冲突,随着红一方面军战略退却的不断深入而日渐白热化,几乎势同水火。毛泽东后来深刻地指出:正确的路线,从来就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①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06、723页。为了彻底地克服反对“诱敌深入”的错误倾向,约在12月初,总前委进驻宁都境内的黄陂时,突然秘密拘捕了省行委书记李文林。拘捕的理由,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一书,是在红军攻占吉安后,总前委从掳获的大批国民党文件中发现一张A B团工作便条,上面有李文林父亲的署名。戴向青先生曾对这一问题提出过严肃的批评和更正。②戴向青:《必须以严肃态度对待肃AB团问题——评刘晓农的四篇文章》,《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5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李文林是在红军反“围剿”战略退却时被拘捕的。这表明,总前委拘捕李文林,与李文林反对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并干扰红军反“围剿”作战准备有直接关系。拘捕李文林的理由当时并未公开宣布,但从后来的情况发展看,最后仍认定他是“A B团首领”,所以史沫特莱的说法更可能是当时中央苏区高层尤其总前委的一种“内部口径”。之所以用“A B团”这样一个敌我矛盾来处理与李文林等人的路线之争,而没有用“内部分歧”的理由来拘捕李文林,显然是当时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所迫。其目的主要是使广大苏区军民,在正确与错误的路线之争中迅速作出判断和抉择,这样才能军民一致、万人一心,全力以赴打破敌人“围剿”。但是,拘捕李文林并没能立即平息“A B团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总前委与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会商后,“考虑到这种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情况,为了巩固部队和地方党的组织,以利粉碎敌人‘围剿’起见,必须帮助地方上肃清反革命组织,才派李韶九率领一个连来富田帮助江西省委肃反”。这就是引起富田事变最直接的原因。③阎中恒:《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79年第4期。
二、富田事变发生前后的反“围剿”战争环境
富田事变的发生,与当时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形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探究富田事变发生的深层原因,决不能不看国民党军10万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和苏区军民反“围剿”作战的大环境。
1930年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作战命令。这份命令下达的范围是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这就意味着它不需要征求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的意见。既是作战命令,它就要求包括红二十军在内的所有部队绝对服从。该命令规定红二十军的任务,是在赣江以东地区与红三军隔赣江“夹江而阵”,骚扰并“牵制敌人进攻吉安”,同时负责红军主力部队的左翼安全。④《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敌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1930年11月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181~182页。
11月5日,国民党各路大军开始进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除留红三军在赣江西岸监视骚扰国民党军外,主力从袁水两岸向赣江以东的崇仁、宜黄、永丰、新干之间地区转移;另以刚由赣南归建的红二十二军担任吉安城防,掩护江西省党政机关转移。由于红军主力部队按计划实行战略退却,致使国民党军连连扑空。
11月16日,朱德、毛泽东签署训令,对红三军“等敌军到吉安并分散后才攻击”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虽全方面军出击之时机尚未成熟,而各路军一有机会,则应尽各种方法各个击破敌之前进部队,以促成全方面军出击之时机。”⑤吴殿尧主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18日,红二十二军主动放弃吉安,东渡赣江。19日,毛泽东和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等在转移途中,发现吉安县备战情况不好,驻在该地的红二十军少数干部对“诱敌深入”方针仍持怀疑态度,遂决定这一带不宜作反“围剿”的战场。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4页。
这时,毛泽东发现“诱敌深入”以来,各地备战工作出现很大问题,遂于11月20日致信江西省行委,严肃批评“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挥部截至现在,好像没有行使他的职务……实在是非常之大的缺点”,要求“省委应该每天开一次会,召集省苏负责人参加,集中指导一切”。⑦毛泽东:《给江西省行委的信》(1930年11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184~186页。从毛泽东这封信来看,当时省行委领导下的各地区反“围剿”准备工作是相当不够的,毛泽东对此也是很不满意的。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检讨红军反“围剿”战争得失,指出:“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A B团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这里“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①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731页。但这一战机显然已不存在。
为避敌锋芒,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1月25日在永丰县沙溪发布命令,决定全军继续后撤,开赴东固、南垄、龙冈地区集中待命。其中规定红三军团和红二十军、红二十二军“担任出击敌人的中路军”任务,并“在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滕代远的具体指挥下,自择路线分途开向东固集中”。②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5页。根据这一命令,红二十军约于11月底到达东固集中待命,并受红三军团彭、滕指挥。
12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令红二十军分散在富田、东固、龙冈地区活动,协同群众在东固附近各山头构筑假工事,以迷惑敌人;方面军主力秘密向苏区中部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③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2页。这种将红二十军置于外围的作战部署,主要是为了将红军内部反对“诱敌深入”的负面因素降低到最低程度,同时也表明总前委对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已不太信任。不久,总前委收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文件,这就相当于拿到了纠正立三路线的尚方宝剑,于是当即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并秘密拘捕了省行委书记李文林。
12月7日,李韶九奉命带队到富田省行委驻地指导肃反。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及时清除“左”倾错误的负面影响,为反“围剿”作战准备扫清障碍。不幸的是,由于李韶九在执行任务时的擅自妄为和工作方法的严重错误,加上省行委和红二十军部分人员严重的抵触情绪,终于引发了富田事变。
12月14日,事变领导人段良弼、谢汉昌、刘敌等将红二十军主力拉到赣江以西地区,擅自撤离指定的反“围剿”作战地区,脱离总前委领导,致使龙冈以西和根据地西北方向洞开。总前委为避免红一方面军主力过早暴露,被迫于15日令方面军主力移至平田、砍柴冈和安福圩地区隐蔽集中。④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页。同时将红二十二军缩编为第六十四师,由粟裕率领,填补由于红二十军撤离而造成的缺口,担负红军主力的西侧安全,并随时准备加入主力部队作战行动。16日,国民党各路大军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区大举进攻。而此时,段良弼、谢汉昌、刘敌等却在河西永阳地区继续扩大“打倒毛泽东”的分裂活动。17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发表《为富田事变宣言》,严正指出:“段良弼、刘敌、李白芳、谢汉昌、金万邦等,早已加入A B团取消派,企图破坏土地革命,消灭苏维埃,阴谋暴动,消灭红军”,“大敌当前他们不打倒蒋介石、鲁涤平,反要打倒毛泽东,不集中力量实行阶级决战,反而企图以‘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分裂革命势力,他们号称最积极的革命,但敌人在河东,他们却拖起一部分军队到河西,快要与敌人决战了,他们却在富田、东固后方来一个叛变,这不是响应蒋介石进攻革命是什么?”宣言还说:段良弼他们“主张直接进攻南昌、九江,这种表面上极左的口号,骨子里恰是实行蒋介石、鲁涤平的毒计”。⑤转引自阎中恒:《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79年第4期。次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又发出《给曾炳春等一封公开信》,号召“凡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⑥转引自戴向青:《富田事变考》,《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79年第4期。
12月19日,在朱、彭、黄发表公开信的次日,国民党军公秉藩师不费一枪一弹即进占东固原红二十军驻地。20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也进到东固,如入无人之境。总前委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新的战场形势,于22日紧急从红十二军中抽出第三十五师向西警戒,独立活动于兴国东北之约溪地区,接替本应由红二十军担负的任务,严密监视张辉瓒、公秉藩两师行动,并将该两敌的注意力向西牵引;红一方面军主力则悄悄集中于黄陂、麻田地区隐蔽待机。
正当总前委与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根据地军民全力进行反“围剿”作战准备时,转到河西永阳的富田事变领导人却以中共江西省行委的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信》,该信针对朱、彭、黄《宣言》和《公开信》,极力为他们的行为进行狡辩。毛泽东针对这封信起草了《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表明对反革命“叛变”行为“采取坚决进攻”的严正立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苏区军民展开“肃清反革命,团结内部,巩固苏区”的工作,“这就打下了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央红军的五次反“围剿”》,解放军档案馆馆藏,档号:1-Y-WS.W-1934-014-001。
12月28日,各路国民党军向红军发起总攻。其前线总指挥兼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以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亲率师部和五十二、五十三旅于29日进占龙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及时调整部署,下达攻击龙冈张辉瓒部的命令。30日,红三军、红四军、红三军团等部合力发起龙冈战斗。由于总前委的果断处置和出色指挥,经过苏区军民的共同奋战,一举取得龙冈首战胜利。张辉瓒第十八师除在东固的第五十四旅外,其余被全歼。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91~96页。倘若红二十军不擅自撤离东固,张辉瓒的五十四旅恐怕也难逃被歼灭的厄运。
三、富田事变的定性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对这一事件作出“A 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的政治认定。其实,富田事变是不是“反革命暴动”,与富田事变被定性为“反革命暴动”,是两个问题。就是说,当初富田事变被定性为“反革命暴动”,与当时的反“围剿”战争形势有直接关系。
一是总前委先声夺人,但仍留有余地。富田事变发生后,首先给事件定性的是《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 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但同时又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名义发出《给曾炳春等一封公开信》,指出:“现在大敌当前,决战在即,东固富田之事变无论主观上怎样要积极革命,或怎样想为革命,但事实上完全为出卖阶级的叛变行为,因为这是分裂了革命势力,破坏了阶级决战,实际上响应了蒋介石、鲁涤平进攻革命。”③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3页。信中还说明了“这次决战战略,只有取‘诱敌深入’苏区,才能大举歼灭敌之主力”的道理;号召“凡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在总前委领导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④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3页。这封公开信明显为富田事变的定性留了余地。这前后两封信,表达了总前委也就是毛泽东当时的基本态度。前一信代表总前委的官方公开声明,是对富田事变的政治定性。起着先声夺人的作用。这封信与朱彭黄《为富田事变宣言》取同样口径。之所以强调“段良弼、刘敌、李白芳、谢汉昌、金万邦等,早已加入A B团取消派”,⑤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3页。言外之意,是要把极少数事变领导人孤立出来,与广大不明真相的官兵和群众划清界限,帮助大家迅速在正确与错误的道路上作出判断和抉择,从而阻止不明真相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后一封信代表了总前委给富田事变定性“背后的说法”。这封信与前一信和宣言相比,取了缓和的口气,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既指出了富田事变客观上会造成的恶果及其严重性,又没有给红二十军领导人枉加A B团的帽子,特别是再次解释了实行“诱敌深入”战略的必要性,表明在朱彭黄看来(其实正是毛泽东的看法)事变领导人并没有发动“反革命暴动”的主观故意,从而起到了从主观上稳定事变领导人、缓和对抗情绪的作用,也体现了在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谋团结奋战、共同对敌的强烈愿望。
二是苏区中央局左右调和,但却失了立场。与毛泽东处理富田事变坚决果断、软硬兼施的高超领导艺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则完全取了调和主义的路线。他一方面认定“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毫无疑的是一种反党反革命的行动”,同时又说“富田事变的主观原因……正是过去赣西南党的路线和工作的错误的结果。……党内一般无原则的小组织派别的斗争,由此发展下去,就造成了这次富田事变”。⑥《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1月16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85年。话虽不错,但却将党内高层路线斗争的情况暴露于广大党员群众面前,在当时苏区军民很多人本来就十分迷茫的情况下,势必造成更大的思想混乱。事变部分领导人就认为,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在处理富田事变的问题上有分歧、有矛盾可以利用,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代替了毛泽东在苏区的领导地位,对他们是有利的。甚至一些犯错误的人也认为项英是支持他们的,他们的斗争会取得胜利。项英对富田事变不加区别地仅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进行宽大处理,统统“采取教育的方法”,甚至“双方处罚”,“以求和平了事”的态度,⑦阎中恒:《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79年第4期。在当时你死我活的战争形势下丧失了政治立场,显然是无原则的调和主义和软弱的表现。
三是中共中央受共产国际影响,态度急转,但仍把控全局。中共中央政治局获知富田事变后,起初明确将这一事件归为内部冲突,并决定“派全权的代表团去中央区解决此事”。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但不久收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指示信,态度便发生急转。远东局认为: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率部包围省行委的行动“是反革命的暴动,总前委领导是对的,这一点用不到再争论”,应通知苏区“无条件的在总前委领导下来作斗争”;并要中共中央起草一信,“立即发下去”。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3月28日,不待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迅速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肯定事变的性质“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 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03~206页。4月17日,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来到江西宁都苏区中央局所在地青塘村,出席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决议,完全否定了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的意见。指出:“中央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反革命进攻革命,尤其是进攻红军与苏区,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这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没有认清富田事变是A 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而用‘党内派别斗争’来解释这个事实。这种解释是非常错误的,脱离阶级立场的”。④《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号》(1931年4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302~303页。在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始终坚定维护总前委的集中统一指挥,指示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无条件的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⑤《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关于肃清苏区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1931年2月23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140~142页。肯定“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指出“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强调:“没有任何党的争执应该引起分裂和破坏红军的行动的,而且绝不容许拒绝执行上级军事机关的命令和破坏军事纪律,我们军队中的党员,对于这种拒绝执行基本任务的行动,应采取最严厉的制裁。”⑥《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3月28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203、204、208页。富田事变的及时解决,为中央苏区的进一步反“围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保证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取得最终胜利,得益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军民的不懈奋斗。革命斗争的对象既来自面对面的敌人,也来自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左”、右倾路线。在苏区革命斗争实践中,有一批顽固执行中央“左”倾路线的领导人,他们不但奉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还通过“小团体”的宗派主义,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实行“无情打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⑦《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68、969页。
富田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军事性分裂活动。事变领导人及所谓A B团主犯,其实主要是一批反对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反A B团扩大化和富田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未成熟时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对党和红军的建设造成了严重危害,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46、147页。但历史进程本身并不是理想化发展的。在第一次反“围剿”的严峻时刻,作为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的总前委如果处置不当,极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当时对富田事变迅速作出“反革命暴动”的政治认定,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必须看到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90~991页。这个决议所体现的主要精神,是用一个党的“道德标准”来对革命斗争中牺牲的同志进行“事后追溯”,不论他是正确路线的维护者,还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只要是为人民利益而死,而不是为反动派卖命,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崇敬”。
但这个基于党道德、党伦理的“道德标准”,并不能拿来否定革命斗争的“是非标准”。当初,富田事变发生时作出的“反革命暴动”的政治认定,是基于革命斗争的“是非标准”;而后来对绝大多数事变参与者作出的平反决定,则是依据中共党的“道德标准”。这两个标准体系不能混为一谈。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战争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是非标准”,不能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则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数以万计的革命先烈的鲜血就要白流。所以,富田事变发生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苏区中央局、中共临时中央基于反“围剿”战争的严峻形势,先后对事变作出“反革命暴动”的政治认定,尤其总前委迅速作出的断然处置措施,这件事没有错。不这样,就不能保证第一次乃至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富田事变的领导者、绝大多数同志,在艰难困苦的革命环境中仍然坚持对敌斗争,并没有投降或投靠国民党,依据中共党的“道德标准”,他们应当得到平反,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崇敬”。②赵金平:《近三十年肃“AB团”和“富田事变”研究》,《淮阴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一些学者正是混淆了“是非”和“道德”这两个标准体系,拿一个“道德标准”来掩盖革命路线的是非斗争,甚至更有少数学者故意或蓄意夸大高层领导之间的“权术”较量。这些其实都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现实表现。笔者认为,富田事变是在中国革命极其严峻的时刻发生的一件极不幸的事件。我们不能用和平时期的政策,尤其不能为了地方主义的目的,去翻革命战争时的旧案。当然,一些学者对这一事件进行个案研究未尝不可,但给后人的启示是十分有限的。
The New Discussion about the AB League and Futian Incident
B efore the first Counter-campaign Against KMT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C-KMTES)over Central Soviet Area(CSA),severe divergencesexisted among the CSA top leadership on the guidance and strategy of C-KMTES,leaving direct negative impact to their operational combat readiness.If remedial measures were not taken in time,it may result in the failure of C-KMTES operations.U nder this circumstance,the expansion of eliminating Anti-B olsheviks was understandable and reasonable in a certain sense.However,it became the powder hose of Futian Incident,which was decisively addressed by the General Front Committee of First Front Army in order toensuretheoverall victory of C-KMTESoperations.
the Central Soviet Area,the First Counter-campaign Against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the Anti-B olshevik Group,Futian Incident,Dai X iangqing.
K27
A
0457-6241(2017)20-0049-08
2017-08-02
王承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军事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