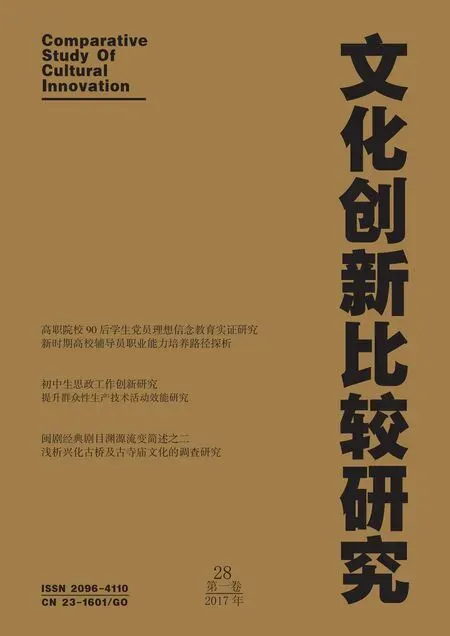痕都斯坦地名研究
柯榕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1 作为国名的痕都斯坦
“痕都斯坦”作为一个地名出现最早可追溯到元宪宗时期,“三年癸丑夏六月,命诸王锡里库及乌台萨里图里哈等,征痕都斯坦、克什米尔等国”。就从这条史料来看 “痕都斯坦”当时应该在印度北部,与克什米尔相连或者至少很接近,而且这一地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政权,类似于当时印度的土邦。痕都斯坦一词也是转译而来的,在汉文中除该译法外,音似而文字略异的还有欣都思、兴都斯坦、因都斯坦、温都斯坦、轩都斯丹等。在明代的典籍中,这个地名则一直没有出现,明代受国力所限,对西部边疆的经营一直较为薄弱,进入清朝之后,痕都斯坦则频繁的出现于典籍中,直到嘉庆、道光之后频率减低,最终消失。这主要是在嘉道之后,印度北部最终为英国所吞并,痕都斯坦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也不复存在。以时间而论,痕都斯坦在汉文中存在的时间约六百年左右,当然这一地理概念是一直存在的,但本文中的痕都斯坦主要在这一时间段内。
痕都斯坦作为一个地名再次进入汉文典籍中则到了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时候,伴随着清军不断西进南下,新的世界开始进入清军的视野,痕都斯坦玉也大致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原。“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1757),博罗尔伯克沙呼沙默特贡斧、匕首诸物。其南有小部落曰温部斯坦,产金丝缎。霍集占走巴达克山时,温都斯坦方以兵相攻,谋劫霍集占,不果。后其部为爱乌汗所并”。此时,痕都斯坦是作为一个政权名称出现在国人视野中。与此事相印证的记载则出现清代的《清朝柔远记》中 ,“当逆回霍集占为王师所拽,假道巴达克山,称将赴阿富汗往默克祖国,为巴达克山擒杀。阿富汗酋爱哈默特沙及溫都斯坦(即北印度之塞哥,又称克什弥尔)兴师问罪。巴达克山惧,貽以中国文缚,具言霍集占负中国及扰己国罪。阿富汗遂与连和,以兵拒温都斯坦,渡河而取其地。”此时对于痕都斯坦的记载相对就较为详细,特别是与霍集占的关系。
从上述两条史料来看,在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痕都斯坦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但这一时期,痕都斯坦并非是一个广义的地理概念,他更多的是指当时这一地区的政权名称。痕都斯坦并未积极配合清军对和卓们的进剿,反而站在其对立面,因此很快被周围的阿乌汗以及巴达克山的政权所灭。对于这一地区的记载相对来说也就较为简略,并未有更深入的探讨。
2 痕都斯坦地理概念内涵的不断丰富
随着准部和回部的逐渐平定,清朝对于我国西部边疆的控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时候,对痕都斯坦的了解则进一步加深,典籍中的记载也更加详细。
成书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载:“痕都斯坦,在拨达克山西南,爱乌罕东。国工治玉,以水磨成器最精,为内地所弗逮。旧于叶尔羌贸易,乾隆二十五年颁救书赠物,今通市如故。其地印度交界,北极高二十九度十五分,距京师偏西四十五度五分,当为古罽宾国地。”又称:“由拔达克山西南行,有部曰阿富罕,东南为痕都斯坦,俱葱岭大国,又东为巴勒提。”“痕都斯坦,境内崇山四围,长何襟带,滨河城堡,棋布星列.自拨达克山内附后,饶闻。”“痕都斯坦东境,直西藏之西。”
目前来看,在《钦定皇與西域图志》中对痕都斯坦的记载相对来说较为详细,书中单列痕都斯坦条,并对其地理位置进行了描述,也间接地提到了痕都斯坦的历史。从这段描述来看,我们可以大致的去界定一下痕都斯坦的地理位置。首先,痕都斯坦这一地区应该是在清朝的统治范围之外的,其在清朝皇帝心中的位置最多算是倾心王化而内附的蛮夷,并不是清朝的固有领土。周南泉在《痕都斯坦及其地所造玉器考》一文中持此观点。而且从阿乌汗攻灭痕都斯坦清廷并未加干涉来看,清朝对于这一地区并无太大的野心,否则,清廷是断然不会坐视葱岭大国被邻国所灭的,这与清廷的政治利益是不相符合的。其次,痕都斯坦的位置大概是处于帕米尔高原之上,书中记载痕都斯坦为葱岭大国,而且在巴达克山抓住霍集占之后,温都斯坦立即兴兵来看,巴达克山距痕都斯坦应该不会太远。“巴达克山,在叶尔羌西千余里,居葱岭右偏。由伊西洱库尔西稍南行,渡喷赤河至其国。”这一点史料中是可以相互印证的。更具体的说,清代的痕都斯坦应该在阿富汗以东、西藏以西、印度以北、叶尔羌以南的这一区域,都可以被称之为痕都斯坦。
在对痕都斯坦的认识中,痕都斯坦玉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媒介,由于当时清朝乾隆皇帝对于痕玉这种艺术品的喜爱,大量的痕玉进入了中原,进入了清朝的宫廷之中。痕玉作为一种外番进贡的产品,不仅仅具有艺术价值,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在乾隆皇帝看来,他是大清国力强盛的标志,是自己文治武功的象征,是自己德治天下,远人来服的代表。所以,乾隆皇帝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去记载他收藏的痕玉,并对其的来历进行了解释,在这一过程中,痕都斯坦的位置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乾隆也将这一地区的概念不断修正和扩大,使之在地理概念这一层面上内涵更为丰富。
乾隆三十三年,叶尔羌办事大臣旌额里进献了一对雕有花叶纹的玉盘,这对玉盘盘面都雕作一朵盛开的二十四瓣莲花,盘底纹饰以多层花饰和莨苕纹装饰,优雅富丽,使得乾隆皇帝为之倾倒。清高宗为此作了《天竺五印度考讹》一文与《题痕都斯坦双玉盘得十韵》一诗。其中《题痕都斯坦双玉盘得十韵》一诗是现存最早以痕都斯坦玉为题的诗作,在这首诗的注中,乾隆皇帝首次对痕都斯坦进行了介绍,“向称温都斯坦乃痕都斯坦之误,今考梵文更正。以新疆道里方向证之,其地当由回部遇葱岭,至拔连克山西南,即其地盖北印度交界说,详考讹篇中。”而《天竺五印度考讹》一文长达810字,集中展示了乾隆皇帝对于痕都斯坦的认识。
乾隆皇帝诗文均按年代先后编辑为 《清高宗御制诗》。综合来讲,清高宗诗词的历史价值高于其艺术价值,其中完整地收录诗题及诗注,为后世对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经核查可知其中涉及玉器(包括古玉、仿古玉、时作玉)的御制诗文就达八百余首(篇),综合诗题、诗的内容等判断,述及自新疆地区贡入玉器的诗与文共七十余首(篇)。诗题有“痕都斯坦”字样的共56首(篇)。这些诗作中一方面对来自痕都斯坦的玉器进行了描绘,另一方面,也对痕都斯坦的位置,物产等进行了解读。所以,就清朝中期来看,乾隆皇帝对于痕都斯坦的认识是有一定高度的。
随着清朝西部边疆的逐渐安定,许多内地的官员、士子因为仕宦或者游历等原因不断地进入新疆,他们留下了许多的文集,在这些文集中,也一定程度上涉及了痕都斯坦。此时,对于痕都斯坦的描述则不仅仅限于其地理位置的考辨,也开始涉及到当地的民俗,物产等,这标志着清人对于痕都斯坦的认识进一步具象化,不再限于一个抽象的概念。这其中以椿园的《西域闻见录》和阮葵生的《茶余客话》记载较为详细,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有一定的涉及。
椿园是满洲正蓝旗人,乾隆时期曾在新疆任职长达十余年,著有《西域见闻录》,其中专列痕都斯坦一条,因为其在新疆任职,地理上距痕都斯坦比较接近,因此资料的可信度也比较高。从书中对于当地的人种描述来看,当地人具有一定的印欧人的特点,高鼻深目,皮肤黝黑,其语言与回子不同,也就是说应该不属于突厥语系。其当地的气候具有明显的热带气候特征,天气炎热,而且潮湿,有瘴气。这与现在印度北部的气候是相吻合的。
3 结语
痕都斯坦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在清人的认识中,其内涵是在不断丰富的,这个变迁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清人天下观的变化。同时痕都斯坦的重要物产玉也作为一个载体进入清廷的视野中,以痕玉来命名那些具有明显伊斯兰风格、胎质轻薄、雕工精细的玉器也一定反映了清朝对这地区的一些感性的认识。 正如许晓东在《痕都斯坦及其玉器考》一文中所指出的“痕都斯坦实质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所指的范围在不断的变化中。对这一问题的梳理既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周边地区的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于历史概念的辩证认识。
[1]痕都斯坦白玉花卉纹瓶[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10):161.
[2]李皛.乾隆年间清朝与阿富汗关系新探[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51-152.
[3]宋少辉.从山西博物院馆藏白玉嵌宝石描金碗议仿痕都斯坦玉器[J].黑龙江史志.2013(13):11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