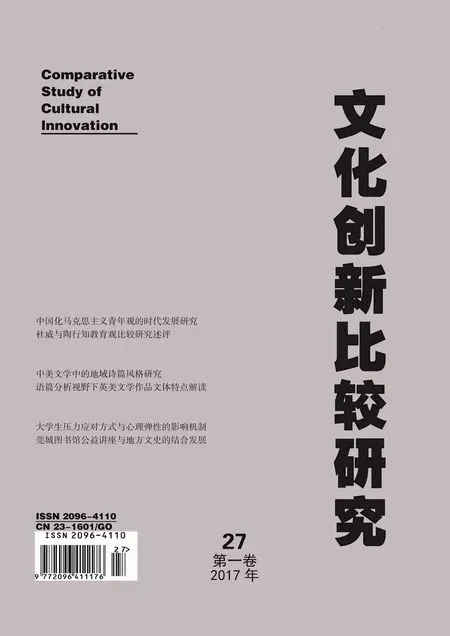论苏童小说《玛多娜生意》
王雨晗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
在苏童三十多年文学创作生涯中,产生了大量的短篇小说,《玛多娜生意》是他201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在语言上这篇小说十分出彩之处,情节也没有特别曲折辗转。但是正如苏童自己所言:“无论是追求真实也好,翻转真实也好,短篇小说的使命还是要去揭露现实。”[1]《玛多娜生意》是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反映,苏童试图以最世俗的眼光去挖掘、创造最纯真的世界。
1 关于人物形象
在《玛多娜生意》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众多的人物,庞德、简玛丽、桃子以及叙述这个故事的“我”。在这四个人中,庞德和“我”、简玛丽和桃子,两两一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小说以庞德和“我”开的广告公司生意不景气为切入点,在一开始就说明了庞德的才华得到了周围人的肯定,而庞德也有几分恃才傲物,仗着一身才华,做一些浪漫的事情,全然不顾公司的利益。庞德甚至几近无知,他的才华成为了他不负责任的接口,面对事业上的失败,只知道将责任推卸于他人,甚至还归咎于公司的名字。而作为他的生意伙伴的“我”,常常苦口婆心的劝庞德,在这里,庞德代表的是“理想”,而“我”则是“现实”的写照。按照一般的小说叙事套路,两人的差异应该会一直持续到最后,但是简玛丽的出现让故事出现了转折。在广告公司倒闭之后,庞德盯着梵高的自画像发呆,然后又刻下了“壮志未酬”四个字。梵高的自画像代表的是庞德的艺术理想,而他“把美工刀扔在字纸篓里,扬长而去了”更像是一种告别,是对过去无知的自己的告别。这个时候,庞德的理想开始发生了转变,由单纯的追求艺术到向“出人头地”靠拢——最为直接与现实的目标,庞德最终和“我”变成了一类人。
小说的另一组对照则是简玛丽和桃子,两个人的差别表现得更加明显。桃子是琵琶老师,她的生活只有两件事:庞德与琵琶,从小到大,桃子的人生一直都是顺风顺水。与桃子相比,简玛丽的人生则要复杂得多:当伴舞、被包养、跑龙套、经商,人生阅历丰富的简玛丽对于庞德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也注定了桃子在与庞德的爱情里是个输家。单纯的桃子只能以死相逼来去维护她与庞德的爱情,最终得到的是他们“被绑架”了的婚姻。在这一组对照中,桃子和简玛丽都发生了改变。桃子为了成全庞德的事业而献出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庞德促成了桃子的改变,包括庞德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桃子变了心,殊不知是庞德自己促成了这些事情的发生。如果说遇上庞德使桃子的人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话,那么对于简玛丽来说,庞德只不过是她的人生中的短暂的停留。没了庞德的简玛丽依旧能够生活,甚至多年后还能笑谈起往事。由当初的打扮时髦的到最后挽起发髻,照顾两个孩子,简玛丽的生活渐渐趋于平淡,她的改变是不靠外力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发的。
2 逃亡的主题
“逃亡”的主题在苏童的作品中时常体现,它是对社会转变时期的焦虑的体现也是对孤独的、空虚的焦虑,在具体的创作中,苏童则更侧重将这种”逃亡“表现为对世俗观念、平淡生活的恐惧,他笔下的这类人物都想要摆脱眼前生活的桎梏,抗拒接受悲剧的宿命,例如《逃》大的主人公陈三麦,一次次地逃离家乡、逃离恐怖的战场,至死都保持着一种逃亡的姿态;《狂奔》在一开篇就描绘了榆在黑暗恐怖的环境中因为内心的不安与害怕而狂奔的场景;“枫杨树系列”小说中的逃亡主题是苏童写得最多的,这些人的逃亡都和灾难联系在一起,他们的逃亡是出于对贫穷和未来的恐惧,想要借逃亡来摆脱悲剧性的命运。然而不管怎么逃,这些人最后要么是再次回到起点,要么是以死亡而告终。
在《玛多娜生意》中,庞德也是一个“逃亡者”,简玛丽的出现给他带来了一丝希望,先是让他觉得自己能谈成玛多娜的生意,后来在婚姻失败之后,他企图通过简玛丽的绿卡去到美国。绿卡遥遥无期,庞德决定自己去美国,开始他的逃亡之路,从云南到越南再到澳大利亚。“去美国”这一举动不仅是因为简玛丽在美国,玛多娜也在美国,更多的是“美国梦”的蛊惑,它让庞德觉得到了美国之后可以实现自己所谓的艺术理想,可以名扬四海。然而和苏童之前的逃亡主题的小说不同,庞德最后没有去美国,而是转头去了新西兰,在葡萄园里摘葡萄,庞德的逃亡之路就此结束。
正如简玛丽所说,“有时候玛多娜是仙女,有时候她就是魔鬼”。玛多娜是美国梦的象征,他是庞德的信仰,到最后庞德放弃了玛多娜,停止逃亡。停止逃亡并不意味着庞德找到了他的理想的栖身之所,他的停止更多的是无奈。当一个不错的机会——调酒师麦克的出现,疲惫了的庞德自然会选择抓住机会。现实最终打败信仰而占据上风,苏童无意于对这种结果进行评价,他将对是非对错的评判权交给读者。
3 苏童创作的转型
提到苏童的作品,首先想到的就是“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香椿树街”是苏童年少成长是的那条苏北老街,而“枫杨树乡”则是他虚构的精神故乡。《玛多娜生意》这篇小说脱离了这两个精神寄托,转而去描绘当下的社会现实生活。广告公司、深圳、包养等,这些都为小说刻下了现代社会的烙印,苏童写的就是发生在大多数人身边的故事。脱离了“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也就意味着苏童向少年时代告别,《刺青时代》、《舒家兄弟》、《桑园留念》等写的都是少年的爱与忧愁,《玛多娜生意》以成年人的视角来写成年人的社会,它体现的是成人世界的规则与成人的情绪。
过去大家常常将苏童和阴郁、暴力、颓废这些词联系起来。在他之前的小说中,常常运用各种意象,用古典优美的语言去描绘一个唯美颓废的江南世界,处处体现的是古典美学,如《蝴蝶与棋》、《桑园留念》、《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他用一种抒情的笔调,将故事放在一种焦虑不安的氛围中,宣泄的是个人的感官体验,这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常常会忽略现实环境,而跟随他的笔触进入那个阴郁诡谲的世界中去,而近些年,苏童将目光转向了现代社会生活,他不再处心积虑地去构建一个唯美、古典的世界,而是更多地采用一种平实的笔调去客观描绘他对现实生活的观察。
同时,由于小说的环境背景变化,使得苏童哎塑造人物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他过去的小说中,香椿树街上的少年代表的是青春的躁动与暴力,又比如《米》中的人性阴暗到了极点的五龙,同时还有逃脱不开的死亡,这些人物都带有鲜明的善与恶、好与坏,而在《玛多娜生意》中,很难去用好或者坏来去评价故事的主人公,这些人就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普通人,在某些方面还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玛多娜生意》作为苏童的新作,承接了之前的创作理念,脱离了之前所建构的精神世界,将目光投向了平实朴素的现实生活,这是苏童在小说创作上的一种反方向的尝试。正如他自己所说,一篇好的小说,读后“或者被感动,或者会心一笑,或者怅怅然,如有骨鲠在喉”[2],而《玛多娜生意》显然就是这种小说。
[1] 苏童:《短篇小说的使命》,文学报,2016年4月21日,第18版
[2] 苏童:《短篇小说,一些元素》,读书,19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