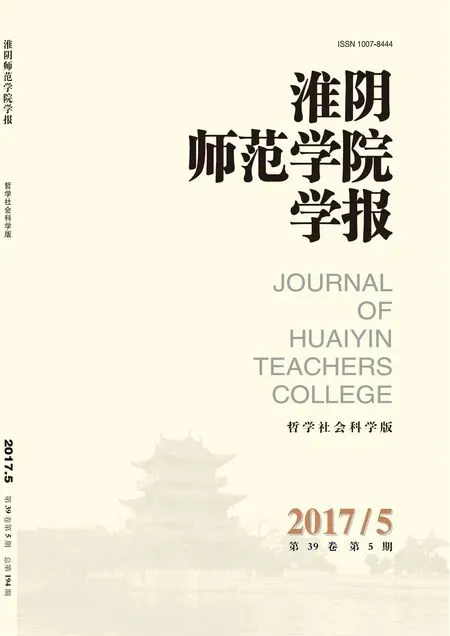徐继畬与晚清东南士人学术取向
陈其泰, 李亚静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5)
徐继畬与晚清东南士人学术取向
陈其泰, 李亚静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5)
鸦片战争前后,徐继畬在福建任地方官多年,福建沿海这一东西方文化撞击交流的前沿地带,为《瀛寰志略》的著成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对于这部爱国主义先驱名著在近代文化史上的价值,我们应该有新的认识:一是为一向暗昧无知的国人展现了一幅比较正确而完整的世界图画;二是对西方列强既富强又富于侵略性的特点有敏锐的认识,并高度赞扬西方民主制度的先进性。在徐继畬及林则徐、王韬、严复等晚清东南士人为代表的进步人物身上,体现出学术的革新取向,开放意识为其基本的特征,在全国起到了开创风气的作用。
徐继畬;《瀛寰志略》;晚清东南士人;开放意识
一、《瀛寰志略》撰著的特殊机遇
作为中国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标志的《南京条约》签订第二年,1843年,徐继畬调任福建布政使,再度来到这个在近代史开端时期举国瞩目的东南重要省份。在此后几年中,他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呕心沥血撰著《瀛寰志略》,至1848年完成。徐氏这部著作不仅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在内容上同为介绍外国史地、论述西方近代制度及文化的先进性,而且撰著时间基本相同。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由于相同的时代需要,徐、魏二人又都具备著述的条件,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而发愤著成的。
换言之,《瀛寰志略》这部名著的产生,是由于时势需要的刺激与著者的特殊机遇二者相交汇的结果。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以“闭关锁国”为国策,造成了中国与西方各国长期隔绝的状态。加上东西文化的巨大差异,难以沟通,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下,近代史开端时期能够冲破思想禁锢首先研究外国的人物,就必须具有过人的胆识,克服各种障碍,既要勇于跨过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的鸿沟,越过东西方文化体系的巨大差异,甚至要冒着被加上“通番”之类的罪名的风险,同时还要克服语言文字上和资料上的种种困难。徐继畬撰《瀛寰志略》和魏源撰《海国图志》一样,有着“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巨大功绩!鸦片战争前后,徐继畬一直在闽、粤沿海地区任地方官,他在这里有机会直接结交外国官员、传教士和知识人士,接触外国知识,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而强烈地感受到了解外部世界的迫切需要。1836年,徐继畬继任福建汀漳龙道,驻扎厦门,鸦片战争时,他毗邻海防前线。1842年任广东按察使,次年调任福建布政使,撰写《瀛寰志略》的资料工作即始于此时。1844年初,他见到了美国传教士雅禆理。当时雅裨理为英国驻厦门领事的翻译,会操厦门语。在这一年内,徐继畬数次会晤雅裨理,据雅裨理日记记载:徐继畬是他“迄今遇见的最喜欢提问的一位中国高级官吏”。徐继畬向雅裨理了解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情况。雅裨理除提供一些外国地图、资料外,还赠送给徐继畬一些基督教的书,如《新政全书》等。徐继畬所重视的并不仅是宗教,而是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版图大小、重大政治事件和商务关系[1]。徐继畬根据雅裨理提供的地图,“钩摩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他的临摹比较粗糙,也不够准确,只是具备了初步基础。1845年徐继畬又从霍蓉生那里购得地图二册,较雅裨理的地图更详密一些,“又得西人著述汉字杂书数种”,摘录其中有用的资料。除此之外,他还曾向传教士甘威廉了解瑞士与西欧的情况。他还结识美国人乔治·史密斯夫妇,向他们询问有关外国的知识。总之,为了著成《瀛寰志略》,只要能找到的资料,他都苦心搜求,“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2]6。五年时间,“未尝一日或辍”,始得告成。他于1846年升迁任福建巡抚,旋兼署闽浙总督,封疆大吏的身份,并未影响他著述的热情,依然为撰著此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福建沿海这一东西方文化撞击、交流的前沿地带,为《瀛寰志略》的著成提供了最适宜的条件。
二、《瀛寰志略》时代价值的再认识
《瀛寰志略》著成后,在中国和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源于1852年将他略早于徐氏完成的《海国图志》一书增订为一百卷,便从《瀛寰志略》中辑录了大量的资料,计有33处之多,约四万字,为《瀛寰志略》全书的四分之一,记欧罗巴各国的资料辑入尤多。徐氏此书撰成,因书中突破了传统学术的范围,介绍了大量新鲜知识和观念,引起顽固派的忌恨,“甫经付梓,即腾谤议”。《清史稿》本传亦云徐氏遭到言者“抨击”。此书与《海国图志》一样在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日本在1861年即有《瀛寰志略》的刊本,以后又经多次翻刻。国内则有1866年总理衙门刻印了此书,后又作为同文馆学习外国知识的教材之一。所以王韬评论说:“近年谈海外掌故者,当以徐仁龛中丞之《瀛寰志略》、魏默深司马之《海国图志》为嚆矢,后有作者弗可及也。……此诚当今有用之书,而吾人所宜盱衡远者也。”“中丞莅官闽峤,膺方面之寄,篙目时艰,无所措手,即欲有所展布,以上答主知而下扶时局,而拘牵陈义者动以成法为不可逾,旧章为不可改,稍有更张,辄多掣肘。中丞内感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3]王韬此论代表了早期改良派对此书的推崇。直到1879年,此书和《海国图志》仍为青年康有为学习外国知识的基本读物,《康海南自编年谱》中载:“光绪五年,二十二岁,……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础。”[4]
《瀛寰志略》的撰成,同《海国图志》一样,成为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起点。它突破了传统学术的范围,提供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外国史地知识和东西方历史趋向的信息,引导国人认识外部世界的广阔和先进性。徐氏深切感受到,时代迫切地需要了解突然打上门来的西方势力及其文化,所以他才有如此的勇气、毅力,揭开中国学术史上新的一页。他本人对传统学问很有根柢,精于考证。晚年回到山西原籍后著有《两汉志沿边十郡考略》等书,这种详据博考、务求真知、严谨深入的治学特点,运用到探求外国史地和近代制度、文化这一新的知识领域来,便形成《瀛寰志略》这样内容令人耳目一新,而又论述系统、熔炼成篇、知识准确度高的特色,这在160年前实为令人赞叹的杰出成就!毫无疑问,《瀛寰志略》一书同《海国图志》一样,都是近代史开端时期了解外国、学习西方的爱国主义先驱名著,对于它在近代史学史以至整个文化史上的价值,应该有新的认识。我以为,最为突出的是以下两项。
一是,《瀛寰志略》为一向暗昧无知的国人展现出一幅比较准确而完整的世界图画。
清朝官修的《皇朝文献通考》说中国居大地中央,四周是海,五洲之说毫无根据。人类世世代代生活的世界,真的是这样吗?徐继畬对这种非科学的臆说明确作了否定。本书开卷为《地球》篇,回答说:“地形如球。”“地球从东西直剖之,北极在上,南极在下,赤道横绕地球之中,日驭之所正照也。”“地球从中间横剖之,北极南极在中。”他又告诉人们,西方人所说五大洲确实存在:“大地之上,环北冰海,披离下垂如肺叶……泰西人分为四土,曰欧罗巴,曰亚细亚,阿非利加,此三土相连,在地球之东半。别一土曰亚墨利加,在地球之西半。”讲得多么明确,又多么形象和简洁!叙述岛屿和大洋则谓:“四大土之外,岛屿甚多,最大者澳大利亚,余则亚细亚之南洋诸岛。”“亚墨利加之海湾群岛。”“四土之外皆海也……曰大洋海,曰大西洋海,曰印度海,曰北冰海,曰南冰海”。他还详述亚细亚大陆之广袤,欧罗巴国家之众多,犬牙交错,“其人性情精密,工于制器,长于用舟,四海之内无所不到,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国”;南北美洲大陆的晚近发现;南冰海的探险……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知识。
欧美国家是本书记述的重点。原因极明显,英、葡等国“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国”,用武力胁迫开商埠、通贸易,在文明发展程度上,它们是先进国家。对于守旧人物不愿承认欧美文明“反有中华所不能及”这个尖锐的问题,“其人性情,工于制器,长于用舟”,已经作了总括性的回答。在卷四《欧罗巴总论》中,进而论述西方文明发展的大势:“其地自夏以前,土人游猎为主,食肉寝皮,如北方蒙古之俗。有夏中叶,希腊各国初被东方文化,耕田造器,百务乃兴。汉初,意大利亚之罗马国,创业垂统,疆土四辟,成泰西一统之势,汉史所谓大秦国也。前五代之末,罗马衰乱,欧罗巴遂散为战国。唐宋之间,西域回部方强,时侵扰欧罗巴,诸国苍惶自救,奔命不暇。先是火炮之法,创于中国,欧罗巴人不习也。元末,有日耳曼人苏尔的斯始仿为之,犹未得运用之法。明洪武年间,元驸马帖木儿王撒马儿罕,威行西域。欧罗巴人有投部下为兵弁携火药炮位以归。诸国讲求练习,尽得其妙。又变通其法,创为鸟枪,用以攻敌,百战百胜。以巨舰涉海巡行,西辟亚墨利加全土,东得印度、南洋诸岛,声势遂纵横于四海。”这段论述讲到了欧洲古代的希腊、罗马文明,讲到中国火药的西传,讲到近代欧洲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所勾画的轮廓大致无误。这一篇欧洲总论,还扼要地讲述了以下各项问题:地理形势;与中国贸易情况;各国版图、人口兵力、财政收入统计数字;技术的进步;风俗;物产和商业;宗教;纪年;语言。徐氏着重论述西方文明当时居于先进地位:“欧人善于思考,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建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政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蓬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至于中土,非偶然也。”“欧罗巴国之东来,先由大西洋而至小西洋,建置埔头,渐及于南洋诸岛,然后内向而聚于粤东。萌芽于明中叶,滥觞于明季,至今日而往来七万里,遂如一苇杭之。天地之气,由西北而通于东南,倘亦运会使然耶!”徐氏虽然不能理解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比起封建主义进步,但他显然意识到东西方先进与落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并且把这个信息传递到国内。
二是,对西方国家既富强又富于侵略性的特点有敏锐的认识,并高度赞扬西方民主制度的先进性。徐氏对于资本主义特点的认识,可以对英吉利的论述为代表。他认为,英国称雄于世界是由于殖民掠夺:“其骤致富强,纵横于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2]21而同时,徐氏又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远比封建专制制度进步。他论述英国的两院制说:“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乡绅房(即下议院),一曰爵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之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5]对于华盛顿所创立的美国民主制度,徐氏更衷心赞扬。他认为华盛顿在领导美国取得独立之后,提出“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创立了四年一选、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总统选举制,这比起封建制度视“朕即国家”、帝位世袭来,是“公”的原则的体现。而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乃是“创古今未有之局”,所以华盛顿是西方世界第一伟人!
当然徐继畬的认识也有明显的局限。如用风水迷信来解释,认为欧洲技术上的先进,与其地理位置“以罗经视之,在乾戌方,独得金气”有关。有的言论还表明他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性缺乏警惕,认为他们只为通商盈利而来,并无其他的目的。说:“英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略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便售其货物。”[6]这种认识实与《瀛寰志略》书中的有关论述相矛盾。
三、开放意识和变革图强:晚清东南士人共同的学术取向
鸦片战争标志着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从此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剧烈变动,引起思想文化领域一系列深刻的变革。江、浙、闽三省所处东南沿海地区,在鸦片战争时期是抗击列强侵略的前线,“五口开埠”中有四个通商口岸即在这一地区。西方国家的商品输入、设厂经营,各种殖民主义活动的进行,文化上“欧风美雨”的侵袭,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的变化是深刻而明显的。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运动大约60年间,反映东南地区学术风气变迁的主要人物,前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徐继畬,中间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后有严复、夏曾佑等。这些士人大多出生于东南三省,从小受到这里地理人文环境的熏陶,外地来三省士人也因在这地区活动,在这里受到社会剧变的刺激,接触到与内地不同的事物,形成迥异于旧传统的新思想,撰写出符合时代需要、传达近代化信息的著作。这些士人,有的彼此交往、志同意合,或有师承关系,或在学问上心向往之、引为同调,放在一起考察是恰当的。徐继畬正属于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
全面、深入地论述这一时期东南地区士人新的学术风尚,无疑是一个内容相当丰富而复杂的课题,需要有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进行充分的研究、探讨。我在这里只是把问题提出来,感想式地粗列出几条纲目,抛砖引玉,期望引起学术界朋友们进一步考察的兴趣。我以为在近代东南士人的进步人物身上,体现出学术的新取向,在全国起到开创新风气的作用。最基本的特征是开放意识,这是支配《瀛寰志略》全书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也是近代东南士人俊秀之士的共有意识,代表了近代文化的前进方向。
徐继畬在撰著此书之时,对于弥漫朝野的排拒外国、闭目塞听、颟顸无知的顽固意识是充分了解的,但他认识到中国处于世界之中,西方势力及其文化已经东来,再实行紧闭国门的办法已绝对行不通,所以他冒着被保守势力忌恨、施压的危险,为著成此书而惨淡经营。在当时官至督抚地位的人物中,只有林则徐和徐继畬有此胆识!徐继畬清醒地认识到欧洲列强势力远达东方,如今往来七万里而如一苇之杭。并说,“天地之气,由西北而通于东南,倘也运会使然耶!”已经相当明显地把西方先进而东方处于落后地位的形势昭示国人。《瀛寰志略》所真实记载的西方国家富强、工于制造、技术先进,并有反映民情、表达民主意志的议会制度,有华盛顿这样的“公天下”的伟人,已清楚地说明在中国以外有别一文明存在,其势力向东方扩展,不可阻挡,中国要变被动为主动,唯有改变陈腐的观念,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正是由于《瀛寰志略》在近代东西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站在应有的高度,向国人展现了外部世界的广阔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性,而且所提供的知识比较准确,因此这部书的影响才长期地与《海国图志》并提,到了19世纪80年代,依旧对于康有为一辈人学习西学具有启蒙教材的意义。林则徐较徐继畬更早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他被委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到达广州后,立即费尽苦心收集有关外国的知识,“刺探西事,翻译西书”,组织幕僚翻译英人慕瑞《地理大全》一书,经林氏润色后编成《四洲志》。书中介绍世界五大洲三十余国之地理、历史、政情,成为当时中国第一部较有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以后他又嘱咐魏源,在此基础上再广泛搜集资料,扩充撰成《海国图志》。他严禁鸦片,但主张保持正常的国际贸易。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记载,林则徐奏请区别对待外商,“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表现出主张与西方国家开放通商的远大眼光,不想道光帝却批驳“同是一国之人,办理相歧,未免自相矛盾”,由此正可反衬出林则徐的识见,林氏坚决抵抗侵略,又敢于承认自己落后,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师敌长技以制敌”,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正是总结林氏的主张而得出的。
冯桂芬中举以后,曾在苏州的紫阳书院和正谊书院,听著名学者讲学,其时任苏州巡抚的林则徐便是书院主讲者之一,故二人有师生之谊。冯桂芬于19世纪60年代初在上海著成《校邠庐抗议》一书,面对中国一再遭受列强欺凌,他满腔义愤地喊出:“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中国要摆脱受屈辱的命运,必须发愤图强,而第一要着是承认中国的落后,了解西方并学习西方的长处,变落后为先进:“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无能,勉强之无庸。……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7]因此他主张“采西学”“制洋器”,改革吏治、科举制度、赋税制度等。他的主张对洋务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又开戊戌维新派的先声。王韬曾受雇于上海英国人办的墨海书馆,后来去过英法等国,于19世纪70年代著成《法国志略》,目的是要把法国历史介绍给国内,用法国的富强和进步激励国人的觉醒,因而在序言中表达了他深刻的寓意:“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玮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言》,光绪庚寅年松隐庐刊本(复印本)。他的著述,直接继承了魏源、徐继畬的学术取向,向国人鼓吹开放意识,了解外国、学习外国。魏、徐的书是介绍世界各国概貌的,王韬所著是专详于列强之一的法国。全书前14卷载史事,在国内首次把法国历史盛衰比较系统地介绍过来。后10卷是专题记载,包括职官、国会、礼俗、学校、工艺技术,以及法国疆域、首都巴黎、地方都邑的地理知识,这一部分更明显地体现出王韬学习西方、寻求富强的见识。书中对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的一套办法,如银行、商会、邮政、铁路都有评论,反映出早期维新派对商业流通和商品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其后所著《弢园文录外编》中,进一步提出变法自强的主张,力倡学习西方“富强之术”,提出贸易、开煤矿、兴铁路、造轮船等各项建议。薛福成于1879年著成《筹洋刍议》。他探究欧美各国取得富强的原因,与重视“通商”密切相关:“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立其基,工商扩其用。”[8]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以工商立国”,“工实居商之先”,但又认为西人恃商为命脉,商“握四民之纲”[9]。他称赞西方议会制度,云:“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10]王韬、薛福成向国人进一步展示了世界进步潮流,推动了戊戌前改革思想的形成,为东南士人的近代学术取向增添了光彩。
至19世纪行将结束时,严复介绍《天演论》,更为中国思想界开创了新纪元。严复于23岁时以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保送到英国学习海军,他不仅学习海军战术和各门自然科学知识,同时以极其难得的开放意识,热心地研读西方哲学和各种社会思想学说。当时他与清朝驻英大使郭嵩焘有交往,因常能对中西政体之异同发表独到的见解而很得郭之赏识。回国后一直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直至担任总办(校长)。甲午战争爆发,严复亲见老大腐败的清王朝被由于学习西方而骤强的日本打得惨败,更加引起他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忧虑。1895年,他先后在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严复怀着“警世”的强烈愿望,系统地介绍西方进步社会学说和进化论思想。1895年,严复撰《原强》一文,即指出比起当时盛行的西学、洋务知识来,更为重要的是传播和掌握西方进化论学说,它可以指导个人的正确行动,指导国家走向富强:“今之扼腕愤肣,讲西学、谈洋务者,亦知近五十年来,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经国利民之一大事乎?”并以简洁的语句介绍达尔文“天演论”的基本观点。他正是怀着让中国学习西方进步哲学思想以变革自强、追赶西方国家的强烈使命感,将1894年刚刚在英国出版的赫胥黎的通俗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及时地在1896年着手译述。在当时情况下,他不作原书直译,而采取意译、改写、插入议论和加上大段按语的方法,着眼于中国国情,就原著某一内容和观点加以发挥。抒发本人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以达到“警世”的目的。严复向国人传播的“天演论”学说是近代学术体系,较之康有为大力推阐的公羊三世说这一传统的朴素进化观高出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进化论哲学的传播,为立志改革、争取祖国富强的人们提供了新的观察历史和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如革命派机关报《民报》即评论说:“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11]严复译作出版后,成为空前畅销书,书市争相翻印,版本达三十多种,新的哲学观风行全国。在严复进行《天演论》论述之时,因听他的讲论而大受激励的是另一位东南学者夏曾佑。夏是杭州人,在其青年时代也因受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的刺激,而有志于进行哲学的探索,原先也深研公羊学说。至1896年底,夏曾佑来到天津,并与严复相结识,两人遂密切往还,朝夕相处。通过严复的讲述,夏氏倾心于西方进化论学说,哲学观点由此实现了飞跃。正由于夏曾佑身上有晚清学者所最可贵的开放意识和向西方学习的精神,因此一旦获听严复讲述“天演论”哲学,便顿时仿佛置身于新的天地,表示倾心服膺,贪婪地学习、领会、消化,如他在致汪康年信中所称赞的,“彼中积学之人,孤识宏怀,而心通来物”,因而也曾想撰成著作向国人传播:“拟尽通其意,然后追想成书,不知生平有此福否?”[12]夏氏这一撰写哲学著作的宏愿虽未能实现,却于20世纪初年独力著成《中国古代史》这部以进化观为主导思想的新型通史著作。自林则徐的《四洲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经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王韬的《法国志略》、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到上一个世纪之交风行国内的严复《天演论》和令人一新耳目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东南学者的开放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对晚清社会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转变,因而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一笔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1] 顾长生.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66-68.
[2] 徐继畬.瀛寰志略·自叙[M].上海:上海书店,2001.
[3] 徐继畬.瀛寰志略·跋[M]//弢园文录外编:卷9.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康有为.康有为自编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2:9-10.
[5] 徐继畬.瀛寰志略:卷7[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02-603.
[6] 徐继畬.致赵盘文明经、谢石珊孝廉书[M]//松龛先生全集:文集3.《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7]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下卷)“制洋器议”[M].戴杨本,点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198.
[8] 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M]//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540.
[9] 薛福成.英吉利利用商务辟荒地议[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1254.
[10] 薛福成.薛福成日记:卷2(光绪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M].蔡少卿,整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569.
[11] 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M]//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3:143.
[12] 夏曾佑致汪康年信第十三函[M]//汪康年师友手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仇海燕
K252
:A
:1007-8444(2017)05-0434-06
:2017-07-20
陈其泰,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