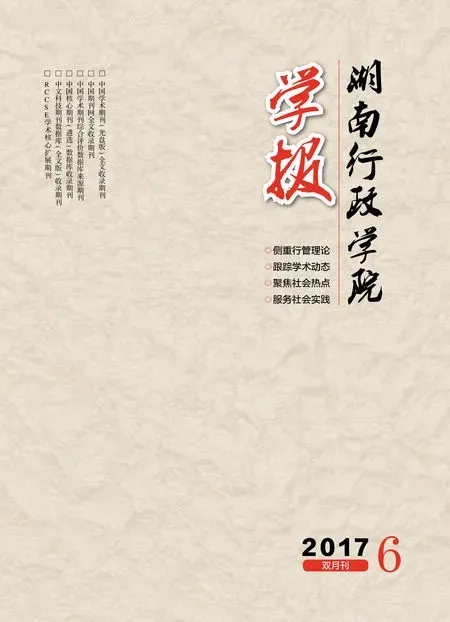山川毓秀 文章汇萃
——历代巴蜀作家文学总集编纂评述
李文泽,霞绍晖,邓秋良
(1,2.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4;3.广铁集团党校,广东 广州 510000)
文史研究
山川毓秀 文章汇萃
——历代巴蜀作家文学总集编纂评述
李文泽1,霞绍晖2,邓秋良3
(1,2.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4;3.广铁集团党校,广东 广州 510000)
从历代的角度讨论自唐、五代至宋、明时代的巴蜀文学总集编纂的概况,简要评述其中各部总集的体例、特色,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有文献记载的巴蜀文学总集是唐、五代出现的,五代后蜀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是现今存世的最早的巴蜀词总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代是巴蜀历史上总集编纂的繁荣时期,编有多种文学总集。《成都文类》是成于宋代的巴蜀文学总集,其收罗丰富,体例完备,为后世编纂总集所取法。蜀中“三苏”是宋代学者之翘楚,其家族精英辈出,故而以“三苏”命名之文学总集,在当时即反复编纂,数量众多,门类多样,是宋代巴蜀文学总集中的珍品。明代所编蜀人总集,以杨慎所编《全蜀艺文志》为最,其注重保存巴蜀历史的特点,在后来的《补续全蜀艺文志》等书中得到了传承。
巴蜀;巴蜀作家;文学总集;编纂
自古以来,巴蜀地域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文学精英,尤其是自西汉文翁办学兴蜀以来,更是出现了大量文学才子,他们以其卓越的文学创作成就傲视中原,成为时代精英中之翘楚,像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唐代的陈子昂、李白,五代的花间词人,宋代的三苏,乃至明代的杨慎,清代的费密、彭端淑、张问陶等,都是各自时代的佼佼者,虽然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却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成为现代巴蜀人引以为自豪的典范。
本文所讨论的“巴蜀文学总集”,其内涵是指历代编纂的收载巴蜀地域作家文学著作的总集。我们发现这类总集编纂的实际情况,也各有不同,在此略作一说明:从其各类总集所收录的内容来看,一些文学总集完全载录巴蜀籍作家的文学作品,这自然是属于巴蜀文学总集的正宗,如宋代所编《成都文类》、明代所编《全蜀艺文志》;一些文学总集其面对的是中国地域的作家,虽然其中包括了部分巴蜀地域作家的作品,但同时又兼及其他地域的作家,这类总集我们则需要区别对待,如果主要以巴蜀作家为主,如五代时的《花间集》,宋代时的《三家宫词》《潼川唱和集》,我们也考虑归入巴蜀文学总集;至于那种以全国范围的作家爲采集对象,川籍作家只是在其中占有部份份额的文学总集,如清末徐世昌所编《晚晴簃诗汇》,则不计算在内。
其次,就总集编纂者的籍贯身份而言,也存在不同的情況:一些总集的编纂者原籍即为巴蜀的学人,这类总集属于“蜀人编蜀集”;而有一些总集并非原籍爲蜀人所编,他們或是仕宦,或是游历于巴蜀的吏员、学人,如五代时的赵崇祚,宋代的赵抃、章楶、袁说友,明代的曹学佺、傅振商,清代的朱云焕,均属于此类;也有一些编者甚至与巴蜀地域毫无关係,如宋代吕祖谦编《东莱标注三苏文集》。在讨论巴蜀文学总集的时候,我们一般不考虑编纂者的籍贯,只关注总集所收录的作品对象。总之,本论文所讨论的“巴蜀文学总集”,可包涵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巴蜀地域(含久宦或游历于蜀的作家)的文章总集,这是从作家群体角度的考察;一是以吟咏巴蜀地域山川景物、人文历史为对象的文学总集,这是基于作品内容范畴的考察。以下我们即从这两大观念出发予以讨论。
以地域为限断来编纂文学总集,溯其渊源,应该肇始于《诗经》的十五国风以及《楚辞》这一类总集。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代都有这类反映不同地域作家的作品总集,以《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为例,我们可以在其“总集”类中找到《吴楚汝南歌诗》《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邯郸河南歌诗》《左冯翊秦歌诗》《齐郑歌诗》《雒阳歌诗》一类的名目,尽管人们现在无从看到这些总集的原貌,但从其书名来判断,显然是汇集各种地域作家诗文的总集,然而很遗憾的是我们在其中却没有发现有巴蜀文学总集的记载。
至后来的《隋书》一类的正史志文,关于巴蜀文学总集的名目仍不见记载,令后世的研究者多少有些惶惑。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显然要么是巴蜀作家作品太少,达不到结集成编的程度,抑或是即使有巴蜀文学总集,然而其影响甚微,因而未被史家所关注采集,故而阙如。
一
巴蜀地域文学总集的产生,现有的记载应该追溯至唐末、五代时期。自唐代开发西川以来,巴蜀地域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其经济、文化地位得到迅速提升,涌现出许多蜀籍作家及作品,尤其是经历了中唐以后的“安史之乱”及后来的多次战乱,战爭虽然祸及全国,然而却很少波及到四川,因而保留下了唐代文化发展的一脉。五代时期的巴蜀,相对于中原地域而言,战乱不多,经济繁荣。在这一时期内,巴蜀的文化事业发展良好,尤其是两蜀的统治者喜好文学,除了重赏文学侍臣以外,他们自己往往也附庸风雅,闲暇时赋诗著文,与文人相唱和,这无疑会大大推动巴蜀文化事业的发展。在当时的华夏大地,巴蜀地域应当是一块文学创作的肥田沃土。
在唐、五代時期编纂的巴蜀文学总集有:
刘赞编纂《蜀国文英》8卷,见《崇文总目》卷11、《宋史》卷209《艺文志》八、《蜀中广记》卷97。
刘赞,蜀人,前蜀乾德时官嘉州司马,时后主王衍荒乐,刘赞尝作歌讽谏,并献《陈后主三阁图》。后迁学士。刘赞长于绘画,工花竹翎毛,著有《玉堂集》,编有《蜀国文英》等。《十国春秋》卷43有传。由于文集久已佚亡,我们只能根据其书名判定它是采录巴蜀地域文人作品的一部总集。
前蜀后主王衍编《烟花集》5卷,集艳诗200篇。
前蜀后主王衍,童年时即能属文,甚有才思,《蜀中广记》卷4尝记载其赋《宴宣华苑宫词》诗云:“辉辉赫赫浮五云,宣华池上月华新。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他酷好靡丽之词,尝集艳体诗二百篇,号《烟花集》。
《烟花集》久已佚亡,只能从目录书的著录知道其尝存世。
赵崇祚编《花间集》5卷,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1,这是现存蜀人所编最早的一部词总集,收录了唐五代以来蜀中诸作家的词作。
赵崇祚事迹,文献记录不详,欧阳炯称其字宏基,为孟蜀(后蜀)卫尉少卿,四库馆臣疑其为赵崇韬兄弟行辈。[1]1823
考察《花间集》内容,是集收录唐末诸家词作,凡18家,其中巴蜀籍或占仕于蜀地的作家有15人之多,只有3人与蜀地无关:
涉及蜀地的作家(包括蜀籍或非蜀人而仕于蜀者)有:韦庄47首,薛昭蕴19首,牛峤31首,毛文锡31首,牛希济11首,欧阳炯17首,顾夐55首,孙光宪60首,魏承班15首,鹿虔扆6首,阎选8首,尹鹗6首,毛熙震29首,李珣37首,温庭筠66首。
其中李珣是一个较特殊的人物,为前蜀梓州(今三台县)人,一说其先人为波斯人,故其友人尹鹗尝戏称他为“李波斯”,著有《琼瑶集》。其妹李舜弦亦有诗才,为前蜀后主王衍昭仪。
与蜀地无关涉的作家有3人:皇甫松11首,张泌27首,①张泌仕于南唐,明代杨慎编《全蜀艺文志》收录其《河渎神》《江城子》2首,见该书卷25。按:此二词亦载于《花间集》卷5。和凝20首。
《花间集》所收集的词作品艺术高妙,远超唐代诸家之作,自宋代以来的作家都对此集称道不已。南宋陆游《跋花间集》即云:“《花间集》者,[2]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陈振孙亦云“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诗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3]。既对其无视国事不滿,又对其体制精巧大加赞赏。清四库馆臣亦谓“诗余体变自唐,而盛行于五代,自宋以后体制益繁,选录益众,溯源星宿,当以此集为最古,唐末名家词曲,俱赖以仅存”,“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1]1823。在《通志》卷70《艺文略》八还著录有两种总集:《西蜀贤良文类》20卷,《青城山丈人观诗》2卷。《通志》将此二集编排于宋人总集之前,既不署作者名,也无法肯定其产生年代。据《蜀中广记》记载,唐开元中明皇感梦,下诏将蜀中丈人观自天国山移于青城山今所,而五代前蜀时也兴修青城山丈人观,于真君殿绘事五岳四渎十二溪女神像。由此记述推测,大致可以判定二集的编纂也应该在唐五代时期。
上述唐、五代巴蜀地域文人的总集除《花间集》尚存于世以外,其余各集均已不存。
二
宋代是历史上巴蜀文学创作辉煌的时代,以“三苏”为代表,蜀中名家辈出,成就斐然,不仅在宋代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在此后的各个時代也声誉卓著,而以汇集蜀地作家为收录对象而编纂的文学总集也层出不穷,数量繁多。
张逸、杨谔《潼川唱和集》1卷,见《通志》卷70《艺文略》八、《宋史》卷209《艺文志》八。
张逸字大隐,郑州荥阳人,进士及第,尝知青神县,后以龙图阁待制知梓州(今四川三台),又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凡四至蜀,为政循良。《宋史》卷426有传。杨谔,梓州人,景祐元年进士。以擅长科场程试诗著称。见司马光《续诗话》。二人时代接近,又都有在潼川(即宋代梓州)交集的经历,故此诗集应为二人在潼川时唱和之诗的汇纂。
宋璋《锦里玉堂编》5卷,见《宋史》卷209《艺文志》八“总集类”。
清雍正《四川通志》卷33载有宋璋,称其为成都府人,宋宝元进士。嘉庆《四川通志》卷188亦云“璋,成都人”。从《宋史》所载类目来看,宋璋所编应当是有关成都的文学总集。
章楶《成都古今诗集》6卷,见《宋史》卷209《艺文志》八。《蜀中广记》卷97亦著录是书,称“人代均不详”。
按:曹学佺所载不确。章楶字质夫,建州浦城人,治平二年进士,尝为成都府路转运使。多年镇守西北,累立边功。宋徽宗建中靖国时擢同知枢密院事。其事迹见《宋史》卷328本传。据《宋史》记载,我们可以确认,章氏编《成都古今诗集》是其在成都府路转运使任内。又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6记载,章楶任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是在宋哲宗元祐初,次年即移职。此集应该是在宋哲宗元祐初编成,其内容应是历代作家吟咏成都的诗文。
刘禹卿编《清才集》10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20著录云:“皇朝刘禹卿编辑古今题剑门诗什铭赋,蒲逢为之序。”按:刘禹卿为北宋元祐时人。康熙《岷州志》卷19收录其诗一首。其余生平事迹均无考。蒲逢,蜀人,宋景祐时进士,其余生平事迹亦不详。据晁公武语,此集当为汇纂吟咏蜀中剑门遗迹的诗賦总集。
费士戣编《固陵集》20卷。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97载:费士戣字达可,广都(今属成都双流)人,“嘉定中为夔守,编集管内山川建置碑文记诵为二十卷,多半夔门之书,在旁县者十之二三”。
而明代杨慎在其《全蜀艺文志》序中则称:“先君子在馆阁日,尝取袁说友所著《成都文类》,李光所编《固陵文类》及成都丙、丁两《记》《舆地纪胜》一书,上下旁搜,左右采获,欲纂为《蜀文献志》而未果也。”
固陵,即夔州的古称,《固陵集》与《固陵文类》应该是同一书而异名,而两处著录其编者却并非同一人。校点本《全蜀艺文志》的整理者刘琳、王晓波先生在其序文中亦尝论及这一问题,他们非常赞同四川师大教授王文才的论断,认为费士戣为此集的领衔者,而实际编者则是李光,因而后来才会出现这种不同署录的情况[4]4。
以上诸总集,仅仅见于各种目录书的著录,原书则久已亡佚,故无从詳尽讨论其内容,而现在还存世的宋代蜀人总集,尚有数种,以下予以讨论。
《三家宫词》3卷,不署编纂人名。《通志》卷248、《直斋书录解题》卷15标署云“唐王建、蜀花蕊夫人、本朝丞相王珪所著”,《蜀中广记》卷97著录相同。
王建,唐代颍州人,大历十年进士,尝仕为陕州司马。与韩愈、张籍同时,相友善。工为诗,思致幽远。
花蕊夫人,本姓费氏,青城(今属成都都江堰市)人,以才色入宫,后蜀主孟昶嬖之,号花蕊夫人,仿效唐王建《宫词》体作宫词一百首。费氏后来随后蜀主入宋,其词亦散落不传。宋熙宁五年,王安国在馆阁奉诏勘定蜀、楚、秦三地所献图书,以备收入馆中。于其中发现有敝纸二张,钞录宫词数十首,乃费氏手迹,其诗奇丽,与王建宫词无异。王安国于是让令史郭祥钞录入馆,并在其兄王安石处数数称诵,同官王珪、冯京都愿意传于世,费氏宫词乃得大行于世。[4]151
王珪,成都华阳(今属成都市)人,早年有才学,进士及第,历仕集贤院、知制诰、翰林学士。神宗熙宁时为参知政事,升为宰相,执政凡十六年。王珪善诗文,语言瑰丽,自成一家。有《华阳集》传世。事迹见《宋史》卷312本传。
宋人编此集是因为三人诗內容奇巧艳丽,诗风相近,又都是七言绝句,体裁相同,尽管王建非蜀人,而花蕊夫人诗又有此特殊经历,故而汇集为一编,此集也可视作蜀人总集。其编集时间,据《直斋书录解题》称王珪为“本朝丞相”,当为王珪任宰相时,即在北宋末年。
《三家宫词》旧有刻本,然“颠舛殊甚”,有将唐代诗人王昌齡、白居易、张籍、杜牧诗窜入王珪诗中者,有将花蕊夫人诗与王珪诗互混者,不一而足。明末毛晋取流传之本,参考其他文籍,一一厘正,故《四库全书》收录此集,署作“明毛晋编”[1]1724。现存是集有明毛晋汲古阁刊本、《四库全书》本等。
袁说友编《成都文类》50卷,这是由仕宦于蜀的非蜀籍人士所编的巴蜀文学总集。
袁说友(1140—1204),字起岩,号东塘居士,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流寓湖州(今属浙江)。隆兴初进士及第,庆元间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后累官至参知政事。
袁说友撰《成都文类序》称:
益,古大都会也。有山川之雄,有文物之盛,奇观绝景,仙游神迹,一草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士,骚人墨客,窥奇吐芳,声流文畅,散落人间,何可一二数也?……爰属僚士,摭诸方策,裒诸碑识,流传之所脍炙,士友之所见闻,大篇雄章,英词绮语,折法度,极眩耀,其以益而文者,悉登载汇辑焉。断自汉以下,迄于淳熙,其文篇凡一千有奇,类为十一目,厘为五十卷,益之文兹备矣。
袁说友序中所谓“十一目”者,是指按文体编为十一类,其类別依次为赋、诗、诏策制、表疏简记、书、序、记、杂记、箴铭赞颂、杂著、诔哀辞祭文。按其序文所言,收录一千篇文章,自汉代迄于南宋淳熙时巴蜀文人之文“兹备矣”,其搜罗汇辑文献之功显然巨大。后来明代杨慎编《全蜀艺文志》亦多有取材。
在现存《成都文类》卷首附有题名记,载录编集者共八人,计有:扈仲荣、杨汝明、费士威,何惪固、宋德之、赵震、徐景望、程迈孙,均为官于巴蜀州县的文学官吏,显然这是编纂此集的实际操作者。
清四库馆臣对该书评价毁誉参半,称其分门过细,“颇伤繁碎”,然“当时风俗使然,不足怪也”,又谓其与明人编《全蜀艺文志》相较,“不免于挂漏,然创始者难工,踵事者易密,固不能一例视之”,尤其强调其搜讨前代遗文之功,称“且使先无此书,则逸篇遗什,复俊(按:即周复俊。四库馆臣误署其为《全蜀艺文志》的编者)必有不能尽考者,其蒐辑之功,亦何可尽没乎?”[1]1699
有宋一代,眉山三苏父子均以文学显,他们不仅是蜀中学术的领军人物,同时也享有文章盛誉,尤其是苏轼的成就更巨,其才情堪称中国历史上旷古第一人,而在苏轼身边更是聚集着称为“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的一批文学之士,将苏氏学术推向极致。“三苏”的文集常被时人编纂成集,作为习学阅读的典范,合刻发行,成为时人的珍藏,在当时即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时谚。宋代人编眉山“三苏”的诗文合集,据祝尚书统计即有:[2]
编者不详: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80卷,南宋绍兴三十年饶州德兴县董应梦集古堂刊本,今存70卷。
编者不详:三苏先生文粹70卷,有宋婺州吴宅桂堂刊本。武谿游孝恭标题:标题三苏文62卷,有清宫藏本,《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六著录。国家图书馆有宋本残卷,存34卷。编者不詳:重广分门三苏先生文粹100卷,宋刊本,今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编者不詳:重广分门三苏先生文粹70卷,有宋刊本残卷,今上海图书馆存11卷①按:祝尚书云:以上二本虽然书名相同,然而编排体例各别,一百卷本为分类辑文,七十卷本则依人系文。抑或是一书,经人改编而异其卷数、编次,或原即二本,唯书名偶同,不可得知。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4:94.。
吕祖谦编:东莱标注三苏文集59卷(苏洵11卷,苏轼26卷,苏辙22卷),今国家图书馆存有宋刊本,缺8卷。
吕商隐编:三苏遗文,卷帙不详。尤袤《遂初堂书目》载录,不署编撰人名。而南宋人陆游有《跋三苏遗文》云:“此书蜀郡吕商隐周辅所编。周辅入朝为史官,得唐安守以归,未至家暴卒,可悲也。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务观识。”
以上所钞录宋人所编“三苏文集”,除吕商隐《三苏遗文》已不存世以外,其余诸集都有宋本或宋残本存世,从编纂内容来看其选择标准各异,有选本,有标注本,数量颇多,这一状况是历史上编纂家族文学总集所绝无仅有的,表现了当时“三苏”文学现象的繁盛境况,也反映出总集编纂在宋代时代特征。
三
明代所编巴蜀文学总集不多,只有寥寥数种,呈现出一种较为冷落的状态,这与明代巴蜀地域学术不振,滞后于别的地域的状况是相吻合的,这一时期是巴蜀学术的低谷。
明人编文学总集,我们首先要提及杨慎所编《全蜀艺文志》46卷②按:是书今存有嘉靖二十四年《四川总志》后附《全蜀志文志》,万历四十七年《四川总志》后附《全蜀艺文志》,《四库全书》钞本,清嘉庆二年成都刊本读月草堂本,嘉庆二十二年张汝杰乐山刊本。。
杨慎(1488—1559),蜀中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武宗、世宗两朝宰辅杨廷和之子,明武宗正德六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因“大礼议”跪于宫门哭谏,忤世宗,被充军云南永昌(今保山),此后一直在流放中度过,直至去世,都未能被旨赦还。《明史》卷192有传。杨慎在流放生涯中曾数次返蜀,于嘉靖十八年(1539)第五次返蜀,四川巡抚刘大谟礼聘其与王元正、杨名重修《四川通志》,杨慎负责修《艺文志》。“始事以八月乙卯日(初二),竣事以九月甲申(初一),自角匝轸,廿八日以毕”[4]12,总共用时二十八天。刘大谟对杨名、王元正所编部分甚不满意,于是又嘱按察司副使周复俊、佥事崔廷槐笔削重编,而对杨慎之《艺文志》未能易焉。《四川总志》刊于嘉靖二十四年,总16卷,又附《艺文志》于其后,单独成编,为64卷,别题为《全蜀艺文志》。
杨慎在《全蜀艺文志序》中称:
先君子在馆阁日,尝取袁说友《成都文类》、李光所编《固陵文类》及《成都》丙、丁两记、《舆地纪胜》一书,上下旁搜,左右采获,欲纂为《蜀文献志》而未果也。悼手泽之如新,怅往志之未绍。罪谪南裔,十有八年。辛丑之春,值捧戎檄,暂过故都,大中丞东阜刘公礼聘旧史氏玉壘王君舜卿、方洲杨君实卿,编录全志,而谬以艺文一局委之慎。乃捡故簏,探行箧,参之近志,复采诸家,择其菁华,褫其繁重,拾其遗逸,翦彼稂稗。……唐宋以下,遗文坠翰,骈出横陈,实繁有昈,乃博选而约载之,为卷尚盈七十。中间凡名宦游士篇咏,关于蜀者载之,若蜀人作仅一篇传者,非关于蜀,亦得载焉。[4]11-12
《全蜀艺文志》收录诗文1873篇,有名氏的作家631人。其收录的范围以与蜀事、蜀人是否有关为标准,如果作者不是蜀人,而有与蜀事相关的诗文,可以收录;作者为蜀人,作品传世甚少,有一篇非关于蜀的作品,亦可收录。所收诗文的范围以唐宋时代人最多,明人作品收录甚少,全书仅有90余篇,去取甚为严格,包括其父杨廷和也仅收诗文3篇,以示其不阿私好。
是书按诗文体裁编排,每类之下则按著者时代先后编次。前50卷门类基本沿袭《成都文类》体例,只在诗中添入“诗余”(词)一类,这与宋代末年词得以长足发展,蔚为大国的情形不无关系。后14卷包括世家、传、碑目、谱、跋、赤(尺)牍、行记、题名,其类目则为杨慎新添。在收文选目的问题上,也显示出杨慎的与众不同之处,将其与《成都文类》两相对照,袁氏是按照传统的文学标准选文,而杨慎则更看重诗文的史料价值,这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其后14卷所增加的几大类目,都属于史料的内容,对于探究巴蜀社会、人物、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卓有帮助;二是在所选诗文也注重选择反映蜀地的历史,而不是一味强调其文学性,如选范成大《益州古寺名画记》,几乎是一篇帐单式的记录,毫无文彩可言,然而却能覆盖蜀中寺院的古代名画目录,故能入编。
《全蜀艺文志》的编纂得力于其父(杨廷和)的前期搜集,方能在短短二十八天内蒇事,故是书的编纂也是了结其父的夙愿,“择其菁华,褫其繁重”,“博选约载”,而使是书成为明代编纂巴蜀文学总集的典范之作。
《全蜀艺文志》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它保留了明代之前的很多文学作品,有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就是依靠《全蜀艺文志》才得以保留下来,据刘、王二先生统计,这类文章大约有350余篇,占了全书的五分之一,可见该书保存巴蜀文献功劳甚钜。
继杨慎编辑《全蜀艺文志》之后,明杜应芳、胡承诏编有《补续全蜀艺文志》56卷。①按:《续修四库全书》收有明万历刻本。又按:《明史》卷97署作“《补蜀艺文志》54卷”,与现存该书卷帙不合,当有误。
杜应芳,湖北黄冈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为礼部主事,出守河间,任四川督学副使,迁福建按察使,归乡,卒。胡承诏,湖北黄陂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为内江县令,有令誉。累迁四川督学,与杜应芳齐名,升四川布政使。
是书称“补续”,其体例則基本沿袭了《全蜀艺文志》,按文体分卷,有一种文体数卷者,亦有一卷之中包罗数种文体者,其具体编排次序为:
卷1、2赋卷3风谣卷4至卷18诗卷19敕、谕、牒、诰卷20表、奏、疏卷21书卷22序卷24至卷32记卷33论、辩、解嘲卷34解、说、考卷35传卷36谱类卷37箴、铭、赞、跋卷38檄文、露布卷39墓碑卷40文卷41杂著卷42至卷45志余(诗话4卷,含诗余)卷46至卷卷51志余(外纪6卷)卷52志余逸编卷53动植纪异谱卷54器物谱卷55岩字石刻谱卷56行纪、题名,钤记附。
与《全蜀志文志》相比较,是书增补收录了前书未收,及晚于杨慎的一些作家及著作。其收文标准仍然主要是以收录蜀人的作品,以及非蜀籍作家吟咏蜀中的作品。
傅振商《蜀藻幽胜录》4卷①按:是书有1985年四川巴蜀书社据重庆图书馆藏明版影印本,本文引文即出自此本。。傅振商字君雨,河南汝阳人,万历丁未年(三十五年)进士,选为翰林庶吉士,散馆授江西道监察御史,迁右都御史,按察山西,未及行丁父忧。期满复职,赈济陕西灾荒,万历四十六年监陕西乡试,后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著有《杜诗分类》《古论元著》《缉玉录》《四家诗选》等,编有《蜀藻幽胜录》一书。事迹见《大清一统志》卷169。
傅振商于《秦蜀幽胜录》卷末有跋語称:“予留滞秦川,三易岁叙,白云凝目,瓜代屡愆,愁绪难遣,聊作蠧鱼,搜寻旧简,秦蜀幽文,几无剩采,泛及泐石,并为洗濯。观者勿讶輶轩,故作幽闲,寂寞采掇,业劳人之郁谱,固黯告于二集间已,至文工拙之辨,须之别淄渑者,裒集者不敢覆育于五色也。己未孟冬。”按:“己未”为万历四十七年,“三易岁叙”云者,是在赈灾关中,典监陕西乡试前后,职闲无事,而得以编纂文集为事。而其书自谓“秦蜀幽胜”,所编次当为陕西、四川两地诗文,而“蜀藻幽胜”,仅及巴蜀作家,不及陕西作家,似另有一编,然而未及见,抑或未能成编。
傅振商在《题蜀藻幽胜录序》中称:
蜀之位坤也,焕为英采必烂,不独受七经,后王、扬续相如帜也,盖世传其英,亦世发其藻矣。然山川奇秀,能拨人笔兴,即游历者峨眉之雪、巫山之云、江光之浩,爽气便横,而琴台草堂、剑阁筹笔之迹,落星捧砚之胜,青羊白鹤之矞,濯锦梅龙之故,又令人凭弔徘徊,纪述骏发,若与苏黄相映者。久而编断石泐,藻采将与人俱往,幸升庵博奥,尽揽收志林,庶借功人,以存什一,复苦脱遗,而荒伧复以芜秽参入,遂令火羞与鱼目共椟。予披沙搜实,止存菁华,汇备饱腹。虽摩诃池上,供十二小吏余渖,未睹其绪,然绣窠自足一披玩。有若听蜀国之弦,江灵之瑟者,蜀之奇藻幽逸之概,大观具是矣。若更有古洞云封、神碑壑隐,俟时出见者,须待五丁开山手更撷之。
据傅氏之叙,其编是集是有感于杨慎所编《全蜀艺文志》,而苦于杨慎一书之脱遗,及“荒伧复以芜秽参入”,于是“披沙搜实,止存菁华”,再编此集,而欲备存“蜀之奇藻幽逸”。《蜀藻幽胜录》一集,选文时限上自汉,下迄于元明②按:有学人谓是书收文下限为元代,然而核查该书实际状况,其卷三载金皋《忠节祠记》文末云“明嘉靖丙戌冬”,可证明收文下限应为明代。,收知名蜀籍人士以及虽非蜀籍却仕宦于蜀的名人之文章二百余篇,如像三国诸葛亮,唐王勃、卢照邻、韦皋、李德裕、裴度、李商隐、陆龟蒙,宋赵抃、黄庭坚、陆游、王十朋,虽为非蜀籍文人,然而均曾仕宦于蜀地,其所撰关于蜀地的文学作品,也予以收录。按文体分卷,分为赋、策、诏、敕、表、书笺、(卷一),序、记、(卷二、三),檄、难、铭、赞、颂、箴、碑、论、杂著、诔、哀辞、祭文、传、谱、跋、尺牍、行纪题名(卷四)。中国古代散文各体具备,令人开卷一览,可以了解有关巴蜀地域的军政大事、风土民情、山川名胜、神话人物等风貌,正如编者所言“蜀之奇藻幽逸之概,大观具是”。
与其他总集略有不同的是,傅氏收录文章时往往附有跋语,短短数语,或论作家德行,或评文章风格,大多画龙点睛,精到典要,如卷一于唐朱桃椎《茅茨赋》下评云:“先生知足,离居盘桓,口无二价,日惟一飡,筑土为室,卷叶为冠,斵轮之妙,齐扁同观。朱君蝉蜕尘世,徜徉茅茨,居然仙矣,岂必更修冲举世高之功,而乃目以真人?易茅茨以仙观,是从仙外觅仙矣,何能识其羽化之妙也?故揭其隐焉。君雨。”卷二何朝隐《洞真观横翠阁记》末云:“君雨评:翠色欲滴,令人有倚峰想。”卷三吴师孟《剑州重阳亭记》末云:“君雨评:抒写清淑,末更洒旷。”卷四李商隐《剑州重阳亭铭》末云:“义山不独诗尚精丽,而记铭亦楚楚秀绝,可谓有才人之致。”以上按语颇能体现上述特色,也反映傅氏的文学观念。
至明代,仍然还有人在续编“三苏文集”,如《四库全书总目》卷192著录有署名明杨慎编《三苏文范》18卷。四库馆臣怀疑其真实性,谓“所取皆近于科举之文,亦不类慎之所为,殆与《翰苑琼琚》(按:也是托名杨慎的伪作)均出依托也”,收入存目。今存有天启刊本、崇祯刊本。四川师大已故教授王文才先生《升庵著述录》云:“其书虽出依托,卷首一帙,搜罗明时所见苏文传本,选评本目,足资稽考,且有升庵父子评语二则,亦甚新奇。”[5]王先生所称杨慎评语,系指杨慎评语:“评三苏者,以奇崛评文安,以雄伟评文忠,以疏宕评文宣,而不知三贤之文,其致一也”。其书每卷均题“成都杨慎用修甫原选,公安袁宏道中郎父参阅”,吴郡姚可达刻。前四卷苏洵文四十一首,卷五至十六苏轼文二百一首,末二卷苏辙文二十三首。每篇皆加圈点、眉批、段意、夹注,文后有东莱、疉山、石斋、阳明、升庵、鹿门、卓吾、中郎、伯敬诸家总评。应该是一种选评本总集。[5]
《蓉溪书屋集》4卷、《续集》5卷。明绵州高金爵字舜举,其父高良贵、子高皥三世通显,筑有蓉溪书屋,时名人多有吟咏之作,正集明方豪(广东开化)辑,凡收78人,续集高第(绵州人)编,凡收71人。《四库总目》卷192“存目类”有载。
《秉忠定议集》2卷,不署编纂人名姓。明嘉靖中,都御史宋沧为四川巡抚,时有真州茂宼周天星、王打鱼等聚众三万馀人,攻城害民,谙熟兵法的宋沧迅速平息祸乱,得明世宗褒诏嘉奖,赐其玺书中有“秉忠定议,倏奏肤功”一语。时同官于蜀之同官作为《凯歌》《露布》等篇,汇集为一书,以纪其事,则用“秉忠定议”为名。《四库总目》卷192“存目类”有载。
巴蜀文学总集的编纂,有文献的记载是在唐、五代,后蜀人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是现存最早的蜀人词总集,收录了蜀中词人作品,纪录了词这一新兴文学样式。《花间集》是汇集中国词作的第一部总集,反映了五代时期巴蜀地域的卓越文学成就,至今仍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著作。
考察巴蜀文学总集的编纂情况,自唐以后各个时代,其实绩参差不齐,这与该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的大环境,尤其是与巴蜀地域的具体状况,紧密关联、相互制约。五代、宋代蜀地文学创作繁荣,人才辈出,文学总集的编纂也相当成功,数量众多,质量亦趋上乘;而元代蜀中各项事业凋落,文学总集的编纂处于停滞状态;明代时期则较元代差胜,编成了不少总集,然而就其横向比较而言,巴蜀地域较之其他地域的学术文化处于相对滞后的状况,与之相应,文学总集的编纂也与其他地域有一定的差距,除了数种文学总集,如《全蜀艺文志》《补续全蜀艺文志》《蜀藻幽胜录》较有特色以外,其馀著作都不甚著称;至清代,巴蜀文学总集的编纂又形成了一次高峰,总集的编纂比较繁荣,无论是编成的数量,抑或编纂质量,均超过明代,在清代文代文坛也足以与其他地域相媲美。
宋代眉山苏氏家族一门三父子,是宋代“蜀学”的领军人物,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都成就斐然,而且其家族后裔,传承其家风,不少人也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崭露头角,成就卓著,因此苏氏家族不仅在宋代时即为人所仰慕,而且垂誉后代,辉耀千古。其以“三苏”命名的文学总集,成为历代巴蜀文学总集编纂的热门,其关注度经久不衰。三苏文学总集数量众多,卷帙浩繁,成为巴蜀文学总集编纂的圧轴。一种家族性文学总集在历史上得以反复编纂,这一现象在中国传统文献编纂史上堪称为绝无仅有,值得研究者们重视探讨。
巴蜀文学总集的编纂得力于一批关注乡邦文化事业的学人的执着追求,无论其本籍即为蜀人,抑或仕宦游历于蜀,他们本着对巴蜀文学的热爱,在各个时代分别编成各类文学总集,记录下巴蜀文学曾经有过的辉煌,使巴蜀地域的学术命脉得以延续、宏扬,而像明代杨慎编《全蜀艺文志》、明清时代新繁费氏编《剑阁芳华集》,甚至凝聚了其家族几代人的努力。這种对本土学术文化的热情关注,值得现代学人继承、宏扬。
[1][清]永瑢, 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4:94.
[3][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14.
[4][明]杨慎编.全蜀艺文志[M].刘琳王晓波校点.北京:线装书局,2003.
[5]王文才.杨慎学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85.
I2
A
1009-3605(2017)06-0094-08
2017-07-09
1.李文泽,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文献、汉语史;2.霞绍晖,男,四川江油人,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历史文献、中国儒学;3.邓秋良,女,湖南宁乡人,广铁集团党校经济管理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铁路史、中国文学史、文学。
秦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