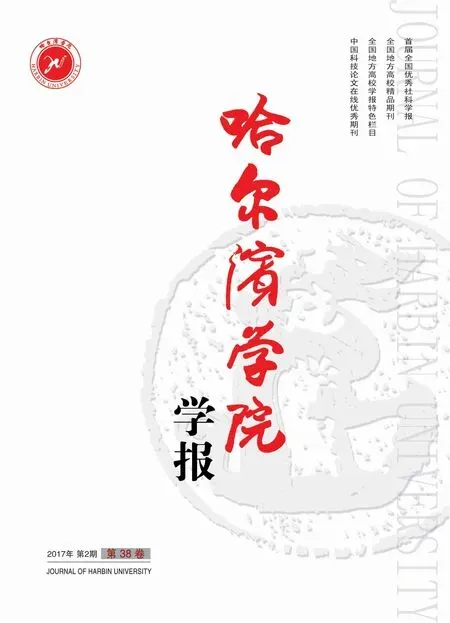从妖祥到贵贱:先秦秦汉相人观念演变探析
林业腾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从妖祥到贵贱:先秦秦汉相人观念演变探析
林业腾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春秋战国之时的相人多以野兽类比人身之相,由其相恶而论其性恶,再由其性恶而论其命凶。汉代相人则直接由相的贵贱论命的贵贱。从吉凶妖祥到吉凶贵贱,是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相术观念关键性的转变,这个转变起于春秋末战国初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时,定型于西汉初年。这个观念转变体现的是祖先崇拜到天命崇拜的转变,也是血缘贵贱到命相贵贱的转变。贵贱观念的加入,使相术真正成为专门之学,也确定了相术的基本性质。
相术;贵贱;观念
相术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极有意思的一门学问,很多相术观念都潜移默化地影响至今。学界对于相术也有很多研究成果,以先秦两汉为例,台湾祝平一的《汉代相人术》和北师大汝企和的《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就是其中的代表。祝平一的《汉代的相人术》是较早的系统研究古代相人术的著作,对汉代的看相行为和社会功能以及“圣人异相”等问题多有研讨。汝企和的《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则认为汉代相术发展比之前的突破在于相人者和相书两个方面,从这两个角度着重考察了汉代相术的发展。
先秦两汉时,相术主要记载在《左传》、《国语》、前四史和东汉王充的《论衡·骨相》和王符的《潜夫论·相列》等有限经典史籍中,因而断代或以书为主的研究不少。相术观念也是研究的重点,天命观、命定论、天人感应,类比象征、阴阳五行观等观念经常被提到,张克明更是在《科学与无神论》上连发了五篇文章来批评相术文化及观念。但是,虽然对相术相关的观念分析有很多,对于观念的动态转变研究还很少涉及,值得进一步深入。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相术观念有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即贵贱观念的加入,相术的主要观念由妖祥转变为贵贱。王晶波的《相术起源和中国古代命运观》提到:“早期相术所相的主要是人的身体状况,其次才是性情,进而命运,直到最后才关涉到人的贵贱吉凶,而这一关键的转变,或许就在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一转变,决定了相术在中国文化中的基本性质和地位。”[1]可惜并没有因此展开论述,而且吉凶观念并不是如贵贱观念一般后来才涉及的。
春秋战国到两汉的相术,在相术发展史中可以称之为早期相术,至晚在汉代才出现职业相者和相书。关于早期相术的分类以及相关的观念也是目前相术研究中争论比较多的两个方面。不同于后世明确的面相、骨相、手相、乳相之分,先秦两汉的相术多是根据体形、面貌、五官、骨骼、气色、体态、手纹等来推测吉凶祸福、贵贱夭寿,而且和卜筮、医术、识人之术联系甚多,春秋战国的相术又和汉代相术有很大的区别,这给相术的分类造成很大问题,标准不一。
因此,早期相术的研究还可以从分类和观念的转变两方面再深入探析梳理,而且在分类上梳理清楚相术与卜筮、医术、识人之术的关系也便于相术观念转念的分析。
一
《荀子·非相篇》:相术是“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吉凶妖祥”,王先谦《荀子集解》对相术的解释是“相,视也,视其骨状而知吉凶贵贱”。[2]荀子说相术为“知吉凶妖祥”,而清人王先谦的集解却说“知吉凶贵贱”,妖祥和贵贱的差别不得不注意。那何为妖祥?《中庸》言:“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朱熹注云:“祯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祸之萌。”[3](P33)
相术的内容,即相法,《荀子·非相篇》中有:“相人之形状颜色”,王充《论衡·骨相篇》中:“相或在内,或在外,或在形体,或在声气”,[4](P60)王符《潜夫论·相列篇》中:“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走,或在声响。”[5](P310)头面手足身形骨节,王符将之概括为骨法,并认为“然其大要,骨法为主,气色为侯”。[5](P314)从形状颜色到骨相和骨法气色,也体现了相术语言准确化和专业化的发展。
形状颜色、骨相、骨法气色是综合概括的说法,若要厘清相术观念的转变还要具体细分为以下六大类:相行走、相气色、相手足、相体型、相面貌和相声音。在这六类中,相行走与其说是相人之术,不如说是识人之术。相气色也与医术“望闻问切”颇多联系。相手足的记载在先秦两汉并不多。相体型、相面貌、相声音这三类是相人术的主体,相术观念的转变也主要是在这三类中体现出来。因此,这六大类型需要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相行走和相气色和相手足需要条条梳理,相体型、相面貌和相声音则要综合分析。
(一)相行走
相行走是基于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经验所作的判断。如斗伯比见莫敖以骄兵出征,说:“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6](P112)又如王孙满见秦师骄而言于周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6](P406)这都是从行为来判断内心,以此预测吉凶。《左传》中因不敬或不礼而被断言其亡乎的记载很多,也是属于相行走类型。
相行走与其说是相人之术,不如说是识人之术。识人之术,儒家极为热衷,孔子曾因宰予昼寝而感叹:“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7](P362)孔子对识人之术有极为贴切的总结,被后世视为圭臬:“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7](P107)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引《四书辨疑》对此这样解释:“盖所以者,言其现为之事也。所由者,言其事迹来历从由也。所安者,言其本心所主定止之处也。”[7](P108)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格外注重了眼睛的重要性:“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洪迈的《容斋四笔》,“人焉廋哉”条指明:“孔圣既已发之于前,孟子知言之要,续为之说,故简亮如此。”[8](P442)孔子和孟子对于识人之术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二)相气色
相气色与医术中的“望闻问切”极为类似,通过看气色来判断吉凶生死。《逸周书·太子晋解》有师旷相太子晋:“汝声轻浮,汝色赤火,色不寿。”[9](P1101)并断言太子晋活不过三年,三年未到,太子晋就死了。此事在《潜夫论·志氏姓篇》和《风俗通·正失篇》皆有引用,《太平御览·方术部·相下篇》亦有援引。但是否属实值得商榷。卢文弨校注此篇之时就曾言:“谢(墉)云:‘此篇诞而陋,与诸篇绝不类’。”[9](P1080)五行五色的言论在《黄帝内经》中多有言及,《风论篇》:“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10](P84)就与师旷的话很相近,若按《黄帝内经》的说法,太子晋的情况是典型的心风之状。但《逸周书》和《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一直争议颇多,各篇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年代也各有不同。据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考证,五行说的理论是在战国后期邹衍那辈人推动下发展成熟的。师旷身为春秋末期之人,加上这种五色的气色论在《左传》《国语》中的确没有相关记载,因此此事多数是后人的附会。但这种附会也正好体现了战国后期到秦汉时期五行气色观念的流行,从《潜夫论》和《风俗通》所引就可知一二。《论衡·自纪》中“人面色部七十有余,颊肌明洁,五色分别,隐微忧喜,皆可得察”[4](P579)的说法也多源于此。
在对相术进行分类时,有些学者将神色也归于气色一类,但实际上,神色和气色有很大区别。相气色更接近于医术,而相神色更接近于知人之术。如襄公二十一年,申叔豫为推辞楚王的任命而装病,卧冰而睡,鲜食而寝,结果楚王使医视之,言:“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6](P97)这纯为医家手段。昭十一年,单子会韩宣子于戚,“视下言徐”,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6](P1340)视下言徐,身体有疾而无力也,叔向能一眼看出,与医家无异也。庄四年,楚武王出征伐随前说“余心荡”,邓曼说,“王禄尽矣”。[6](P135)楚武王遂行而卒于樠木之下。心荡,心有隐疾也。也近乎医术。
相神色,实际上与识人之术中的察言观色并无二致,“贵贱在於骨法,忧喜在於容色”,容色即神色之意。这部分内容与相行走是重合的。如桓公九年冬,曹伯有疾而使太子朝鲁,曹太子乐奏而叹,施父曰:“曹大子其有忧乎。”[6](P101)施父由曹太子之叹而知其有忧,曹太子之忧实际上是忧其父亲的病情。果然,没过多久,来年正月,曹伯就死了。
成十四年,卫定公卒,太子不哀也,不内酌饮。夫人姜氏叹曰:“是夫也,将不唯卫国之败,其必始于未亡人!”[6](P735)卫太子临丧不哀,夫人姜氏认为其必为祸卫国。《汉书·李陵传》中关于汉武帝有类似记载:“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11](P766)孔子也曾有言:“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7](P260)
由此而论,相气色中的望面五色极有可能是战国后期到秦汉才流行的,春秋之世甚少记载。而相气色和医术类似,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则是相神色的识人之术。
相术到底相的是什么,若是相身体状况,与医术类似。若是相性情,则与识人之术类似。相术与医术和识人之术的区别就在于,医术看的是健康与否,知人之术看的是性情善恶,而相术则将之提高到命的层次,或者说相术的核心概念是命运。以此而言,相行走和相气色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相术或者说纯正的相术,是医术和识人之术掺入相术中或者说相术吸收了部分医术和识人之术的内容。
(三)相手足
相手足的记载并不多,在《左传》中仅见三例。仲子的“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6](P1)和唐叔虞的“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6](P1196)还有季友的“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6](P1600)仲子略有不同,手纹应该理解为“鲁”字而不是“为鲁夫人”,初生小孩之手能容纳四个字的手纹并不实际。
以内容论,三者都是“生而有文”在手,为鲁夫人是命;友字是名;虞字是名也是命。但实际上,“生而有文”在手本身就代表着天命在身。
以时间论,唐叔虞和季友的“生而有文”之事都是相隔甚久才分别由子产和史墨口中说出,而在此之前并无记载,且其语境也值得注意。晋侯有疾,卜人说是实沈、台骀作祟,子产所回答的是实沈、台骀的来历,此二人之名出自卜人之口而晋“史莫之知”。[6](P1196)晋国史官都不知道而子产和卜人却知道,一方面可能体现的是子产的博闻和晋国史官的寡识。另一方面,实沈、台骀之事可能仅在卜人之间所传闻,而史家则不知亦不记。赵简子问为何季氏出其君而民不怪罪,史墨回答的是季氏有天命,“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6](P1600)并用季友手纹来作佐证。赵简子表面上问的是季氏,其实问的是赵氏,当时正是六卿分晋之时。史墨的回答亦是为了迎合赵简子的需要。
汉代史册中关于并无手纹的记载,仅有《后汉书·李固传》的“鼎角匿犀,足履龟文”。[12](P608)但李固的“鼎角匿犀”和光武帝的“日角”、[12](P1)梁皇后的“日角偃月”[12](P80)皆是南朝范晔的《后汉书》所记载,与先秦和西汉关于面貌的记载截然不同,除了说明东汉相术较前代在术语上更具专业性,也不排除出自东汉以后的可能性。
考证“生而有文在手”是否属实并无意义,只需将其看作是符命,而且是生而带来的先天符命即可。从这点看,手纹与梦兰入腹和梦龙入腹并无区别,只是方式不同。“生而有文”在手在汉代典籍并不多见,可见当时此种观念并不甚流行。倒是《潜夫论·相列篇》有“手足欲深细明直”,[5](P310)与后世流行的三大主线的手相学有点渊源。可是,后世史书中,“生而有文”在手作为天命象征的一种重要手法,因很有效果而被后世经常援用,郑樵《通志·氏族略》“生而有文”条就记载武氏的“武”字、鲜于氏的“左鱼右羊”、阎氏的“阎”字等,对此郑樵有言:“臣谨按《左氏》谓季友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因以命之。每疑其诞也。后人由此复广其道焉”。[13](P485)
二
相体型、相面貌、相声音这三种类型是早期相术的主要构成,也最能体现相术观念的转变,在具体相人过程中也多是综合这三方面来得出结论,所以这三类应该合在一起。春秋战国相术和秦汉相术有很大不同。先秦相术是由相到性再到命,两汉相术是直接由相到命。
春秋战国时期经常以兽类来比附人的身体。如楚国大夫子上论商臣之相:“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楚国令尹子文论子越椒之相:“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晋国叔向之母论其孙子伯石之相“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6]还有《国语·晋语》中她论其子叔鱼之相,“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餍也,必以贿死。”[14](P212)好歹叔鱼出生后还是她看了之后才说的,杨食我(伯石)出生她看都不看,问其号而还,“其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14](P212)
从记载来看,这几处相人之事都是发生在晋国和楚国,这说明春秋时期晋楚相人习气较流行,估计也与史料来源有关。孟子曾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3](P295)可见,晋楚鲁三国史书记载较其他各国完备。相人事例在其他国家未必没有,只是不曾记于史册而得以流传。
又或者这种以兽类比附人身的观念最初流行于晋楚两地,战国时才逐渐流行于各国。周内史叔服相公孙敖的两个儿子就不曾如此,仅用“丰下”一词。[6](P419)这是“相人”二字在可见的经典中最早的记载。荀子说“古无相人,学者不道也。”除了说世俗所称,学者不道,有也当无以外,古时无专业的相人者也是一个原因。史官应该是最早拥有相人技能的群体。这种技能继而又扩散到士大夫。周王室大夫如单襄公、刘康公之流虽经常因诸侯不敬不礼而言其必亡,也未曾论及长相和用兽相比附。
战国时齐、越、秦皆有兽相记载,可见观念流传之广。《战国策·齐策》记载貌辨言齐太子,“太子相不仁,过颐豕视,若是者倍反,不若废太子,更立卫姬婴儿郊师。”[15](P480)至于越国范蠡论勾践之相“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16](P1573)一是时间相隔已久,此种兽相观念流传渐广;二是吴国是靠申公巫臣过去教习车战才与中原通使,晋楚文化对吴越两地影响颇多,也就无怪乎范蠡能有此言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大梁人尉缭论秦始皇相“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16](P197)可见,尉缭的文化根底也是出自晋楚两地。这种兽相观念后来也体现在《汉书·王莽传》中的王莽之相。
从内容来看,这种兽相观念体现的是性情的善恶。熊虎之状,虎狼之心,豺狼之声都是恶相,是狠人、忍人之相。由其相恶而论其性恶,再由其性恶而论其命凶。王充《论衡·骨相篇》言:“故范蠡、尉缭见性行之证,而以定处来事之实,实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系於形体,明矣。”[4](P60)这是从身体到性情再到命运的逻辑推论步骤。这种命运也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宗族国家的命运。这是兴亡观的体现。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逻辑框架中没有贵贱观念的存在。王晶波说“早期相术所相的主要是人的身体状况,其次才是性情,进而命运,直到最后才关涉到人的贵贱吉凶”,是比较准确的,但还值得再细究下去。身体、性情、命运这三点若按相术的发展过程而言是否就是如此循序渐进未可得知,因为命的观念由来已久。但在逻辑层面的推论顺序的确如此。相术中贵贱观念是后来加入的,也由此决定了相术在中国文化中的性质,但吉凶的观念一早就有,并不是如贵贱一样是后来加入的。
兽相还蕴含着对被相者的道德评价,而且贬义为多。专诸的勇士之相“碓颡而深目,虎膺而熊背”[17](P14)算是不多的正面例子之一,仅言其勇武而不言性恶。这种兽相的评价有可能是出自最初的相人者,也有可能出自事后的流传,还有可能出自史家的丑化手法。神化或者丑化,其出发点是一样的,即政权的合法性。可以用数轴理论来比喻。一个数轴,从原点出发,往正数方向走是神化,往负数方向走就是丑化,而原点就是政权的合法性依据。
从发生之时来看,子上论商臣和貌辨论齐太子皆是因为立储,子文和叔向之母则是孩子出生之时。若从古时立储和孩子出生需要占卜来看,在这里,相术实际上是发挥着占卜的作用或者说取代了占卜。《论衡·卜筮》云:“夫钻龟揲蓍,自有兆数,兆数之见,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适与相逢。”[4](P483)由此而言,早期相术和卜筮功能类似,都是为了寻求吉凶的兆数启示,只是方式不同。占卜是钻龟揲蓍,相术是揣度形体性命。或者说,当“天道远人道迩”之后,占卜的可信度已逐渐减低,“枯龟之骨,死蓍之茎,问生之天地,世人谓之天地报应,误矣。”[4](P481)但对命运天命的追问探索并不曾减少,于是基于天人交感的理论背景下,“欲知天,以人事”[4](P480)的实际背景下,以人身为媒介来解释天命的相术得到更多关注和发展。可以说,相术在卜筮的基础上发展,最终把卜筮兼容,相者相工取代了先秦的巫史卜祝。到了东汉,后宫纳妃就靠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来挑选“姿色端丽,合法相者”。[12](P69)
与先秦相比,汉代相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记载来看,专业相者除了有许负、田文、茅通、朱建平等有名有姓的记载外,相工相者二词也多次出现。相工已成为一种制度,一种职业。相较于战国时姑布子卿和唐举的零星记载,许负等人更趋于职业化,影响也更深,后世诸多以许负命名的相术就可看出一二。另外非职业相人者也大量出现,如相刘邦的吕父、相卫青的钳徒、相翟方进的蔡父,连刘邦都亲自相刘濞,可见相术流传之广,上到皇帝,下到贩夫走卒都热衷相术。武帝的外婆臧兒在女儿嫁给金王孙并生下一女后,在卜筮到“两女皆当贵”[16](P1763)之后,又从金氏把女儿夺了回来并送入太子宫,这才生了武帝。因为“两女皆当贵”这一句话而做出如此之事,可见相术观念影响之深。
相书的出现也表明,相术实现了经验积累到理论总结的蜕变,这是相术发展极其重要的一步。汝企和的《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认为汉代相术发展比之前的突破在于相人者和相书两个方面很有创见,[18]但是相术还有一个关键的变化就是贵贱观念的加入。
从内容看,不同于先秦相术的以兽相知妖祥,汉代是以命相知贵贱。兽相之例仅见于班超的“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12](P486)班超之相也不同于之前的恶相,而是万里封侯之相。其他的如刘邦的“君相贵不可言”,卫青的“贵人也,官至封侯”,薄姬的“云当生天子”,英布的“当刑而王”,周亚夫的“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於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和邓通的“当贫饿死”,李广的“数奇”,[16]翟方进的“小史有封侯骨”,黄霸之妻的“此妇人当富贵”。[11]诸多例子皆是讲命之贵贱,而全无先秦之时的宗族国家兴亡之感。此相汉世称之为骨相,也体现了相术对人体这个媒介认识的深入。但也许用命相更为准确。而且有意思的是命相还分出等级,有贵不可言的帝王之相,封王封侯之相,还有贫贱饿死之相,实际上就是汉世等级观念加强在天命中的体现。
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曾言:“西周及其以前之所谓命,都是与统治权有关。到了春秋时期,扩大而为‘民受天地之衷以生,所谓命也’的一般人的命;即天所命于人的不仅是王者的政权,更进而成为一般人民道德根据的命;这是天命观念划时代的大发展。”[19](P384)国家之命有兴衰成败,个人之命则是高低贵贱。这也是天命下移后个人命运观在相术中的体现。但为何会有如此之转念呢?
赵翼的《廿二史劄记》中著名的“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一条已说明白:“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20](P37)
商周时,实行世卿世禄,权利的合法性依据是血缘,普遍的信仰是祖先崇拜,而亲族关系是决定政治地位的重要因素。春秋末战国初,世卿世禄逐渐崩溃,士阶级兴起,布衣阶层逐渐上位掌权,血缘已不足以作为充分的权利依据,而天命观念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于是从天命中衍生出类血缘的存在,即命相,天命之子或者天命眷顾即为贵命。这是由血缘贵贱到命相贵贱的转变,是由祖先崇拜到天命崇拜的转变,突破了世俗血缘关系的限制,将之放大到天命血缘的范畴。这一转变在汉初定型,但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末战国初的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如姑布子卿相赵简子诸子,言翟婢所生的毋恤为“此真将军矣”,理由是“天所授,虽贱必贵”。[16](P1609)可见天命贵贱逐渐取代血缘贵贱。
王充《论衡·吉验》言:“创业龙兴,由微贱起於颠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尝无天人神怪光显之验乎!”[4](P48)就点出其中奥妙,关键是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起于微末而得登高位,若无命运的推动怎么说都说不过去。相术是验证天命贵贱的一种重要方式,其他的如梦占、卜筮、感生等手法在此时期也颇多运用。只是相比之下,战国初以梦占卜筮为主,西汉初以相术为主,而东汉初则加入了很多谶纬符命的成分,且相术术语更具专业化。
三
《荀子·非相》有:“相人之形貌颜色而知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2](P72)是相人之术古人没有呢还是学者不道呢?王先谦解释荀子的意思是“世俗所称,学者不道。故虽有,直以为无耳”。[2](P72)既然存在在世俗中,为何原始社会却找不到相关记载呢?
早期相术和卜筮、医术和识人之术关系极为密切。卜筮之术由史官掌握,而内史叔服正是最早的有记载的相人者。但早期相术在史官技能中并不占多少比重。相术的流行是伴随着“天道远人道迩”而逐渐流行发展的。换言之,相术其实是卜筮的简化。卜筮是通过龟甲蓍草等媒介来得到天地间的吉凶预兆,相术同样如此,只是这个媒介变成了人的身体。而要从身体这个媒介中得到信息,需要的是类似医术“望、闻、问、切”的能力。
在不需要额外的媒介后,相术开始大范围的流传扩散,出现了三种发展趋势,其一是相人之术和占卜联系在一起,成专门之学,由专业的相者掌握,相者相士取代了先秦巫史卜祝的职能,相术实现职业化、专门化的转变;[21]其二是相人之术脱离占卜的局限,大范围流传,民间爱好相术的人大量出现,相术成大众之学,且与识人之术联系紧密;其三是相术较彻底地去神秘化后独立成为识人之术,主要根据身体行为和性情来作为判断依据,并不涉及命运层面。
卜筮之术、相人之术、识人之术,是由天道到人道逐步简化和发展的过程。相术是在卜筮的基础上融合部分医术和识人之术发展起来的。也正因为如此,更要厘清相术和卜筮、医术、识人之术的关系。在相术的六大类中,相行走与识人之术极为相近。相气色与医术“望闻问切”也颇多联系。相术和医术、识人之术这三者往往会交叉在一起,难以区分。但是,相术的核心概念是命,这是相术和医术、识人之术的区别所在。相手足的记载在先秦两汉并不多。相术观念的转变主要是体现在相体型、相面貌、相声音这三类中。
在剖析相术观念中,天命观和天人感应是经常被提到的,但多流于表面,忽略了动态的研究。天命观是相术的核心观念,不应仅限于命定论,还要关注天命观的演变。相术观念的转变是由于天命观的转变,天命观的转变又在于世俗权力合法性依据的改变,而权利合法性依据的转变又是由于社会背景的转变,由世卿世禄之局面逐渐转为布衣将相之局面。这一变局起于春秋末战国初而止于刘邦建立。商周到春秋战国再到秦汉,实现了祖先崇拜到天命崇拜的转变,血缘贵贱到命相贵贱的转变。相术的观念也由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妖祥兴亡转变为以等级为基础的高低贵贱。实际上,贵贱观念的加入才使相术独立于卜筮,成为专门之学。
[1]王晶波.相术起源和中国古代命运观[J].甘肃社会科学,2004,(5).
[2]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王充.张宗祥.论衡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王符.汪继培.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8]洪迈.容斋随笔[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9]黄怀信.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0]黄帝内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班固.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2]范晔.后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13]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左丘明.韦昭.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5]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7]赵晔.吴越春秋[M].济南:齐鲁书社,2000.
[18]汝企和.两汉时期之相人术和汉代社会[J].齐鲁学刊,2005,(5).
[19]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0]赵翼.王树民.廿二史箚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1]幽亚雪.“引经决狱”影响下的西汉司法审判制度[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6,(4).
责任编辑:赵 岸
From Animals as Symbols of Luck to Noble and Humble Blood:The Change of Pre-Qin Physiognomist’s Views
LIN Ye-teng
(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0)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physiognomists often used the image of the animals to analogy the human. A person may be judged as evil because he looked evil. Furthermore,he may be concluded to have a bad life since his nature was evil. At Han period,physiognomists judged people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looked noble or humble. The change of using animals as symbols of luck to judging noble or humble looks is a key change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Qin-Han period. This change started at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when Qin was split into three parts and came into being at the early West Han period. This change of opinions is the change of ancestor worshiping and destiny worshiping,which is the change of the value of blood,from noble to humble,and destiny,from noble to humble. The idea of nobly and humble makes physiognomy a discipline and claims its basics.
physiognomy;noble and humble;opinion
2016-04-08
林业腾(1990-),男,广东雷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1004—5856(2017)02—0110—06
K23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2.028
——论庄子之“物无贵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