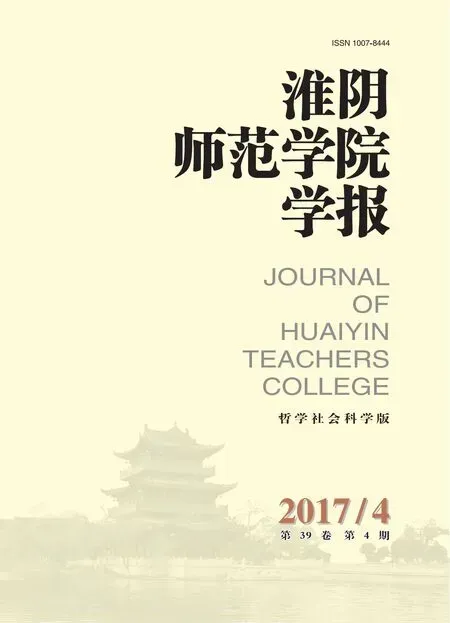论《资本论》中的商品形象及其美学蕴含
黄世权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论《资本论》中的商品形象及其美学蕴含
黄世权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遵循劳动二重性分析商品的特性,透视商品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性质,由此描绘商品的物神形象和拜物教性质,揭示商品这一资本主义世界最为普通的形象所具有的丰富的哲学美学蕴含。马克思通过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揭示意识形态的客观生成过程,并展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化方法。最后,马克思更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社会关系臻于澄明之境的社会条件,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话。《资本论》的商品形象分析奠定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哲学美学起点,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审美批判的基本方向。
资本论;商品形象;物神;拜物教;意识形态批判;澄明之境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秘密的破解直接从最为常见的一个现象或形象入手,这就是商品。商品不仅是资本主义世界随处可见的人工制品,是资本主义的现实物质起点,同时在商品身上也隐藏着资本主义的秘密。当然,在广阔的历史视野上,商品的发生发展,也展示了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规律和轨迹,而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商品蔚然成风,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和自身特色渲染得淋漓尽致。马克思的商品分析,建立在劳动的二重性的基础上,即形成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形成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感性特征,抽象劳动形成了商品超感觉的神秘性质,这就是拜物教和物神形象。马克思从商品拜物教中分析出人类劳动的神秘化倾向和生成意识形态的客观进程,同时马克思也展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前景,最后马克思还畅想未来社会关系如何走向“明白而合理”的澄明之境的具体方案。《资本论》首章的商品分析,奠定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路径,一直延伸到最遥远的远景。*马克思在《商品》章所奠定的拜物教及其美学含蕴,在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中分化为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这些拜物教沆瀣一气,编织了一个严密的意识形态迷雾和神话结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逐渐深入的批判,就是一步步地消解这些蛛网般的神话网络。在次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从商品拜物教延伸至资本拜物教,是一种独特的戳穿神话的快意之旅。马克思商品分析所揭示的商品美学,则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成为最重要的美学现象,激起了后马克思时代的美学家持续深入地批判。对此的讨论构成了笔者另外两篇论文《晚期资本主义的商品美学》和《最美丽的商品:晚期资本主义的身体美学》的主要内容。
一、拜物教的起源:商品的幽灵属性和物神形象
马克思对商品这一形象的处理,一开始就显示了高度的美学意味。马克思从商品的价值两重性入手分析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商品的物质属性看得见摸得着,作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商品一下子就变得奇妙难知了: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的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1]50-51
自由娴熟地运用具体性和普遍性相统一的辩证法的分析,马克思一开始就抓住了商品这个看似简单其实内蕴深刻的劳动产品的既实又虚的本性。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及其各自属性的区分,奠定了《资本论》的商品分析以及货币和资本分析的基本框架。如果说使用价值构成了商品的物质属性,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具体的东西,那么交换价值的存在,却赋予了商品超越感觉的抽象品格,这种抽象品格虽然论其实质不过是人类抽象劳动的体现,但是却赋予了商品一种神奇的属性。两种价值的结合,使得商品既具体可感同时又超越感觉之上。正是这种具体可感又超越感觉的奇妙结合,使商品一开始就染上了奇特的玄学色彩,马克思忍不住称之为“幽灵”般的对象。
毫无疑问,马克思指称的这种幽灵形象构成了《资本论》论述起点的商品现象的基本特点。幽灵,它具有人类的形象,但是却没有人类的物理属性,是介于感觉和超感觉之间的奇妙结合。因此,它构成了人类生活中为人津津乐道的美学形象。*德里达把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称之为驱魔,并且分析了马克思著作中的大量的幽灵的谱系,认为马克思特别喜欢使用幽灵来指代精神形态。从《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都贯穿了对幽灵的驱逐。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马克思用幽灵形象也深刻地揭示了商品这种独特美学形象的特点,既具有光彩夺目的感性形象同时又超越感觉,另有深意,不能仅凭感觉予以把握。一切美学现象和美学形象其实都具有这个特点,是感性形式和超感性内涵的融合。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2]在黑格尔这个深刻的美的定义中,超感性的理念就必须通过具体的感性显现出来。强调感性与超感性的结合,是黑格尔哲学中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这条重要原理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很多的重要概念和观点都与这位古典大师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借助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思维,马克思揭示了劳动的二重性。这一重要区分,确立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高度。在美学的意义上,劳动的具体感性和抽象属性的这种结合,一开始就使商品这种物质产品包含了审美的属性,同时它的幽灵般的属性也隐含了人类审美的基本秘密。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商品身上带着劳动的二重性,也就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形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形成了商品可以自由交换的基础。这里有趣的不是马克思对具体劳动的论述,而是对抽象劳动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劳动形式的分析,马克思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揭示了商品的一个更重要的性质和形象特点,这就是拜物教的性质,或者说物神的形象。马克思在分析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的主导物品符号时展现出了异常精湛的分析能力,这种分析实际上也是一种去神秘化,一种类似于德里达所说的“驱魔”。*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开头对商品的幽灵性质的揭示,“一开始就是一个宏大的驱魔场面”。见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马克思说得很有意思:“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1]88
马克思用辩证法的犀利眼光洞穿了商品这种貌似简单实际复杂的劳动产品的神秘性质,并用形而上学和神学的怪诞来形容商品的奇特之处。在这里形而上学当然是指商品的超感觉的特质,而神学的怪诞则是指神学对世界的颠倒,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对待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进一步落实,马克思这里看似信手拈来的对神学的嘲讽,其实指向的主要是基督教这种神学。在马克思的批判对象中,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神学都是脱离现实沉浸在超感觉的意识,特别是基督教是对世界的颠倒的反映。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形而上学和神学都是对世界的歪曲的认识,颠倒的认识,而造成这种歪曲和颠倒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颠倒的世界是马克思哲学和美学中的一个异常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来源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黑格尔看来,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对世界的一种颠倒,因此,资产阶级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的辩护就是一种颠倒的认识。客观事物运动本身也会产生颠倒的效果,例如货币就可以把一切都颠倒过来。资本主义世界就是一个颠倒的世界,一切宗教的世界都是颠倒的世界。马克思的批判就是把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正如他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一样。从这个意义讲,马克思这种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批判实际上就是一种颠倒行为,类似一种旨在解构的修辞行为,就像保罗·德曼在《阅读的寓言》里论述里尔克的诗歌修辞特征所显示的。见Pual de Man, Allegories of Reading,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就像劳动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就具有了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神秘性质,人类在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和认识自身现实时也会陷入形而上学或神学的泥淖中。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直接触及人类认识世界的奥秘,这就是普遍存在的神秘化过程。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连带对人类意识形态建构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是对这种存在于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之中的神秘化的破解。马克思接着分析:
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1]89-90
马克思的分析建立在抽象劳动这一基点上,正是这种超感觉的抽象的人类劳动奠定了物品交换的基础,也就是促成了商品的出现,但也正是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劳动造成了商品的神秘性质。商品交换过程中,我们看不到抽象劳动的存在,只能看到具体劳动所形成的物质属性,也就是劳动产品的具体物理属性。因此,商品交换只能呈现出物与物的关系,它无法将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出来。马克思用人类视神经成像这一物理现象来说明这一点,本来一物在人类眼睛中的形象,是视神经的主观产物,但是却被人类当成外在事物的客观形式。主观的形象取得了客观的形式。同理,商品在人们眼里也仅仅具有物品的属性,而它所具有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淹没不见了。为了更进一步说清这一点,马克思再次回到宗教,宗教所创立的产物,本来是人类头脑的产物,一旦作为神物出现,却成为超越于人类之上的东西,成为人类顶礼膜拜的圣物。商品也具有这种虚幻性质,本来是人手的产物,却获得了与人无关、独立自主的性质,马克思称之为拜物教或者说物神。马克思这里所洞悉的人类物质实践的神秘化,其实是根于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本性。这种神秘化可以与康德对人类理性的深刻洞见联系起来思考,或许能得到更透彻的理解。康德认识到人类的理性天然地会产生幻相,这就是他所说的“纯粹理性的先验幻相”[3]259。这种幻相来源于人类理性把主观的东西偷换成了客观的东西,把思维的主观条件当成了客体的知识。可惊的是,这是人类理性固有的一种本性,不可根除。“纯粹理性有一种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辩证论,它不是某个生手由于缺乏知识而陷进去的,或者是某个诡辩论者为了迷惑有理性的人而故意编造出来的,而是不可阻挡地依附于人类理性身上的,甚至在我们揭穿了它的假象之后,它仍然不断地迷乱人类理性。”[3]261不过,与康德稍显不同的是,马克思更接近黑格尔的习惯,强调存在与思维的统一,在他看来,商品的这种神秘化,主要的是来自商品本身,来自商品身上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结合,而不单纯是理性的认识上的幻相。
马克思在商品这种人类的劳动产品身上发现了人类劳动的二重性所造成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神秘性质,发现了商品的谜一般的、幽灵般的拜物教色彩,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而马克思把商品形象与形而上学和宗教联系起来论述,更包含着非常深刻的哲学美学内涵。从方法上说,马克思是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来思考商品的特征,把商品的生产与人类劳动的哲学含义深刻联系起来,在劳动本体的意义进行说明,同时也揭示了这种卢卡奇称之为“劳动本体”所含蕴的美学意义。[4]在此,马克思也并不是在一般的联想和比喻的意义上把商品与宗教联系在一起,虽然马克思也是说“找一个比喻”,但是马克思并不是在这里才把两者联系起来,在其他更多的场合,马克思也把资本主义的诸多现象与宗教现象一起论述,就在论述商品的拜物教这一节里的后面,马克思也谈到宗教存在的土壤。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货币和资本与基督教联系起来论述,是马克思一贯的兴趣,这里其实包含了马克思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和美学命题,也是马克思特有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旨趣所在。*日本学者广松涉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始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和物化现象结合起来,并命名为“物象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对这种物象化的批判。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当事者的直接意识中,通过物象的对象面貌而曲折地映现的失态称作物象化”,并强调这种物象是客观的。广松涉这个概念,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看,较完善地概括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所具有的美学意义,的确,由于物化和拜物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和货币,都是以具体的形态而魅惑人类的意识,是以物象的形式而存在和运动的。这些物象都是具体客观的,并以这个特点而掩盖了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物化现实以物象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商品和货币天然地具有美学的特征。见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2页。
二、商品拜物教与意识形态批判
如同形而上学和神学一样,商品这种人类劳动的产品,天然地就具有神秘的性质和魅惑的色彩,不过这种神秘性质和魅惑色彩并不是来自人类的有意行为,而是人类活动天然固有的。形而上学和神学其实也是这样,在信奉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人看来,形而上学和神学所创造或臆想的产物,是自然的产物,并不是人的思想或观念的产物,它们是永恒存在的,超越人的感觉之上,从柏拉图的神秘的理式、康德的神秘的物自体到黑格尔的理念,不过是这些形而上学思想家的主观的构想,却演变成宇宙或世界的本源,这与基督教以及其他神学所设想的上帝和天国等抽象概念一样,都是脱离了人类感觉的超感觉的神秘之物,这些神秘之物反过来成为人类精神顶礼膜拜的圣物、神物,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对世界的看法。人类在对待自己的造物的时候,从商品到哲学理念再到宗教幻想,都有一个异常强大的倾向,把自己的造物当作神物来膜拜,将人类的意志屈服于自己的造物。对待艺术也是这样。人类的精神总是被自己造的东西遮蔽,这些人类劳动的造物形成一个强大的迷雾,让人类无法看清世界的真相以及世界与自身的关系。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一道构建起这层浓浓的迷雾,人类自己创造的世界成了令人类自我迷失的东西。马克思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因此包含着这样一个重要的洞见:人类的行为本身就具有神秘化的倾向,会自动生成意识形态的迷雾,因此只有运用科学的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才能破解它们,并让人类认清自身的处境。而由于一些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有意掩盖,这种被意识形态遮蔽的情形就更严重了。*关于拜物教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可参看Dimitri Dimoulis and John Milios: Commodity Fetishism vs. Capitalism Fetish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ume 12: 3(3—42), Kon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2004.该文对拜物教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拜物教归结为意识形态,就像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做的那样。鉴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无比复杂,我倾向于接受伊格尔顿的一个说法,即意识形态实际上也包含一个历史的客观过程,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并不仅仅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家所制造的虚假意识,它也是社会运动的客观产物。这样,商品拜物教自然也就生成了意识形态。伊格尔顿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最有名的范例就是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the most celebrated instance of this sense, is Marx`s theory of fetishism of commodities)见Terry Eagleton,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Verso 1991, p30.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时论述了科学研究的意义,就透露出了马克思这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随后谈到一般的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与科学分析。这一段话以及后面对宗教的批判都具有极为突出的方法论的意义,显示了马克思这种独特的分析方法的深刻性。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1]93
马克思这里所强调的是本来属于历史的产物,在人们看来却成了自古就存在的自然形式。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概括了人类思维谬误的一个规律:历史的自然化。原本历史的东西被视为自然而然的东西,天然的东西,甚至永恒不变的东西。例如商品世界的特殊商品,货币,长期以来人们就无法看清它的历史性质,而把它视为天然存在的东西。马克思说这些自然形式,对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它们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范畴。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般人们以及他的精神代表,都把这些本属历史的东西当作客观自然的天经地义的范畴来接受,用以解释建立在这些范畴之上的经济现象。对于这种错误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在这一节的一个很长的注释里再次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做法,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99在下一个注释里,马克思再次引用自己在《哲学的贫困》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经济学家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们臆造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一切异教都是人为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1]99
马克思指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的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神秘性和魔幻性,其实都是从商品生产的独特形式中产生的,商品生产的独特形式就是劳动分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社会劳动的同等性使得私人劳动的成果得以自由交换,却无法理解交换背后的原因。马克思设想了几种不存在商品交换或交换不完善的社会形式,一个是孤岛上事事亲为、没有交换的鲁滨逊,一个是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最后一个是自由人联合体,这三种生产形式中都没有发达的商品交易,一切劳动成果都不是按照商品交换的方式分配,因而一切劳动都呈现出清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物的关系。这就是马克思强调的一旦逃离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商品的神秘和魔化就荡然无存了。顺便说一句,马克思这个形象的说法也具有深远的方法论意义,对人类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真正的科学分析必须跳出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本身,而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它们还原为历史现象而非天然存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和奥秘的破解,是这种方法的运用典范。*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反复声言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达到的科学,与早期的著述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其实这是夸张的说法,经不起细致的推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奥秘的揭示,其实是源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研究中就已形成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纯熟运用。
马克思从这里再次升华,把论题从生产形式与精神生产的形式联系起来,并指出两者内在的一致性。马克思说:
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1]97
马克思这里揭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解释模式,生产形式或方式,会有相应的精神生产的方式。精神生产方式会采取与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商品生产的前提是抽象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是价值的共同性,这种对抽象的认识,本身就表现出高度的精神向度,因此在对待整体世界上,自然也会采取相应的崇拜抽象的特征,表现在宗教上就是基督教对抽象人的崇拜。马克思还对比了古代世界由于人类的生产力低下,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于狭隘的境界,因此他们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也是狭隘的。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会反映在一定的精神生产方式中。马克思相信,人类要获得对世界的清楚无误的看法,必须当人类互相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清楚明白的时候,才有可能:
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1]97
马克思这里的论述是在西方的文化历史语境里展开的,因而他谈到宗教的地方未必符合西方之外的世界例如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形。但是马克思这里所论述的日常生活与宗教反映的关系,包含着一个深刻的洞见,揭示了宗教以及一般意识形态的由来:由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没有到达明白而合理的关系,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就会随之产生;当这些关系清楚明白,宗教或者意识形态就消失了。社会物质生产例如商品生产所带有的神秘性,如果人类能够把一切生产都纳入有意识的计划之中,也就不再存在了。人类相互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都处于明白而合理的关系之中,一切都变得清晰明白,没有任何看不到摸不着的力量从中阻梗,自然宗教的神秘,意识形态的欺骗,都一一消失。马克思在此描述了一个高度明亮的世界,清晰的世界,一目了然的世界。但是,我们仍然忍不住想问一下,如此清晰明白的世界,没有一丝微云,没有一点荫翳,是不是过于清晰明白了?它果真能够到达吗?对此,人类又有何真正实际可行的方法?
三、社会生产关系的“澄明之境”
如果我们拓展一下马克思提出的这一宏伟论题的哲学含义,这种清晰明白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正也是后来的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澄明之境”的基本思想吗?[5]海德格尔希望通过去蔽的方式达到此在的澄明之境,恢复此在原本具有的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明白而合理的关系。他用个体的存在形态也就是此在来替换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的社会存在,同时这种海德格尔始终也没有找到通往澄明之境的确切方法,最终还是逃不脱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玄思,或者更多地借助于语言来开展的美学行为。[6]*海德格尔所鼓吹的“澄明之境”赖以抵达的途径是“去蔽”,在早期的《存在与时间》里他尽管提出了“去蔽”的概念,但并没有找到“去蔽”的方法,只有到了晚期,他才在语言中找到“去蔽”的途径。通过语言来去蔽,最终到达澄明之境,其实在海德格尔这里并没有特别高明的地方。倒是他的后学伽达默尔揭示了语言的对话结构,并在此结构上建立起相互理解的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澄明之境”。但是这种澄明之境的开启,虽然与马克思可以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对话,但是并没有越出马克思的问题域,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清楚明白的关系仍然还是没建立。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与海德格尔的始终拘囿于个体主义的形上玄思的存在主义不同,马克思所畅想的这种澄明之境,是作为人类整体的社会存在的物质实践行为,而且需要通过长期而艰苦的实践活动,才有可能达到。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式的存在主义比起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来说,气象要磅礴得多,视野要宽广得多,同时也要实在得多。当然,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明白而合理的关系,在马克思这里似乎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至少在马克思看来都是一个物质实践的问题,在终极的程度上可以通过人类总体的物质实践予以解决,尽管这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自然过程。马克思把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都看作“自然”过程,实际上也值得稍作讨论。看起来似乎马克思仍然是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说这番话的,就像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把历史看作“人的真正的自然史”一样。[7]但是,联系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历史观,这里把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自然产物”,并不违背马克思的总体的历史观,即两分法的历史观:史前史和真正的历史。马克思这里强调的这个“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始终属于史前史阶段,而“将来的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属于真正的历史阶段。
显然,这是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生产方式时纵笔所至,由商品的神秘性拓展至人类社会生产的神秘性,顺便谈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长期以来的这种神秘关系时表达的观点,有些地方的确存在着辨认不细的缺点。毫无疑问,在我们现在的知识基础上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绝对不能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无疑要复杂得多,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今天的科学的视域中,已经高度简化为一个物质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主要是一种物质交换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所界定的本来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也就是说人从自然中索取生产生活资料。当然,除了这层关系,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还包含着自然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自然的改造,也就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课题,自然的人化。因此,在马克思的视域中,人与自然之间总体上存在着两种关系,一种是物质的生存关系,一种是精神的审美关系。当然,在古代,还包括把自然神话化并加以敬畏的宗教关系,以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关系。
显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人与自然的关系要远为复杂。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集中了物质、生理、心理、伦理、个性、宗教、政治、审美等方面的因素,每一个个体都是一个多方面差异的个体,在这种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涉及阶级、国家、民族、集团、阶层、宗教派别和政治团体等因素的千差万别、难以化约的矛盾与差异,就以更小的因素如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等来说,人与人之间也可以构成足够复杂因而很难明白而合理的关系。固然,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地化约为纯粹经济物质关系,以占有物质生产生活资料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自然就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区分得一目了然,清晰明白,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区分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正如每一个商品生产者、交换者无法洞悉商品背后的抽象劳动一样,每一个个体或者作为社会团体的一员,也无法看透由千头万绪或者用马克思本人的术语“社会关系总和”所织成的无比复杂的关系网络,因而每一个个体都无法把握人与人之间的明白而合理的关系。作为有限的个体,沉没在海洋般浩瀚杳渺的关系之中,怎么努力,不管是用物质实践的方式,还是用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或者神学的启示方式,基本上都无法取得一种上帝般的全景视角,对自己与他人以及总体人类的关系清晰把握。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并不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物质实践的历史过程,而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的乌托邦式的愿景,一个人类上升到上帝位置的梦想。其实,马克思在这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把握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不管是作为认识主体还是行动主体,都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来施行,而必须是由单独的个体来施行,尽管这些单独的个体是人类整体中的一员。正是这种个体性,决定了这个认识主体或实践主体的视域的狭隘性,他或她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一种结合了宏观鸟瞰和微观辨析的眼光。也许,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框架内来理解哈贝马斯批评马克思“没有发展人的科学的观念”[8]。
正是在人的有限性这点上,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形成了一个有益的对话。海德格尔从马克思的人类整体退回去,坚持从个体出发,并不标志着存在主义的狭隘偏颇,相反,倒显示了存在主义的审慎与明智。海德格尔对人的存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就是人的存在的有限性。每一个此在都存在于具体的时空结构之中,作为一种被抛的存在,他被各种烦神恼人的事情所纠缠,也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等织成的复杂的网络中,日夜沉沦。因此,此在首先是作为在世(being-in-the-world)的存在者,而不是作为理性的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而存在的。[9]认真梳理起来,海德格尔这个观点也没有特别的新意,只不过在与黑格尔、马克思这种充满理性主义雄心的背景的对比下,显得异常契合20世纪人类的普遍沮丧而谨慎的心情。这种审慎和谦虚,或者说对人类的有限性的自知之明,远在康德那里就有十分坚定的觉悟。在康德的哲学里,人类只能依靠时间和空间这两种先验形式把握经验现象,而现象世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的总体是无限的,因而不可能凭借直觉的方式把握,只能用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总体,因此康德强调“世界永远也不能整个地被给予”[3]426。换句更通俗的话说,我们不可能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不可能对由千千万万单独个体组成的人类全体的千丝万缕般的复杂关系了然于目,了然于心。有限的个体顶多只能有限地把握无限的现象世界。个人不可能获得上帝的全景视野,由无数个体构成的人类总体同样也不能,因为实际上没有人类总体的视野,只有一个个单独的个体的视野。
这样看来,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自然之间,即使在科学高度发达,物质实践力量巨大的现代社会,也很难达到清晰明白的澄明之境,因此,我倒宁愿承认,与其把这个问题单纯地当作一个物质的技术的问题,不如让它停留在美学的、形而上学的、伦理学的层面上,总而言之,让它长久地作为一个文化问题而存在,可能会更有意义些。
四、结语
马克思对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的发现和物神形象的描绘,在《资本论》中具有深远的意义,它奠定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旨趣,这就是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融合了哲学和美学的视野。它在劳动的两重性的基础上开展资本主义世界最常见的现象——商品这一既感性又超感性的社会产品的分析。从最平常的商品形象入手,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这种拜物教性质一直延伸至商品进一步发展的形态——货币和资本,并且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最终迷惑了人类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认识和秘密破解,马克思商品分析奠定了《资本论》后来的深入批判,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交织起来,愈闹愈烈,随着资本主义从早期到盛期,到今天的晚期阶段,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渗透到现代人类生产和生活之中,因而也引起了当代后马克思主义者们持续和深入的批判。
对商品拜物教的揭示,马克思显示了精湛的辩证法的素养,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也是马克思独特的意识形态分析的精彩实践。马克思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进一步提炼出意识形态批判的视野,在马克思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社会劳动的抽象性,任何客观的社会生产生活形式都会自动地生成意识形态的迷雾,而生活于这个历史阶段的理论家局限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一般难以跳出自己时代的生产方式进行反思,因而不可能获得超越意识形态的科学视域,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理论家为了自己的现实利益,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自愿地营造神秘化和永恒化的理论形态,进一步加固意识形态的壁垒。马克思指出了突破这种壁垒的历史化方法,同时也在此基础上阐明通往未来社会关系澄明之境的方案,当然,这一问题域必将长期甚至永远处于开放的积极状态,召唤着人类的理论探索,特别是具体的社会实践。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黑格尔.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2.
[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Lukacs.The Ontology of Social Being.Volume 3 Labour[M].London:Merlin Press,1980.
[5] 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37.
[6]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82.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11.
[8]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56.
[9]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19.
责任编辑:刘海宁
A811
A
1007-8444(2017)04-0384-08
2016-12-28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的诗性话语研究”(13YJA751018)。
黄世权,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