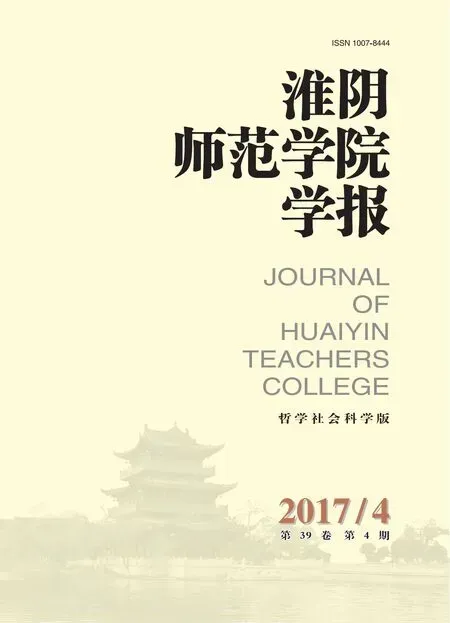家族传承、江南文脉与民国情怀:葛亮文学世界的文化基因
高 山, 施 军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家族传承、江南文脉与民国情怀:葛亮文学世界的文化基因
高 山, 施 军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葛亮是目前华语文学最具特色和潜力的作家之一。葛亮的小说和散文创作,蕴藉着南京的笃实与香港的浮华,融个人生活的质地和历史的脉络为一体,叙事干净绵密,语言雅白韵古,洞悉历史与人性的明暗曲折。葛亮文学创作的成功,最恰当地诠释了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繁荣发展所召唤的文脉传承创新与文化自信,清晰地显现出中国文学文化传统的基因特征,正因为如此,他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乃至他的整个文学世界,在当下的文学文化语境中尤其值得认真解读和研究。
葛亮的文学世界;家族传承;江南文脉;民国情怀;文化基因
2008年秋,《朱雀》杀青之际,葛亮写下这样一段话:“这部小说,写了五年。如今完成,人已届而立。这五年间,于我之前单纯的人生,有了变故,也经历了苦痛。我并不确定我是否真的会因此而成长。而这小说,却是一个忠诚的时间见证。”[1]其中的况味可以想见。次年,《朱雀》获“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文十大小说”奖。
2013年葛亮凭借香港都市题材短篇小说集《浣熊》获得“亚洲周刊2012年全球华文十大小说”奖,却反响不大,葛亮略显沉寂。
2015年10月,葛亮通过台湾经联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北鸢》,2016年1月即凭此小说第三次获得“亚洲周刊全球华文十大小说”奖。201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简体本《北鸢》。2016年9月22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阅读季在北京西华书房举办长篇小说《北鸢》新书首发式,葛亮与止庵、史航、蒋方舟等就“民国书写”的话题展开讨论。虽然绝大多数人还未读过,接踵而至的却是出版社、评论界和各种媒体的好评如潮。2016年9月25日,葛亮与天津文坛名宿冯骥才、王振良对谈天津民国历史与文化,腾讯视频更以“与葛亮行民国怀旧之旅”为题全程直播葛亮的天津之行[2]。这当然不仅仅是出版发行和媒体炒作的策略,还是作家作品的魅力、民国历史风物的韵味和当下社会文化语境等因素共同酝酿而成的一席文学盛宴。
回顾葛亮十多年的文学创作道路,不难发现,由小说、散文、影视评论和文学批评等诸多文体构成的葛亮的文学世界中,隐现着一种深厚而独特的中国文学文化的基因链条,简而言之,就是显赫的家族传承、绵延的江南文脉、香港流散的海派余韵和牵肠挂肚的民国情怀。
这是葛亮文学道路之所以成功的一种几乎无法复制的文学密码与文化基因;葛亮选择的文学道路,也是当下中国文学与文化繁荣发展所呼唤的那种拥有“文化自信与文脉传承”特质的创新与成功之路。唯其如此,葛亮的文学世界才值得当下的批评界、学术界认真解读研究。
一、家族与家学传承
从各种媒体搜检有关葛亮的访谈、对话以及葛亮小说的评论文章,他显赫的家世背景总是无法回避的话题。然而,至今没有人比较细致地梳理葛亮家族那些赫赫人名背后蔓延纠葛的血脉关系与历史掌故,这未尝不是一件憾事。
葛亮1978年出生于南京,祖籍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南京大学本科,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现当代中国作家研究、现代中文小说创作、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影视艺术、香港文学对话、中国文学与大众文化等课程[3]。
1902年3月,《陈独秀年谱》记载,陈独秀从日本回安徽,“与何春台、潘赞化、葛温仲、张伯寅、柏文澜等青年于安庆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识,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4]。文中的“葛温仲”正是葛亮的曾祖父,他是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四世孙邓绳侯的女婿,是陈独秀二姐的姻亲,是清华大学名教授、哲学家兼美术史家邓以蛰的姐夫,是民初安徽省立中学全皖中学的首任校长。
葛亮的祖父葛康俞是葛温仲的二儿子,是陈独秀二姐的女婿,是邓以蛰的外甥,是邓以蛰之子、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表哥。葛康俞是中国现代书画家、美术史家,早年与李可染、艾青同学于杭州国立艺专,后辗转任安徽大学、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20世纪40年代他著有美术史巨著《据几曾看》,惜乎时代历史的波折,直到2003年才在老友王世襄的奔波之下重见天日。王世襄先生在写给台北故宫博物院临生副院长的推荐书信里这样评价:“先生工书画,行楷醇厚有古风,山水萧散澹远,可与宾虹先生抗衡,文华尤典雅隽永,耐人寻味。惜英年早逝,使人感伤。遗著《据几曾看》一种,著录历代书画名迹一百九十六件,计一百九十四页。卷末有宗白华、启元白跋,皆推崇备至。”[5]
葛康俞和陈独秀的交往需要单独叙述。陈独秀是葛康俞妻子的舅舅,自然也就成了他的表舅;两人年龄相差32岁,且辈分不同,然而共同的书画爱好却使得他们走动频繁、关系格外亲近。手头和见过的资料显示,他们之间最少有三次比较长时间的相处。
第一次应该是葛康俞少年时期,地点在北京,虽然由于资料的不足,我们无法了解更多的信息,但是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陈独秀在中国传统的书画领域给少年葛康俞以极大的影响,证据是葛亮在他的新作长篇小说《北鸢》的自序《时间煮海》里如是说,“其最为重要的著作于一九四零年代撰成,始自少年时舅父陈独秀的濡染,‘予自北平舅氏归,乃知书画有益,可以乐我生也’”[6],而日后书画也真的成了葛康俞安身立命之所。
两个人的第二次长时间相处的时间地点、甚至交往的一些细节都比较清晰,这是因为后人发现的陈独秀的一件书法作品,竟然详细地记录了他们这次交往的情形。“此李君大钊兄早年偶尔游戏所书,当时予喜其秀丽娟洁携归以壮行笥,盖民国纪元前于神户事也。忽忽垂十余年,事隔日久已淡忘之矣。今康俞仁弟于书帙中捡得,爱好之情见乎词色,与予曩昔有相类者。以其同好乃举赠之,翌日复出纸索书因识颠末于次。时民国十五年秋九月独秀记于沪滨之越东草堂西楼。”而且较早披露上述引文的作者胡寄樵,还细心地为书法条幅中提到的“康俞仁弟”专门做了一条注释,文曰:“康俞,即葛康俞,与陈独秀有师门之谊,画家,安徽大学教授,葛康俞之妻即陈独秀二姐之小女儿。”[7]这是1926年的9月,葛康俞时年15岁。
他们的第三次交往是在抗战爆发之后。“据葛康俞弟弟葛康素《谈陈仲甫先生书法》记述,1939年秋,陈独秀居四川江津鹤山坪期间,葛氏兄弟因避战乱也在四川江津,两家常有往来。陈独秀知其弟兄俩‘终日习书,殆废寝食’,曾亲书‘论书三则’指导……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几年,葛氏兄弟曾多次拜望舅舅,一次谈得兴起,陈独秀还展纸挥毫,书写一幅自己诗作赠葛康俞:‘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改。’不久,1942年5月27日晚9时许,陈独秀病逝于江津鹤山坪,6月1日安葬,墓地在江津县城西门外鼎山之麓。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7个大字,亦隶亦篆,古味盎然,就出自葛康俞之手,并由他亲自錾刻于墓碑之上。”[8]
于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在中国近现代政党史上曾经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在中国近现代新文学新文化史上曾经开天辟地的人物,因为家族的血脉瓜瓞,家学的谱系流变,就这样生生内化为葛亮文学世界的骨血基因。
葛亮的显赫家族中自然还有一些名字值得提一提。比如,他外公的姨夫褚玉璞,是民国初年赫赫有名的军阀,曾经担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是葛亮的新作《北鸢》中没落军阀石玉璞的原型,鼎盛时与张学良、张宗昌并称“奉鲁直三英”;再比如,因为第二任妻子方瑞是邓石如和方苞的后人而有亲缘关系的姑祖父曹禺。前者已经成为葛亮小说中的人物而流传不朽,而至于后者,葛亮曾以其最具戏剧性的小说《竹夫人》向《雷雨》致敬,不过想来即便有读者看到葛亮在小说结尾处写下的“写于曹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字句,也未必会想到其中的渊源和滋味。
除了这些显赫的家族成员外,还有许多同样显赫的名字出没在葛亮家族的历史记忆里,李可染、艾青、宗白华、启功、王世襄,等等。这些人虽然大多数并未与葛亮有着直接接触,然而通过祖辈、父辈的血脉传承和人文熏染,他必定领会了身处历史时空或宏阔或逼仄的褶皱里,这些家族的前辈亲友们从容不迫、坦荡磊落的人性光芒。这些东西才是那些赫赫人名背后或之上,对于葛亮和我们所有人最珍贵、最无可比拟的精神财富,这些东西才是葛亮的文学世界得以熠熠生辉的原因,这些东西才是葛亮文学创作自信心的源泉。
二、江南文脉与海派余韵
2013年岁末,笔者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葛亮的两篇散文,即长篇小说《朱雀》的“后记”《我们的城池》和中短篇小说集《戏年》的“代跋”《书想戏梦话江南》,已经揭示了葛亮对于江南文脉的认同和皈依。文章重点复述了《书想戏梦话江南》中葛亮对江南文脉文学与文化历史谱系的梳理:“从吴承恩的《西游记》到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从沈复的《浮生六记》到袁枚的‘随园’,从周瘦鹃的《紫罗兰》到刘半农的‘新文学革命’,从朱自清到钱钟书、杨绛夫妇,最后则是与葛亮有着相同流散足迹的叶灵凤。这篇文章里,葛亮不仅梳理了江南文脉优美丰厚的历史谱系,而且匠心独运地拈出‘旁逸斜出’‘奇与通透’等无关庙堂、和时代格格不入的精神气质作为叙述江南文脉历史谱系的线索。文中葛亮对江南文脉群英的倾慕溢于言表,对江南文坛的人文历史掌故如数家珍,处处显示出其自招为江南文脉私淑的心甘情愿。”[9]
王德威在内地简体本《朱雀》的序言里,则以南京的书写传统为葛亮补足了江南文脉的地理风貌,从中世纪左思的《吴都赋》、庾信的《哀江南赋》,到明清以来的《桃花扇》《儒林外史》《红楼梦》;还有民国时期朱自清、俞平伯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1932年鲁迅的“六代绮罗成归梦,石头城上月如钩”,甚至毛泽东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也提及了当代作家叶兆言的《夜泊秦淮》、朱文的《我爱美元》和毕飞宇的《推拿》[10]。
江南文脉对葛亮的滋养是多层面的、综合性的,既有文学观念与审美格调的塑形,也有人性善恶和历史进退的体认。比如,因为发现“平凡本身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所以发现“再浓厚的小说说到最后,感动我们的往往是极其细微的东西。一句话,一个远景,甚至只是一张脸”[11],继而发现西方人对《浮生六记》喜欢得无以复加,原因是这里面寄寓着“一种美好务实几乎可以说与现代合为一辙的生活观,恰是长期被规条约束的中国人所不敢也不愿触碰的。所谓浮生,说到底,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观念,不是建基于庙堂,而是从人自身出发”[12],最终发现也许“主义或时代,大约都成了‘人’背后茫茫然的帘幕。性与死亡,虽则亦时常出人意表,却每每切肤可触”[13]。
由此可见,葛亮对江南文脉“旁逸斜出”“奇与通透”的精神气质、审美品位和人文谱系的认读领会是深入细致的,是融会贯通的,绝非一时对话访谈的谈资,也非一般写作意义上的征引,而是浸入骨髓、溶于血脉的。因此,到目前为止,他创作的两部长篇小说中,《朱雀》是把抗战、内战、“文革”、大地震、伟人去世、改革开放等宏大的历史虚化为背景,把苏格兰、日本、美国、俄国、南洋等异域时空交织成帷幕,而舞台中央和聚光灯下,那些朱雀一般喷射着火焰的叶氏女子们以及她们的情事,毫发毕现;而《北鸢》却正像葛亮在自序中借祖父谈观画论品时所言,“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迄,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
于是,江南文脉经由葛亮,具体落成为他为《北鸢》命名时,曹霑散佚残本《废艺斋集稿》中一册《南鹞北鸢考工志》重见天日时焕发出的“久藏的民间真精神”。这种文学文化资源的接受与传承,是葛亮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与成功之源。
葛亮移居香港后,香港文化骨子里流散的海派风韵,也成为他文学世界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文化资源。他的一系列作品清晰地揭示了这一过程。2010年第1期《天涯》上,葛亮发表了他最重要的散文作品之一《拾岁纪》,记录了他千禧年至己丑年(2009年)近十年间的生活,“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既非港岛的速度与喧嚣,也非港大的优雅与清净,而是葛亮从南京的秦淮河、扬子江到香港维港、外海这种水域的越界,也许港岛的土地空间确实逼仄了些,但视野却也因接近海洋而开阔”[9]54。《浮华暂借——张爱玲与香港的“半生缘”》《镜像魅影——香港制造的“老上海”》,则从海派文学经典作家和香港电影的视角,揭开了互为镜像的上海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之间错位、叠加与并置等复杂吊诡的关系。
难怪眼光敏锐的批评者一眼看出,出身南京、定居香港、却首先在台湾文坛崭露头角的葛亮与20世纪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等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与新旧海派作家张爱玲和王安忆之间的暗通款曲[10]7-8。
然而在我看来,有着深刻内在联系的江南文脉与海派余韵,显赫家世的影响,以及他所处的弹性创作空间,既可能成全葛亮,也可能限制葛亮。其中存在的危机,在《亚洲周刊》为他获得2012年度“全球华文十大小说”奖的短篇小说集《浣熊》颁布的获奖词中隐隐而现,“这是葛亮‘最具香港特色’的作品。每一颗饱受煎熬的心灵,都是一头暴躁咆哮的猛虎。而聪明成熟的体制懂得怎样麻醉猛虎,研磨它的剑齿、修剪它的利爪,甚至摘除它的荷尔蒙腺体。时代的‘进步’似乎就汇集于这种手术的冷静与不动声色。然而,再娴熟的手术也会发生意外。这部小说致力展现的即是一例”[14]。虽然这段孤立的文字无法完整理解,但是其中的文字表述与葛亮小说的美学形式之间的距离还是清晰可辨的。
因为葛亮的作品是有倾向性的,他的作品“对于一般政治和道德立场的超越性在于,它昭示了一个人对艺术的忠诚,对任何生命律动的尊崇和敬畏,对观察、描写以及小说美学的忘我投入”[15]。难能可贵的是,葛亮在最新的长篇小说《北鸢》中,已经开始显现出处理这种事物的机智,正如他曾清醒地说到“历史于南京像是一道符咒”,因此他也一定清楚,对于他的文学创作之路而言,历史也正如此。当然,更远的将来还需拭目以待。
三、金陵风物与民国情怀
2012年,葛亮在小说集《戏年》最后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长篇散文《书想戏梦话江南》,文末他详细追述了与自己有着相同流散足迹的前辈海派文人叶灵凤。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葛亮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叶灵凤寓居港岛37年间所写的12部抒写故土南京山川风物的散文随笔集,几乎篇篇都以南京的历史地标、文化掌故、地方名物为题。
这其中也折射出葛亮对自己的出生地和家族最终的居住地南京的记挂。而他自己的小说散文作品里更是充斥着有关南京的符码,这不仅仅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更是因为他生命的记忆已经与这些东西融为一体。2016年8月,葛亮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小山河》。其中有几篇径直以人的肉身记忆为题,或许是作者已经有意无意中发觉,记忆原本就是肉身性的?这几篇文章分别是《腔调》《气味》《声音》和《舌尖》,南京的方言、锅贴饺梅花糕、朝天宫的喧闹……凡此种种南京的记忆已经与书写者的肉身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南京的历史就这样经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活生生地活出来、回想出来。而南京的历史又是和民国的历史水乳交融的。
相对于普通人而言,葛亮因为家族、家学的渊源与民国历史的关系更具温度、更紧密、也更复杂。因此,他才会说,“民国是个好时代,好在作文与做人的尺度。及至当世,仍可以为之鉴,躬身自省,反求诸己。世故人情,皆有温度。内有渊源,举重若轻”[5]2。
葛亮对民国的温情在他的小说散文中几乎随处可见。短篇小说《泥人尹》讲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混迹于南京朝天宫的无锡籍泥塑艺人尹传礼的故事。尹师傅的手艺自然精妙无比,因了这手艺而来的生存的挣扎与起伏也自然精彩,然而尹传礼身上最具内蕴的是手艺背后的人生阅历。尹氏家族在无锡原本有“尹半城”之称。尹传礼的父亲年轻时因为政治的理想,携大半家产投奔孙传芳,可惜北伐时当了炮灰,郁郁而终之际,把尹传礼托孤于无锡泥塑艺人世家,由此尹传礼走上了从大家公子哥蜕变为泥塑艺人的人生轨迹。民国风云际会与个人身世穷达就这样恰如其分地勾连在一起,而只有在更大的背景下,个人的命运才会显得或庄严或滑稽或无可奈何。
当然,致敬一个时代,就文学而言,非长篇小说莫属。因为历史时空巨大的躯体需要一个更巨大的时空来承载,而长篇小说的语言形式更具这样的弹性。在葛亮的文学创作里,情形也大致相同。他对民国时代的衷情,主要是通过两部长篇小说《朱雀》和《北鸢》实现的。
《朱雀》的故事,按照线性时间的顺序,开始于1923年叶氏南京“齐仁堂”药铺的重新开张,结束于千禧年前一天,叶氏第三代女主人公的画廊在夫子庙重新开张的那一天。其间以过去与现实交错的小说叙事形式,以社会时代的动荡和人性命运的起伏为背景,展开了叶氏三代女性颠簸曲折的人生画卷,而小说整体骨子里的源头,仍是民国风云在个人运命、金陵城池上镌刻下的累累伤痕,以及这些伤痕的时空延绵、形变与贯穿。
新作《北鸢》艺术上回归中国传统小说叙事风格。结构上,以卢文笙和冯仁桢的成长为线索,叙述卢、冯两个家族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缠绕的命运跌宕;语言上,既汲取《世说新语》《红楼梦》《阅微草堂笔记》《浮生六记》和《海上花列传》等诸多古典文学语言滋养,又呈现作者对文学语言的独特感悟,构建出一种个性化的、雅白韵古的语言风格;叙事上,以民国日常生活为叙述焦点,工笔细描民国时期上层士绅家族的器物风俗、人文修养、人情往来等日常生活细节,置个体人性善恶、命运否泰和情爱纠葛于家族兴衰、时局动荡的舞台中心。正如作者自序中所述:“本文无意钩沉史海,但躬身反照……中国近代风云迭转。人的起落,却是朝夕间事。这其中,有许多枝蔓,藏在岁月的肌理中,裂痕一般。阳光下似乎触目惊心,但在晦暗之处,便了无痕迹。这是有关历史的藏匿。”[6]3
回顾葛亮十多年的文学创作道路,我们可以发现,葛亮文学世界的文化基因与密码主要是由家族传承、江南文脉和民国情怀这三种元素构成。当然,我们并不能忽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素养和外国文学资源的影响,只是这些并非葛亮所独有,而上述三种元素的水乳交融,才是葛亮文学创作道路之所以成功且几乎无法复制的原因。这些元素同时也昭示了葛亮文学世界所包含的文化自信与文脉传承创新的特质,因应了中国文学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需求和呼唤。至于葛亮文学创作审美特质的研究,与本文主旨关系并不密切,则留待将来。
[1] 葛亮.后记:我们的城池[M]//葛亮.朱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450.
[2] 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16-09-24公告.
[3]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网站[EB/OL].(2011)[2016-09-24].http://chi.hkbu.edu.hk/teachers/gel.html
[4]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0-21.
[5] 葛亮.自序:一封信[M]//葛亮.小山河.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6] 葛亮.时间煮海[M]//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7] 胡寄樵.陈独秀认识李大钊时间考[J].近代史研究,1990(5):220-222.
[8] 钱念孙.一位不该忘却的美术家[N].中国艺术报,2013-03-22(8).
[9] 高山.越界与间离:葛亮的意义[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3(4):52-56.
[10] 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M]//葛亮.朱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11] 葛亮.说小说[M]//葛亮.德律风.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305-309.
[12] 葛亮.书想戏梦话江南[M]//葛亮.戏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96.
[13] 葛亮.经年[M]//葛亮.小山河.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155.
[14] 葛亮.浣熊[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封底.
[15] 韩少功.葛亮的感觉[M]//葛亮.七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Ⅱ.
责任编辑:刘海宁
I247
A
1007-8444(2017)04-0365-05
2017-02-24
2016年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新世纪江苏小说研究”(16ZWA003)。
高山,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关于葛亮研究的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