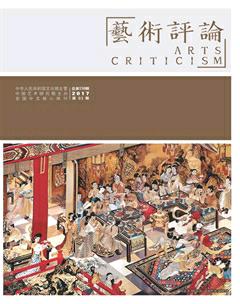追溯与断裂
蔡郁婉
自1999年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始, 80后写作者们渐次进入公众视野,并多以书写一代人的个体经验和青春体验而为大众所熟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书写青春”这一 80后作者曾经的优长逐渐成为他们的局限,面临着写作难以介入现实的质疑。面对这一局面,一部分 80后作者也开始尝试着突破和转型。張悦然的新作《茧》即是其中一例。与此前的创作相比,《茧》显示了接续历史的明确意图。在李佳栖与程恭对程恭祖父遇害真相的追问中,小说试图突破 80后的代际经验,重返父辈的历史。
张悦然早期的写作,或书写个人经验,如《这些那些》《赤道划破城市的脸》;或以代际经验为基础构筑幻想,如《樱桃之远》《十爱》等。对青春体验的叙述和表达是其写作的重要部分,但也暴露了写作一直悬空于现实与历史的短处。作为写作者,张悦然较早地认识到自己写作的局限。在其出版于 2006年的长篇小说《誓鸟》中,张悦然就已尝试着摆脱熟稔的题材。《誓鸟》也因之被视为其转型之作。但《誓鸟》的转型却很难说是成功的。小说浓重的传奇色彩削弱了其对时空典型性的表现,而爱与宽囿主题与其较早的作品如《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一脉相承。在《誓鸟》之后,张悦然在一系列短篇如《好事近》《动物形状的烟火》等之中继续尝试着对现实与历史进行书写。与这些短篇相比,《茧》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叙述更为合理,对历史与现实显得更加细腻而深入,并显示了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茧》中渴望抵达历史现实的正是张悦然本人。如果说,张悦然曾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已不能让青春连着陆地” [1];那么,《茧》即是她对“接地”的一次尝试。
事实上,近年来 80后写作的发展正在不断改变着其最初“青春文学”的刻板印象,《茧》所显示的转向并不是孤例。它与周嘉宁的《密林中》、蒋峰的《白色流淌一片》一道,显示了 80后一代对零余个体对孤独体验的思考和对精神病态的追问;也与颜歌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张怡微的《因为梦见你离开》一道,显示了他们对现实敏锐的观照。作为年少成名的80后写作者,当时光以不可抗拒之力裹挟着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他们的写作也在不断突破早期写作囿于青春体验的局限,以更为冷静的笔锋去呈现与剖析现实,叙事上转向绵密厚重,文字也一改华丽纤弱。除了这些少年成名的作家的创作之外,还有马金莲对西部农村的书写,甫跃辉对城镇化进程中个体艰难生存的关注,文珍对大都市背景之下精神重压与空虚的表现等,这些都在不断地扩充着 “80后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正如“茧”这一标题所显示的,程恭与李佳栖对真相的寻找与对历史的追溯正是一次破“茧”而出,显示了一种沟通个人经验与历史的意图。本文将通过李佳栖这一人物,探讨《茧》如何呈现 80后一代人对现实、对历史的思考。
一
《茧》对历史的回溯贯穿着一个从“弑父”到“寻父”过程。在小说中,李佳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祖父祖母家中度过的。父亲李牧原长期居于异地,又因车祸而早逝。可以说,在李佳栖的生命中扮演着父亲这一角色的是祖父李翼生。这是一个严厉的、强制的“父亲”,也是李佳栖一直试图反抗和解构的对象。另一方面,李翼生是谋杀程恭祖父的最大嫌疑者。这造成了两家人难以化解的矛盾,也是李牧原悲剧人生与李佳栖叛逆青春的重要原因。因此,直到祖父临终,李佳栖也未与祖父达成有效的和解。但是,正如张悦然所指出的,“我们到底在这个世界中处在什么位置。要建立这个坐标,就必须了解父辈和过往的历史。了解他们,才能更了解我们自己 ”[2];那么此处,对祖父及家庭的否认便使李佳栖面临着无法定位自我的局面,导致了李佳栖青春期里的自我迷失。这正是李佳栖“寻父”的重要动因之一。而父亲李牧原在其成长过程中的缺席为“寻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前提。
父亲李牧原是对李佳栖影响极大的一个人物。《茧》中不断地描写童年的李佳栖与父亲相处时温暖甜蜜的回忆。而这并不仅仅是出于一个失怙少女对早逝父亲的纪念。借助于对父亲的寻找,李佳栖尝试着将自己也楔入历史之中。在李佳栖找到的有关父亲的线索中,我们也得以勾连出一段中国 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的历史: 1990年父亲辞去教职离开济南,是因为支持前一年夏天去北京的学生。而前往北京之后,父亲加入了 90年代初中国人向俄罗斯销售轻工产品的热潮中。父亲的每一段经历之后,都存在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与其说是确认父亲在历史之中的栖身之所,毋宁说是李佳栖在为自己寻找一处立足之地。
同时,李佳栖的几段情感遭遇也都与“寻父”紧密联系。在许亚琛与殷正的身上都显示了父亲的身影。许亚琛曾是父亲的学生,而殷正是父亲的旧同事。前者使李佳栖重温了父亲在世时的快乐童年,后者的诗人身份则投射了一个诗意的父亲。通过他们,李佳栖“复活”了一个理想的父亲。在与许亚琛及殷正的交流中,李佳栖不断地接近理想之父,从而亲近了那段她无法介入的历史之中。另一方面,如果说身体与情感提供的是极为个人性的体验,那么以身体作为进入历史的渠道,恰恰显示了小说打通个人经验与历史书写的意图。而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那里,身体更是女性认识自我、确立主体性的重要途径。 “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 [3],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 [4]。但李佳栖通过身体,反复确认的是自己 “父亲的女儿 ”的身份。而李佳栖借助这一身份所跻身的,也是一段父亲的历史。
然而,在李佳栖“寻父”的过程中,一个真实的李牧原产生了。殷正对李佳栖忏悔式的叙述中,作为诗人,他在成为诗社社长后却显示了强烈的权力欲,希望得到所有人的拥护;作为学者,他因为著作未获得重视而选择了仕途,却由于敏感脆弱而难以坚持目标。显然,这个李牧原偏离了李佳栖的长久以来的建构。她所“寻”到的不是父亲的真正经历,而是自己一厢情愿描绘的“理想之父”。同时,迫使李牧原最终离职的匿名信举报恰恰是由殷正寄出的。如果说,殷正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李牧原空缺的父亲位置,那么此处理想之父的倒塌则是双重的。李佳栖试图借助这一形象去沟通、接续历史的可能性也随之失效。如果说,李佳栖寻找父亲的线索,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 [5],而她追寻历史的过程却是隔阂历史的、一厢情愿的建构,并最终再度显示了自己被从历史之中抽离出来、无所依凭的处境。
二
而与李佳栖“寻父”相对应的是她的“弑母”。《茧》描写了李佳栖与其母之间极为不和谐的母女关系。
在小说中,母亲来自农村,因为婚姻而进入城市,她身上与城市生活不相容的部分都被定义为失礼和庸俗。事实上,母亲是不断被城市话语所贬抑的他者。甚至在女兒的凝视中,母亲也是衰老而丑陋的:母亲“有天跑去文了眉毛和眼线晚上卸去一脸的颜色,面庞晕着乏暗的黄气,像一面污糟的铜镜,只有那几道用钢针刺上去的线条粗悍可见,看起来很惊悚” [6]。李佳栖以日常生活的庸俗琐屑代表母亲,并毫不掩饰她对母亲的生疏乃至鄙夷。然而,正是使母亲变得衰老、庸俗的家务,保障了父亲的理想主义与诗意形象。但是在旁人的小心翼翼与讳莫如深之中,母亲被进一步贬抑成一个无能的主妇,是父亲走向超越的障碍。而母亲所遭遇的贬抑实际是双重的——在婚姻之中,母亲所遭受的也是一种贬抑。她与父亲的婚姻并非真正地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祖父所实施的谋杀行为,使父亲与汪露寒之间的恋情被阻断。与母亲这一农村女孩的婚姻是父亲对抗祖父的手段之一。换而言之,母亲并未得到父亲真正的爱与尊重。她只是父亲用以挑战、反抗父权家长的工具。在父亲的抗议过程中,母亲作为一个人的情感、欲望,通通被牺牲了。可以说,城市对农村居高临下的鄙视中,在李家父子两代人的战争中,母亲最终成为一个被扼杀了的生命。
但是,李佳栖却并未从母亲的经历中指认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李佳栖对母亲的嘲讽,实际无视了造就母亲神经质和可悲处境的真正原因。也正是在这种嘲笑中,李佳栖在无意中参与了扼杀母亲的过程。母亲是她急于摆脱的影子。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母亲是被父亲抛弃的对象。李佳栖拒绝自己身上母亲的影子,即是拒绝成为父亲所厌恶的对象。这实际上仍是为了更进一步地亲近父亲、认同父亲,从而进入历史。然而这恰恰意味着另一条进入历史的道路被封闭了。
正如埃莱娜 ·西苏所言,“在妇女身上,总是多多少少有那母亲的影子,她让万事如意,她哺育儿女,她起来反对分离。这是一种无法被切断却能击败清规戒律的力量” [7]。然而在《茧》之中,李佳栖亲自“切断”了这种力量。这一“切断”是与母亲的割离,也是与母亲历史的断绝——这正如小说这一幕场景所显示的,当母亲喜悦地提到再婚对象林叔叔家里有一座她梦寐以求的小院子时,李佳栖则冷淡地表示羡慕母亲的“幸福可以一件件地列在清单上 ”[8],再次显示了对母亲之庸俗的鄙薄。这里,母亲对土地难以割舍的感情联系着她的来自农村的身份。而李佳栖冷漠地拒绝了母亲,实际也是拒绝作为自己生命来处之一的乡土。而那未尝不是进入历史的有效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女性与母亲的关系也并不止于两个女性之间的联系。以母女关系为基础,个体的女性能够沟通其他的女性;以母亲为纽带,个体的女性得以联系悠长的女性历史。女性之间情感、经验相通的同性联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女性借助于母女关系的建构,能够摆脱孤立无援的状态。这正是苏珊 ·格巴所指出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孩子、食物、衣服等——的艺术是妇女独特的创造。如果在父系文化背景下这被视为一种空白的话,那么在口头讲述故事传统中,在女性集体内它却是值得褒扬的” [9]。女性历史正是在代代女性的口口相传之中获得延续的。在这历史中,“她们和我成了一个人 ”[10]。因此,当李佳栖轻视、贬抑母亲的家务劳动,并更进一步否定母亲时,她实际上拒绝了代代相传的女性历史。可以说,《茧》借助李佳栖的视角,呈现的其实是父子对抗的男性历史。即使是李佳栖对父权家长的祖父李翼生的质疑,仍是基于她对父亲李牧原的认同。在此意义上,李佳栖对祖父的反抗实际是李翼生与李牧原这一父子之间对抗的一种延续。然而事实上,在这对父子关系的夹缝中,有矛盾两难的祖母,有被压抑被扼杀的母亲。《茧》中的女性群像,本可以为李佳栖性别意识的建构以及历史的溯源提供多样的参照和途径,以共通的性别经验进入女性的历史。但遗憾的是,小说或忽略或否定了这些女性形象,而封闭了李佳栖进入历史的这一可能。但作为“父亲的女儿 ”,李佳栖却始终难以在父亲的历史之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既拒绝母亲 /女性的历史,又难以进入父亲的历史,李佳栖在成长过程中的始终是漂泊不定、迷惘混沌的个体。
三
与其此前的小说相比,《茧》对其所书写的历史有了清晰、明确的界定。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个人经验的局限,使个人话语突入历史叙事。但正如李佳栖难以真正有效地将自己嵌入历史之中,《茧》对父辈历史的叙述也停留于浅层。
程恭的祖父是如何在“文革”中遇害,这是《茧》的中心事件。《茧》也是以程恭、李佳栖对真相的追寻为线索来组织全文的。但是,在程恭祖父遇害的真相逐渐被呈现出来的过程中,小说的叙述却并未有效地标识出“文革”这一独特的时代背景。“文革”背景的选择似乎只是为了使祖父的头颅之中被钉入铁钉,最终找不到凶手却只能不了了之这一情节进行得更为合理与顺利。事实上,叙述返回旧日时空之中时,置于小说中心的始终仍只是“事件”本身,而非历史。历史在《茧》之中,是被局限在程、李、汪三家人的遭际与恩怨纠葛之中的。而这些个体所遭遇的变故与悲欢也并未成为呈现时代的窗口。李牧原与汪露寒恋情是在汪露寒父亲被作为谋杀案的替罪羊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但小说却较少触及人物在这一处境之下心理的挣扎矛盾,而在更大程度上仅仅将其书写为一段少年恋情。小说对李牧原与汪露寒恋情的描述似曾相识,与张悦然早期的作品如《黑猫不睡》《葵花走失在 1890》中的叙述具有某种相似性。在张悦然对父辈的历史进行叙述时,或仍然套用了自己的青春经验。正如小说的这段描述所呈现的,当李牧原与汪露寒共处时,“她一边洗衣服一边听他念小说,听到优美的段落,她会让他再读一遍,慢一点。有时候故事很滑稽,他干脆表演起来,逗得她哈哈笑。阳光好的时候,她忍不住撬掉图钉,打开所有的窗帘,一边擦地抹窗台,一边哼起歌来” [11]。动荡混乱的时代则被金色的阳光隔绝于室外,而少
年的恋情被置于一个仿佛从历史之中断裂而出的、独立于时代的空间里。历史在此再度远离。
另一方面,《茧》一般以旁观者的视角来叙述父辈的往事。这种转述的叙述角度虽然提供了从总体上把握事件的可能性,但是它也导致了叙述无法真切地贴近人物。正如小说叙述了汪露寒在父親自杀之后受到的排挤与打击,但她精神的创痛却被以她与李牧原无法延续的恋情一笔带过。而李牧原意外之死所具有的悲剧力量,也被他与汪露寒之间看似俗套的三角情爱关系所冲淡。与《茧》对李佳栖、程恭等一代人的青春期及成长创痛的细腻揣摩与绵密书写相比,叙述者对父辈历史的叙述显得颇为粗疏,从而显示了其与历史之间始终存在着的隔阂。就《茧》对历史的重返而言,对外,小说未曾对大时代进行有效的观照和再现;对内,小说对父辈们在特定时代背景中的心灵史与情感交锋的把握也失之无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历史的隔阂正显示了《茧》的某种位置——在面对往事时,《茧》所拥有的始终只是一份旁观者的地位。它观看历史,却无法真正地进入历史。有趣的是,《茧》还引入了对讲述李翼生生命历程的纪录片片段。这些片段借助不同受访者的叙述来展示李翼生的一生。但这无助于使李翼生的形象血肉丰满起来,在纪录片冷静的观照下,这一形象仍显得扁平而空洞。如果说,程恭与李佳栖对往事不懈的追问显示了某种介入历史的企图,那么小说借助纪录片这一形式对历史所进行的再现反而确认了叙述者的旁观地位——永远无法获得一份历史的在场。而在小说的结尾处,宽囿终于伴随着李翼生的死亡而来临。李佳栖与程恭由此而获得解脱。然而,也正是李翼生的死亡再一次将他们指认为历史的旁观者——面对不得不背负的历史,他们始终无法参与其中。历史参与者纷纷退场带来的解脱,实际却显示了一种断裂。
尽管正如小说所言,李牧原与汪露寒的生命从此被这一谋杀连在一起,所有人的命运也因此而被牢牢钉死,然而在李佳栖们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历史却被呈现得简化与单薄,并仅仅被处理为这段往事的背景。这一背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可被替换的。小说中的个人话语与历史叙述之间仍存在着某种断裂。尽管张悦然表示,“在写《茧》的时候,我完全无意于构建什么宏大的背景,我只是关心我的人物的命运” [12]。但是,人物命运无法脱离与历史的联系。对历史叙述的搁浅,也影响了《茧》对个人命运的深入挖掘。
结语
《茧》试以 80后的代际经验为基础观照和诠释历史,从而对自我 /个体进行重新定位。尽管在书写个人命运的名义下,《茧》对历史的叙述颇令人遗憾地断裂在有限的个人经验之中,但在对父辈历史的追溯中,小说仍较为有效地呈现了个体与历史之间的交锋。这确实显示了一种写作上的转向。对张悦然而言,这是对其写作困境的一次有效突围,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自觉。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的写作或许也将由此从“生怪冷酷” [13]而转向更开阔、更深入的现实。而作为 80后写作的代表之一,张悦然在写作上的转向对更新公众对 80后写作的固有印象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张悦然.我已不能让青春连着陆地[I].张悦然主编.鲤 ·嫉妒.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2][12]武靖雅.张悦然:承载在个体身上的历史,并不比集体、国家的历史要微小.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789698.html.[3][4][7]埃莱娜 ·西苏.美杜莎的笑声[C].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4,194,197.[5][6][8][11]张悦然.茧[I].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385, 337 -338,156,155.[9][10]苏珊 ·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C].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79, 179.
[13] 邵燕君.由“玉女忧伤”到“生冷怪酷”[J].南方文坛,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