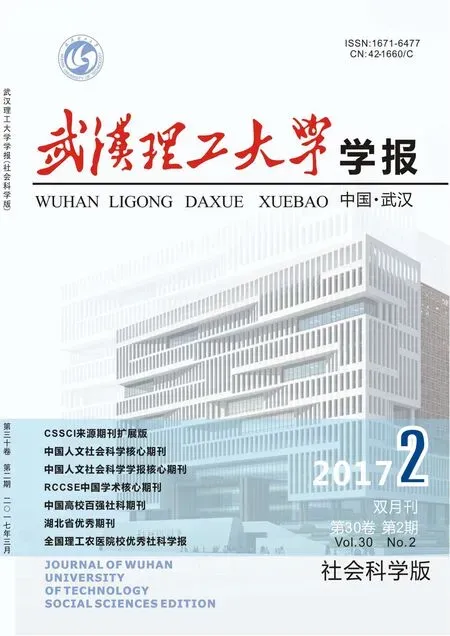日本《通信监听法》之检讨及其启示
李 牧,王和文(武汉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日本《通信监听法》之检讨及其启示
李 牧,王和文*
(武汉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日本《通信监听法》自实施以来,对规范技侦手段,制约公权力滥用,打击违法犯罪等发挥出重要作用,但对其反对之声也十分强烈。其监听范围、执行、监督、救济等方面有其自己的特点,合宪性、立法目的、修正案也备受诟病。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专门监听立法势在必行。以《通信监听法》为镜鉴,构建我国专门监听立法时应注意严格限定监听主体和监听对象、健全审查监督机制、赋予被监听人事后救济权以及实现打击犯罪,兼顾保障人权的立法目的。
通信监听;监听法;技术侦查;监察委员会
刑事“侦查监听”①是犯罪侦查活动中非常重要的措施,而经常采取的手段即为通信监听,极易对公民的秘密通讯自由造成侵害。监听措施的使用一方面是基于刑事侦查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可能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何权衡两者的关系是多数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为防止监听滥用,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在范围、原则、程序以及要件等方面,对监听予以立法规制。就相关立法现状而言,我国监听立法较为零散,2012年我国在通信监听方面的立法迈向了一个新台阶,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监听措施纳入其中,但主要是原则性条款。2014年《反间谍法》、2015年《国家安全法》等法律也只是提及了监听措施,并无专门规定。随着监听措施的广泛运用,在法治建设全面推进的背景下,亟需制定一部专门的监听法来调整监听关系。日本是制定通信监听法相对较晚的国家,其立法大量借鉴了域外的立法经验,在借鉴的基础上其又独树一帜。本文将对此予以剖析,以期对我国的监听立法有所裨益。
一、日本《通信监听法》的特点
日本新的《通信监听法》②由三十九个法律条文、七个附则、两个附表构成。内容涉及通信监听立法目的、相关概念的定义、通信监听的条件与实施程序、特定的计算机关于监听记录的处理、通信监听的监督与救济以及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等。从监听范围、执行、监督、救济程序方面来看,其主要特点表现如下:
(一)适用范围较广,但实施要件严格
在适用监听范围上,之前的《通信监听法》主要是针对毒品(麻药、兴奋剂等)、武器(枪炮、弹药等)、走私贩运,及组织杀人等四大犯罪类型;此外,在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相当于死刑、无期徒刑或无期监禁的犯罪;以及数人共同为上述四大犯罪类型而准备实施的并且最高刑期为20年以上的徒刑或监禁的犯罪,也可以实施监听。2016年的修正案通过后,在四大类型犯罪的基础上,把爆炸、防火、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拐卖未成年人、盗窃、抢劫、诈骗、恐吓、儿童性交易犯罪纳入到监听的范围③。这样一来,在刑法中最常的犯罪类型都已纳入到监听的范围,可见,只要行为人触犯刑法,日本侦查机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进行监听。但另一方面日本在实施要件上表现得非常严格,要同时满足以下这四个要件才能实施监听:一是有充足的理由足以怀疑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所列举的罪,即侦查机关在实施监听前必须掌握了相应有力的证据;二是数人共同实施犯罪;三是犯罪嫌疑人正在使用的电话号码或者其他方法的通信手段已经和通信运营商订立了合同,或者该通信与犯罪有关;四是侦查手段穷尽原则,即如果不使用监听手段,查明案件真相极其困难。
(二)监听期限较短,监听地点严格限制
日本法官在核发通信监听令状,并限定10日以内的通信监听期间,依据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的请求,法官认为必要时监听的期间予以延长,但累计不得超过30日。日本的监听期间相比于其他国家是比较短的,美国授权监听期限为30日,英国为3个月,而法国监听期限长达4个月。日本在监听地点上作了严格限制,有人居住或者有人看守的宅邸、建筑物或船舶内不得进行监听,这是为了避免不当侵害其他无关的人,通信监听的手段与侦查犯罪的目的必须要存在关联性,通信本身属于一方传达意思,另一方回复意见的双方沟通模式,虽然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进行的通信内容有可能传递或显示犯罪线索,但并非都与犯罪有关,因此,为了保障无关人的通信秘密自由,作了严格限制。
(三)设立了多种监督方式
首先,被监听人可以进行事后的监督。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把已经制作监听记录的目的、实施起止时间、监听手段、罪名以及不服告知申述信息,在监听结束后的30日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被监听人。其次,法院也进行相应的监督。侦查机关实施通信监听后,将通信运营商已经加密的监听原始记录,立即提交给核发监听令状的法官所属法院,当申请人有正当理由向法院提出请求时,法院可采用的专用的仪器(特定的计算机)对加密监听数据进行复原,保证了原始监听记录的真实性,防止被篡改。再者,监听行为受国会监督。关于通信监听政府每年要向国会报告三项信息:一是监听令状的申请及核发件数;二是申请及核发的罪名、监听对象及通信方式的种类、通信监听实施的时间段、通信监听实施期间的通信次数;三是因通信监听手段而逮捕的人数。最后,监听行为还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向国会报告的监听信息应向社会公开发表,只有罪名的公开,有妨碍侦查时才不公开,但在妨碍消除后要进行公开。
(四)被监听人享有一定的救济权利
首先,被监听人享有听取的权利。该法规定,一般情况下应在监听结束后的30日以内,将有关监听事项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除了客观原因无法得知被监听人的情况或者不知道被监听人所在地以外,都要通知。另外在特殊情况下,监听时间会延长一些,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向法院申请通知的期间延长,法官认为有妨碍侦查的情形时,可以将通知的期间延长至60日以内。收到通知的被监听人如果向法院申请听取、阅览或者复制监听记录中有关自己参与的该通信的部分内容,法院认为确认监听记录的正确性有必要,或者认为有其他正当理由时,法院应当采用专用的仪器对加密的原始记录进行复原,准许听取、阅览或者复制原监听记录中认为必要的部分。其次,被监听人有申诉的权利。对法官、检察官、司法警察作出的裁判、处分不服的,被监听人可以向法院进行申诉。
二、日本《通信监听法》之检讨
日本《通信监听法》立法框架比较健全,从立法目的、适用的监听范围、监听令状的签发、执行的监督、以及事后的救济等方面规定得较详细,操作性强。在程序的设计方面也极具特色,如关于侦查机关在侦破哪些案件时能否针对通信线路及对话进行监听,究竟在附加什么样的条件下,履行什么样的程序才被法律所允许,以及作为正当程序的核心内容告知义务在该法中都有所体现。虽然如此,日本《通信监听法》从立法到实施一直并不顺利,可谓是阻力重重。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法依据存在违宪之嫌
《通信监听法》虽为避免侵犯宪法所赋予公民的个人隐私与通讯秘密权,设定了较为严格的实施要件,且事先必须得到法官签发的监听令状,检察官或警察才可以实施监听措施,整个监听程序也设置了相应的监督,以符合日本宪法第13条与第21条对隐私权与通讯秘密的保障,看似采取监听措施有法可依。但其实不然,该法与日本宪法第21条和第35条相抵触,宪法规定了搜查与扣留应当依据主管司法官署上单独签发的命令书才可以实施,而搜查与扣留并不包含监听,电话监听属于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97条但书关于强制处分的规定,该条规定:“为实现侦查的目的,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但除本法有特别规定的以外,不得进行强制处分。”而法律特别规定属于强制处分的类型仅有搜索、扣押、勘验检查、逮捕、羁押[1],并没有监听。另外监听处分与上述类型的强制处分要件是不同的,即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类型,在没有对宪法作出修改的情况下通过《通信监听法》是违宪的[2]。因此,日本部分民众认为,无论该法程序看似如何正当,即使有法官签署的监听令状,通信监听仍然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这种情况导致日本一些政党与团体多次游行抗议,认为该法与宪法保障的通信秘密相抵触,在该法实施之日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停止该法律的实施。
(二)立法目的存在非正当之疑
日本制定《通信监听法》主要是为了应对有组织的共同犯罪,以及协助各国共同打击犯罪。然而对组织犯罪而言,自由民主党在立法时提出《通信监听法》能否真正地打击像奥姆真理教这类犯罪集团,是否真的能瓦解犯罪集团、逮捕集团首脑等效果皆不得而知。对回应国际间共同打击犯罪方面,由于各国制定通信监听相关法律的背景、原因都有所不同,如德国曾经为了达到军事目的而制定,法国则是为制止警察随意监听而制定,美国则是要打击黑手党、塔利班等恐怖组织而将监听作为重要手段。日本在制定之初也有反省警察权力无限上涨造成的人权侵害,但事实上,《通信监听法》施行后,犯罪集团首脑都明白电话联系是要被监听的,势必改用其他暗语或其他联系方式进行联络,甚至改为使用他人号码或不断更换新号码,使侦查机关在申请令状时无法掌握,又因科技的日新月异,除电话外,犯罪集团还可以使用网络等新方式进行联络,并且对其加密,这样一来,侦查机关使用监听手段侦破案件的效果可能差强人意,从这个角度看,该法意义不大。该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如果是为了加强打击组织犯罪,不仅执行效果令人存疑,也严重侵犯了日本宪法保障公民隐私与秘密通信自由的权利,而且《通信监听法》自施行以来,法务省也没有提供该法对于破案率提高、犯罪率下降有明显效果的确切数据。此外,以美国1969年至1972年期间的数据来看,共电话监听73 000人,其中72 000人是清白的或与犯罪案件无关的人,数据显示通过监听只有1.4%的概率查出犯罪,却有98.6%无辜者的隐私与秘密通信自由被侵犯④。由此看来,一般民众承认通信监听是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侦查方法,但是极大地侵犯了公民的隐私与秘密通信自由。日本针对特定号码进行通信监听有执行上的困难时,侦查机关还可能进一步将权限扩大至室内监听、通信卫星监控等,这可能成为法务省及侦查机关扩权的利器,极大地侵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当权者有用正当的立法目的来掩盖扩权,其立法目的存在不正当之嫌。
(三)修正案存在多点之争
虽然日本新的《通信监听法》已颁布,但在此之前该法修正案引发了强烈争议,这并非个案,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在保障人权与打击高科技、高智商犯罪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最为困难。2013年日本法务省开始研讨与推动通信监听相关法案革新,于2015年向国会提交了《通信监听法》修正案,以下几个争议的焦点仍值得我们关注,以期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1.扩大适用范围引发国民恐慌。在原来规定的四大类型通信监听对象犯罪外,增加盗窃、抢劫、诈欺、杀人、拘禁、诱拐儿童等9种犯罪⑤。再者,2020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可能面临的国际化、组织化的犯罪更加严峻,安倍政权正在研议共谋罪立法,这样一来,监听犯罪范围将被扩大至600个罪名以上⑥,难免造成公民对国家权力过度扩张而感到恐慌,基于此,有部分市民强烈要求废除该法⑦。尽管存在较大争议,但新法还是通过了该规定。
2.装置监听器材(bugging)监听遭到各界强烈反对。日本法务省为改变过度依赖口供及自证其罪的刑事司法制度现状,并活用通信监听手段,参考德国立法中采用的严格的对话监听模式[3],当时的草案提出专门针对电信汇款诈欺集团的窝点、暴力集团的常聚地及暴力集团骨干、首脑使用的车辆,以及实施控制下交付(controlled delivery)的情形等进行对话监听,凭借强化搜查方式,便于掌握重大犯罪相关信息,提出了增加装置监听器材(bugging)进行对话监听。对此,日本各地律师公会、市民团体提出反对意见。律师公会认为,现行《通信监听法》监听对象犯罪限于所列举的重大犯罪,且搜查手段必须要符合必要性原则和法定程序。法务省的提案允许室内监听,其有效性有待考证,然而一旦在室内设置监听器材,即是长期而广泛地进行对话监控,将极大侵犯公民隐私,应谨慎为之。以“新搜查手法反对联络会议”为首的市民团体方面,认为进行室内设置器材监听的做法将严重侵害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隐私权,它以改革创新为名的新搜查手法只是将警察权限无限上涨,并把日本变成监视国家⑧。由于该规定遭到各界的强烈反对,国会最终通过该法时删除了该项规定。
3.废除见证人制度导致监听缺乏监督。之前的《通信监听法》第12条规定进行监听时,必须由通信运营商或其代表人参与见证并对该措施发表意见,负责为日本法务省草拟提案的新时代刑事司法制度特别部会提出,为求监听更加合理及效率,拟将通信营运商监听所得的资料,以暗号或加密处理后传送给侦查机关,由搜查行动组“解密”变为声音档案后再进行听取,这样一来,即排除了通信运营商作为监听程序中的参与活动,而该声音档案可能事后遭录音、伪造变造或篡改,缺乏监督会使真实性难以确保,通信运营商扮演公正与专业的第三人被排除,难以取信于民。对此,虽争议较大,但日本认为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确保监听记录的真实性,所以,新法最后还是废除了见证人制度。
三、我国监听立法的构建
当下各国使用监听手段侦破重大刑事犯罪已成为趋势,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我国专门监听立法势在必行,但为了避免重蹈日本颁布该法以来出现的问题,应以其发生的问题为镜鉴,同时,借鉴其成功的立法经验,立足国情,在专门监听立法构建时应重点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确立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并重的立法目的
打击犯罪兼顾保障人权的立法目的应始终贯穿于立法过程中,它既是监听立法的起点也是归宿,应尽量避免像日本颁布该法以来那样遭到非正当性质疑。首先,应避免不当侵害,进行通信监听必须符合最小限度侵害原则。通信监听是目前侦查机关执行犯罪调查、搜集证据的有效利器之一,但也是国家侵犯公民隐私权最严重的做法。因此,应使公民或犯罪嫌疑人权利所受到的侵害降至最低,对此,这也是对于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重要保障。再者,尊重当事人的隐私的合理期待,如日本与特定关系的人通信是受人委托执行其业务时,不得监听,除非其属于监听对象犯罪嫌疑人,才能进行有线通信的监听,此规定也类似于德国司法实务与诉讼法上的见解,律师与当事人间的谈话,原则上不得加以监听录音,以保障当事人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4],除非律师自己是共同被告或者触犯了使刑罚无效的罪。日本和德国的通信监听法制均重视特定业务关系所存在的高度信赖感以及通话内容与过程中对隐私的合理期待,仅在特殊业务从业人员成为犯罪嫌疑人时,信赖与隐私保障才给予排除,从保障人权的角度考量,其做法值得借鉴。最后,应做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实体公正固然重要,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程序公正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若程序不公正,则人权保障也就无从谈起。在监听过程中,违反相关程序以及不符合程序收集非法监听所获得的资料,法院不得采纳,监听侦查所得证据不得游离于法治之外,必须接受正当法律程序的检验[5]。
(二)严格限定监听主体和监听对象
为了使监听措施不被滥用,监听主体方面应严格限定,即有侦查权的机关才能采取监听措施。根据宪法第40条的规定,我国目前可以对通信进行检查的主体限定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8条的规定,实际上真正实施技术侦查措施(通信监听)的只有公安机关(包含国安机关)。因此,我国在制定专门监听立法时,严格限定监听主体为拥有侦查权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另外还需要注意一个新的问题,即我国在推进监察体制改革,现已在京晋浙三地试点设立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职权,将来形成“一府一委两院”(政府、监察委、检察院、法院)的新体制。由于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也即监察委员会行使相应的侦查权,为了侦破重大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以及丰富监察手段的需要可能会赋予监察委员会使用监听措施的权力。如果改革全面推进,在制定监听立法时应考虑修改宪法第40条等相关条文。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8条的规定,我国目前可以实施侦查监听的犯罪内容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另外重大的职务犯罪以及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也可实施技术侦查。关于技术侦查措施仅仅用5个条文进行规定,在适用的范围上规定得过于宽泛,没有严格限定,如“重大”、“其他严重”等规范的构成要素,因而侦查机关可能通过自由裁量权把不应被监听的犯罪纳入到监听的范围,导致权力被滥用,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日本之前的《通信监听法》对犯罪对象范围限四大犯罪类型,但新的《通信监听法》监听犯罪对象过大,遭到强烈反对,一些团体游行示威,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因此,我国监听立法在犯罪对象上应以重罪为原则,打击犯罪的同时也要符合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规定上应当更具体,严格限定适用的罪名。
在监听通信范围方面,日本监听手段仅限于有线通信(wiretapping),增加装置监听器材(bugging)进行对话的监听被禁止,监听对象通信内容小于我国规定的范围,实践中所监听的通信范围在我国没有被严格限定,其几乎涵盖有线与无线的通信,包括了通讯监听、监视、网络监控、邮件检查、乔装侦査、特工行动等多种具有较大差异的特殊侦査手段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室内装设监听器材设备不仅仅涉及侵入住宅,显然有侵犯居住自由之嫌,属于侵犯公民隐私权、居住权等基本权利,必须有更为严格谨慎的程序和限制要件为宜。总之,监听手段应避免过度扩张,要受到严格限制,其立法目的要正当,更应符合宪法保障公民通信秘密与隐私的目的。所以,在监听通信范围方面也应受到限制,关于增加装置监听器材(bugging)进行对话监听,原则上禁止,但可以例外规定侵犯国家安全等利益可以实施。
(三)健全审查监督机制
监听令状需要由法官审查及核发,多数国家亦采用,刑事侦查程序中引入令状制度,“其基本要求是在侦查阶段引入中立的审判机关,就强制侦查的理由进行司法审查,以判断强制侦查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其本质上通过司法权控制侦查权以保障人权”[6],健全监督机制防止权力被滥用,避免类似于日本国民因《通信监听法》的实施时感到恐慌的局面。因此,我国可以建立监听令状制度,监听令状的审查批准可以结合我国现存制度参照检察机关关于逮捕令的程序,检察机关要对监听侦查的力度和范围、实质要件等严格审查,赋予司法机关在事前、事中加以审查及监督的权力。其次,要实现事后的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政府年度的工作报告要把监听案件总汇信息纳入到报告的内容,接受各级人大的监督,人大“质询对于督促政府改进工作、将自身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有一定的效果的”[7]。
(四)赋予被监听人事后救济权
由于通信监听不像传统的“强制处分”⑩,在执行时即可明确得知已受强制处分的状况,往往在事后才发现自己遭到检察机关的监听,因此,要赋予被监听人事后救济的权利,弥补监听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瑕疵以及对于公民权利的不当侵犯。首先,要赋予被监听人的听取、阅览与复制权,即刑事程序中阅卷权应当包含可以阅览监听侦查相关法律文书的权利,被监听人对监听记录的真实性有异议,或有其他正当理由,法院应根据被监听人的申请,可以批准其听取、阅览或复制监听原始纪录中有关个人通信部分的内容,被监听人可以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其进行质证,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应当保密的证据外,应当公开质证。另外,被监听人如对监听程序有异议也可提出,法院应当受理,如存在违法收集的证据材料,法院应当对其证据进行排除。其次,对于疑难复杂且争议较大的案件可以举行听证。最后,对于侦查机关在实施监听侦查期间对公民权利造成严重侵害的,应明确被纳入到国家赔偿的范围。
四、结 语
在法治思想与人权保障盛行的今天,个人权利保护意识不断高涨,尤其是隐私权成为了人们日益关注的重要权利。特别是“棱镜门”事件后,监听与隐私权的保护更成为关注的焦点。我国法治建设正全面推进,一切权力必须受到法的有效规范和制约。我国当下采取监听措施主要依据部门规章,尚无专门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法治精神。同时,由于分散立法,特别是零散的规定,难以统一规范监听行为。以日本通信监听立法实践为镜鉴,制定一部专门的监听法无疑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注释:
①我国学者在技术侦查界说上主要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咱,我们采用监听侦查与狭义的技术侦查的含义基本相同的观点。参见曾赟的《监听侦查的法治实践: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158页。
②该法原名《犯罪捜査のための通信傍受に関する法律》,我国有学者称为《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通讯的法律》。参见宋英辉的《刑事程序中的技术侦查研究》一文,《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84页。但由于名称稍长,我们把它称为《通信监听法》,参见于青、管克江的《日本〈通信监听法〉起争议》一文,《人民日报》2000年8月22日第(7)版。日本新的《通信监听法》于2016年12月1日逐步开始实施,该法并非公布之日起实施,而是从公布之日起三年内通过政令的方式决定对相应的条款公布施行。
③改正法情報刑事訴訟法編[EB/OL].(2016-09-01)[2016-09-09].https://www.sanseido-publ.co.jp/publ/roppou/roppou_dic/moroku_2016_tuika/moroku_2016_tuika_keiso.htmlJHJ6.
④数据统计来源于[EB/OL].[2016-08-25].http://biglibrary.co/download/against-the-law-the-nixon-court-and-criminal-justice.pdf.
⑤日本刑事司法改革方案出炉[EB/OL].(2014-09-23)[2016-08-12].http://japan.people.com.cn/n/2014/0923/c35467-25713444.html.
⑥盗聴法の改正問題~通信監視の捜査手法も併せて[EB/OL].(2013-06-20)[2016-08-12].http://www006.upp.so-net.ne.jp/kansi-no/kenkyukai/documents/20130620yamashita.pdf.
⑦盗聴法(通信傍受法)の大幅拡大および刑事訴訟法の改悪に反対し、刑事訴訟法等改正案の廃案を求める法律家団体の共同声明[EB/OL].(2016-05-02)[2016-08-12].http://www.jlaf.jp/html/menu2/2016/20160502142617_5.pdf.
⑧〈寄稿〉刑事司法大改悪許すな 新捜査手法反対連絡会議呼びかけ人弁護士西村正治[EB/OL].(2014-07-14)[2016-08-20].http://www.zenshin.org/zh/f-kiji/2014/07/f26400602.html.
⑨技术侦查可分为三类:其一,侵入通讯联络的技术侦査,如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等,其侵入式特点直接关涉公民隐私权;其二,监控相对人活动的技术侦査,如监视、定位等,主要涉及公民日常生活自由权和独处的权利;其三,监控相对人物品的技术侦查,如秘搜、邮件检査等传统监控方法,主要涉及公民财产权利及其背后的隐私权。参见胡铭的《技术侦查:模糊授权抑或严格规制—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3条为中心》,《清华法学》2013年第6期,第243页。
⑩日本有学者认为对重要权利及利益的制约,且无需征得被处分人的同意而实施的处分称为强制处分。参见井上正仁的《強制捜査と任意捜査》(新版),有斐閣2014年版,第243页。
[1]绿大辅.日本侦查程序中的强制处分法定主义[J].肖 萍,译.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2):167-168.
[2]奥平康弘.盗聴法の総合的研究:通信傍受法と市民的自由[M].东京:日本评论社,2001:6.
[3]彭 勃.论监听作为侦查手段的法律问题[J].法商研究,2002(6):11-16.
[4]克劳思·罗科信(Claus Roxin).(德国)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81.
[5]曾 赟.监听侦查的法治实践: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J].法学研究,2015(3):158-175.
[6]孙长永,高峰.刑事侦查中的司法令状制度探析[J].广东社会科学,2006(2):184-189.
[7]吕艳滨.西方主要国家议会监督手段之比较[J].环球法律评论,2003(2):232-239.
(责任编辑 江海波)
Review and Enlightenment of Japanese Wiretapping Law
LI Mu, WANG He-wen
(SchoolofHumanitiesandLaw,WUT,Wuhan430070,Hubei,China)
“The Japanese Wiretapping Law”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gulating the means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restricting the abuse of public power, and cracking down on illegal crimes,but the abolition of it is also very strong.Its scope of wiretapping, execution, supervision, relief and other aspect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ts constitutionality, legislative purpose, Amendments have been a lot of criticism.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le of law, Chinese special wiretapping legislation is also imperativ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trictly limit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object of the wiretapping,improve and perfect the mechanism of auditing and supervision,grant the right to relief after being wiretapped an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mbating crime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where we establish special The Wiretapping Law.
wiretapping;wiretapping law; technological investigation; The Oversight Committee
2016-10-16
李 牧(1968-),男,湖北省仙桃市人,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宪法、行政法研究; 王和文(1986-),男,贵州省黔东南市人,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宪法、行政法研究。
D911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