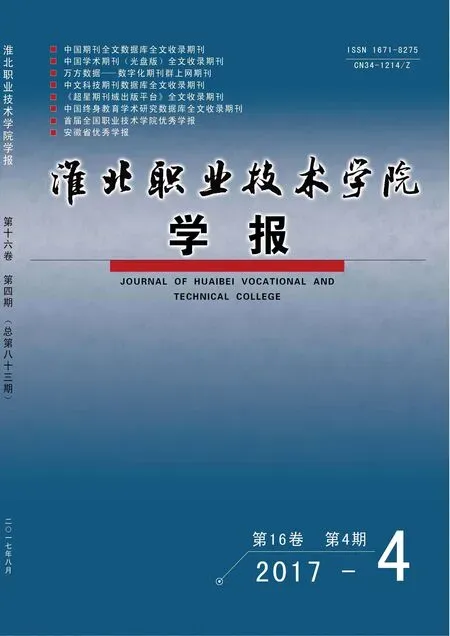“灵”与“肉”的角逐
——思特里克兰德与康斯坦丝的比较研究
刘晓玉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灵”与“肉”的角逐
——思特里克兰德与康斯坦丝的比较研究
刘晓玉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月亮与六便士》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以下分别简称“《月》”和“《查》”)两部作品,均表现出男、女主人公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精神与肉体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希望逃离现实社会,回到精神、肉体自由和谐的原始社会,恢复被压抑的人性,实现自由与自我。其中,在追逐自由的过程中,思特里克兰德与康斯坦丝分别经历了“灵”与“肉”的冲突、“灵”与“肉”的分离以及“灵”与“肉”的和谐三个阶段,最终获得他们的理想与爱情自由。从思特里克兰德与康斯坦丝的追求中,体现了“灵”与“肉”的自由和谐不仅是20世纪社会人们的追求,同样也是生活于21世纪中的我们的理想追求。
思特里克兰德;康斯坦丝;“灵”;“肉”
“灵”在新华字典中有多重释义,如有效验、聪明、精神、反应灵敏等,然其与肉体对应的应属精神意义。精神与肉体之关系在多数作家作品中因其艺术内涵都得到很好的艺术阐释,如但丁的《神曲》、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一些作品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审美表现。同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小说家毛姆与劳伦斯,两人处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十字路口,都善于从作品中主人公的内心来追求早已丢失掉的人性与自由。两人的作品《月》和《查》都从精神与肉体的关系出发来探讨西方人在快速发展的机械社会中所遭遇的异化。
毛姆的《月》以“我”的视角叙述了思特里克兰德在幸福美好的家庭生活中突然不辞而别,去巴黎寻找他画画的梦想,而巴黎的世俗生活使他难以找到绘画的灵感,并且肉体也饱受折磨。他随后来到远离文明社会的塔希提岛上,在这里,他的精神得到了自由舒展,并与一位土著女子同居,“灵”与“肉”走向和谐统一,他完成了一幅幅巨画,但最后却因麻风病而离世。《查》描述了克利福德在战争中下半身瘫痪,妻子康斯坦丝在不能忍受克利福德的精神、肉体压迫后与猎场看守人梅勒斯之间产生了微妙的感情,最终两人的“灵”与“肉”走向和谐,从而实现了其人性的复归。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最后追逐的结果不尽相同,但他们在追逐的过程中都经历了“灵”与“肉”的角逐(即“灵”与“肉”的冲突、“灵”与“肉”的分离及“灵”与“肉”的和谐三个阶段),这也正为两部作品进行对比分析找到了切入点。
一、“灵”与“肉”的冲突
在《月》中,似乎没有关于“灵”与“肉”冲突的长篇大论,但我们可以感到思在之前幸福美好的家庭生活中内心的激烈冲突。作品开头从思特里克兰德的太太写起,她喜欢结交作家,她很爱她的丈夫……作者愈是这样写,愈为后来思特里克兰德为什么不辞而别留下悬念。随后,作者代表其太太到巴黎与思特里克兰德谈判,当听到他说是为了画画才离开时,其吃惊诧异之情不言而喻。40多岁的人说要画画,尽管他自己也知道太晚,但他说:“一个人要是跌进水里,他游泳游得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得挣扎出去,不然就得淹死。”[1]71可以感觉到思特里克兰德走到如此地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知道他起步晚,但深藏在他体内关于祖先的集体无意识不断地冲撞着他的灵魂,由不得他不画。灵魂的蠢蠢欲动使他的肉体看上去似乎也那么突兀,明明是得体的穿着,光滑的脸庞,却感觉像是一个上层社会人家的马车夫。“灵”与“肉”的冲突使他显得与社会格格不入,其结果就是离开伦敦,走向巴黎。
而在《查》中康斯坦丝(又名“康妮”)的冲突叙述就比较直接。新婚不久的克利福德参加战争,不久却被残废地推回来。随后他们一块儿回到拉格比庄园,两个人相依为命。康妮觉得克利福德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就充满感情地支持他的一切活动。久而久之,克利福德的所作所为(如写小说、对待村民的态度、对待孩子的看法)使康妮渐渐感到他的精神也随着战争而摧残,康妮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总是感觉到莫名的压抑。父亲在拉格比对她说道:“康妮,我希望你不会因为客观原因而不得不独守春闺。”[2]18她反驳父亲自己为什么不能这样。其实,这时她的“灵”与“肉”已经起了冲突,只是她自己没有意识到。与世隔绝的生活使她心头跳动着不安的情绪,她急切地想逃出这种不安,慢慢地,她衣带渐宽。随着父亲第二次直白地提醒她:“你干吗不找个情人呢?”[2]21再加上克利福德的朋友米凯利斯的挑逗,她知道自己的不安在哪里了。至此,她意识到自己放弃肉体幸福而不断跟随克利福德的精神快乐是自欺欺人的,她试图投进米凯利斯以及梅勒斯的怀抱……
两位主人公,一个人生活得太过幸福,致使他突然离家出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遭到旁人的怀疑与蔑视,为什么他选择在旅行回来之后离家呢?想必他的内心已经过苦苦挣扎,尽管作者把他写得如此冷血,这种对比显示出强烈的张力,把思特里克兰德的“灵”与“肉”的冲突表现得更加极致。另一个主人公康斯坦丝,一心只为自己的丈夫考虑,为丈夫的欢乐而欢乐,直到自己的衣带渐宽、父亲的提醒以及他人的引诱,她才发现守着高尚的道德精神只会使自己的肉体越来越沉重。刘小枫曾说:“精神只有不再作为支撑物的时候,它才会自由。自我欺骗时,精神特别难受。”[3]220两人都活在精神的自我欺骗中,因此,两人的“灵”与“肉”才会产生或明或暗的冲突。然而,这样的冲突是在违背道德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接下来,他们的“灵”与“肉”展开怎样的角逐呢?
二、“灵”与“肉”的分离
两位主人公在经历“灵”与“肉”的冲突后分别抛下沉重的肉身,开始追逐自己想要的“灵魂”自由。思特里克兰德在巴黎一家破旧的小旅馆开始了画画之路。在那里没有妻子悉心的照顾,甚至三餐都保证不了,以前的衣服现在穿着足足大了一号,但这些对他来说似乎毫无影响。尽管已抛弃沉重的肉体,可精神的寄托似乎也无迹可寻。他的画除了画家施特略夫外无人赏识。此画家自己的画毫无成就,但他却有一双发现艺术的慧眼,他认定思特里克兰德一定是一位大艺术家。因此,慷慨无私地解囊相助。而思特里克兰德却把这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没有感激、没有谢意,甚至最后还害得他家破人亡,他也没有怨言。可以说,如果没有施特略夫的大力帮助,思特里克兰德或许连活着都是一个问题。在一次生病中,他终于打破了两人的“友谊”。他被请求住到施特略夫家里,在病情恢复的过程中,他充满情欲的肉身深深地吸引了施特略夫太太,致使他最后离开施特略夫家时,施特略夫太太义无反顾地要跟随他离开。这里,似乎思特里克兰德的灵魂与肉体没有分离,然而在他对“我”说的话中就可见分晓:“我不需要爱情。我没有时间搞恋爱……我无法克服自己的欲望,我恨它,它囚禁着我的精神。”[1]228思特里克兰德无法左右隐藏在自己体内的“魔鬼”,他只能任凭自己放肆一次,借以实现灵魂对身体的绝对支配权。
《查》中的康妮在婚后长期面对毫无热情的丈夫,她打心底里厌恶他,“她觉得她之所以嫁给他,就是厌恶他,一种秘密的、肉体上的厌恶。”[2]118实际上,她嫁给他仅仅是被他的精神所吸引。现在,他的精神的萎缩使康妮觉得生活已无意义。与米凯利斯短暂的激情进一步加深了她对当今社会的无助、失望。她开始逃避文明社会,走进小树林,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梅勒斯的出现使她的心里泛起了层层涟漪。看到赤裸着上半身的梅勒斯,她的心里竟然现出了感动。感动那胴体的美丽、感动那胴体背后的纯洁生命。在随后的几次相遇后,两个精神、肉体的孤独之人拥抱在了一起。然而,她觉得她的“灵”与“肉”是分离的,对于肉体的交欢她没有兴奋,甚至觉得有点好笑。她的灵魂不断地处于矛盾之中,肉体上的渴望复活与精神上的无尽拷问使得她做出抉择:我不要再和他保持这样的关系,我从中仅仅是想获得孩子。对于这样的决定,她离开了拉格比,与姐姐出去游玩,借此希望怀上孩子……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四章中说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4]这其实也暗指自己有肉身的羁绊,以致做事情不能大显身手。两位主人公都因为“吾有身”而不得不做出一些违逆自己灵魂的事情,他们似乎也渴望“吾无身”,这样,自己的灵魂就不用遭到拷问。思特里克兰德希望自己没有肉欲,一心一意的作画;康妮希望没有肉欲,这样就不会对不起自己的丈夫。两人都在经历着“灵”与“肉”分离的折磨,因此,两人都想逃离。最终,思特里克兰德远离文明,来到南太平洋与世隔绝的原始气息浓重的塔希提岛;康妮离开拉格比,暂时逃离心灵的叩问,以期获得些许的安宁。
三、“灵” 与“肉”的和谐
“什么叫美好的生活?按阿蕾特的说法,当身体是灵魂的仆人时,生活就是美好的,只有灵魂才能拉住神明的衣襟。”[3]79漂落到塔希提岛上的思特里克兰德仿佛回到了心中的伊甸园。在这里,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仍是一个永远缺钱花的流浪汉,但没有人嘲笑他,视他为异类,相反还愿意与他交朋友。他的心灵受到前所未有的震颤,因为他找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天地。在房东的帮助下,他与一位土著女人爱塔结婚,以此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并且满足他身体内时刻潜伏着的“魔鬼”的欲求。没有世俗社会的纷扰,他的灵魂处于自由翱翔状态;没有女人霸占他的灵魂与肉体,他身心处于安宁恬适状态,“灵”与“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因此,他创作了一幅幅杰作。在思特里克兰德的晚年,由于身染麻风病,他与爱塔及他们的孩子过起了“隐居”生活。这样的生活使思特里克兰德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画画。最后,在他居住的屋子画出了一幅惊人的“巨画”,但他让爱塔把这间屋子烧掉。这应该是思特里克兰德最终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才走得如此平静安详。
康妮在与梅勒斯多次的肉体交合后,她的灵魂也渐渐发生变化。最初结合时,她只是觉得诧异,似睡非睡,随后她不理解他如何发现她肉体的美,甚至于觉得他的动作很滑稽,但是“她觉得,自己灵魂深处,有一种新的搅动,一种新的赤裸在那里浮现。”[2]154可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她觉得身体内的另一个自我时刻想冲破自己,不停地在她的子宫和肺腑里流动,虽然有一些负担,但却很舒服。接着,两人的结合使她觉得自己的灵魂是一个旁观者,俯瞰并嘲笑着所谓神圣的爱。她觉得两个不爱的人保持这种关系,真是滑稽透顶。紧接着,她如欲火重生后的凤凰,觉得自己再次成为一个女人,并且可以和梅勒斯一起享受快乐。渐渐地,她爱上了他,爱上了他的肉体,爱上了他的阳刚气,爱上了他们的志同道合。她知道是时候要冲破束缚在灵魂上的压迫了,她要与克利福德离婚,和梅勒斯在一起,她要让自己的灵魂与肉体合二为一,并且使灵魂支配肉体。最终,她向克利福德提出离婚,并期望与梅勒斯走向远方。此时,灵魂的复活与“直觉的诞生帮助她消解了理性思维的魔障,使她从形形色色的心灵镣铐中超逸而出,并且转而以活生生的生命与活生生的世界融为一体。”[5]
两位主人公在肉体饱受折磨、灵魂屡遭拷问后,终于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挣脱了这一切。塔希提和拉格比是思特里克兰德和康妮的理想归宿,自然人爱塔和梅勒斯是他们理想的伴侣。只有当人的自然欲望释放后,灵魂才自由,肉体才不显得突兀。毛姆虽然对思特里克兰德的“灵”与“肉”描述不那么明显,但我们读起作品来,可明显地感到精神与肉体在大自然中的一种宁静和谐。劳伦斯就不同了,他通过大段的性描写来呼唤长期受到压抑的精神和肉体,希望他们和谐相处。正是两者的叙述方式不同,才使我们的灵魂在阅读中不断地经受检阅,是否也如主人公一样不断进行着层层角逐?
人性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由肉体与灵魂或精神结合而成,而灵魂与肉体不是简单地存在着,它们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也就使人性这个话题贯穿了整个西方文学史,从古希腊神话到文艺复兴,再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各个时期的作家均从不同层面涉及到了它的存在。尤其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阶段,它被提及到领先地位,人性异化、人失去自我,人成为非人,这些都引起作家们的深刻关注。以上两位作家直击人性的构成层面,以不同视角向我们展示社会上人的“灵”与“肉”受到的压抑以及希望逃脱其压抑实现人性的复归。这让我们想到,文学作品仅仅是生活的反映,它不提供给我们如何解决问题,只是给予我们某些方面的启示。从“灵”与“肉”的角度比较分析两部作品中两位主人公,给我们提供了人在社会中是如何存在以及怎样存在的思考,同时也突出了该比较研究的价值意义所在。
[1] 毛姆.月亮与六便士[M].傅惟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2] 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M].赵苏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4] 老子.道德经[M].熊春锦,校注.北京:中央译文出版社,2006:42.
[5] 蒙雪琴.现代性挤压下的现实主义反动:评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108.
责任编辑:张彩云
2017-04-20
刘晓玉(1992—),女,河南洛阳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与文化。
I109
A
1671-8275(2017)04-012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