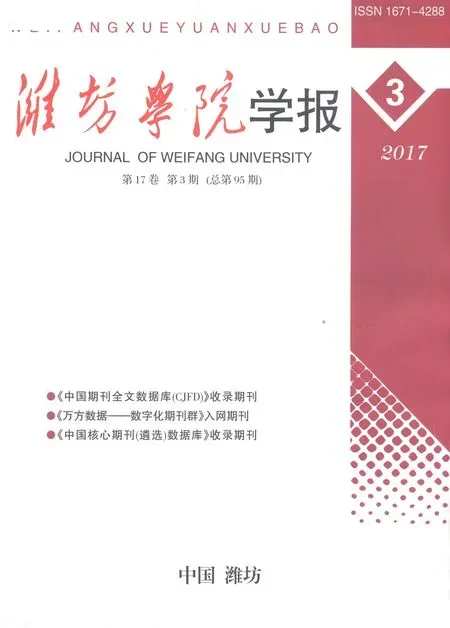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限度及其合理性调适
王幸平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限度及其合理性调适
王幸平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为解决奥匈帝国民族问题和国家的统一问题,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他们的民族理论即“民族文化自治”。但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折中立场,从而决定了他们的民族理论具有三个方面的限度: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区分;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要求和传统奥匈帝国国家结构之间的矛盾以及现代国家领土原则和民族非地域原则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所提出的民族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化发展与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等问题却成为现代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主题。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合理性调适,从而为解决当前民族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文化自治;非地域原则;多民族国家统一
近些年来,由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而引起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造成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局动荡、民族独立和国家分裂,因此民族问题成为21世纪影响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问题。面对复杂的民族矛盾,世界不少国家开始采用民族文化自治来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以维护民族发展和国家领土的完整。第二国际时期,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民族问题与党的任务的关系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卡尔·伦纳和奥托·鲍威尔提出了他们的民族理论即“民族文化自治”。在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全面地评判这一民族理论及其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了解他们的民族理论对我国民族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民族文化自治”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伦纳和鲍威尔的民族理论是针对多民族奥匈帝国复杂的民族矛盾而提出的理论。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各个民族意识不断增强,民族运动此起彼伏,它们要求民族权力和发展。但是在现代国家集中分散制度下,各个民族为了国家权力而进行斗争。“民族斗争使得各阶级更加渴望民族和平。这就必须从法律上调整民族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民族自治的要求。”[1]在鲍威尔看来民族自治不仅是民族斗争必然结果,而且是民族和平的要求。因为民族和平能够保证经济生产流通与交换秩序的正常进行。相反民族斗争则破坏了社会生产秩序,导致社会生产无法进行,从而破坏了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民族之间的斗争还意味着一旦一个民族掌握了国家权力必然会导致其他民族失去权力,所以说每一个民族都是另外一个民族的潜在敌人或对手。民族斗争的结果就是国家行政机构以及立法机关陷于停顿,国家无法发挥它的管理和立法职能,从而使每一个民族都失去了国家中的权力和地位。“正是工人阶级在民族斗争中扛起了民族自治的旗帜。如果工人阶级不想被排除在当前的政治斗争之外,那么他就必须寻找一种解决这一斗争方法来调动人们的热情。他们找到的手段就是民族自决。民族斗争越是激烈,工人阶级就越是强调它的纲领。”[2]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民族渴望结束国内民族之间的争斗以保持民族之间的和平,恢复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和立法机构,从而在民族自治中管理和发展民族文化。
民族自治从实质上来说实际上是民族自我管理,自我决定民族事务。“民族自治只有在性格原则上才能成立。每一个民族有权发展本民族文化。任何民族不再为国家权力而斗争。”[3]这就需要国家在制度上保证民族的民主权力。同时它还是民族在社会发展中需要。社会生产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以及民族文化的变化,进而引起了民族观念和意识的变化。民族意识的觉醒不但改变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而且改变了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关系,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非历史民族”开始认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要求在国家中的平等权利和地位。所以鲍威尔认为奥匈帝国中的民族问题并不在于国家政治制度,也不在于社会发展水平,而是在于“非历史民族”的觉醒。传统的民族领土原则以及集中分散制度(centralist-atomist)导致了民族斗争,因此民族文化自治就是赋予民族自我管理的权力,这主要体现在民族管理委员会的权力上。“民族对于国家的权利基于行政的民主形式,基于行政区域中的自我管理。”[4]由选举成立的民族管理委员会有使用本民族语言以及成立民族学校和教育制度,对本民族成员进行征税。民族文化自治理论主张各个民族不管居住在何处,他们都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成立民族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主要职能就是负责管理民族文化事务。民族事务是由民族委员会来管理,而公共事务由国家来管理。这种对于国家公共事务与民族事务的区分成为后来多元文化主义者关于个人民族身份与国家公民身份理论的先声。[5]
二、作为民族和国家关系调整的“民族文化自治”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鲍威尔之所以把教育和民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手段,这是和他的民族原则以及民族国家关系的有机调整理论分不开的。
鲍威尔反对把语言、地域等客观性因素作为民族区分的标准,提出了“民族性格”原则,主张用文化基础的“性格原则”代替领土原则以解决民族问题。民族性格原则是以文化作为民族区分的标准,具有相同文化的人们形成民族文化共同体,不管他们居住在何处都享有本民族文化教育与管理事务的权力。
对于民族来说,一定的领土也起着重要作用。民族最初是在自然形成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它包括地域、血缘和语言等。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的界限往往就是民族之间区分的界限。但是伦纳认为社会发展使得“经济和文化的利益把距离遥远的人们统一起来。个人不再束缚于土地:知识范围内社会联系取代了世袭的社会结构。”[6]自然地理界限不再成为民族之间的界限。因此鲍威尔反对把地域因素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准,但是这并不说明他否认民族中的地域因素,相反他承认“地域”对民族存在和发展是有着重要作用。由于民族是人的联合而不是地域的联合,但“这并不是说领土原则是错误的和无法成立的。相反,它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原则。”[7]鲍威尔认为领土是国家形成的必要因素,因为“国家必然是一个领土实体。它必须有一些领土以形成制度上或多或少的独立性以及经济区域上的自足性,并且在战略上反对外来敌人。”[8]另外鲍威尔区分了同样作为非历史民族的捷克人与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发展影响下所导致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捷克人有着自己的祖国,从而保证了国外的捷克人形成自己语言和文化特性。而由于犹太人没有自己的祖国,所以无法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这就形成了捷克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自治。犹太人却是融入所在地民族文化中去,而无法形成民族自治。
现代国家把民族作为成立的基础,但是一方面民族在法律中并没有它的地位和权利,另一方面民族的发展又离不开统治阶级以及国家法律的影响,这就导致了在集中分散制度下各民族为了发展民族文化而争夺国家中的权力。斗争的结果就是国家行政机关以及立法机关陷于瘫痪,从而使得各个民族在国家中都没有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其结果就是“集中分散制度”的解体。在民族与国家的有机调整中,民族在法律上是享有权利的实体,它有管理本民族文化事务的权力,而且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集中分散的关系,而是一种“命运共同体”。
伦纳和鲍威尔认为解决民族之间的斗争就要“通过选举的民族委员会来管理自己的民族文化事务。民族委员会有权利为自己的组织成员成立德语学校,不管他们住在何处;通过征税来满足民族筹集资金的需要。”[9]这样,法律上的民族实体满足了各个民族自我发展的要求,使得各民族不再为国家权力而斗争,民族与国家关系的有机调整既保证了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又保证了国家的统一。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匈帝国内被压迫民族纷纷独立,奥匈帝国走向解体,因此从法律上把民族作为实体来调整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的愿望也宣告落空。
三、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的限度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伦纳和鲍威尔所提出的民族理论得到了重新认识,并在许多国家中得到运用。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发展转变为文化发展的因素,又与这一理论所形成的历史条件有关,但他们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这是由民族文化自治理论自身的限度所决定的。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它以社会改良来维护奥匈帝国统一为目的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旧的国家体制范围内不改变传统国家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前提下,实行国家政治与文化的有机调整来发展民族文化,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它根本无法实现发展民族文化的目的,更遑论完成工人阶级革命的任务。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性质与方向做出了恰当的判断,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因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由西欧发达国家转向东方殖民地国家。[10]他批判鲍威尔没有看到这一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他的民族理论是倒退到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来追求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权利,而不是前进到社会主义范围内追求民主权利,所以他批判鲍威尔民族文化自治理论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11]在现实民族意识觉醒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条件下,国家统一与民族发展的关系成为突出问题。民族文化自治理论既是国家政治制度的表达,也是民族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
其次,奥匈帝国腐朽的专制制度和社会民主党人民主权利要求之间的矛盾。在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影响下,针对奥地利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及无产阶级政党革命运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理论,试图在传统政治制度框架下维护帝国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但是衰败的封建帝国以及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本质决定了具有改良色彩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必然失败的命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和全球化发展,传统民族国家以及自由民主理论受到了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挑战。国家统一与民族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旨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发展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并作为解决多民族国家统一问题重要手段,显示了它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批判性同时,还要分析它在现实中所具有的合理性价值,以便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发挥它在我国解决民族问题中的作用。
再次,现代国家中的民族属性与领土之间内在关联性决定了民族发展的区域特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是在民族概念的“非地域原则”基础上,实行国家政治与民族调整,在民族自由发展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由于这一理论忽视了现代国家的领土特征,所以民族自治必须以地域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国家统一和民族自由。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就是在国家领土和主权统一的基础上,承认民族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但是数量上也是在文化上的区分,正是各个民族之间的区分才有实行民族自治的必要性。它要求在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自治,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和经济,从而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又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一定的民族聚居区域是实施这一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民族文化与教育的发展是这一制度本身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以此来看,民族区域自治以及文化自治虽然在民族发展原则和基础上存在着差异,但是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以及发挥民族自我管理权力是一致的,它们在调整国家与民族关系,解决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问题则是相互补充的。如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国家层面上对于少数民族实施的民族保护制度,它体现了民族自我发展的权利以及民族平等的原则。而民族文化自治则更多的是在民族层面上实现民族的自我管理,主要体现了在具体制度与技术操作层面上来实现作为民族自治主体的权力。因此民族文化自治在国家统一和建设时期可以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这就需要在坚持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条件下对民族文化自治进行理论上以及实践上的调适,从而发挥它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价值和作用。
20世纪以来,尤其是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东方和西方两大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被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所取代。因此有人看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不再是意识形态斗争和阶级斗争,而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冲突。比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的确说明了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以及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冲突的表现。但是他把不同民族文明价值作为世界上的矛盾和冲突根源,实际上是把意识形态斗争归结为文明的矛盾,它实际上遮蔽了资本主义国家扩张和统治世界的本质,并没有指出造成文明冲突背后的深层根源。实际上从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来看,多元化发展只是一个表象。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对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对于资本还不能控制的区域,它就利用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种手段进行渗透和控制,从而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范围内。所以冷战结束以后,文化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实文化手段也是资本主义在进行征服和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只不过是它随着资本主义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初期军事占领、殖民掠夺是资本扩张的主要方式,为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和基础。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运动打击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开始瓦解,于是资本主义就开始采用经济渗透和不平等贸易来继续帝国主义殖民掠夺政策。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民族问题形成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他们的民族理论也正反映了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从政治到文化上的转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学的发展道路,因此这一时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后来西方“马克思学”的源头。[12]随着世界范围内地区矛盾和冲突日益频繁,尤其是种族矛盾和斗争成为世界各国突出的问题。尽管不少国家开始采用了民族文化自治理论,但是民族冲突和矛盾依然严峻,民族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是由于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掠夺所造成的民族问题,可以说资本主义扩张和掠夺的本质不变,民族问题本质就不会改变。所以在吸取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教训,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和解决我国民族问题,这是促进民族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和基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揭示了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阐述了民族文化发展和国家统一之间的关系。
四、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合理性调适
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再次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所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所包含的民族自由以及多民族国家统一理论开辟了解决当前民族问题的新途径,它所包含的民族与自由、少数民族的民主与平等权利,民族文化多元化等理论,也成为包括当前“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少数民族权利”问题所讨论的内容。因此对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做出合理性调适,为我们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提供必要的借鉴。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民族与民主制度建设。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国家权力,它主要包括:一是民族在国家中的地位,这在国家中表现为民主问题;二是各个民族之间的外部关系,它表现为平等问题;三是民族对于内部事务的权限,它表现为自治问题。鲍威尔民族文化自治理论正是从民主制度、民族平等以及自治上来解决国家统一与民族自由问题,以希望在不改变帝国权力结构的前提下,实现国家职能、民主制度的转变以及民族自我管理。鲍威尔提出的民族理论固然不能解决奥匈帝国的民族问题,但是他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与结构下对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调整以及民族文化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对于当前解决民族问题,维护国家统一提供了一种尝试和选择。鲍威尔指出,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把一种民主制度从抽象的法律意义变为民族成员的生活意识和观念,把政治制度“实体”意义上的民主转变为生活“主体”意义上的民主。这包括尊重民族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既在国家法律层面上具有它的实体意义,又在生活层面上实现民族成员的自觉性与主体性。
其二,民族文化与自主性。鲍威尔通过对资本主义本质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分析,批判了民族国家制度,这对于我们摆脱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窠臼,发展民族文化自主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当前世界的民族运动浪潮对于我国的统一以及民族问题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鲍威尔的民族国家批判理论使我们能够认清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与本质,从而坚持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西方民族国家模式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它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和需求而产生的。这种国家模式具有西欧地域性,在性质上是属于资产阶级。当前诸多国家中的民族问题从某方面来讲并不是由于国家制度造成的,而是由于民族-国家制度所引起的。第二,民族国家的本质是和资产阶级利益以及资本的本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确立以后,民族国家就由追求自由与民主开始转变为资产阶级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手段,它一方面在国内力图避免使用民族国家理论以引起民族独立运动,从而威胁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大力宣扬民族国家理论,以排斥其他国家保证自己的最大利益。另外它还是瓦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利器,从而控制更多分裂出来的民族国家,最终获得更多的殖民地。当前不少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就是误入了西方民族国家理论陷阱而成为这一理论的旗鼓手。第三,民族的非地域原则。当前社会条件下,以固定的区域、语言无法作为区分民族的依据,况且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文化上的融合也使得民族之间越来越难以区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调民族地域划分,一方面容易在这一区域内形成新的少数民族而造成“多数倒置”问题;另一方面,民族独立分子把区域内的自治作为谋取国家主权的跳板,从而在自治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形成独立的要求。民族非地域原则取消了民族地域性的本质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划分的地理基础。因此重新审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就成为新时代条件下维护国家统一以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必然和现实要求。
[1][2][3][4][5][7][8][9]Otto Bauer,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and Social Democrac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1,p318,p320,p283,p288,pxvii,p25,p356,p222.
[6]Karl Renner(1899),State and Nation,in National Cultural Autonomy and its Contemporary Critics,Ephraim Nimni(Edt.),Routledge,New York:2005,p28.
[10]列宁全集[M].第 2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63-263.
[11]列宁全集[M].第 2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36.
[12]姚顺良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25.
A8/D562
A
1671-4288(2017)03-0077-05
2016-12-09
国家民委后期资助项目“奥托·鲍威尔民族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16-GMH-003)阶段性成果。
王幸平(1973-)男,山东菏泽人,潍坊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王家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