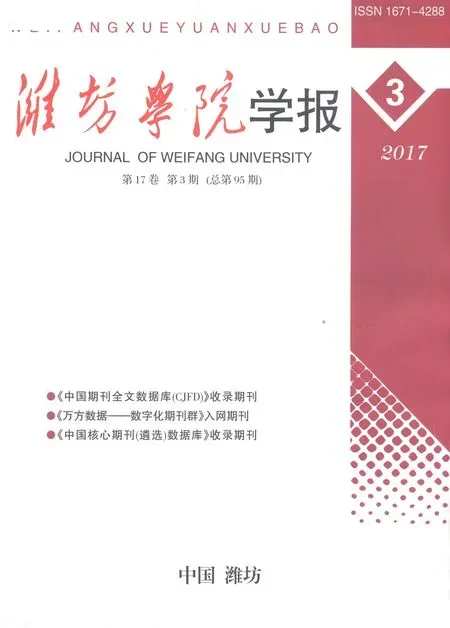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辗转腾挪
——论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
王恒升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辗转腾挪
——论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
王恒升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迄今为止,莫言共创作了十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形式上各种各样,艺术表现方法多姿多彩,但写作内容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历史,一个是现实,莫言总是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辗转腾挪。这一点,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学高度一致,而且表现出了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崇尚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高尚追求。
长篇小说;历史;现实;辗转腾挪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就崇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写出了众多彪炳史册的宏大巨著。考察这些恢弘著作的写作内容,无外乎两个,一个是历史,一个是现实。历史与现实构成了传统文学的主要内涵。它们共同为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自新文学以降,文学的表现内容有了极大的丰富,出现了远如武侠、言情,近如玄幻、穿越的创作,但占据文学主流的,依然是以历史和现实为写作对象的作品。绝大多数作家仍然在历史和现实两大传统领域精耕细作,辛勤耕耘。莫言即是其中之一。迄今为止,莫言共创作十一部长篇小说。虽然从创作理念和文本形式上说,莫言的作品和传统文学有较大的出入,它吸收借鉴了一些西方现代派的东西,继承学习了一些传统的东西,更融合创新了一些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的新形式、新方法、新手法,但就内容而言,仍旧没有脱离历史和现实两大题材。他的创作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但仔细品味,就不难发现,他只不过善于在历史和现实之间辗转腾挪,就自己感兴趣的某个历史话题或某种社会现象,要么做出富有深度的历史探究,要么做出富有卓见的现实评判,或者,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从历史的深处追寻现实的场景,从现实的存在探掘历史的根由。
一
莫言纯粹将历史作为小说内容的,有三部作品,它们是《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和《檀香刑》。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应该从构思到结构都浑然一体,是作者才华、能力、经验、思想、精神、技术、身体、耐力的一次完整的体现。而《红高粱家族》不是。它是由5部中篇小说联袂拼接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虽然说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主题、风格、氛围一脉相承,有明显的连续性,但它确实是在各自独立成篇后又连缀而成的,缺少内在肌理的一致性。《红高粱》是第一部,发表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于是莫言乘胜追击,又连续写了《高粱酒》《高梁殡》《狗道》《奇死》,将一个原本已经讲得很透彻很圆满很凝练也很震撼的故事,稀释成了一部注了水的历史大片。然而,尽管《红高粱家族》结构上让人感到不严谨,风格上让人感到重复,但它透露出来的对于历史本相的还原与揭示,还是让人感到震惊不已。它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抗战历史的传统而简单的认知,拓展了长期以来抗战文学过于狭窄的写作路径,深化了人们对于变化莫测的复杂的人性的认识,开阔了人们的艺术审美视野。不无夸张地说,它与周梅森的《国殇》《大捷》、乔良的《灵旗》等一起,改变了当代战争文学在题材、主题与艺术表现等方面的固有走向。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抗战文学应如《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高举着民族大旗,张扬着民族大义,彰显着正义主张,鸣响着胜利号角。尤其是在歌颂胜利者的光辉形象中,人民军队及其它的领导者,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规律,是被历史所深刻证明了的。但是,这不是全部。在14年的抗战史中,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游击战争,也有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还有民间自发的各式各样的抗战。总之,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每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无论什么背景,出于什么考量,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其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多姿多彩的民族抗战却被诠释成了一种单一政党领导的抗战,没有得到全面地艺术展示。久而久之,抗战历史也就成了一种残缺不全的历史,或者说,成了一种被过滤了的净化了的历史。显然,这样的历史不是历史的全貌,不利于全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轻装前进。任何时候,对历史的正确态度都应该是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莫言,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有了表现土匪抗战的《红高粱》及其家族。莫言曾说:“写土匪抗战,事实上也是有一点历史根据的。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的胶东地区冒出了几十支游击队,一帮土匪摇身一变,树立一个旗号,我不是土匪了,我是抗日游击队,实际上还是按照过去的生活方式在生存。”[1]还说,土匪“本来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他们也是破坏社会安定的力量。”“只有到了要么是饿死要么是被敌人杀死的时候,才会奋起反抗。”[2]《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就是在日本鬼子侵占了家乡,原本自由自在的生活空间被逼仄到无法生存的状况下,才愤然举起了抗日大旗。虽然这种自发的抗日行为多半会因为没有正确理论和正确政党的指导,不会长久,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抗日形势。余占鳌的所作所为,也不会因为有了抗日行动就会消弭半点匪性,他后来的经历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它毕竟是一种可歌可泣的抗日行为,是一种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爆发,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的原始生命追求,应该值得肯定。莫言通过对家乡抗战历史的挖掘,揭开了历史的厚重帷幕,发现了土匪抗战的历史史实,认识到了它们蕴藏的巨大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将它们真实地再现了出来。不但丰富了抗战文学的题材,繁荣了抗战文学的英雄人物谱系,打破了读者原有的阅读期待心理,升华了读者的审美情趣,而且更重要的是,将历史追索推向了纵深,引领了新时期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隆隆前行。难怪王彪编选《新历史小说选》和张清华写作《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时,都把《红高粱家族》看作是“新历史小说”或“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直接出发点之一。
《食草家族》是一部秉承着《红高粱家族》写下来的小说。从风格到内容再到形式,几乎如出一辙。就风格而言,《红高粱家族》就有溢丑现象。其中对罗汉大爷被日寇残忍剥皮的描写,对余占鳌往酒里撒尿偶得佳酿的描写,对麻风病人的肮脏描写,对井底的癞蛤蟆和毒蛇的可怕描写,对狗吞人尸、人食狗肉的无奈描写,对高密东北乡人的几个高度鲜明的对比概括,尤其是描写到这些细节时,莫言表现出来的细致从容,津津乐道,无不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到了《食草家族》,这种溢丑现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但详细描写了乱伦、偷情,而且浓墨重彩地描画了大便,超出了人们心理所能承受的极限。就内容而言,《红高粱家族》除了反映民间抗战,还有一个很突出的内容,就是讴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蓬勃生命。甚至相对于抗战,讴歌生命强力、张扬生命本质,是一个更加光彩夺目的内容。这一内容到了《食草家族》中,又有了新的表现。如果说《红高粱家族》主要是从“我爷爷”“我奶奶”不受羁绊、为所欲为的浪荡行为,歌颂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把种的退化作为隐线处理的话,那么,《食草家族》则是通过四老爷、九老爷年轻时生命力旺盛,八九十岁了依然精神矍铄,来映照食草家族的后代们因为长期脱离土地,而导致的生命力孱弱、脚上普遍长蹼、出现逆生长的现象,把种的退化作为主要内容来描写。通过对种的退化的神奇描写,反衬了自然伟力的强大。就形式而言,《红高粱家族》是一部虚构的家族史小说,是以“我”的视角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传奇人生。《食草家族》也是一部虚构的家族史小说,也是以后辈的眼光来评述前辈人的故事和后人的生活。在结构上,《食草家族》如同《红高粱家族》一样,也是一部狗尾续貂式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是先有中篇《红高粱》,然后才有其他。《食草家族》是先有中篇《红蝗》,然后才有其他。而且都在第一部中,把想说的都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对读者而言,读了第一部,不读其他几部,都几乎不会留有什么遗憾。
如果说,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把艺术视角伸向了曾经被遮蔽的历史,在《食草家族》中,又将艺术视角伸向了荒诞不经的民间野史,那么在《檀香刑》中,他把历史事实和艺术想象巧妙地架构在一起,展现了一部惨烈的酷刑文化史。孙丙抗德事件,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事的。1900年,高密人孙文率领乡民以德国人修筑胶济铁路给当地民众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为由,同德国人及其清政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不幸壮烈牺牲。孙文的抗德行为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胶济铁路的既成事实,但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乡民的利益,迫使德国胶澳总督和清政府改变了原先的设计线路,更多地预留了铁路桥梁和涵洞,不致高密西部低洼区壅水成患。更重要的是,在当时那种列强环伺、觊觎我邦的情况下,孙文领导的高密人民的抗德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伟大反抗精神。虽然这一历史事件到了小说中,孙文被改称孙丙,并且为了增加小说的艺术趣味和阅读噱头,将孙丙写成了一个失落的戏子,头脑中不乏愚昧的想法,行为中不乏滑稽的举动,甚至有些懵懂傻逼,分不清戏里戏外,但抗德初衷和抗德行为还是基本符合历史真实的。当然,莫言写《檀香刑》,绝不是为了再现这一历史事件,而是借助这一历史事件,展现中国历史上的酷刑文化。酷刑,是指对一个人故意施加的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任何使他在肉体上或精神上极度痛苦的惩罚。酷刑自古就有。愈往人类历史的深处追溯,酷刑的程度愈烈。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施行过酷刑,中国也不例外。也许是因为历史更悠久、更动荡、更反复无常,中国较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在使用酷刑方面更惨烈,更骇人听闻。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酷刑很多,诸如凌迟、梳洗、剥皮、烹煮、车裂、刖刑、宫刑、幽闭、腰斩、缢首、灌铅、抽肠、活埋、杖杀、骑木驴、俱五刑、剜鼻、株连等,每一种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著名的酷刑案例,如秦始皇坑儒、李斯遭腰斩、商鞅被五马分尸、孙膑遭刖刑、司马迁受宫刑等,每一种想起来也都令人不寒而栗。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鲁迅先生曾感叹:“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或异族屠戮,奴隶,敲诈,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3]虽然越到后世,文明程度越高,对肉体实施的酷刑越来越少,但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一部厚重的酷刑文化,况且这种酷刑文化有越来越演变成精神枷锁的趋势,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来继续摧残中国民众而已。酷刑文化在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心灵史上,产生了严重的心理暗影。《檀香刑》总共写了六次行刑过程,可谓是对酷刑文化的高度凝练。其中,“阎王闩”和“檀香刑”是莫言通过艺术想象虚构出来的,虽然艺术象征的意味大于实际操练,但残酷的本质却与历史上的实有酷刑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檀香刑》所阐发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讲述几次酷刑刑术的执行过程,而在于通过刽子手赵甲的口吻,来讲述酷刑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行刑人的心路历程,从一个更独特的层面上,展现了酷刑文化的丰富内涵。在赵甲看来,他研究、发明、实施任何一种酷刑,都不只是用来结束一个人的自然生命,而是用来宣示皇家政权的至高无上和不容冒犯的威仪,以及自己这一职业在维护皇权统治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此一来,他精心创造的“檀香刑”,就不是一项单纯的酷刑刑术了,而成了一个酷刑文化的象征性、标志性、隐喻性符号。
历史是什么?是教科书中明确记载的文字,还是民间口口相诵的传说?是一种既定的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与本质的所谓的真实印迹,还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认识。同样,文学对于历史的艺术反映,也会有不同的回声。可以说,莫言关于历史题材内容的写作,回应了这些认知。
二
莫言关注现实内容的长篇小说,有四部,它们是《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红树林》。白居易曾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莫言创作上述四部小说,无不是感时抚事。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完整构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在这之前,《红高粱家族》已经出版,但它是由五部中篇联袂而成的,缺乏前后一致的贯通。《天堂蒜薹之歌》的写作时间极短,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莫言一气呵成。莫言之所以写得快,与两件事情对他的强烈刺激有关。一件事情是1987年夏天发生的震惊全国的“苍山蒜薹事件”。当时,由于一些领导干部不作为,又加上地方利益保护主义思想作祟,致使农民丰收的蒜薹卖不出去,大面积烂在地里。农民一气之下,用蒜薹堵了县政府大门。农民想见县长,希望政府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农民负担。但政府官员避而不见,导致农民采取了更激烈的行动。农民冲进县政府,砸毁了县长办公室,焚烧了政府办公大楼,一时间舆论大哗。后来,事件虽然得到妥善处理,政府干部要么被撤职,要么被降职或调走,领头闹事的农民受到法办,但事情的前因后果产生的冲击波对莫言影响很大。说到底,莫言那时虽已远离乡村,身栖京华,但他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农民,他对一切漠视农民利益的行为都深恶痛绝。所以,当他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后,马上就萌发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曾说:“我看了这个报道以后,内心马上就很冲动,当时感觉到是想替农民说话,实际上我是替自己说话。直到现在我一直认为自己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1987年我更感觉我就是一个农民,家里都是农民,农村的任何一个事情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我写《天堂蒜薹之歌》,实际上是把我积压多年的、一个农民的愤怒和痛苦发泄出来。”[4]另一件事情发生在1984年10月,莫言的四叔被乡镇书记的汽车撞死。当年,莫言的四叔和亲家一起往县城送甜菜。返回的路上,被给书记拉盖房材料的汽车撞死,连同已经怀孕的拉车的母牛也一起撞死。虽然那个书记和莫言一家还沾亲带故,但最后处理事故的方式和态度却让莫言很不满意。3500元钱就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两头牛打发了,而且扬言,即便是打官司让交通队处理,交通队也向着他们。莫言听说这事后,气愤不过,想把事情闹大,希望死者和死者的家属得到起码的尊重。但是,由于死者的孩子们不争气,根本不看重死去的父亲,看重的是到手的钱财,再加上父母等人的反复劝阻,莫言最后才放弃了抗争。然而,尽管不再争执,但农民生命贱如草芥这件事,仍然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莫言的心头,让他久久不能释怀。这次,“苍山蒜薹事件”再次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使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便想用笔来表达对农民的怜悯和同情。在小说中,莫言将以上两件事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反映了农民的生活现状,揭示了农民的悲哀、愚昧、让人可怜可叹的思想状况,又揭露了领导干部的不作为,抨击了愈演愈烈的官僚腐败作风,表现出了强烈的干预现实的创作态度。莫言写这部小说时,正值新历史小说创作风生水起,而他作为领头人之一,毅然从历史的深处折回身来,写出这样一部充满人生苦难和现实窘况的小说,不能不说表现出了巨大的敢于担当的勇气。小说的艺术也很高明,它不仅具有鲜明的写实风格,透露着严苛的批判精神,而且在叙述方式、艺术结构、语言表述等各方面,做了迥然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形式的探索,形成了一种整体时空统一而局部时空错乱、于严谨中又透露着活泼的别具一格的小说形式。
紧接着《天堂蒜薹之歌》,莫言又写了《十三步》。应该说,《十三步》的内容很有现实意义,它写的是教育问题,触及了社会弊端,反映了社会矛盾,尤其是把教师放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艺术关照,其凸显的社会意义就更加显著。教育问题,一直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问题。教师的待遇问题,或曰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一直是诸多社会问题中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谌容的《人到中年》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就是因为她写了知识分子问题,反映了刚从“文革”中跋涉过来、仍处在拨乱反正中的中年知识分子艰窘的生存状况,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共鸣。莫言写作《十三步》时,虽然陆文婷、傅家杰遭遇的不受社会重视的尴尬现象有了很大改观,但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压力大、经济困难的现状,依然严重地存在着,它们依然是教师从教道路上的拦路虎。《十三步》讲的主要就是这一内容。中年物理教师方富贵活活地累死在讲台上,另一教师张赤球为了摆脱贫困,让殡仪馆整容师给他改头换脸、一门心思挣大钱。但现实是残酷的,一个称职的老师未必是一个称职的生意人。张赤球空有发财梦想,却无实际经营之道,因此,他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一番之后,不得不灰溜溜地以失败告终。当年,经济双轨制改革启动以后,有多少人怀揣发财梦想,毅然下海经商,又有多少人被无情的经济大潮拍死在了沙滩上,落了个人财两空。张赤球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的心理和行为,是当时一批一心想逃离传统体制约束、实现发财之梦的人的形象写照。如果塑造好了,张赤球也许会成为又一个陆文婷式的艺术典型。但遗憾的是,莫言根本没有把精力放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而是本末倒置,放在了如何讲述故事上,将艺术表现手段当成了小说写作的终极目的,浪费了一个绝好的描绘社会巨变的现实题材。在《十三步》中,莫言沉溺于多个人称的叙述实验,在“你”“我”“他”、方富贵、张赤球、李玉蝉、“蜡美人”等叙述主体的频繁转换中不能自拔,不仅没有矗立起任何一个人物形象,而且连最基本的人物赖以存在的故事情节都没有交代清楚。也许,莫言把希望寄托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希望通过读者的二度创作把作者故意打碎的生活片段连接起来,实现人物形象的再塑。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读者的二度创作是建立在作者的一度创作的坚实基础之上的,而且是建立在一度创作开启了读者的思维空间,让读者拥有了更高、更阔大的思考平台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一个毫无头绪的非理性的语言迷宫里,让读者找不着北。莫言之所以如此写,显然受到了当时风靡文坛的先锋文学思潮的影响,滑入了“怎么看不懂就怎么写”的泥淖。莫言自己后来都感叹:“《十三步》这部小说我想真正看懂的人并不太多,确实写得太前卫了,把汉语里面所有的人称都实验了一遍。”[5]
同是先锋小说,《酒国》的实验比《十三步》要理性很多,也成功很多。《酒国》聚焦社会腐败问题,比同样是反腐题材的如张平的《抉择》《十面埋伏》等直面现实的官场小说,其讽喻性、穿透力也更强烈一些。《酒国》写的是一个叫酒国市的地方,已经腐败到了烹食婴孩的地步。高级检察院的特别侦察员丁钩儿奉命去侦破此案,没想到却深陷其中,被腐败分子同化。最后,丁钩儿掉入一个巨大的茅坑被淹死,实际上象征的就是曾经对腐败深恶痛绝的他,再也回不到清白之身了。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社会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不仅请客、送礼司空见惯,就是社会道德也每况愈下,全社会出现了久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笑贫不笑娼的奇怪现象。莫言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将它以变形、夸张、荒诞等形式,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如果说,贾平凹的《废都》是通过一个城市的文人们的集体陷落,来形容全社会道德沦丧的话,那么,莫言的《酒国》就是通过一个城市的肆无忌惮的吃喝,来象征全社会无孔不入的腐败。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
《红树林》是莫言从部队转业到中国检察日报以后写的一篇作品,而且是一部先有电视剧后有小说文本的作品。它同样是一部反映腐败的小说,写一个城市的女市长林岚如何从一个渔村少女成长为一座沿海城市的市长,又如何经受不住贪欲、情欲的腐蚀,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虽然其中夹杂着情爱、母爱、错爱和社会遗留问题,但贪腐的主题还是很明显的。可以说,这样的贪腐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不足为奇,相信每一个受审的贪官都能讲出一大串比林岚的故事还要精彩得多的故事。那么,莫言为什么写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主要原因是作为检察日报的工作人员,他要完成这方面的任务。由于他当时还不了解国家工作人员是如何渎职犯罪的,尤其不了解贪官们的心理动因和贪腐轨迹,所以描写起来有模式化、概念化、拼凑化倾向,不像写其他作品那样驾轻就熟,水到渠成。又由于是由电视剧改编而来,情节设置上有明显的桥段化现象,所以又显得不够自然、人性。后来,莫言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我认为写这样的题材应该把贪官污吏当成人来写,从人的角度考虑,从自我的内心考虑,或者说,要把贪官污吏当成‘我’自己来写。在当前的社会机制和法律状况下,假如我变成了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级别的官员时,能不能保持清廉?会不会也跟那些贪官一样变成了人民的罪人?并由此对我们的社会制度进行反思……这里边应该包含着对社会的批判和对于自我的批判,涉及人的根本弱点,和一个存在诸多问题的社会对人的弱点的纵容……”[6]如果莫言真从这些方面来写贪官污吏,也许会塑造出一个令人难忘的贪官形象。
纯粹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不是莫言的强项。这从以上四部小说发表或出版以后的社会反响中就可以看出来。莫言的文学特质是想象力丰富,虚构力强大,如果让莫言写一个莫须有的故事,他便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特质,天上地下,云里雾里,渲染出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但是如果让他感时就事,他便会像老虎关在笼子里,有本事施展不出来。况且,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故事,有的远比人们想象的精彩。
三
莫言还有四部长篇小说,是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要么从历史的深处追寻现实的存在,要么从现实的场景探掘历史的根由,历史和现实互为表里,互相依存,在一个广阔的时空背景上,探索、展现民族和国家的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它们是:《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
《丰乳肥臀》是莫言极其看重的一部小说,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丰乳肥臀》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是他的代表作的意思。《丰乳肥臀》也是一部极具争议的小说,誉者称赞它是一部“通向伟大的汉语小说”、“一部真正具备了‘诗’和‘史’的品格,一部富有思想和美学含量的磅礴和宏伟的作品,”[7]毁者批评它是一部“不顾历史事实”,用“障眼法,用色情、性变态掩盖他的投枪所指”[8]的作品。那么,《丰乳肥臀》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这还要从它的基本品质说起。在新时期文学史上,有一个阶段是新历史小说的天下。所谓新历史小说,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的小说。传统历史小说把历史当作一种既定的客观存在,小说所做的一切,既是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或出现过的人进行还原式讲述,让人们通过小说来了解历史。虽然其中也有虚构,但虚构多发生在细节描写上,对故事的进展和人物的性格无伤大雅。它追求的是所谓的历史的“真实性”。而新历史小说则把历史看作是一种话语形式或文本存在,里面充满了想象与虚构。因为在历史的生成过程中,它深受“讲述话语的年代”的影响,是话语讲述主体在一定的时空场域或意识形态的控制中选择、构造、再塑的结果。所谓的历史的“真实性”,是永远也无法真正还原的。因此,新历史小说家认为,利用小说揭示历史的真相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通过与历史的对话,传达出个人的某些历史认知、历史情绪或历史感慨。基于此,新历史小说普遍呈现出了叙事立场的民间化、历史视角的个人化、历史进程的偶然化、还原历史的欲望化、主题表达的隐喻化、人物塑造的人性化等众多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的新特征。《丰乳肥臀》是一部典型的新历史小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它,也许有些歧义就不会产生。《丰乳肥臀》以上官家的母亲上官鲁氏和儿女们的命运变迁为脉络,勾勒起了云谲波诡的近百年中国历史。如果说,上官鲁氏和几个大女儿的命运主要展现的是中国现代史,那么儿子上官金童的遭遇主要映照的就是中国当代史。百年中国历史,在上官一家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中,演绎得荡气回肠,令人不胜唏嘘。上官鲁氏的悲惨命运,源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人生观。为了生一个儿子,她忍辱负重,一连生了八个女儿,才始得上官金童。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上官金童,从而使得几个女儿如野高梁般蓬勃生长。适逢战争年代,几个女儿为了爱情,各有所靠,又使得她们被各种政治力量所绑架,开始了跌宕起伏的苦难人生。她们一会儿荡上人生的巅峰,一会儿滑入人生的低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治的力量无所不在。上官金童在母亲的百般疼爱下,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能力,终其一生只能吊在女人的奶头上惨淡度日。最后,当母亲去世,又遭遇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开放年代,他无以为继,只好皈依宗教,继续过着吃白食的生活。显然,上官金童的隐喻意义更为突出,一个本没有多少传统基因的“杂种”,欲想在传统浓郁的氛围中生存下来,是何等的艰难!历史的“丑花”终究没有结出现实的“甜果”。
《四十一炮》是莫言对新时期农村改革开放历史的反思与追问。通过亲历者罗小通忏悔式的叙述,把当代中国社会步入市场经济以来农村变革的成与败、罪与罚、光荣与梦想、贪婪与无耻,形象地展示了出来,表现出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强烈的现实批判力度。毫无疑问,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利好变化,这从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可以看到。但也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也给农村带来了一些让人忧虑的副产品。比如,人情的冷漠,人际关系的紧张,欲望的膨胀,以及不择手段地谋求利益最大化带来的道德沦丧和双面人的大量出现。小说中,罗小通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亲眼观察,反映了这一切。如果说,罗小通在五通神庙里向大和尚诉说的关于父母亲、妹妹、老兰、野骡子等的一切话语,是对农村改革开放历史的追忆,那么,他在五通神庙里观察到的一切,就是对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现实的总结。原本善良、朴实、厚道甚至有点不开窍的罗通和杨玉珍在被老兰拖入欲望追求的快车道后,一发不可收拾,朝着欲望的深渊急速滑落下去。虽然罗通最后有所醒悟,虽然罗小通在家破人亡后毅然走上了反叛之路,但是他们都是以付出巨大的代价为前提的。况且,罗小通的反叛并没有起任何作用。他想斩断老兰这棵欲望之根,朝他发射了四十一发炮弹,却发现根本无济于事,老兰照样活得生龙活虎,戾气逼人。十年前,老兰是欲望的始作俑者,十年后,老兰是欲望的收获者。十年前,老兰仅仅是一个屠宰村的村长,充其量兼着村办华昌肉食品公司的董事长,十年后,老兰成了著名的乡村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市政协常委。老兰的不凡经历和前后变化,说明了欲望在改革开放年代展现出的强大的生命力。欲望本无罪,甚至在人类历史上起过进步催化剂的作用,但是如果任由欲望泛滥,它也会成为人类精神的一剂毒药,对生产力产生破坏作用。只不过,徜徉在改革红利中的人们,尚未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莫言用一部《四十一炮》,向人们敲响了警钟。
莫言多次说过,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农民。当然,这不是说身份,而是说情怀。既然莫言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农民,那么他就经常把乡土当作自己的关注对象,把农村、农民当作艺术反映的焦点。继《天堂蒜薹之歌》《四十一炮》后,他又写了《生死疲劳》。《生死疲劳》的时空含量远比《天堂蒜薹之歌》《四十一炮》辽阔,它从1950年1月1日写起,一直写到新千禧年的到来,在长达50年的时间跨度上,全面展现了几代农民的命运变迁,为当代中国农村、农民书写了一部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的传奇大书。同时,从纯粹的农民的情感出发,对当代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与评判。中国农民最在意什么?粗览一下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农民最在意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无论古代任何一次的朝代更迭,还是近代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即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战争,农民和土地都是首先考虑并解决的问题。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了掌控历史变迁的主动权。一部中国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史。就中国当代历史而言,同样存在这个规律。哪个阶段农村和农业政策把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理顺了,农民就会心情舒畅,社会就会发展,哪个阶段出现了偏差,农民就会怨声载道,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莫言发现了这个规律,并通过《生死疲劳》活画出了一部当代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史。他曾说:“几千年以来中国改朝换代,农民起义,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土地。土地兼并再均分,反反复复。1949年之后,农村的变迁实际上还是土地的问题……根本问题就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9]
《生死疲劳》中的人物,无不为土地生,为土地死,为土地而“生死疲劳”。其中,“单干户”蓝脸给人印象最深。他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改运动,历经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直到改革开放,都坚持单干,以不变应万变,与时局赌博,迎来了一个土地政策的轮回。《生死疲劳》中的洪泰岳,也是一位极具典型化意义的农民形象。如果说,蓝脸传达出的是传统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那么洪泰岳传达出的就是新型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这种新型农民,是在党领导的农村革命道路上萌芽的,在党指引的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上成熟的,同时又是在党的农村土地政策改弦更张之后变得冥顽不化的,某种程度上,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化身、坚定的执行者和后来的陌路人。他与坚持单干的蓝脸一样固执,不过他执着的是集体化道路。现在看来,如何评价坚持单干的蓝脸和积极入社的乡亲们在那个时代的选择孰是孰非,已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形象地诠释出了农民对建国后土地政策的鲜明态度,成了后人认识那段历史的最好的见证人。
在莫言自己的历史记忆中,给他留下最深刻最惨痛印象的莫过于计划生育政策了。同时,这也是共和国历史上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一段印记。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处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和对未来的发展考虑,国家开始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虽然独生子女政策在一定时间内缓解了人口爆炸带来的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但从长远看,也存留了许多隐患。造成劳动力缺乏固然严重,而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养老问题、教育问题、承担灾难问题乃至民族素质问题等等,则更加让人忧心忡忡。否则,国家也不会一再修改计划生育政策,不断增加人口生育数量。但即便如此,计划生育仍然在几代人身上留下了终生难以抹去的隐痛。莫言是其中的一个。莫言本来可以和老一辈人一样,享受儿孙满堂带来的欢乐,但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却使他不敢越雷池一步。个人的惨痛记忆和民族、国家的历史融合在一起,不时地揉搓着他的心,促使他最终写出了全面反映计划生育政策的《蛙》,将计划生育政策的来龙去脉以及给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造成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形象地描述了出来。其实,莫言对计划生育的思考,早就开始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在计划生育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就写了短篇小说《爆炸》《弃婴》《地道》,从不同侧面对计划生育进行了艺术反映,显示出了一个有良心的作家对事关国家、民族大业的大事小情的拳拳之心。
在《蛙》中,莫言并没有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一味地抨击计划生育政策,而是比较理性的阐释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诞生与实施过程,让不明事理的人了解了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从小说中的“我”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三封信中完全可以看出来。当然,如果莫言仅仅是站在国家的层面上,以政府代言人的身份解释计划生育政策,那《蛙》是完全没有可能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写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同身份的人迥然不同的心路历程,以及后来人们对它的深刻反思。其中,“我”和姑姑的形象比较有代表性。“我”是一个计划生育的受难者,原配妻子死在引产的手术台上,续弦妻子又不能生育,“我”只好通过非法的手段来获取子嗣。虽然一开始“我”不知道实情,但当知道了陈眉代孕的孩子是自己的骨肉时,“我”便不择手段地同陈眉争夺了起来。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高知县谬断婴儿案。孰是孰非,历史留下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姑姑是计划生育的坚定执行者,在长达三十多年的从医经历中,经她之手做掉的婴儿达二千八百多个。然而,到了晚年,她却违背伦理,怂恿“我”占有非法出生的婴儿。同时违背初衷,在自己的家里捏了二千八百多个泥娃娃,祭奠那些被她亲手做掉的婴儿。如何理解姑姑前后心理和行为的巨大反转,也只有从她年轻时爱情的不幸遭遇、执拗的性格、严酷无情的政治压力和人性本质的软弱入手,才能看得清楚,而这些,又包含了怎样丰富多彩的历史和现实内涵。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总有一根剪不断、理还乱的纽带。莫言顺着这根纽带,游走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尽可能地对国家、民族走过的一段路程,以及结出的现实果实,进行形象地评说。其目的,无非是认清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
以上,我们对莫言的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了一次回眸式巡礼,足见莫言秉承了中国文人的道义意识和担当精神。当然,这只是从内容上而言。在艺术上,莫言并没有拘囿于传统文学的窠臼,而是广采博取,为我所用,创造了一个斑斓多彩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为道义意识和担当精神增光添彩的,也有达意未尽的。个中缘由,上文已做过简单交代,在此不再深入分析。
[1][2][4][5]莫言.在文学种种现象的背后——2002年12月与王尧长谈[M]//莫言对话新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75,74-75,79,81.
[3]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0-181.
[6]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2002年与大江健三郎、张艺谋对话[M]//莫言对话新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496.
[7]张清华.叙述的极限[J].当代作家评论,2003,(2).
[8]彭荆风.视角的瘫痪——评《丰乳肥臀》[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5).
[9]莫言.重建宏大叙事——与李敬泽对话[M]//莫言对话新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305.
I206.7
A
1671-4288(2017)03-0014-07
2017-03-16
王恒升(1964-),男,山东潍坊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