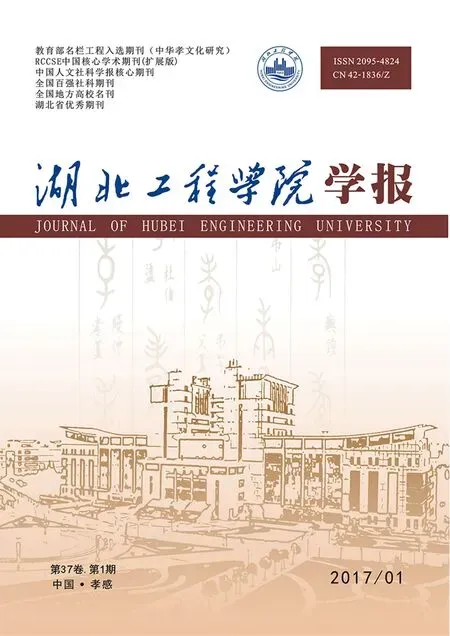鲁迅对民间文学之“民”的敬重
陈祖英
(1.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2.福建行政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鲁迅对民间文学之“民”的敬重
陈祖英1,2
(1.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2.福建行政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将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鲁迅所讨论的民间文学之“民”,是与士大夫、知识分子相对的不识字的劳动人民。由于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鲁迅对浙东农村有切身的感受,对民众充满敬意。对于民间文学,鲁迅不仅具体礼赞其“清新刚健”的风格,还借鉴民间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创作。虽然他认同并敬重“民”,但他自己并不是民众中的一员,他似乎想在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达到“立人”之目的。
鲁迅;民间文学;民众;敬重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民间文艺学者。在民间文艺学方面,鲁迅“不但具有浓厚兴趣、深湛教养,而且具有极光辉的见解, 留下了大量的、可贵的文献。即使鲁迅生平没有上面所述的多方面的优越成就, 只有民间文艺学方面的这些活动和贡献, 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的学者,他在我们学艺史上的位置也是不容忽视的”[1]。对于鲁迅的民间文学观以及他在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很多学者都进行过深入的论述。本文拟从鲁迅的民间文学观入手讨论以下几个问题:鲁迅是如何看待民间文学之“民”的,他与同时代的学者对待“民”的认识有什么不同,他对“民”的态度对我们今天所从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什么启示意义。
什么是民间文学?中国民俗学之父、民间文艺家钟敬文先生是这样界定的:“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劳动生产、日常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2]到底谁是民间文学之“民”,这一直是民俗学家和民间文艺家所讨论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对“民”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胡愈之把“民”视为民族全体(《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1921年7卷1号);《歌谣周刊》(1922年12月17日在北京大学创刊,由周作人、常惠主编),把“民”看作国民;《民俗周刊》(1928年3月创刊,由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编印,钟敬文、容肇祖、刘万章、杨成志等先后担任编辑)宣称“民”是平民或民众;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50年3月在北京成立)确定“民”为劳动人民;钟敬文(1903-2002)把“民”看作有具体差异的全民族。[3]通观鲁迅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述,他所说的“民”是与士大夫、知识分子相对的不识字的劳动人民(或称工农大众)。以往的鲁迅研究者们在谈及鲁迅对民众的态度时,主要是根据其小说创作,讨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分析阿Q、祥林嫂等“民”的悲剧,以凸显鲁迅对“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摩罗诗力说》)的态度。如果结合鲁迅先生对民间文学的阐释,我们就会发现,鲁迅对“民”是满怀尊重和大爱的,这源于他的“立人”思想,源于他那颗拳拳赤子之心,也只有把这些劳苦大众当作普通平等的“人”来敬重和深爱,才会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情。鲁迅的同代人胡适、周作人等,他们也提倡“白话文学”和“民间文学”,但“民”对他们而言是想象的他者,是落后的愚昧的需要知识分子启蒙的对象。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鲁迅对“民”的尊重与同情时,才能真正体会到鲁迅的伟大。
一、鲁迅对“民”的敬重
鲁迅对“民”的敬重,首先表现在他对“民”的敬意和对民间文艺创作的肯定。这里的“民”是相对于士大夫而言的。鲁迅所敬重的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4]。在敬重“民”的同时,鲁迅对民间文学的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将一直被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学士所轻视的民间文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多次肯定其首创精神和积极作用。他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5]他提醒人们注意:“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6]15鲁迅将劳动人民称为诗人和小说家,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封建文人看来,民间文学是“下里巴人”,不能登大雅之堂。虽然在《礼记·王制》中就有周代“采诗”和“陈诗”制度的记载,《汉书·艺文志》中也提到采录民间口传作品的“稗官”,历代官府和文人都或多或少地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过不同程度的采集和评论,但统治阶级采集民间作品是出于政治目的,骨子里对劳动人民是鄙视的。与鲁迅同时代的文人,讥笑民间文学荒诞粗鄙的不在少数,即使在当今社会,真正从内心深处尊重劳动者、肯定民间文艺的人又有多少呢。因此,我们现在重新梳理鲁迅对民众的态度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鲁迅对“民”的敬重更表现在他对“民”的缺陷以及民间文学的局限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众所周知,鲁迅从不避讳国民劣根性的存在,不过,鲁迅不仅看到了民众麻木、愚昧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勤劳、善良的一面;他既看到民众的聪明与智慧,也看到他们的弱点和局限。如在批评“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时,鲁迅指出,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但“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7]联系到他创作小说的目的——“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联想到他在“怒其不争”的同时“哀其不幸”,这些都表明,鲁迅希望民众觉醒与强大,从而也让我们感受他在作品中所寄寓的对民众深深的爱。
同样的,鲁迅在肯定民间文学的同时,也看到民间文学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局限性。比如,鲁迅提到由于劳动人民不识字,但可能间接接受一些统治阶级的思想,反映在民间文学上便存在一些虽出自劳动人民之口,却以统治阶级的思想为思想的口头作品。鲁迅对于这类作品中非民众的思想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把它们与真正的民间文学作了严格的区别。对于民间文学在艺术上的粗糙、表现方法的低下等不足,鲁迅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提出要对其进行积极的改造。
二、鲁迅与“民”的渊源
鲁迅对“民”的敬重源于他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他所受的浙江民间文化的滋养。比如,他对保姆长妈妈的敬意:这位连名字都没有的长妈妈曾用自己辛苦挣来的有限工资给鲁迅买书,满足了他儿时求知的渴望;再比如,对农村小朋友的回忆和敬意:在外婆家,一大群纯朴善良的农村孩子陪他一起做游戏,送他去看社戏。这样的生活经历让鲁迅有机会接近农民,了解和认识农民。鲁迅从幼年起就喜爱听祖母和长妈妈讲民间故事和传说,而且还喜欢收集、描摹民间绘画,看民间社戏,对目连戏中“无常”和“女吊”的形象更是念念不忘。广泛接触民间文学的经历,自然培养了鲁迅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后来由于家道中落,鲁迅受尽了奚落和侮辱,感受到世态炎凉,也让他更清楚地看到社会的复杂性,看到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由于鲁迅的底色是对广大民众的爱,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他非常注重维护劳动者的尊严,敬重下层民众的智慧和他们的创造。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他谈到了自己对农村社会的感受。他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8]这种亲身经历和直接体验,可以说是鲁迅理解并尊重民众的基础。
鲁迅少年时代在农村的经历和体验,在浙东民间文化滋养下对民间文化精神蕴涵的深刻感悟,加深了鲁迅和劳动人民在精神上的联系,以致后来鲁迅自觉地倡导民间文化,学习民间创作中的长处。“这不仅仅由于他作为一个文学家,需要借鉴民间创作,更不可忽视的是,他热爱人民,自觉地站在劳动人民一边。”[9]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比较一下鲁迅与同时代的那些提倡民间文学的学者对待“民”的态度。鲁迅虽然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但由于家庭变故,他跟广大工农大众有比较多的接触,他体验到了真正的民间生活。当时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于革命的目的,也非常重视民间文学,他们利用民间文艺形式宣传革命思想,以争取民众的支持。这样的出发点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在谈及民间文学时,是远离民众的,与“民”是有距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户晓辉指出,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初期,“民”的概念“既包含被理想化了的农民等下层阶级,也包含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想象和自我认同的形象,同时还混杂着‘民族全体’的意义指向(至少在精神象征上被认为是如此)”[10]。笔者认为,鲁迅的“民”指的是那些他从小接触过的不识字的普通工农大众,他的“民间”是他切身感受过的浙东民间。与那些传统士大夫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同,鲁迅是以“我们”的姿态和“民”站在一起,是认同民众的情感的。
三、鲁迅对“民”的赞扬与维护
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最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宝库,其创作主体是以“不识字”的劳动者为主的下层民众。鲁迅通常是在具体的比较研究中赞扬劳动人民和他们创造的民间文学的价值的。首先,鲁迅认为文学起源于劳动,充分肯定劳动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鲁迅关于文艺起源于劳动的学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不断思考的结果。早在1908年,受西方人类学派的影响,鲁迅认为神话起源于初民们对解答使人惊奇的自然现象的想象。在1925年出版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书中,鲁迅认为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在1935年出版的《门外文谈》一书中,他明确地提出文学起源于劳动。他说:“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6]1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 “民”的推崇与敬爱。除民间文学外,鲁迅对民间艺术、民间技术乃至民间文化都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比如,他说汉人古刻“气魄深沉雄大”,认为唐人线画“流动如生”。[11]他称赞制造玩具的手艺人是天才,将社会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归于广大人民,认为“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12]。
鲁迅不仅礼赞“民”在民间文艺方面的杰出创造,更是身体力行地做了许多民间文学艺术资料的辑佚工作。在1913年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13]中,鲁迅曾建议成立“国民文术研究会”,负责搜集、整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资料。鲁迅不仅回到家乡搜寻绍兴的传说故事,辑成《会稽郡故事杂集》(1915),还翻译介绍了许多外国的民间故事传说,如翻译了高尔基以民间传说故事为题材的《俄罗斯的童话》(1935);他不仅通过纸质文本进行搜集,如从《太平广记》《艺文类聚》等古籍类书中整理出大量古代的民间神话、传说和故事,还留心并及时记录当时在民间口头流传的活态文本,如他在教育部任职时随手记录下同事口中吟唱的六首儿歌;他不仅收集整理民间文学的材料,还收集包含古代神话、传说和社会风俗画像的汉唐石刻、民间木刻等民间艺术。从鲁迅留下的宝贵资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劳动人民的敬重,对民众所创造的文学艺术的尊重及维护。
其次,鲁迅具体分析了民间文学“清新刚健”的艺术风格。从思想内容上看,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真情实感的抒发,是“心志郁于内”[14]的真情表达。如《笑林广记》里的一则笑话,属鼠知县的寿辰,属员们集资送他一只金鼠。没想到知县得陇望蜀,暗示明年是夫人的生日,夫人属牛。笑话三言两语,用夸张诙谐的构思概括了一位官员狡黠、贪得无厌的丑恶嘴脸,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对统治阶级的鄙视。从艺术样式上看,民间文学的体裁形式多种多样,神话、传说、童话、笑话、山歌、谣谚、小戏等,这些不拘格套的体裁正是民众生活丰富多彩的体现。从语言表达上看,鲁迅直言“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15],虽比不上士大夫文学的细致,但那些士大夫文学家在语言表达上未必能做得到刚健清新。如民谣“匪是梳子梳,兵是蓖子蓖,军阀就如剃刀剃,官府抽筋又剥皮”,用老百姓的日常工具打比方,抒发了在兵匪官绅压迫剥削下,劳动人民心中的愤慨之情,既形象又简洁。
鲁迅不仅通过与作家文学的比较来突出民间文学的“清新刚健”,表达对劳动人民艺术创造才能的赞赏,更直接通过与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包括知识者的面目)的对比来显示对民众的敬重。如他在《二丑艺术》中对浙东一处戏班中的“二花脸”(即二丑)的描述,这是一类倚靠权门凌蔑百姓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在帮闲的同时又想遮掩自己的真面目。他们软弱、卑劣又残忍的腐朽性格,自以为通过揭露主人的缺点得以掩盖,殊不知老百姓早已看透了他们,并创造了角色,让他们出现在戏台上。可见,鲁迅在他的作品中解剖的国民的种种劣根性,针对的不是大众而是庸众,对于民众群体中的优秀品质,他是极力赞扬并表示钦佩的。
四、鲁迅对民间文学的辨析与提升
鲁迅不仅研究民间文学,肯定劳动人民的文艺成就,还积极学习和借鉴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进行创作,学者们对此已有诸多论述,如刘玉凯《论鲁迅的创作与民间文学》(《山茶》1981年第1期)、林平《浅谈民间文学对鲁迅的影响》(《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第2期)、朱晓进《鲁迅与民俗文化》(《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10期)等。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可看到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的优秀元素在鲁迅的作品中熠熠生辉。但鲁迅毕竟不是民间文学家,他借用神话传说等题材所创作的作品(如《故事新篇》)也从来没有被人们视为民间文学,甚至由于鲁迅善于吸取古今中外各种艺术营养为我所用,以至于有些人根本看不出民间文学对鲁迅创作的影响。鲁迅通常会对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进行融化翻新,联系现实,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鲁迅更善于学习民间文学的艺术手法,取之长避之短,为自己的创作服务。在某种意义上,鲁迅是一座连接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桥梁。他将“不识字的作家”介绍给读书人,让读书人知道“从唱本说书里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16],希望他们能平等对待民众并向民众学习;同时,他将民间文学的诸多元素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一方面给其他读书人学习民间文学提供范例,另一方面也期待“不识字”的民众识字后能阅读丰富的民间文学,接触民俗文化。而这些都是建立在鲁迅对“民”敬重的基础之上的,是他的“立人”思想的具体体现。
鲁迅在运用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进行创作的同时,也注意维护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的纯粹性。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民间文学更是从民众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真实地反映现实,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统治阶级在禁绝扼杀不了像风一样流传的民间文学的情况下,便采取篡改和伪造的手段来破坏民间文学的纯洁性。鲁迅曾举浙西一个笑话,说劳作于大热天正午的农妇想像刚睡午觉醒来的皇后娘娘,叫太监拿个柿饼来。鲁迅尖锐地指出,这“其实是‘高等华人话’。在下等华人自己,那时也许未必这么说,即使这么说,也并不以为笑话的”[17]。鲁迅无情地揭露出这类披着民间文学形式的外衣,实际上却不是劳动人民的作品,自然也就不是民间文学了。一些非民间性的东西渗透到民间文学作品之中,这种情况在过去的民间文学中比较常见,现当代的民间文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就需要研究者具体地分析,批判地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虽然认同多数不识字的工农大众,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普通民众中的一员,要不然,就不会有《一件小事》中“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18],也不能揭露假冒的民间文学作品。鲁迅敬重“民”,敢于暴露、剖析自我,并向“民”的优秀品质学习;但他作为一名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又着眼于现实,清醒地解剖着“民”的麻木与愚昧。这正是鲁迅既复杂又深刻的一种表现。
总之,鲁迅对广大下层民众表现出崇高的敬意,对工农大众创作的民间文学极为赞赏和推崇。虽然他没有专门讨论民间文艺学这门学科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他在民间文艺学方面的许多见解是与他对当时社会、文化的感想和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对“民”的敬重对于我们当今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一些人对当前我国正在广泛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以为然,甚至指责和非难,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些人没有像鲁迅那样发自内心地尊重“民”,真正地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我们认为,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者应该像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 “小伙计”那样,多凝视,多聆听,即便是对孔乙己这样的边缘人,也不应嘲笑,而是给予一份尊重。
[1] 钟敬文.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J].文学评论,1982(2):51.
[2] 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
[3] 高丙中.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2.
[4] 鲁迅.“题未定”(九)[M]//鲁迅.门外文谈.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73.
[5] 鲁迅.致姚克[M]//鲁迅全集(编年版):第8卷(193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13.
[6] 鲁迅.不识字的作家[M]//鲁迅.门外文谈.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
[7] 鲁迅.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 [M]//鲁迅.门外文谈.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23-24.
[8] 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M]//鲁迅全集(编年版):第7卷(193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12.
[9] 刘玉凯.鲁迅对民间文学理论的贡献[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1):101.
[10] 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130.
[11] 鲁迅.致李桦[M] //鲁迅全集(编年版):第9卷(193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517.
[12] 鲁迅.经验[M]//鲁迅全集(编年版)第7卷(193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06.
[13] 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M]//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卷(1898-191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51-255.
[14]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4:220.
[15] 鲁迅.偶成[M]//鲁迅全集(编年版)第7卷(193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14.
[16] 鲁迅.论第三种人[M]//鲁迅全集(编年版)第6卷(1929-1932).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801.
[17] 鲁迅.“人话”[M]// 鲁迅全集(编年版)第7卷(193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09.
[18] 鲁迅.一件小事[M]//钱理群,王得后.鲁迅小说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45.
(责任编辑:李天喜)
Lu Xun’ s Respect for “the Folk” in Folk Literature
Chen Zuying1,2
(1.SchoolofLiterature,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ng100875,China;2.FujianAdministrationSchool,Fuzhou,Fujian350001,China)
As an important pioneer of modern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Lu Xun mentioned the folk literature which used to be vulgar to an unprecedented height. “The folk” in folk literature discussed by Lu Xun were illiterate working people, compared with the intellectuals. Because of his childhood life experience and the real experience in the rural areas in eastern Zhejiang, he was full of respect for the working people. Lu Xun not only praised the “fresh and vigorous” style of folk literature, but also learned and referenced the content and art of folk literature to literary creation. Although he agreed with “the folk” and showed respect for them, he was not one of the folk. It seemed that he wanted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folk literature and written litera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his purpose of “cultivating the new generation”
Lu Xun; folk literature; the folk; respect
2016-11-06
陈祖英(1974- ),女,江西奉新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行政学院副教授。
I206.6
A
2095-4824(2017)01-0062-05
——李福清汉学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