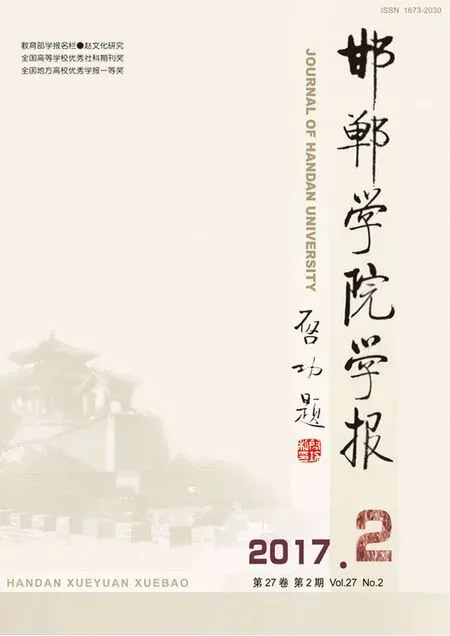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战略决策(纪念七七抗战八十周年)
李良志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战略决策(纪念七七抗战八十周年)
李良志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日本的既定方针是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继而称霸世界。由于当时中日力量对比悬殊,中国共产党要挽救危亡,首先必须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建成后,又有一个在统战内部如何合作、如何斗争的问题。中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其战略决策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且都得到过共产国际的有益指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战略决策。
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奋起抵抗,伟大的14年抗战开始了,同时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我国人民提出了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第一、由于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那么中国人民到底要不要抗战?第二、中国人民如何抵抗?如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对这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都作出了正确回答。对要不要抵抗,中共中央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和劳苦大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1-4对于如何抵抗,如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回答是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下面,本文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作简要概述。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提出和形成过程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提出及形成过程,由于受党内极左思潮的影响,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
1932年4月15日,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中共中央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口号。[2]229由当时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转变到要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萌芽。
1933年初,日本的侵略由关外侵入关内,占领山海关、热河、察哈尔、绥远,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率部进行长城抗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新的时局,起草了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统战文件。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文件于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2]317文件第一次提出了与各抗日军队联合的口号。文件发表后,得到舆论界的热烈响应。
1933年12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起草了新的统战文件,提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六条纲领: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立即设法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4月20日,文件以“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由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章乃器等1779人签名公开发表。文件提出了工农商学兵大联合的口号,不再坚持推翻国民党政府是进行抗战的先决条件;将过去主张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改为主张联合一切反日国家和民族,号召建立“广大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3]232-237文件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签名拥护者达几十万人之多。
上述两个统战文件虽提出了联合资产阶级、及联合各抗日军队的口号,但我党在共产国际下层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下,认为统一战线仅包括工、农、士兵等劳苦大众,对资产阶级与各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主张和行动,均持怀疑与不信任态度,于是表面上欢迎和号召他们抗日,也一定程度参与和支持他们抗日;而与此同时,却又通过我们的宣传舆论揭露他们。如说冯玉祥组建察哈尔同盟军抗日,不过是“高挂抗日反蒋旗帜”、“欺骗士兵群众”,“勾引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察哈尔、绥远,以便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反苏战争。”[4]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领导第十九路军于1933年底发动福建事变,宣布反蒋、抗日,我党却指责他们不过是“空喊革命口号”,玩弄“欺骗群众的把戏”,应予“最严厉地无情地揭露”。[5]579
1934年春,鉴于世界法西斯势力的猖獗,苏联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实施和平外交新路线,逐步调整了同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关系。共产国际被要求重新审定过去的统战策略,执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随即反省和检讨了过去在对待冯玉祥和福建人民政府中的极左错误,决定要认真执行联合一切反蒋派别反日、反蒋,上层统战与下层统战同时并举的新策略。1935年6月15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名义,由毛泽东、朱德等署名,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同日又以上海临时中央局名义,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宣言》,指出“蒋介石是古今中外最大的卖国贼”,“目前中国唯一的救法,只有团结一切反日反蒋的民众,站在一条战线上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卖国集团、蓝衣社匪徒!”,“凡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或不满意于蒋介石等卖国贼的,不管他是谁,都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①这两个文件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开会前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吴玉章,鉴于华北事变的严重局势,急电在苏联南部疗养的王明速返莫斯科,商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回来后,在代表团会议上作了报告,并与吴玉章等一起起草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经代表团多次讨论,于7月14日通过了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题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件。之后,代表团将文本译成俄文,呈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审阅,得到了满意认可。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作报告,首先向世界各共产党宣读了文件的主要内容。1935年10月1日,此文件正式刊登在吴玉章等主办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②《救国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预,于1935年12月初被迫停刊,于同年12月9日复刊,改名为《救国时报》。由于文件签署的时间为8月1日,故称《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程中,以崭新面貌出现的统战文件。其特点是:一、它完全摆脱了过去下层统一战线的禁锢,把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二、宣言所主张的联合,已不再局限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援等,而是要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国防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求得更有成效、更高级的联合;三、宣言虽尚未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仍称他为主要敌人,但却号召各党派抛弃陈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四、宣言不再是出于揭露国民党等的斗争策略需要,而是真心诚意愿同各抗日力量团结对敌。[2]679-682代表团为了迅速恢复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的电讯连系,并把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传达到中共中央,相继派张浩、阎红彦、刘长胜等从莫斯科启程回国。1935年11月18日,张浩风尘仆仆穿过六月飞雪的蒙古大戈壁,首先回到陕北。这时,中共中央领导的红军,已克服万难在陕北落脚,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贯彻了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指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中国,把中国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变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严重改变了中国各阶级、阶层、政党、各军队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议指出:“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日、反蒋,“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始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为适应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决议规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要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在农村土地政策上,决定只取消富农的封建剥削部分。决议还说,当前党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必须予以坚决纠正。[2]734-745
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对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分裂状况,及利用这些分裂的意义;对统一战线中党的领导权问题;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严重性和危害等等,一一作了精辟分析。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策略路线的形成。胡乔木在其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什么是在红军结束长征后,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形成,作了如下阐述:他说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1931年到1934年的党中央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在1935年的长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以后“在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的帮助之下,党在8月1日发表了号召统一战线的宣言,特别是党中央政治局在12月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12月27日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才满足了这个要求。”[6]37胡乔木的这段话,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二、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争取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
《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但它是不完整的,其主要之点,是未把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南京政府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上述两个文件仍是反日、反蒋并提,均视蒋为“主要敌人”。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也说蒋介石“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总头子就是蒋介石”。[7]130但是,要实现真正的全民族抗日,就决不能没有蒋介石的参加,而争取他抗日也是有可能的。第一,蒋介石不是降日派,而是抗日派。他虽在“九·一八”事变后实行了不抵抗政策,但也进行过 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抗战,和1933年的长城抗战。从1932年起,他就在各方面作抗日的准备,如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划分全国战区,确定以四川为中心的大西南国防基地,整军备战,从德国等购置武器,实行新兵役法,训练民众,培养预备役军官,成立资源委员会,加强重工业、手工业生产,新修、延长、连接苏嘉、浙赣、黄埔、陇海等铁路,建设全国公路网,改革币制,着手沿海大城市的工业、学校、机关内迁等等。第二,他从 1935年冬开始,就主动寻找渠道,在南京、上海、莫斯科等地,与中共代表进行联合抗日的秘密谈判。1936年1月,他通过宋庆龄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和谈要求,宋庆龄派上海中央局工作人员董健吾(公开身份牧师),于1936年初抵达陕北。第三,蒋介石当时拥有全国性政权,广泛的国际联系,拥有大大优于红军的国防实力:正规军约200万人,飞机600架,飞行员约3000人,大小舰艇100余艘,总吨位约6万吨。
当时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都十分重视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权,认为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没有蒋介石的参加,而且还必须以国民党军为主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虽落后于共产国际,但却也是一步一趋紧跟的。从1935年11月到1936年春,王明等相继在《救国报》《救国时报》上发表了《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快邮代电》《东北抗日联军呼吁国内军政领袖》《中华民族一致对外》《关于抗日讨蒋》《统一对外与联共》《致纽约商报主笔的信》等文章,不断降低反蒋调门,宣称只要蒋介石“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不仅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8]“抗日不分党派,不分信仰”,“反日者便是我们的朋友,对任何人是如此,对蒋介石也如此。”[9]在上述文章中,还称呼蒋介石为“蒋先生”、“蒋委员长”、“南京蒋总司令”等等。
这时的陕北中共中央,在对待争取蒋介石的问题上,其态度比较迟疑。1936年初,我党与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谈判合作抗日,2月9日,毛泽东在致张学良、王以哲的电报中说:指望与蒋介石合作抗日,无异如与虎谋皮。2月21日,毛泽东指示谈判代表李克农,与张学良谈判时,必须坚持抗日与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蒋。3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把国民党内各派分为民族革命派、民族改良派和民族反革命派,认为蒋介石是民族反革命派的代表,其反革命路线现在与将来皆不变。5月25日,毛泽东在致阎锡山的信中,称蒋介石是“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要求阎与中共同反蒋,“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10]1531936年6月,发生两广事变,6月8日毛泽东在答《红色中华》记者问时,号召全国人民赞助两广的反蒋斗争,“推翻汉奸头子蒋介石”,宣称“我们不愿与汉奸讲统一”。[11]209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此时仍坚持反日、反蒋并重,表示不同意。1936年7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问题,认为中共中央应改变关于国内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并举的方针,放弃苏维埃政权形式,以民主共和国代替苏维埃人民国。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书记处会议上又说,抗日反蒋并提不恰当,中共应同蒋介石谈判,应造成一种局面,逼蒋介石抗日,使蒋介石不得不参加统一战线,这个问题已“晚解决了两三年,但是,晚解决总比不解决好,现在要加以扭转。”[12]84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又对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其要点有:一、批评中共中央“把蒋介石与日寇等量齐观”,“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指出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我们“不能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为了切实有效地进行武装抗日,还需要有蒋介石的军队参加。”二、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提出“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在普选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三、强调“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订共同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共产党和红军司令部应该宣布他们准备马上派出谈判代表团,或者在苏区接待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团。”四、如果蒋介石的军队继续进攻红军,红军必须自卫,但“同时要继续开展运动和采取具体措施,以争取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达成协议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86
中共中央及时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指示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承认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已有变化,在今天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过去我们提抗日必须反蒋,现在已不合适,我们要与蒋介石联合,我们的许多策略有改变的必要,红军可以改人民军,苏维埃改人民政府,军事上可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
1936年8月12日,毛泽东等在致第四方面军的电报中说:现在南京是我们“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应“继续停战议和和请蒋抗日”,“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实行“先礼后兵政策”。①《洛甫、林育英、毛泽东等同志致朱、张、任电》——关于今后战略方针之建议,1936年8月12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同年秋,中共中央在一封给各军团的指示中又说:“日寇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因此把蒋介石与日寇看一律,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同时,进行抗日讨蒋的斗争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和所有蒋介石的军队看成日本的同盟者,要实行严重的武装抗日,必须蒋军全部或最大部分参加。”②《中央为联蒋逼蒋抗日策略给各军团的指示》(此文件未标明时间,中央档案馆推定的时间为1936年8、9月。)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2]773-777
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向全党指明:“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口号,也是不适当的”,现在党的方针是“逼蒋抗日”。[2]778-779
9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放弃苏维埃共和国口号,愿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中共中央在作出上述决定、指示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亲自给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陈果夫及许多国民党军政领袖发出要求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件,仅毛泽东一人发出的信件就有70多封,有时他一天发出9封信。与此同时,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也在南京、上海两地积极进行。中共中央还拟定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由周恩来亲自带到南京或广州与国民党商谈。这个草案,既是我党的谈判案,也是我党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纲领。它反映我党从1936年8月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上的重大转变,即从反蒋到逼蒋政策的完成。
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局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声称“外敌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13]35-36于是他从1930年10月起至1934年10月,每次以几十万、上百万大军,对红区进行了五次大“围剿”。在前 4次“围剿”中,他损兵折将,被打得大败;但在第五次“围剿”中,由于红军受到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和党内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1935年10月,红军战胜万难,抵达陕北,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员至约6000余人。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总兵力也才约4万余人,红军实力已大大地削弱了。此时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濒临了即将崩溃的危机”,[14]68“更走到了日暮途穷的绝境”,[15]57只要“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解决”,[15]220-226红军即可消灭殆尽。于是他于1936年10月22日,亲自飞抵西安,以36万大军,50架飞机,胁迫西北驻军张学良、杨虎城部全力进攻红军。可是蒋介石不知道,此时张学良、杨虎城率领的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早已结下了城下之盟,订立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张学良还亲自到洛川、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会谈,张还两次向红军赠送巨款与物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学良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要求蒋介石掉转枪头抗日。张学良先开始是“言谏”,而后是“哭谏”[16]121;蒋介石却说:“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之事”[16]131,“你现在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政策也不能变”[16]135。“哭谏”无效,张、杨最后下定决心实行“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将蒋介石扣押在西安新城大楼,将他带领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军政大员,全部囚禁在西京招待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给毛泽东发出“文寅”电报:“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集中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北进。弟毅①毅,即张学良,当时在他与中共的来往电报中,毛泽东称他为李毅,或李宜。(作者注)。、文寅”。[16]135
张学良由逼蒋抗日,一下转变为捉蒋抗日,这是中共中央万万没有想到,也是完全不知道的。这一突然事变,既震惊了中外,也震惊了陕北的中共中央。事变前,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已完全放弃了反蒋抗日,转变为坚定执行逼蒋抗日的政策。现在这个仍执行灭共政策的蒋介石,突然成了阶下囚,被张学良扣押起来,那么此时如何处置这个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又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新问题了。
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 12日凌晨的紧急来电后,毛泽东立即作了回复,并连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事变问题。从12日回复张学良的第一个电报,至12月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五天之中,由毛泽东亲拟发给西安的电报共37份,其中发给张学良的有23份之多。这些电报多以“东”或“东、来”署名,有的电报还冠以“万万火急”字样。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37份电报中,从当时我党的公开舆论及举行的群众活动中,可以看出: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内部都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对蒋不可冒失,军事布署上,应尽量争取南京政权,联合非蒋系队伍,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立场;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决不可错失千载难逢之良机,对蒋必予严惩,军事上应取进攻姿态,准备打几个大仗,以促时局剧变。后一种意见,一时之间还占上风。下述事实,可佐证这一点:
12月12日,在发给张学良的“万万火急”电报中,我党要求张学良必须把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不可交其他部队,严防其收买属员,情况紧急时诛之为上。同日,中央在致刘少奇的电报中,要求中共北方局揭发蒋之对外投降、对内镇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人民审判”。[10]316
12月13日,中央要求张学良立即逮捕或驱逐军队中的法西斯分子,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此为最紧任务之一。同日,《红色中华》在报道西安事变消息时,也提出全国人民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这天,保安召开群众大会,中央领导人出席,会上提出: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欠人民的血债高积如山,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要求把蒋介石押到保安,由全国人民公审。
1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七封解决事变的电报,建议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张学良为总司令,下辖三个集团军,东北军编为联军第1集团军,张学良兼任总司令;第十七集团军编为第2集团军,杨虎城任总司令;红军编为第3集团军,朱德任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组成主席团,张学良为主席团主席,杨虎城、朱德为副主席,统一军事政治领导。联军主力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火速抢占潼关,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在近期,杨虎城固守西安城,张部与红军担任野战,红军开赴西峰镇,靠近西安,以西安为抗日首都。认为只要打得几个大胜仗,即可大大展开战局。电报还拟就了联军的十大口号,如打倒汉奸卖国贼!建立救国政府!等等。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9份有关解决事变的电报,其中的一则是向张学良转达华北负责人的意见:嘱张学良胆大些,胆再大些,要干到底,赶快消灭敌人;认为红军早已要求给蒋以更大的严重的打击,对南京取进攻防御姿态,但当蒋尚在人世时,各方总还是在犹豫观望,所言不为无见,望加多酌。同日,红军将领毛泽东等15人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介石,并交付国人裁判。
12月16日,《红色中华》报发表《蒋介石罪大恶极——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社论,历数蒋介石的种种罪恶,声讨他“虽百死也不足赎其罪于万一。”要求将他交给人民公审,交给人民裁判。
12月17日,周恩来抵达西安,与张、杨紧急磋商如何解决事变问题。可以看出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中共中央的政策开始了转变。周恩来这天致电中共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17]73此电第一次出现“保蒋安全”字样。
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详告外界对事变的反映,并陈述个人对解决事变的意见。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指出只要国民党承诺下列几点:一、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抗日救国政府和抗日联军;二、调回讨伐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西北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则“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10]321-322从这个电报开始,无论党内外文件,均再无严惩蒋介石的字语和要求。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文件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性质、发展前途,明确、坚定地指出,为了防止和反对新的内战,推动南京进一步走向抗日,我们必须和平解决事变。同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和西安当局发出通电,公开阐明了我党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心,并就建立和平提出四点建议。
至此,在西安事变这一突发事件中,中共中央对如何处置蒋介石、以及相联系的军事对峙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中共中央最初要求审蒋、罢蒋,甚至诛蒋,这是历史的积怨,事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而迅速转变为放蒋,是党的英明、伟大、成熟。那么,促使这一重大转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第一,张学良扣蒋,仅仅是为了逼蒋抗日,他毫无除蒋之念。12月12日,他在致宋美龄的信中,明确无误地说:蒋“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使全国“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因而“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学良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18]174
第二,苏联、共产国际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事变当日,中共中央一连三次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事变实况及中共中央处置事变的意见与部署,但共产国际迟迟未作回复。至12月16日,才收到季米特洛夫关于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来电。这则电报,因字迹不清,20日共产国际重发后,中央才正式读到。虽然如此,中共中央从苏联公开发表的报刊舆论中,早已得知苏联、共产国际谴责事变、主张和平解决,主张放蒋的明确立场。中共中央在12月17日致张学良的一封电报中,为了安抚张学良急切想得苏联赞助的心情,失望地告诉他:“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目前远方“为应付外交,尚不敢公开赞助。”①毛泽东:《关于集力抗战问题给张学良的复电》(1936年12月17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第三,出乎意料,南京军政界在事变面前,没有出现什么分裂,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团结一致,同声谴责张、杨;而一向与蒋介石离心离德的地方势力派,如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西南的刘湘、刘文辉、龙云,新疆的盛世才……等,均表示不敢苟同事变,要求释放蒋回南京;一贯与中共友好,累遭蒋介石迫害的冯玉祥将军,居然对事变表示“莫名骇异”,对蒋讲了不少美言,说“外侮日深,国家风雨飘摇,谋国内和衷共济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要求先释介公回京,并愿亲自来陕作人质。冯玉祥还告诫张学良,“勿受他人之挑拨离间”。12月16日,冯玉祥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竟赞同作出讨伐张学良叛变的决议。当时所有地方势力与国民党派别中,只有李济深是唯一的例外,他公开表示了对张、杨的理解和支持,严厉批评南京讨伐张、杨。
第四,广大的著名爱国人士、专家学者,对事变均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与不安。学界名流蒋梦麟、梅贻琦、徐涌明、李蒸、李书华、陆志韦、李麟玉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岩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否则足下将永为民族之罪人矣!”当时设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着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也于12月15日发表紧急宣言,称事变“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不幸”,“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民族危亡之际,“谁要挑起内战,谁就是敌人的奸细,民族的罪人”,“一定为天下所唾弃。”他们齐声要求“立即恢复蒋先生自由。”中共的好朋友杜重远,也指事变为“变乱”,说“凡属国人莫不痛心。”
第五,英、美等西方民主国家,一致主张事变和平解决。只有日本帝国主义,趁火打劫,声称张学良“赤化”,日本绝不能坐视不管。
第六,实力对比悬殊,以张、杨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军,在空前的内战中对峙南京政府军,前途未卜,军事上绝无胜利把握,而政治舆论上,成众矢之的,极为孤立。长期的大规模的内战,只会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上述严重实况,中共中央不会不仔细酌量,以制定自己的决策。
蒋介石在事变中逃窜不成,被找回来以后,态度十分顽固强硬,他谴责张、杨,拒绝接受张、杨提出的和平解决事变的所有条件。12月13日,他致信宋美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决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19]23-2412月20日,蒋介石又给宋美龄、蒋经国、蒋纬国及全国同胞共立下三封遗嘱,说“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唯有一死以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19]23-24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抵西安,与张、杨、蒋介石见面,宋氏兄妹劝说蒋介石妥协,和平解决事变,蒋的立场有所软化。
12月23日、24日,张、杨同宋子文、宋美龄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周恩来遵中央指示,在谈判中作了大量工作,双方于24日达成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协议。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出潼关。(二)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民主国会召开前,苏区名称不变,但可加上抗日或救国字样。(五)召开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我国抗日的国家合作。当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阐述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说:只要蒋介石改变内战的误国政策,不仅他个人可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听蒋先生指挥。[20]55蒋介石深受感动,他在后来的记述中说:此次事变“我当时就断定,这是张、杨二逆受共匪欺诈,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国家以致命的一击”;“即使张、杨有悔意,而其主谋之共匪,必认为千载一时之良机……非迫我接受他的条件,即必制我的死命”;“但是这件震动世界事变的真相,到了事后才完全明了,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15]75-76会谈中,蒋对周恩来承诺:同意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答应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21]73
12月25日,张学良在未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仓促陪蒋介石先飞洛阳,然后飞抵南京。蒋在飞离西安机场时,对张、杨说:“今后我绝不剿共”。[16]73但千古功臣张学良从此一直被蒋介石囚禁至他生命的最后。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认识了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的道理,认识了共产党无谋害他之心,又积极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从而愿意“联红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成为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四、中国共产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
蒋介石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是被迫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他一面抗战,一面也不忘取消共产党、取消党领导的武装。比如,在红军改编问题上,他最初只准红军保留三千至五千人,师长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回国,量才录用。遭到我党反对后,他又提出要向我军派遣从副师长至副连长的一系列副职,还要派联络参谋,“毛、朱两同志须出来做事”,[10]515红军改编后,不许设立总指挥部,还必须“移防”等等。在共产党地位问题上,他提出要成立两党合并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任主席,并拥有最后决定权。1938年 12月12日,蒋在重庆约见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声称他坚决反对共产党员跨党,说“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此事乃是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我这个意见,至死不变”。[10]183我军深入敌后抗战,依靠正确的战略战术、以及正确的军政政策、军民政策,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至1940年,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敌后共建立 16块抗日根据地,拥有约一亿人口。蒋介石视我党力量为眼中钉,于是制定了一系列秘密反共法令,反共摩擦随之迭起。
中共中央怎样应对蒋介石的反共摩擦,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毛泽东先后书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著作,制定了我党的斗争策略。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并未熄灭,有时还会很激烈,因此民族斗争不能否认或抹杀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又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的需要和允许,不能破坏和不利于民族斗争。这就是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根据这一原理,我党应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执行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在进行斗争时,又必须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在这一斗争策略指引下,我党迅速打退了国民党,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政变”,1940年1月6日,阎军被歼灭一部;1月30日至2月2日,又歼灭阎军一个旅和一个师的大部,稳定了山西政局。之后我党主动与阎锡山言和,阎无可奈何,接受了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界,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旧军的活动区域的和谈协议。在河北,八路军385旅等,也于1940年春,先后击退了国民党军朱怀冰部和石友三部对冀西、冀南和冀鲁豫根据地的进攻,歼灭了朱怀冰部主力,重创石友三部。随后,八路军主动与国民党军第一战区谈判,达成停止冲突,划界驻防的协议。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359旅,也迅速平息了胡宗南部在陇东、关中、绥德地区制造的武装叛乱,保卫了边区的安宁。
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不仅没有吸取教训,改弦更张,而且迅速将反共的重点由华北移到华中,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其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改称为“陕北行政公署”,归陕西省领导;八路军准予编三个军、六个师,新四军准编两个师,其余部队一律限期取消;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转移到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按这个提示案,50万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将被缩编为 10万人,并将被全部驱赶到黄河以北之狭小区域。国民党的这个无理要求,当然被我严词拒绝。
10月19日,国民党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发出“皓电”,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不服从命令”,限令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指定地区。11月1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联名发出“佳电”,一面拒绝国民党要求华中我军全部北移的无理要求;另外也顾全大局作出让步,表示我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蒋介石视中共中央的让步为软弱可欺,连续发出“齐电”和手令,坚持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悉数开赴黄河北指定地区,同时又命令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做好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准备。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北移途中,在路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是我军自抗战以来遭到的最严重的损失。造成这一损失的原因较多,情况也复杂,但与中共中央对事变前形势的分析失误有重要关系。中共中央曾以为,当时英、美、苏都支持中国抗战,蒋介石急于想参加英、美同盟,他对德、日的劝降、诱降不可达成妥协,因而对我党我军的攻击、压迫,不过是为了煽动舆论,是恐吓多于实际。下面所引电文可佐证这一点:
1940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22]103-104
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他是一筹莫展的。”“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更强了,彼更弱了。”“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22]103-104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一则全党通报中说:“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22]116-117
1940年12月30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复刘为章电……大家意见以拖一下为好。他们反共,让他们去反,剿共也让他们来剿,反得全国天怒人怨,那时我们再表示态度,率性不着急。”[22]127
1940年12月31日(皖南事变前夕),中共中央在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指示中说:“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的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答复蒋之命令,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及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并不急了。”[22]127
由于对事变前夕的时局作了上述乐观的估计与分析,党中央同意皖南新四军于1940年底至12月初,在苏北发动了极不适当的曹甸战役,一举消灭韩德勤部 8000余人。这一战役极大地坚定了蒋介石迅速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决心。而毛泽东却认为:“苏北动作不碍大局,……打通苏皖,顾、韩会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22]105“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23]243
皖南事变突发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又是如何分析时局,以及决定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呢?中央认为:“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如果一月十七日以前争取蒋介石好转还有可能性,因而这个争取政策还是正确的,在一月十七日以后,这种可能性就已经没有了,因而对于蒋介石的争取政策也就不正确了。”蒋介石“把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除了和他完全对立以外,没有其他路走”,“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24]530-534“现在已经不是打退反动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争取时局的可能性“已没有了”。①《毛泽东同志关于皖南事变后我之军事方针给彭德怀同志的指示》(1941年1月23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根据上述对事变后的形势的分析,中共中央对蒋介石采取了政治上大反攻和军事上准备反攻的斗争策略。
政治上的反攻,包括在舆论上大张旗鼓地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在皖南事变中的种种罪行,举行种种抗议集会;终止我党驻国统区的各类办事处同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关系,撤退办事处与国统区的干部;针锋相对,重建新四军军部,并扩大新四军为七个师;提出我党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如必须收回“一·一七”反动命令,给事变平反,惩办祸首等;不再向国民党当局呈送任何文件,报告中共有关军、政情况,亦不领取款项;拒不参加国民参政会;准备在各抗日根据地召开皖南事变中死难者追悼大会,由群众提出“成立中央政府”,“请求八路军派兵南下”,“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大后方镇压亲日派”等口号。中央认为政治上不怕僵,愈僵愈对我有利,于蒋不利。
军事上准备反攻,其内容包括:
1941年1月13日,中央指示在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②《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以答复皖南事变的指示》(1941年1月13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月14日,“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我华北各部队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③《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反攻的指示》(1941年1月14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月19日,中央致电彭德怀、刘少奇:“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手,打到甘、云川。”①《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在政治、军事、组织上应采取的步骤致彭德怀、刘少奇电》(1941年1月19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月20日,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扩大为7个师,委任各级指挥员,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等五人组成。同日,中央又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指示军事上暂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23]262
1月23日,中央致电彭德怀:“军事方面暂时仍取守势,目前还不能下调动大部队的决心,(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又询问彭:你处有多少炮,多少炮兵?能否抽带5万兵力西进打到四川?有无5万人的4个月经费?②《毛泽东同志关于皖南事变后我之军事方针给彭德怀同志的指示》(1941年1月23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同日,中央又致电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 9位高级将领,指示做好反击蒋介石“剿共”战争的财政准备,以便防止一进入国统区即发生给养困难,“因此应多收集金银、法币。各地区筹款数目,应敷部队出动5个月之用。此事须在2至3个月内准备完毕。”③《毛泽东等同志关于财政上准备以对付蒋介石剿共战争的指示》(1941年)(此件无月、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月24日,中央又致电彭德怀、聂荣臻等,指示西北应增兵,各兵团停止作战、休整、转入安全之地,停止消耗枪弹,保存公粮。
1月30日,中央致电周恩来,指示我出兵,至快在半年后,“苏联如再接济重庆武器甚为不好。”④《毛泽东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1月3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月1日,中央致电彭德怀:“准备出兵,要积极加紧”,“黄河以南部队应准备出豫西(鄂豫陕边),那是左翼的主要方向。”“封锁线已有详细调查,黄河渡船准备容易。”⑤《毛泽东同志关于华北分期出兵和利用日蒋矛盾等问题给彭德怀同志的指示电》(1941年2月1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同日,中央致电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要在华中建立鄂豫陕边、江南、苏鲁等三个基本战略区。指示说:“华北的任务是出陕甘川云贵,你们的任务是出鄂豫陕边与闽浙赣区,南方的任务是经营五岭南北。”[25]621-623同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李先念部队有绝大战略意义”,我们应千方百计将办事处、《新华日报》及党与非党干部疏散到那里去。指示应立即在湘西、川东、川北、川陕边建立五个小的武装根据地。⑥《中央关于大后方干部尽量向李先念处疏散与建立五个根据地问题致周恩来同志电》(1941年2月1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月2日,中央致电各军事将领并告周恩来、董必武:日寇发动豫南战役,八路军暂“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但“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⑦《毛泽东同志关于当前形势与对蒋介石的方针的指示》(1941年2月2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同日,中央致电刘少奇等,“你们应不失时机集中大力向河南发展。”⑧《毛泽东等同志关于新四军应乘机大力向河南发展的指示》(1941年2月2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对于中共中央上述军事上准备大反攻的部署,党内也有持怀疑态度的。刘少奇于1941年1月15日致电毛泽东:“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下令制止,即证明蒋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刘少奇分析了华中我军实力与处境,“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皖东北敌伪匪猖獗,已全部成游击区,原来巩固地区均已丧失,淮海地区亦不能支持,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华中“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有利”,他还说,华中仅有少数地区可对国民党实行反攻,但“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且有极大危险。”他认为我党应主要是在全国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建议中央“平心静气”、“细心考虑”。⑨《刘少奇关于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问题向毛泽东等的建议》(1941年1月15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941年2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也致电毛泽东反对中共中央的决策,“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相反,要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尽共产党和我们军队所能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扩大。请重新考虑一下目前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并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告诉我们。”[26]133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当然也反映了苏联政府的观点。1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会晤苏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时,潘就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必须同蒋介石会晤,不要期待蒋介石向中共乞求,要就所有的问题进行会晤和交谈,形势要求这样做,这一会谈只会对中共和中国有利。”[27]110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的意见,多少是沮丧的,他在1月20日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中说:“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①《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1941年1月2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但毛泽东还是接受了季米特洛夫的意见。2月13日,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我们作出的决定符合您的指示,与您的指示没有分歧”,当前“日本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还是主要矛盾”,“近日日本人在河南省展开攻势,因此蒋介石约 20万军队从反共战线调往抗日前线”,“在这个时候剿共军对我们实行大规模进攻已经不可能”,我们“在军事方面,继续实行防御政策”,“再过两三个月,我们将获得更有利的条件,那时就可以结束这个事件”。[26]150-152
季米特洛夫与刘少奇的正确意见,以及日寇发动豫南战役和国民党在战役中的惨重损失,使毛泽东果断地改变了“军事上大反攻”的设想。1941年2月14日,他致电周恩来:“国民党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制共可能停顿,敌必向蒋进攻,崔可夫的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的中心”。在此情形下,我们的军事攻势“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而政治攻势“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相成。”②《毛泽东同志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同志电》,(1941年2月14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2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陈毅、刘少奇等14位将领:“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因此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因此“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新四军已无合法地位了,“本来可以大闹”,但为利用日蒋矛盾“亦不应该去大后方”,“彭雪枫过新黄河的活动应暂时放弃,主力向河南发展任务,目前应改为准备而不实行”,“八路军机动部队准备亦然。”③《中央军委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军军事方针的指示》,(1941年2月17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随即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召开关于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殉国烈士的群众大会。2月20日,中央还批评第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在所发“训令”中,有关混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认为“整个资产阶级已经或快要叛变了”;“提倡土地革命”;将统一战线教育与阶级斗争教育对立,只强调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强调右倾危险,却不强调防止左倾危险等错误。④《中央对前总二月九日训令的批示》(1941年2月20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从此开始,中共中央全力关注对国民党的政治大反攻。毛泽东曾预料,蒋介石的“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敌人攻击得如此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⑤《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致周恩来同志电》(1941年2月7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事实果真如此,蒋介石为了摆脱事变后的困境,把皖南事变由反共政治问题,变为地方军纪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企图利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的召开,迫使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于是他给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下达任务,以各种办法迫使周恩来就范。张冲,浙江乐清人,字淮南,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代理组织部长,为蒋介石所重用;他从 1935年冬起,一直参与国共合作抗日的秘密谈判。对中共比较客观、公允,同周恩来也有较好的交谊。
于是,国共两党围绕参不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的新政治战斗开始了。
1941年1月25日,周恩来就根据中央的指示,将我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交给张冲转蒋介石,嗣后又将“十二条”递送国民参政会及参政会的民主党派领袖和部分有正义感的参政员。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我们目的,不在蒋介石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⑥《毛泽东同志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同志电》(1941年2月14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谈判从1月25日开始,一直谈到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开幕前夕,张冲死死缠住周恩来不放,他软磨硬顶,千方百计,苦苦哀求,有时一次达三小时之久。谈判中,他多次主动表示让步,如说我军移黄河以北之事,可以延期,新四军可并入八路军,然后扩大八路军编制;为给国民党中央留面子,第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赴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队全部留华中,愿留多少就留多少,还我一军,以补新四军之缺;归还叶挺及其他干部;边区及冀察政权照前议;中共7名参政员,不一定全出席参政会,毛泽东不能来,指人呈意即可;只须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或者他们中一人出席也可;为解决事变,可成立调解委员会,蒋介石为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还可成立党派委员会;军事进攻与政治压迫,总要解决,由蒋负责,再不许发生新的事件……等等。张冲有时也有恐吓之语,如说蒋介石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弄不好“会翻脸”的。
2月25日,张冲再次缠住周恩来,苦求周恩来收回“十二条”,先与蒋见面。他说:“为了国家计,他跪下都可以”,“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中共是忠,国民党是奸,中共要顾大局,国民党是不顾大局的,要求周恩来“前函可称文字有错,拿出校对一次,以便蒋能见周,否则在公函压迫下蒋训令大家,蒋说蒋是被迫而见的。”①《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与张冲谈判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1年2月25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在谈判过程中,参政会中的民主党派领袖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励、褚辅成、左舜生、梁漱溟、罗隆基等,频频会见周恩来,请求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同时他们也向参政会秘书处和蒋介石施压,认为中共参政员无论如何也必须出席会议。蒋介石说“政府既选毛泽东等七人继续为参政员,即是政府希望其出席,且国民政府召集此次会议,对于彼等同发通知。”[28]520王世杰除了亲自与周恩来谈判,还请民主党派领袖劝请董必武、邓颖超务必出席,说为此次参政会开幕可考虑延长一天。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国民党不接受“十二条”就不出席此次参政会,也不见蒋。不过由于张冲的苦苦哀求,以及蒋介石与王世杰态度的软化;特别是各民主党派领袖、救国会领袖们不断地敦请,周恩来对中共参政员是否应与会,态度也有所变化。他在3月1日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是僵局对峙着,须打开一关。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蒋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样,……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我已一夜多未睡,……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毛主席,现在已是十八点了,只是今夜无论如何谈不出结果”,“全重庆都在等待我们消息”,“僵局必须打开,中间办法已没有用,一切待中央立即指示。”[22]225中共中央随即两次致电周恩来:“此次谈判决不会有结果,故你们的决心须在不出席上,亦不宜外出活动,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如我们此时出席,我们即失掉一切立场,结果将非常之坏。”参政会主席团即选周为主席“亦决不能出席”。[22]226书记处反复讨论、考虑,“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只要熬过这一关,就有好转可能。”[22]228
周恩来完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参政员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
3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开幕式上致词,在谈及战时国内党派关系时,一改过去的强硬反共腔调,“我全国同胞均须认识,一切党派观念及所谓左倾右倾之意识理论,已经是陈腐落伍的旧时代的空谈,不能适应今天的时局了”,“资本与劳动,在被征服国家,一经亡国,均自无用。”因此全国同胞惟有“向保卫国家的唯一目的共同奋斗”,“放弃一切不合时代的旧观念。”[28]487-4883月6日,蒋介石又在参政会上作关于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问题的报告,将中共前后两次提出的“十二条”诬为日本的“广田三原则”,又大谈“一个军队”、“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和军令政令的统一,但也不得不说他希望“与全国友军亲爱精诚,和衷共济,共同一致抗战到底”,我政府和全国人民“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他要求各参政员“恳切向毛泽东、董必武等参政员劝勉”,今后能“共聚一堂,精诚团结”,对皖南事变“求得合理的解决。”[28]525-526
3月9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选举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中共参政员虽未出席会议,但董必武仍被选为驻会常委。
3月14日,蒋介石由宋美龄陪同,约见周恩来,蒋说:“两月多未见,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见面。”你们的各种条件,我知道,都是向我提的,“当然没有那样答复,现在开完会,情形缓和了,可以谈谈”。周恩来提及新四军事件,国民党的种种压迫事件,欲见叶挺、以及他回延安和我军防地、扩编等问题。蒋对新四军不作答,说压迫是“底下做的”;说解除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李涛、给周发回延安护照等均可解决;蒋不再提我军北移问题,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又说叶挺“尚未到。当去查,如到,可见他。”蒋约下星期再见,宋美龄说要请吃饭。[22]235-236
3月25日,由宋美龄出面,宴请周恩来、邓颖超,蒋介石、贺耀祖、张冲作陪。周恩来又提及停止军事压迫、党派委员会隶属、会见叶挺、给我军发饷等问题。蒋说:关于停止军事进攻,只要中共听命令,“问题好解决”,成立党派委员会可隶属国防委员会,饷“可先发一月”,叶挺“尚在上饶”。会谈氛围缓和。[22]239-240
此时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目睹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前后所作所为,日益表示出对国民党的不满,酝酿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组织。3月13日,召开了筹备会第一次会议。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书、《同盟简章》等文件,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蒋介石对民盟的成立大为不满,大骂张群为什么不阻止其成立。从这时起,民盟日益靠近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盟友、诤友,使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阵营进一步壮大,国民党顽固派势力日益孤立。毛泽东对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大失人心、委曲求全,及民盟的成立,作了这样的总结:他说“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某种变化的关键”,蒋介石企图以民族领袖维持其一党专政“必然徒劳无功”。[7]736-737
1941年5月,日寇集中6个师团10万余兵力,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发动了中条山战役,其目的是歼灭山西南部的国民党军。在大军压境下,蒋介石亲自约见周恩来,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阻敌前进。毛泽东向八路军总部多次下达指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在敌后猛击日军,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25]641-643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重挫国民党之后,回到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常态,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一致赞扬。
1943年春夏,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又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但由于这时我党我军更加强大和有充分准备,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舆论压力下,这次反共高潮还未来得及充分发动,即偃旗息鼓。
中共中央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蒋介石要反共,但不能彻底地反;他要对日妥协,也不能彻底地妥协;他视中共实力的迅速发展壮大为眼中钉,但他无能为力;他不能不与我党并肩抗战,走完中国抗战的历史过程。抗战胜利后,我党仍坚持长期合作的政策,提出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联合政府,他拒绝接受,在美帝国主义的强大支持下,发动内战,自取灭亡。1956年,蒋介石在台湾出版《苏俄在中国》一书,在总结他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他“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15]240,这完全是错误的。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光明正大,不是害了他,而是救了他。如果他后来不背离这一政策,与中共长期合作,他的下场完全会是另一种局面。
[1]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
[2]中共中央书记处. 六大以来(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M]. 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1985.
[4]冯玉祥的“抗日”喜剧[N]. 红色中华,第105期.
[5]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胡乔木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8]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N]. 救国报,1935-11-7.
[9]关于抗日讨蒋[N]. 救国时报,1935-12-14.
[10]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11]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6辑[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12]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二)[J]. 中共党史研究,1988(2).
[13]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M]. 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14]古屋贤二. 蒋总统秘录:第1册[M]. 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
[15]蒋中正. 苏俄在中国[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1956.
[16]刘长春,赵杰. 张学良[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17]西安事变研究会. 西安事变文电选[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8]汪新、王相声. 1936,历史在这里拐弯——西安事变始末纪实[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
[19]曾景忠. 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
[20]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 西安事变简史[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21]周恩来选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2]中央档案馆.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23]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4]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25]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卷[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6]黄修荣.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27]历史和现代·一个外交官的札记[J]. 苏联《远东问题》,1991(1).
[28]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国民参政会纪实(下)[M]. 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苏红霞 校对:李俊丹)
K265
A
1673-2030(2017)02-0005-13
2017-04-05
李良志(1928—),男,湖南汉寿人,原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现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顾问,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