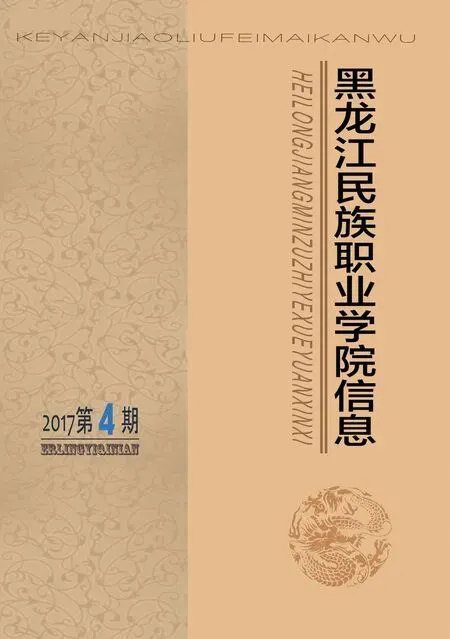清代杜尔伯特旗蒙古族教育的几种形式
包玉林
(杜尔伯特文化研究会,黑龙江 杜尔伯特 166200)
清代杜尔伯特旗蒙古族教育的几种形式
包玉林
(杜尔伯特文化研究会,黑龙江 杜尔伯特 166200)
依据有关史料叙述了清代杜尔伯特旗蒙古族教育的六种方式,分析了蒙古族教育迟滞落后的原因,揭露了清政府抑制蒙古族教育、遏制民族觉醒、控制蒙古族发展进步的政策。
清代;杜尔伯特旗;蒙古族;教育形式
0 引言
蒙古族教育事业走过了大元时期的辉煌后,便消沉下来。明代,在北元蒙古封建主的割据与混战下,蒙古地区没有什么正规教育可谈。到了清代,满清政府对蒙古族文化教育的总的方针是抑制、控制,蒙古族教育仍然十分落后。清廷一方面继续实行笼络蒙古族上层人物的政策,康熙后“南不封王,北不断亲”,羁縻蒙古王公贵族;另一方面,在蒙古地区大力提倡和推行藏传佛教,愚昧广大民众,控制蒙古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遏制民族觉醒。
清廷对蒙古族教育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即“蒙古八旗”与外藩蒙古各不相同。蒙古八旗是清朝赖以勃兴的基本军事力量之一,清廷一向对蒙古八旗“视犹一体”,对其教育问题也很重视。早在入关前的崇德年间,“于盛京建立学校,考取儒生。凡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子弟皆入学。”[1]入关后,“在京师和各驻防地兴建了大批各级各类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人才。”[2]蒙古八旗等八旗子弟可在驻防地接受学校教育。清廷在全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录用国家需要的人才,蒙古八旗子弟可以参加文科、武科、翻译科考试,考中者做官。而外藩蒙古的内扎萨克、外扎萨克各盟旗子弟不能参加各类科举。“清朝对外藩蒙古民众的教育绝不提倡,相反却采取隔离和愚弄的手段加以抑制,如禁止蒙汉两大民族的文化交流,禁止蒙古人学习、使用汉文,严禁延聘汉人为师等等”[3]。清代,外藩蒙古的官办学校少的可怜。据清代史料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归化城设立了一个土默特官学;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科布多设立了一个翻译人才学校;仅此二处,别无他家。
探究清廷对蒙古八旗教育与外藩蒙古教育实行有区别政策的原因有二:一是蒙古八旗属蒙古旗人,“入关以后,八旗蒙古人彻底脱离了以往的游牧生活,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圈——汉文化圈。从文化形态上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一个先满洲化,继而汉化的历史过程”[4]。二是满清政府对外藩蒙古部落的疑忌戒备之心未尝有一日懈怠,害怕蒙古强大,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削弱和限制。除了设置盟旗,“画地驻牧”,严禁随意往来和废除马市,阻滞商贸,延迟经济发展外,抑制教育发展,压抑文化人才出现也是其十分险恶的政策措施。
1 教育形式
在清廷抑制政策下,杜尔伯特旗谈不上任何正规教育,但是,蒙古子弟在困难中还是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学习蒙古文字。依据有关史料和杜尔伯特努图克人(土生土长的人)的口述史料,蒙古族教育形式大约有以下六种形式:
1.1 “留内教养”
为了培养忠于朝廷的统治者代理人,清廷组织外藩蒙古各王公贵族的子弟到京师接受封建皇室的正规教育。“应将蒙古王、贝勒、公、扎萨克等之子,年十五岁以上者令其来京教养,交与理藩院请旨……人品聪敏,已经出痘者,开具年岁,造册送院。”经培养教育,将来有可能承袭扎萨克之责的王公子弟,“令回居本旗,讲究生理,学习骑射,冬季进京居住,照旧肄业,俟十八岁时即令回旗办事。”[5]杜尔伯特旗扎萨克之子也接受过“留内教养”,这毕竟是国家培养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
1.2 “印务房教育”
蒙古地区的公文需要用蒙古文、满文书写,急需翻译人才。为此,各扎萨克旗的印务房的主管人员——管旗章京(札黑拉格齐),招收一定数量的本旗蒙古贵族和官吏子弟,自任教师,教授满文、蒙古文以及公文书信的实用知识,以培养通晓满文、蒙古文的笔帖式(书写员)。这种教育方式比较实用,但普通牧民子弟没有机会入学。
1.3 家庭教育
明末到清中期,杜尔伯特旗蒙古族大多通过父授子承、母授子承的家庭教学开展蒙古文教育,这是最普遍和最主要的教育方式。“居住在黑龙江地区的蒙古居民,几乎家家都有手抄本蒙文识字读本——《阿日本·浩亦尔·套鲁盖》(十二字头字母),亦称《查干套鲁盖》。利用这种课本一代一代地传教,沿袭了蒙古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至今在齐齐哈尔市图书馆古籍部仍藏有光绪十五年的手抄本《查干套鲁盖》”[6]胡都木蒙古文字有7个单元音,有24个基本单辅音,《蒙文识字读本》就是用这些蒙古文字母拼写成若干个音节的读本,学习方便,入门快。会读、会写这些音节,基本上就能通读蒙古文学作品和写蒙古文文章了。所以,除特别困苦的人家外,杜尔伯特旗稍有能力的牧民,家家都有这种课本,并用此对子女进行启蒙教育,很有效。
1.4 私塾教育
清中后期,有一定财力的人家,开始聘请识字者在家里教孩子学习蒙古文,便有了私塾。“从土默特右旗、土默特左旗、喀喇沁旗迁来一部分蒙古人,他们带来了辽河、大凌河流域先进的蒙古文化,成为杜尔伯特旗有文化的人。同治年间开始,杜尔伯特旗的贵族台吉,聘请土默特、喀喇沁人做‘巴格西’,即家庭教师,给其子女教授蒙文。当时巴彦查干王府、后新屯贝子府、东吐莫公府、保日浩特公府等4 处都有巴格西教授王公台吉贵族子弟。”[7]“光绪三年(1877年),杜尔伯特旗后新屯台吉道尔吉,创办了一所家庭私塾,从土默特旗请来一位兼通蒙古、汉、满三种语言文字的教师王金宝先生做家庭教师,教授其儿子乌尔图那苏图和两个侄子,共3名学生。”,“宣统元年(1909年),杜尔伯特旗扎萨克府所在地巴彦查干建立一所蒙文私塾,共7名学生,都是王公、台吉和扎萨克府官员子弟,从喀喇沁旗聘一位冯先生任教。主要教授蒙古文的《查干套鲁盖》和蒙译本《百家姓》、《三字经》、《名贤集》、《千字文》等书籍”[8]。
1.5 寺院教育
建立清朝以后,清廷在蒙古地区大兴喇嘛教,且日趋兴旺。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康熙敕建的杜尔伯特旗寺建成,赐名余庆寺,又称银庙。后来移址重建,改称乌勒木吉特古斯·白雅斯古郎图·查干黑德,汉译为富余正洁寺,俗称大庙。到清朝中期时,兴建寺庙最为兴盛,富余正洁寺已建成庞大的庙宇群落,庙中喇嘛已达500 多人。各努图克也建起自己的努图克寺庙,有势力的台吉还建有家族寺庙,全旗建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寺庙。这些寺庙的喇嘛都通晓蒙古文和藏文,他们招收沙比(小喇嘛,即徒弟)教授经文,学习蒙古文,所以,寺庙的喇嘛是杜尔伯特旗学习和传授蒙古文的先驱者。
“黄教毕竟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渊源、吸收了印度——西藏——蒙古等民族文化传统的宗教文化,自有其传播和延续的方式。这就是独特的寺院教育,正是借助寺院教育形式,蒙古的古老文化得以继承下来”[9]。小喇嘛都要经过修行即研习佛教经典才能成为学识渊博的大喇嘛,因此,寺庙成为喇嘛研习经典、探讨学问的学府。较大的喇嘛寺都设有几个专门学部(扎仓),作为喇嘛学习、深造的场所。扎仓共有六种:却伊剌、曼巴、卓特巴、洞阔尔、吉多尔、拉麻哩木,此外还有跳神学部(千巴扎仓)、艺术学部(上下花院)等。有些寺庙几个学部全都设有,称学问寺,很多喇嘛在这里学习毕业获得较高的学位,荣归家乡寺庙,或被外地寺庙迎请担任住持。多数寺庙的学部难以设置齐全,但至少也设有一个或两个。因而,各地喇嘛寺就成为了学校,既是喇嘛唪经朝拜的场所,也是研讨学术的组织,学位较高的喇嘛是教师、学长,学位较低的小喇嘛则是学生。杜尔伯特旗富余正洁寺也设有学部,一是阿克巴扎仓,即密宗学部;二是曼巴扎仓,即医药学部;三是洞阔尔学部,即学习天文、历算、占卜等自然科学学部。喇嘛们无论学习哪一个学部的学问,佛教经文是必须熟读背诵的,只有达到“莫勒伦巴”的学位,才有资格当达喇嘛。在东北各喇嘛寺庙,佛经文本大多都是藏文的,唯独杜尔伯特旗富余正洁寺的经文是蒙古文的。全旗各努图克庙、家族寺庙的喇嘛们也都学习蒙古文经书,用蒙古语诵经。所以,富余正洁寺成了全旗蒙古语文教育的最高学府,也是全旗继承、弘扬蒙古族文化的圣地。
1.6 学校教育
清末,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再无能力遏制蒙古地区的教育,地处偏僻的杜尔伯特旗也迎来了教育的曙光。移民垦区首先办起了学校教育,但没有一所是为蒙古族子弟学习蒙古语文而设立的。光绪年间在旗内三个驿站和珰奈屯开始建立学校: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在多耐站(今巴彦查干乡太和村)设立武兴(武兴设治公所)初、高等小学校、在他拉哈站(今他拉哈镇他拉哈村)设立武南初等小学校、在温特河站(今泰来县大兴村)设立温特河初等小学校、在珰奈(烟筒屯镇珰奈屯)由安达厅翟卒创立一处国民学校并招收蒙人子弟9 人。宣统元年(1909)六月,武兴初、高等小学校改称局(哈拉火烧屯垦局)立第一初、高等两级小学校,武南初等小学校改称局立第一初级小学校。另外,多耐站王纯嘏创办私立女子小学校1 所。这样,共建立学校5 所。这些学校是安达厅、武兴设治公所等移民垦局设办的,主要招收的是汉族子弟,学习汉文,蒙古族子弟极少。
在清朝200多年严密控制下,蒙古族教育极为落后。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廷被迫推行新政,筹蒙改制,才给蒙古以极大的冲击与震动,使蒙古民族内部产生了图强变革的意识和主张。开启民智、兴办教育,成为振兴蒙古的首个要务。杜尔伯特旗内没有学习蒙古文字的学校,但在齐齐哈尔创办的东部各蒙古旗联办学校,为杜尔伯特旗蒙古族子弟创造了学校教育的机会。据《黑龙江蒙文教育史》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在省城齐齐哈尔兴育学堂旧址,今东四小学校址处成立了满、蒙师范学堂。招收杜尔伯特旗、郭尔罗斯后旗、扎赉特旗、依克明安旗以及布特哈、墨尔根、瑷珲等地有满、蒙文基础并识汉文者入学,学制一年半,以译文为主课,为少数民族学校培养师资为宗旨”[10]。据《黑龙江省志·教育志》表2-103记载:“满、蒙师范学堂,校址在省城西门外,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开办,教职员10人,班数2,学生90人。”[11]杜尔伯特旗一些有条件的蒙古族子弟纷纷到这所学校读书。可知,到了清末,杜尔伯特旗蒙古族子弟才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盛京将军将原有奉天八旗蒙古文官学改建为蒙古文学堂,并从次年起招收哲里木盟各旗蒙古子弟。该校后来又扩建改称为蒙古文高等学堂。杜尔伯特旗蒙古子弟,又多了一个接受学校教育之处。
关于杜尔伯特旗的清末教育情况,理藩院叶大匡、春德的《调查杜尔伯特旗报告书》的“学堂”条有记载,基本反映了本旗学校教育的状况。现移录如下:
“杜尔伯特旗蒙众多不读书,不特读汉文书者极鲜,即读蒙文书者亦甚寥寥。因该旗印务处不用汉文翻译,故旗众亦不读汉文书。历年虽奉明诏谕令蒙旗兴学,而该旗茫无所知,不解学堂作何办法。其始黑龙江省拟由所属蒙旗各捐助学堂经费银五千两,今将蒙旗学生概送省城学堂肄业,而蒙旗子弟不肯远赴省城,各旗又互相观望,费亦未缴,因循至今。昨由江省提学司札派东布特哈镶白旗人,名平德布者,到该旗创办学堂。阅札文内所言,系因蒙人阜海曾在黑龙江省报效开办蒙旗学堂,经费银三千两,除拨二千两开办呼伦贝尔小学堂外,余賸千两遴派江省满蒙师范学堂毕业生五人,分驰扎赉特、依克明安、前后郭尔罗斯及杜尔伯特旗各创办小学堂一处。发给各该学员银各二百两,以十两作赴蒙旗旅费,以五十两採办教科各书及黑板、粉笔应用等物,以五十两置办桌凳,按月发给该学员薪水银十六两、伙食银四两,纸笔柴炭油烛银六两,堂内仆役工食银六两,月共额支银三十二两。自本年七月初一日起,所有常年经费即由各该旗自筹支给。拟此办法为蒙旗提倡开学,实于学务前途大有裨益。惟该学员平德布汉语稍逊迟钝,字音亦未真确,恐于口讲指授稍难。及该学员见该扎萨克后,贝子谓现在尚无经费,负债数万亦尚未还,无从筹措,且学生汉语不通,汉字不识,一时亦难照学堂办理。惟先将私塾改良,暂招学生习学汉语,认识汉字,俟明年升科有款,再行请派学员办理学堂,现请暂行回省云云。平德布因即回省,该旗仍无学堂。该旗意欲先将私塾改良,使通汉文汉语,再改学堂规则,亦属蒙旗切要办法。此外,该旗境内三台站均各立学堂,经费地方自筹,概系商民及站丁子弟,蒙人则不与焉”[12]。
此种学校教育窘状,完全是因为清廷在200多年间对蒙古旗文化教育加以别有用心的遏制所致。
[1]吴廷燮等.奉天通志(教育二,清上)[M].(150).
[2]义都合西格.蒙古民族通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4):445.
[3]义都合西格.蒙古民族通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4): 453.
[4]义都合西格.蒙古民族通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4):445.
[5]理藩院则例·宾客清吏司·教养[M].乾隆朝.
[6]波·少布,乌云达来.黑龙江蒙文教育史[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4:52.
[7]波·少布,何日莫奇.黑龙江蒙古部落史[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1:144.
[8]波·少布,乌云达来.黑龙江蒙文教育史[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4:55.
[9]义都合西格.蒙古民族通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4):453.
[10]波·少布,乌云达来.黑龙江蒙文教育史[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4:57.
[11]黑龙江地方编篡委员会.黑龙江省志·教育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6:266.
[12]叶大匡,春德.哲里木盟十旗调查报告书[G]//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一.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393-396.
[责任编辑 宝 玉]
2017-06-04
包玉林(博彦贺喜格),1949-,男,蒙古族,黑龙江杜尔伯特人,黑龙江省民族研究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蒙古学研究会理事长、杜尔伯特文化研究会理事长、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蒙古族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