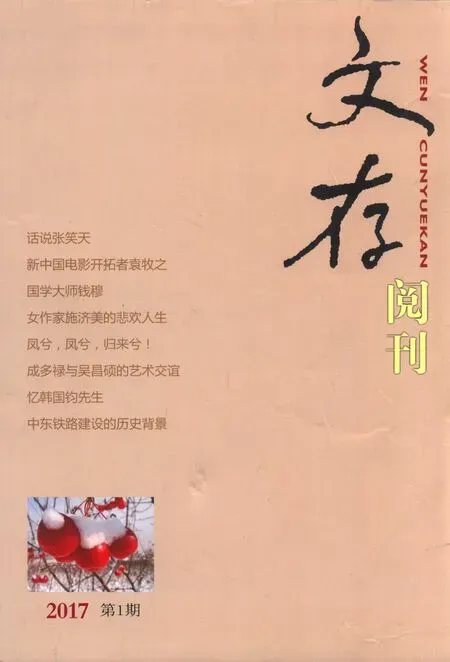话说张笑天
乔迈
话说张笑天
乔迈

2016年2月25日,中国著名作家、吉林省原作协主席张笑天先生仙逝。先生生前,为吉林省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文存阅刊》杂志也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指导。在纪念先生离去一周年的日子,我们选编了一组回忆先生的文章,以表达对先生的缅怀和思念之情!
张笑天天生就是当作家的材料。天工造化,造化神奇,直木为梁,曲木为犁,该成龙的成龙,该成凤的成凤,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十步之内可寻芳草。
1939年11月13日,有位男孩在张广才岭和松花江环抱的一个小地方 (黑龙江省延寿县)出世,那男孩刚一君临世界就仰天大笑——是为笑天——他那笑声包含的信息加以解读就是:我不必作将军或巨贾,我当成为作家。
邓友梅说,张笑天是怪才
什么叫“下笔万言,倚马可待”?说的就是张笑天。想当初,他刚从隐藏在长白山皱褶里的山城敦化调来长春电影制片厂,远没有像后来那样如雷贯耳,如日中天,却已经开始制造神奇和传奇。
从1973年张笑天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雁鸣湖畔》迄今30年来,读者和观众见到他的作品计有:长篇小说21部,中篇小说52部,短篇小说和散文难以胜数,电影文学剧本40部,已拍摄24部,电视剧300部(集),还有只收纯文学作品的《张笑天文集》,这样巨大的产量,在中国作家中,如果不说是绝无仅有的,也得算是为数甚少的,极为罕见的,叫人吃惊不小的,文坛之上难得一遇的。
围绕张笑天写作之快,曾出现了种种说法。怀疑论者大摇其头连呼“不可能”,说“那怎么可能”;相信论者则在张笑天头上制造了一个神秘光圈,例如说这个人可能长了两个脑子,写作时,一个脑子管上句,另一个赶紧琢磨下句,张笑天的朋友、如今已然驾鹤西游的作家顾笑言就对张笑天说过:“不用臭美,等你死了,看那些医学院怎么抢你脑袋当研究材料吧。”
1981年夏天,有一个笔会在大长山岛举行,笼络来不少小说家。大作家邓友梅来了,也是大作家的从维熙也来了。二位都在20世纪50年代早早成名,与此时资历尚浅的张笑天比起来,恍然前辈。
偏偏邓友梅跟张笑天合住在一幢将军楼里,邓住里间,张在外间。
有一天会方没安排活动,大家意识到主人圈鸡准备捡蛋了,于是赶紧埋头书案。邓友梅虽然贵为前辈,其时年龄也不大,人又非常随和爱乐子,尤其是他那一双眼睛,总是带着很有生气的顽皮模样,无论谁跟他接触,都会从心底里感到投缘。那时候邓友梅就不好生下蛋,一会儿从里屋溜出来,踅到张笑天身后偷看,每一回都见到那个年轻人在伏案疾书。午餐时他就郑重报告大家,说笑天已经写了几千几千字啦,弟兄们多努力呀。大家就都转过头来看那个快手,主人就大高兴叫服务员快斟酒快斟酒呀发什么愣呢!
邓友梅和从维熙后来把他们的观感形诸文字,给我们留下关于张笑天写作的第一手资料,二位文坛大家写道:“我俩曾目睹他的笔下如行云流水,一日之内,写成万余字的短篇小说。不但文稿清清爽爽,而且少有丢字漏词及涂抹之处。文思的彩翼在稿纸上展翅飞翔,使同行们为之目瞪口呆。”
那次笔会,张笑天于不经意间风头出尽。面对才华横溢的京、津、沪作家以及江南塞北才男俊女,为关东文人长了志气。
邓友梅和从维熙在惊叹张笑天非同寻常的写作效率时,曾试图解释缘由,他们写道:“如果仅用‘精力旺盛’和‘年富力强’来探索笑天同志的创作道路,或用‘才思敏捷’以及‘天赋厚实’等词汇,来解释发生在笑天同志身上的文学现象,那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文坛上‘年富力强’和‘才思敏捷’的佼佼者,多如天上繁星,但在创作产量和作品表现的生活幅度上,都是很难和笑天同志媲美的。”
这几乎就是一锤定音。后来,文学界在碰到张笑天连绵不绝地发出的难解之谜时,就都摇摇头,说一句“真个怪才”,然后大家各自走开了事。
这个张笑天,他为文是个“怪才”,他的为人也是颇为怪哉的。
阎敏军说,你大事不糊涂
早先当过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阎敏军跟张笑天一块去日本访问,有一天,忽然看着张笑天含笑点头,说:“你这个人呀……”张笑天被顶头上司看得心里发毛,却还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问:“我这人怎么啦?”
长影厂长说:“你大事不糊涂呀。”张笑天立刻脸绽笑纹,分明有点受宠若惊。他觉得阎厂长对自个的评价可能稍微高了点。不是嘛,若论写东西,他对自己的能力毫不怀疑,但若说到对待生活工作中碰到的“大事儿”,他认为自己嘛……也不差啥。
张笑天才华横溢,四面出击,他的电影剧本创作独树一帜,《开国大典》拍成影片后,连夺10项重奖,跻身“红色经典”行列。《重庆谈判》塑造的毛泽东、蒋介石形象,让人看后耳目一新,连国民党人士也服气,这部戏当然地获得了包括全国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奖在内的多项大奖。他的另外一批电影创作,如《她从雾中来》《佩剑将军》《黄河之滨》和《末代皇后》等,其艺术质量都称上乘。《末代皇后》获巴西电影节奖。张笑天的电视连续剧《亚细亚人》《太平天国》(获电视飞天奖)《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施琅大将军》《孙中山》《明月出天山》等,无一例外地在中央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如果把张笑天在长、中、短篇小说和电影、电视剧五大方面的创作成果,分给5个人,那么,这5个人都会在中国当代文坛成名。一个人同时干了5个人的活计,而且都干得相当不坏。

2012年6月,本文作者乔迈(右二)与吉林省著名作家(右起)朱晶、张笑天、苏守信、于笑然、潘大成合影。
假如人们都像邓友梅那样切近观察张笑天写作,人们都会受到震动。当初我国还没有引进电脑写作,作家们的劳动被形象地叫作笔耕,既然是耕,手上就会留下老茧。多数作家都是食指和中指才有茧子的,张笑天则整个右小臂下部都有,那是洋洋千万字大观留给他的生命一景。刚及中年,张笑天的头顶就迅速变秃,前额愈来愈开阔,额上皱纹愈来愈深峻,走路的时候,背也有点驼了——它们似在默默讲述着一个人的故事,一个高产作家的故事。故事的主旨是:这位作家虽然天赋甚高,但他不是完全仰赖天赋的。
为了当作家,张笑天下过不少人难以想象的笨功夫。一本《新华字典》,8800多字,怎么念怎么解,他全给背下来了,人们惊为奇迹。其实人们只看见了结果,却不知道为了这结果,他是怎样把别人用来闲玩和吃饭、睡觉的工夫都拿来用功的。
张笑天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当过10年中学语文教员,他让学生作文,自己也和学生一起作文(范文),他让学生留心观察生活,自己也跟学生一道观察生活。
他当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辅导老师,大考之前,总要自己先写出二三十篇范文,学生管这叫“押题”,哪知道老师是在同时训练自己写作。他是出色的“押题”专家。1965年高考语文作文题为《我站在世界地图前边》,他交给学生的自作范文中,有一篇题为《我站在地球仪前边》。难怪学生跑出考场,要放声高呼“张笑天万岁”了。这种“恭维”令他在“文革”中大吃苦头,是不难想象的。
他的朋友、如今也已仙逝的作家张天民早些年和张笑天还不熟,抽调到吉林省对台办工作,有一回他交给张笑天一篇稿子,嘱他一星期改出来,哪知道第二天张笑天就来交卷,改得头头是道,张天民愕然曰:“这人可能是站着写东西的。”
“站着写”,就是在没有条件写的地方写,在没有可能写的时候写。“站着写”,形象地说明了这位作家艰难的文学经历和非同寻常的写作能力。“站着写”曾经是他的劣势,他把它转化成了优势。
张笑天自己说:“我是从历史的夹缝里钻出来的。”从夹缝里钻出来的人,自然格外珍惜能够从事写作的时光。
所以他高产。张笑天高产不是像别人揶揄的“写作机器”。就算是机器吧,当它轰轰烈烈开动起来,流水线上不断涌出产品的时候,不是恰好说明这部机器运转灵活,并且有着充足的原材料供应吗?
作家的原材料是生活。张笑天深入生活之认真、刻苦、不避艰难险阻,也是值得称道的,不过外界不大了解罢了。外界只知道他的作品多,就误以为他是光写作不深入生活的。其实,张笑天有多少创作记录,就有多少深入生活的记录,他的作品多,正是仰仗于生活的积累厚实。
为了深入生活,他还敢冒风险。写小说《雨燕岛》时,就和导演陈家林一起跑到麻风病人聚居的孤岛上,连防护服都没穿,就兴致勃勃地和那些有着强烈传染性和危险性的病人谈话,连医护人员看了都说,当作家也不易。
还有,为一部73万字的《永宁碑》,他手抄了多达一千二百余万字的资料,两个月写成初稿,又两个月改完二稿,又一个月改第三稿,其间的困苦劳顿艰辛竭蹶,令人望而生畏。就算是一部机器吧,那也是超负荷运转的机器。不错,张笑天作品是多,名声是大,但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呀!
张笑天说,我怕宣传,让我自己说
张笑天离开长影以后,来到吉林省作家协会,任不管事的兼职副主席,列席党组会议,主要是当驻会专业作家。这样的安排,明眼人一看便知,多少带点边缘味道。但是在客观上,张笑天却祸兮福倚,他卸去了费力不讨好的文学剧本副厂长的繁冗事务,倒可以静下心来写作了。
无官一身轻之后的张笑天,果然恢复了从前的自由潇洒。他像一匹生有健翅的天马,山南海北、天上地下飞来跑去;他又像一只恪尽职守的母鸡,无论走到哪里,身后总会留下捡也捡不过来的蛋。这一时期他的产量之高叫人目不暇接。如果我们有几天没见到张笑天了,忽然见到他,问他“干什么呢”,他说“写电影呢”,那就是说,又一部电影剧本已经脱稿。一件事不做完,他是不会露面的。他这个人,虽然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但在谈到自己时却很有分寸,他随时随地都会产生巨大的创作成绩,但他从不张扬自己。按照中国人的标准,这就是谦虚了。
他又自信,又谦虚。一个名声很大的人能够这样,说明他是处在人生一个较高层面上的。
一个人,你不和他接触,就不能真正了解他。围绕张笑天的种种流言,多数是这么产生的。
天津作家吴若增有一次谈到张笑天,说很受感动,那是由一件小事引出来的。
他们也是一块参加笔会,笔会内容之一是为业余作者看稿子。吴若增很快看完了分到手的部分,却见张笑天走过来,说请他帮着看一篇。他以为张笑天有意偷懒,想捉别人替自己当差,刚要给几句,不料张笑天认真地说:“我看三遍了,没想好怎么跟作者谈,想听听你的意见,一个业余作者,写篇稿子不容易。”
世界上最难的事是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人定是心地善良的人。吴若增为此写出文章发出感叹。
为了能够集中心思写作,他在生活中总是采取低调姿态,不大喜欢抛头露面,在社交场合,他给人的印象往往不大自在,说话很少,也曾对一位朋友坦露心迹,说,那样活着不累吗?他想逃避,不过他逃避不了。人们总要留意他,指画他,包括制造绯闻-——谁让你把自己造就成一位名人呢?
这也没什么。张笑天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他肯定懂得,不管历史怎样曲折发展,最后总要恢复公正。1997年秋天,张笑天众望所归被推举为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其时,他又出手了,是30集电视连续剧《汉宫飞燕》和50集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与电视剧同时脱稿的还有同名长篇小说。张笑天认为长篇小说《太平天国》是他所有作品中的“扛鼎之作”。此前,他还写了电影剧本《北纬38度线》《香港回归》,以及以三峡大坝建设为题材的《世纪之梦》。
随着省作协与省文联合并,张笑天又当上了省文联主席,作协、文联两主席一肩挑。
一个当作家的人都这样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张笑天偏爱讲人生不易-——莫非还是大观园里的凤辣子说得对:大有大的难处-——这位众说纷纭的人物,写过一篇文章,我记得题目叫《我怕宣传,让我自己说》。
唔!张笑天,你想说什么呢?你是不是想说,你的故乡长长的蚂蜒河,苍翠的长寿山,那山那水养育了你,你的作家梦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做起来的?
你是不是想说,在中国做人难,当作家也难,写得慢了说你江郎才尽,写得快了说你胡诌乱侃,你想说作家要理解社会,社会也该理解作家?
你可能还想说说你的童年伙伴、青年友人、老师和同学,还有你的妻子杨静,我听说杨静头一回见到你印象不佳,皱眉说“这个人挺丑的”-——那是由于她自己很俊的缘故吧-——但你后来成为“三家村”在你那小地方的“黑干将”的时候,造反派叫她跟你离婚,她说“那可不行”。
你也许还要说写作辛苦,但假若人有来世,你会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作家这个职业。你是唯物论者,知道来世可能不存在,所以你总想“把来世的活计并到今生一块干”。
哦,张笑天,怪不得你写得那么快那么多!
(作者/著名作家,曾任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