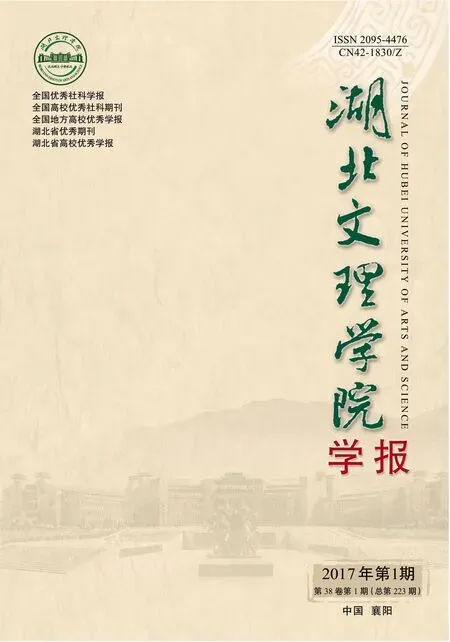城市与乡村:新写实小说的两副面孔
张 望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城市与乡村:新写实小说的两副面孔
张 望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写实小说”拥有“零度写作”“直描原生态生活”两个理论特征,已是文学史的普遍共识。即使如此,仍无法忽视其具体文本存在的城市书写和乡村书写的差异。在文学史公认的四位“新写实小说”作家(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的新写实小说作品中,存在着以池莉、方方为代表的城市书写和以刘恒、刘震云为代表的乡村书写的差异,该差异展现了“新写实小说”的两副面孔,也证明了“新写实小说”的内在丰富性,同时,也揭示出“新写实小说”在命名过程中的矛盾与其理论的尴尬。
新写实小说;城市书写;乡村书写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被一大串不断演进的“词汇”描述着,从“伤痕”“反思”“改革”到“寻根”“先锋”再到“新写实”,记录着中国文学一个潮流不断演进、思潮迅速更迭的特殊时期。作为这个文学链条的重要一环——“新写实小说”——被各种文学史不断加以言说,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无法绕开的重要话题。《中国当代文学史》[1]《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3]等文学史著作对“新写实小说”的概述基本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4]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池莉、方方、刘震云、刘恒四位为代表作家,以刘震云《单位》《一地鸡毛》《故乡天下黄花》、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你是一条河》《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方方《风景》、刘恒《伏羲伏羲》《狗日的粮食》等为代表作品,以“零度情感”的方式“书写生活的原生态”,描写“纯态事实”的文学流派或文学潮流。
但是,进入“新写实小说”的众多文本之中,不难发现“新写实小说”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异”,即以刘恒、刘震云为代表的乡村书写,和以池莉、方方为代表的城市书写之间,在内容选择、写作形式、精神气质上均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而这两类作品所体现出的差异性特征,不仅表明了“新写实小说”的内在丰富性,同时,也使得“新写实小说”的概念或其理论本身显示出某种分裂的不合理之处,而这种不合理,也将“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史地位推向了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
一、物质与精神,不一样的贫瘠
1989年6月《钟山》杂志上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新写实宣言”中指出:新写实小说“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5]然而作为艺术文本的文学始终是不可能达到对于生活的“原生态”还原,所以一切还是取决于作家在写作时的选择。“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写作时,选择了一种相悖于传统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摒弃了对人生重大题材、英雄形象的宏大叙事,而是相反地注视于人的基本生存,追求一种日常化、琐碎化的生活样态的呈现,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特征,表现出顽强的生命欲望和本能冲动。
所以,在内容素材的选择上,不论是乡村书写还是城市书写,“新写实小说”在“直面人生”、呈现生活原生态时,都青睐于描写下层民众的贫瘠和困难的生存处境。
(一)乡村:物质匮乏的困境
乡村的“生存贫瘠”常常表现为农民物质的缺乏,而这物质具体就是吃食。乡村书写的文本常常带有一种强烈的宿命色彩,文本将乡村物质的贫瘠视为一种无因之果,贫困就是贫困,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缘无故,无始无终。所以农民并不为自己的处境感到可怜或者愤慨,也不会追本溯源地思考自己衣食贫困的根源,当然也自然不会产生任何思想上、情绪上的动作,就仿佛是被苦难生活推着走的生物,并不表现出强烈的痛苦,也不表现出奋勇地抗争,只要还拥有一口气,便就这样苟延残喘,艰难但却平静地活着。
刘震云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面叙述到自然灾害使得人民群众饥饿不已,被饿死者成千上万,被逼无奈的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人们为了换得粮食,甚至要将自己的子女拿去卖掉,将自己年轻的老婆和十五六岁的女儿驮到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但即使这样,他们仍然只能换取少量的粮食。《塔铺》中学校大多数同学也处在贫穷之中,“学校伙食极差,同学们家庭都不富裕,从家里带一些冷窝窝头,在伙上买块咸菜,买一碗糊糊就着吃,舍得花五分钱买一碗白菜汤,算是改善生活”,[6]同学“磨桌”因为吃不饱,甚至到厕所躲起来烧蝉吃。刘恒的作品《狗日的粮食》也写农民粮食的贫瘠,在作品中,曹杏花因为吃的缺乏,以两百斤谷子的价格卖给了杨天宽,由于对于粮食的渴望,她的每一个子女都以粮食命名,因为孩子众多,她每天的生活都围绕着一个问题“明儿个吃啥”而过活,无法逃脱的饥荒,已是他们宿命的悲剧。
(二)城市:精神困窘的荒漠
不同于乡村的物质匮乏,城市的“生存贫瘠”常表现为城市人精神的困窘。这里的城市人又要分为两个类讨论,一类是城市的贫民,一类是城市的知识分子。
城市贫民面临着物质贫困所带来的精神困扰,与乡村农民的物质贫瘠不同的是,城市贫民的物质困顿不再是衣食的缺少,而是围绕着住房、薪资的不满足。相比于食物的匮乏,住房的狭窄、薪资的微薄虽然不致命,却充满欲望的挑逗,挑逗着城市贫民顽强抗争,在这过程中他们不断地丧失尊严和安全感,从而形成一种精神上的烦恼与困窘。池莉《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太阳出世》里的赵胜天、方方《风景》里的一家人等等,都是城市贫民的缩影。《烦恼人生》中,印家厚一家住在如猪狗窝一样的房子里,他每天为住房、奖金、家庭关系而操碎了心,这一切都让他感到一种作为男人的无助和失败感,比如在《烦恼人生》的开头,写印家厚的儿子夜晚摔床受伤,老婆抱怨印家厚没本事弄不来大房子才使得儿子摔床,两人于是发生口角,在气愤中印家厚又拉断了电灯拉线,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描述“印家厚异常清楚地看到,所谓家,就是一架平衡木,他和老婆摇摇晃晃在平衡木上保持平衡。你首先下地抱住了儿子,可我为儿子包扎了伤口。我扯断了开关我修理,你借的房子你骄傲。印家厚异常酸楚,又壮起胆子去揪起子。”[7]这段叙述可以看出由于家庭生活水平的低下,他会面临妻子的抱怨,面临儿子的受伤害,这一切都使得印家厚不断得丢失他作为男性的尊严,也让他饱受精神的折磨。这种精神折磨不同于农村贫民,农民的那种即使精神痛苦也是因为不能拥有更多粮食,饥饿的生理痛苦带来的。但是城市贫民的这种精神折磨却是单纯来自于一种“不满足”,而不是“不能拥有”,所谓“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凡是不能参加各种活动并享有该社会习惯上的生活条件和乐趣的人,就是穷人。”[8]所以他们的精神困顿来自于相比较之下的差距引发的痛苦与尊严的丢失。
跟城市贫民又不同的是城市知识分子,他们面临的是一片精神的荒原,一种单纯来自于精神层面的困顿。知识分子的追求与清高,在一个思想不断变幻、价值不断扭曲、欲望无限膨胀、追求日渐世俗的时代面前,突然显得无力和可笑。他们的理想被社会现实消解,价值观不断被冲击和解构,他们不再拥有天然的“优越感”,也不再敢于担当“社会启蒙者”的角色,而是面临着“被教育”“被启蒙”的境地,面对一个不再追求精神崇高的时代和社会,知识分子的消沉和精神困境可见一斑。池莉《你以为你是谁》中的李老师和博士生宜欣、方方《惟妙惟肖的爱情》中的禾呈和惟妙、刘震云《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刘恒《虚证》中的郭晋云便是当下城市失落知识分子的缩影。精神彷徨和“被教育”“被启蒙”是他们面临的无法言说的尴尬境地。一向清高的李老师却只能挣扎在破败拥挤的洞庭里十六号,吃着猫才吃的小鱼,“吃猫食的人还配讲形而上学——你以为你是谁”?[9]博士生宜欣与物质主义者陆武桥交往,被陆武桥“六百六一斤的大螃蟹”“打的回家”等“高谈阔论”迷得找不着北,甘愿成为陆家的主妇。小林遇到做烤鸭店老板曾经的大学同学“小李白”,问起是否还写诗,得到的回答竟是“狗屁!那是年轻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瞎扯淡!如果你还写诗,不得饿死……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你说呢?”[10]听了这番“大道理”的小林也只有点头称是。知识分子就这样在这个逐渐变幻的世界中经历着世俗、私欲的侵袭,甚至被教以放弃崇高理想,去接受世俗观念,这一切都造成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巨大打击。
二、时代与个体,不一样的距离
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命运,铸造了中国由启蒙救亡、发展图强而来的泛政治观念膨胀的社会现实,而这种社会现实导致政治压倒一切,并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而在这种思维方式所带来的特定视角之下,复杂多元的生活关系、丰富个性的心灵都会被扭曲、变异,最后只剩下阶级斗争、阶级矛盾的社会教条式的痕迹。所以回望中国历史学家们笔下的历史,或者说近代史,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很刻板的如演算般的大事件和结论,以及大时代背景中符号化的人物,却永远无法看到真正鲜活的人物、真正的人性。
池莉曾经说:“哈姆雷特的悲剧在中国几个人有?我的悲哀,我那邻居孤老太婆的悲哀,我的许多熟人朋友同学同事的悲哀遍及全中国。这悲哀犹如一声轻微的叹息,在茫茫苍穹里流动,那么虚幻又那么实在,有时候甚至让人留意不到,值不得思索,但它总有一刻使人感到不胜重负。”[11]“新写实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传统历史的某种逻辑链条,并试图重构一种新的历史逻辑。[12]新写实作家们反感于宏大历史观,他们将人物与历史有意地进行拆解,在他们笔下历史、时代的外在显性特性被弱化,而将更多的目光投射于人性和生存状态,使人物生存于历史的感性湍流之中,充分展现小人物精神世界的一切。
虽然“新写实小说”均声称弱化时代背景,关注个体的人性与命运,但落到具体文本却仍具有明显差异。在“新写实小说”的乡村书写中,人与时代背景很明显脱离得更加彻底,历史环境被虚化、弱化得更加彻底,人物更像是一个独立于时代和历史背景之外的个体,生命感更强。而城市书写则不同,虽然我们可以感觉到作家尽量弱化时代感,但是当城市书写对城市人生存状态描写时,仍会发现作家们所截取的那部分生存状态都与当下的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乡村:脱离时代的原始人性
乡村书写虽然将故事都几乎设定在了历史中的乡村,但是这些文本却跟当时的时代背景关系甚少。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就很有代表性。同样是表现乡村社会的贫困,该作品却不同于诸如《白毛女》《创业史》《“漏斗户”主》等“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这些作品大力探讨农村贫穷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将农村贫困的原因归因到阶级剥削、民族压迫、极左思潮迫害等方面,要关注的不是贫困本身,而是让人民看清楚贫困的根源,从而唤起人民为了自我解放而投入斗争。但显然“新写实小说”并不醉心于此,在《狗日的粮食》中,瘿袋女人和丈夫杨天宽,他们口里念叨的永远是“明儿个吃啥”,但他们却从未问过“我们为什么没吃的”。作者关注贫困本身,关注人在困境中的生存状态,却并不关注贫困的原因。新写实作家认为贫困就是贫困,没有缘由,没有休止,这也就是“新写实小说”乡村书写带有宿命意味的原因。同样的,《伏羲伏羲》也并不将人物镶嵌进任何时代之中,而是仅仅关注杨天青和菊豆之间的性爱悲剧,探讨人性中欲与理的矛盾关系。《故乡天下黄花》写的是马村的近代史,但是也并不将一个村庄的历史同时代背景相联接,而是深入到马村的芸芸众生之中,挖掘他们被权力欲望异化的畸形人性。这些文本触探人性最内在的东西,并不刻意地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涂抹上社会意义的色彩,而是力图在一种原初的生存意义的基础上,探寻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本能,因此我们看到的是自然的人,与外在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无关的人。
(二)城市:紧贴时代的社会人格
“新写实小说”的城市书写则区别于乡村书写,虽然关注点仍然在人的生存之上,但是城市书写所截取的那部分困顿的生存状态几乎来自于时代、社会、历史的影响,城市书写写的是社会的人。
《风景》《烦恼人生》这样的作品,都表现人物无休止的、单调的、枯燥的、不断循环往复的生活状态,但是他们生活方式的循环意味和生活环境的压抑并不是出自他们自愿的选择,也非来自他们自身的原因,而是外部社会环境所预设的,是他们无法摆脱的,既然无法摆脱现实,也无法改变,为了获得心理平衡,他们不得不用臆想、梦幻、自嘲的方式宣泄心理压力。其实处于中国计划经济的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意味着一成不变,七哥、印家厚这样的人物就像成千上万的普通百姓的缩影,犹如一个庞大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自身的生命依附于大机器,国家机器的运转为他们带来无休止的循环生活,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一切。到了9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城市书写依旧紧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90年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有了显著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改革开放的现实成果,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康伟业(《来来往往》)、王建国(《午夜起舞》)、陆武桥(《你以为你是谁》)等一大批“时代弄潮儿”形象。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金钱,同时也带来了思想的世俗化,带来崇高理想的陷落、信仰的危机,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理所应当又会看到禾呈(《惟妙惟肖的爱情》)、李老师(《你以为你是谁》)等一大批精神失落的知识分子。所以“新写实小说”的城市书写,虽然想要弱化时代背景,冷静地关注、叙述人本身,但他所截取的那部分生存状态却注定了其无法真正与社会历史背景作一个很好的切割,在叙述人的同时,又无疑不是在叙述时代,所以它触及的也无法是一个“自然的人”。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官方意识形态束缚的挑战与反叛,但真正的解脱束缚,是完全彻底地跳脱出意识形态的捆绑,而让作品变得更加纯粹。“新写实小说”的城市书写,一味地注视于底层贫民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困顿,这种片面的截取,又无疑使得“新写实小说”跳入另一个意识形态的怪圈之中,所以,总的来说“新写实小说”的城市书写依旧紧贴时代背景,无法做到很好地脱离。
三、零度情感成立与否,不一样的程度
“零度写作”是新写实小说被公认的特点之一。“零度写作”这一概念是罗兰巴特在其《写作的零度》中提出的。正如研究者们所普遍认同的,“新写实小说”的零度写作特点主要表现在作家对于自身所描写的生活现象保持客观态度,尽量淡化主观情感的直接介入,不显示明显的判断倾向,强调去除政治性、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纯洁写作”。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零度”并不是说无情感、无倾向,我们发现“新写实小说”在高举“零度写作”这面旗帜时,其代表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却不断地与之背离,特别表现在城市书写之中。和城市书写相比,“新写实小说”的乡村书写似乎将“零度写作”做得更加到位。
在乡村书写中,一切发生的人的行动和行为,似乎都无关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没有什么革命与反动、也没有先进和落后、敌人与朋友。对于所有行为,文本都不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感情倾向,作者也不做简单直接的价值判断,或者说我们难以明显地看出作者的价值取向,本能冲动成为人物的全部动机以及情节的基本推动力。[13]刘恒《狗日的粮食》中瘿袋女人为了粮食做出很多不知廉耻的行为,但是对这一切的描述,文本只作平静地展现,并没有做出任何道德判断。《伏羲伏羲》里杨天青与自己的婶子发生不伦的关系,文本也没有加以道德伦理上的批判,相反是从人的性欲望、本能爱出发来展示一种道德伦理与人性本能的矛盾冲突。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中,人们饥饿到卖儿卖女,将漂亮的妻子卖为妓女换得粮食,面对这一切作者也不做价值判断。同时在小说中还提到面对1942年的饥荒,最有效最实际的救济是欧美人的粥场和日本人的军粮,于是他抛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饥饿,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面对这样一个平时可以轻易作答的问题,作者却在最后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样不作价值判断。
不像乡村书写的文本对于农民的行为不做简单的价值判断,“新写实小说”的城市书写则处处表现出作者对于城市贫民和城市知识分子处境和行为的价值判断,不论是理解下的包容与肯定,还是审视下的批判与质疑,都可以从文本中明显地找出蛛丝马迹。比如“新写实小说”作家池莉,她的作品就常常用一种关切、认同的态度,来描述城市人的世俗生活。除此之外,她的小说还常常借人物之口发一些议论,或者抨击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比如她的代表作《不谈爱情》,小说并非不谈爱情,而是不谈虚指意的爱情,池莉以温和的态度认同了一种平庸的世俗爱情,她将爱情比作一场交易,家庭、地位、身份均是筹码。小说中的吉玲为了摆脱花楼街,嫁到知识分子家庭,可谓处心积虑、用心良苦,同样的知识分子庄建非也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在婚姻里就像打仗般相互算计着。但即使这样,池莉还是借小说中梅莹这个人物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倾向,“婚姻不是个人的,是大家的。你不可能独立自主,不可能粗心大意。你不渗透别人别人就渗透你。婚姻不是单纯性的意思,远远不是。”[14]她将婚姻看做一种互相渗透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建立于纯粹爱情之上的婚姻,也就表明了池莉本人对于世俗婚姻观爱情观的认同。再比如方方的《风景》,它以冷静近乎冷酷的语态描写了一个最底层家庭的奋斗与挣扎,深刻地还原了底层生存的图景。虽然她用一种极端强化的不动声色、冷静客观来叙述,但是仍然不能忽视其中潜藏的批判性,方方曾在《仅谈七哥》一文中表示:“该责难和痛恨的是生长七哥们的土壤。”[15]所以它批判了我们周遭生存环境对于人性的扭曲与异化。
四、“新写实小说”的内在丰富性与命名尴尬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零度情感”的方式“书写生活的原生态”,描写“纯态事实”的“新写实小说”并非文学史或者评论界认为的那般“整齐划一”。立足于“新写实小说”在学界所公认的几大特点切入分析探究,发现在“新写实小说”内部,可以划分为以池莉、方方为代表的城市书写,和以刘恒、刘震云为代表的乡村书写,这两者在内容选择、写作方式和精神气质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值得关注。同时,“城市新写实”与“乡村新写实”的差异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新写实小说”内在的丰富性,而在这种统一的“新写实小说”概念之下所彰显的丰富性,又在有意无意地挑战“新写实小说”的理论底线,从某种程度上揭露出“新写实小说”命名及其理论的尴尬。
20多年前,被评论界推崇或者说“炒作”起来的“新写实小说”,在今天看来是那么面目不清,同其他流派的作品之间的界限又显得那么模糊。所以,与其将“新写实小说”视为一个文学流派,不如说其更像一个阶段性的转瞬即逝的文学创作风潮,多少年来,“新写实小说”在大众误读与文学史重述中被不断地建构,[16]大众话语的广泛传播以及文学史叙述的权威性,使得“新写实小说”成为一种不可质疑的定势存在于接受者之中。“新写实小说”的提出距离历史现场太近,在一片“喧哗与骚动”中被匆忙提出,也就易被表面的片段印象和自身的主观臆测所迷惑,而匆忙地下新的结论,或者易用已有的理论框架去应对新的文学创作现象,从而制造出新兴文学虚假繁荣的泡沫。同时,“新写实小说”理论要求仅仅立足于当时一小批文学作品的表面特征而提出,时间一长,作品一多,也就使得作品和理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因此即使在20多年中“新写实小说”不断扩大其理论外延、也并不足以将“新写实小说”本身与其他的小说流派区分开,所以,被强行规约到这个概念之下的作家作品之间存在众多与其理论相悖的差异也就不奇怪了。另一方面,文学制度的规约一定程度地影响文学史的书写。1949年以来,各类文学史几乎就是各高校通用的文科教材,在这个前提下,学者们修文学史时既要保证作为大学教材的绝对权威性,又要尽量保持客观公正,避免个人情感与偏见的介入。这就使得文学史家陷入一种不自由的境地,很难在叙述同时代文学史的时候全身心地投入到与文本和作家的对话中,通过细读文本和感悟来实现其对作家作品的独特价值判断。[17]于是他们采取讨巧的方式便是套用批评家或者媒体制造的,在读者的观念里业已形成绝对优势的话语方式来叙述,文学史家一味地跟随在评论家和媒体之后人云亦云,就很难做出很有见地和个性的文学史作品。文学史叙述与大众强势话语的合谋使得“新写实小说”即使内部呈现出如此巨大的“城乡分裂”,外表却仍然显示出“不变的大统一”。
20多年后反思“新写实小说”带给我们的启示颇多。为了避免新的文学流派与其理论相脱节的尴尬,新的文学流派、文学概念的提出需要将时间的跨度拉大,去宏观地审视与思考,需摒弃大众强势话语的干扰,不断地去伪存真,新的文学理论和概念才会褪尽一切的浮华与骚动,真正地获得不断发展的生命力。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45-347.
[2]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306-310.
[3] 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77-180.
[4] 王莹莹,张小刚.“新写实小说”的文学史形象——兼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若干问题[J].广西社会科学,2010(7):102-108.
[5] 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卷首语[J].钟山,1989(3):4.
[6] 刘震云.塔铺[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34.
[7] 池 莉.烦恼人生[M].北京: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6.
[8] 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在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49.
[9] 池 莉.你以为你是谁[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34.
[10] 刘震云.一地鸡毛[M].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33.
[11] 池 莉.我写《烦恼人生》[J].小说选刊,1988(12):22.
[12] 崔建军.人和历史反思与重构——对新写实小说文化价值的一种认识[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29-30.
[13] 崔志远.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48.
[14] 池 莉.不谈爱情[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48.
[15] 方 方.仅谈七哥[J].中篇小说选刊,1988:5.
[16] 陈小碧.“误读”与重述:话语建构中的“新写实”[J].文艺争鸣,2011(12):40-46.
[17] 马德翠.对“新写实小说”如何进入文学史的反思[J].河北学刊,2007(4):124-127.
(责任编辑:倪向阳)
City and Country: Two Types of New Realistic Novels
ZHANG W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The new realistic novel, spring up in 1980’s, is characteristic of “zero writing” and “directly writing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life”. Even s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rban literature and the rural literature should not be ignored. In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 difference shows two types of new realistic novels, and the richness as well. Meanwhile, it discloses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process of naming and the embarrassment of its theory.
new realistic novel; urban writing; rural writing
2016-11-21
“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SWU1609312)
张 望(1993— ),男,重庆万州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I207.67
A
2095-4476(2017)01-005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