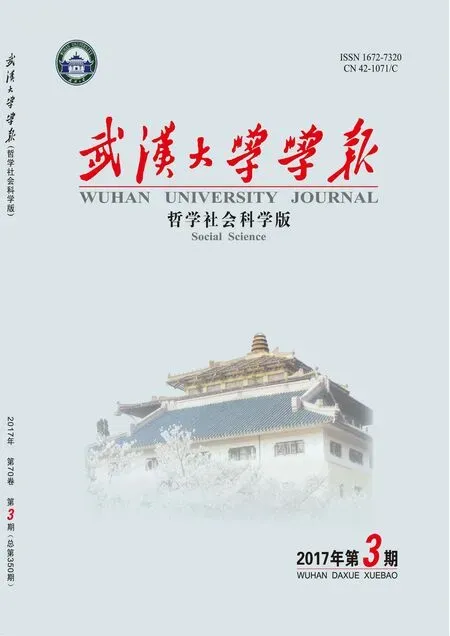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约束
叶海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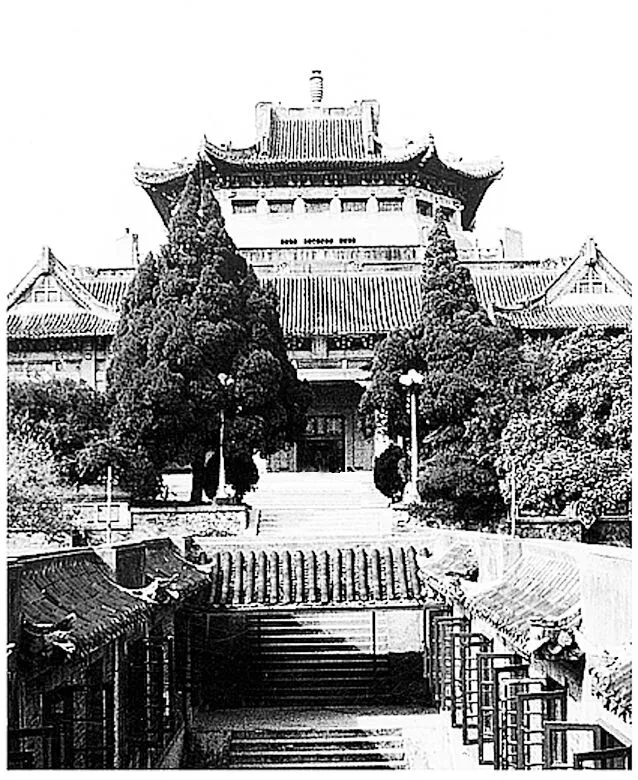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约束
叶海波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认识分歧凸显了改革应遵从何种宪法程序、如何恪守宪法边界及如何落实宪法指示的理论问题。以修法程序改革的观点不但逻辑错误,也必然导致监察全覆盖与人大无限权力间的内在矛盾。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当遵从宪法修改的程序,先由全国人大修宪创设机构,再实施宪法建立机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当恪守宪法根本规范确立的边界,不得改变以“党领导人民建设一个民主、法治、权力制约和人权受保障的现代化共和国”为内容的宪法根本。权力单向监督并非宪法根本规范的核心内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形成闭环式的权力监督结构,但并未动摇人大制度的根本。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当落实宪法的指示,合理配置监察权,建立监察组织法、行为法和基准法的融贯体系,以法律明确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和监察标准,并以既有的机关监督机制为基础建立环伺式的监察权监督模式,形成“有限”和“有效”监察的国家监察法治体系。
国家监察; 宪法; 约束; 体制改革
自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渐次展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便是其中之一。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2016:2)指出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2016年10月27日,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中共中央委员会,2016)2016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顶层设计步入实践操作阶段。随之,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6年12月25日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由党的意志和党内决策转化为国家的意志和法律规定。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历史性地将监察机关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并列,激发社会对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热烈讨论,其中的主题之一便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法律根据。针对这一问题,马怀德教授(2016:3)主张修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童之伟教授(2016:3-13)提出修宪改革国家监察体制的主张,二者观点鲜明对立。同时,对于修宪改革国家监察体制的限制和限度,秦前红教授(2017:176-182)认为,监察体制改革难以突围我国以人大为核心的一元二层权力单向监督的构架,否则便颠覆了人大制度。上述理论争论反映了法治国家的基本共识,即论者均认为“改革权”的行使必须于法有据,并触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关键议题——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约束。然则,源于论题的限制,上述诸位学者并未全面论述这一议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旨在通过设立国家监察机关,完善国家监察制度,形成“人大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一委”,实现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全面和有效监察,具有三个根本特征:(1)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监察权配置为核心内容的公权行为,遵循权力法定的原则;(2)国家监察机关作为反腐败机制,具有工具性价值,服从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3)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宪法上权力关系的重新配置,属于宪制的变迁。基于这些特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须服从法治的根本原则,而相关理论研究则应当回答如下三个问题:一是作为一项公权行为,依照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权”属于何种性质的权力?应当由哪一国家机关行使?应当遵循何种法律程序?质言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当服从何种程序性约束?二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重置现行宪法确立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这种“改革权”受到何种实体层面的限制?能否变动宪法赖以存立的根本规范?是否存在宪法上的边界?三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实现何种目标?现行宪法是否为国家监察制度的设计确立了优劣和良善的判断标准,从而构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根本指示?上述三个问题次第铺开,依次涉及以什么方式开展改革(程序)、哪些内容可以/不可以改革(边界)、如何通过改革形成最佳制度体系(指示)三个基本问题。本文试图在回应相关学术争论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程序
现行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国家机关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习近平总书记(2014:1)将这一宪法原则在改革中的应用阐释为:“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作为一项涉及国家权力重新配置的重大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自然也必须依法而行。考察现行宪法可发现,“监察”一语分别出现在宪法第八十九条*该条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和第一百零七条*该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仅指行政监察。更为明确的是,现行宪法中的国家机关并不包括与“一府两院”并列且由同级人大产生的国家监察机关。如何在法治轨道上行使这项重大的“改革权”,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将国家监察机关安置于宪法和法律之中,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面临的首要课题,也是法学界应当回答的问题。
(一) 修法抑或修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法治路径之争
关于如何依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法学界形成了修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和修宪改革国家监察体制的两种观点。马怀德、张瑜教授(2016:A4)认为可以由国家立法机关以修改法律的程序改革国家监察体制,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将之更名为《国家监察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形成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的监察委员会,统一行使监察执法权,对所有国家机关、公务人员、法律法规授权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国家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务管理活动的组织进行覆盖式监督。如若按照马怀德教授的主张行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可以快速铺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修订事实上构成对现行宪法的实质修改,修法行为及修订后的《国家监察法》必然受到合宪性追问,国家监察机关的权威可能因此而弱化。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这一追问的实质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可以行使立法权实质性的修订宪法。马怀德教授(2016:3)对此作出如下回应:人民享有国家的一切权力,全国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故全国人大可以行使国家的一切权力,包括设定国家机构的权力。全国人大可以制定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故享有制定设立国家机构的法律和作出设立国家机构的决定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可以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作部分修改,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作出关于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根据惯例,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设立国家监察机关。这一回应的实质是认为全国人大的权力源于人民,人民享有多少权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便享有多少权力,其权力范围不以宪法为限,其权力行使也不受宪法限制;基于这一前提,并不存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修改方式设立监察机关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的问题。修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论的本质是全国人大至上论,这致使该主张存在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无限的主权性权力,国家监察机关便不可能监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就无法实现公权行使监察全覆盖的目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将功亏一篑。
童之伟教授(2016:5-6)在批判修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论的基础上提出修宪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论,认为“全国人大无权在没有宪法根据的情况下创设新的国家机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只可以行使全国人大的部分权力,无权行使全国人大的全部权力”,“讨论做重大政治改革的授权问题,要以宪法为根据,不能以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近年来作出的授权决定的领域和范围’的主观感觉为根据”,“全国范围设置国家监察机关必须修宪才行。”虽然修宪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论并未明确回应全国人大与现行宪法的关系,但显然,其中隐含的前提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源于宪法,受限于宪法,立法权的行使不能导致宪法的实质修订,否则便与宪法规定不符,实质是主张“宪法之下的立法权”。总之,童之伟教授(2016:3-13)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于宪法的授权,现行宪法明确授予全国人大修宪权,不能以法律修改的方式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行修宪权之实,唯有修改宪法方能全面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无论是试点改革还是全面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均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二) “人大职权”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路径
围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法治路径之争凸显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核心命题之一,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程序约束,其实质是全国人大改革国家监察体制的宪法权限问题。根据现行宪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全国人大行使基本法律制定权,制定基本法律,享有修宪权,可以修订宪法,两种权力性质不同,行使程序有别。修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论以人民的名义确证全国人大的无限权力,在此基础上主张全国人大立法权的无限性,以常设机关的地位证成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无限权力及其对全国人大的替代,若果真如此行事,组成人数较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便可以以立法的形式配置国家监察权,设立国家监察机关,实质性地修改宪法。这明显违反修宪程序和人大权限的宪法规定。修宪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论主张唯有修改宪法才能全面设立国家监察机关,但未全面地从理论上批驳修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论的论据,特别是“全国人大可以行使人民所有的一切权力”的人大主权机关论,理论上应当在厘清全国人大宪法地位的基础上明确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程序。
现行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宣告了人民主权原则。该条又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有学者据此认为,全国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主权机关(江国华,2004:380-397),完全统一地行使国家的一切权力(蔡定剑,1998:28),全国人大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不受任何实定法限制,其中的规则形成权,既包括制定宪法的权力*韩大元教授认为全国人大为我国制宪机关,享有制宪权。参见周叶中主编:《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0页。,也包括制定民事、刑事等法律的权力,属于一国的根本性权力。在《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合宪性讨论、《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之争中,人大主权机关论均被一些学者征用为立论前提(叶海波,2013:23-24),修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论同样如此。人大主权机关论及其应用者将全国人大视为位于宪法典之先、之上、创制宪法的主权者,是对现行宪法第二条的错误理解。
现行宪法第二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二者指向的权力具有本质区别,前者的用语是“权力”并指明是“一切权力”,后者的用语是“国家权力”,但未明确是“一切国家权力”。人民享有的“权力”是一种主权意义的本原性权力,具有派生性,是一种政治决断权,主要表现为制定宪法,创制国家制度,授予具体的国家权力,形成国家权力架构。作为主权决断的结果,具体的国家权力自然也为主权者所享有,因此人民享有的“一切权力”包括本源性的主权(创制宪法的权力)和被派生的具体国家权力(宪法创制的权力)。全国人大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可以行使的权力只能是与其代表机关的地位相称的权力,而且必须是人民通过制定宪法授予其行使的权力,这是且仅是宪法设定的、并授予全国人大的“国家权力”,而不是“一切国家权力”,更不是人民享有的“一切权力”。从逻辑上讲,作为代表机关,全国人大至少不享有授权自身具体权力的权力,也不享有选择代表的权力。基于以上的分析,不难发现,修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论的立论——“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就意味着,全国人大可以代表人民通过制定法律、作出决定方式行使国家一切权力(着重号为引者加),包括设立国家机关的权力”(马怀德,2016:03)——明显不能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置将国家监察执法权集中于一个机关之手,既缩小了现行宪法规定的国务院及检察机关的权限,也在形式上扩大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人事决定权和监督权范围,设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因而是更改人民制宪授予的权力范围及宪定权力关系,是对既有授权的变更,必须由人民或其代表以修改宪法的程序来完成。总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享有通过行使立法权,以制定或修改法律、作出决定的方式重新配置国家权力、根本性地改变宪定权力结构的权力。这进而决定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只能遵循修宪程序。
园田杂草的治理须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遵循“安全、高效、经济”的原则,在了解杂草的生物学特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园艺、生物、物理、化学等防除措施,将杂草的危害控制在其生态经济危害水平之下。
(三) 宪法修订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正当程序
宪法以国家权力配置为核心内容,“如果说宪法只规定一项内容,那就是规定政府权力的范围、国家机关的设立、组织及其职权,以及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蔡定剑,2002:95),国家权力的结构性安排属于一国宪法绝对保留的事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结构的重新安排,改革的主体和程序必须符合宪法的程序性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四条规定了全国人大的修宪权及修宪程序,这为全国人大修订宪法改变宪定国家权力配置结构、设置国家监察委员会提供了形式上的权力依据,也构成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基本程序。其具体内容是:只有全国人大方能展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国家监察机关,而全国人大在推进这项改革时,必须以修改宪法的方式进行,并遵循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以及既往宪法修订的惯例,修宪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应当以如下步骤展开: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公开征求意见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据此提出修正案,由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一经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告天下,宪法层面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便告完成。全国人大应当随之行使立法权,制定国家监察机关组织法和行为法等配套法律,实施宪法修正案关于国家监察机关的规定,中央与地方亦应当随之成立监察委员会,行使宪法设定的国家监察权,最终完成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
二、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边界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国家权力关系的重构来实现权力行使的有效监督,属于国家权力宪法配置的更新。“监察全覆盖”意味着对各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的监察,监察内容不可避免地扩展至民主立法*如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议决权行使的监督客观上涉及民主决策。、行政决定、检察事务和司法事务,进而实质性地改变人大制度的内容和国家机关间的宪法关系,形成一种相互监督的关系。概而言之,以修宪的方式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将根本性地改革宪法确立的权力架构和权力关系。那么,全国人大是否可以修改宪法建立全覆盖的国家监察体制全面监察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即现行宪法是否确认一些核心条款,这些条款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具体制度安排构成实质性约束和边界?全国人大修宪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时是否不得改变宪法中的某些内容?如所周知,修宪权是否存在界限,理论上曾有争论(豆星星,2006:3-4),但承认修宪权的宪法限制渐为共识。在宪法中明确限制宪法修改的实例并不少见,美国是始作俑者*该宪法第五条规定:“在1808年以前制定的修正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影响本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第一项和第四项。”。现代国家或者规定共和政体*意大利宪法和法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九条和第八十九条第五款规定均规定:共和政体不得成为宪法修改之对象。、宪法原则和根本精神*挪威宪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修正案决不能同本宪法所包含的原则相抵触,只能在不改变宪法精神的前提下对某些具体条款进行修改。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对本基本法的修正案,不得影响联邦按州划分之原则,各州参与立法的原则或第一条和第二十条规定的基本原则。、领土范围*法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四款规定:如果有损于领土完整,任何修改程序均不开始或者继续进行。等条款不得修改,或者规定宪法在若干时间内不得修改*法国1791年宪法第七篇第三条规定:行将召集的一届和再下一届立法议会,不得提议修改任何宪法条文。或必须修改*葡萄牙1919年宪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宪法每隔10年修改一次。。我国现行宪法虽然设定了宪法修改的程序,但并未明确规定宪法修改的界限,理论上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修宪的实体界限和边界也认识不一。本文认为,宪法根本规范构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外在边界。
(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界限的理论分歧
马怀德教授(2016:03)主张以修法的程序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强调全国人大及常委会享有人民享有的一切权力,自然不认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受宪法约束,因而也不认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存在外在的宪法边界。童之伟教授(2016:6)虽然认为“在宪法规定之外新增设一种在中央与国务院平行、在地方与各级人民政府平行的国家机关,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宪法的根本”,但这里所谓的“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宪法的根本”并非主张宪法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构成实体层面的约束。童之伟教授(2016:6)认为,“是否准许进行改革试点,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范围,要授权进行改革试点必须由全国人大为之”,在试点成功后全国范围内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时,“必须修宪才行”。这一立论的逻辑前提是,宪法是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根本的活动准则,如果以修法而非修宪的方式设立监察委员会,便违反了宪法关于修宪权和立法权的规定,也是对宪法的权威和效力的否定,并且客观上侵犯了全国人大的修宪权,是“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宪法的根本”。推而论之,这种观点认为,立法权必须受宪法约束,修宪权则不受宪法的实质约束。以修宪的方式设定监察委员会,使监察委员会成为宪法上而非宪法外的机构,正是严格遵循宪法规定的行为,也是宪法权威和人大制度的实现,是维护而非“动摇”人大制度和宪法的根本。勿宁说,该文恰恰认为,修宪权正是宪法设定的一项装置,以回应人大制度和宪法变迁的需要,全国人大修宪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时,所要改革的正是宪法中设立的权力制度,因此其修改宪法时不受这些条款的限制。基于这种隐含的认识,童之伟教授(2016:3-13)在探讨如何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纳入法治轨道时,全然未提及全国人大修宪改革国家监察制度的实体限制问题。
秦前红教授(2017:181)在新近发表的论文中以反问的方式提出修宪改革国家监察体制的宪法边界问题,认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前置问题是监察委员会运行要求“宪制机关具备明确的权力分置”。“这个前提是否已具备?”即“人大制度所要求的权力一元与监察体制必备的权力多元如何能相容相生?”秦前红教授(2017:181)持否定的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议行合一”的基本原则,本级人大选举产生其他同级国家机关,其他同级国家机关对本级人大负责,受它监督。这是一种一元二级单向监督的权力结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求权力一元二级转变为权力多元同级,“这意味着对‘议行合一’体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彻底颠覆”(秦前红,2017:181)。质言之,这一观点认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宪制化必然动摇人大制度,即便全国人大以宪法修改的程序展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个根本也动之不得,人大制度构成修宪改革国家监察体制的限制,一元二级单向监督的权力结构构成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外在边界,国家监察只能限缩为对人大工作人员的法纪监督,不宜扩张至立法民主的领域。两种对立性的观点凸显了如下需要明确的问题:修宪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是否受现行宪法的实体性约束?如果这种约束存在,现行宪法的哪些条款和内容构成对这项改革的约束和边界?
(二) 宪法根本规范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禁区”
现代宪法立基于“宪法核心部分理论”之上(陈慈阳,2004:131),主要由宪法核和宪法律组成,宪法核“是一种根本规范,它提供实定法客观合理性的依据,表明实定法创始的出发点”,是“宪法的宪法”,“宪法律是一种相对意义的宪法”,“有关根本规范的内容是不得以任何形式修改与变更的,而宪法律则可根据社会变化的实际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改与调整。”(周叶中,2000:127)宪法核与宪法律相区别的最大效应,“就是建立不得以通常修宪程序更改的宪法核心领域”(吴庚,2004:25)。这意味着,“修改宪法的主要目的是调整、扩大、改善和纠正宪法,不是破坏宪法的结构,或者说违反宪法的根本精神,否则,那无异于‘宪法崩溃’或‘宪法革命’。”(Charles A.Kelbley,2004:1504)以宪法核心理论反观中国现行宪法,不难发现,我国现行宪法也建立了宪法核和宪法律的二元结构。我国现行宪法序言最后一段宣告:“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一宣告以递进式的恢宏气势声明现行宪法作为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缘由:本宪法“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因而是“国家的根本法”,因而“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而是“根本的活动准则”(陈端洪,2016:5-25)。申言之,现行宪法确认了以“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为内容的宪法根本规范,方才成为宪法,宪法修改不得改变这些内容,这些内容自然构成宪法修改的约束和边界。因此,修宪机关修改宪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时,其“改革权”并非不受限制,只能以修改宪法律的方式配置国家监察权,不得改变宪法核。“对宪法的‘修改’权并不包含摧毁它的权力在内。”(William L.Marbuty,1919:225)宪法核具有禁止修改的防御功能,构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外在边界,是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消极和否定性约束。
上引的观点之一(童之伟,2016:3-13)认为只要全国人大以修宪方式改革国家监察体制,便符合宪法和法治要求,显然忽视了“改革权”的宪法约束。另一观点(秦前红,2017:181)认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难以突破人大制度下的权力监督结构和关系,后者实际上是对前者的限制,但对我国现行宪法根本规范的解读值得商榷。我国现行宪法共有六处使用“根本”一语,分别是序言第七段的“根本任务”、序言最后一段的“根本任务”、“根本制度”、“根本法”、“根本的活动准则”、第一条第二款的“根本制度”。其中,“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法”和“根本的活动准则”陈述了现行宪法在实定法体系中的地位、效力及性质。“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是理解现行宪法根本规范的关键词。“现代化”既指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状态,还是一套评价标准,主要指人类以其理性对外在世界加以征服并控制的种种努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指中国人民运用理性建立更具合理性的社会的努力和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通常被分解为根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人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共中央,2014)。这两条规范合而为一,即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的共和国*有学者将“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视为中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第485~511页。。随着实践的推进,我国宪法进一步地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素:首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人民主权原则,次为依法而治的法治中国原则,再为维护人之尊严的人权保障原则。现行宪法的根本规范可具体地表述为党领导人民建设一个民主、法治、权力制约和人权受保障的现代化共和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自然不得在形式上或者实质上更改这一根本规范,这一根本规范构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外在边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通过设立国家监察机关,改变不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实现权力监督的现代化,并强化党对反腐败的领导(王歧山,2016),显然未实质性地改变宪法的根本规范。当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改变了人大制度的内容,因此,理论上需要明确人大制度下的权力监督关系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在“不得为”的层面之外,从“可否为”的角度进一步厘清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边界。
宪法核直接以“不得侵犯”的方式划定了修宪改革国家监察体制的宪法边界,同时明确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可以涉足的空间。简单而言,宪法核犹如一个圆形,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得触及的“禁区”,该区域之外的范围,则可以根据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需要加以变动。理论上的描述易于理解,但实践中的操作则要复杂得多,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边界并非在一张白纸上划一个圆圈并解释为宪法核那么简单,仍需要针对具体的问题作出分析,其中之一便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人大制度的关系。秦前红教授(2017:181)认为人大制度下的权力一元多层单向监督结构构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界限,应当将对人大的国家监察限定为立法民主之外的领域,主要集中于对公职人员的法纪监督,否则便是“对‘议行合一’体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彻底颠覆”。这种观点实质上将权力单向监督理解为宪法根本规范的具体内容。本文认为,应当从人大宪法地位的角度认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人大制度的关系。
日本著名宪法学家美浓部达吉(2005:55-56)认为,代议机关具有三重依次而存的地位:始为代表国民的机关,国民是第一次的原始的国家机关,代议机关是第二次的代表的国家机关,次为行使立法权的机关,终为政治统治机关,监督政府是其主要权能。代议机关的代表、立法和监督功能源于其作为代议机关的宪法地位。我国人大制度亦遵循这样的逻辑,包括民主、立法和权力监督的多重内涵,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代议机关和代表机关,基于民主的原理,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人大并由人大选举产生同级国家机关,人大享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人大制度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和最高制度形式,任何改变人大制度的行为,若产生否定人民主体地位的结果,便是动摇宪法的根本。但需要明确的是,人民主权强调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主要由人民的代表来行使这些权力,人民代表组成的机关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这并非意味着人民代表的权力是绝对和不受限制的。哈耶克(2001:36)明确指出:“‘民主’这个术语仅仅意指:不论存在什么样的最高权力,它都应当由人民之多数或他们的代表来掌控,但是它却没有论涉到这种权力的权限问题。常常有人错误地认为,任何最高权力都必定是无限的或不受限制的。显而易见,我们根本无法从多数的意见应当占据支配地位这项要求当中推论出这样一项要求,即多数就特定问题的意志应当是无限的或不受限制的。”申言之,人民主权和民主原则的确认并非意味着对法治、权力监督和人权保障原则的否定,民主与法治可以有机结合(秦前红、叶海波,2005:66-74)。我国现行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通过列举的形式,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限定于该二条确定的范围,同时在第五条和第三十三条宣告了法治和人权原则。基于宪法至上和法治国家的现代国家原则,人大作为代议机关亦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其享有的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并不能否定对其自身权力监督的必要性,也并不意味着对人大的监督只能是人大的自我和同体监督。事实上,对于在人大中任职的公职人员违法犯罪行为,我国亦存在着多种监督机制。现行宪法第三条虽然规定人大监督同级其他国家机关,但这一规定不应当被理解为禁止修订宪法建立监督人大的制度。本质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既未改变人大作为代议机关的宪法地位,也未否定人民主权原则,更未否定人大基于代表机关的身份而享有的监督权,而只是补缺了人大制度下权力监督的开环模式,有助于形成一个首尾相链的闭环式监督体系,是国家制度合理化和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努力。
三、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指示
宪法“是以根本规范为指导的价值体系与规范体系,它既表现为实定法意义上的规范活动,又表现为超实定法的价值与原理,甚至表现为超合法性的规范。”(周叶中,2000:127)宪法构筑一国的价值秩序,设立国家权力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制度实现这一秩序,并通过这些制度的实施将观念的宪法转化为现实的宪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是谋求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国家监察制度,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落实现行宪法建立的价值秩序。宪法根本规范不仅仅具有设定禁区、禁止修改的防御性内涵,更具有价值实现的肯定性和积极性内涵,构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指示,决定了国家监察制度的内容,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设立落实宪法精神的最佳制度,可谓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方针。笔者认为,契合宪法根本规范、最有助于宪法精神得以实现的国家监察体制,必须是一种达致“有限”和“有效”标准的国家监察法治模式。
(一) 宪法根本规范与有限国家监察
现行宪法的根本规范是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基于现代化的原理与经验,公权力的受限性是其内容之一,这意味着国家监察权的有限性。“有限”意指权限和监督。在权限的维度上,监察权力必须是有限权力,而非无限权力。这首先要求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切权力均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而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则应当是明确、具体和清晰的,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力止于宪法和法律,特别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法对其权力的列举。除了以组织法限定监察权限外,还应当在行为法层面规范监察权。申言之,针对组织法所规定的每一项具体监察权力,应当制定配套的行为法,明确权力行使的程序,包括明确监察对象、监察启动条件、监察程序、监察手段、监察决定,等等*童之伟教授对具体应当制定和修改的法律进行了研究,但并非完全基于组织法与行为法紧密结合的原则。参见童之伟:《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之方略》,载《法学》2016年第12期,第3~13页。。在组织法和行为法之外,还应当制定监察基准法,明确监察判断标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决定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按照管理权限,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监督检查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调查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并作出处置决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不难发现,“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道德操守”均为“口袋式术语”,其内涵和外延并不清晰。立法者应当遵从法律的确定性原则,梳理公权清单,确定合法和合理的标准,建立公德标准,实践监察权力有限性原则。概而言之,在权限的维度,防止监察权过于宽泛的关键是建立监察组织法、监察行为和监察基准法的有机体系,分别明确监察权力的范围、行使的程序和处置的标准。
在监督的维度上,有限监察要求建立基于监察权限的问责机制。童之伟教授(2017:1)认为,防止“监察体制改革过犹不及”,最可靠的办法是“创造和维持制约者与被制约者享有的政治综合权重比大致均衡的局面。”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是如何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我国现行法律确立了多元监督机制,如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检察机关的公诉监督和公益诉讼监督、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以及社会媒体、组织和公民的社会监督,这是有效监督监察权力的制度基础。监察委员会对所在地区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这自然包括对本机关公职人员的监察,因此,国家监察体制不可避免地存在同体监督和自我监督的问题。螳螂捕蝉式的设立监督机构并不经济也无必要,建立具有实效性、环伺式的监察权监督机制,是唯一选择。如上所述,相关监督机制并不缺少,关键是如何强化这些机制的实效。
(二) 宪法根本规范与有效国家监察
权力有限性是宪法根本规范的基本内涵,这不仅意味着国家监察权的有限性,也意味着其他国家权力的有限性,作为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行使公权的制度,国家监察必须是“有效”监察,方才符合宪法根本规范的要求。“有效”意旨高效和实效。高效要求监察权限配置适当、相对集中,监察组织构架完整,内部组织结构合理,监察程序设定清晰,监察标准明确,权力行使流程化,实效则要求监察委员会以维护法制的权威为首要目标,将规范层面的法秩序转化为实践中的权力受监察状态。有效监察的形成,除了要求构建相关制度外,还要求以监察权激活既有监督机制。以立法、行政、检察和审判为例。监察委员会在监察人大、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公职人员时,若这些机关的公职人员存在违反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等要求的情形时,其参与作出的立法与决议、行政决定与命令、检察决定、法院裁判可能违反合法性和公正性的要求,若仅仅处理履职的公职人员而放生这些存在瑕疵的决定,监察的实效便大打折扣。符合法治原则的路径是授权监察机关提请有权监督上述主体的国家机关进行监督,如提请同级人大撤销或者改变其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提请上级人民政府或者同级人大或者常委会撤销(改变)下级/同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提请本级或上级人民法院再审相关案件,等等。在提请的同时,监察机关应当同时提交监察案卷或者报告监察案情,披露相关公职人员违法并影响其履职的情形。这种提请监督机制具有多重功能,既激活了既有的机关监督机制,披露制度又事实上构成对监察机关的监督,同时维护了人大立法和行政决策的自主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的宪法原则。总之,有效的监察体制应当深深嵌入现行法律设定的监督体系之中,各机关间形成互相监督、相互配合的监督方式,并以宪法和法律为监察和监督的唯一根据。
四、 结 语
宪法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遵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当遵循宪法修改的正当程序,不得破坏“党领导人民建设一个民主、法治、权力制约和人权受保障的现代化共和国”的根本规范,并应当建立一套最佳制度落实其核心价值。
首先,全国人大独享宪法修改权,唯有全国人大才能改革国家监察体制,但全国人大必须遵循宪法确立的程序、以宪法修改而非法律修改的方式展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变迁属于宪法修改的范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旨在重构宪法权力结构,实现公权的有效制约,该项“改革权”本质上是修宪权。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享有修宪权,因此必须由全国人大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全国人大的职权源于宪法的授权,必须服从宪法对权力行使的程序性安排,全国人大在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时不能任意为之,必须以宪法修改的程序改革国家监察体制,不得以立法权的行使程序替而代之。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为《国家监察法》的改革方式,虽然高效便捷但面临合宪性合法性缺失的先天不足,只会削弱国家监察的权威。修法改革国家监察体制的观点实际上承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权力的无限性,但又主张国家监察的全覆盖,必然面临国家监察机关如何监察权力无限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问题。以修宪方式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虽然程序相对冗长,但会构筑国家监察制度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更符合以法治方式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原则。
其次,宪法核和根本规范划定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边界,全国人大修宪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时不得侵入宪法根本规范划定的“宪法禁区”。历经数十年的变迁,我国现行宪法形成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一个民主、法治、权力制约和人权受保障的现代化共和国”的根本规范,包括现代化、党的领导、共和国、法治、民主、人权及权力监督等核心内涵。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能改变这一根本规范,更不能有悖于民主、人权、法治、权力制约及党的领导的原则。人大制度下的一元多层单向权力监督结构并非宪法根本规范的核心内涵,也不构成反对双向、循环式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正当理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改变人大制度下的单向权力监督结构,但未改变民主的核心原则,改革形成首尾相衔的闭环权力制约模式,使国家制度更符合法治、权力制约及人权保障等核心原则的要求,亦有助于强化党对反腐败的领导,因而未动摇宪法的“根本”。
最后,宪法是国家法律秩序和价值秩序的根基和根本,不仅禁止任何破坏根本规范的行为,更要求形成具体的国家制度落实国家根本规范,促成现实的法秩序,因而具有价值实现的积极和肯定内涵,是重大改革的根本指示。全国人大应当根据宪法根本规范的指示,依据宪法修改程序,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形成一个符合“有限”和“有效”标准的国家监察法治模式。有限监察要求形成监察组织法、行为法和基准法的融贯体系,以法律方式明确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和监察标准,亦要求激活既有监督机制,有效监督监察权的行使。有效监察要求监察权限集中、组织结构合理、监察流程清晰、监察标准明确,并且将监察权的行使嵌入机关监督机制之中,借助公职人员履职监察实现机关行为的监督,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1] 蔡定剑(1998).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
[2] 蔡定剑(2002).关于什么是宪法.中外法学,1.
[3] 陈慈阳(2004).宪法学.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4] 陈端洪(2016).宪法的法律性阐释及证立.清华法学,3.
[5] 豆星星(2006).论修宪权的界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1.
[6] [英]哈耶克(2001).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淆.载哈耶克.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选编、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7] 江国华(2004).宪法的形而上之学.武汉:武汉出版社.
[8] 马怀德(2016).全面从严治党亟待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光明日报,2016-11-12.
[9] 马怀德、张 瑜(2016).通过修法完善国家监察体制.学习时报,2016-07-14.
[10] [日]美浓部达吉(2005).议会制度论.邹敬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1] 秦前红、叶海波(2005).论民主与法治的分离与契合.法制与社会发展,1.
[12] 秦前红(2017).困境、改革与出路:从“三驾马车”到国家监察——我国监察体系的宪制思考.中国法律评论,1.
[13]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6-12/25/content_2004968.htm.
[14] 童之伟(2016).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之方略.法学,12.
[15] 童之伟(2017).对监察委员自身的监督制约何以强化.法学评论,1.
[16] 王岐山(2016).王岐山在北京、山西、浙江调研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时强调实现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中纪委网站,http://www.ccdi.gov.cn/ldhd/gcsy/201611/t20161128_90211.html.
[17] 吴 庚(2004).宪法的解释与适用.台北:三民书局.
[18] 习近平(2014).把抓落实作为推进改革工作的重点 真抓实干蹄疾步稳务求实效.人民日报,2014-03-01.
[19] 习近平(2016).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05-03.
[20] 叶海波(2013).“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法学家,5.
[21] 中共中央(201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28/c_1113015330.htm.
[22] 中共中央委员会(2016).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2016年10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27/c_1119801528.htm.
[23] 周叶中(2000).宪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4] Charles A.Kelbley(2004).Are there Limits to Constitutional Change? Rawls on Comprehensive Doctrines,Un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and the Basis of Equality.FordhamLawReview,72(5).
[25] William L.Marbuty(1919).The Limitations upon the Amending Power.HarvardLawReview,33(2).
■责任编辑:李 媛
Constitutional Restraints on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YeHaibo
(Shenzhen University)
The essence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is to reconstruct the constitutional power system.How to advance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according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 is a central issue which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will face.Differen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legal procedure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and have proposed jurisprudential problems such as how to exercise the power to reform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according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what is the constitutional restriction on this power.This paper,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restraints on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as its theme, mainly studies which constitutional procefure shall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follow, law amending process or the Constitution amending process? Which constitutional contents can be amended or not when the NPC carries forward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and reconstructs the state power? How to 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al boundary on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How to design specific system? And which system doe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itution’s basic norm mostly?This paper mainly adopt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ogical analysis and text analysis.Firstly, it specifies the main divergences between different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to extract core academic propositions through analyzing scholars’ main viewpoints and theoretical deduction process.Secondly, it summarizes the real meanings and contents of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text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regards them as the normalization premise of the follow-up theoretical deduction.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argues that:First,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power structure and power relation shall follow amending procedures of the Constitution.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aims at reconstructing the Constitution power structure and effective control over public powers, and the NPC shall not arbitrarily exercise the power to reform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The NPC exercises the power exclusively to amend the Constitution and shall reform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following the amending procedures of the Constitution.Second, the core and the basic norm of the Constitution have specified the constitutional boundary on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which is “the constitutional forbidden zone”, and the NPC shall not surpass it when reform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The basic norm of the Constitution i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CP, and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construct a democratic modern republic under rule of law and with human rights safeguarded.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shall neither change this basic norm nor go against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rule of law, restriction of power and the Party’s leadership.As the one-way power supervision structure under the NPC system is not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e basic norm of the Constitution, it can not restrict the reform to form a two-way and circular power supervision and restriction system.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will change the one-way power supervision structure under the NPC system but will not change the cor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while the closed-loop power restriction mode formed in reform allows the state system to meet more the requirements of such core principles as rule of law, power restric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 the CCP’s leading in anti-corruption, so it will not shake the base of the Constitution.Third, the Constitu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legal order and value order.It not only prohibits any behavior destroying the basic norm but also requires forming specific state system to implement the State basic norm and facilitate realistic legal order, so it has an active and positive connotation of value realization and is the fundamental instruction for vital reforms.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shall implement the constitutional instructions, reasonably allocate supervision power, establish an integrated system of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law, behavior law and standard law, specify supervision power and function, procedure and standard, and establish a circular mode to control supervision power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organization supervision system, so as to form a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under rule of law, in which the state supervision power and function is limited and effective.The innovative part of this paper is that it has specified the basic norm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boundary” and “instruction” func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imited” and “effective” supervision standards for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state supervision; the Constitution; restraint; structural reform
10.14086/j.cnki.wujss.2017.03.002
D911;D912.1
A
1672-7320(2017)03-0014-11
2017-01-12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重大攻关项目(14JZD003)
■作者地址:叶海波,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法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Email: yeahighbo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