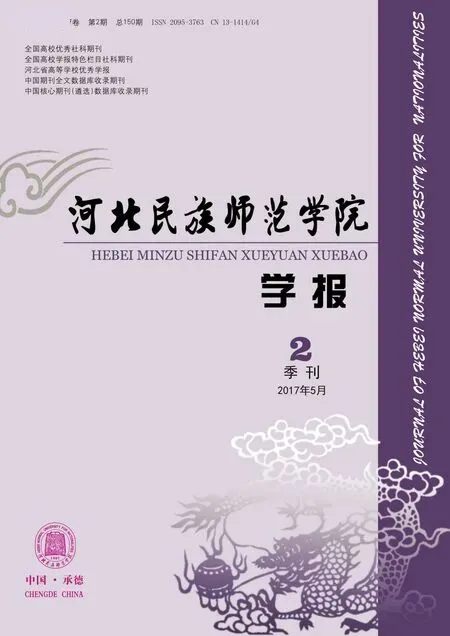中江兆民“心之自由”①思想的形成
常潇琳
(东京大学 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日本 153-0041)
中江兆民“心之自由”①思想的形成
常潇琳
(东京大学 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日本 153-0041)
中江兆民被称作“东洋卢梭”,他曾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翻译成古汉语,在日本乃至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对卢梭的自由思想进行翻译的基础上,中江兆民更是对“心之自由”展开了自己独特的论述。“心之自由”“心思之自由”“リベルテーモラル”等都是中江对“道德的自由”(liberty moral)的译语。本文中,笔者分析了中江兆民“心之自由”的思想之所以得以展开的现实和理论的两方面原因,并且对中江兆民生平文献中的相关论述进行整理,梳理出其“心之自由”思想由伦理学层面逐渐深入到意志自由的哲学层面的思想发展的脉络,最后对其“心之自由”的思想进行评价。
中江兆民;卢梭;心之自由
序言
为了改变日本社会藩阀政府当权、人民不得自由的现状,明治时期,许多日本思想家致力于翻译西洋书籍、发表社论,从而积极提倡公民自由,中江兆民就是其中十分活跃的一位。中江兆民以“东洋卢梭”的称号著称,以学习、引进卢梭的自由思想为起点,在不断地学习、论战等实践中,他逐渐发展出一套具有中江特色的“心之自由”思想。
在中江兆民看来,公民自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行为的自由”(リベルテーポリチック)和“心思的自由”(リベルテーモラル)。其中,“心思的自由”是超越于“行为的自由”之上的更高级的自由概念,并且作为“行为的自由”成立之基础。因此,相对于“行为的自由”,中江兆民更为重视“心思的自由”。②1881年3月18日发表的《东洋自由新闻》第一号社说是已发现的资料中中江兆民谈到自由观的第一篇文章。在该文中,中江兆民首先将“自由”(liberty)定义为“自主、自由、不羁独立”,而后区分了“心思的自由”(リベルテーモラル,liberty-moral)和“行为的自由”(リベルテーポリチック,liberty-political)。船越素子认为:结合《民约译解》中“天命之自由”和“人义之自由”的区分,中江兆民在该文中所说的“心思的自由”和“行为的自由”应当都属于社会状态下的自由,亦即市民的自由(“人义之自由”),不过“道德的自由”非但不能被包含在市民的自由中,反而可以说“道德的自由”才是社会状态中所有自由的基础。(参考船越 素子:中江兆民のリベルテーモラルをめぐって,哲学会誌 (31), 32-43, 1996-07-27)
以往的许多中江兆民研究者们已经“心思之自由”中蕴含的东方色彩予以关注,将其作为中江兆民思想的特色进行把握。③这类研究的代表性作品有:船越 素子:中江兆民のリベルテーモラルをめぐって ,哲学会誌 (31), 32-43, 1996-07-27、宫村治雄《日本政治思想史——以“自由”概念为中心》一书第十四章《“心思的自由”(リベルテーモラル)与“列士彪弗利”(レス ピユブリカ)——中江兆民的思想》(宮村治雄:2005『日本政治思想史――「自由」の観念を軸にして』、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第十四章「心思ノ自由(リベルテーモラル)」と「列士 彪弗利(レス ピユブリカ)」――中江兆民の思想)等。前人的研究对中江兆民“心之自由”的文本做了归纳梳理,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不过这些研究大都停留在问题的表层,并没有在知其然之外探寻其所以然,如此便失却了探究中江兆民自由思想发展脉络及深入哲学层面对其自由思想进行把握的机会。
本文中,笔者将从中江兆民为什么着重强调“心之自由”、对于“心之自由”中江兆民说了什么以及是怎样说的进行详细分析,梳理出其“心之自由”思想由伦理学层面逐渐深入到意志自由的哲学层面的思想发展的脉络,最后对其“心之自由”的思想进行评价。
一、“心之自由”的提起缘由
关于中江兆民为什么着重强调“心之自由”,笔者认为有基于现实政治的外部原因和出于理论辩护及发展的内部原因。
中江兆民一生作为理论家积极地关心政治参与政治,在自由民权运动中,他被视作自由民权阵营的理论家,为改变当时日本藩阀政府当权的状况,积极呼吁人民主权、民主宪法。正是怀着这样的现实抱负,中江兆民在理论上倡导自由,尤其是倡导社会状态下的公民自由。最初,在接触西方自由思想并吸收引进时,中江兆民选取了卢梭作为切入点,通过《民约译解》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进行的翻译、改造和解说,着重突出了卢梭自由思想中的“社会自由”(中江译为“人义之自由”)来为自由民权运动争取人民主权做理论支撑。
中江兆民的这种努力在现实层面遭遇了打击。1887年,明治政府颁布“保安条例”,包括中江兆民在内的许多民权派人士被驱逐出东京。1888年,中江兆民在大阪水平社(争取部落民解放的组织)的支持下当选为议员。不久,由于在预算问题上,议会中自由党土佐派的卖身投靠政府,对其十分失望的中江兆民愤而退出议会。可以说,现实层面官方的打压和民权派成员中部分人以争取公民自由为手段博取政治权力的现实是中江兆民在对“自由”进行理论上更深入的思索并转向伦理与哲学层面的“心之自由”的一大契机。
在理论层面,卢梭式的自由思想在日本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也受到了质疑与攻讦,而从卢梭的理论本身并不能很好的对此进行回应。卢梭本人在《社会契约论》的后半部分中(中江兆民并没有译出)也从理论的实现层面考量到国家的大小、人口的多少、气候和风俗的优劣等方面对国家政治道路选择的影响,并且认为:“‘自由’并不是任何一种地带的气候都能结出的果实,因此,它也不是所有各国的人民都能得到的。我们愈是思考孟德斯鸠的这个看法,愈能感到他的看法是对的;愈反驳它,反而愈能找到新的证据证明它。”[1]卢梭的这个观点继承自孟德斯鸠,同是自由思想家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整整用了四章(第14-17章)来讨论法律和气候的关系,其重点更是落在了风土与国民性及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上。
而孟德斯鸠的这种看法在明治初年的日本社会也引起了讨论。在《明六杂志》第四号和第五号上,箕作麟祥分作上下两篇以《人民的自由与土地的气候相关论》为题,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三卷第十七章一到四节进行翻译刊出。孟德斯鸠认为不同气候下国民的性情不用,北方寒冷,人民往往勇武;南方温暖,人民往往胆怯,更是举了中国和朝鲜的例子来予以证明。文中还对亚洲、欧洲的气候及其影响进行了说明,认为亚洲奴役和欧洲自由。原因是亚洲地处平原、国土毗邻且人民的勇气强弱有别,故而相互征伐形成大的国家;“在欧洲,由于大多数国家都生活在温带,相邻国家的人们一样勇敢,所以谁也征服不了谁,各国都保持自由。”[2]107由于亚洲国家譬如中国,国土面积很大,必须依靠强大的中央集权才能维系,因而“亚洲只有奴役,没有自由。专制统治笼罩着整个国家,人们的自由十分有限,更致命的是,人们不知道自由为何物,他们麻醉于做奴隶的快乐中。”[2]108
这其实涉及到了“自由”是具有特殊性还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江兆民没有正面地就风土气候来做辩护,而是选取了东方传统哲学的思考方式,将探讨的重点放在不受风土气候影响的、更为本质、更为抽象的“心之自由”上。这种思考方式可以说是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气质与心性之辩这一问题意识的延长线上。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曾有过类似问题的讨论。《中庸》第十章的文本就提出了“南”“北”与“勇”的问题: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子路向孔子请教关于“强”的问题,孔子反问道:你所问的是南方的强、北方的强还是你的强呢?而后孔子具体阐释了南方人性情宽柔,能忍人所难忍,此乃君子之强;北方人性情刚猛,勇武坚强,此乃强者之强。最后孔子引出了他所推崇的强的定义:“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国有道,不变塞”“国无道,至死不变”的“四强”。
在这段话中,关于“强”这种性格、性质与“南方”“北方”这样的地域差别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了历代学者争论的关注点。有许多儒者从南北方地理、气候、风土的差异出发,论证了这些风土差异对人气质的影响,进而对“南方之强”“北方之强”的优劣进行了评价①譬如孔安国认为:“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和柔为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性刚猛,恒好斗争,故以甲铠为席,寝宿于中,至死不厌,非君子所处,而强梁者居之。”([南宋]卫湜著,《中庸集说》,漓江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87页。),这一类观点可以说与孟德斯鸠的看法相通;此外,更有一些思想家认为“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不过都是血气之强,从都是血气的共同点来否定二者,从而强调“戒谨不睹、恐惧不闻”中所涵养而来的性中之强。譬如王夫之②“子曰,强出于性也,而生乎气,有以性之刚正者而作其气焉,有以气之偏至者而迷其性焉,此不可不辨也。今而之所欲知之强,果何谓乎?夫气之偏至,则因乎地矣,若吾性中刚正所生之气,则任道之资,学者所尚,而地不足以限之也。而将问南方之强与?南方之气中刚而外柔,遂相习而为南方之强矣。而将问北方之强与?北方之气悍发而难制,遂相习而为北方之强矣。抑而知习俗之不可以移人,而变化气质之自能全吾性之坚贞以无所屈,为学者任道之全功,而将知此以务而之所当勉与?”([明]王夫之著,《读四书大全》,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9月版。)论述到“南方之强”“北方之强”都是因地之所限而相习成风,是“气之偏至”者,这种因地域风俗而导致的气质之性的差异是不足以为道德根本的,为学者应当克服习俗习气的影响,变化气质,自全其本性之坚贞。王夫之的这种思考方式是以形而上的、作为本体的“性”为道德的根本依归,超越了地域风俗等外在环境条件乃至风土习气之所限。
由于资料有限,我们不能说中江兆民是否直接受到了王夫之的启发,不过,通过论证“人心之自由乃性中所有”来肯定无论东方、西方都有创作运思之能,都有实现社会、人心自由的可能性的这种论证方式,则无疑是与这种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相通的。深受汉学教养的中江兆民借用了儒学的思维方式巧妙地回应了理论诘难,开始了对以卢梭为开始的自由思想的改造和超越并逐渐形成了中江兆民自己的“心之自由”思想。
二、“心之自由”思想的发展历程
下面,笔者将对中江兆民“心之自由”思想相关的文本进行分析,沿着从《民约译解》到社论再到哲学译著最后到《续一年有半》的进程,对中江兆民由卢梭自由观开始,到伦理层面的“心之自由”的探讨,最后深入到“意志自由”的哲学层面的思想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一)“心之自由”的总论:《民约译解》
《民约译解》一书是中江兆民最著名的谈到自由的译作。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着重于讨论“天然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而对于“道德的自由”只略有提及,并认为非该书重点而未加详论。然而中江兆民在《民约译解》的翻译中则对“心之自由”做了展开和发挥。
中江兆民对“道德的自由”一段翻译为:
因此约所得,更有一,何谓也?曰,心之自由是也。夫为形气之所驱,不知自克修者,是亦奴隶之类耳,至于自我为法,而自我循之者,其心胸绰有余裕。虽然论心之自由,理学之事,非是书之旨,议论之序,偶及此云尔。
(解)邦国未建之时,人人从欲禋情,不知自修厉。故就貌而观,虽如极活泼自由,实不免为形气之所驱役,本心始未能为主宰,非奴隶之类乎?民约既立,凡为士者,莫不皆与议法,故曰自我为法。而法制既设,莫不皆相率循之,故曰自我循之。夫自为法而自循之,则我之本心,曾不少有受抑制,故曰心胸绰有余裕。要之因民约所得,比其所失,相禋远甚。故第六章末端亦言,人人之于民约,无乎所失,而有乎所得矣,参观而益明白。[3]
很明显,中江兆民并没有忠实于原著地一笔带过,而是加以了特别的关注。从中江兆民的翻译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运用了十分具有儒学意蕴的表达,譬如“形气所驱”“自克修”“理学之事”等等。明显地,中江兆民在此处将“道德的自由”与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所强调的“修养”“工夫”联系在一起。在“解”中,中江兆民的态度则表达得更为鲜明:在自然状态下人们虽然拥有“天然的自由”,然而这样的自由却并不值得推崇,因为人们受到“形气”的驱使,“本心始未能做主宰”,故而仍然属于奴隶之类。而只有当人们进入了社会状态,“为士者”参与立法,然后自己去遵循它,虽然貌似有了一层束缚,但是由于是自己遵守自己所立之法,故而本心并未受到抑制,“心胸绰有余裕”。
由于这一段文字是基于译文所作的发挥,故而也受到了颇多限制。不过,从这有限的文字中,我们通过大胆地推测,似乎可以把握到中江兆民今后对“心之自由”进行展开和发挥的方向。这样的方向在中江兆民所选用的译语中已初露端倪,不过,思想的发展和成熟则需要更久的时间来酝酿和显现出来。那么,不妨在此,基于这一段论述,我们先来做出一种有根据的猜想,而后在中江兆民之后论述到“心之自由”的文本中为此猜想寻求论证。以下,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对其进行把握:
1.从中江兆民对“自然状态”下的描述中所使用的“形气”和“本心”之辩,我们可以发现他仍然使用了传统儒学的论证方式。这样的论证早在孟子就有,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①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章句下·第十九节》),这“几希”之处就在于人讲道德、有“四端”之心,人之为人就是要“求其放心”,让道德之心做主宰将先天具有的善端扩充开去,否则人受形气之私所蔽,让本心放逸,则与禽兽无异。这里,中江兆民并没有直接使用“人禽之辩”,不过从“自由人”与“奴隶”这组对立中可以看出中江兆民的论述在思维理路上是承继了传统儒学心性论、修养论的论证方式。
而这种思维方式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更是被大大发扬,对理、气、心、性展开了复杂的论辩。中江兆民所使用的“本心始未能为主宰”的提法,让我们有理由将其与阳明学联系起来。
2.在“解”中,中江兆民讲到“民约既立,凡为士者,莫不皆与议法”。“为士者”一词在不经意间透漏出中江兆民骨子里的儒者情怀。中江兆民没有用“人”或“民”这样的泛称指代词,而是使用了“士”。“士”之一字在中国的语境下既可以指代等级身份,亦可泛称读书人。而在日本明治以前,由于并没有科举进士的制度,故而“士”则特指武士阶层,是身份的象征。明治维新后,新政府虽然收回了武士阶层的特权,宣布四民平等,然而社会观念上强烈的等级意识并没有完全消除,明治政府官方也划分了属于新贵族的“华族”。对于这种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中江兆民一向是深恶痛绝、高声抵制的。由此,我们可以说中江兆民所说的参与立法的“士”并不是指代具有等级身份之意的“武士”,反而是与中国读书人所谓的“士君子”之“士”相通,意涵人在知识文化层面的修养,亦即指代知识分子阶层。
中国“士”的特征在于他们虽不一定具备现实的政治权力,然而却有着作为“圣学”“道统”的继承者的自信与自觉,培养起了“学而优则仕”的政治意识和超越现实境遇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情怀。中江兆民出身于最低级的武士阶层(“足轻”①级别很低的下级武士。),因而他有机会进入土佐藩校文武馆学习汉学,成为一个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读书人。或许由于出身寒门,中江兆民在汉学中更容易从君子修身成仁晋身士大夫担当家国天下的儒者情怀中找到共鸣。
在“民约既立,凡为士者,莫不皆与议法”这一句中,通过“为士者”这样的表达方式对于参与“议法”的人群进行了限定,这层意思当然是与卢梭原义有所出入的。从理想层面,我们可以体会到中江兆民对于作为“为士者”的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恰恰可以导向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担当政治建构任务的自觉。而现实上说,这似乎表达出中江兆民支持传统儒家政治结构中“精英政治”的政治倾向性。可以说无论是从理想情怀上说还是从政治理想上说,中江兆民都是与传统的士君子相通的。关于这一点,以往的研究者并没有予以充分注意。
3.中江兆民在译文和解中两次提到“心胸绰有余裕”一语,这种状态描述可以做两层理解。第一,从否定的定义上讲,“心胸绰有余裕”指内心不受羁缚。由于人人遵守的是自己参与设立的“法”,故而内心并没有因遵守“法”而受到强迫感、束缚感,这一层含义是行文中直接表达出来的。第二,从肯定的定义上讲,则表达出应对从容、胸怀宽广、自由自在而又自得其乐的状态,这一层含义则是“心胸绰有余裕”这一译语中隐含的格义意。
遵守法度,而又能从容洒落,“绰有余裕”,这样的“道德自由”与儒家的“禋矩之道”若合符节。从“绰有余裕”的从容洒脱上说,早在孔子时就提出过君子经过一生的省察克治、道德修养而达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在状态。自宋儒以降,强调自我道德修砺的儒家虽有严肃整备的诚敬倾向,然而也不能忽视其亦寻求“心胸绰有余裕”的洒落气象。宋儒自周敦颐起就提出“寻孔颜乐处”的命题。在这里,“孔颜之乐”是指“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是超越了人生利害而达到的内在幸福和愉快。人生应当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这种境界。”[4]
可以说,在儒家系统中,严格的自我道德要求并不与“心之自由”相冲突,反而,“心之自由”正是通过自我道德修养而达到的一种道德境界。而这也正是中江兆民寻求自由与东洋精神之间联系时所找到的结合处。
综上所述,通过对“心之自由”这一段所做的译和解,中江兆民回答了“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达到什么结果”的问题,亦即,士君子通过道德省察让本心做主宰来达到心胸绰有余裕的道德自由境界。从以上的分析来看,中江兆民对“心之自由”进行把握时所定下的基调便是饱含儒家色彩的。
当然仅凭这一段来得出这样的结论证据稍显薄弱,不过,这样的证据将在接下来谈到的文本中不断被发现。
(二)“心之自由”的本体论:社论《心思之自由》
1881年(明治十四年)3月25日,中江兆民在《东洋自由新闻》第四号发表了题为《心思之自由》的社论。在该篇中极力阐明“心之自由”乃性中所有这一命题,并如此论证:
虽然仲尼未言性,而其诏曾参曰:‘吾道一以贯之’,夫一心能应万事,此为仲尼言人心自由乃性中所有。瞿昙曰:‘唯此一事实’,其意亦与仲尼一贯之义相同,此瞿昙亦以人心之自由性有之。设令一至圣一如来斯言无异,考之前所举之事实,则人心之自由性有之亦非大彰明较著乎?[5]
中江兆民引用了孔子“吾道一以贯之”和《法华经》中“唯此一事实”来论证“人心之自由”乃性中所有,这一处是中江兆民谈论“心之自由”时少有的极为重要的义理探讨,却为历来研究者们所忽视。下面我们着重对这两处进行具体的分析。“吾道一以贯之”典出《论语·里仁》篇: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对此,历来注家多有争论。宋儒以前多数注者认为曾子的“忠恕”之说解释了“一以贯之”之道。①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5页。宋儒多以义理阐发,质疑孔子之道既然“一以贯之”,那么曾子以“忠”“恕”二者解释未免不得原意,因而比起“忠恕之道”更为注重“一贯”者。朱熹进一步将“一贯”解释为“以一心应万事”,而能贯者乃是“理”,将“一以贯之”与“理一分殊”联系起来。②《朱子语类》:“一以贯之,犹言以一心应万事。”又云:“曾子未闻一贯之前,见圣人千头万绪都好,不知皆是此一心做来。及圣人告之,方知皆从此一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万叶都是此根上生气流注去贯也。”(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1页。)王阳明则用良知说来解释,他将“一”解释为:“人心固有之理,良知之不昧者是也。常知则常一,常一则事有万变。”③王阳明在《反身录》中说:“子贡聪明博识,而学味本原,故夫子借己已开发,使之反博归约,务敦本原。本原诚虚灵纯粹,终始无间,自然四端万善,溥博渊泉而时出,肆应不穷,无往不贯,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贞夫一,斯贯矣。问一,曰即人心固有之理,良知之不昧者是也。常知则常一,常一则事有万变。理本一致,故曰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聪明博识,足以穷理,而不足以融理;足以明道,而非所以体道。若欲心与理融,打成片段,事与道凝,左右逢源,须黜聪坠明,将平日种种闻见种种记忆尽情舍却,尽情瞥脱,令中心空空洞洞了无一翳,斯干干净净方有入机,否则憧憧往来,障道不浅。”(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60页。)清儒返归汉学,尊重文本,仍以“忠恕”释“一贯”,不过,清人注重实学,将“贯”训为“事”“习”“行”,认为“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见之,非徒以文学为教也。”④洪颐煊《读书丛录》:“按《尔雅·释诂》云:‘贯,事也。’又云:‘贯,习也。’古人解贯字皆属行说,即孔子所谓道也。曾氏以忠恕解一贯,忠即是一,恕即是贯。恕非忠不立,忠非恕不行,此皆一贯之义,非忠恕之外别有一贯之用也。孔子因能行者少,故偶呼曾氏以发之。”(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8-259页。)很显然,中江兆民直接采用了朱熹“一心能应万事”的解释。不过朱熹更强调的是以“理一”来“贯”万事万物,而中江兆民却并没有谈到“理”,而只侧重于心之灵明自由,从这一点说似乎与陆王心学更为接近。这种解释方法与明清以来主流的解释大相径庭,而与宋明理学相通。
从中江兆民并列引用的佛教中“唯此一事实”的例子中更加明确地表明了中江兆民的这种个人理解倾向。
“唯此一事实”一句出自《法华经·方便品》⑤《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姚秦·鸠摩罗什译。《法华经》在大乘佛教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华严经》《楞严经》并称“经中之王”,是天台宗立说的主要依据,对于中国佛教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法华经》产生于大乘佛法兴起、人们把小乘(“声闻”“缘觉”)、大乘(“菩萨”)截然二分的背景下。经旨在于确立一乘,提出了“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思想,融会三乘为一乘(佛乘)。将“声闻”“缘觉”二乘解释为方便(权)说,其终究仍以成佛为目标。(亦称《妙法莲华经》)的偈: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乘法 无二亦无三 除佛方便说
但以假名字 引导于众生 说佛智慧故 诸佛出于世
唯此一事实 余二则非真
在这段偈中说到:在十方诸国佛土中,佛因为教化众生,使用了种种的方便法门,因而有了后人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的分类。不过所谓的二乘、三乘都只是方便法门,只有佛乘(菩萨乘)才是唯一真实的。佛陀之所以使用这些方便法门,目的是为了引导不同根器的众生,而唯有“佛乘”才是得到佛的智慧,最终达到成佛的目的的究竟法门。
该偈中“唯此一真实”一句旨在强调佛乘的根本性、究竟性,从中并不能直接读出“唯此一事实”中的“一”乃是“心”的意思。然而中江兆民却将其与“吾道一以贯之”相参照,同样以“一心能应万物”的理路对这句话做了理解,并为“人心之自由乃性中所有”这一命题做论证,这可以说是中江兆民个人的创造性发挥,而这种与宋儒相通的理解方式或许也如宋儒般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
在《续一年有半》中,中江兆民再次引用了“唯此一真实,余二即非真”这句话,并将其理解为“使世界万物都归结于一个无,仅仅把心当做存在”,他认为这种主观的讲法并不究竟,是“权宜的说法”,释迦牟尼在晚年才调和主观论和客观论。不得不说,这种讲法仍然是对经文的误解,这种从“多次主张主观论”到“使这两者互相调和”的描述①参见:中江兆民著,吴藻溪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1页。参照日语原文,对译文有部分修改。,与其说是描述了释迦牟尼的思想变化,不如说是中江兆民对自己思维历程的表白。这中变化也体现了中江兆民从中期“心之自由”的理解到晚年对“意志自由”理解的变化当中,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详述。
将中江兆民的这种理解方式的选择置于社会主流理论的发展背景中,则更有意趣。对于宋明理学借用禅学解释“一以贯之”的做法,近世以来,已被明清的主流中国学者以及江户的日本学者所指摘、批判,如方东树、张甄陶、王夫之、林罗山、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等。试举两例以说明之:王夫之对于儒佛之别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孔子所云“吾道一以贯之”是“一致百虑”,如同一粒粟种种下生长出无数粟来,道作为本体与本源,这是符合天地之理的;而释氏之说则是要破除天下万物之有而归于一无,是“收摄天下固有之道而反之”,“天地之间,既无此理,亦无此事”,而那些借用佛学解释儒学之俗儒正是拾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之唾余”,乃是“俗儒”。按照王夫之的说法,那么中江兆民则恰恰成了这种“俗儒”。②“潜室倒述易语,错谬之甚也。易云:“同归殊途,一致百虑。”是一以贯之。若云“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则是贯之以一。释氏万法归一说,正从此出。此中分别,一线千里。“同归殊途,一致百虑”者,若将一粒粟种下,生出无数粟来,既天理之自然,亦圣人成能之事也。其云“殊途同归,百虑一致”,则是将太仓之粟倒并作一粒,天地之间,既无此理,亦无此事。而释氏所以云尔者,只他要消灭得者世界到那一无所有底天地,但留此石火电光依稀若有者谓之曰一。已而并此一而欲除之,则又曰一归何处,所以有蕉心之喻,芭蕉直是无心也。若夫尽己者,己之尽也。推己者,己之推也。己者同归一致,尽以推者殊途百虑也。若倒着易文说,则收摄天下固有之道而反之,若执一己以为归属,岂非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之唾余哉?比见俗儒倒用此二语甚多,不意潜室已为之作佣。”(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1页。)而荻生徂徕认为宋儒将“一以贯之”与“心”“性”相联系,又讲“豁然贯通”,这些与禅宗顿悟法门无疑,这种学问方法表面上排佛,实际上却偷偷学习借鉴佛教,最终会导致孔子之教、先王之道泯灭无存。他在对宋儒极力批驳的基础上认为孔子所说的“吾道”乃是“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是先王为了“安民”而立的。③“大抵宋世禅学甚盛,其渠魁者,自圣自智。称尊王公前,横行一世,儒者莫之能抗。盖后世无爵而尊者,莫是过也。儒者心羡之,而风习所渐,其所见亦似之,故曰“性”曰“心”,皆彼法所尚。豁然贯通,即彼顿悟。孔、曾、思、孟,道统相承,即彼四七二三,遂以孔门一贯,大小之事,曾子之“唯”,即迦叶微笑矣。岂不儿戏乎?过此以往,天理人欲即真如无明。理气即空假二谛,天道人道即法身应身,圣贤即如来菩萨,十二元会即成住坏空,持敬即坐禅,知行即解行,阳排而阴学之。至于其流裔,操戈自攻,要之不能出彼范围中,悲哉!如此章一贯之旨。诚非不能大知之者所及。然游夏以上,岂不与闻?特门人所录,偶有参与赐耳。千载之后,据遗文仅存者,而谓二子独得闻之。又以其有详略而为二子优劣,可不谓凿乎?盖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先王为安民立之。”(荻生徂徕·论语徵:乙卷[A].)可以看出,王夫之和荻生徂徕所批判的,恰恰是中江兆民所赞同和使用的理解。中江兆民继承了宋儒“一心能应万物”的解释方式,并且并列引用的佛教的观点,从心之灵明知觉可以包摄万物的角度理解“心思之自由”。这恰恰是与中日近世以来倾向实学的理论发展方向相逆的。
通过这种理解方式的选择,中江兆民着重强调了自由之心的形而上性和本体性,为人皆有是心,皆可得心之自由做论证。不过,该篇中所谈到的“心之自由”侧重于心的认识功能,并未赋予道德属性,还不具有浓郁的伦理学意义,不能做到使“心之自由”包摄“道德的自由”之含义。
(三)“心之自由”的道德论:《理学钩玄》
《理学钩玄》是中江兆民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出版于1886年,在该书中中江兆民借鉴了Jourdain的《哲学讲义》、Franck的《哲学辞典》、Fouillée的《哲学史》和Lefèvre的《哲学》,比较系统概要地介绍了西方哲学。①参考船越 素子:中江兆民のリベルテーモラルをめぐって ,哲学会誌 (31), 32-43, 1996-07-27。
在该书第一卷第七章《断之机能》的“心之自由,一名道德的自由”一节中,中江兆民讲到:“心之自由就吾人能自作决断之处言,与政治之自由及身体之自由自有区别。盖心之自由常有,而政治之自由与身体之自由非常有。”这就是将“心之自由”区别于身体和政治上的自由,而肯定其作为一个本质属性的存在。接下来中江兆民讲到:
心之自由乃性中所有,此事于实际中考察则尤为明了不容质疑。何也?吾人夫赖自知之能做一反观时,则于我心奥底有活泼自由之性,欲为善则为之善,欲为恶则亦可为之恶,乃明知自决一事之自由,无受他者妨碍。是知古来豪杰之士,或挺身于战阵之间为国殉节,或倡所欲言欲广益人类,为一世之人而受猜忌终至死于非命之属。彼者皆因自信甚笃而至于是者,初非不知逡巡依违、不肯为他人先,非不知阳变其说以免祸之术,曩者若自决保其身,特一瞬间之事耳。彼从正义之旨趣与利己之旨趣中做选择,于是自做决断听从正义之旨趣,是其所以捐躯弃命而不自避之所由。[6]
中江兆民认为“心”的作用首先表现为“自知之能”,使用此“自知之能”稍作反思,则发现心中有“活泼自由之性”,这是个人道德的保证,因为为善为恶成为了个人自由的选择。这之后,中江兆民以历来仁人志士杀身成仁为例,论证为善的乃是基于心之自由之上的道德选择。
中江兆民的这种通过“自知之能”进行道德选择的理路与阳明学中“良知良能”的说法十分接近,其使用的“活泼”一词对心的形容也可以在宋明理学中找到出处。
将心描述为“活泼泼地”,始于程颢②程颢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二程集·遗书》卷之三,中华书局,1931版,第59页。),而又被阳明心学所发扬。《传习录》中有:
问:“‘逝者如斯’是说自家心性活泼泼地否?”先生曰:“然。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川水一般;若须臾间断,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处,圣人也只如此。”[7]
不过可以看出,中江兆民的说法与阳明稍有所异,从上一段的表述中,可以看出,阳明虽然对于“自家心性活泼泼地”给出了肯定回答,但是却也加上了一个限制,即要达到“活泼泼地”状态,要先经过“时时致良知的功夫”,良知良能虽然是人性中所有,然而常常会受到遮蔽,需得“致良知”的功夫才能使其彰显,从而与天地相似,这便将学问做到至极处,即使圣人也不过做得如此。可见在阳明处,“活泼泼”虽就本质上讲是一个本然状态,然而落实在现世中则更是被设定为一种道德境界,是需要经过“致良知”的努力修养才能达到的结果状态。而在中江兆民处,则忽视了“致良知”的修养工夫论,而将“活泼自由之性”看做使用“自知之能”稍作反观便可发现的常在常显之性,这一点似乎与阳明左派的观点更为契合。③譬如阳明左派代表人为王艮,在《王心斋先生遗集》中认为“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凡涉人为,便是作伪”(《遗集》卷一《语录》)。
这一阶段,中江兆民将道德的根基建立在主体的自由意志上,认为道德的行为是主体依据自我的意志选择而做出的自觉的行为,从中人产生了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而或自喜或悔恨,这样使得“心之自由”的思想注入了伦理性和道德性。不过,在工夫论的实践方面,此时的“心之自由”理论还待进一步完善。
(四)心之自由”的工夫论:《道德学大原论》与《续一年有半》
《道德学大原论》是叔本华的《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一书中的第二部分《道德的基础》的译作,该书翻译于1894年,也即在中江兆民暂时远离了言论活动并投身实业活动期间;而《续一年有半》则是中江兆民的最后一部书,写于中江贫病交加的晚年。在这两部晚年的著作里,在对前中期的理论进行继承和深化的同时,中江兆民的“心之自由”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续一年有半》首先体现了继承的一方面,譬如第二章第十七节的《自省的能力》一节就延续了《理学钩玄》中的“自知之能”。中江兆民将“自省之能”定义为“指自己反省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在说什么,在想什么的能力。” “我们正因为具有这种能力,所以自己知道做的事正当不正当。所以假使做的正当,就自己夸耀,内心感到愉快,假使做的不正当,就自己悔恨。”[8]110这种提法与《理学钩玄》中并无二致。
另一方面,晚年的论述中也体现了其对《理学钩玄》时期观点的修正和进一步深入。譬如,中江兆民突破了前述“心之自由”思想中主观性的表述方式,将“客观性”[8]111也纳入思考范围,这说明中江兆民已经突破了“一心能应万物”的纯粹主观性、理想性的世界观,在其思想中注入了客观性、现实性的因素。又如,中江兆民引用了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孟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一乐也”,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典故来形容那些能够“运用自省的能力检点自己”的人所能体会到的“自乐”的道德境界,并且直接使用了“人禽之别”之喻来区分有自省之能与无自省之能之人的区别。①哪怕只有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假使自己也还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也就是说,运用自省的能力检点自己的地位,以所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而自乐,在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悠游自得,该是多么幸福啊!与其说,有没有自省的能力是聪明和愚笨的区别,倒不如可以说,那是人和兽的区别。有这种能力就是人,没有这种能力就是兽。社会上的衣冠禽兽,为什么这么多呀!(参见:中江兆民著,吴藻溪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1页。)可以看出,在中江兆民的思维世界里道德境界是一种“乐”的境界,而这种境界中既有儒学中通过自我修养克制达到“孔颜之乐”的成分,亦有道家及禅宗中逍遥游的超脱洒逸情怀。②正是这种情怀使得中江兆民在罹患癌症时得以以超然的心态面对,在《一年有半》中,中江兆民多次表现出这种道家超脱生死的精神,譬如“啊!所谓一年半也是无,五十年、一百年也是无。就是说,我是虚无海上一虚舟。”(中江兆民著,吴藻溪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页。)关于中江兆民思想与庄子的关系,已有学者予以研究,譬如片山寿昭 , 徐水生:西周と中江兆民における興西思想の出会い——とくに「自由」の概念を中心として ,Doshish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umanities (151), p1-35, 1991-10。在本文中,笔者认为,中江兆民的“心之自由”中当然包含了道家的自由精神,不过在整个理论系统中,作为升华性理论构成的道德境界仍然是以儒家的为主体的。这种“乐”的道德境界正是在对“心之自由”赋予道德意义后的进一步理论升华。这样,我们对上文中提出的关于“孔颜之乐”的道德境界的猜想进行了回应。
不过,与前中期的心之自由思想相比,在《续一年有半》最为突出的却是兆民对他先前坚信不疑的意志自由提出的质疑,在“十六 果断行动、行动的自由、意志的自由”一节中,中江兆民直接提出人的精神是否具有自由的意志这样的问题:“意志的自由不过是一个空名呢?还是意志的自由真正存在,目的却可以听任我们的选择呢?”[8]108这样的问题可以说直接动摇了中江兆民以往所建立的心之自由观的根基。然而,中江兆民仍然坚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实际上,所谓意志的自由,是极端薄弱的。”[8]108并举了如果让一个人从一杯酒和一碟小豆馅年糕中做选择,富人一定喝酒,穷人一定选取小豆馅年糕的例子③“试就眼前的事情打个比方。假定这里有一杯酒,一碟小豆馅年糕,恐怕富人一定喝酒,穷人一定取小豆馅年糕吧。假定情况不是那样,这个富人故意出乎意料之外,去取小豆馅年糕,那就必定是看到满座客人的情况而这样做的。这仍然是由于在自身之外有行动的理由存在,而不是纯粹从意志的自由去判断的。假使富人并不是为了其他原因而是从自己的意志出发,违反生平的习惯,取了小豆馅年糕,那么,所谓意志的自由,就必定变成没有意义的事。”(中江兆民著,吴藻溪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8-109页。)来论证人的选择实际上受到习惯的影响,而并非出自自由意志。而后又举了苏格拉底和孔丘为善,盗跖和石川五右卫门为恶,皆是出于习惯,其意志并没有自由的例子,进一步否定了道德的成立对自由意志的依赖。
中江兆民在最后一部书中对自由意志的存在提出质疑,并否定了道德的成立对自由意志的依赖,这并不是突然性的心血来潮。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新的观点的形成是受到了叔本华的影响。在《伦理学的两个基本原理》一书中,叔本华否定了自由意志,并且批判了在以往的哲学中,常常过于重视主体的选择性而忽略了客体的因素①“其做法则是让愿望完全出自主体,而没有很好地考虑客体蕴含的因素,即动机。”(叔本华著,任立、孟庆时译,《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商务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17页。),他认为:“如果我们认为人的意欲是自由的,那就绝对无法看出美德和劣性到底是从何而来。”[9]60因此,他强调基于客体的“动因”对人的选择行为的影响。叔本华正是从否定无差别的自由意志的出发,确立了其道德自由。②“如果我们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论述,完全放弃了人的行为的一切自由,并把人大行为看作是完全服从于极其严格的必然性的,那么我们就达到了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将能把握作为较高级种类的真正的道德自由了。”(叔本华著,任立、孟庆时译,《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商务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17页。)而中江兆民于1894年翻译的《道德学大原论》正是是叔本华的《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一书中的第二部分《道德的基础》的译作。而中江兆民所提到的穷人富人的例子则更是化用了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的第一篇论文《论意志的自由》中的例子。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显而易见。
在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以及其与道德间的联系后,叔本华进一步认为正是由于意欲并非是随意的、自由的,故而每个人面对某件事时的选择才会固定下来,而这种固定的选择是基于人的根本素质所决定,而一个人的根本素质则构成了这个人的性格。在叔本华看来,人的性格具有四个特点:个体性、验知性、持续如一、与生俱来。也即,人天生便具有了独特的性格特点,后天的学习不能“改良人的性格、人的内心,而只是帮助一个人的头脑认识。”“性格是不会改变的,动因以必然性发挥作用,但这些动因却必须先通过认知这一关,因为认知是动因的媒介。”[9]57换言之,人的性格是不能改变的,而人的认知则是可以改变的,后天的法律、教育等目的仅只是为了改变的人的认知,从而干预人在面对选择时“动因”的强度,有效地趋利避害因而不作出犯罪行为。
叔本华的这种观点对于笃信儒家道德的中江兆民来说无疑是走的太远了,因而,中江兆民利用改译的手法对叔本华的观点进行了改造。在《道德学大原论》中,中江兆民的译文是:“行为看似是变易的,实则皆出于性质,其意趣与最初相比其实并没有改变。唯经由学问经验之效可稍得次序,从而产生改变。”这样,在对叔本华的观点进行翻译后,中江兆民通过加上的一句“唯经由学问经验之效可稍得次序”从而做了一个让步。也即,中江兆民始终相信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学问修养变化气质,改变道德属性。这种观点在《续一年有半》中也是一脉相承的,在举了苏格拉底、孔丘、盗跖和石川五右卫门的例子来论证意志没有自由之后,中江兆民仍然肯定了苏格拉底、孔丘的道德值得尊重与肯定,这是由于我们“有决定平日所习惯了的事物的自由。”[8]109
中江兆民虽然接受了叔本华的观点,认为人的意志自由是薄弱的,但是,他并没有坚持到底,一并否定了人的性格可以改变这一点。他在否定意志自由时做了让步,认为这种否定是指我们并非做什么事情都有自由,而将自由落实到“有决定平日所习惯了的事物的自由”上去。那么他这么做的理由何在?中江兆民在下面的话中予以了进一步说明:
假使以为行动的理由,即目的物方面,丝毫没有其他力量的影响,而由纯粹的意志的自由去控制行动的话,那么平日的修养,周围的环境,时代的风气,以及所有一切能够移风易俗,影响身体的事物,都将失掉了作用;而这在历史事实上是被否定了的。
轻视意志的自由,重视行动的自由,并重视平日的修养,这是我们少犯过错的唯一方法。
从这两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江兆民明显只是借用了叔本华论证意志自由薄弱性的一部分,来协调知与行之间的平衡,并无意否定“平日的修养、周围的环境、时代的风气,以及所有一切能够移风易俗,影响身体的事物”,反而他鼓励人们重视平日的修养,不断地积善成德、改变气质。
中江兆民苦心孤诣地于晚年推翻其先前的观点,否定意志的自由,其目的并不在于要否定其一生所坚持的重视儒学教养、建设“宇宙第一善国”的理想,反而是为了补足之前理论中所缺欠的现实性、工夫论。
这样的改变或许来源于中江兆民对于现实的感悟。前文中我们提到了中江兆民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遇到了现实上的挫折,在政治实践屡屡受挫的情况下,中江兆民暂时远离了言论活动并于1893年起他决心创办实业,自己筹措政治活动资金,以摆脱政府的控制,结果屡屡失败,以债台高筑告终。1897年,他试图再度参与政治,组建“国民党”,出版机关刊物《百零一》,不久也遭挫折。1900年底,他被医生诊断身患癌症,被宣告他余命只“一年有半”。这时的中江兆民以惊人的毅力和豁达的心态面对,完成最后的著作《一年有半》及《续一年有半》。中江兆民经历现实性的各种挑战,这使得他在主观的精神世界外,更加关注与客观性世界的“对待”,为“心之自由”思想的最后发展添加了客观性和工夫论的内涵,不得不说这已不仅仅是理论性的思辨,而是通过中江兆民一生的上下求索实践从而达到的体悟。
从以活泼的心统摄万物的主观性立场,到更加重视行动、修养的工夫论,中江兆民兆民的这种思想变化与其被标签性地定义为由传统儒学及唯心主义转变为晚年的唯物主义,倒不如说他始终坚持着儒家道德的思维模式做根基,在理论上则对早年倾向于阳明左派的主观立场有所纠偏,使得立论更为中正。可以说,中江兆民的“心之自由”思想在其晚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三、如何看待中江兆民“心之自由”的思想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江兆民的“心之自由”思想是经过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的,其中虽然受到了卢梭、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家的影响,然而其“心之自由”思想的根本思考方法仍然根植于儒学之中。历来对于中江兆民的思想究竟应归属于孟子、庄子、朱子学、阳明学等那一派中有所论辩,而作为证据的往往是中江兆民所直接使用的语言。通过分析,笔者认为,由于中江兆民对“心之自由”的论述是散见于各篇文章或译著的章节中的,中江兆民本人并无意系统地对此问题展开论述,在文字的使用上,中江兆民对上述各家皆有所运用,故而,我们不能说中江兆民单单受了哪一种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中江兆民的“心之自由”思想中体现了包括孟子、庄子、朱子学、阳明学乃至西方哲学诸家在内的综合影响。而从义理上讲,笔者则认为中江兆民的整个思考理路与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更为贴切。
那么,中江兆民为何要越过明清及江户而选择从宋明理学出发理解西洋性、近代性的“自由”?置于近代化这个特殊的节点上,中江兆民“心之自由”的思想如何体现其近代性价值?
近代以来,人们惯常使用将传统与近代二分的思维模式来思索近代,譬如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就批判到明治时期思想家常常使用传统资源吸收自由平等等近代价值,导致理解的偏差并在天皇制国家的选择上表现出软弱性和不彻底性来。具体而言,丸山认为“在我国(日本)旧制度精神的代表是儒教”,并且认为这种“儒教的思维模式”是“自由平等的仇敌”。具体而言,这种传统的儒教思考方式是从中国传入的、建构江户时代封建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朱子学。此外,中江兆民的研究者植手通也认为正是因为兆民信奉“朱子学的自然法思想”,从而导致从这种自然法出发对自由和权利的感念有“不彻底”的理解。①参考《丸山真男集》第三卷(岩波书店,1995)中《日本自由意识的形成和特质》(p.155)、《自由民权运动史》(p.243-4),植手通《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岩波书店,1974),p.116-7. 及井上厚史论文:Nakae Chomin and Confucianism: examining his hermeneutic of free right ,Shimane journal of North East Asian research (14·15), 117-140, 2008-03
丸山真男等人从中江兆民自由思想的儒学根基来批评其对君主制国家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及其思想中近代性的欠乏,这是与这批研究者们经历军国主义和二战的生活背景不无关系的。然而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定义近代性并以此对中江兆民进行评价,这种思维模式在今天看来明显是有失偏颇的。
联系到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充斥着从感性的方面理解自由(即如同英国保皇党最主要的思想家罗伯特·费尔马所说的“各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自由生活,不受法律约束”的状态,或者如霍布斯所说的“自由就是意味着根本不存在反对物,自由就是不存在任何妨碍运动的东西。”[10])或者从功利主义、进化论的角度解读自由的偏颇;再联系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因积极进化而转向否定儒教、主张“人欲”亦“天理”“人欲”是人类最本质特征等观点从而致使“人欲”泛滥、道德坠地的现实情况,可以说中江兆民从儒学根基中寻找资源,从而接受并深化自由思想,使其更为理性化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同时,中江兆民成功地阐发了“心之自由”的思想,使其具有本体论、道德论和工夫论的内涵,这种从传统思想根源中寻找到与西方近代自由思想相通之处的道路对于东方的近代化选择来说无疑是十分具有借鉴意义的。这种从卢梭自由思想出发,并受到叔本华自由思想影响的中江兆民自由思想最终从儒学中寻找到了根基,可以说中江兆民所谈的自由,当然是一种自由思想,不过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思想的东方自由思想。这种理论尝试对于“东方的近代”这个主题而言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中江兆民的这种尝试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可能性。
不过,我们也并不能说这种尝试在理论上是完全成功的。
首先,中江兆民虽然意识到自由的实现首先需要制度的保障,故而他通过翻译《民约译解》来强调“人义之自由”,并且大声疾呼言论自由、开设议会、制定宪法等呼吁实现“行为之自由”的具体政策。然而,最终落实于儒家道德的“心之自由”的理论根基,无疑是在理论层面对斗争性的弱化。中江兆民在表述中多次强调日本社会“自古神圣相承”、百官贤明、官民一体共同建立宇宙第一善国的愿望①在《一千七百九十三年法兰西民权之告示》一文中:“吾邦臣民,沐浴圣化,于今二千有余载,忠孝之教,沦浃人人骨髓”,如果盲目地效仿美国和法国一样的民主政体,“不免为名分之大罪人”。(《中江兆民全集》第14卷,第78页。)在《策论》中,中江主张:东西方各有所长,日本应当取长补短,英法的优势在于技术和理论,日本的优势在于优良的道德传统。后发的日本要祛除轻弛之习,就要将东西方两种传统相结合,“宜可令公私学簧课技书理论之外更钻研彼邦之道学,又兼讲习汉土之经传”,若真如此,日本将成为凌英驾法的“宇宙第一善国”。(《中江兆民全集》第1卷,第25-26页。),可见在中江兆民的思想更倾向于改良而非改革,对于天皇制保留了丸山真男等人所批判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其次,在“心之自由”思想形成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中江兆民的“心之自由”偏重于主体性、主观性,这不可避免地面对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共性问题:由“内圣”如何开出“外王”?具体的说,这种“人心之自由乃性中之所有”的论证虽然解决了自由在东方也具有内生性的问题,但是同样埋下了这样的问题:由个人主体性主观性所体会到的“心之自由”乃至道德境界如何可以为自由的制度乃至自由的近代社会的形成做保障?
最后,中江兆民的这一整套“心之自由”的理论是建立在“人义之自由”需要道德的自由作为保障这样的前提下的。中江兆民从儒家道德这个层面来理解卢梭所谓的“道德的自由”,这其中便存在了这样的问题:既然儒家道德就可以满足要求,那么自古便讲求儒家道德教化的中国以及推广儒教数百年之久的日本社会中为何并没有能形成“人义之自由”根基的道德自由基础呢?
四、结语
本文中首先对中江兆民提出“心之自由”的原因予以挖掘,重点论述了中江兆民“心之自由”思想发展和形成的过程,最后对其“心之自由”思想进行评论。
通过梳理,笔者理出了中江兆民“心之自由”思想成型的发展脉络,认为《民约译解》中其“心之自由”思想已初露端倪;在社论时期,中江兆民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为“心之自由”做了本体论论证;在《理学钩玄》里,中江兆民进一步将“心之自由”与道德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中江将“心之自由”理解为意志自由,并将其作为道德的根基;经过《道德学大原论》中叔本华的影响,在《续一年有半》中中江兆民对其前期的思想进行大幅度的改造,将客体纳入思考范围以消解前期自由思想中的主体性和主观性,通过质疑和弱化自由意志的存在,将“心之自由”定义为通过修养决定习惯的自由选择,进而强调行为和修养的重要性,为其“心之自由”思想增添了工夫论内涵。
[1][法]卢梭(Rousseau,J.J.)著,李平沤译.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87.
[2][法]孟德斯鸠著,申林译.论法的精神[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3]日]中江兆民著,岩崎徂堂編.中江兆民全集(第一卷)[M].东京:岩波書店,1983:98.
[4] 陈来.宋明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44.
[5][日]中江兆民著,岩崎徂堂編.中江兆民全集(第十四卷)[M].东京:岩波書店,1983:14.
[6][日]中江兆民著,岩崎徂堂編.中江兆民全集(第七卷)[M].东京:岩波書店,1983:59.
[7]王阳明.传习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331.
[8][日]中江兆民著,吴藻溪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9][德]叔本华著,韦启昌译.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0]卞崇道,[日]加藤尚武编.当代日本思想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276.
The Formation of Chomin Nakae’s Thought of “the Freedom of Heart-mind”
CHANG Xiao-lin
(Graduate Schools for Law an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153-0041)
Chomin Nakae was called Japanese Rousseau. He once translated Rousseau’sThe Social Contractinto ancient Chinese, which played a signi fi c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Japan, even in that of China.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Rousseau’s idea of freedom, Chomin Nakae expanded his unique discussion on the freedom of heart-mind.Kokoronojiyuu(心之自由),sinnsinojiyuu(心思之自由)and riberutemoraru are all Chomin’s translation of liberty moral.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has analyzed the realistic reason and the theoretical reason why Chomin expanded the thought of Kokoronojiyuu, and arranged the related dissertations throughout his lifetime. The author has also carded the logical connection of his thoughts developed in different periods, form ethical level to philosophical level of free will. Finally, his thought of the freedom of heart-mind is evaluated.
Chomin Nakae; Rousseau; the freedom of heart-mind
B313
A
2095-3763(2017)-0055-13
10.16729/j.cnki.jhnun.2017.02.008
2016-10-15
常潇琳(1990-),女,河北沙河人,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思想史。
① 在中江兆民的文本中,他曾使用“心ノ自由”“心思ノ自由”“道德ノ自由”“リベルテーモラル”等多个译语来翻译“liberty moral”,这几种译语在中江兆民的文本中并没有加以区分,故而在本章的论述中,笔者对这几个词亦不予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