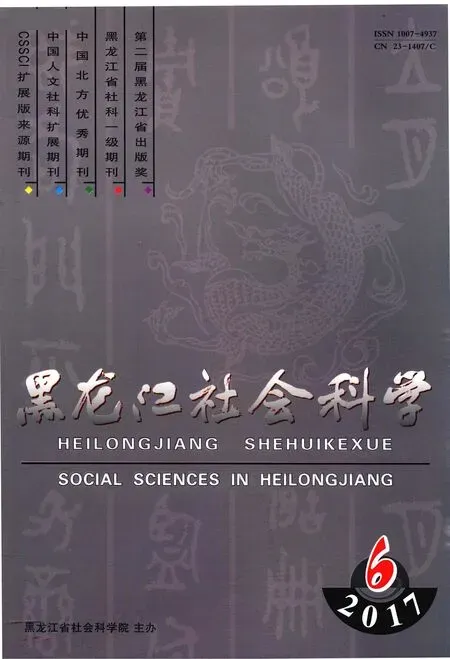明洪武、永乐时期辽东军屯对黑龙江地区开发的影响
战继发,胡梧挺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哈尔滨 150018)
·历史学研究·
明洪武、永乐时期辽东军屯对黑龙江地区开发的影响
战继发,胡梧挺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哈尔滨 150018)
明代曾在辽东设置军屯,洪武、永乐年间为其极盛时期。洪武、永乐年间的辽东军屯,既解决了明辽东驻军的军粮补给问题,节省了“海运饷辽”的成本,也为明代巩固东北边疆与经略辽东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辽东军屯还为明初经略黑龙江地区、设置奴儿干都司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人员保障,对明代东北女真等民族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黑龙江地区的开发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明洪武、永乐时期;辽东军屯;黑龙江地区
军屯作为明代屯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之大,为历代之最。它是对太祖朱元璋寓兵于农、以屯养兵思想的制度化。辽东军屯作为明代军屯的重要代表,从兴屯之初即体现着朱元璋的上述思想,并且在其极盛时期也的确实现了“足食足兵”的目标,进而对明朝经略与巩固东北边疆地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学界对于辽东军屯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不过对于辽东军屯与明代黑龙江地区开发的关系,特别是洪武、永乐时期的辽东军屯对于奴儿干地区经略的作用与影响的讨论似乎略显不足。因此笔者不揣谫陋,就此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一点个人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一、洪武、永乐时期辽东军屯概况
明代辽东军屯始于明初洪武四年(1371)以后,即指挥佥事马云、叶旺二人在辽东立军府而兴屯垦。不过,此时的辽东军屯正处于萌芽期,其规模很小,据洪武七年“海运饷辽”诏书记载:“户部言定辽诸卫初设屯种,兵食未遂。诏命水军右卫指挥同知吴迈、广洋卫指挥佥事陈权率舟师出海转运粮储,以备定辽边饷。”*《明太祖实录》卷八七,洪武七年正月乙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546页。可见,直到洪武七年辽东军屯出产的军粮仍无法自给,还要依靠海运来补给。此后数年,海运粮饷成为辽东卫所获取军饷补给的主要途径,据《明史·河渠志》记载:“辽左及迆北数用兵,于是靖海侯吴祯、延安侯唐胜宗、航海侯张赫、舳舻侯朱寿先后转辽饷,以为常。督江、浙边海卫军大舟百余艘,运粮数十万。赐将校以下绮帛、胡椒、苏木、钱钞有差,民夫则复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1]而这种海运饷辽的情况至洪武十五年开始出现变数,由于大规模的海运饷辽造成兵民溺水而死的情况很多,而明政府对海运溺死者要给予重金抚恤,这无疑造成了巨大的海运成本,因此朱元璋命群臣商议在辽东大兴军屯之法,史载:“(洪武十五年五月)士卒馈运渡海有溺死者。上闻之,命群臣议屯田之法,谕之曰:‘昔辽左之地,在元为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来归,因时仕之。其时有劝复立辽阳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旷人稀,不欲建置劳民,但立卫以兵戍之,其粮饷岁输海上。每闻一夫有航海之行,家人怀诀别之意,然事非获已,忧在朕心;至其复命,士卒无虞,心乃释然。近闻有溺死者,朕终夕不寐,尔等其议屯田之法,以图长久之利。’”*《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五,洪武十五年五月,第2283-2284页。此后至洪武二十七年,明廷始有命辽东卫所屯田之令:“(洪武二十七年六月戊寅)命辽东定辽等二十一卫军士自明年俱令屯田自食,以纾海运之劳。”*《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三,洪武二十七年六月戊寅,第3403页。自洪武十五年命朝臣商议辽东屯田办法,直至12年后,明廷才有卫所屯田辽东的命令,而这期间海运饷辽并未停止,据洪武二十九年中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朱信上奏:“比岁海运辽东粮六十万石,今海舟既多,宜增其数。”为此,朱元璋特命增运十万石,“以苏州府嘉定县粮米输往太仓,俾转运之。”*《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戊戌,第3560页。可见,从洪武十五年至二十九年,海运饷辽仍在持续进行,且有增加运量之势。直至洪武三十年,明廷先是派左军左都督杨文前往辽东督军屯种*《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洪武三十年正月己巳,第3608页。,数月之后,朱元璋又谕户部:“辽东海运,连岁不绝。近闻彼处军饷颇有赢余,今后不须转运,止令本处军人屯田自给。其三十一年海运粮米,可于太仓、镇海、苏州三卫仓收贮。仍令左军都督府移文辽东都司知之。其沙岭粮储,发军护守,次第运至辽东城中海州卫仓储之。”*《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五,洪武三十年十月戊子,第3684页。至此,在明廷商议辽东屯田办法15年后,海运饷辽终于停止。笔者认为,海运饷辽被叫停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辽东卫所多年囤积的海运军粮“颇有赢余”而“不须转运”;二是因为辽东军屯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且朝廷有对其未来取得更大成效的预期。
明成祖永乐年间,辽东军屯在洪武年间的基础上又有进展。永乐二年(1404),明廷决定扩大辽东军屯的规模。由于增扩军屯需要大量耕牛,并且耕牛转输不易,因此明廷特向朝鲜就近征购耕牛,史载:“(永乐二年六月)辛卯,朝鲜国王李芳远遣使送耕牛万头至辽东。先是,上欲广屯田于辽东,命礼部遣人征牛于朝鲜。至是送至,命户部每一牛酬绢一匹、布四匹,乃赐其王文绮表里各百六十;敕辽东都司以牛分给屯戍。”*《明太宗实录》卷三二,永乐二年六月辛卯,第571页。
洪武、永乐时期是辽东军屯从无到有并走向兴盛的时期。一方面,辽东军屯的制度与办法在洪武时期得以确立;另一方面,辽东军屯的成效也十分显著,无论是屯垦田顷亩数,还是屯田产粮数额,都达到了有明一代辽东军屯的峰值。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户部郎中毛泰在其关于整肃辽东军屯的奏疏中说:“洪武初,辽东粮料俱从太仓海运。其后罢海运,置屯田。八分屯种,二分戍逻,每军限田五十亩,租十五石。以指挥、千户、百户为田官,都指挥为总督。岁夏、秋二征,以资官军俸粮。自洪武至永乐,为田二万五千三百余亩,粮七十一万六千石有奇。当时边有储积之饶,国无运饷之费,诚足食足兵之道也。”*《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成化十九年九月戊申,第4139页。(按“二万五千三百余亩”,据王毓铨考证,“亩”应为“顷”字之讹[2])毛泰的这段话不仅追溯了辽东从依赖海运到罢运兴屯的简要过程,还记载了辽东军屯的制度办法。总体而言,辽东军屯的组织管理方式,与其他地区并无不同,也是在都指挥的总督下,由指挥、千户、百户等“田官”逐级负责,其屯种与戍守军士的比例也遵循8:2的全国通例。更重要的是,毛泰在其奏疏中还记录了洪武至永乐年间辽东军屯的顷亩与产粮总额:屯田25 300多顷,产粮716 000多石。由此可见,洪武、永乐年间辽东军屯成效显著,正如毛泰奏疏所云,这一时期的辽东军屯,真正实现了“边有储积之饶,国无运饷之费”“足食足兵”的目的。
辽东军屯在永乐中期以后的发展较之前又有所变化,根据武宗正德三年(1508)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周熊的奏疏,永乐十七年“辽东定辽左等二十五卫,原额屯田共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五十亩,该粮六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五石。”*《明武宗实录》卷三九,正德三年六月己卯,第915页。如果将永乐十七年的数字与前引“自洪武至永乐”的数额相比较可见,无论是屯田顷亩数还是产粮额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不过,永乐十七年的这两个数字与明中期以后辽东军屯屯田顷亩数与产粮量(田12 073顷,粮241 460石。据周熊奏疏)*《明武宗实录》卷三九,正德三年六月己卯,第915-916页。相比,仍然十分可观。
综上所述,明代洪武、永乐年间的辽东军屯,一方面解决了驻守辽东军队的军粮问题,节省了海运饷辽的运输成本。辽屯建置以后,耕垦情况虽有反复,然而总体来说,其出产粮食数量并不在少数,虽然未必总能达到洪武、永乐年间“边有储积之饶,国无运饷之费”这种仅靠仓储屯粮便足充军用的程度,但至少能达到“实收子粒足以充军食之半”*《明穆宗实录》卷三五,隆庆三年七月辛卯,第902页。的程度。
另一方面,洪武、永乐年间的辽东军屯巩固并加强了明代辽东边防,为明代的辽东经略做出了贡献。洪武、永乐年间的辽东军屯,一度实现了辽东各卫所的军粮自给,这为明代辽东驻防的维持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在辽东兴屯的基础上,明代在辽东兴修边墙、墩堡等防御设施,不仅长期有效地抵御了辽东女真诸部的进攻,而且将辽东都司的卫所设置向东北扩展至开原-铁岭一线,扩大了明政府直接有效控制的辽东边疆地区。
二、辽东军屯与奴儿干都司的设立
洪武、永乐年间的辽东军屯不仅实现了辽东驻军粮饷自给的目的,而且还对奴儿干都司的设立与黑龙江流域的经略和开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奴儿干都司是明代在黑龙江流域设置的统辖松花江、黑龙江流域女真诸部的军事行政机构。早在洪武二十年(1387)至二十八年期间,为了追剿蒙元残余势力,明政府即曾派大将率军进入到松花江、嫩江及黑龙江流域一带,还深入到鄂嫩河流域,使得黑龙江上游、松花江南北至与黑龙江交汇处的大片土地都归入明朝版图。
在军事经略的基础上,永乐元年(1403),明廷“遣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烈迷诸部落招抚之”[3]733。永乐二年,有“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把剌答哈来朝”,于是明政府遂“置奴儿干卫,以把剌嗒哈、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驴等为千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明太宗实录》卷二八,永乐二年二月癸酉,第504页。。此后,奴儿干及周边各女真部落头目相继来朝贡,如“(永乐三年三月)奴儿干卫指挥同知把剌答哈及兀者左卫头目木答忽等九十七人来朝,赐之钞币”*《明太宗实录》卷四十,永乐三年三月己亥,第662页。;“(永乐三年三月)癸亥,赐女直及奴儿干、黑龙江、忽剌温之地野人女直把剌荅……等宴于会同馆”*《明太宗实录》卷四十,永乐三年三月癸亥,第668页。等。
至永乐七年,奴儿干地区部落头目忽剌冬奴入朝,向明政府请求在奴儿干地区设置“元帅府”,明廷考虑到忽剌冬奴所陈述的情况与奴儿干地区的重要战略位置,可能是出于经略黑龙江流域的目的,批准了其请求,设奴儿干都司。史载:“(永乐七年闰四月己酉)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初,头目忽剌冬奴等来朝,已立卫,至是,复奏其地冲要,宜令元帅府,故置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统属其众,岁贡海青等物,仍设狥站递送。”*《明太宗实录》卷九一,永乐七年闰四月己酉,第1194页。同年六月,明政府又进一步完善奴儿干都司的组织结构,“己未,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经历司经历一员。”*《明太宗实录》卷九三,永乐七年六月己未,第1236页。
关于奴儿干都司的具体位置,史载:“松花江东北一月之程,所谓黑龙江之地,则又立奴儿干都司。”[4]可见,都司治所设在黑龙江下游。又据晚清文献《西伯利东偏纪要》记载:“查由特林喇嘛庙西北下山,沿江行里许,有石岩高数丈,上甚平旷,有古城基,周曰二三里,街道行迹宛然,瓦砾亦多,今为林木所翳,非披荆履棘不能周知。”[5]该处城址应即奴儿干都司治所原址,即当黑龙江与阿姆贡河汇合口右岸的特林地方[6]。
在奴儿干都司建立后,明政府日益强化了对奴儿干地区女真诸部头目的招抚,先是派内官亦失哈等人前往奴儿干“开设”都司,“招安抚慰”,据永乐十一年所立《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记载:“永乐九年春,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复至其国,开设奴儿干都司。”[7]这里的“开设”,并非创立之意,而是指都司官员前往奴儿干设衙门办事。继而,明政府又在松花江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新置11卫:“(永乐十年八月丙寅)奴儿干乞里迷、伏里其、兀剌、曩加儿、古鲁、失都哈、兀失奚等处女直野人头目准土奴、塔失等百七十八人来朝贡方物,置只儿蛮、兀剌、顺民、囊哈儿、古鲁、满泾、哈儿蛮、塔亭、也孙伦、可木、弗思木十一卫,命准土奴等为指挥、千百户,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明太宗实录》卷一三一,永乐十年八月丙寅,第1618页。
明政府还直接向奴儿干都司派军队短期驻防,如史载:“(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壬子,命辽东都司以兵三百往奴儿干都司获印。先尝与兵二百,至是,都指挥同知康旺请益,故有是命,且敕旺踰二年遣还”*《明太宗实录》卷一五六,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壬子,第1795页。;“(洪熙元年十一月乙卯)敕辽东都司赐随内官亦失哈等往奴儿干官军一千五十人钞有差”*《明宣宗实录》卷十一,洪熙元年十一月乙卯,第309页。;“(宣德二年九月)壬寅,赐往奴儿干及招谕回还官军钞,千户一百锭,百户八十锭,旗军四十锭,命辽东都司给之”*《明宣宗实录》卷三一,宣德二年九月壬寅,第807-808页。;“(宣德二年九月乙巳)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又言:差往奴儿干官军三千人,人给行粮七石,总二万一千石,宜循例,于辽东都司支给,从之”*《明宣宗实录》卷三一,宣德二年九月乙巳,第810页。;“(宣德二年十月庚辰)赐差往奴儿干指挥佥事金声等官军钞有差。”*《明宣宗实录》卷三二,宣德二年十月庚辰,第829页。从史料反映出的情况来看,明政府向奴儿干地区派兵一次少则三五百人,多至一到三千人,奴儿干地区驻防明军的规模大致如此。这些派驻奴儿干的军队,并非长期驻扎,而是以二年左右为期,到期即行遣还。
奴儿干都司的建立,加强了明朝在黑龙江地区的政治与文化影响,推动了明政府在黑龙江流域的建政。随着归附明朝部落的不断增多,明政府在奴儿干地区设置的卫所也日益增加。永乐七年后,明政府在从开原东北至松花江以西的范围内,“置卫一百八十四(曰建州、曰必里、曰毛怜等名)、所二十,为坫(站)为地面者各七,选其酋及族目授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3]733-734至万历年间,奴儿干都司下属卫所情况,据《大明会典》记载,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8]。万历384卫之数,较之永乐184卫,已增加一倍有余,由此亦可见奴儿干都司对明代经略黑龙江流域作用之大。
三、辽东军屯对黑龙江地区开发的影响
明洪武、永乐时期辽东军屯对黑龙江地区开发的作用与影响,主要体现在为明代经略辽东迆北奴儿干都司地区提供了人力与物质保障,并对奴儿干地区诸部与明朝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奴儿干都司虽然在组织结构和形式上也属于明代都司一级的军政机构,但又具有其特殊性。由于奴儿干地方各卫所官员往往是直接由当地部族头目担任,因此奴儿干都司与各卫所之间并没有非常紧密的统属关系,而是维系着一种羁属关系。各卫所由其官员,也就是地方部族头目管理,并定期向朝廷进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而由朝廷任命的都司官员——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则定期前往都司所在地,开衙办事,受命招抚当地居民,但“与各卫所不相辖属”[3]734。另外,奴儿干都司也没有通常地方都司那样的规模较大的常备军长期驻防,而只有朝廷定期派往该地短期驻防或执行安抚任务的小规模部队。所以,这就使得明政府在奴儿干地区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推行如在辽东那样的大规模军屯。从前引史料来看,明政府先后派驻奴儿干地区执行短期驻防任务的官兵,主要是来自辽东都司,而朝廷赐给驻防官兵的宝钞及其向奴儿干地区行军过程中所需的“行粮”,主要都是“命辽东都司给之”“于辽东都司支给”。
此外,明政府派往奴儿干地区的都司官员在招抚、驻防期间的粮食补给也主要依靠辽东都司的运输,史载:“(宣德四年十二月壬辰)召内官亦失哈等还。初,命亦失哈等率官军往奴儿干,先于松花江造船运粮,所费良重。上闻之,谕行在工部臣曰:‘造船不易,使远方无益,徒以此烦扰军民。’遂敕总兵官都督巫凯,凡亦失哈所赍颁赐外夷段匹等物,悉于辽东官库寄贮,命亦失哈等回京”*《明宣宗实录》卷六十,宣德四年十二月壬辰,第1435页。;又“(宣德五年十一月庚戌)罢松花江造船之役。初,命辽东运粮,造船于松花江,将遣使往奴儿干之地招谕。至是,总兵官都督巫凯奏虏寇犯边,上曰:‘虏觇知边实,故来钞掠。’命悉罢之”*《明宣宗实录》卷七二,宣德五年十一月庚戌,第1682页。;又“(宣德七年五月)丙寅,以松花江造船军士多未还,敕海西地面都指挥塔失纳答、野人指挥头目葛郎哥纳等曰:‘比遣中官亦失哈等往使奴儿干等处,令都指挥刘清领军松花江造船运粮。今各官还朝,而军士未还者五百余人,朕以尔等归心朝廷,野人女直亦遵法度,未必诱引藏匿,敕至即为寻究,遣人送辽东总兵官处,庶见尔等归向之诚。’”*《明宣宗实录》卷九十,宣德七年五月丙寅,第2057页。由以上诸记载可见,明政府派往奴儿干的官员及部队,其所需粮食给养要依靠辽东的军屯储粮,并通过在松花江上造船,运输供给;而在松花江上造船的明军士兵的规模要超过500人。这些事例虽然都发生在宣德年间,但正是由于洪武、永乐时期辽东军屯的兴盛,才使得此后辽东都司成为明朝经略黑龙江地区的后勤保障基地。由于从辽东运输粮食以及在松花江上造船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宣德四年以后,明政府召回内官亦失哈,并罢除造船工作。辽粮罢运及亦失哈的召回,从一个侧面说明辽东的粮食补给对于明政府经略奴儿干地区至关重要,以至于辽粮罢运之后,对奴儿干地区的经略也无法开展,随之停摆是必然的。
再者,辽东军屯推动辽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繁荣,进而对黑龙江地区各民族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前文已言,万历年间奴儿干都司下属的卫所较之永乐时期增加一倍有余,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辽东都司作为明朝经略黑龙江流域的保障基地以及辽东地区的经济繁荣分不开的。洪武、永乐时期辽东军屯的兴起,使得周边部族前往辽东贸易者日益增多,因此明政府特在辽东开原等地设置互市场所,以与周边鞑靼、女真诸部进行贸易,此即所谓“辽东马市”。史载:“(永乐四年三月甲午)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初,外夷以马鬻于边……至是来者众,故设二市。”*《明太宗实录》卷五二,永乐四年三月甲午,第776页。辽东马市是明朝与东北少数民族经贸往来的重要窗口,也是辽东地区较为先进的经济生产方式向东北女真诸部传播的重要通道。这一点从辽东马市交易货物的种类中便可见出端倪。此处以明嘉靖、万历年间两份辽东都司呈报的辽东马市抽分银物清册所记三起交易货物为例: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初八日一起,买卖夷人磨磨等四十四名,从广顺关进入,到市与买卖人李见等易换牛只等物……
大牛二只,抽银四钱;小牛三只,抽银三钱;牛犊一只,抽银五分;山羊八只,抽银八分;锅一口,抽银三分;貂皮二张,抽银四分;豹皮一张,抽银一钱;狍皮十一张,抽银五分五厘……参二百七十八园,抽银二钱七分八厘……蜜八十九斤,抽银八分九厘;靴一十三双,抽银一分三厘;木枯一百四十斤,抽银九分三厘;(狐)睡皮一十一张,抽银一钱一分;榛子四斗,抽银四厘;段袄一件,抽银五分;羊马皮五张,抽银一分;铧子二件,抽银一分。(《□□□指挥佥事完仁呈报马市抽分与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五份)》(嘉靖二十九年八月))[9]一八六,716-717
(万历十二年三月)初九日一起,广顺关进入夷人都督猛骨孛罗等六百五十名,到市与买卖人孔保等易……张等物,共抽银一十八两八钱八分九厘。
一、入市货物抽银一十二两九分五厘。
袄子三件,抽银四钱五分;铧子二百八十三件,抽银一两四钱一分五厘;锅七口,抽银二钱一分;水靴九双,抽银一钱八分;牛三十六(只)……
(同月某日入市货物)……袄子十五件,抽银二两二钱五分;牛三只,抽银七钱五分;羊七只,抽银一钱四分。
一、易换货物抽银一十两六钱七分六厘。
貂皮三百二十一张,抽银八两二分五厘;蘑菇四十五斤,抽银三分;鹿皮三张半,抽银七分;狐皮三十五张,抽银三钱五分;睡皮六张,抽银六……参一百一十二斤半,抽银一两一钱二分五厘;狍皮十六张,抽银八分;羊皮一百一十八张,抽银二钱三分六厘;马一匹,抽银七钱。(《马市抽分与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万历十二年三月))[9]一九四,816-817
由上述材料可知,前往辽东马市交易的诸部女真人(即“买卖夷人”),用马匹、兽皮、药材、山货等土产,换取汉人的丝织品、衣物、生活用品及生产工具等。其中,牛、犁铧等农业生产用具的交易量较大,有时一次交易就达到了牛数十只及铧子几百件。
而且,明辽东都司对那些愿意归顺朝廷、经常前往马市进行交易的诸部女真人采取招抚政策,时常用银物对其进行“抚赏”,如:“(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参将赏夷人歹答儿等十名官段三匹,官色布十五匹,官白中布十匹,官铧七件”;“(嘉靖二十九年八月某日)赏镇北关进入买卖夷人都督猛阿等九十九名,用银五两七钱三厘七毫四丝三忽。桌面二十九张,用银一两七钱六毫一丝八忽;酒二十四壶,用银二钱;下程猪肉四十斤四两,用银五钱三厘一毫二丝五忽;牛三只,用银三两三钱;官段五匹;官白中布七十九匹;官色布二十六匹;官小锅九口;官铧四十一件;官盐一十二包零二十斤。”(《□□□指挥佥事完仁呈报马市抽分与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五份)》(嘉靖二十九年八月))[9]一八六,725-726由此可见,辽东都司赏给归顺女真人的物品,除了用于款待酒宴所必备的桌面、酒肉以外,仍以丝绸、布匹、锅、盐、犁铧、牛等为主,并且一次赏赐竟能达到数十件铧之多。据此可以推测,辽东都司不仅向其周边的东北女真诸部输送了大量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还输送了牛、犁铧等大量农具,使得汉人的生活方式与农业生产方式对女真诸部产生了很大影响,进而推动了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农业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可以说,正是由于辽东军屯为明代辽东地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才使得辽东地区成为明朝政府经略黑龙江地区的后勤基地。同时,对于包括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东北边疆民族而言,辽东都司所辖地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它吸引了大批周边民族人口前来归附或贸易,进而又通过贸易往来,加快了汉族生产生活方式向东北边疆地区的传播,从而促进了女真等少数民族本已有之的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些无疑都是辽东军屯对包括黑龙江流域在内的东北边疆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1] 明史:卷八六(河渠志四·海运)[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14.
[2]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上编第七章(屯地总额)[M].北京:中华书局,2009:110.
[3]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女直)[M].余思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4] [明]马文升.抚安东夷记[M]//潘喆,等.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2.
[5] [清]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六七[M]//李兴盛,等.黑水丛书·陈浏集(外十六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1300-1301.
[6]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第四章第二节(奴儿干都指挥使司)[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236.
[7] 钟民岩,等.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校释[J].考古学报,1975,(2).
[8] 大明会典:卷一二五(兵部八·城隍二·属夷)[M]//续修四库全书:七八九(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63-269.
[9] 辽宁省档案馆,等.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第一部分(辽东都指挥使司·马市)[G].沈阳:辽沈书社,1985.
K248.1
A
1007-4937(2017)06-0160-06
2017-09-29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临时课题“明代辽东军屯研究”
战继发(1961—),男,山东梁山人,党委副书记,编审,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胡梧挺(1981—),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从事渤海国史、隋唐五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