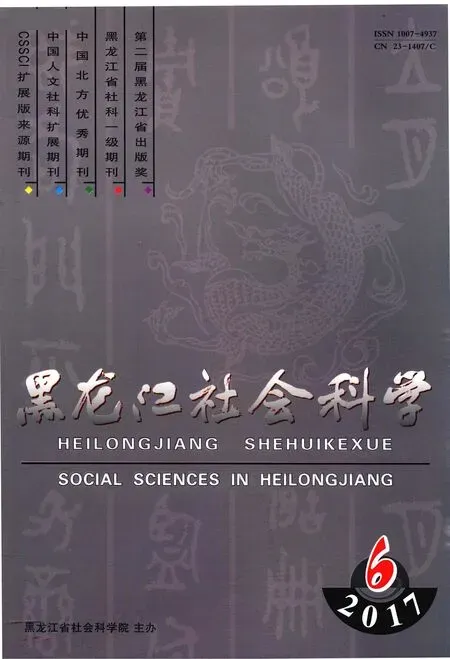空间批评视域下托妮·莫里森《家》的解析
曹颖哲,高 原
(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哈尔滨 150040)
·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
空间批评视域下托妮·莫里森《家》的解析
曹颖哲,高 原
(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哈尔滨 150040)
托妮·莫里森是美国当代著名黑人女作家。小说《家》问世于2012年,是她耄耋之年的新作。运用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批评理论,可以看出这部小说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画卷:在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无论南方北方,白人都在空间占有和使用上拥有绝对控制权,并借此直接和间接地对黑人进行剥削、压迫和规训。身为黑人的主人公意识到白人至上的社会空间剥削和压迫的本质,由南方乡村迁徙到北方城市,试图寻求改变,并在此过程中与白人主流文化价值观进行了艰苦博弈,最终回归南方黑人社区,与周围的人紧密团结在一起,在种族主义盛行的社会空间中重新构建起了属于黑人自己的家园。
托妮·莫里森;《家》;社会空间
托妮·莫里森是美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家,其作品大多基于对美国黑人生活的敏锐观察,内容饱含炙热的种族情感,语言充满诗意与乐感,作品主题丰富多元,涉及种族、性别、阶级、文化等多个维度。布莱克波恩称莫里森“早已超越了美国生活中黑人经历的卓越记录者,她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也是美国本土产生的最配得上称之为民族作家的黑人女性”[1]2。莫里森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并于2012年发表了第10部小说《家》。小说通过空间场所的频频变换,讲述了弗兰克和茜兄妹俩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经历的离家、迁徙、回乡的故事。
空间理论兴起于20世纪后期,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作为空间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于1974年发表第一部系统论述当代空间问题的著作《空间的生产》,拉开了“空间转向”的序幕。列斐伏尔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等多个层面纳入对空间问题的思考,突破了传统的空间观念,将空间赋予社会性,提出了“社会空间”这一概念,并指出“当社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与心理空间(像哲学家和数学家定义的那样)和物质空间(像实践-感觉活动和对自然的知觉所定义的那样)区别开来的时候,其特殊性才得以显现”[1]27。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与社会生产密不可分,“(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的)产物”[2]26。即每个社会都会生产自己的空间,反过来,空间也暗示了对社会关系的容纳和掩盖。空间中蕴含着繁复的社会关系,“不但包括生物性生产关系,比如夫妻、性别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物质性生产关系,即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物质资料的占有、剥削及产品分配关系”[3]。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启发并影响着米歇尔·福柯、大卫·哈维、爱德华·苏贾等后继哲学家对空间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使得空间研究进入到哲学、经济、历史、地理等众多领域,也为20世纪末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论来源。
一、南方乡村——空间侵略下的压迫与挟制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除了作为一种生产的工具,它还是一种控制的工具,因而也是统治和权力的工具”[2]26。小说《家》中,在美国南方,白人对黑人的土地进行大肆掠夺。3K党肆意驱逐黑人,用暴力威逼镇上的黑人居民在24小时之内全员撤离。在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面对白人的公然威胁,黑人只有服从才能活命,否则便是死路一条。像克劳福德老人,坐在自家的门廊上拒绝离开,誓死守护家园,结果就被活活打死。因此,尽管心存困惑、不甘与愤怒,镇上的人们还是收拾行李,放弃了自己的土地、庄稼和其他一切财物,远离故土,踏上了逃亡之路。黑人遭受空间上的侵略,丧失了容身之处,南方乡村彻底成为白人统治的空间,也成为他们榨取剩余价值、争夺利益的场所。主人公弗兰克的继祖母丽诺尔的前夫曾在主路通往乡下的岔路路口开了一家加油站,白人为夺得丰厚的利润而把他枪杀,还在他的胸前张贴了带有侮辱性字眼的字条——“滚远点儿,马上”[4]86。然而,处于大萧条这个最黑暗时期的美国,黑人的生命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警察敷衍塞责,只是声称会进行调查并拿走了纸条,之后便杳无音信。显然,白人在空间上拥有控制权使得他们在利益争夺的战场上也握有绝对的主导权,他们可以对黑人的财产肆意掠夺与抢占,而黑人却无法获得伸张正义的渠道,只能被迫接受残酷的现实。
除了侵占黑人的土地,谋夺黑人的利益,白人还通过剥夺与限定黑人的空间使用权对黑人的人权与尊严进行辚轹与践踏。如:黑人进入白人家只能走后门,因为前门是具有尊贵地位的白人出入的空间,禁止“身份卑微”的黑人通过。白人长期以来在空间的占有和使用上拥有的绝对主动权,不仅造成对黑人直接的压迫与挟制,也间接地固化了他们在黑人心目中不可置疑的地位和身份,并成为一种对黑人进行规训的手段。主人公茜工作的地方是白人博医生的家——“一座宽敞的两层小楼”[4]56,厨房比打工的烤肉店大得多,拥有着“比电影院还华丽的起居室”[4]57。而茜作为黑人则被禁止进入主人的起居室。与白人华丽宽敞的房间相比,茜的栖身之地是一处“狭小,没有窗户”[4]61的地下室,令人窒息的空间充斥着强烈的压迫感。反差强烈的空间映射出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一张权力关系的大网把茜牢牢罩住。本应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异化成了占有与被剥削的关系,而茜却对此感到满足,一心为崇敬的白人医生做助手,热爱这份工作并极力配合,即便沦为医学实验的牺牲品依旧坚信其在为崇高的医学事业做贡献。在福柯的政治理论中,规训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博医生家里的“空间霸权”正是这样一种权力类型,一种建立于空间上并通过空间起作用的权力机制,有力地实现了规训的功能,即制造有用的主体,使之服从于同一种标准,变得顺从,易于驾驭[5]。显然,白人通过对黑人实行空间上的压制使得黑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规训,并在长期的规训中丧失了反抗的能力。
更可悲的是,失去生存空间的黑人群体承受了来自白人的肆意压迫,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转过身来,又将这种压迫施加给自己的同胞。丈夫被白人枪杀后,丽诺尔继承了一些积蓄和洛特斯一处荒废的房产,怀揣500块保险金来到洛特斯,与当地的鳏夫塞勒姆结了婚,从而成了弗兰克和茜的继祖母。与其他黑人的经济状况相比,略好之处在于,她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因此,被白人剥夺了生存和利益空间的丽诺尔,面对种族内部的黑人却自认为高人一等,瞧不起洛特斯的每一个人。弗兰克一家为躲避种族主义的暴行逃到洛特斯来投靠她:拥挤的空间造成起居不便、成员的增多带来经济的拮据与额外的家务、夜间婴儿的啼哭……这些都令她不堪其苦。于是,在这个她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空间里,丽诺尔便将心头的阴郁与愤懑全部发泄在了两个年幼的孩子身上。在这里,她不但可以肆意宣泄怨气,还拥有分配一切空间与资源的权力,其他人必须言听计从。弗兰克一家人奉命唯谨,只能心怀感激、毫无怨言地听从丽诺尔的一切安排。祖父母独享盐渍猪肉,而孩子们则只能喝汤;茜与父母只能睡在祖母家的地板上,弗兰克叔叔睡在拼接的两把椅子上,弗兰克则睡在房子外的废弃秋千上。寄人篱下的无奈与苦楚,激发了弗兰克的父母对早日拥有自己的房子的强烈渴望。他们不辞辛劳、不分昼夜、身兼数职而无暇顾及兄妹二人,对孩子的关爱“如同剃须刀般锋利短促而单薄”[4]50。于是,对现实生存空间的失望与厌弃,加之无处汲取家庭关爱,激发了弗兰克逃离南方融入向往中的北方去寻求自由生活的渴望。
二、北方城市——空间霸权下的剥夺与欺压
列斐伏尔指出,“为了改变生活,我们首先要改变空间”[2]15。白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剥削压迫黑人,获取了更大的剩余价值,并通过侵占压榨黑人的空间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得以生存和发展。而长期生活在闭塞南方的黑人,不堪承受种族主义的迫害,迫切希望改变百无聊赖、不知所终的生活。相比闭塞落后的南方乡村,北方充满着机遇,对自由生活的渴望使得黑人迫切希望融入繁华自由的北方城市。因此,大部分黑人逃离南方涌入北方,去追寻更为自由的生活模式与更为开放的生存空间。然而种族主义笼罩下的北方则对黑人进行了更为残酷的剥夺与欺压。
弗兰克为了逃离南方,选择参军奔赴战场来改变现有的生活,并将自己视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将为美国效力视为一种荣誉。他在战场上奋勇厮杀,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目睹战友被炸得血肉模糊、尸骨不全,还因此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但脱南入北寻求自由的他却不被这个新的空间所接纳,依然不得不挣扎于种族歧视的漩涡中,始终无法获得与白人平等的权利。退役后的弗兰克来到北方某城市,试图同白人一样寻求新的生活,然而却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正如牧师洛克所言,“你来自佐治亚,进了一支黑白混合的军队,也许你就以为北边跟南边很不一样了。别信,也别指望。习惯这东西跟法律一样真实,也一样很危险”[4]17。身为拥有军功章的退伍老兵的他却租不到房子,找不到工作。白人则将弗兰克视作危险的存在,于是他被当成滋事的精神病患者关在了城市中心的精神病院里。精神病院作为惩戒滋事黑人的场所,可谓是一个社会与时代的缩影。在精神病院这个白人医生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空间里,黑人的身体与灵魂均不受自己控制,没有尊严与自由可言。遭受虐待而并非被施以救治的黑人大多死于残忍的不端医疗行为,黑人尸体的最终归宿便是卖给医学院供医生进行医疗实验,以便为有钱的白人提供更好的救治手段。于是教堂成为种族主义残害下黑人求救的首选空间,也是黑人能够被接纳的唯一空间。所以弗兰克听从牧师洛克的建议,来到波特兰向杰西梅纳德牧师求助。但是这个年轻、健壮且高大的退伍老兵,却受到了对方的鄙夷,感受不到一丝关爱。因为这位牧师扶困济危的对象仅限于那些穿戴整齐的穷人,所以弗兰克被拒绝入内。他让弗兰克待在靠近车道的后廊上,并用带着歉意的口吻解释说“我的女儿们在家”[4]20。可见白人认为黑人是粗暴的、野蛮的,会对女人们造成伤害。当然他也为弗兰克引介了不会被拒绝的旅馆与餐馆,但是这样的地方却是少之又少。
弗兰克的女友莉莉,节衣缩食,勤恳工作,只为能够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然而,终于能付得起房子的首付了,却被公然带有种族歧视的“规定”拒之门外:“犹太人、黑人、马来人或者亚洲人均不得使用或占有该房产的任何一个部分。”[4]73可见,黑人即便拥有相当的物质条件却也无法获得精神人权层面的平等。黑人不被允许在车站的柜台前歇脚;无端被警察搜身,肆意没收私有财物,以至于出入公共场所需要时刻保持警觉才能免受伤害;即便车上没有什么人,也只能谨慎地坐在最后一排,并且尽量蜷缩自己的身躯;火车上的一对年轻黑人夫妇,只因为丈夫去车站的咖啡店买咖啡,就遭到欺凌与毒打,妻子为了保护丈夫也受到连累;比利的儿子托马斯,只因在人行道上玩弄玩具枪,就被白人开枪射中造成右臂残疾。可见,即便黑人为了改变生活而脱离南方乡村,做出了改变空间的努力,但是他们在北方却遭受了更为强大的空间霸权的碾压,依旧生存在狭窄阴暗的夹缝中,从事着卑微低下的工作,政治和法律无法给予黑人同白人一样的平等待遇。
三、黑人社区——空间抗争下的回归与博弈
白人为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对黑人实施空间上的欺压,将黑人斥逐到边缘地区,但是“哪里有空间的压迫哪里就有空间的反抗。压迫是与反抗并存的,是辩证统一的,对空间的压迫越大,反抗的声音也就越大”[6]。因此,饱受压迫的黑人社区便成为黑人奋起反抗的空间。而“反抗社会空间的有效途径,即意识上的空间革命”[6]。黑人只有在意识层面彻底觉悟,深刻体认到社会空间剥削和压迫的本质,才能得以实现真正的反抗。
白人医生明目张胆地进行活体试验,依靠侵犯黑人的生命权来推动“崇高”的医疗事业的发展,茜就成了白人医生不端医疗行为下的牺牲品,致使自己永久丧失生育能力。而救出妹妹、带她回“家”的信念于是成了弗兰克唯一的精神支柱。在黑人同胞的帮助下,弗兰克可谓直面残酷的现实,勇于抗争。在途中与白人的冲突中,他不再懦弱,而是“跳上他的背,开始狠揍他的脸,恨不得把牙签插进他的喉咙。伴随着每一拳而来的快感熟悉得让人激动。他根本停不下来,也根本不想停”[4]102。这场打斗让弗兰克获得了反抗的兴奋与狂喜,对救出妹妹充满了信心与勇气。他只身一人来到白人医生家,一个处处弥漫着种族主义气息、彰显着白人至高无上而黑人只能任人蹂躏的权力关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白人医生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反抗之火已经在弗兰克心中熊熊燃起,甚至面对医生的枪口他也毫无惧色,将这个空间中不合理的秩序、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残酷的统治一举打破,不费一拳一脚成功解救出了妹妹,并带妹妹重返南方黑人社区。
弗兰克的反抗举动反映了在白人统治的社会空间中黑人对于自身所遭遇的不公与歧视的抗争,彰显了黑人百折不挠的集体精神。回归黑人社区的行动实质上是黑人与白人之间在争夺生存空间上的斗争,也暗示着种族与阶级之间的较量,以及黑人白人间文化价值观上的博弈。莫里森在谈到社会和邻里的作用时曾说过:“我创作的焦点在邻里与社区上……现在各社会机构担任的职责过去都是由邻居们来做的。如果有人生病,别人来照顾他们;如果有人需要食物,其他人会送过来;人老了,会有人来赡养老人;如果有人精神失常,邻居们会给他们栖身之地;邻里们会介入你的生活,他们认为你属于他们这个群体。”[7]尽管弗兰克等一度逃离了南方乡村,但是南方乡村中充满爱的黑人社区才是黑人真正的“家”。面对茜的遭遇,社区妇女的治疗方法以及在治疗过程中显现的热情与耐心,彰显了黑人的价值观与文化精髓。她们轮流照顾茜,每个人都有一套不同的药方,并传达给茜黑人应有的坚强独立的价值观:“你是自由的。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有义务拯救你。”[4]130她们为茜疗伤,“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强盗医生劫掠破坏过的东西修复如初”[4]133;还教她如何管理自己的园子,因为“花园可以象征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美好的理想,花园的管理象征一个人对各种威胁的应对和处理”[8]。在勤劳豁达的黑人妇女们的帮助下,茜的独具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园艺才能得以发挥,她逐渐摆脱了精神枷锁的束缚,驱赶了灵魂深处的阴霾,开始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以坚强独立的姿态应对挑战,由那个凡事都要躲在哥哥身后瑟瑟发抖不知所措的小女孩,蜕变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坚忍个体。她的花园蓬勃盎然,植物竞相冲破泥土奋发向上生长,成了灰暗生活中的美好一隅,就像黑人社区这个有着强大生命力、有着自我追求的集体一样。黑人社区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人们懂得尊重自己、拯救自己,他们拥有智慧、热爱生活,并善于创造生活。人们像家人一样彼此帮助扶持、乐于分享、共度苦难,面对任何人都表现出强大的包容与仁慈。在白人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社会里,黑人社区彰显的强大生命力和成员之间的仁慈友爱反映了黑人的抗争与求生本能,是对主流社会受过高等教育却缺乏道德与人性的白人群体最有力的回击,批驳了主流文化的不端,挑战了主流文化的权威性,使黑人得以立足并能够对抗白人的空间霸权。黑人社区赋予了兄妹二人强大的文化力量,使得兄妹二人得以重生,并决心在社区安家,开始崭新的生活。
北方城市作为美国社会空间中的主导空间,聚集着丰厚的资本与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黑人不属于这个空间。南方乡村的黑人社区才是黑人的根之所系,它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是为黑人提供庇佑与安全感的真正家园。弗兰克和茜最终通过回归和立足黑人社区,保存了自己并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与独立,在种族主义盛行的社会空间中构建起了属于黑人自己的家园。空间理论强调空间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为社会关系所建构。黑人只有重拾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在种族主义盛行的社会空间中抵制种族的歧视,反抗种族的压迫;只有秉承传统的集体价值观,团结在一起,才能共同构建自由和谐的民族家园并得以长久地生存与发展。
[1] Peterson,Nancy.“Introduction: Reading Toni Morrison——From the Seventies to the Nineties”,in Toni Morrison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2] Lefebvre,Henry.The Production of Space[M].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1991.
[3] 潘可礼.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J].南京大学学报,2005,(1).
[4] Morrison,Toni.Home[M].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2012.
[5] 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779.
[6] 刘先颖.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评述[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20.
[7]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M].Taylor-Guthrie,Danille Kathleen,Ed..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111.
[8] 王守仁,吴新云.国家·社区·房子——莫里森小说《家》对美国黑人生存空间的想象[J].当代外国文学,2013,(1).
I3/7
A
1007-4937(2017)06-0156-04
2017-08-1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托妮·莫里森小说新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研究”(2572014CC12)
曹颖哲(1976—),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从事英美文学研究;高原(1991—),女,辽宁朝阳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 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