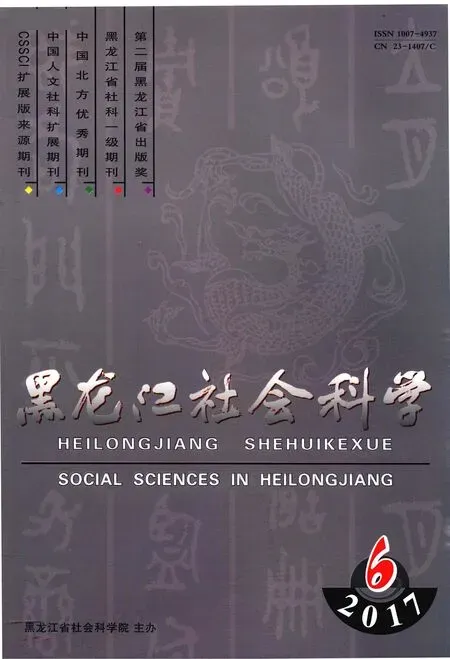齐与不齐之间
——《淮南鸿烈》中的风俗、人情、礼乐
宋 霞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哲学问题研究·
齐与不齐之间
——《淮南鸿烈》中的风俗、人情、礼乐
宋 霞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淮南鸿烈》在处理礼乐和人情,以及礼乐制度和地方风俗等问题上,呈现出个人情感的抒发和社会秩序建构之间的张力。《淮南鸿烈》在继承儒家以礼乐治理社会的主要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转化:首先,《淮南鸿烈》注重礼乐在政治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了民性(情)是礼乐的根源,认为礼乐仅是人性(情)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次,指出统治者因天地之化修礼乐的重要性,但应该明确的问题是,以礼乐治世仅为救败的权变之法,而非“通经之术”,礼乐本身也应该因时而变、与时而迁;最后,其以《齐俗训》为对象,对大一统的礼乐制度和不同地域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在“齐”与“不齐”之间实现了“道”与“事”、“集团”与“个体”之间的圆融。
西汉;《淮南鸿烈》;风俗;人情;礼乐
《淮南鸿烈》由西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集体编写而成。作为汉高祖之孙、淮南王刘长之子的刘安,生于汉文帝即位后的公元前179年,文帝十六年即公元前164年被封为淮南王。《淮南鸿烈》一书是在景帝驾崩时即公元前141年开始编撰,在武帝即位翌年即公元前139年完成,并上书朝廷。刘安的一生经历了文景武三代,由其统编的《淮南鸿烈》成书过程则跨越景武二代。从文景时期以黄老治国取得“大治”,到汉武帝以儒学为尊的历史时期,《淮南鸿烈》全书的前后过渡恰好应和了当时意识形态转化的全过程,其中也夹杂了在大一统礼乐制度和代表了个体性、地域性的民情风俗之间的摇摆不定。
高诱在《淮南鸿烈·叙目》对参与该书撰写者的“天下方术之士”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1]5参与撰写《淮南鸿烈》的“方术之士”主要涉及儒道二派,儒道二家思想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在《淮南鸿烈》的表述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被先秦儒家推崇、被道家“无视”的礼乐问题上,《淮南鸿烈》尽可能地将二家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总之,无论是从《淮南鸿烈》成书的历史背景,还是从其撰写者的学派归属来看,《淮南鸿烈》的主要理路是,在突出礼乐制度对刘氏天下秩序建构所起到的作用的同时,突出对不同区域民情风俗的重视,这是对处理好统一和个性、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有益探索。
一、情与性——礼乐之本
在礼乐问题上,《淮南鸿烈》认为,礼乐是人真实情感的来源,而作为外在表现形式的礼乐应该符合人情感发用的实际状况。
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饮食之性,故有大飨之谊;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经哭踊之节。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为之节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声,故风俗不流;因其宁家室、乐妻子,教之以顺,故父子有亲;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赦长幼有序。然后修朝聘以明贵贱,飨饮习射以明长幼,时搜振旅以习用兵也,入学痒序以修人伦[1]1386。
《淮南鸿烈》将礼乐的来源看成是人性所固有,而礼乐则是人性之所好的外在化表现。先秦儒家在礼乐的问题上具有同样的观点,《礼记·乐记》言:“礼者,天之序也;乐者,天之和也。”[2]在孔子看来,礼是用来节文人情的,乐是用来和乐人情的,只有礼乐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情、礼、乐的和合。在礼乐与人情、人性的主次关系上,孔子强调不可以徒重外在的礼乐,故《论语·阳货》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3]礼以敬为本,玉帛作为礼的文饰,只是用来表达敬意的;乐以和为重,钟鼓作为音乐的器具,只是用来传情达意的;礼乐呈现的意义不是外在的形式规模,而是内化了的人情。荀子在《礼论》中对礼的起源、内容和功用有着系统的论述,强调“隆礼”。荀子对礼的论述是以其人性论为基础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4]欲望是人生而具有的,但欲望无限制的发展就会引起社会的混乱和人际关系的疏离,此时就需要以礼来定秩序。需要说明的是,在荀子那里,礼并不是用来节制人的欲望的,而是对人生而具有的欲求加以“给养”。《淮南鸿烈》在人性的问题上,坚持了道家的一贯宗风,站在“非道德主义”的立场,从不对人性做出善恶价值判断,而是将人性看成“道”蕴于人自身的必然结果。对于人性和人情的关系问题,《淮南鸿烈》认为,人情是人性在与外物交接过程中由静而动的自然延伸,*《淮南鸿烈集释》记载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暂且不论人情好恶是人性由静而动的必然趋向还是对人性本身的戕害,单纯从动静的角度来看,即从好憎之情是人性与物交接过程必然的产物和存在这一点来说,情性在《淮南鸿烈》看来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参见何宁:《淮南鸿烈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页)。人情和人性的关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谓的大婚之礼、大飨之谊、钟鼓管弦之音、衰经哭踊之节不仅是以人性为基础,更是以人情为根据,圣人因循人性、人情制作礼乐,有了固定的制度节文,人伦之理便也由此而形成。
《淮南鸿烈》以人性(情)作为礼乐产生的根源,在礼乐和人性(情)的关系上,强调“文为质设”的原则,强调礼乐与人性(情)的表里、主次关系。“礼者,实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而仁发恲以见容,礼不过实,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1]784既然礼乐仅仅是外化了的人性(情),那么,儒墨二家主张的三年之丧、三月之服和五缞之服就是对人性(情)过分地矫正;靡费国家财货、专求乐外在的华贵就会丧失乐中所蕴含的真情实意,《主术训》说耗费民力、国财的乐只能使乐失去其产生的根基。*“故民至于焦唇沸肝,有今无储,而乃始撞大钟,击鸣鼓,吹竿笙,弹琴瑟,是犹贯甲胄而入宗庙,被罗纨而从军旅,失乐之所由生矣。”(参见何宁:《淮南鸿烈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84页)
《淮南鸿烈》强调,只有以真实的人情人性为根本,礼才能充分发挥秩序建构的作用,乐才能实现和乐人情的实际效果。《齐俗训》言:“故礼丰不足以效爱,而诚心可以怀远。”[1]779这是说,即便礼在形式上有所亏欠,但只要心诚意实,就不必去过分苛求。对于乐,蕴含人的真情实意的乐,不仅能感通他人,更能引起他人的共鸣。《泰族训》曰:“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1]1425《淮南鸿烈》以三代之乐为例证,强调其经久不衰的原因在于浸透在乐中的情感是真诚的。《览冥训》更以师旷奏“白雪之音”之后晋国大旱三年为反面例证,说明师旷的情感意志是与民相同、与天相通的,因此达到了“感天动地”的效果。
礼乐以人性(情)为根本的观点与礼乐发挥功用的界限是密切相关的,《淮南鸿烈》强调礼乐“佐实喻意”和“合欢宣意”的功能。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还之礼也,蹀《采齐》《肆夏》之容也,以为旷日烦民而无所用,故制礼足以佐实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筦箫,扬干戚,奋羽旄,以为费财乱政,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喜不羡于音[1]785-786。
礼乐既然是人性(情)的外在纹饰,就需要将其作用发挥至极,但不可超过人性(情)发用的界限。实际上,礼乐与人性(情)的紧张关系无非就是旧有的礼乐无法表达新产生的、突变的情感,而新产生的、突变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符合人之“常情”的。尤其是乐,乐表达的人性(情)要恰到好处,当人之性(情)沉浸在享受乐的同时,不可过分沉溺于其中以至扰乱本性。
对于久湛于礼乐之俗和礼乐之制的人来说,如果其在面对礼之宏大、乐之绮丽时,能不为其营乱精神、扰乱气志、迷失本性,那么,就可以说实现了“自得”,即道家推崇的“圣人”:“故虽游于江浔海裔,驰要褭,建翠盖,目观《掉羽》《武》《象》之乐,耳听滔朗奇丽《激》《抮》之音,扬郑、卫之浩乐,结激楚之遗风,射沼滨之高鸟,逐苑圃之走兽,此齐民之所以淫泆流湎;圣人处之,不足以营其精神,乱其气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1]74-76《淮南鸿烈》强调“得道者”或“体道之人”是能在日常行为中落实“道”的人,其不因外在形色(包括物与环境)而变化,在礼乐的问题上也是如此,礼乐虽然是人性(情)的真实表达,但是,对于固定化了的礼乐,也不可执着其中,而是需要实现对礼乐本身的超越,这样才能通晓天机、自得其乐,这就是所谓的“自得”而非“得彼”的“体道之人”。
二、经与权——礼乐之治
以人之性(情)为核心的礼乐不仅是人真情实意的外在表达,更是现实政治秩序建构的必要条件。原始道家对礼乐本身并非持完全反对的态度,其将礼乐看成大道离析的结果,认为礼乐愈加繁复,对于治理愈是没有实际效果,最后只能加剧社会的混乱和衰败,故《老子》第三十八章言:“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5]礼的运用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是治理不善的,这就更加需要礼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余英时在《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一书中说道:“但必须强调的是,道家也是针对传统礼乐而提出其理论的。《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也明言‘礼’是‘乱之首’,意谓原始的道体正在逐渐衰落倒退。另一方面,庄子也教我们如何从忘掉礼乐开始,从而达到‘坐忘’来超越现实世界,回归大道。(Watson,p.90)所以,《道德经》所论的‘失道’过程与《庄子》所说的‘得道’历程,恰成一往一复。庄子虽然把所有现有的礼乐制度斥为无意义的人为事物,但他并没有提出要扬弃礼乐,甚至还提及‘礼意’。不过,显然在他看来,对着已过世的妻子鼓盆而歌,是比哭哭啼啼更有意义的丧礼。”(参见余英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淮南鸿烈》一方面强调君主应该顺人(性)情和天地之所化,修礼乐以抚百姓、安社稷;另一方面,又认为礼乐应该因时而化、与时而迁,并对将礼乐看成天下大治的唯一途径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可以说,《淮南鸿烈》对礼乐的态度和观点,不仅是对其成书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中意识形态变迁总结的结果,更是其编撰者对社会深入洞察和理性分析的必然。
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岁于南郊。还乃赏赐,封诸侯,修礼乐,飨左右。命太尉,先杰俊,选贤良,举孝悌。行爵出禄,佐天长养,继修增高,无有隳坏。毋兴土功,毋伐大树。令野虞,行田原,劝农事,驱兽畜,勿令害谷。天子以彘尝麦,先荐寝庙。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决小罪。断薄刑[1]396。
《时则训》以四时、寒暑和十二月之常法为参照对象,对君主在政治运行和百姓治理方面做出行为规劝,如在立夏之时,统治者不仅要带领百官去南郊迎夏季的到来,还需要修礼乐之制、封百官之赏、举贤良之孝、节百姓之功,等等。在立夏之时修礼乐,损益既有的礼乐制度,能够达到礼乐陶冶人情、讽喻民风、实现治理的现实效益,因为有了根据世事变化加以增损的礼乐,就会形成对社稷百姓制度性的保障。就修礼乐这一点来说,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特征,面临着不同的时代问题,礼乐仅仅适用于当时的时代,不可固守“一世之迹”,故《齐俗训》言:“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1]796《齐俗训》为了说明礼乐要应时而变,借刍狗土龙纵然有绮绣朱丝的华丽外表,但却仅适用于“尸祝袀袨”这一场合的例子,结合舜征三苗、禹遭洪水、武王伐纣的历史史实,言明统治者修礼乐要“应时耦变”“见形施宜”。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1]921-922。
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1]919。
礼乐只要以利国利民为根本目的,就不必限定于三代时期的礼乐章法,所谓的“法古”与“修今”,也只是相对而言的,以三代为底本,以现实为依托的礼乐之修才是合时宜的。《淮南鸿烈》将礼乐的治世功能纳入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认为对礼乐的不同程度的运用,是决定治世或衰世的关键。以繁复的礼乐进行社会治理,无疑是叠床架屋,不仅使整个社会浊气弥漫,更会导致历史发展的失落与倒退。上古时期,民众处于蒙童一般真诚纯朴的状态,只求基本生活的满足和真情实感的宣泄,这种社会运行状态虽然不明确言礼,但在这种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完全是按照礼的方式进行交往的。礼本来是为了别尊卑、异贵贱的,义是为了对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的伦系加以规范的,当今提倡礼义之人,“恭敬而忮”“布施而德”,完全违背了礼的本意,不仅人的真性情沦为伪诈,而且整个社会也失去了正常运行的根本。更有甚者,统治者将礼看作社会救弊的唯一方法,不厌其烦地以“礼”去治理和教化,认为礼的施行可以穷治世之本,这样,礼就会变得愈来愈烦琐并失去其灵活性。
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也,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阴阳从而包之,则财足而人澹矣,贪鄙忿争不得生焉。由此观之,则仁义不用矣。道德定于天下而民纯朴,则目不营于色,耳不淫于声,坐俳而歌谣,被发而浮游,虽有毛嫱、西施之色,不知说也,掉羽、武象,不知乐也,淫泆无别不生焉。由此观之,礼乐不用也[1]569。
《淮南鸿烈》认为,仁义礼乐是人真性情的外在表现,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必要举措,但即便如此,仁义礼乐也只是“衰世之造”“末世之用”,《本经训》言:“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1]569从长远来看,作为救败权变之方的礼乐是道德离散的结果,但这并不是对礼乐作用的完全否定,《淮南鸿烈》强调,只有以道为本、以德为根,才能在“朴散为器”之后实现对理想治世的归复,即在道德的指导下,适时、适宜地运用礼乐:“是故以道为竿,以德为纶,礼乐为钩,仁义为饵,投之于江,浮之于海,万物纷纷,孰非其有?”[1]108单纯地以礼乐治世是徒然的,会导致社会的混乱、社会历史的衰败,以及人真性情的沉沦,这是一个不断远离道德的过程,但这并不是一个不可逆反的过程。《淮南鸿烈》讲道德之意,论人情之本,讲的就是“朴散为器”之后的社会和人性“返归于朴”的可能途径。道德与礼乐的差别不仅是形上形下之别、本旨仪表之分,更是在面对不同地域的礼乐风俗时,以何者为原则和标准的问题。
三、齐与不齐——礼俗之辩
《淮南鸿烈》将礼乐纳入政治领域加以论述,强调作为外在仪表的礼乐制度要以人性(情)为本,注重礼乐制度的治世功能,对礼乐制度本身的变革也有详细说明。治国理政不仅要注重作为手段的礼乐制度,更需要处理好其与地方风俗之间的关系,*池田知久是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两者关系的角度来阐述的。在池田知久看来,《齐俗训》不仅是对中央集权的一种消极批判,也是对儒家所提倡的作为“移风易俗”手段的礼乐的抗争,同时其作为一种不同的方案,从尊重不同地区风俗的角度提出地方分权。池田知久将地方的风俗看成是零散的,将中央提倡的礼乐制度看成是系统的,但是,地方风俗中也包含了系统化的礼乐形式,虽然其无法与中央所提倡的儒家的礼乐相媲美(参见池田知久:《睡虎地〈语书〉与〈淮南子·齐俗〉》篇——围绕着“风俗”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对此《齐俗训》一篇就以“齐”与“不齐”为切入点,对礼俗关系及其中的政治意味进行了辩证,在“齐”与“不齐”之间,架构出《淮南鸿烈》的“齐俗”观。对“齐俗”的解释,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任继愈先生认为,“齐俗”的含义就是以“不齐”为“齐”,承认存在差别的、多样性的地方风俗。*任继愈认为:“《齐俗训》以‘齐俗’为命篇,其真意是以不齐为齐,承认差别,统而包容之。”(参见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292页)以“不齐”为“齐”理解“齐俗”的含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庄子·齐物论》*在“齐物”之论的题意解释中,概括有如下三种:即谓无我见则物齐;谓物本自齐,非人为能齐;谓物不能齐、不当齐也不必齐,这就是万物实际存在的情况。在“齐物论”的题解中,概括来说也有三种解释:谓齐一众论,即是言战国时期各家学问的不同,因此要齐同众论为一;谓众论本齐,不必通过人为的努力去齐;谓齐“物与论”,即是说面对天下的众物、众言,只要做到与道为一即可(参见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5页-第36页)。的继承。杨树达先生在对此理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齐俗”并不像许慎注解的那样,使不同地域风俗完全与中央提倡的礼乐制度保持齐同,他认为“齐俗”本意为“侪俗”:“史记游侠传云:‘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浮沉而取荣名哉!’侪俗与齐俗同。”[6]杨树达先生以“侪俗”解释“齐俗”,肯定了各地风俗存在的差异性,强调面对众多“不齐同”的地域风俗时,要尊重不同地区礼乐风俗的多样性,认为多样表现形式的风俗并不妨害人真实情感的一致性,其在承认和尊重地域风俗多样性的同时,也认为不同地域风俗与巩固王朝统治的礼乐制度,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并没有高下之分。
既然“齐”的含义不仅包含了尊重有差异的地方风俗,也包含在价值上地方风俗和中央礼乐的平等地位,那么,两者又是怎样实现“齐”的呢?
义者,循理而行宜也;礼者,体情制文者也。义者宜也,礼者体也……故制礼义,行至德,而不拘于儒墨[1]788-791。
故行齐于俗,可随也;事周于能,易为也。矜伪以惑世,伉行以违众,圣人不以为民俗[1]767。
首先,相互差异的风俗礼乐的形成和固定,是需要以适宜为原则的。《齐俗训》强调适宜的重要性时说:“故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1]771-772“三代时期”的圣王治理天下都需要因时、因地,选择适宜的地理环境安居百姓,选择适宜的方式运作人事,选择适宜的器械服务民众,等等。从适宜的角度看,不同地域的风俗符合其所在地的民情,其发用是适宜的、适用的;为巩固大一统的礼乐制度也是如此,其在一等程度上是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因此,其可以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但是,不论是地域性的风俗,还是中央的礼乐制度,两者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1]768若能使两者并行不悖,地域性的风俗和中央的礼乐制度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由此观之,物无贵贱。因其所贵而贵之,物无不贵也;因其所贱而贱之,物无不贱也。”[1]770其次,从被民众接受的程度来看,地方风俗的形成是需要被民众普遍认可的,这就肯定了地方风俗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为巩固统治由中央确定的统一的礼乐制度,如果其在具体的运作中被当成惑世愚民的工具,不被民众接收和认可,就不会在社会治理方面发挥长远的效益。按照上述两点思路,在《淮南鸿烈》将“齐俗”解释为“齐于俗”之中,蕴含着这样一层含义——即使以礼乐制度作为普遍性的治世举措,也要遵循地方性的发展特点,尊重差异、理解个性,与各地的民俗风情相“齐”,除此,如果没有以合乎时宜和被民众认可接受的程度为参考依据,大一统王朝所颁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礼乐制度也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
除此之外,对于“齐”与“不齐”,还可以从“道”与“事”的角度进行理解。如前所述,不论是中央的礼乐制度,还是地方风俗的形成和固定,都需要以适宜为原则,即因时、因地。“因循”法则在道家尤其在黄老道家历来都是被推崇的方法。“因循”的根本源于“道”。《原道训》以铺陈和转承的方式对“道”加以描述。《齐俗训》也说:“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妙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1]797-798一切事物产生的来源和存在的根据就是“道”,“道”落实于具体事物之中成就其本性,因此,事事物物各不相同,但其归宿是“道”。从“道”的角度来看,中央提倡的礼乐制度与地方风俗,虽然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其背后共有的“道”的指向,因此,地方风俗和礼乐制度是“齐同”的,也是“齐等”的:“所为者各异,而所道者一也。夫禀道以通物者,无以相非也。”[1]798不论是地域风俗,还是大一统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本质上没有区别,所谓的“齐”就是以“道”为齐,而“不齐”就是从现实经验角度讲有不同形式和不同适用范围的风俗和礼乐。
结 论
《淮南鸿烈》对礼乐来源、作用和具体应用的阐述,不仅为大一统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其强调对不同地区民情风俗的尊重和重视,表达了淮南王刘安为其属国求“个性发展”的申述。但若将其作为对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家礼乐制度的抗衡,甚至将其看成刘安之后,对中央政权反叛的证据,则有失偏颇。淮南王刘安在汉武帝即位不久后才上书《淮南鸿烈》一书,那时儒家礼乐定为一尊的局面尚未形成;而《要略》作为全书的总结,用简短的文字介绍了《淮南鸿烈》成书的主要意图和各个篇目的主旨大意:“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纲纪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1]1437又言:“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家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1]1454《淮南鸿烈》将“论事”与“言道”结合,在人事中特别重视为帝王之道提供可资的借鉴。《淮南鸿烈》在处理礼乐和人情,以及大一统的礼乐制度和地方性风俗礼乐的问题上,呈现出的个人情感的抒发和社会秩序建构之间的张力,与其说是对地方分权的一种蓄谋,毋宁说是为处理好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问题而做出的有益探索。
[1]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 朱彬.礼记训纂[M].北京:中华书局,2010:569.
[3]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4:1216.
[4]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409.
[5]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93.
[6] 杨树达.淮南子证闻 盐铁论要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2.
B2
A
1007-4937(2017)06-0096-05
2017-08-30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淮南鸿烈》‘适情’思想研究”(17XNH115)
宋霞(1990—),女,山东青岛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道家哲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