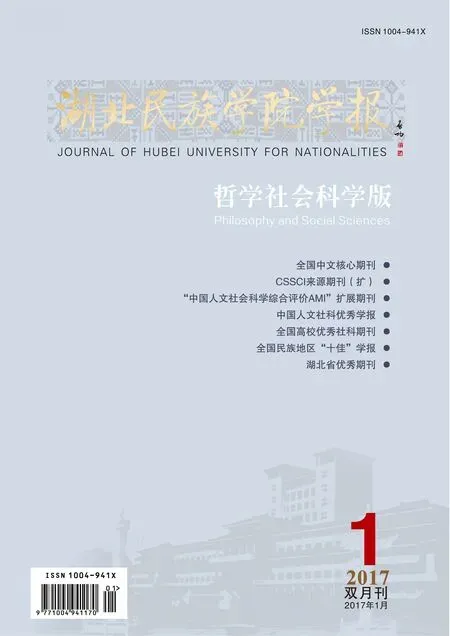西方脉络与中国图景:风险文化理论及其本土调适
张广利,王伯承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西方脉络与中国图景:风险文化理论及其本土调适
张广利,王伯承
(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风险社会研究的文化向度形成了系统的风险文化理论:现代社会风险不是一种社会秩序,而凸显的是一种文化现象;风险是人们主观意识的结果和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建构;而且风险认知本身即是一种问题解决的取向——风险的消弭也有赖于风险文化的再造与风险认知的重塑。西方风险文化理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风险确定性的解构、价值理性的回归、信任危机的弥合,但是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其过于主观的理想化色彩、夸大了社会边缘群体的作用。此外,风险文化理论主要基于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及其文化脉络,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而缺乏非西方经验的总结。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人对物”的征服和开发,中国文化传统则注重“人对人”之间关系的处理——意涵的是一种德行文化、和谐文化,而非西方的智性文化、对抗文化。在现代社会风险弥漫的场域下,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就是实现风险文化理论的本土化建构。这种西方理论的本土调适,进一步实现了风险文化理论的新生,对新时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启示意义,现代风险的“中国式回答”一定程度上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实现的另一种呈现。
风险文化理论;主观意识;价值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理论本土化
英国学者玛丽·道格拉斯是第一位研究风险问题的社会学家,亦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研究文化向度的肇始者。道格拉斯本人或许都没意识到,在他之后会引发风险社会理论的系统研究。而集大成者就是德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他于1986年首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并指出了现代社会诸如疯牛病、核危机、环境灾难、气候变化等现代社会风险无处不在,人类社会已经行进到了“文明的火山上”[1]。之后,随着吉登斯、拉什等人的加入,继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风险社会研究的热潮。作为反思现代性的一种理论体现,不同学者对于风险社会的有不同的理解,进而对风险社会的研究路径也不尽相同,德伯拉·勒普顿归纳了三种研究范式: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文化—象征理论和风险治理性理论[2]。杨雪冬则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总结为现实主义的、文化意义上的和制度主义的三个理论流派。[3]张广利则总结了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三个研究维度:制度维度、文化维度、系统与环境维度。[4]不论基于何种理路对现代社会风险进行研究和探讨,风险文化向度是学者们无法回避的路向;然而这种秉承主观主义的研究范式的存在,尚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总结。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整体基于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取向,忽略了其他国家的经验,秉承风险社会理论文化向度的研究旨趣——风险本身即是特定思想与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与建构,应对现代社会风险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亟须从西方风险文化理论的思想精髓出发, 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吸收其中有利于风险预防和风险规避的合理成分,实现中国本土风险文化的建构。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辉煌、内涵博大精深,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和价值理应在风险社会的时代得以彰显。
一、从“实在风险”到“风险感知”:风险文化理论的滥觞
与其说贝克开创了风险社会理论,不如说他也曾是一位大海边拾贝壳的孩子……他的发现也是站在前人肩上的,这里的前人正是风险文化理论的开创者玛丽·道格拉斯,1982年在和维尔达夫斯基合著的《风险与文化》一书中,她率先解释了公众不断增强的风险意识和关注科技风险的新现象。四年后,贝克正式提出并建构了“风险社会”理论,指出现代风险——与现代性的过分膨胀具有密切相关——是技术理性的必然产物和现代性制度*现代社会创设了各种激励措施、保障制度、预防体系等——无论是冒险取向还是安全取向的制度,这些制度本身也带来了另一种风险,即制度运转失灵、制度执行无效、制度监管缺位、制度异化等所带来的社会风险。的固有困境。这种判断和逻辑走向*从制度性风险的角度看,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制度话语将风险推卸给最没有抵御能力的底层民众。造就了现代社会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财富在上层集聚、风险在底层集聚。之后,拉什汲取了道格拉斯和维尔达夫斯基研究的有益养分并通过“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的对比论述,开辟了风险社会研究的文化向度,并系统地提出了风险文化理论。拉什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和理论表述无法准确描绘出我们当前的社会风险情境,因为风险并非客观实在的、并非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具体来说,风险文化理论强调现代社会风险是文化意义上的,把风险社会的出现表征为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技术发展的副作用及其引起的灾难使人类获得了新的认识——原本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以人们的认知为中介,使人类产生担忧和恐惧,进而引起了新的问题。所以,风险文化理论认为:现代社会风险不是一种制度规制下的社会秩序,而是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是人们主观意识的结果,社会风险凸显的是一种文化现象。
(一)现代风险是人们主观意识的结果
“风险社会”还是“风险文化”的概念之争,实质上是要回答:现代社会风险到底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事实还是人们主观意识的后果。不同于贝克、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大量充斥的各种风险问题是全球化时代不能回避的客观现实,道格拉斯、拉什为代表的学者则表示现代社会中的风险一直都存在着,且恒定如一,大量增加的是人们的风险意识。风险社会主观主义者在认知和管控风险中强调文化的作用,认为现代风险问题是制造风险的文化的产物。[5]
传统社会的推动力可以用“我饿”来概括,意涵人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后果;而风险社会的集体性格则可以用“我怕”来概括,意涵一种不确定的风险。进一步讲,在风险文化理论的界定中,我们生活的时代和之前的时代同样具有危险性,区别是风险的种类上的差异。在工业社会以前,人们面对的风险主要是来自外部环境中的各种自然灾害,譬如地震、洪水、台风、旱涝灾害、滑坡泥石流等等;到了现代社会,地壳运动、大气环流、万有引力、物质运动的规律依然存在,我们依然遭受着此种原因带来的各种风险,只不过这些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威胁已经被置换为现代工业社会“制造的风险”所产生的威胁,譬如大气污染、核辐射对人体健康可能带来的危害。对此,我们没必要流露出比工业社会之前(面对各种风险和灾难)更多的恐惧。因为我们的恐惧一直都存在,只不过从一种恐惧类型转移到另一种类型。风险理论家普遍承认恐惧和风险是密切联系起来的,风险“已经成为恐惧、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感情的核心”[6],“对风险的反思现在被吸收进不安全、受害者和恐惧的广泛文化中”[7]。总之,风险文化理论始终坚持:当代社会风险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所以现代风险是人们主观意识的结果 。
(二)现代风险是特定风险文化背景中的建构
风险文化理论认为,伴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的提升,人们对风险的感知能力也越来越强;而且不同文化背景中社会群体对风险的感知状况也是不同的。拉什基于道格拉斯和维尔达夫斯基的研究,提出了三种风险文化,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8]。风险文化理论认为风险是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建构”,例如环境污染在发达国家被视为风险,在落后地区和亟待开发地区却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国际环境下,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也是不同的:例如在经济繁荣时期和经济萧条时期,不同区域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群体对市场和投资风险的理解是不同的。
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和市场个人主义文化构成了社会的主流和中心,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则是社会主流和中心构成威胁的边缘群体,这种文化的对立,继而导致了社会失序和社会解组。在风险的责任归咎上,信任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群体潜意识中最突出的风险即来自于对其他社会群体的不信任开始,譬如失信的专家系统带来的制度性风险和技术性风险,又如战争、犯罪、艾滋病等等,每一个群体都在谴责他们不信任的其他群体,并把它们当作风险的肇事者,再如近年来频发的环境抗争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政府视之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企业将之看成影响经济效益的风险,而广大群众感知的却是环境污染的风险。可见,现代社会风险作为特定风险文化背景下的一种主观建构思维,是制造风险的文化日益突出的结果。
(三)风险认知作为一种问题解决的取向
风险文化理论关于现代风险是特定风险文化背景中的建构的论断,有利于理解现代风险的生成逻辑,体悟现代社会风险的存在、感知和应对,也正是风险的这种现实性与建构性相融合的特性,决定了它的问题解决取向——风险文化产生了风险,风险的消弭也有赖于风险文化的再造与风险认知的重塑。即便如制度风险的代表人物贝克也不得不承认:风险是指向未来的,风险对社会的刺激在于未来的预期,促使人们提早采取行动[9]。一方面,很多危险和破坏今天已经发生了;另一方面,风险生成理论的探寻,有利于寻找有效应对风险的方法。因而,风险意识和风险认知拥有一种与风险预防和风险规避相联系的特质。风险文化理论的话语下,人们应对现代风险更多地不再是诉诸技术更新来排除风险,而只是通过道德理念和价值信念来处理现代社会风险充盈带来的各种问题,譬如通过生态启蒙实现生态理性,以环境正义的理念对环境弱势群体权益的尊重和保护的实现来解决在全球弥散的环境风险。
在现代社会风险应对上,风险文化理论主张全面提升人类整体的风险意识,摒弃消极的悲观主义和盲目的乐观主义,强调立足现实,既承认风险的毁灭和破坏作用,又承认人类成长进步的光明前景,强调把风险意识作为一种具体的反省批判意识[10]。转变人的自我观念,确立合理的自我意识,合理地控制自我,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最终实现风险的规避。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风险文化理论强调风险意识和风险认知的优化提升,这本身就是一种消弭现代社会风险的问题解决取向。可见,风险文化理论肇始于对客观实在风险的感知与体验,形成了应对现代社会风险问题的独特视角。
二、理性重塑与信任建构:风险文化理论的价值
有别于传统社会统治合法性基础的宗教、权威,现代社会合法性的基础是称为“理性化”的理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认为人类行为是受到个体利益最大化驱使的,这样的观点一时甚嚣尘上。该论调试图证明稳定的社会规范能够作为个体利益的后果而产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社会是以“理性”为思想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启蒙理性的价值预设本是要使人性摆脱宗教和神权的束缚,体现人的价值、使人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这种理性主义的发展固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大幅进步;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启蒙时期的理性发生裂变,集中表现为工具理性主导了价值理性——启蒙理性以数学计算为自己的原则,变成了没有任何价值的形式理性。继而形成了如贝克所言的技术风险、生态风险等“文明的火山”。而风险文化理论基于对主体性的强调,从风险意识与风险认知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风险确定性的解构,直指人类精神家园荒芜的根源,以期重新找回被价值理性遗忘的边缘与角落。
(一)标准化与确定性的解构
秉持客观主义立场的风险社会理论假定了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早期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程,从而也假定了一种标准化的社会发展状态——“风险存在”是现代化发展无可逃避的逻辑。而风险文化理论却高调地宣称:风险应该被感知,而绝非一种客观之物,风险是基于在特定文化背景和社会形式中孕育而被定义和感知的,而且风险在特定环境下还会产生社会放大的效应,特别是灾难事件往往与社会心理和文化制度等因素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人们的风险感知能力并形塑风险行为。所以,拉什宣称“我们也许需要开始向风险社会说再见了。风险社会如今已是日薄西山并终将寿终正寝。我们将要拥抱风险文化,尽管有些许焦虑不安,但绝无担忧和恐惧”[11]61。因为利益群体对风险的感知有助于风险的公众参与与治理。
在风险应对上从依靠专家系统的确定性判断到社会边缘群体的审美自反,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彰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现代风险确定性判断的解构。不同于贝克和吉登斯的自反性现代化的论断,认为现代社会发展成果对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破坏与风险毫无疑问是一种无可逃避且客观存在的现实后果;风险文化理论致力于发掘自反性现代化的美学维度,从另外一个层面弥补了贝克和吉登斯在现代性分析上的欠缺和不足,强调人类行为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对抗的主客对立关系;而是可以发挥个体的能动作用,通过主体的自我反思与价值诉求来为规避现代社会风险开辟道路。
(二)价值理性的回归
不同于贝克、吉登斯等人强调现代风险的制度性以及应对风险的程序性和规范性;风险文化理论镶嵌于反制度性之中,依靠的不是规则和规范而是道德和价值。这种价值体现的是渗透于日常生活中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 强调自反性现代化不仅是认知性和制度性的,而且还是美学维度的,是基于道德和价值之上的“自我诠释”。
康德把审美判断分为决定性判断和反身性判断,拉什指出,前者是一种客观判断;而后者是一种情感性的主观判断[12]52——审美的反思性——崇高的审美判断将暴露出作为主体的人的致命缺点和弱点,暴露出人性中令人恐惧和颤栗的阴暗角落。这种审美判断概括出来的风险让我们触及自身的不足。风险文化理论敦促人们在体验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负面作用后,重新回到了价值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怀抱。特别是风险文化理论强调社会边缘群体在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作用,认为他们是价值理性的倡导者,只有这种无功利性的主体才是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真正中介者和终结者。相对于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以及对社会风险的确定性判断,道德理性与价值关怀的回归成为理性分裂和现代社会风险的“解毒剂 ”[13]15。
(三)信任危机的弥合
信任危机的产生源自于专家系统的失信,媒介作为专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风险弥漫的时代,在风险制造和风险应对上,不同的专家系统往往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作为公共权力交换的设租寻租活动便不可避免,专家被收买的风险增大了,现代社会风险即滥觞于这种知识和权力共谋。
然而,风险文化理论则认为现代社会风险不仅是制度建构的产物,还是一般大众认知的结果:前者强调风险制造,但这种观点并不否认风险发生的外在因素,而是认为利益集团决定了风险问题是否应纳入公共议程以及何时采用何种应对方式,它强调风险发生原因和风险损失是一种话语权下的建构;后者强调风险认知,只有公众觉知风险,才能形成与专家、学者、权力部门等风险制造者的互动。在专家系统遭遇信任危机的第二次现代性*贝克将社会划分为两种类型:一为“简单现代化” 社会,另一类是“自反性现代化”社会。后一种社会形态又被称为“第二次现代化”社会,意指现代化的胜利成果开始危及现代社会本身。,社会边缘群体和社会公众的作用无疑正当其时,在风险应对和规避方面,公众参与风险决策可以使风险政策制定更科学化。例如央视主播柴静的雾霾深度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甫一播出,通过视频网站、社交网络等共同的力量即刻引起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对这种环境风险的关注,问题直指加快落实中国能源体制改革。社会通过更广泛的观点采集、意见表达,就更有可能形成新的、原创性的思想,而不是在技术官僚制下形成某种决策。所以,风险文化理论强调通过增强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关注处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努力提高他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能力,进而增加公众的话语权,通过专家系统与社会公众的双向互动与互信,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风险应对制度的有效性。
三、从西方理论到东方经验:风险文化理论的局限
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一种潜在可能性;而风险意识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亦体现为一种不确定性。这两种不确定性的叠加,更是体现为风险演变机理的复杂性。一方面,就风险文化理论本身而言存在着主观化、理想化与夸大化的局限;另一方面,从风险文化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上来讲,因中国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西方的这种理论陈述不完全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
(一)过于主观化和理想化
风险文化理论认为实实在在的现代风险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群体的特定文化观念促进了风险意识的形成发展,文化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关注并获得现代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意识。因此,在风险应对问题上,他们并不像制度主义者主张的那样,通过制度再造和国际合作来有效地控制风险,而是通过社团活动等非政府组织运动来应对风险。通过审美反思获得带有主观性判断的价值标准为基础建立起反思性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应对社会风险的治理方式不是制度规范,而是要依靠高度自觉的风险文化意识来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自省与反思。总体来看, 这种视角为摆脱风险社会的制度主义结构困境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然而风险文化维度过于倚重从文化视角和人们的主观意识出发阐释风险问题,忽视了现代社会的制度性存在的作用,尤其是把风险应对寄希望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的风险感知和文化信念, 甚至将问题的解决引向了美学领域,带有明显的主观化和理想化色彩。
(二)夸大了社会边缘群体的作用
风险文化理论倡导对风险社会进行反思,坚持从文化和群体的角度出发,认为处于社会边缘的社团群体最具现实精神、非功利性、道德意识和公共情感;相对于社会主导群体的工具理性,对社会边缘群体作用的强调实质上是对价值理性的召回。在个体化的时代,在应对社会风险的问题上,提升社会边缘群体的话语权固然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这是时代进步的一种诉求,弱者的声音不能被忽视。然而,在发生全球性危机的时候,处于社会主流地位的专家系统依然是应对风险的中流砥柱,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着应对风险最雄厚的资本和资源。此外,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他们本身对于现代社会风险的发生更加敏感,这虽然有利于积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但基于自身应对能力有限常常也会诱发出过度反应,比如谣言的制造与传播,集体恐慌的猝发等。社会边缘群体的集体非理性行动,往往会制造出新的风险,例如日本核泄漏后引发的抢购食盐热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三)西方中心主义,忽略了其他国家的经验
与风险文化理论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社会风险论述的情境不同,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还处于一个传统与现代兼具的混合型社会形态,社会风险呈现历时性的风险共时性存在的格局:既遭受着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社会问题丛生等现代社会风险;又深受地震、海啸、滑坡、泥石流、沙尘天气等传统自然灾害的荼毒。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意识和感知里,传统自然风险依然在社会风险结构里占据主导地位。以中国为例,我国的社会风险结构与西方有明显不同[12]。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风险而言,因为 “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传统社会、简单现代化社会和高度现代化社会并存的社会形态。基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区域时空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使得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相互交织、彼此渗透、错综复杂:农村和边远地区面临着极端恶劣气候等自然灾害威胁;中西部地区处于工业化进程早期阶段面临着生产事故、意外伤害等与简单现代性相关的社会风险;而只有北、上、广、深、津等已接近西方国家发展水平的沿海城市和发达地区存在着的主要是与高度现代化相联系的现代社会风险。而且在风险应对上,西方风险文化理论重新宣扬了对价值、信仰、共同意义的追求,企图通过社群重建来形塑医治过度工具理性的弊病,而中国传统上是长期处于一种重伦理、轻团体生活的一种社会形态,进而缺乏凝合边缘社会群体进行社群重建的土壤。
四、传统复兴与本土调适:风险文化理论的新生
西方风险文化理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现代社会风险确定性的解构、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回归、信任危机的弥合,但是仍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其过于主观的理想化色彩、夸大了社会边缘群体的作用。虽然针对当今高风险社会的各种理论流派越来越倾向于一种融合的态势,即风险既是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认知;但是不管风险社会理论,抑或风险文化理论,都体现了一种以西方社会为背景的理论反思,形成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理论,而忽略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此外,在精神气质上,也存在着中西文化分途: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人与物”的对立以及“人对物”的征服和开发,中国文化传统则注重“人对人”之间关系的处理——意涵的是一种德行文化、和谐文化,而非西方的智性文化、对抗文化。历史悠久辉煌、内涵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绵绵五千年而长盛不衰,在全球社会风险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价值应该得到彰显。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
回溯往昔,中华文化在历史上曾独领风骚数千年;直到近代,列强纷纷入侵,国家贫弱,致使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积重难返……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时代使命迫使我们不得不向西方看齐,学习西方的“精气神”,勿论马克思主义、抑或自由主义,卸下“背负”了五千年的精神枷锁,通过简单化地抛却传统、“轻装上阵、加速前行”成了鸦片战争后这个国家思想解放、文化发展的主要轨迹。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当发现西方近代理性对信仰、人性对神性的胜利,我们适时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打倒“孔家店”成为时代的呼声。然而,西方近代文化代表着的工业文明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却由于工具理性盛行而导致人的物化和价值缺失,继而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和蜂拥而至的现代社会风险。民国时期,梁启超在游历海外的过程中,通过见闻感受较早对西方文化下的近代工业文明进行了批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严复在晚期开始认识到西方文化的负面效应,并认为西方文化的极端化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而中华文化的价值则正当其时——“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会书楼不一而足,其宝贵中国美术者,蚁聚蜂屯,价值千百往时,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13]可见,自反性现代化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在重建传统;梁启超、严复所处的时代与我们虽然相去甚远,但殊途同归,中国文化传统的固有价值不容抹杀——重建风险弥漫社会中支离破碎的自我认同与意义缺失,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找到有益的文化资源和智慧因子。国学大师晚年曾梁漱溟有言,“四书五经,故是最富矿藏,惟需用新式机器发掘陶炼而已”;然而,文化复兴,这个1840年以来的课题,至今仍然未得到解决。时至今日,我们已然吹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号角——如果没有文化的复兴,便不能算作真正的民族复兴——应对风险问题的中国式回答对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做出自身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实现的另一种呈现。
(二)中国文化传统具备抑制风险的内在属性
西方价值理念中对自然的征服,而不顾“征服”所造成的危害,如果我们依旧沿袭西方的文化,人类的生存环境只能是越来越恶化。梁漱溟曾指出,“所谓中国文化复兴者非他,意指以伦理本位代自我中心,原来一味向外用力是‘人对物’的态度,而不是‘人对人’的态度。西洋人靠此态度制胜自然,是其成功,但用此态度对人除出现了势力均衡之民主制度外,大体上是失败的,特别在民族间在国际酿成大战,可能把人类毁灭了,把文化也毁灭了,那真算得文化上之彻底失败。”[14]不似西方文化讲究过度进取,中国文化传统是在进取中思量与自然和平共处的规则。如何唤醒人与自然和平共处,是现在风险社会理论话语下我们迫切需要关注的话题;而中国“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崇尚自然的思想精神回应了这一诉求。以此观照现代社会风险,在风险文化的视域下,中国文化传统具备抑制风险的内在属性,特别是集中体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谐文化与德行文化之中。
1.和谐文化,而非对抗文化
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种、培养、教育、发展等;而在中国,“文化”出自“人文化成”的简称。《周易.贲彖》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人文化成”至少包含了四层含义:其一,“人”凸现不能与禽兽等同,人类的道德判断之于生活不流于动物式的本能;其二,“文”通“纹”,其引申涵义为语言、礼仪、制度等人类使用象征符号;其三,“化”则为培育、改造、教化的意思,以此与暴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其本身的伦理意义即在于追求和平、反对冲突;其四,“成”指培育、改造的效用而言,“化成”表明教化并发生功效,内化为道德意识、外显为公序良俗。可见,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体现的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行为的作用,亦合风险文化理论所倡导的价值理性的回归。中国文化传统重视道德生活和人伦规范的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根本上是在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而非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一味地向“物”用力的对抗特质。
2.德性文化,而非智性文化
中国文化传统注重“人对人”之间关系的处理,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人对物”的征服和开发。进一步讲,中国文化传统是一种德性文化,而不同于西方的智性文化。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启蒙运动,人权对神权、民主对专制、科学对愚昧的胜利,理性主义开启了现代性的步伐,并产生的不同于传统的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至此,工业社会的蓬勃发展势不可遏,但同时也失去了道德文明的庇护,各种现代性问题接踵而至,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特点。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启蒙时期的理性发生裂变,一个面相是工具理性的泛滥,科技理性、经济理性的膨胀,盲目地追求科技进步,经济发展;而另一个面相是被忽略的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以及附着其上的社会畸形发展、伦理道德滑坡。我们谈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就是要恢复道德和价值来医治和慰藉虚妄无根的现代心灵。[15]“毁灭人类的并不是科学,而是只知相争不知相让之人生态度。此种以自我为中心,而不能尊重对方,一味向外用力,而决不肯向内用力之人生态度,从来便是人类祸根。不过,加上科学其祸大,没有科学其祸小。是人类不善用科学,科学岂任其咎?今后人类要免于自己毁灭,必须改变此种人生态度而后可”。[14]中国的文化传统注重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为五伦八德的伦理与道德精神,对人和自然是仁民爱物、民胞物与;意欲避免重蹈西方工业社会发展的危机,通过对自己的修省立诚,透过教育而重植人心,或可以德性文化有效应对现代社会风险。
(三)中国本土风险文化的建构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历的一系列社会转型性风险需要我们对其密切关注并及时解决。尽管中国目前并没有真正进入“高风险社会”阶段,但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风险文化理论作为一种以风险意识和风险认知为核心的知识体系, 致力于对现代社会风险确定性的解构、推动社会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回归、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其本质是要在现代社会风险笼罩的氛围中形成以道德和价值为基础的风险规避文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前行,社会分化和利益失衡等问题日益加剧,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风险的各种表征已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自然生态等各个层面和领域呈现出来,并呈现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特点。面对全球风险社会的复杂局面,我们迫切需要从西方风险文化理论的思想出发, 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吸收有利于风险预防和风险规避的合理成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通过增强风险意识来治理社会风险,防止其从潜在的形态变为显在的现实,继而形成当代中国社会的风险文化,以应对我国目前的各种社会风险。中国风险文化的建构,其着重点是指对一些可以医治现代社会风险的文化因子——预防和规避我国各种社会风险有利、对应对全球社会风险有所贡献的知识和智慧——进行系统的提炼和总结。可以形成思想文化要素、艺术文化要素、实用文化要素、政治文化要素涉入的中国本土风险文化建构。具体来说,思想文化要素是基于“和”文化,形成以和为本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艺术文化要素是基于审美文化,弘扬中国传统的经验美学、伦理美学而非西式的理性美学和宗教美学;实用文化要素则可以基于语言、节日、社交、饮食、生活等日常禁忌文化,形成主体自觉的风险规避意识;政治文化要素主要可以基于民惟邦本、修身自律、重刑促廉、廉洁从政等中国廉政文化,实现政府清明、国家稳定的内在文化诉求。
五、小结
《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的“以”是指“用”的意思,总体意思是教人要懂得顺应天道,懂得承载包容。比较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西方文化宗教信仰浓厚、政治和教化有别、理想与现实分离、价值和知识对立,而中国文化中宗教信仰淡泊、政治主宰教化、理想和现实不分、价值统领知识。所以,就风险文化理论话语下的价值和文化知识的关系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蕴含着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内在属性,特别是中国文化传统强调的是一种德性文化、和谐文化,而非西方的智性文化、对抗文化。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并非指的是古籍典章制度在现代社会的恢复,而是在风险弥漫的时代实现中国本土风险文化的建构,于西方理论精髓与中华文化精神的融会贯通中最终实现风险的规避与消弭,这是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亦是新常态模式下的中国对全球风险社会治理做出的独特贡献。
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要按照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国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和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16]。立足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中华大地,吸吮着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化养分,在风险社会的时代,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和价值应该得到彰显,这种西方理论的本土调适,进一步实现了风险文化理论的新生,对新时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风险的“中国式回答”一定程度上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实现的另一种呈现。
[1]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3.
[2] Deborah Lupton. Risk and Sociocultural Theory:New Directions and Perspective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3] 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7-29.
[4] 张广利,许丽娜.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三个研究维度探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8+16.
[5] 张宁.风险文化理论研究及其启示:文化视角下的风险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12):91-96..
[6] Deborah Lupton. Risk [M].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9.
[7] Cohen, S.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3rd ed.)[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2.
[8] (英)斯科特·拉什,王武龙. 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52-63.
[9]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5.
[10] 刘岩.风险文化的二重性与风险责任伦理构建[J].社会科学战线,2010(8):205-209.
[11〗 B. Adam, U.Beck,J. Van Loon. In the Risk Society and Beyond: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M].London:Sage,2000.
[12] 王伯承.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困境与中国本土化启示[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5(6):27-32.
[13] 严复.严复集(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690.
[14] 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170.
[15] 邓立光.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EB/OL].凤凰网历史(2010-04-24) [2015-10-04].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jiachunqiu2/detail_2010_04/24/1055943_0.shtml.
[16]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EB/OL].新华网(2016-05-17)[2016-05-18].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2.html.
责任编辑:毕 曼
2016-12-01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2ASH001),项目负责人:张广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WE1222001);上海市重点学科社会学建设项目(项目编号:B501)。
张广利(1963-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社会理论、社会风险;王伯承(1988- ),男,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风险。
C91-0
A
1004-941(2017)01-013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