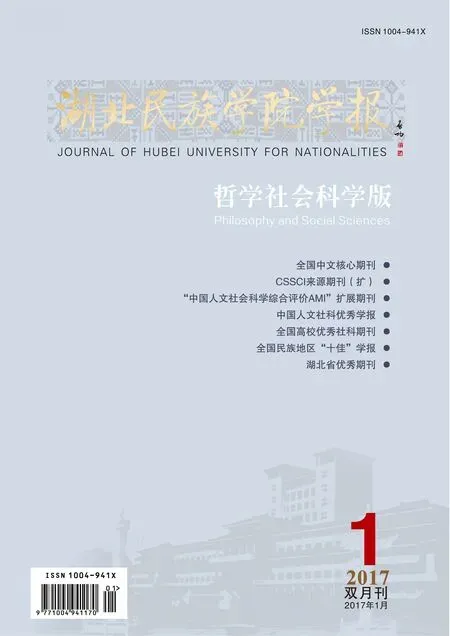文本与阐释:当代欧美托尔斯泰研究述评
陈祥波
(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文本与阐释:当代欧美托尔斯泰研究述评
陈祥波
(湖北民族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国内的托尔斯泰研究注重对俄国文献的参考,对欧美的研究成果似有忽略,本文意在弥补此方面的不足,分析欧美当代托尔斯泰研究的部分经典英文文献,包括两部权威学者的专著、两部论文集、一部丛刊、一部论文选刊,对欧美的托尔斯泰研究现状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描画,以期对于国内的托尔斯泰研究提供资讯和参考。
欧美;当代;托尔斯泰研究;英文文献
从目前国内已发表的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研究的论文和论著来看,欧美当代的托尔斯泰研究领域里最重要的学者和学术成果均处于缺席的状态。要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欧美当代的托尔斯泰研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有赖相关研究机构的支持和学者们的共识和通力合作。本文仅根据已掌握的英文资料,对欧美当代的托尔斯泰研究现状作一个初步的梳理和主要轮廓的描画,这些英文资料包括:两部个人专著,作者均是此领域的权威,借此可以一窥欧美当代研究的高度;两部论文集,一部辞典性质的丛刊,这三本书的文章作者、词条撰写者均是此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借此可以一探欧美当代研究的深度;一份论文选刊,它选录各种学术期刊上登载的文章,借此可以一览欧美当代研究的广度。
两部个人专著,一部是《托尔斯泰的艺术和思想:1847-1880》(Tolstoy’s Art and Thought, 1847-1880)[1],作者唐娜·图申·奥尔文(Donna Tussing Orwin 1967-),当代欧美托尔斯泰研究权威,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斯拉夫研究中心的俄国文学教授,目前担任“托尔斯泰协会”主席(President of the Tolstoy Society)、《托尔斯泰年度论文》(Anniversary Essays on Tolstoy)期刊的主编,她的个人专著还有《托尔斯泰论战争:<战争与和平>的叙事艺术和历史真理》(Tolstoy On War: Narrative Art and Historical Truth in “War and Peace”)、《良心觉醒的后果: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Consequences of Consciousness: Turgenew, Dostoevsky, and Tolstoy),主编《托尔斯泰剑桥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lstoy)、《托尔斯泰和<战争与和平>的起源》(Tolstoy and the Genesis of “War and Peace”)两部论文集,同时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托尔斯泰的论文。此书是奥尔文教授的代表著作,亦是欧美托尔斯泰研究的一个经典文献。作者说她写此书有两个目的:一是澄清托尔斯泰作品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以期让当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托尔斯泰;二是阐明托尔斯泰作品的主题并不在对肉体秘密的揭示,而在于个体生命中肉体和灵魂、大地和天空、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和挣扎。她研究的作品范围包括托尔斯泰早期的自传三部曲、五十年代的作品一直到《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她探讨了托尔斯泰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纠葛,托尔斯泰一直在努力协调客体和主体,她认为后者的理性主义事实上对托尔斯泰的二元论思想产生了影响,歌德式的现实主义无疑也是他的一个思想资源,歌德的思想间接地影响到了他对黑格尔的看法,反黑格尔“历史精神”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个基础底色。而对托尔斯泰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卢梭这个“高贵的野蛮人”,《哥萨克》就是这个影响的直接表现。在分析《战争与和平》时,论者认为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的作家充满了乐观精神,个人能够找到道路通达能够赋予生命意义的统一法则,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很奇怪但可能是真实的是,我认为,《战争与和平》的伟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托尔斯泰是把战争作为一个自然现象来表现的,他反感的只是文明的修饰。”[2]而对《安娜·卡列宁娜》看法,论者认为悲剧在于安娜具有判断善与恶的良知。这本书最主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它分析了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和时代对托尔斯泰自然观的影响,认为这位作家对于自然的深切理解和表现得益于这两个因素。论者分析了一些富有天才的同时代人,如费特、鲍特金和斯坦科维奇的作品与托尔斯泰之间的关联,认为托尔斯泰正是受到他们的影响发展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的原始力量影响到人类的身上就表现为理性化了的爱。
第二部个人专著是《托尔斯泰批评导论》(Tolsto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3]),作者克瑞斯欣(R.F.Christian)是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俄语教授,当代欧美托尔斯泰研究权威,他于1962年发表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一些研究奠定了他在此领域的学术地位,这些研究主要是分析了托尔斯泰在创作中遇到的问题,作家是如何改变了一些人物、情景和情节的安排的,这些分析和观点被采纳进了这本专著的第五章。这部专著可看作是他七十年代以前的个人研究的总结,主要内容是评述托尔斯泰的小说和故事,其次是戏剧和文论,并没有涉及托尔斯泰的社会、哲学、政治方面,唯一的例外的是分析了《忏悔录》。全书的一大半是对《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宁娜》的分析,对《战争与和平》的人物、叙事结构、历史观的分析颇有见地,有意思的是,论者的结论是这部作品反映出托尔斯泰的天才不在于“创造性”而在于“强调的才能”,而《安娜·卡列宁娜》的价值在于“提出了问题而没有答案”,论者同时反驳了那些关于这部小说的结构、风格存在缺陷的观点。在对《哥萨克》的分析中,论者似乎低估了叶罗什卡这个人物形象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个人物是托尔斯泰精神的一个方面的重要象征,梅列日科夫斯基对此有著名的论述。第七章对《忏悔录》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评述,同时分析了《复活》,指出聂赫柳多夫这个人物的虚假性,因为这个人物的转变是不可信的。对晚期的作品的评述中,对《伊万·伊利奇之死》,论者认为伊利奇的悲剧在于自私,而那个青年农民是一个不真实的幻影。最后一章评述了托尔斯泰的戏剧和文论,论者认为《黑暗的力量》明显好于《文明的果实》。附录有一篇内容翔实的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年谱,还有一篇托尔斯泰的简传。
两部论文集,首先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托尔斯泰剑桥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lstoy[4]),主编唐娜·图申·奥尔文,这个指南分“长篇三部”、“体裁”和“总论”三个部分,共十二篇文章,作者均是目前欧美学界的代表学者。开篇是奥尔文撰写的一份长达四十七页的托尔斯泰年谱,信息量大资料性很强,对中国研究者而言是不可多得的一个英文索引。第一部分,首先是莫森(Gary Saul Morson )对三部长篇小说的一个富有洞见的通论,接着芭芭拉·南奎斯特(Barbara Lonnqvist )的文章通过分析“熊、袋子、铁器、星星”这些意象,探讨了《安娜·卡列宁娜》的“结构迷宫”(labyrinth of linkages)论题;第二部分,理查德·弗瑞伯恩(Richard Freeborn )的文章分析了《伊万·伊利奇之死》《克莱采奏鸣曲》《谢尔盖神父》三篇小说,他认为:“于托尔斯泰言,人类真正的目标——幸福,道德,爱,四海皆兄弟,化干戈为玉帛——总是被情欲威胁,这其中的罪魁祸首,是色欲。”[5]“《谢尔盖神父》这部作品反映了托尔斯泰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他立志追求一种精神性的神圣生活,但是这种追求却被色欲困扰。同时期的另一部作品《魔鬼》(1889),这个小说主要的故事素材是他自己在1850年代与农村姑娘阿卡丝尼亚的私情,在这部几乎是自传的小说中,他表达了这同一个矛盾。《谢尔盖神父》对这一主题的探索要丰富得多,达到了更深刻的精神层面。”“《谢尔盖神父》这部作品反映了托尔斯泰这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他立志追求一种精神性的神圣生活,但是这种追求却被色欲的困扰。同时期的另一部作品《魔鬼》(1889),这个小说主要的故事素材是他自己在1850年代与农村姑娘阿卡丝尼亚的私情,在这部几乎是自传的小说中,他表达了这同一个矛盾。《谢尔盖神父》对这一主题的探索要丰富得多,达到了更深刻的精神层面。”“卡萨茨基的性格缺点,正如托尔斯泰自己,是力求完美。”加雷斯·琼尼斯(W.Gareth Jones )的文章分析了戏剧作品,他认为这些戏剧水平参差不齐,总的来讲,托尔斯泰的天才并不在此。第三部分,莉莎·克纳普(Liza Knapp )的文章认为托尔斯泰对孩子的喜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它不仅反映了作家精神的一个特质,而且还导致他的小说的叙事特点,这个特点她称之为 “儿童视角”(child-narrator),她还重点探讨了托尔斯泰的虚无主义,文章引用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的话说:“在鲜花烂漫之中,总是隐藏着一只毒蝎,这只毒蝎就是:‘为什么活着?’”论者的结论是:“托尔斯泰对上帝的追求,源自他的‘虚无’,这个虚无只能用信仰来填补。”克雷(George R. Clay )的文章《托尔斯泰在二十世纪》(Tolsto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论述了托尔斯泰对于二十世纪的影响,大部分的内容是分析对乔伊斯的影响。全书收尾的文章是奥尔文的《托尔斯泰的勇气》(Courage in Tolstoy),她深入分析了托尔斯泰身上的精神悖论:理性与疯狂、哲学与宗教、实践与理论。
第二部论文集:《托尔斯泰研究新论回顾》(Reviews: New Essays on Tolstoy),主编马尔科姆·琼尼斯(Malcolm Jones ),此书是为纪念托尔斯泰诞辰150周年而编辑的论文集,收录了截止80年代的一些研究文章。克瑞斯欣撰写了序,第一篇论文是亨利·吉福德(Henry Gifford 1913-2003)的《论托尔斯泰的翻译》(On Translating Tolstoy),评述了作者认为的四个最优秀的英语翻译者:路易斯、莫德、加尼特、埃德蒙德;主编马尔科姆·琼尼斯的文章探讨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关于托尔斯泰的人物性格塑造手法的观点;布瑞格斯(A.D.P.Briggs )的《<哈吉·穆拉特>低调叙事的力量》(Hadji Murat,the Power of Understatement)和另外两篇从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文章都是分析叙事结构的论文, 娄尼斯(A.V.Knowles )的《<战争与和平>之上的战争: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公爵》(War over War and Peace: Prince Andrey Bolkonsky)分析了安德烈这个人物对于叙事的作用,加雷斯·琼尼斯(W.Gareth Jones )的《一个布道的人:<战争与和平>的叙事》(A man speaking to men: the nattatives of War and Peace)则分析了皮埃尔的精神发展对于叙事的功能;格林伍德(E.B.Greenwood )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宗教》(Tolstoy and Religion)主要是批驳关于托尔斯泰宗教观的一般看法;兰坡特(Lampert )的文章评述了托尔斯泰的政治思想的演变,他认为作家从一个旁观者逐渐转向了革命的支持者;施尼(F.F.Seeley )则分析了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有趣的是,论者用儿童精神学的理论来解释作家在逻辑上的幼稚。
一部辞典性质的丛刊:《世界文学索引》(Reference Guide of World Literature),盖尔集团(Gale Group)出版,其“托尔斯泰”部分的各个词条均由托尔斯泰研究的一流学者执笔,所以也可以说是当代欧美研究成果的结晶,它的内容涉及面广。派克(Chrisopher R. Pike)在为该书撰写的“托尔斯泰”条目里写道:“高加索故事系列开启了卢梭式的‘自然’与‘文明’对抗的主题,它一直延续到《哥萨克》和《哈吉·穆拉特》中,这个主题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乡村与城市,莫斯科与彼得堡,俄罗斯与欧洲,人民与统治者,民众信仰与教会教条。”认为:“《安娜·卡列宁娜》描写的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人与人疏离、躁动不安,既沉湎于社会虚伪的习俗,也被这种虚伪拖得筋疲力尽。”派克的结论认为:“托尔斯泰对道德法则的探索,形成了一种新的、简朴的、似乎是‘真的’基督教信仰。”爱德华·瓦西奥莱克(Edward Wasiolek )撰写的“《安娜·卡列宁娜》”条目则写道:“可以说,《安娜·卡列宁娜》实际上描写的是两个正相对立的爱情:安娜的不正常的毁灭性的爱情,与列文和基蒂健康的爱情。托尔斯泰似乎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只有是建立在生育、艰苦的劳动和简单的欲求的基础上,生活和爱情才是健康的;相反,如果是建立在性快感和自私的基础上,则是不正常的。”“安娜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占有欲、嫉妒和可怜。”“《伊万·伊利奇之死》”条目里写道:“伊万·伊利奇按照时俗安排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要做到愉快而得体,在这种生活方式里,不存在痛苦和死亡。尽管作为事实,痛苦和死亡是存在的,但是它们被刻意地忽视了。一个不承认痛苦和死亡的社会,是一个没有爱和同情心的社会。托尔斯泰似乎意在指出,正是死亡意识才把人类凝聚在一起,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我们建立的生活将如伊万·伊利奇的一样,生活在一个孤立无助、行尸走肉的社会之中。”另一位学者慕斯密林(Arnold Mcmilin )撰写的“《克莱采奏鸣曲》”条目:“尽管《克莱采奏鸣曲》表面主张的是性欲的克制,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篇小说的真正主题是嫉妒。嫉妒,是晚年的托尔斯泰非常个人性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部论文选刊:《二十世纪文学批评》(Twenty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郎曼出版集团(Longman Publishing Group)出版,其“托尔斯泰”的条目辑选欧美大大小小各种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文章,可以说,当代欧美的托尔斯泰研究有价值的成果基本上被囊括一尽,这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是极有价值的资料来源。它的信息量之大可想而知,即使我们这里蜻蜓点水式的评述,内容还是十分庞杂,所以我们分几个方面来做一个陈述。
关于托尔斯泰精神特点方面,毛瑞斯·纳金(Maurice Lakin ):“他的内心生活是一个持续的战场,理性与情感这两者告知他的生命之真理永远在这战场上厮杀。”论者引亨利·特罗亚(Henri Troyat 1911-2007)的话说:“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十个、二十个人,这些人都互为你死我活的敌人:一个拥有特权的贵族与穿戴如老农的人民之友,一个狂热的斯拉夫主义者与欧化的和平主义人士,一个私有制的激烈批判者与财产日渐增长的地主,一个酷嗜猎杀的射手与动物保护者,一个健啖之人与素食主义者,一个东正教长老式的信仰者与猛烈抨击教会的异端分子,一个艺术家与蔑视艺术的人,一个情欲旺盛之人与禁欲主义者。”休·福塞特(Hugh I'Anson Fausset):“或许在很多时候他的观点过分偏激,从不妥协,过分的单纯了,他不是任何别的类型的人,他仅仅只是这样一种人:竭尽全力追求真理,坚信真理和思想对于他自己和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奥尔雷(James Olney )则引述厄内斯特·西蒙斯的话说:“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小说家里,没有任何其他人像托尔斯泰那样写作,他的小说是自传性的,他把自己的生活和观察全变成了作品。”
关于教信仰方面,维塔利·斯文特索夫(Vitalii Svintsov )的论文《信仰与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及其他》逐一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尤其对他们的上帝观念仔细检讨。文中指出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区别:“‘真理(理性)或上帝(谬误)’这选择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镜子中的人和映象一样正好相反,前者对谬误的坚拒和后者对‘基督真理’的虔信本质上是同一个主题的变形罢了。”*Vitalii Svintsov,“Faith and Unbelief:Dostoevsky,Tolstoy,Chekhov,and Others”,in Russian Social Science Review,2002,(1):73-103.作者认为托尔斯泰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在心里竭力寻找基督,但是他的知识和理性使他拒绝相信神迹,这些神迹为托氏所齿冷。休·福塞特认为:“或许在很多时候他的观点过分偏激,从不妥协,过分的单纯了,他不是任何别的类型的人,他仅仅只是这样一种人:竭尽全力追求真理,坚信真理和思想对于他自己和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卡因(T.G..S.Cain )认为:“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了一个贯彻了其一生的信念,他写道:‘建立一个新的宗教,一个新的基督教,它剔除了所有的教条和神秘,没有复活的许诺只有现世的幸福,一个基于自身行动的宗教。’”“为何以及如何生活,这些问题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并不新鲜,它们折磨了他一生,这些问题成了他所有作品的中心。”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 1908-1973)分析了早期和晚期的作品,他的结论是:“总而言之,老年托尔斯泰的那口装满托尔斯泰主义的黑色箱子(屠格涅夫说托尔斯泰有一口装满了神秘的道德主义的箱子——引者注),与童年托尔斯泰的小绿棍,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关于死亡与托尔斯泰的关系的方面,我们发现这是当代欧美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论文数量最多,这个问题的论述中心在于对《伊万·伊利奇之死》的解读,这部分的导论是这样开篇的:“《伊万·伊利奇之死》惹人注目,它是托尔斯泰1870年代的道德和精神危机之后的第一部小说类作品,它以艺术的形式表达了这位作家精神转变后的人生理念,因此普遍认为这部作品是托尔斯泰文学生涯的分水岭。”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 1921-1980)认为:“海德格尔与托尔斯泰就有更大的关系了,《存在与时间》最终探讨的是死亡,其关于死亡的看法,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伊万·伊利奇之死》的注解。”菲利普·拉夫:“伊万·伊利奇是每个人,当他奄奄一息之际所陷入的孤立无援的绝境,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即无可逃避的死亡之现实。”罗伊·皮瑞特(Roy W. Perrett )的文章《托尔斯泰:死亡与生命的意义》分析了托尔斯泰的两个文本:一个是“传记类”的《忏悔录》,一个是“小说类”的《伊凡·伊里奇之死》。通过解读前者,作者认为托尔斯泰最终不能违反自己的理性去盲信。对后者的解释,他认为死亡让伊里奇认识到他客体化的生活世界没有给他的主体的生命意义任何保障,当死亡降临的时候,注定被摧毁。“托尔斯泰最终不能违反自己的理性去盲信。对后者的解释,他认为死亡让伊里奇认识到他客体化的生活世界没有给他的主体的生命意义任何保障,当死亡降临的时候,注定被摧毁。”马克·弗里曼(Mark Freeman )的论文《死亡,叙事整体和自我理解的极端挑战:<伊万·伊利奇之死>的一种解读》,认为托尔斯泰的小说总是一个接一个的灰色人生,人物在生活中不断陷入迷惘和绝望,只有当他们面临衰老和死亡的时候,才逐渐看清楚了整个的人生面目。作者得出结论说岁月和死亡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人生的意义,而对于托尔斯泰的小说叙事来讲,这样的终极价值的观照才使得他的故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特瑞林(Lionel Trilling )则说:“托尔斯泰用伊万·伊利奇的死警示我们如何才能生活得有意义。”威廉姆斯(Michael V. Williams )的《托尔斯泰的<伊万·伊利奇之死>:在跌落之后》(Tolstoy’s ‘The Death of Ivan Ilych’: After the Fall)是一篇颇具独识的文章,他认为伊万从梯子上跌下来这个物理现象,其实是一个象征:“伊万的跌落实际上是一次自我意识的跌入,它导致了一种内心世界的重生,即他开始意识作为人的意义。伊万仕途的升迁其实是一种沉沦,因为它的代价是自我和童真。”他进而认为,整篇小说都建立在这样一个“跌落——爬起”的反讽结构中,伊利奇仕途的升迁实际是跌落,从小孩成长为大人其实是跌落,相反的是,他从梯子上跌落开始了精神地爬起,向死亡的跌落却意味着新生。萨里斯(Rima Salys )有相似的观点,他说:“伊万活着的时候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而他的死却导致了精神生命的重生。”帕奇慕斯(Temira Pachmus )的文章《<伊万·伊利奇之死>的主题:爱和死亡》(The Theme of Love and Death in Tolstoy’s ‘The Death of Ivan Ilyich’)主要探讨了死亡与托尔斯泰的关系,他引证一些传记和回忆录的资料,说明托尔斯泰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现出对死亡的强烈意识,“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深知其夫对死亡的恐惧,在一则日记中她写道:‘他对死亡充满了巨大的恐惧。’伯爵夫人的妹妹,塔基亚娜·库兹明斯卡娅,也有相似的回忆:‘托尔斯泰经常提到死亡。我记得他有一次说,是啊,我们的生活多么安乐!只是如果想到死亡,人就不能生活了。”他认为托尔斯泰的死亡意识根本上是形而上性质的,而非动物性生理性的恐惧,他说:“梅列日科夫斯基,这位敏感的评论家,认为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恐惧含有物理性质,但并非源自这位作家的肉体恐惧,毋宁说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特征,他说:‘这种恐惧是一种更为内在的和根本的类型,它的根源是抽象的或者说是形而上的,而非动物性的。’”最后,他总结道:“我们可以设想,托尔斯泰这个形而上的观念与柏拉图、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的哲学是一致的,那就是:就人类所能认知的最高事实而言,万物共存天地人一体的和谐关系乃是宇宙的终极真理。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之为爱。爱,是最高的事实,这是托尔斯泰的结论。”
相对于欧美当代的托尔斯泰研究成果的丰富性而言,以上述评真是沧海取其一粟,是真正意义上的“以管窥豹”,我们的这个工作只是一种努力,希望引起国内的研究者注意到欧美同行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亦是一种抛砖引玉,希望对于欧美的托尔斯泰研究成果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译介。
[1] Orwin, Donna Tussing. Tolstoy’s Art and Thought, 1847-1880[M].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Christian, R. F. Tolsto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3] Orwin, Donna Tussing.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olsto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4] Johns, Malcolm.ed. Reviews: New Essays on Tolsto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5] Henderson, Lesley;Hall, Sarah M. ed. Reference Guide to World Literature[J].second edition vol. 2 M-Z, London: St. James Press, 1995.
责任编辑:毕 曼
2016-12-15
陈祥波(1974- ),男,湖北利川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I06
A
1004-941(2017)01-01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