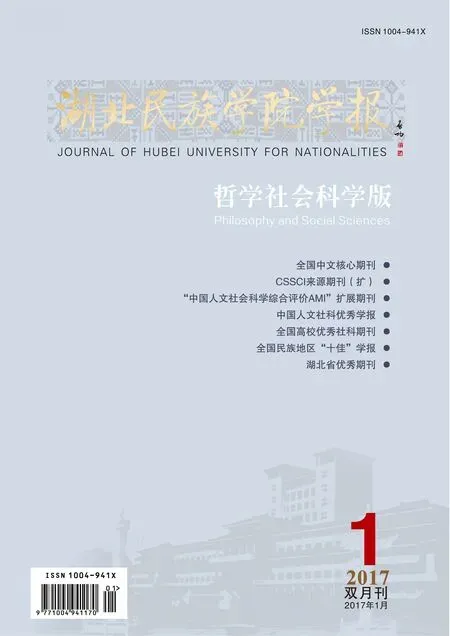厦门大学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传统与未来展望
董建辉,黄铭松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厦门大学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传统与未来展望
董建辉,黄铭松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林惠祥先生是大陆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拓荒者,他的相关论著开创了厦大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学术传统。20世纪下半叶,在无法亲赴台湾开展田野调查的情况下,厦大同仁继续坚持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在台湾原住民族的起源、族称、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及传统特色文化等研究领域有所推进。进入21世纪,厦大人类学者当在传承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固有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境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力求创新、突破。
厦门大学;台湾原住民族;传统;展望
厦门地处台湾海峡西岸,自古以来与台湾关系密切。职是之故,厦门大学(以下简称厦大)向有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学术传统。自林惠祥先生1929年亲赴台湾开展田野调查,开启大陆学者对原住民族研究之先河,近一个世纪以来,厦大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传统绵延不断,始终占据着整个大陆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半壁江山。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厦大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回顾厦大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学术历程,总结其经验得失,有助于厦大同仁更好地思考与展望,在海峡两岸学术与文化交流日趋繁密的背景下,如何传承既有的学术传统,推进大陆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
一、“开辟荆榛”:林惠祥开启台湾原住民族之研究
林惠祥是我国早期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也是厦大人类学的奠基人。1929年,他受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委派,利用前往台北替父奔丧之机,化名林石仁,假托为商人,“乘机入番地,研究番族,搜集其风俗习惯之标本”[1]6。期间,他多次赴台北圆山西麓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贝塚”考察。又从台北南方山区乌来社开始,历桃园角板山,经苏澳、花莲,再转赴台东、新港,回到台北后,复折往日月潭,先后访问了卑南、马兰、哈喇巴宛、大马武窟、知本、水社等番社,涉及太么(泰雅)、派宛(排湾)、阿眉(阿美)、蒲嫩(布农)等族。*依今日之认定,卑南、知本等社为卑南族,日月潭水社为邵族。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辛考察,他收集了圆山遗址石器、陶器100多件,及大量原住民族文物标本,其中以“樟脑木所刳制之独木舟……长丈余,尤不易得”[1]6。1930年,他在前此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完成了《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由中央研究院以“专刊”的形式出版[2]。同年6月,交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是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番情概说》有9章,依序是总论、各族分述、生活状况、社会组织、馘首及战争、宗教、艺术、语言、智识;中篇《标本图说》将所搜集的原住民族器物共264件分10类,附照片予以说明;下篇《游踪纪要》简述其考察台湾原住民族的经历。文末并附录《中国古书所载台湾及其番族之沿革考略》,考证台湾与大陆的渊源关系。该书最突出之处是,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综合运用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对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考察。“这样一种多学科、多视角、多形态的多元著述范式,无论是在同时代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中还是在当下的学术著作当中都相当稀见”[3]。林惠祥的这本“开辟荆榛之作”[4]是大陆学者首次以科学的方法系统开展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它开启了大陆科学研究台湾原住民族之先河。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评价说,《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家研究台湾高山族的韧始”[5]。
1935年,林惠祥在厦大任教已届4年。为了给自创之人类学标本陈列所添加藏品,他又于“暑假自费复往台湾,再入番地,采买标本”[1]8。历两周,采得标本有番刀、枪、弓、箭、衣饰、雕刻物、船模、史前石器等数十件。这些标本如今都已成为他1953年创立的厦大人类博物馆的馆藏珍贵文物。
基于1929年和1935年先后两次亲赴台湾原住民族地区田野调查的经历,加上1937年在闽西武平小径背山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之所得,林惠祥对于台湾与大陆的渊源关系有了逐渐深入的思考。早在1932年底出版的《世界人种志》中,他就将台湾原住民族归入海洋蒙古利亚种——马来种,误称“台湾番族也属马来族,在石器时代由南方移入”[1]160。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他再次确认:“番族确系自南洋移入,惟其移入之时必甚古,因台湾全岛无论山岳平原均有石器时代遗址,可证其移入时尚在石器时代”。[6]79但在以后的著述中,他对此一认识发生了怀疑。[3]例如在1947年发表的《福建民族之由来》中,林惠祥提出:“古越族与马来族在体质上及文化上似颇有关系,然证据尚未充分,只可作为假说,未可即视为定论。此事之解决须待将来地下之史前遗址遗物发现甚多,方可据以论断也。”[7]745到1955年,林惠祥发表了《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他关于台湾原住民族起源的成熟看法。他提出:“台湾在新石器时代便曾有一支人类由中国大陆的沿海地方漂流过去,带了新石器的文化即磨制石器和印纹陶、彩陶、黑陶等技术进入台湾,这种从大陆过去的新石器时代人,便成为后来的高山族的一支来源。”当然,因为“马来人既散布到南洋各岛,达到菲律宾的也难免会有一些人被漂流到台湾来”,所以说“台湾土人的来源不止一种,其中的一种出自中国大陆的古越族,其后与来自南方的别族逐渐混合,而成为现在的高山族”[8]215-216。换言之,台湾原住民族的来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林惠祥并未将视野局限于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而是进一步拓展到马来族与华南的关系。为此,他在编译出版《苏门答腊民族志》(1945)、《婆罗洲民族志》(1946)的基础上,又撰写综论性专著《南洋人种风俗概说》(1948)及相关论文《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1957)、《南洋民族的来源与分类》(1958)等。在《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一文中,林惠祥从体质特征、文化习俗、考古遗存等多方面,论述了东亚大陆、台湾、东南亚群岛土著民族文化的源流关系,将大陆东南的百越民族及其先民文化确定为包括台湾原住民族在内的“马来”种族与文化的祖先,并且明确提出百越民族及其先民南迁南洋群岛有东、西两条路线。他说:“马来族的重要成分蒙古利亚种海洋系是从华南来的”“马来族南迁的路线应有二条:第一是西线,是主要的,即由印度支那经苏门答腊、爪哇等到菲律宾,其证据是印纹陶和有肩石斧。第二是东线,是由闽粤沿海到台湾,然后转到菲律宾、苏拉威西、苏禄、婆罗洲,其证据是有段石锛、有肩石斧”[9]。
从1931年调任厦大人类学、社会学教授,到1958年因脑溢血辞世,再除去抗战爆发后10年的流亡南洋时光,林惠祥在厦大实际担任教职的时间尚不足20年。但是,就是在这数十年间,林惠祥奠定了厦大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根基。他在台湾原住民族研究领域留给厦大的学术财富突出体现在:其一,以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作为厦大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旁及闽台区域文化、畲族、疍民及南洋研究;其二,立足人类学田野调查,综合运用人类学(含民族学)、考古学及历史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将台湾原住民族置于东亚大陆与南洋民族历史文化关系的学术框架中去加以考察;其三,注重文物标本的采集,内容包括史前遗物、历史时代古物和现代民族风俗品,并设立人类博物馆以陈列,既可供教学科研参考,又可开放给一般民众参观。
二、继往开来:20世纪后半叶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
林惠祥逝世后,他所开创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事业由其助手陈国强和同仁以及他们的弟子继续朝前推进。早在1958年,在全国开展的关于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中,陈国强就参加了高山族小组的调查,并担任组长,集中搜集整理台湾原住民族的史料,对定居大陆的台湾原住民族展开调查访问,在此基础上编写了《高山族简史简志合编》[10],1980年又改编为《高山族简史》[11]。这是我国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台湾原住民族简史。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两岸阻隔的历史原因,陈国强和他的同仁未能承袭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传统,亲赴台湾地区开展原住民族的实地考察,而只能依靠有限的文献史料及少量的考古学证据,进行台湾原住民族的起源、族称、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及传统特色文化等研究。这些研究都带有明显的“史”的特征,与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凭借地理之便,深入台湾原住民族地区,开展广度、深度俱佳的民族学考察,产生一批经典的台湾原住民民族志*举其要者,有卫惠林、林衡立:《同胄志·曹族篇》,载《台湾省通志稿》(卷八),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52年;陈奇禄、李亦园、唐美君:《日月潭邵族调查报告》,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专刊第一种,1958年;卫惠林、刘斌雄:《兰屿雅美族的社会组织》,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之1,1962年;李亦园:《马太安阿美族的物质文化》,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之2,1962年;《南澳的泰雅人》(上、下),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之5~6,1963年;丘其谦:《布农族卡社群的社会组织》,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之7,1966年;刘斌雄等:《秀姑峦阿美族的社会组织》,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之8,1965年;阮昌锐:《大港口的阿美族》(上、下),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之18~19,1969年;石磊:《筏湾——一个排湾部落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报告》,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之21,1971年;李壬癸:《鲁凯结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第64种,1973年;卫惠林:《埔里巴宰七社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甲种之27,1981年。,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
(一)族源、族称
台湾原住民族的来源主要有土著说、南来说、大陆说和多源说4种。如前所述,林惠祥持多源说。陈国强运用新的考古学发现、文献记载及民间传说等,论证林惠祥的观点,而且更明确地提出,台湾原住民族的主要来源是大陆的古人类和古越人,他们“主要来自祖国大陆东南沿海”,是“南方古代‘百越’的一支”,至于其他来源如南洋的马来人、黑矮人、汉人等,都是较晚近的事。*陈国强:《高山族来源的探讨》,《厦大学报》1961年第3期;《从台湾考古发现探讨高山族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他提出古越族渡台的路线是“由浙江而福建,由福建而台湾,然后由台湾迁移到菲律宾”[12]。其中一个重要依据是,第四纪更新世冰期,因海面下降,大陆和台湾连为一体,以后又形成“东山陆桥”,这为台湾“左镇人”和“长滨文化”主人由大陆迁移台湾提供了地理上的便利[13]。受其影响,郭志超以冰期及其后海陆变迁和海流为自然依据,结合神话传说和部分考古资料,进而讨论了南洋马来土著迁台的路线[14]。辛土城也从考古学和文史证据出发,论述了宋元时期溯至石器时代台湾原住民族及其先民与海峡两岸汉族及古民族的关系[15]。邓晓华对比壮侗语系和南岛语系的同源词所反映的文化特征,得出和考古学、民族学一致的结论,即“现存台湾的南岛语是大陆原南岛语的继续,操原南岛语的是古越人,原南岛语的老家是古百越文化区”[16]。
台湾原住民族自古有不同的族称,这些族称多系“他称”。1953年大陆的全国人口普查,正式确立了“高山族”这一名称。但是,这一名称是否合适,厦大同仁有不同意见,为此争论激烈。陈国强追溯了从古至今台湾原住民族的名称沿革,认为“高山族这一名称有其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原因”,赞成使用这一族称[17]。他指出,日本学者将台湾原住民族划分为若干族,是秉承侵略者的意图。根据对阿美、泰雅、排湾、布农、曹、赛夏、雅美等各族自称的意义分析,他认为,这些名称只能“作为高山族(民族)内不同支系、地区的称呼”[18]。陈碧笙的意见则相左,他认为“高山族”的名称与日本殖民统治密切相关,“台湾土著居民不是一族,而是分为七至九族”,各族在体质、语言、住区、生活习惯、生产力水平、社会组织、阶级分化以及心理状态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所以“似应逐渐代以各族固有的名称”[19]。针对这一争论,当时即有学者中肯地指出,历史上台湾原住民族的称谓一直在变化之中,如何科学、准确、实事求是地给他们以确切的族称,的确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而又急需确认的难题[20]。
(二)宗教信仰
台湾原住民族有繁杂多样的宗教信仰,“从平权社会的精灵信仰,到阶层社会的多神信仰及其相应的宗教仪式,不但与其不同的社会制度有所关联,也被用来解释各种未知的现象和指导人际和群际的对应”[21]82。20世纪50~60年代后,又大多改宗基督宗教。因缺乏实地调查,厦大同仁多仅依据文本资料,对台湾原住民族较早期的传统宗教及其仪式实践进行探讨,并冠其名为“原始宗教”。陈国强考察了台湾原住民族从泛灵到神灵的发展及其象征形式,以及巫术、禁忌与占卜[22]339-353。范可考察了台湾原住民族宗教信仰的社会基础、自然环境背景及巫术、祭仪。*参见范可:《略论高山族原始宗教的社会基础》,《人类学研究》1985年创刊号;《试析高山族原始宗教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高山族巫术论析》,《思想战线》1987年第5期;《高山族祭仪分析》,《厦大学报》1988年第1期。陈在正探讨了台湾中部平埔族的汉化及其妈祖信仰[23]。陈国强编写了《高山族神话传说》[24],并从民间文学的视野,对台湾原住民族的神话及民间传说进行了分类介绍,将台湾原住民族的神话体系类分为有关族源、自然现象、风俗和技术起源、动植物等4类[25]。
(三)社会经济发展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的相互作用、辩证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受其影响,厦大同仁结合台湾史上的重大事件,从多个不同层面,探索台湾原住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及其动因。陈国强先后考察了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政府统一台湾及日本窃据台湾等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政策措施对台湾原住民族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参见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的高山族》,《厦大学报》1962年第2期;《17世纪前后高山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厦大学报》1979年第1期;《康熙时期台湾高山族社会的发展状况》,《民族研究》1984年第3期;《清朝对高山族教化政策评述》,《厦大学报》1993年第2期;《日据时期的台湾少数民族》,《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并且注重从生产力的角度把握台湾原住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后者体现在诸如《台湾高山族原始农业的起源和发展》[26]《台湾原住民族的人口、语言和宗教》[27]等论著中。
厦大同仁对台湾原住民族社会发展的研究,十分重视经济层面的考察,这与厦大的历史研究重视社会经济史考察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陈国强以《临海水土志》和《隋书·流求传》两篇史料为据,分析了台湾的古代社会经济,认为“台湾古代社会经历了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28]。陈碧笙依据陈第的《东番记》及荷人揆一的《被忽视的福摩萨》等资料,分析了17世纪中叶平埔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认为当时平埔各部落的社会经济水平大体上还处于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的初期[29]。郭志超以汉“番”土地关系与原住民族“番社”内部的土地租佃关系为因果关系,集中分析了台湾原住民族内部封建租佃制的产生,进而分四个区域探讨台湾原住民族清代的社会经济形态。*郭志超:《清代高山族土地关系的新变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清代高山族划分及其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战线》1986年第5期。
(四)民族关系
从三国时期开始,台湾原住民族就与汉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有了往来。明清以后,随着汉人成规模移民台湾,两者间的关系更为密切。陈国强分4个阶段回顾了清代以前汉族与台湾原住民族在共同的生产实践和反抗外来侵略中形成的关系,充分肯定两族“在古代的关系主流是友好的”[30]。他特别分析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建设台湾的过程中,台湾原住民所给予的支持,及郑成功对原住民族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指出这种双向互动促进了汉族与台湾原住民族的团结[31]168-195。陈碧笙探讨了17世纪中叶平埔族与汉族之间因为商品交换所发生的接触、融合关系[32],并对二者间在土地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进行了分析,也指出在两族关系中,同化与融合是主流,矛盾和冲突是次要的[33]。
一些学者从更微观的事件或人物的角度去考察台湾原住民族与汉族的关系。陈国强回顾了噶玛兰的开发史,肯定噶玛兰通判姚莹(1785~1853)在其中所做的贡献,指出噶玛兰的开发史是海峡两岸的汉族和原住民族共同开发台湾的生动例证[34]196-212。他还分析了台湾巡抚刘铭传在任内采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及其对台湾原住民族及两族关系的影响[35]213-229;论述了蓝鼎元(1680~1733)治理台湾的贡献以及他对台湾原住民族的记述[36]。陈孔立针对过去不少论著认为番族参加了林爽文起义并在其中起了不少作用的观点,以档案史料为据,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过去关于番族参加起义的例子是没有根据的,相反,部分番族还被清政府利用参加镇压起义的活动。对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应该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37]。郭志超探讨了清代汉族影响下台湾原住民族的农业技术变革[38],以及汉族与原住民族之间的贸易关系[39]。
在民族关系的研究上,厦大同仁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基本都将台湾原住民族视为一个整体,即所谓“台湾高山族”,而极少考虑其内部七族或九族的差异性。而且,他们所指称的“高山族”其实主要指的还是汉化程度较深的平埔族。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其他专题的研究中,只是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五)民族特色文化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厦大同仁也将研究视野投向台湾原住民族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其成果有综合性的,也有专论性的。综合性的以陈国强、林嘉煌的《高山族文化》为代表。该书主要借鉴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从经济生活、纺织技术与衣饰、住所与交通、社会与家庭、生活与用具、婚姻与丧葬、宗教信仰、原始艺术、歌舞、民间文学等方面,比较全面地介绍台湾原住民族的社会与生活。书中并收录了收藏于厦大人类博物馆和复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的许多台湾原住民族文物的资料照片[40]。专论性的如陈国强的《高山族艋舺与雅美人渔船》[41]《台湾高山族的纺织技术》[42];郭志超的《高山族雅美人的渔业文化》[43];石奕龙的《别具一格的高山族传统体育活动——刺球》[44]《风情万种的高山族飞天之戏——荡秋千》[45];金汤、建辉的《高山族蛇崇拜习俗》[46]等,既有物质文化,也有精神文化。
也有少数学者独辟蹊径,以史料或博物馆藏品为线索,探讨台湾原住民族的古代传统文化。如陈国强考证陈第的《东番记》,总结其中所反映的明代晚期台湾原住民族生活与文化10个方面的内容[47];李祖基结合对厦大人类博物馆的泰雅族“贝珠衣”藏品的考察,对战国地理古籍《禹贡》所谓“卉服”“织贝”做出解释,认为“卉服”就是史前社会的人们用草藤、树叶编织的衣服,“织贝”就是用贝壳制成织物[48]。这是台湾原住民族先民的衣饰文化,由此亦可证“岛夷”之“岛”即台湾。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岸人民的交往日益增多,大陆各界希望对台湾原住民族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陈国强作为“1949年以后大陆首批访问台湾的社会科学家代表团成员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台湾调查高山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第一位大陆学者”[49],与友人合作,撰写了《台湾少数民族》[50]《高山族风情录》[51]《高山族民俗》[52]《台湾原住民的姓名》[53]等一系列兼具学术性、通俗性与科普性的著作,全面介绍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生活。其中,《台湾原住民的姓名》不仅是与两位台湾同胞合作完成的成果,而且首次使用了“台湾原住民”这一称呼,取代之前惯用的“高山族”。但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该书一直未能正式出版。
总之,在20世纪后半叶,以陈国强教授为首要代表的厦大学者延续了林惠祥开创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传统,而且在诸多方面进一步细化了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使大陆民众对台湾原住民族的社会文化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他们的研究基本体现了中国人类学的“南派”风格,即重视文化史的构建,融合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地受后来的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并与我国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相结合;相对来说不大注重理论,而偏向材料的搜集和解释”*中山大学黄淑娉教授语,参见吴敏:《梁钊韬对近30年中国人类学影响深远》,《南方日报》2013年6月13日。。再者,因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陆学者都不能亲赴台湾原住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调查,所以相关研究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恐无法真实反映台湾原住民族社会文化之面貌。有学者评价说:“林(惠祥)先生所开创的以田野调查与考古学、历史学三者综合运用于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传统,在迄今为止的两岸学人的著述当中依然并不多见,这多多少少地意味着林先生的研究尚难以接续下去。”[3]这一意见令人深思。
三、传承创新:21世纪初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及展望
自20世纪90年代始,有关南岛语族起源问题的讨论成为学术热点。一些境外学者甚至利用南岛语族研究的学术性,着眼于超越学术范畴的政治目标。众所周知,台湾原住民族是南岛语族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居住在最北端的南岛语族。从19世纪末起,中外学者就开始关注南岛语族起源问题,并形成了南来说与大陆说*南来说又可细分为中南半岛说、密克罗尼西亚说和新几内亚说几种;大陆说则有华南说、闽台说和西南说等诸家。两种主要观点。有如所述,林惠祥早年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曾误认台湾原住民族为源自南洋马来族,以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方逐步修正、完善自己的认识。陈国强等第二代厦大学者运用多学科的证据,论证并深化了林惠祥的相关观点。在21世纪初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厦大第三代学者借助新的论证手段如语言分类学、分子人类学等,同其他大陆学者一道,再次加入这场论战,从而形成对某些境外学者的“隔空喊话”。
郭志超直陈南岛语族东南亚起源论的学术缺陷,提出台湾原住民族与南岛语族大陆起源的考古学新证据[54]。吴春明分析南岛语族研究中存在的4个误区,*参见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南岛语族”起源研究述评》,《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指出陈国强等学者主张的“闽台说”忽视了东南土著文化的统一性[55],主张南岛语族起源的“一体说”,即认为南岛语族与上古百越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换言之,二者间不存在谁起源于谁的问题。董建辉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谨慎支持南岛语族起源的“闽台说”,指出“一体说”过于关注共性,忽视了南岛语族内部的差异性,“既回避了南岛语族的起源和迁徙等重要问题,无助于研究的深入和相关问题的解决,也无法对南岛语族内部诸支系之间历史上和现实存在着的文化差异做出合理的解释”[56]。
这场有关南岛语族起源的论争,说到底,其核心和实质其实就是台湾原住民族的起源问题。相较于林惠祥先生开创包括厦大在内的大陆台湾原住民族研究时的“核心和重点”,也即“台湾原住民的族源和历史”*陈建樾教授提出:“台湾原住民的族源和历史是林惠祥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参见陈建樾:《林惠祥与中国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厦大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当然,新的亮点也还是有的。例如,张先清结合新的史料,论述了17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在台湾殖民时的传教活动与原住民族社会互动的复杂性[57]。几位年轻的博士追随受业导师的学术之路,完成了他们有关台湾原住民族的博士论文,*周典恩:《清代台湾拓垦中的族群关系研究》,厦门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李凌霞:《帝国边陲与熟番地权——以北台湾苗栗地区后垄社群为中心(1684~1895)》,厦门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罗春寒:《清代台湾民族政策研究》,厦门大学2007年博士后论文。这意味着厦大的台湾原住民族研究薪火相传,并或将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学术种子播撒得更远、更广。
反观外围的学术环境,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日本学者的系统考察,20世纪50年代后台湾本土学者的深入调研,积累了一批极富价值的台湾原住民民族志资料。近年来更有一些热心学者和机构,将17世纪西班牙、荷兰殖民台湾时期所形成的大量外文资料,以及18、19世纪欧美商人、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地政府官员、船员等撰写的日志、游记、报告、见闻等,迻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这些珍贵资料涵盖了近500年来台湾原住民族的社会生活及其与外来者之间的多层面互动,是厦大同仁拓展台湾原住民族研究的宝贵财富。再者,台海两岸当下往来频繁,每日往返航班逾百,学术交流与合作日密,这为大陆学者重返台湾原住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调研提供了极大便利。面临诸多“利好”,有着深厚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传统的厦大人类学科该如何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进而形成自己鲜明的研究特色,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我们认为,首先,在研究的主题上,应在深化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例如,台湾原住民族的社会适应与文化变迁研究。近代以来,台湾经历了多个政权统治,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在外来文化的强势介入及影响下,台湾原住民族不得不做出主动或被动的适应,社会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其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生计方式等都与传统发生了巨大位移。以人类学的视野全面考察台湾原住民族的社会适应和文化变迁,总结其不同时期的策略及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台湾原住民族的社会处境,把握其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台湾方面的相关研究可参见许木柱:《阿美族的社会文化变迁与青少年适应》,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乙种第17号,1987年;《文化、个人与适应》,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1991年。再如,台湾当局的民族政策及其对台湾原住民族的影响研究。台湾原住民族社会变化之剧烈,当以20世纪50年代后为最。其中,台湾当局的民族政策为最大影响因素。大陆学者已开展了相关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建樾、郝时远等,*参见陈建樾:《从“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评述》,《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走向民粹化的族群政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原住民运动与原住民政策研究》,《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郝时远:《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但似乎还远不足。立足于实地考察,以台湾原住民族为“主位”立场的考察尤其稀少。又如,台湾原住民族与大陆少数民族的比较研究。语言学的证据表明,壮侗语族与南岛语族关系密切,均源自古越民族。*参见邓晓华:《从语言推论壮侗语族与南岛语系的史前文化关系》,《语言研究》1992年第1期;倪大白:《中国的壮侗语与南岛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南岛语与百越诸语的关系》,《民族语文》1994年第3期。大陆属于壮侗语族的民族包括壮族、傣族、侗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等民族,他们的文化底层应有不少成分与台湾原住民族相似或相近。其中,海南岛黎族的生存环境与台湾原住民族类似,更有诸多文化因素趋同。开展台湾原住民族与大陆少数民族的比较研究,辅之以语言学的相关证据,无疑可深化业界对台湾原住民族起源及其与大陆关系的科学认识。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田野调查为台湾原住民族研究之本。现在两岸交通便利,政治氛围尚可,人员、经费也基本无虞,加之台湾原住民族淳朴热情,友善好客,很适宜开展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田野调查作业。在研究过程中,可因循但不拘泥于“南派”人类学传统。具体而言,民族学、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仍可运用,但语言学、分子人类学等其他多学科的手段等也可作为辅助。另一方面,“北派”人类学重视理论提升与建构的传统也需要借鉴。20世纪后半期西方人类学各分支学科如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等等发展迅速,并派生出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均足资为我们所运用,并在个案考察的基础上予以深化或修正。
再次,在研究手段上,交流与合作是一个大的趋势。与自然科学相较,人文社会科学不太注重合作。人类学领域似乎更是如此,总以为田野调查是个人的事,后现代民族志尤其强调个人的主观体验与阐释、理解。这种看法未必全对。就台湾原住民族研究而言,日本学者、台湾学者都有深度实地调研的传统,并且形成了台湾原住民族各大族群的经典民族志。大陆学者不仅应该向他们学习、取经,更应该谋求与他们进行合作。台湾学者有丰富的调查经验,广泛的人脉资源,更有近水楼台的地理之便。两岸学者联手合作,以更为理论、宏观和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台湾原住民族的社会文化,当可以催生出更高水准的研究成果。
[1] 林惠祥.自传·二十五年之秘密[M]//蒋炳钊,吴春明.林惠祥文集(上).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2]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J].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第三号,1930.
[3] 陈建樾.林惠祥与中国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J].民族研究.2011(4).
[4] 郭志超.开辟荆榛.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M]//汪毅夫,郭志超.纪念林惠祥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5] 李亦园.林惠祥的人类学贡献:怀念乡前辈林教授逝世四十周年[J].东南学术,1998(5).
[6] 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M]//蒋炳钊.天风海涛室遗稿.厦门:鹭江出版社,2001.
[7] 林惠祥.福建民族之由来[M]//蒋炳钊,吴春明.林惠祥文集(中).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8] 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M]//林惠祥,蒋炳钊.天风海涛室遗稿.厦门:鹭江出版社,2001:215-216.
[9] 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1958(1).
[10] 高山族简史简志编写组.高山族简史简志[M].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
[11] 高山族简史编写组.高山族简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12] 陈国强.我国东南古代越族的来源与迁移[J].民族研究,1980(6).
[13] 陈国强.闽台旧石器时代古人类与文化[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4).
[14] 郭志超.高山族来源管探[J].华侨大学学报,1988(1).
[15] 辛土城.台湾海峡两岸的古闽越族[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16] 邓晓华.从语言推论壮侗语族与南岛语系的史前文化关系[J].语言研究,1992(1).
[17] 陈国强.高山族名称沿革考[J].厦门大学学报,1963(4).
[18] 陈国强.台湾少数民族的形成与名称[J].民族研究,1996(3).
[19] 陈碧笙.论台湾土著居民并非一族且不能称为“高山族”[J].台湾研究动态,1981.
[20] 郑启五.关于“高山族”的族称[J].台湾研究集刊,2000(4).
[21] 王嵩山.台湾原住民的社会与文化[M].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22] 陈国强.台湾高山族的原始宗教[M]//台湾高山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8.
[23] 陈在正.台湾中部平埔族的汉化与妈祖信仰[J].台湾研究集刊,1990(2),(3).
[24] 陈国强.高山族神话传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25] 陈国强.高山族民间文学.民间文学[J].1979(5).
[26] 陈国强.台湾高山族原始农业的起源和发展[J].农业考古,1981(2).
[27] 陈国强.台湾原住民族的人口、语言和宗教[J].台湾研究集刊,1983(2).
[28] 陈国强.从两篇史料看台湾古代社会经济[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2).
[29] 陈碧笙.17世纪中叶台湾平埔族社会经济及其与汉族关系初探[J].社会科学战线,1981(3).
[30] 陈国强.清代以前台湾高山族与汉族古代的友好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1982(3).
[31] 陈国强.高山族支持郑成功收复台湾[M]//台湾高山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8.
[32] 陈碧笙.17世纪中叶台湾平埔族社会经济及其与汉族关系初探[J].社会科学战线,1981(3).
[33] 陈碧笙.清代汉族与平埔族之间的矛盾与融合[J].台湾研究集刊,1985(4).
[34] 陈国强.台湾噶玛兰的开发与姚莹的贡献[M]//台湾高山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8.
[35] 陈国强.刘铭传与高山族[M]//台湾高山族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8.
[36] 陈国强,林加煌.蓝鼎元治理台湾高山族的贡献[J].云南社会科学,1994(5).
[37] 孔立.台湾番族与林爽文起义——兼论清政府对番族的政策[J].福建论坛,1985(2).
[38] 郭志超.清代汉族影响下的高山族农业技术之变革[J].台湾研究集刊,1985(1).
[39] 郭志超.清代汉族与高山族的贸易关系[M]//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40] 陈国强,林嘉煌.高山族文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41] 陈国强.高山族艋舺与雅美人渔船[J].民族文化,1982(3).
[42] 陈国强.台湾高山族的纺织技术[J].民族学报,1983(3).
[43] 郭志超.高山族雅美人的渔业文化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44] 石奕龙.别具一格的高山族传统体育活动——刺球[J].台声,1999(9).
[45] 石奕龙.风情万种的高山族飞天之戏——荡秋千[J].台声,1999(11).
[46] 金汤,建辉.高山族蛇崇拜习俗[J].福建民族,1998(4).
[47] 陈国强.陈第与台湾高山族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1992(2).
[48] 李祖基.《禹贡》岛夷“卉服”、“织贝”新解[N].光明日报(理论版),2000-06-30.
[49] 查本恩,韩思斯.田野调查魂归田野——民族学家陈国强教授逝世[N].厦门晚报,2004-08-04.
[50] 陈国强,田珏.台湾少数民族[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51] 陈国强.高山族风情录[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52] 田富达,陈国强.高山族民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53] 陈国强,林瑶棋,陈炎正.台湾原住民的姓名[M].中国人类学学会,1999.
[54] 郭志超,吴春明.台湾原住民“南来论”辨析[J].厦门大学学报,2002(2).
[55] 吴春明,陈文.“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闽台说”商榷[J].民族研究,2003(4).
[56] 董建辉,陈支平.南岛语族起源研究的文化、学术与政治倾向[J].人文国际,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57] 张先清.传教、冲突与文化解释——17世纪台湾原住民与传教士的相遇[J].学术月刊,2013(12).
责任编辑:刘伦文
2016-12-30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4ZDB113)。
董建辉(1966- ),江西流坑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三峡大学“楚天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东南民族史;黄铭松(1970- ),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
C912.4
A
1004-941(2017)01-00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