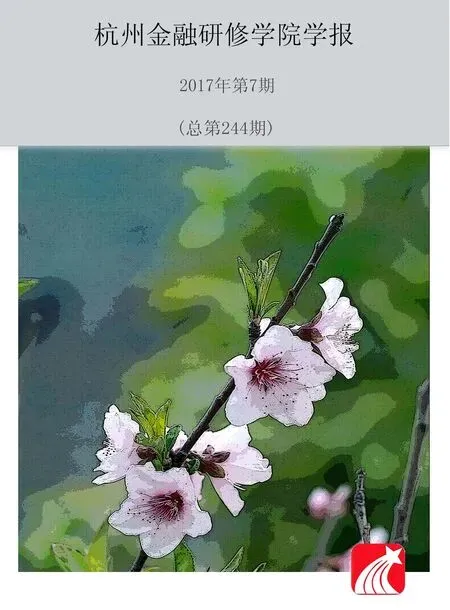悠悠岁月 悠悠戏曲
薛谷香
悠悠岁月 悠悠戏曲
薛谷香
一
母亲对戏曲的热爱可以追溯到她的年少时代。
据我外公、外婆和舅舅说,她小时候书读不好,对越剧和沪剧却天生着迷,还偷偷地把外公、外婆给她缴学费的钱拿去学越剧。外公、外婆出于“为她好”的动机强行带她回家,为她再缴更昂贵的学费,让她转学去更好的学校读书,如此折腾了几次,由于外公、外婆太强势,母亲反抗无果,只能放弃学戏。但是书还是读不好,母亲勉强读到中等师范学校毕业。自我有记忆以来,母亲对外公、外婆一直有颇多微词,核心就是:“都怪他们不让我学戏,否则我的命没有那么苦。”而她的哥哥,即我的舅舅读书却很好,一口气读完医科大学,终身当医生。
母亲天生丽质,年轻时候的照片酷似电影演员王晓棠,清晰的双眼皮,迷人的大眼睛,说话唱戏时眼睛很亮,笑起来眼角上挑,即便后来有了鱼尾纹,笑起来还是很好看。母亲不光喜爱越剧,也喜爱沪剧,连歌也唱得很好。从形象到嗓音方面,我和姐姐都远不及母亲。
母亲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很短,没有过七年之痒以离婚结束,因而我们有一位同母异父的大哥,名义上被过继给了舅舅、舅妈,实际上是在外公、外婆的抚养下长大。尽管母亲对他没有尽过养育之责,但他和我们一样对母亲很有孝心。
母亲第二次婚姻也不算长,我父亲离世时母亲才46周岁。这段婚姻有了姐姐和我。
每当外公、外婆觉得母亲的生活境遇不如舅舅时就会说:“都是因为你书读得不好,否则你的命不会那么苦。”
而实际上,假如外公、外婆让母亲按自己的意愿去唱戏的话,没准可以成为一代名伶,据说和母亲同期学越剧的就有两位是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年轻时母亲的容貌和扮相都绝对不逊于她们。
然而历史没有假如。
二
记事以来父亲、母亲吵得最凶的事情发生在文革“扫四旧”前夕。父亲把母亲收藏的所有剧本、画报悉数撕毁烧掉,母亲发疯一样地和父亲争吵,并以火中取栗的勇敢从中抢救出一本被父亲撕成两半的剧本,叫《阿必大回娘家》,是早期的沪剧剧本。母亲居然用针线把这个剧本一页一页地缝好,并不顾父亲的意愿,把这本有“封资修”之嫌的剧本珍藏起来。其实后来得悉这个戏说的是穷人的故事,至少是有批判封建主义的立场。
即便是“文革”,即便家里遭抄家,即便父亲挨批斗,母亲自己被拉上去陪斗,即便在父亲被关牛棚的日子,母亲都偷偷保存着这个剧本。
即便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母亲还是会偷偷地唱几句戏,念上几句戏曲中的对白。
比如:“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我合不拢笑口把喜讯接,数遍指头把佳期等。”这是越剧《红楼梦》,彼时唱词内容与母亲和我们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比梦还要远。我们唯一盼望的是被划成“地主”的父亲有一天可以平反。
比如:“我真傻呀我真笨,我又是懊恼又是恨,我拿了一小篮一只碗,叫阿毛一面剥豆一面看门……”这是越剧《祥林嫂》,唱词乃至母亲的眼光中有无比的凄苦与自责。其实那样一段岁月,远不是母亲用自责便可以改变的。
还比如:“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只要河流水不断,跟着流水走天下。”这是电影《舞台姐妹》中越剧唱腔的插曲。
日子无比艰难,幸而母亲可以偷偷唱戏。
三
后来父亲平反了。
各类戏曲也终于从被打上“封资修”烙印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母亲可以边听收音机边大声哼唱各种曲目了。
当邻居家的年轻人情窦初开,以《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十八相送”唱段相互暗送秋波的时候,母亲以地道的范派和袁派唱腔为大家尽情地演唱了“草桥结拜”“十八相送”“回十八”和“楼台会”等经典唱段,得到邻居们的盛赞。后来电影《红楼梦》重新上映,更是引发了邻里的越剧热,母亲变得神采飞扬,从唱功到身段,和人家讲得眉飞色舞,什么徐玉兰的徐派,王文娟的王派,什么演琪官的曹银娣,就是电影《舞台姐妹》里演邢月红的,她属于陆派,是陆锦花的大弟子。然后怎么抬腿,怎么走碎步,怎么甩水袖,眼神要怎么运用,看她津津乐道,看她眉飞色舞……
然而母亲的戏曲天分和爱好却较少感染姐姐和我,我们的爱好都在别处。
父亲后来得了肺癌,一年以后医治无效离开了我们。
尚是人到中年的母亲依旧形象可人,说媒的人开始神神秘秘地出现于我家,于是姐姐和我开诚布公地和母亲谈了我们的意愿:只要母亲乐意,她怎么选择我们都支持。母亲表示不愿意再改嫁了。
后来的日子里,母亲和我说:“你说封建迷信是不是很害人?一定要骗祥林嫂说,嫁了两个男人的人死了以后要被阎王爷锯开分给她两个死鬼男人?”
听后心有戚戚,我连忙说:“是啊是啊!哪有什么阎王?再说祥林嫂那么可怜,一生靠劳动吃饭。嫁两次男人怎么啦?鲁迅先生如果把故事写下去,就算有阎王,他也应该惩罚那些作恶的人,比如绑架她、逼她改嫁的人贩子婆婆。”
四
戏曲于母亲的意义,或不失为精神鸦片,是除了子孙以外填补她精神和情感寂寞的安慰和寄托。
“官人啊,官人好比天上月,为妻好比月边星,月若明来星也亮,月若暗来星也昏。”这是越剧《盘夫索夫》唱词。“春香!你变那长安钟楼万寿钟,我变锤儿来打钟。打一更,当当叮;打二更,叮叮当。人家只当是打更钟,谁知道你我钟楼两相逢。”这是越剧《春香传》唱词。母亲说:“戏曲里的爱情总是那么甜蜜。真好。”
就算第一万遍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红楼梦》,母亲照样会先笑后哭,被剧中人物的悲剧故事感动。
当然,在看戏方面母亲也会与时俱进,看一些新人新戏,比如沪剧《甲午海战》:“一世颠簸在那浪淘中,披霜带露餐风雪,到头来惨死在日寇手,深仇大恨犹在胸……”我便会为其补充相关的甲午战争的背景知识,企图让她的视野可以有所拓宽。但母亲按自己的方式接受:“噢,原来是这样!邓大人是好人,李中堂是坏人!”呵呵,我好无奈。
比如沪剧《璇子》:“金丝鸟在那里鸣叫歌唱,一声声似对我述说哀伤,想当初栖山林迎风戏雨,蓝天下沐骄阳自由翱翔,叹如今望长空枉生双翅,终日里困樊笼寂寞惆怅。”类似讲明星的故事倒不费我解释,母亲自己会有贴切的理解。
而且母亲对比她年轻一代的越剧沪剧演员,哪个人师承哪派搞得清清楚楚,有问必答,不光给你解释,还给你唱上一段,张口就来。
母亲有时候入戏太深,常常以戏为坐标定义自身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中年以后的她稍有些剑走偏锋了。
比如:“像这样的好书,老爷却不许我读,今天背地里,我偏要读它一个爽快啊,读遍书斋经与史,难得西厢绝妙词……”母亲会以《红楼梦》中“读西厢”的唱词作发挥:“他们不让我唱戏,不让我看戏文,其实就和这个老爷一样,很坏。”
比如:“翻上高山把路赶,眼前已是山河湾,气急心跳头发昏,天摇地动山要坍……秋宝,秋宝,我听得秋宝还在哭,还在哭,哭破喉咙把亲娘喊,你是娘的心头肉……春宝,春宝,姆妈晓得你有病,日日夜夜心事担,求神拜佛保佑你呀,但愿你平平安安在家里,想必你越长越聪明,皮老虎姆妈替你带回来”,这是沪剧《为奴隶的母亲》唱词“回家路上”。原著是左翼作家柔石,讲的是春宝娘为了谋生替地主家作“典妻”,待生下儿子秋宝后被迫与秋宝分开,在回家的路上,一边想秋宝,一边想春宝,还用省下的钱给春宝买了一个皮老虎玩具。母亲会突然对我们说:“其实我没有对你们大哥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很对不起他;又在心里很偏心你大哥,对不起你们姐妹。”
其实姐姐和我早已明事理,会尽力劝导母亲:“大哥在外婆家,条件比我家好多了,所有人都对他那么好,你有什么不安心呢?”“你就尽量在心里偏心大哥就是了,我们才不会吃醋呢。”
随着年事渐高,母亲的身体渐渐走下坡路了。她得了帕金森综合症和睡眠障碍,一直靠药物维持。开始对生活有各种戏剧性妄念,总设想她的生活永远不可能风平浪静,总有“风刀霜剑严相逼”,总有反派角色存在,而这些反派角色的任务就是迫害她。一开始她和姐姐、姐夫生活在一起,她有时妄想姐姐、姐夫是反派角色,就算姐姐、姐夫再顺着她,关系也处不好,但又不妨碍她很爱姐姐的孩子。后来姐姐、姐夫在不远处买了商品房搬出去,也经常去照顾她。母亲又总是抱怨住她楼上的邻居要故意迫害她,晚上会很闹腾,不让她睡,为此姐姐没少和楼上人家打招呼,让他们尽量轻一点。
在她尚能出行的那些年,她也每年来杭州住上一阵子。我家是顶楼的跃层公寓,也没有楼上人家吵闹一说。可母亲也总是能编排出反派角色,一开始是把矛头指向来我家的朋友,尤其是朋友中的男士,别人来的时候她挺客气,在别人走后她会大开门窗,并沿途擦地擦桌子,她要把别人的气味连同接触过的痕迹统统消灭掉,并委婉地和我说:“你以后最好不要叫他们到我们家里来,尤其是不要叫男人来我家。”当我不再请朋友来我家之后,母亲会渐渐把矛头指向我先生,横竖看不顺眼他。然而,她也十分疼爱我儿子,但总是待不到两个月就要回上海了。
后来我们分析,母亲与他人相处不好,总有受迫害妄念,其实一方面与她的戏剧情结有关,另一方面与我们家庭在“文革”那段真实的受迫害经历有关。我们都走出来了,而她没有,有时候她会在噩梦中叫:“不要,不要烧我的剧本。不要拉我去陪斗,我不是地主婆。”于历史而言,一场运动只是它的一段记录,于母亲而言,是大半生的阴影。
而母亲对待男人类似于洁癖性质的排斥,实际上属于一种从伦理到心理再到生理的矫枉过正,或与她过早开始寡居有关。幸而母亲对和她有血缘关系的男性不仅不排斥,而且疼爱有加,除了暗自“偏心”我们大哥以外,对孙子外孙一口一个:“心肝肉,宝贝肉。”“手心手背都是肉,老太婆舍不得那两块肉。”
其实这也是越剧唱词。
五
近年来母亲已有越来越明显的阿尔茨海默症。
周遭的人和事情以及时间顺序意味着什么,她已经渐渐弄不明白了,也渐渐不能自理生活了。后来母亲骨折两次,导致完全失去自理能力。第二次骨折康复阶段恰逢去年春节阶段,连保姆都请不到。我和姐姐只能全力以赴、不分昼夜地照顾她,无奈半辈子缺乏体力劳动锻炼的我们,面对失智又失能的母亲,根本算不上是合格的护工,硬撑一周之后我便发高烧了,自责也没用。
于是我们唯有为其选择了医养结合的护理院。
每一次去护理院看母亲,都会令我想起米兰·昆德拉说的话:“面对生命那无可挽回的溃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理解它。”看看护理院的老人们,就会知道,岁月对人生命的侵蚀是如此残忍、如此不堪。看着母亲的生命力一天一天像快要燃尽的蜡烛一样越来越黯淡,头脑一天比一天混乱,足以令我绝望;而这样的现状或预示着我自己身上的基因在未来的类似表现,也足以令我绝望,“理解它”的目的在于平和地接受它,并且不那么绝望地走下去。
母亲不再记得除了我大哥、我姐姐和我以外的人了。连她最心爱的孙子、外孙叫什么名字都不记得了,也搞不清楚所有的亲人和她是什么关系,甚至有一次管我姐姐叫“姆妈”。大家去看她,首先得问她:“您说说我是谁?叫什么名字?”她会羞怯地说:“不好意思,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好在我每次去,她都十分高兴:“谷香,你怎么有空来了?”可能于她而言,我姐姐去看她属于常态,就和空气一样习惯,而我去看她属于福利,是额外的欢喜。我很惭愧。
她会兴奋地说:“我要请你去饭店吃饭。”而实际上她连下地走路都不会了。
她会告诉我最近的“经历”:“我昨天才去看了你的外公、外婆和舅舅。他们对我可好了,一点也不反对我去学唱戏了。”而实际上,他们三个早已作古。
她有时会问我们:“那我第一个男人到哪里去了呢?他为什么不来看我?”我们又怎么知道?
有时候又会说:“我怎么会把所有事情都搞糟了呢?我脑子坏掉了吗?是不是所有人都在为我吃苦,都在责怪我?”我们尽量安慰她:“年纪大了脑子糊涂点没有关系的。没有人为你吃苦,所有的人都爱你。”
前几天我从杭州赶去看她,在喂好她吃中饭,待她午睡之后,发现护理院的房间里可以用WiFi,便用手机搜索了1959年由著名沪剧演员大汇串的音配像《雷雨》全剧给她看。原来我的意图只在打发半天时间,没想到母亲和变了一个人似的!
她的思路居然可以如此清晰:“这是以前的演员唱的,而表演是另外一些演员。蘩漪是丁是娥唱的,表演的是马丽丽;周朴园是解洪元唱的,表演的是汪华忠;周萍是王盘声唱的;四凤是杨飞飞唱的。”
“这段叫‘盘凤’,是蘩漪和四凤的戏,她们的唱词说的是她们都爱着周萍,都和周萍有故事。只不过蘩漪清楚四凤的,而四凤不知道蘩漪。这段叫‘求萍’是蘩漪和周萍的戏,因为周萍已经和四凤好了,但蘩漪不甘心。”
“你听你听,我先不跟你说了。”接着母亲居然一字不差地跟上了蘩漪:“体面,侬也讲体面?吶周家门庭好体面,我十八年来看得多,罪罪恶恶我都清楚,我自身做事自身当,自己会把责任负……是你,是你大少爷来引诱了我……”
蘩漪在手机里的丁是娥、马丽丽,以及手机外床榻上的母亲的共同演绎下呼之欲出,我为之陶醉,居然也忘情地进入剧情和唱腔——
四凤(由手机里的杨飞飞、卢燕萍和床榻上的母亲共同演绎):“独坐孤灯呆思忖,心如乱麻难安宁。娘亲要我罚过咒,罚过咒,难道我真的就不见周家的人。心里的苦楚向谁诉,难以启齿告母亲。娘啊娘,你哪知女儿肚中情,孩儿是犯下了弥天的罪啊,枉费娘亲爱女心……”
唱得母亲已泣不成声。随后她含泪和我说:“啊,杨飞飞唱得太好了。这才是艺术家!这才是好戏!我发现我真的老了,好几句我都唱不上去了。”
我脱口而出:“不,您唱得真好。我为您骄傲。”
- 杭州金融研修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从严治党与从严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