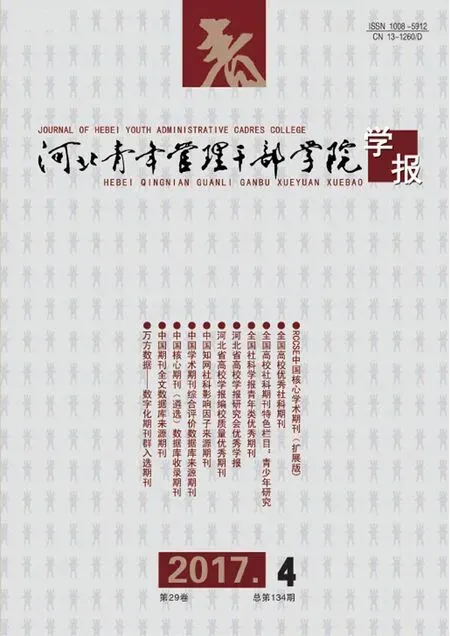佐哈尔:为翻译文学正名
李天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佐哈尔:为翻译文学正名
李天杨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把翻译研究从语言学领域带入文化领域,他认为,翻译不再是本质和界线一成不变的现象,而是一种与特定文化系统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活动。他的多元系统论对翻译学影响巨大,其价值在于拓展了翻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为翻译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思路。
佐哈尔; 文学多元系统; 翻译文学系统; 翻译策略
引言
虽然“文化转向”这个词是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教授苏姗·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首先提出来的,但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mar Even-Zohar)是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视角带入文化的奠基人,描写派主力[1]。佐哈尔对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进行了多年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论——多元系统化。他提出的多元系统化,不仅对翻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文学也具有很大影响。以“佐哈尔”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按照“被引”排列检索结果可以发现,我国许多著名翻译研究者都对佐哈尔及其理论进行过研究并发表过相关论文;而按照“发表时间”排列检索结果可以发现,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翻译研究者使用多元系统理论进行翻译研究,还有很多学者对该理论本身进行研究。佐哈尔和他的多元系统理论也是一代代翻译新人初入翻译研究领域时绝不会错过的。本文将对多元系统理论进行阐述,以期对“该理论为何经久不衰”这个问题作出一些回答。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认为,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缘起于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区别。文学翻译即忠实于原创的全翻译,而翻译文学是指采取适应本国文化背景的翻译策略、语言特点所产出的翻译作品。佐哈尔将翻译文学称为向创作靠拢的“半翻译”和“准翻译”(semi- and quasi-translations)。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区别就在于对该社会、文化等产生的影响。翻译文学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要远大于文学翻译。所以,佐哈尔不同意形式主义者传统的美学标准,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2]。他认为儿童文学、恐怖文学以及翻译文学等文学形式不是边缘化的,而是具有文学造诣、社会作用和研究价值的。佐哈尔在他的《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中第一次提出“多元系统”这个概念,他分别在1979年、1990年和1997年发表三篇文章对多元系统理论进行论述。本文是对其1979年文章的翻译和阐述,该文现收录在Venuti教授的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中,篇名为《翻译文学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二、基本概念
在翻译和阐述之前,笔者认为有几个基本概念是读者需要知道的。第一,什么是多元系统?佐哈尔概括为:社会符号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多元系统,也就是由若干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有些子系统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而有些则处于边缘位置。第二,文学多元系统内部是怎样的?佐哈尔把他的研究定位在文学多元系统,文学多元系统简单举例来看是这样的:第一层按地区国别来分类,我们有亚洲的中国;第二层按文学类型来分类,我们有中国的诗、成人文学、儿童文学、恐怖文学,等等;第三层按是否翻译来分类,我们有翻译的儿童文学和原创的非翻译的儿童文学;第四层按译自哪国来分类,我们有分别译自法国、美国、俄罗斯、拉美国家或者其他国家的儿童文学。第三,什么是形式库?形式库(repertoire)是支配文本制作的规律和元素(可能是单个的元素或者整体的模式)的集成体[3]。佐哈尔认为,任何系统产品的制造和使用方式都由形式库控制[3]。探讨文学和翻译,“形式库”是读者必须知道的概念。
三、主要观点
以下是笔者对原文进行的翻译和阐述,原文分五部分,以数字分隔,均没有标题,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各部分主要内容进行了概括,并加上了标题。
(一)关于翻译文学系统的存在和建立
作者首先指出,通过对各种史料的研究,史学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翻译对一个国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塑造民族文化以至世界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比如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但很少有学者谈及这个问题。也很少有学者谈及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具体作用和地位。因此,作者在这里设问,翻译文学的背后是不是也存在着像原创文学中一样的文化和语言关系的网络进而能够形成系统呢?作者指出,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即选择方面和借用方面。第一方面即选择方面,笔者在这里用杨宪益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不幸的是,我俩(还有其夫人戴乃迭)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作品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2]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在杨先生所描述的那个年代,被选中的翻译文学都带有极强的与文化和语言有关的共同点,比如都受当时的政治气候影响,因目的语(我们将有关的环境如杨先生所处的时代,人如杨先生描述的编辑等因素在这里通称为目的语)的选择,这些共同点使各个独立的翻译文学作品形成文化和语言的网络,进而形成系统。第二方面即借用方面,笔者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清末民初我国现代小说形式库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翻译,对当时的语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当时青年、学者的思想观念、理论、行为甚至产生了颠覆性的作用,这些影响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这些影响具有共同的特点,那么从影响这个角度来看,翻译文学系统也应该是存在。这两点共同告诉我们,翻译文学系统也是存在的,是有其文化和语言关系网络的。证明了翻译文学系统的存在,那这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怎样的?是中心的还是边缘的?是创新突破的还是保守陈旧的?是基本的还是次要的?在这里,作者用了一个比喻来引导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而是说无数个多元系统就好比星群(constellation),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由翻译文学系统与这个星群的关系决定的。
(二)关于翻译文学系统的位置和发展演进
作者首先讨论了翻译文学系统处在中心位置时的几个问题。为系统走向中心位置出力的翻译家,作者称他们为先锋,笔者认为处在中心位置的系统便可以称为先锋。这个位置是与文学史上的情况(由诸多事件组成)相融合的,这些事件决定了翻译文学系统的能力和前景。作者说,在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系统将处在中心位置。其一,文学系统尚未形成还很年轻(when a polysystem has not yet been crystallized, that is to say, when a literature is “young”,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established),中国清末民初时的翻译文学便是一个较好的例证。当时,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细嫩”状态,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出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则连影子都没有,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翻译小说占当时出版发表的小说的五分之四[2],翻译文学丰富了我国现代小说、白话诗、话剧等文学形式的形式库。其二,某个文学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处在边缘或虚弱状态(when a literature is either “peripheral” (within a large group of correlated literatures) or “weak” or both),“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翻译文学是一个较好的例证。由于特定历史、政治、文化条件的制约,原本资源非常丰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周边国家(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的文学资源的中国文学,此时却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而苏联(高尔基的《母亲》)、越南、朝鲜、 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连同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 在当时都被翻译引进国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其三,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期的出现(when there are turning points, crises, or literary vacuums in a literature),“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可以较好地印证这一点。这些情况下的翻译和原创很接近[2],创作的成分很少。
在这一部分,作者还特别强调了三点:其一,“虚弱”的文学系统带来创新的能力定不如那些强大的或处于中心的文学系统,在“文革”时期,译自越南社会主义文学的翻译文学,我们当然要肯定它们的作用,但是这个本来就较为弱小的系统带来的创新及影响力,不如译自处在中心位置的苏联文学的翻译文学带来的影响力。其二,有些文学多元系统的等级在其形成伊始便已较为坚固,比如在欧洲文学中出现了以上三种情况的一种或多种时,其受到的影响就可能不会像中国文学那么大。其三,翻译文学带来了原创文学形式库的创新,也使得原创文学系统内部获得重新洗牌的机会以及许多其他的新的可能。
当翻译文学系统处在边缘位置时,就是一种保守的情况,此时在进行文学翻译时,绝大多数情况都要求(有时甚至是必须)使用目的语原有的词汇和表达(当然这些原有的原创的词汇表达本身也在发展),与目的语稍有偏差,即被视为罪过[3]。在这种情况下便形成了一个关乎翻译本身的引入和保守的矛盾,那就是:进行翻译,一个很大作用就在于引入新的表达、新的思想,而处在边缘位置的翻译文学系统只能保守旧有的表达和思想,这当然不利于翻译文学系统走向中心去。
讨论了两种位置问题,作者简要提及了两点有关系统发展的问题。作者说,随着系统的不断发展,曾经在中心位置的系统也会保守起来,以此来保护这个系统所带来的形式库,如严复的理论原是个一级模式 但走进中心之后,固定下来,就变成了二级模式,形成了新的保守主义,阻碍了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4]。还有一种情况是,处在次级的系统甚至会压制更次级的系统。
(三)关于翻译文学系统的分层和正名
作者认为,翻译文学系统内部也是分层的,他以二战时期的希伯来文学为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说明。相较英、德、波等语言的翻译文学,苏联翻译文学在当时的希伯来文学中占据着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希伯来文学形式库所引入的最具创新精神的词汇和表达皆从俄语翻译文学而来,其他引入词汇和表达都是英、德、波等次级语言翻译文学通力合作的结果,它们的影响力远不及苏联翻译文学。
讨论到这里,笔者认为,为翻译文学正名的问题就正式出现了〔作者并没有在原文中表达正名的意思,该正名是笔者通过原文(以下原文笔者未做改动)对作者意图的猜想〕。作者说目前的研究还不能确保翻译文学有特别的地位,或者说中心地位,翻译文学还是边缘的,尤其是考虑到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学多元系统的特点,比如法国文学多元系统内部就是十分坚固的,翻译文学很难有所作为,而法国文学对整个欧洲文学影响十分深远,但随着翻译文学系统自己的发展以及各种新情况的发生,处在边缘地位的翻译文学系统就有发展到中心地位的可能性,就有发挥作用的可能。笔者认为,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要求翻译文学系统时时处在中心,但翻译文学系统处在中心位置的可能性及其相应的影响是我们必须看到的,这大概就是作者想要为翻译文学正的名。
(四)关于在两种不同位置下翻译者的不同翻译策略
在翻译文学系统处在中心位置时,作者认为此时的翻译模式是一级创造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去引入新的词汇和表达形式,打破目的语原有的、固定的词汇和表达形式,这个作用还是产生在目的语形式库中的。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调,在进行引入和打破的创造过程中、在与目的语自身文学系统的竞争过程中,一旦因为翻译文学系统太过于具有原语的特点、太过于革命而失败的话,它将再无东山再起之日。
在翻译文学系统处在边缘位置时,作者认为此时的翻译模式是二级保守模式,翻译者只得套用目的语中原有的、固定的词汇和表达,这种模式下的翻译多是不充分的,只是可接受的。
以上这些策略手段绝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问题,一级创造模式下不是肆意可以打破的,二级保守模式下也不是没有引入和创新,到底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手段还是要看目的语本身文学系统的允许程度、开放程度和官方认可程度。
最后作者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全文:翻译不再是本质和界线一成不变的现象,而是一种和特定文化系统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活动。
四、评价
首先是根茨勒(Gentzler)教授说佐哈尔的多系统理论使翻译研究不再只是孤立的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描述性的翻译研究和文化转向,这也与佐哈尔在第一部分中“星群”的观点相呼应。当然,佐哈尔的观点也有缺点,根茨勒教授总结如下:其一,佐哈尔的理论实际例子太少。其二,关于多元系统理论,大部分都是佐哈尔自己的逻辑,自己的假说。这种理想化的模型缺乏对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各种情况的考虑,尤其是没有考虑各种束缚条件和缺少对译者本身的关照。其三,佐哈尔说多元系统是科学的模型,这个模型真的客观吗[5]192-197?
谢天振教授对佐哈尔多元系统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一,“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2]其二,使人们能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待翻译问题,以把握它的真正本质,可以使人们不再纠缠于原文和译文间的对等问题,而把译本看作是存在于目标系统中的一个实体,来研究它的各种性质。正是这一点后来发展成了 Toury 的“目标侧重翻译理论”(Target- oriented approach)。其三,既然译文并不只是在几种现成的语言学模式里作出选择,而是受多种系统的制约,那么就可以从更广泛的系统间传递的角度来认识翻译现象。”[2]
根茨勒教授和谢天振教授的评价,笔者认为是对其他许多研究者评价的概括和总结,较具有参考意义,限于篇幅,笔者不再转引其他学者的评价。
五、思考
研读原文几遍,且看过一些评论后,笔者自己有两点想法。其一,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的价值是巨大的,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学从语言学研究带入了文化学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翻译学的发展,拓展了翻译家的视角,让很多研究者从更高更广的层次认识翻译学、研究翻译学。或许这也正是“这一理论经久不衰”的原因。作者在上文中论述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单独拿出作为各种不同研究的理论依据,或者对各部分的理论本身进行研究、深挖和发展。这也是本文开头说该理论是经典理论的原因之一。其二,作者关于翻译文学系统的观点是不是可以推广到其他类型的翻译呢?比如科技翻译。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1] 林克难. 翻译研究:从规范走向描写[J]. 中国翻译,2001(6):43-45.
[2] 谢天振. 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 外国语,2003(4):59-66.
[3] [以色列]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 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21-27.
[4] 张南峰. 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J]. 外国语,2001(4):61-69.
[5] [美]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编辑:刘小明
2017-02-16
李天杨(1992—),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硕士研究生,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