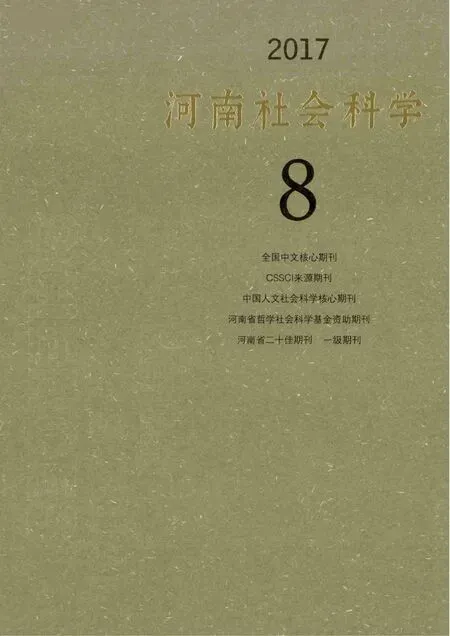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动力研究
唐建兵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动力研究
唐建兵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由于农村社区发展主体动力把握失准而导致功能作用失衡,新型农村社区发展之路显得崎岖艰难。从社区发展的动力来看,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已经从政府“顶层设计”转向注重“基层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动力包括外助力和内驱力两个重要部分。外助力包括政府支持、市场推动、第三部门帮助等,内驱力包括农民致富欲望和社区参与、精英示范带动、社区文化内聚等。正是有效整合了“外助内驱”力,在协调配合中促使各种动力要素有序运行而推动着新型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
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动力;“外助内驱”
当前,我国正处在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时期,“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愈加明显。在此形势下,新型农村社区研究议题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201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方向,使新型农村社区步入发展快车道。但遗憾的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高潮的美好愿景并未如期而至,甚至于“农村社区作为农民生活共同体正陷入信任与认同危机”[1]。如此结果原因何在呢?动力把握失准亦是主要原因。
一、新型农村社区的特点及其发展动力分析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认为,社区即“由共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共同体”[2]。但是,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滕尼斯笔下的“天堂”已是逝而不返。亦如其言,“即使这种原初的共同存在、共同生活以及共同工作的状态已被改变,它依然保留并能更新其精神的形式、政治的形式以及其合作的功能”[2]。
(一)新型农村社区的特点
新型农村社区是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背景下提出的概念,是在政府指导规划下,合并若干较为分散的行政村,或经撤村并镇,或者由一个具备社区要素的行政村建设而成的农村社区。与传统农村行政村相比,新型农村社区呈现出新特点:一是“村委会”成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主体,并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承担更多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二是传统行政村中原有的村民自治组织内涵更加丰富。基层农村社会管理由“村民自治”管理转化为“多元共治”,逐步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基层社会管理格局。三是新型农村社区基本满足了承接农村公共服务功能的现实需要,成为不断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载体。四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城乡分治走向统筹共治、融合发展,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动力分析
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是多主体协同共助、合力助推的结果。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既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亦需要企业、社会组织的帮助和扶持,更需要农民的积极参与。
1.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动力要素分析
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动力可分为外助力和内驱力两部分。外助力包括政府支持、市场推动、第三部门帮助等;内驱力包括农民致富的欲望、社区参与力、精英的示范带动力、社区文化内聚力等。实践经验表明,有效整合“外助力、内驱力”并采取动态的机制运作,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才有可持续的动力源泉。(1)农民参与是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内驱力的动力源泉。农民是生活在社区中的主体力量,他们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支持不支持是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好坏的唯一标准。农村是否建社区,如何发展社区,不仅需要政府规划指导,还应尊重农民意愿,倾听其意见和建议。农民能够在农村社区发展中萌发致富的欲望并主动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才有持续动力。(2)精英示范是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内驱力的动力引擎。农民致富愿望和参与热情是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动力,点燃他们潜在的干劲和热情,让潜在原动力转化为社区发展的内生驱动力,需要社区精英创新示范作用。(3)文化引领是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内驱力的精神动力。优秀的村落文化培养社区农民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淳朴的乡土人情可以唤起共同体意识,吸引外出精英和人才回乡发展,增强农民间的互助与合作精神,最终形成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内在的精神支持和持久的凝聚力。(4)政府支持是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外助力的主导力。福利的功能在于发挥作用产生原有市场所不能自发形成的结果,它通过凌驾于市场之上的操控力,来对部分服务和商品进行分配。政府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支持和资金倾斜是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外助动力。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攻坚期,破解新型农村社区发展难题关键在于政府的支持和推动。(5)企业扶持是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外助力的推动力。产业推动能够实现社区周边运作建设工业园区、农业园区和农业现代化基地,既解决社区农民就业问题,也解决了产业园区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需求问题。(6)第三部门协作是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外助力的协调力。第三部门在农村社区兴起“使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关注社会的伦理和责任,有助于培养高尚的社会人格和道德情操,增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3],有助于弥补政府缺位和市场缺陷。可以说,第三部门的专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在服务提供和行动安排上弥补了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这一缺陷。
2.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动力运行
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动力运行主要是通过社区搭建的互助合作平台,发挥社区的整合凝聚功能,让政府、企业和农民联动运作,发挥各自优势,整合社会资源,让外部助力转化为内在驱力,让内驱力变得更有发展动力,多力汇合共同推动新型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1)发挥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发展中的顶层设计作用。政府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顶层设计者,要做好规划设计。规划设计要做到与当地经济和发展规划衔接好,与农村基层党建发展同步,还要坚持因地制宜,最大限度地回应农民的诉求,保护农民利益不受损失,避免强制性的大拆大建。一是着力提高企业参与农村社区发展的积极性,解决建设资金匮乏、融资渠道单一的问题。优化投资环境,拓宽投资融资渠道,让企业和农民都有生产发展的积极性,确保实现企业能增产、农民能增加收入。二是认真落实有关政策,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重点建设并保障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人居环境改善时既要守住青山绿水,又要留住乡情乡愁。三是鼓励第三部门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在引导村“两委”发挥作用的同时,积极提高农民主动参与性,社会组织要积极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四是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的家风,弘扬公序良俗。发现和培养乡土文化能人、民间文化传承人等各类文化人才,营造健康向上的乡村文明,着力提高农村社区生活品质,进一步凝聚有利于农村社区发展的创新活力和动力。(2)利用市场运作方式发展村办企业。从我国农村经历的“政权下乡”“乡政村组模式”“村民自治”和“社区服务”等治理演进历程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政府渐退而市场趋进的过程。在市场运作机制已经引入农村社区的宏大背景下,推进农村社区发展必须加强市场主体的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就是要强化以当地优势产业为主导,采用市场化运作为手段,吸引城市优秀企业进村,为企业能够获得预期收益提供便利条件,实现城市企业下得来、留得住、办得好。企业的良性发展,有效实现了农村资源与现代化市场的对接,成为农民收益稳定的可靠保证,是农村社区健康发展的推动力量。(3)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新型社区发展的干劲。农民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主人,更应当明确其主人翁的地位,实现我国基层农村社会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在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新农村建设大潮中,农民除了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意愿,还应当发挥主体作用,这样的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社区农民要利用好政府的支持政策,以社区精英为发展的目标榜样,以积极到企业就业为收入保障,发挥自我资源优势,争取在新型农村社区发展中个人行动起来、家庭富裕起来、生活质量提高起来,推动城乡一体化目标尽快实现。
二、新型农村社区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政府主体存在越位错位现象
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是探索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农村“三化”协调科学发展新路子的重大创新举措,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密切合作、协同推进。政府具有政策调控和资源分配等方面的优势,作用不可小视,“如果说政府对农村社区发展的组织、动员、引导和推动属于政府干预的话,那么,这种干预是政府责任的体现”[4]。但应当看到,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实践中,政府不同于传统农村社区的“全能者”角色,包揽着几乎所有的管理和服务职能,而是充当“代理型”或协调服务者的角色,要主动地从越位错位的泥潭中挣脱出来。然而,在履职尽责这一“合法性”外衣的庇护下,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中很难摆正自己的位置,想问题、办事情更多的是从便于政府权力行使的角度出发,越俎代庖式地替农民做主、代农民决策。为了凸显政绩、追求速度而刻意塑造“形象工程”,对农民的心理感受和真实意愿顾及甚少,乃至行政行为偏离了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现了主体越位错位的现象。
(二)农民主体地位未能充分体现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农民群众是主体”[5]。没有农民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农民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意愿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社区发展效果的好坏。不可否认,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推进实践中,农民参与意识较以前有明显提高,但是基于主客观因素影响,仍然存在参与环境差、主体意识不强、社区参与率低的问题。不尊重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农民的合理诉求和实际需要也被极大地忽视了。有些地方甚至存在着“政府兴致勃勃、农民冷眼旁观”的现象。政府自导自演,“强制性”和“规划性”干预导致农民正当利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旧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新的社会矛盾又不断滋生。在这种情况下,当涉及自身利益时,农民往往认为自己的主体地位体现不充分,缺少最起码的话语权,在旧房改造、村庄拆迁和住房安置等环节自身利益必然会遭到损失,因而在社区发展的实践中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合作,甚至以“冷暴力”对抗,结果导致群体性事件和干群冲突时有发生。此外,由于传统村落文化的消极影响,部分农民综合素质不高、思想观念相对保守,一方面拒绝改变、抵制改革,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怀着抵触情绪;另一方面集体观念淡薄,始终对集体、公益事业漠不关心,这些都影响其在新型农村社区发展中主体作用的发挥。
(三)企业主体带动作用不明显
企业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市场化运作方面本应发挥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在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村办企业布局较为分散,总体规模较小,创新发展能力明显不足,很难形成规模优势,无法发挥集聚效应的有效作用,经济社会效益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另外,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是点宽面广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村庄拆迁和村落合并,而且还需要公共服务设施的同步跟进,这些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但目前推进社区发展的资金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和农民自筹,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参与农村社区发展程度较低。亦不可否认,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推进实践中政府也积极整合闲置土地、零散资金、富余劳动力等各类资源,开辟产业集聚区和农民创业园,以期吸引更多的外来企业进驻,为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由于进驻的企业同质性程度偏高,彼此之间互补性不足,结果未表现出有效的产业支撑力。企业主体与农民犹如一对命运共同体,而目前农村企业的发展态势不能让农民更直观地感受到企业的内在吸引力,农民离村入企、就近择业的意愿不高,企业也没有充分发挥辐射带动和示范引导作用。
(四)第三部门公益服务空间狭小
第三部门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一股社会力量,是农村社区多元治理的主体之一。第三部门参与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可以弥补现行农村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的局限,维护和实现以农民利益为核心的社区利益,推进社区的科学健康发展。但是,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实践中,第三部门所面临的问题相当突出。一是运作行政化倾向。当前,第三部门大部分运行资金源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资助,其行为必然“偏离它们基于价值观而为自己设定的使命”[6],活动的开展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表现出强烈的行政色彩和政府依赖。二是缺乏社会公信力。第三部门具有自生性、草根性等特征,专业化程度较低,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准确定位存在较大困难。这些组织与基层政府缺少互信、沟通和交流,其需求和呼声政府也很少回应,农民对其信任度不高。三是服务质量缺乏专业性。受环境条件的限制,第三部门工作人员以志愿者为主,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其服务质量难以满足农民的多样化需求。
三、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动力系统构建
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动力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动力系统的各构成要素是密切联系、相互协作、相互制约的。可以说,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驱力与外助力的整合和协调程度。
(一)外力助推:农村社区发展的倚重力量
1.积极发挥政府的组织发动、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作用
在加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我国积极地推进农村社区发展,尽管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民政部亦出台了指导性意见和实施方案,但就全国而言,这些规划和政策还是相当宏观的。具体到各省、市乃至县、区等基层,应当如何实施呢?显然需要基层政府在学习、领会中央相关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制订更为详细的实施计划和措施。同时要积极发挥指导和监督作用,引导农村社区发展方向,并做好农村社区发展的宣传动员工作,让广大农民真正意识到,推进农村社区发展,是政府还权于民,增强群众自我服务意识的重要体现,并非村委会与居委会之间简单的名词互换。当然,做到这些,仅是其一。尚需提及的是,农村社区发展尚处于试点阶段,各级政府除给予政策、制度等基础性的保障以外,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向农村社区集聚、配置,以便有效推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壮大集体经济,增加村民收入,促进水电、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改善,提升乡风文明程度和公共服务水平,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2.充分挖掘企业主体的市场带动作用
第一,政府服务以外的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市场主体承接。就政府职能的角度而言,制度性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征,不能引入市场机制而必须由政府提供。但是,某些准公共物品在消费方面却具有较大程度的外部性,具有消费中的争夺性和排斥性等。此类公共物品譬如乡村公用设施、教育、医疗等,其生产和服务从有效性的角度而言,借助市场化运作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可能效果更为明显,而政府仅充当其间的购买者。第二,营利性的商业服务离不开市场主体参与。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不仅农民思想更趋活跃、开放,而且乡村活动主体也更趋多元化。因为他们也有着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满足单纯依靠政府提供显然是不行的,因而需要引入市场竞争、市场调节机制,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进来,才能杜绝“一家独大”。况且,也只有在自由、公平的竞争中,农民及其他活动主体才能享受到快捷、高效的商业服务。第三,发挥农村资源最大价值需要市场主体参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民择业就业、资源开发利用和农产品生产销售,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创造良好的环境,通过市场调节才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最大化地发挥资源的潜在价值。由此可见,将多元的市场主体引入农村社区发展活动当中,其作用发挥不是阻力而是助力,对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可以起到助推、拉动作用。
3.第三部门提供的志愿公益服务,有助于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利益
在市场经济支配下,农民的社会需求更趋多元化,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免不了会受利益最大化等市场法则的干扰,心中天平潜意识地向利益一方倾斜。从私利性的角度出发,部分农民对农村社区的服务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和公共设施维护等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公共利益观念缺失的乡村社会还能称之为社区吗?英国社会学家R.麦基弗认为,社区建立在成员的共同利益之上,社区的主要特征是共同的善或公共利益,社区不是简单的个人利益的集合。而第三部门的介入,通过公益广告和举办公益活动等方式,凸显社区公共利益。第三部门在乡村社会的积极作为,一方面能够培养社区居民高尚的道德情操,增强了他们的集体公益意识和社区责任感;另一方面能够起到良好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有纠偏补正之效果,引导社区居民热心社区公益事业。
(二)内力驱动:推进农村社区发展的关键动力
1.密切沟通、增进互信,构筑和谐高效的农村社区发展引擎
当前,农村社区发展存在“村委会直转社区”“村委会创建社区”“撤销村委会建立新社区”等三种基本形式,无论哪种创建形式,社区居委会成员间的和谐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为成员间的权力欲望、权益分配、情感机缘等复杂因素制约,彼此缺乏深度信任,相互间契合度低、协调性差,加之受价值观念、决策方式、目标趋向等多重因素影响,决策中彼此掣肘、相互抵牾而严重地影响到工作效率。“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构件,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个人之间对于相互合作所持有的信心。”[7]从这个角度而言,有效发挥农村社区居委会的引擎作用,就是要在营造社区居委会成员间和谐团结氛围的基础上,积极创设沟通交流平台,通过改进沟通方式、增进情感交流而逐步弥合因情感缺失而形成的心理鸿沟,从而建立起深度信任关系。
2.凝聚情感、齐聚共识,培育农村社区发展相对稳定的动力主体
农民是农村社区的主体力量,是推进农村社区发展的原生动力。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建设农村社区的关键。第一,凝聚情感、齐聚共识。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业服务工业、农村支援城市乃天经地义的事,长期以来导致了农村的贫穷和落后,“真累、真苦、真穷”乃是农民生活处境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命运、摆脱贫穷,青壮年劳力入城务工而常年不归。将落后农村建设成为富有现代气息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离不开农民这个主体力量。为此,需要营造良好环境,并充分借助血缘、地缘等情感纽带促进入城农民尤其是青壮年主动返乡创业,让他们在“熟人社会”的交流互动中增进乡缘情分,逐步凝聚社区共识。第二,尊重民意、弘扬民主。农村社区发展必须顺应社会形势,充分体察民意。说到底,农村社区是农民群众自发参与的自治性组织,其建设不能由政府代位决策,而应当以农民为本位,结合客观环境并尊重农民的主观意愿,让他们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凡是涉及社区发展的事,农民应当拥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以利于最终决策。第三,引导发展、维护民利。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农村社区发展的重要目标,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当着眼于农村环境质量改善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因此,在建设推进中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让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这些都是培育农民社区意识,调动农民社区发展热情的基本条件。
3.严格程序、规范运作,引导农村民间组织有序健康发展
随着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迅猛发展,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不容否认,随着现代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接地气”的第三部门在农村社会发芽生根、茁壮成长,譬如专业合作社、红白理事会、农民文艺演出队、民俗民风协会、矛盾纠纷协调会等。其中大部分社会组织旨在维护农民权益、表达农民诉求、满足农民需要,对农村公共利益和公益事业发展有着强力助推作用。但也应当看到,部分第三部门的成立还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程序不合法、运作不规范,因而在农村社区发展中的作用仍相当有限。就当前形势来看,发挥农村第三部门在社区发展中的正向作用,才能进一步彰显其存在价值。一方面,民政、工商等部门要立足农村实际和农民生活,进一步完善制度,为更多的第三部门进入农村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为地方性“草根组织”孕育、发展提供政策制度保障和人才资金支持,并创造适宜条件将这些社会组织纳入农村社区的组织结构体系中,使其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农村各类社会组织尚需要完善其功能,规范其运作,在满足农民利益需求之时不能超越法律许可的权限,保证在阳光下运行。
[1]龚世俊,李宁.公共服务视域下的新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模式创新[J].南京社会科学,2010,(11):82—86.
[2][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3.
[3]刘桂云.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及其法律环境[J].河北法学,2010,(7):141—145.
[4]管义伟.农村社区建设:逻辑起点与人文关怀[J].社会主义研究,2011,(1):116—120.
[5]喻新安.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探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94.
[6]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兴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26.
[7]李新春.信任、忠诚与家族主义困境[J].管理世界,2002,(6):87—93.
The Research of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mmunities in Urbanization Process
TangJianbing
In basic socialgovernance practices,because the main driverofruralcommunity development is been grasped the phrase,result in the functional imbalance,make the road to new rural communities seems to be rugged difficult,from the motivation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mmunities has translate from top government design to focusing on grass roots practices.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mmunities include outside help and drive two important part.Community outside the power include the government’s support,market action,third department assistance ect;drive include famer’s desire for wealth,community participation,elite normal drive,community culture ect.New rural community effectively integrate help drive outside.In effective coordination to encourage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all kind of power elements,to promote new rural commun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Rural Communities;Momentum;Drive within the Outside Help
D6
A
1007-905X(2017)08-0058-05
2017-03-10
安徽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5D58);安徽省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招标课题(AHWH2016205)
唐建兵,男,法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乡村发展与社会治理研究。
编辑 王秀芳 陈 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