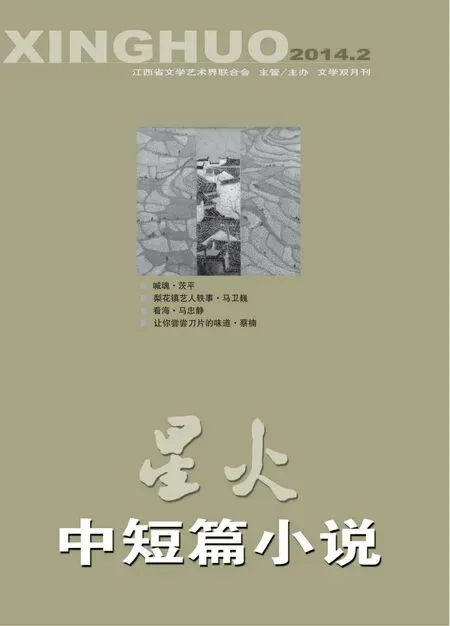越来越轻
○朝 颜
越来越轻
○朝 颜

朝颜,1980年出生,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散文》《青年文学》等刊。获《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人民文学》杂志社全国征文奖等多种奖项,作品多次被《散文选刊》选载,入选多种选本。出版有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
眼望岁月与流水汇成的长河
回想时间是另一条河,
要知道我们就像河流一去不复返
一张张脸孔水一样掠过。
——博尔赫斯
一
第三次走近这座新坟,已是清明。所有人都在静默,忧伤弥漫在空气里。原是春和景明的日子,天空却似乎越降越低。我的婆母,她一向活得很认真。可是谁知道呢,活着活着,她就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住在水晶岭上的“中华显妣”。
我们跪在坟前,为她烧一个装满“巨款”的箱笼。火势渐旺,先生的舅母提醒道:“喊啊,快喊你妈妈出来接啊。”先生嗫嚅了嘴唇,却终是没能喊出口,倒把眼泪给逼了出来,在鼻腔里隐忍地抽着。风越刮越大,漫卷起一团一团的灰烬,在我们头顶上旋舞着,像一群怎么也散不去的黑蝴蝶。我望着跪在我左边的兄弟俩,蓦地想到,他们都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了,突然间满是凄凉。
我承认,她活着的时候我并不见得有多么喜欢她,可是她死亡,我却的的确确抽心抽肺地痛过。在与她成为家人的十二年间,我们龃龉不断。天知道中年守寡的她有多么爱她的儿子,而且爱得毫无技巧。作为一个夺爱者,入侵者,我竟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用瑞金人惯用的笑谈说,就是“初次结婚,没经验”。于是,还未交手,碰个头破血流便已成定局。
那时候,她多么健壮,多么具有把控力。整个家庭,完全运行在她多年建立的秩序之中。每一个齿轮的咬合都显得至关重要,容不得半点松懈。从农村进入城市,我像一个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平生第一次将一个人的意见看得如此之重:剪掉长头发,是因为她担心堵塞下水道;说话轻声细语,是因为她多次说过我吹喇叭放广播;甚至散步快到家时,我必须立即将先生拉着我的手甩掉,因为她郑重地与我谈过,那样会丢她的脸……
真的,我曾经以为她可以活一百岁。学过几年中医的她极其讲究养生,每日清淡规律的饮食,早睡早起,还坚持锻炼,出门永远步行。在我印象中,她连感冒都很少患。记得一年去叶坪红军广场参加红博会开幕式,我们都去了。我是和单位同事一起去当观众,婆母则是老年腰鼓队成员,在大太阳底下打了几个小时的腰鼓。最后,我和办公室的好几个年轻人都中暑了,她却金刚不坏。
我们家中极少来客,但每个人用的碗筷杯子仍严格区分,各用各的,各洗各的,不得逾越雷池半步。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渐渐适应过来,从此乖乖地遵循。心想这是有多么科学多么卫生啊,这才是真正的文明人,而我从前所过的生活,都显得那样粗鄙不堪。我自惭形秽,甚至不太敢把父母和亲戚带进家中,生怕破坏了她的规矩。我还怕父母那麦菜岭人招牌式的高声说笑被她诟病,又来上一句“山旮旯里人”。我受不得这样的鄙夷,我要尽量努力地把自己炼成一枚正宗合格的城里人。
和先生建立恋爱关系之后,他很认真地和我说,要带我去体检。“你看你老是感冒,去检查一下吧,正常人每年都要体检的。”我知道,我丝毫没有怀疑过他对我的好。“妈妈带你去,找她熟悉的医生。”他又说。
那时已是秋凉时节,她握着我的手臂,拉着我往检查室走。她热乎乎的手心触在我的皮肤上,与我的冰凉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很容易便被那种热乎感动得一塌糊涂,暗自思忖,未来能有这样一个好婆母,真够幸运的。几乎不经任何思考,我便伸出手去,任医生在我手臂上抽了满满一试管的血。至于查什么,怎么查,我却一概不知。直到最后,检查的结果,我依然一无所知。只记得从医院出来,先生悄悄从怀里掏出一枝被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玫瑰花,叮嘱我别让他妈妈看见了。
经年以后,我渐谙世事,有一次突然想起这事,方才悟出其中玄机:亏得我当年身体健康,单纯如一张白纸。否则,踏进那个家门,叫她婆母的人还会是我吗?我忍不住追问先生,他一言不发。
二
那些张牙舞爪的细胞是怎样潜伏在她的体内,渐渐肆虐的呢?谁也不知道。
她那么爱干净,皮肤白嫩,肌肉紧实,声音清亮甜润,曾数次被打电话到我家的朋友误以为是个少女,令我这个被职业损害了嗓子的年轻人羡慕至极。吵架的时候,她还能发出比我高八度的吼声。她生气用手指着我的时候,常常令我望而生畏,脑海里总要浮现出“力拔山兮气盖世”这样的词句。
可是后来,她开始喊疼,说话细若蚊音,比任何时候都要温柔,都要和蔼可亲。从来没想过会有一天,她开始需要并接受我的伺候,但这一天还是来了。我蹲在卫生间里,安顿她坐在一张结实的椅子上,为她擦洗身体。水是用艾梗煮沸过的,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弥散着一股迎接新生婴儿般的气息。在她的内心里,做完一次大手术后回到家中,无异于一场新生。只有我们知道,接她回来,是已经明白住院没有多大意义了。
我洗得很小心,敷完一条手臂,再敷另一边。一遍,又一遍。然后是腿,还有脚。我搓着它们,比任何一次对任何人都要仔细,都要耐心。我期盼着那些流水可以带走一些痛,那些香气可以让她暂时忘了体内的暗疾。我听她絮叨着:“我说了不要做骨扫描的,他们非说要排除一下才放心。那东西放射性真强,做完就开始疼了。你看,扫描结果不是正常吗,白花钱买罪受。”她轻轻地叹气,责怪着子女们的太过周全。我能说些什么呢?我能告诉她看到的那张结果图与她无关,而真正的遍布阴影的扫描图被封存在每一个知情者的喉腔以下吗?
热热的水汽润湿了我的眼眶,安慰的话语从我的唇边出来,却是轻描淡写:“是啊,现代的仪器,很多都有副作用呢。恢复总有个过程,慢慢就好了。”我知道,她心里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就在上午,她还唠叨着要看好院子里的那几畦菜地,别让人给占去了。她说这地方好,可是寸土必争呢。先生生气了:“你给我好好养病,别老操心着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我们不差那点买菜的钱。”她据理力争着:“我总有好的时候,我还要自己种呢。自己种的菜多好,没有农药化肥,环保着呢,坨坨(我女儿小名)就最爱吃我种的小白菜。”
我知道,内心里有个念想,其实是件好事。可是先生却急火攻心,眼睛里只看得见那魔鬼般摧毁一切的病。那可是癌细胞啊,它们像一条毒蛇,盘踞在骨头缝里咝咝地吐着信子和冷气,一点一点地吞食着人的肉体和生命。只要一想到有千军万马的敌兵正在亲人的身体里步步推进,寒意和绝望就从脚底一直上升到头顶。每一时,每一刻,邪恶之花都在隐秘的地方开得疯狂,而你无力铲除,无计可施。
起初只是血尿,时好时坏地纠缠着。她知道,有一个肾脏年轻时动过手术,她一直小心翼翼地哄着它,对它好,不让它受半点委屈。可它还是背叛了她,不再老老实实地坚守岗位,鼓捣出那么多令人不舒服的状况来。各种常规性的检查都做过,没有发现个中原因。或许,还是老毛病罢。于是找了熟悉的医生输液,吃下许多的消炎药片。她谨遵医嘱,温顺地配合一切。那边厢,她养的几只母鸡都下蛋了,她种的草莓也在结果了。一切都欣欣然生长着希望的样子,她怎么能想到会有更猛烈的潮水正在以覆盖一切之势朝她涌来呢?
终于有医生提出做癌细胞的检查了。她犹豫了很久,她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种东西会与她沾上关系的。而且从肾部抽取细胞,亦是一个损伤性不小的手术。先生与弟妹们反复地商量和论证,然后是轮番的劝说,直到她点头同意。
我们期待的那一场虚惊没有到来,血尿的背后原本是潜隐着一只凶猛的老虎啊。她只好丢下她所操持的一切,住进一个更远更大的医院。在那座城市里,她成了一个处处需要别人照顾的病人。从此,她园子里的菜再也没有得到过她的照顾,兀自凋零。
三
冬天了,我还在乡下驻村,做着貌似无比重要的工作,却疏离了真正需要我的亲人。我内心愧疚,又无可奈何。
那天晚上,山风呼呼地掠过耳际,像一场席卷一切的忧伤,令人无处躲藏。先生从那座城市打来电话:“妈妈要动大手术了,风险很大,你必须请假过来,带上女儿。”尽量压低的声音里,夹带着难以抑制的哽咽。我猜,他一定是躲在病房外面打的电话。几分钟后,他必将又一次整理好脸上的笑容,重新轻松地出现在她的面前。
在确认了肾部周边的器官没有被癌细胞侵入之后,医生认为摘除那个肾是最佳的方案了。把病根拔除,只要后期保养得当,癌细胞不再扩散,完全可以再活很多年。婆母一向相信医生,相信科学。她是知道的,我们家对面那栋楼里住着的杨老头,多年前就没有了膀胱,腰间挂着一个尿袋子,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所以,这次的劝说几乎没费多大的劲。
我带着女儿匆匆地赶赴那座城市,彼时婆母人已消瘦,但仍行动自如。先生带着我们去饭店吃饭。她和她的小儿子并排走在前面,高与矮,胖和瘦,年轻跟衰老像黑白两面旗帜那样鲜明触目。她的头就靠在他的肩膀上,那个用宽大的臂膀揽着她往前走的人,曾经是她像护鸡雏那样守护着长大的小孩。北风翻动她花白的头发,满目的苍凉。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弱,那是一种怎样令人心疼的弱,我感觉到自己眼睛里泛起一股热热的东西,刹那间就把多年郁积下的前嫌给尽释了。
先生拿着照相机,叫我们轮流与她合影。每一个人都心照不宣地笑着,默契地配合着。我们坐在饭店里,多么像其乐融融的一家子。风平浪静的下面深藏着多少波涛汹涌,沟壑暗礁,有谁知道呢?她翻动着菜谱,每挑一个,都是儿子的最爱。当然,她还会用心地计算着价格,不动声色地达到俭省的目的。这对于一个做了半辈子优秀会计的人来说,并非难事。她吃得很少,嘴里吞吐的全是唠叨:“广,你胃不好,少吃点辣椒。文,这块鱼是大骨头的,你吃。”这些年来,她一直致力于向我示范一种爱的方式,对象是她的儿子。而我笨拙、任性、不管不顾地向先生索取宠爱,让她失望至极。我就坐在她的对面,我知道她不会关心我喜欢吃什么,吃了多少。但我再也无心计较。多少年过去,习惯都可以成为自然。
就要上手术台了,我挥着手和她告别:“妈,顺哦。”“嗯。”她表情安详自然,眼睛里含着即将上战场奋力杀敌的那种英勇。女儿走过去,怯怯地叫了一声奶奶。她说:“坨坨啊,等奶奶好了,还帮你提琴,送你去弹琴的地方。那么重,上次我们都走了好久才到哦。”我知道,那是唯一的一次,因此她记得那么牢。因为我的下乡驻村,孩子与她发生了相对更多的关联。如果这样的理由可以成为一个鼓胀的风帆,扬起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我真愿意它多些,再多些。
而希望是一回事,生命的暗流朝向哪一方奔跑又是另一回事。那一台手术像一场没有退路的赌局,我们是疯狂的赌徒,为之押上了所有,只为等一个明朗的结局。
再过几天,就要立春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行,手术成功了,她如期地苏醒了,她顺利地放屁了,她开始说话了,她能够进食了。一个万木复苏的春天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甚至欢喜地预计着,再过一段时间,等伤口恢复好,就接她回家。儿女们还谋划着物色一幢带个小花园的房子,好搬过去住,让她自由自在地种菜养鸡,不再为了方寸之地与别人争执怄气。
她亦满心欢喜,对每一个前来探望的老姐妹诉说病情,抱怨住院的日子多么憋闷。她多么想早日好起来,可以继续去跳广场舞,去打腰鼓,去种一大堆自己喜欢的菜。
那时候,谁会想到,器官之外,还有骨头。那邪恶的触手无孔不入,早已伸向更加致命的地方。直到骨扫描确认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骨头上,她仍然相信自己正在一天天地好转。可不是么,伤口一日日地在愈合,她也开始渐渐能坐能站能走动。未来还有一大片的日子在等着她去过,她怎么能怀疑死亡的脚步正在一步一步朝她逼近呢?
四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目击一个人的离去。
她躺在专用的护理床上,薄得像一页纸。彼时她的身上已经没有肉了,唯有那双脚板顽强地向上昂着,显得特别大。一天一夜的发烧和昏迷,已经让我们预知了某种结局正在无可避免地到来。请来的医生还在作最后的努力,扎针、输液,试图缓解病人的痛苦。先生的舅母流着泪,用湿毛巾一遍遍地敷着她的额头、腋下、腹股沟,一遍遍地叫着:“姐姐哎,现在给你打退烧针了哦。姐姐哎,你要挺住哦,你好不容易把孩子们都拉扯大了,该是你享福的时候了。”
一滴泪从她的眼角滑落。
大家围在床边乱乱地喊着:“妈妈,姐姐,奶奶,嫂子……”可是她再也不会回答了,连点个头也不能够。她开始剧烈地喘息,然后是一口痰吊在喉腔呼噜呼噜地响,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像一支即将崩断的弩……泪水一下子从所有人的眼里奔涌而出。
谁知道她有多么的不甘,有多少的不舍?就在过完年不久,我去街上买宁都肉丸给她换换口味。她尝过后,还问我多少钱一碗,然后捞起来一个一个地数,最后很是不满地说:“就这么小一粒,差不多平均两毛钱一个,这也太贵了。”是的,我买的东西很少有称她心的。从嫁过去那天起,她就开始了对我的培训:“瘦肉要去华塘路买,那个卖猪肉的女人蛮善良的。青菜要一大早去农贸市场,很多乡下的菜农挑担来卖的,新鲜,便宜。买了鱼最好到满叔的摊位上过下秤,那些鱼贩子,都奸猾着呢。还有,油炸糕必须是绵塘市场的才好吃,买米不能上超市,应该去机米的店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好吧,我都记住了,直到今天还记在心里,可是我有多少次真正执行过呢?我知道她不放心我,她从来不认为她的儿子和我生活在一起会非常幸福。
可是后来,她所重视的所有规律和秩序都在土崩瓦解。她用了大半辈子的破沙发、旧电视柜,还有简陋的防盗门,都被儿女们强行换了新的。她坚守了一生的厨房重地,也被他人占领。她只能躺在床上,等着别人将寡淡的稀饭、素面,或者清汤喂进她的嘴里。她看着自己的阵地在一点一点地沦陷,身体在一点一点地萎缩。她常常由儿女们抱在怀里,翻身、便溺,越来越轻。在逐渐捕获真相以后,她终于不再为了担心依赖而拒用止痛药。其实她已经吃了很久,只是一直被告知是消炎药。子女在背叛她,身体在背叛她,整个世界都在与她背道而驰。
那天我给她喂食,几口之后,她摇摇头就停下了。我反复地劝着:“你要吃下去,肠胃才能蠕动,才不会便秘呀。”“大肉都落了,反正是捱时间了。”她轻轻地说。我退出房间,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总有一个暗夜等在生命的那一端,可是我们都未能学会从容淡定地接受。
四月,正是连枯草都不得不萌芽的春天。可是我的婆母,却被殡仪馆的人从床上抬下来,像一片被风刮落的树叶,轻飘飘的。一个黄色的大袋子将她套住,拉链刷地合上。从此,好与不好,都不会再见。我只是想,一直在想:一个人,怎么就变成了一件物体呢?大街上,化妆品店传出劲爆的流行音乐,一辆急救车鸣着尖锐的笛音呼啸而过,许多的小摊小贩高声地叫卖……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欢笑,有人啼哭。除了死亡,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停下奔忙的脚步。
我们在殡仪馆等了很久。她出来的时候,已经把整个身子都蜷进了一个雕花的骨灰盒里。一块红布遮盖了她一生的秘密,一生的重量,以及一生的爱与恨,幸福和痛苦。先生抱着她,庄重地走着,走上一辆车,然后,轻轻地将她放在膝盖上。风掀动路边的树叶,和任何时候都没有两样。只是对于我们,世界从此不一样了。因为有一个至亲的人,从我们的生活中退场了。
她将自己退到一座山上,越来越轻,最后化为一抔土,与大地融为一体。来年春天,会有一群黑蝴蝶,没心没肺地覆盖一座旧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