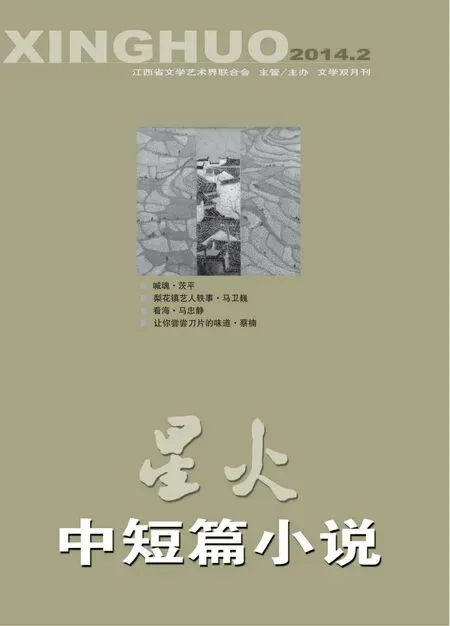“一切刚开始时的样子”(访谈)
○李 壮 何向阳
“一切刚开始时的样子”(访谈)
○李 壮 何向阳

李壮,山东青岛人,生于1989年12月,现居北京。青年评论家、青年诗人,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文学评论及诗歌作品发表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诗刊》《星星》等刊,出版有诗集《午夜站台》。
李壮:何老师您好!您的诗歌创作,我最近一直都有关注。我注意到,您前年出版的《青衿》收入了您从大学时代起的许多旧作,而去年以来,我们看到您新完成的诗作也一直在以惊人的频率发表。是怎样的契机让您在这么多年之后,重新审视自己的诗歌写作,并进入了一个创作的爆发期?
何向阳: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停。前年出版《青衿》,从以前那些笔记本里抽出来这些诗,108首,好像显得挺多的,实际更多。这几年发得比较少,但写得其实不少。当然跟专业诗人比起来,写得还是不够多,有些诗人一天能写好多首,但我一年也就写二十多首,一个月大概一两首这样的速度。可能是我还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专业写诗的人,没有这样一个限制,我的写作反而进入了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这种状态对诗人来说其实是比较好的状态,没有压力,但我近年来觉得有些不太满足。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一个评论家的角色出现的,渐渐大家遗忘了你同时更是一个创作者。
最早十三四岁开始写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大学生诗选也选了我的诗,以前在《诗刊》《十月》都发表过组诗,后来写散文、评论,慢慢大家看你就有一种定型的眼光了,就把你定位为一个评论家。所以自己有一种不满足。理论,毕竟是在别人的创作之上的阐释和解说,是一种二度创作。当然它也是一种创作,但毕竟不是一种原初的创作。《青衿》的封面,一开始出版社有很多想法,例如介绍它是评论家的第一部诗集啊,八十年代的结晶啊,女性主义等等。但后来我说封面设计还是简单一点,只保留一句话,“一切刚开始时的样子”。因为最开始我就是以写诗进入文学的,现在回到诗歌,算是保持了初心。这就是一切刚开始时的样子。找得到开始,一切便不复杂,所以,近年在《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等发表了一些诗,有重新上路的感觉。
李壮:重温“一切刚开始时的样子”,这里面是否有重新审视、整理自己诗歌写作的考虑?回顾这二三十年来的创作历程,您在提笔写作的原动力以及面对诗歌进入语言的姿态方式等层面,又有怎样的变化?
何向阳:这本诗集其实也算不上一个回顾。过去的写作已经定型了,无可更改,出版时一字未改。重要的还是回到原点,重新找到自己的初心。至于面对诗歌的姿态,或者说进入语言的方式这些方面,我其实没有考虑太多。但是现在再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包括近几年的诗,当然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跟以前那种特别清纯、比较青涩的东西有所不同。以前是一种单纯的抒情,纯粹的心灵倾诉,现在还是有一点沧桑感了。随着岁月的叠加,随着内心经历和历练的增长,可能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当时那些爱情诗可能有点强说愁的意思。没有爱情的时候,因为受了其他很多诗歌的影响,我也在写爱情。没谈恋爱的时候,已经在诗中写给爱人很多诗了;没有失恋的时候,好像自己在诗中已经失恋了很多次了。那种诗的假想性,包括诗中的自我主人公意识,还是比较强。那么现在可能有些东西要放下一点,就是生活中更多的具体的东西进来之后,内心可能有些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体现在姿态上、方式、语言上,包括出现一些节奏上的、形式上的变化,可能都会有。比如形式上的,原来我的诗可能每一句都比较长,但是现在的诗好像是尽量凝练,句子不长,一行有时也就两个字;也不是说刻意去做,但确实会让人感觉它已经不是原来那种好像很排比、很适合朗读的东西。我现在的诗,在内在构成上好像比原来更复杂一些,很多时候它呈现为一种繁枝式的结构。原来它可能是一株花草,或者是一种灌木,现在可能这棵树的枝桠多了一点、复杂了一点。
为什么这么多年后又重新整理、强化自己的诗歌写作?可能还是来源于对世界的感受。许多东西,并不是理论能够解决的。理论能解决的只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比如道理,伦理,哲理,至于另一些诸如情感、爱意层面的问题,还是需要另外一种文体,或者说另外一种形式,才能让自己完成言说。
李壮:一直以来,说到您的名字,大家首先想到的一般都是“优秀的评论家”。现在您可以说是左右开弓,一手写诗,一手写评论。其实我自己也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会遇到一点障碍。在我的理解中,做评论更多是靠理性思维,它要求写作者保持头脑的清醒、逻辑的清晰,要能准确地抓住问题关键所在。但写诗往往要靠感性思维,要有一种“精确的混沌”,恰恰不敢太清晰;就像一场兴致勃勃的围猎,它有所指却在不断延宕,不能上来一枪就直接把猎物给撂倒了。因此就我个人而言,两套思维方式、表述方式之间的转换,其实是有点费劲的。您这两支笔的切换是否顺畅?
何向阳:我们遇到的是同一个问题。一边理性思维,一边感性思维,在这种思维中间的确有一种转换。就是说,我们的写作,其实不像纯诗人、纯理论家那样单纯。同时有兼容,一方检验另一方,另一方又同时监督第一方。所以说,很自我较劲。还是一个怎么来切换的问题。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两难问题,其实是可以调和的,诗人,理论家,诗人理论家,当然也有诗人哲学家,诗人对理论哲学为什么感兴趣?因为诗人追求真的东西,他比较纯粹,不像小说家有时候更倾向于模糊,诗人追问终极的东西,一种纯粹的原初的存在,小说家关注的是生活的具体与多元,而诗人的减法与理论家的减法,从“减”的角度是一致的。理论是一种减法,诗其实也是一种减法,它不是一种叠加。小说是一种叠加,几个人一件事,他给它补充,扩展,它是加法,它要的是丰富与复杂。但是诗、理论好像都是在做减法,它要讲的是“一”,而不是“一切”。
这里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既算是对前一个问题的补充,也正好与这一个问题有关。我的第一首诗13岁写的,不是爱情诗,是写对花的感受。第一篇评论发表于19岁,1985年对《黄土地》的影评。而人类最早产生的也不是理论,不是评论,理论是后来的事,最初都是诗。中国最早的文字也是从《诗经》开始的。作为我个人来说,不是先从评论出发,诗是我的出发地。但是你说到有没有障碍,或者有没有对个人的这种撕裂、转换的困难,理论上好像应该有,但实际上我倒觉得问题不大,因为评论是我研究生之后训练的一种结果,它的逻辑,包括它的资源,比如八十年代我们读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哲学方面、美学方面、社会学方面的书,构成了我们当时那个比较清晰的逻辑性的一种思维。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文字当中,渐渐地有了一些显影,这些显影,要知道,它是有一个暗房的,就像我们洗照片,照片上的东西的来源是书本上的,并不是生活中原本的,是前人的文字,它们构成了我们就对文学的一种观察。
从西方的一些东西再回头来看中国的一些文学,我们有哪些不满足的,有哪些觉得可以再扩展的,或者是哪些我们觉得还能够再往前延伸的,重新思考我们文学史,重新思考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的这样一种走向,包括对当代作家的一些评定,我们会拿来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当然不一定是完整、全面的,也不一定精确,但是它毕竟有了一个参照系,就是比没有参照系要好一点。我们当年其实特别热衷于这样一个参照系,比如拿来弗洛伊德的那样一种东西,或者拿来罗素的这样一些东西,我们去检测当代的一些大家,包括已经逝去的一些大家,在文学史上响当当的、鼎鼎有名的一些大家,我们都来检测。比如说对郁达夫的一些评定,用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去看他。拿来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对莫言做一些参照,是吧?我们的理论与作家共生于这样的一种参照系中,完全脱离这种“影响的焦虑”几无可能,创作者本人也都承认,他们也受到了这些哲学,包括文学思潮的影响。他们带着很深的一种时代的、文化的、时尚的印记,那么拿这种东西来评定,或者来进行一种“围猎”,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当然,谁能最终逃脱掉这种“戳记”,谁才能真正地成为并成就自己。
李壮:我想到李敬泽老师一句貌似调侃的话,他说搞文学的人往往不讲理,讲理又热爱文学,只好去搞文学评论了。至于既写评论又写诗的人,可能恰恰是兼具了讲理与不讲理两种特质,他(她)的体内或许同时居住了一个苏格拉底和一个狄奥尼索斯。在这个过程中,诗歌貌似“不讲理”的形象思维和情感逻辑,是不是也会带给您不一样的满足感?
何向阳:就理论评论而言,你看似是在评说别人,理论别人,其实这些文字写下来也是在自我提醒。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创作者,不单纯是一个评论者,如果是单纯一个评论家,不搞创作的话,你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又写作又评论的人,在你持有理论评论这种武器枪口对外的时候,其实反过来也是在提醒自己,自我也同样在警戒之内。我觉得这样的“双面人”比较辛苦,他不像一个单纯的作家,不搞理论,或者只有一些理论思维,他把这种理论思维贯穿到他的写作当中,比如像阎连科,或者刘震云,他有自己的一种理论一些思考,但他不拿这个武器去评说别人,他只是把这些消化在他的小说写作当中去了,创作只是他个人理论的一种实验,他不是很辛苦。他也不企图指导别人。比如写诗,他就是写诗,从诗中抽出一些理论,但是他这种理论可以为他个人的诗歌创作服务。他也单纯。但是两支笔同时运转的人就比较辛苦,就是说他时时刻刻要警惕自己,会不会走入自己围猎的这个陷阱当中去。所谓批判的武器,同样也是武器的批判,是吧?有时候可能一两句话逻辑没弄清楚,别人就可以拿这个武器来批判你。
所以,我近年越来越倾心于“不太讲理”的诗,创作的快乐在于抒发,而不在于“博弈”,前者是一对于多的,对于“多”,有时也可理解为对于“空”,而后者恰恰是一对于一。所以说,前者更其自由。而后者,时时要保持着一种“斗争”的论辩意识。
李壮:但写诗有时候是不必想那么多的。预先想得太多,反而不好。
何向阳:当然。一旦写诗,有些东西反而能放下。就是说它活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境界里,天马行空,它能够缓释你的角色疲劳。还原你本来的自己。当然理论对诗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形象的东西,其实也有一定的情感逻辑。但是我觉得诗带给我的满足感其实比理论带给我的满足感要更强烈一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们写理论的时候好像有很多限定,这种限定不是说外在对你的限定,或者是时代对你的限定,或者是你的智力本身对你的限定,而是你受制于对象本身给你的限定。这种限定是无形当中的,但它的确存在。你比如说评说这个对象,可能他的作品——他的诗作、他的小说,或者他的剧本,本身就是在一个框架里面,你无法跳跃出这个框架。你当然可以在哲学层面或者社会学层面上予以延伸,但是你必得依据它的根基去扩展;它像一个石头砸下去,涟漪是在水面上,你不能突破这个圆,那么你就是受到了限制。但是诗它就像一匹野马,它在荒原上,可以奔跑到无限的领域。你这句话写出来,这个诗句写出来,下个诗句谁也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有时候你突然写出了第二句的时候,你自己也很意外。这种不断产生的意外感,可能正是让我们感觉满足的一个原因。
李壮:到具体的诗歌文本上来谈一谈吧。您的诗歌一直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其实围绕“抒情”这个概念,当下诗歌界一直都有争论。有的人认为,抒情本身就带有农耕文明的印记,在当下语境中,诗歌把赌注押在抒情上会变得危险。这其实是在怀疑抒情在当下诗歌写作,甚至整体性的文学经验表达中的有效性。另一些声音则表示,我们不应该以一种生物进化式的思维来谈论文学,不能说时代变化了,有一些东西就一定会过时,因此,把抒情与现代性对立起来并不合适,重要的是要找到抒情与当下语境的合适的对接方式。对此,您怎么看?
何向阳: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把抒情跟农耕文明画上等号,其实比把诗歌赌注押在非抒情性上更加危险。抒情的确带有农耕文明的印记,但是我并不觉得只有农耕文明才能抒情,同样我也不觉得进入工业文明比农耕文明在文学上就更先进,或者说与农耕文明相并的抒情就是一种落后的标志,而在诗中抒情就变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事。我对这种贴标签的理论取向一直不太习惯。对个体而言,我认为恰恰是需要瓦解掉这样一些理论的定论。我的诗歌确实带有很大的抒情性,因为爱情诗居多,对人的爱情,对自然的爱情,对所遇事物的爱情,免不了抒情。但是不是能说,现代性的东西,就要跟抒情性对立起来,现代性是抒情的反面?好像不然。至于说要找到抒情和当下语境合适的对接方式,我觉得抒情是诗的一种发源,是一种永恒性的东西,它不随着时代的终结或者文明形式的改变而变化或者终结。而且现在我们也很难说农耕文明已经在中国终结了。
况且,即便农耕文明有一天在中国终结掉,抒情也不可能全部被现代性或者被某一种其他的什么性全然取代。因为它是一种根源的、起初的东西。比如说我读沃尔科特,读他85岁新出的《白鹭》,抒情和现代性兼具,他对海的那种爱,对于生死的认识,写得非常优雅迷人,但里面又具有很强烈的一种现代性。这两个东西都在诗里得以体现,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现在我们一谈到抒情就觉得低级,一谈到现代性就觉得很深奥、高端。但是我觉得像沃尔科特这样的诗人就已经超越了这些,他不纠缠于这些其实仍是形式上的高低,超越了时代。你说他活在20世纪,那其实是抒情慢慢兴起而又消失的一个时代。二十世纪末期又是一个现代性兴起的时期,那么现在这个二十一世纪又是后现代性的开始,是消解现代性的一个时代。他的诗能穿越这三个时代,又使这三个时代在诗中都得到体现。而且他的诗音乐感、节奏性都特别强,这个诗人很了不起。
李壮:很多时候,线性历史观或者单一的美学胃口对文学是没有好处的。辛普森说,美国诗歌需要一只强大的胃,能同时消化月亮、煤、橡皮和铀。这话对美国合适,对中国也合适;侧重“橡皮和铀”可以,回返到“月亮”也未尝不可。当各异的元素同时汇聚在同一个诗人甚至同一首诗中的时候,说不定最能够显示诗人的活力和力量。
何向阳:我很喜欢的一个芬兰女诗人,索德格朗,她的诗我觉得就是这样。她被称为北欧现代性的开创性的诗人,她生活在十九世纪,死于二十世纪初期。她的诗本身确实有很大的抒情性,她先用德语创作,然后又用瑞典语创作。当然她的诗也就只有二百多首,现在我们国内全集也出来了。但是她的抒情和现代性,好像是很难给她剥离、分裂开来的。比如她的《冷却的白昼》中,有一首就是“临近黄昏时,白昼冷却下来,吸取我的手的温暖吧,我的手和春天有同样的血液。”这句,很精彩,“我的手和春天有同样的血液,接受我的手,接受我苍白的胳膊,接受我那柔弱的肩膀和渴望,这感觉有点陌生,你沉重的头靠在我的胸前,一个唯一的夜,一个这样的夜。”我觉得它既现代又抒情,是吧?我的手和春天有同样的血液,这写出来就很现代,但是它又是让人感觉很抒情,我觉得它是女性对于事物的感知,跳动很大,切换得也特别快。比如她这首诗的第四节,“你寻求一只花朵,却找到一颗果实,你寻求一汪泉水,却找到一片汪洋,你寻找一位女人,却找到一个灵魂,你失望了。”这就是象征性特别强烈,意象感也很强,但是它确实又不乏抒情性。你找一个女人,但是你却找到了一个灵魂,你总是找不到你要找的那个东西,你找到的东西可能总是多于你要找的,但是你还是失望,你还是不满足。你本来要找花朵,最后找到果实,本来是多于你要的东西;你要找一汪泉水,但是汪洋给你更多了;你找到女人了,女人很具体,可能是肉身的东西多一点,但是你找到一个灵魂,灵魂更高贵,但是你还是失望……我觉得这里头寓意很多,也有抒情的底子,但是它又跨越了那个具体。再比如她的《我的灵魂》,她一直在关注灵魂,“我的灵魂不会讲故事,不懂道理,我的灵魂只会哭笑,扭紧它的手,我的灵魂不会记忆和防御,我的灵魂不会考虑和赞许。”都是很单纯的东西,跟故事、跟道理都很远,有时只是人的一种哭笑,灵魂也是很朴素的一个灵魂。现在我们写诗,好像很难再去写这样的诗了,我的灵魂怎么样,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四个排比句全是“我的灵魂”,这样写出来好像特别像我说的《青衿》里头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诗,就是感觉不会修辞。但是她这首诗确实是已经成为了诗歌史上很经典的作品。包括她写美都是这样写,“美是唤醒命运的微风,那扇子轻轻地摇动。”这个已经非常现代了,那种切换、组合,语言的修辞能力也非常强了,虽然是译诗,但是我觉得也能体会到它那种原创的美。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抒情的一种理解。
当然我觉得最好的诗肯定是各种元素都能够具备,它不是单纯的小女孩的或者是少女的一种抒情,那样一眼见底的东西,而是兼具对整个时代的一些观察,包括一些情感问题,一些现代人心灵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诗了。当然要写出这种诗还需要人生的历练。诗,是人的整体的世界观的体现,语言只是传达这一感知的外在“工具”。
李壮:您这一组《晨暮间》,在形式上很有特点。每个诗行都不长,诗句被您切分得很细很短;一眼看去,您的这些诗作在外观上多是高挑纤细,像美人侧影,又像《诗经》里的蒹葭。这样的外在形式同时也塑造了您这组诗歌内在的节奏甚至音调。这是您有意为之吗?
何向阳:因喜欢音乐,所以你说的这个形式的节奏感的感觉,可能确实存在,但也不是我刻意,它可能自然而然地渗透在诗歌里面。比如它的节奏、它的乐感,我觉得诗而能歌,这好像是一种特别好的、特别美的一种感觉。但是后来诗和歌慢慢分离了。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会下意识去找回一种东西,找回一种它原来的、和谐的东西,就是有别于散文、有别于其他文体的一种语言形式,甚至有别于译诗的文体。因为译诗经过翻译之后,语言的节奏可能还有所保留,但是语言的韵律可能会遭到一些破坏。当然更有别于我现在从事的评论的这样一种形式,因为评论上世纪八十年代受影响于欧美文学,那种译文句子都特别长。我的评论,如果跟这个诗对照来看,评论的文字,甚至能够三行没有一个标点,转来转去。有时候我父亲看了我的评论开玩笑:您的中心词在哪呢?你都把我们绕进去了。他说你受翻译的影响太厉害了,应该找回一种很简洁的东西,要用简约、爽快、干净的语言,去写出你想写的那些句子。但是在评论当中我很难做到,一方面受八十年代欧美评论的哲学翻译的译丛的影响,可能还是有些痕迹,要清除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一方面也是想说的太多,非把道理讲清楚不可的心理使然。但是在诗当中我觉得可能会找到一种回归,找到一种语言形式的东西。
说到短句。其实我诗里的短句,有时候在写了一首、写出来感觉很不错的时候,这种节奏感突然就找到了。比如《此刻》:“此刻,你指给我看的大海,已经平静下来,此刻,鱼翔浅底,礁石突立,此刻,你不在礁石之上,你在哪里。”“此刻灯光转暗,车厢沉寂”,最后“此刻,你不坐在我的对面,你在哪里。”后来又到了坐高铁的时候,从南京到合肥,我当时是拿了一张纸在车厢里写诗,句子不约前来:“此刻你不在我的纸上,你在哪里”。它是一个回环往复的,就像一首歌一样,落脚于“此刻”,回归到“你在哪里”,等于是一个时间、一个空间的交替变换。在你进行一种语言的尝试之后,你会感觉它有一种音调,有它自身创造出来的一种乐感,我觉得挺有意思。
比如我之前一直在创作的一组诗《蓝色变奏》。整理《青衿》的时候我就尝试着放一些“蓝色变奏”进去,就是写一些短诗之后,总是有一个组诗,大概是四首到六首这样,叫“蓝色变奏”。蓝色,Blue,布鲁斯,它是一种忧郁的变奏。穿插进去,青春当中的一些快乐、一些单纯之外,好像还有另外一个音调进去。我明年要出一个新诗集,是这几年写的,中间总是有一个疑问的《谁》。这种间奏或许也是一种音乐的?人到中年,可能疑问多一点,问题也多了一点,这个“谁”其实是对自我主体的一个角色之问,或者对对方的一个身份之问,或者对自我被双重的身份撕裂的时候一种分离之问。大概七八首诗,短诗、长诗之外,突然有一首短诗进去,这个《谁》,就像一个钉子一样楔进去,楔到木头里面。这样会使整个诗集里头也有一种节奏,这种节奏,刘琼对《青衿》的评论中注意到了,让我感到她作为一位评论家的敏锐。除了在单纯的一首诗中完成这种音调感之外,整个诗集我也能够做到这点,有一个自我的、回环往复的一种东西。像《蓝色变奏》,九组诗,在《青衿》里面,已然变成了一种结构。评论界还比较认可,因为这些诗本身也是写作于八、九十年代。在不同的阶段,总是有一种蓝色的、忧郁的变奏穿插在里,它使青春里面又有了一种苦涩的味道。其实有我青春期的一些影子在里面。
李壮:您说的这些忽然让我想到爱伦坡,他有一个观点被波德莱尔翻译成法语,深刻影响了法国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爱伦坡认为,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形式”常常成为诗歌的起源,诗歌创作过程的开端是一种“音调”;它形成了构成一种言说的预感、一种“无形体的氛围”,然后具体的词语甚至内容意义才被召唤而来,被选择、组合进而构成一首诗。这说的是语言形式对诗歌写作的原发性推动力。您的诗歌写作中是否也存在这种强烈的形式推动感?
何向阳:我尽力做到。诗和歌,现在我们分开了。诗人对歌词不屑一顾,觉得那都是大众的。但是我觉得有些流行的歌曲,比如汪峰的一些歌词里面,很多是有诗意的,我很喜欢。他那种游吟诗人的调子,包括许多思考,其实有挺强的时代感、现代性。形式元素背后其实有传播功能,现在很多诗人在拒绝诗歌的传播功能,我觉得这其实是有一定损失的。因为你不能够轻看任何一个听众,也不能觉得诗人高高在上、任何听众都不理解你,总是把自己囚禁起来。歌曲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能产生一些共鸣;但是诗由于一种自我封闭,可能已经割裂、排斥了很多本来能够成为你的共鸣者的读者。诗歌的形式感、音乐性,确实能够推动它的传播。当然传播较之创造仍属第二位,关键是你要找到并确认自己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时代的共在性面前,它是独有的。后一点对一个诗人而言或是难的,但又是必须不可的。
李壮:您的诗歌在意境、节奏、意象,甚至具体用词上,都很有古典意趣。您是否从中国古典美学中汲取了很多养分?我们都在讲回归本土美学、挖掘传统资源,那么在您看来,这种传统如何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中实现具体的美学转换?同时,您的这组诗也让我想到不少西方经典诗人。例如《谁》的后半部分让我想到辛波丝卡,《你》的某些细节让我想到里尔克《严重的时刻》,您的诗在整体情味上似乎也有几分聂鲁达的影子。顺便谈谈您的阅读喜好和影响谱系吧。
何向阳:其实从理论上来说,哪个诗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一个谱系,这是“影响的焦虑”。谁都希望自己本身就是开创者,但事实是有一个阅读和影响谱系在,并不影响一个诗人的质量。当然就我而言,我的谱系还不是从辛波斯卡开始。辛波斯卡、里尔克也就是这二十多年来热起来的吧,聂鲁达的时间长一点。他们都是我喜欢的诗人,但如果捋一捋线头的话,最早影响我的可能还是白朗宁夫人,她的《爱情十四行诗》。最早我记得是方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她15岁摔断腿,39岁遇到了白朗宁,写诗,结婚,奇迹般地站起来,50多岁去世。白朗宁夫人写十四行诗,格律形式要求很严的,不容易仿写,然而她对爱情的歌赞、坚贞,还是影响我很深。包括传统诗歌,《诗经》当中我觉得也有一些,直到李清照,她前期的诗,对爱情的那种抒写,给了我挺多影响。后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狄金森。她是一个很特别的诗人,她对于事物的细小、幽微之处特别关心。一个诗人,她跟小说家不同。小说家关心人的走向,或者关心事件的结果、过程,关心戏剧的起伏。但狄金森关心特别幽微的地方,我特别喜欢她在最细微处去着笔的那样一种微观内省的气质,这个气质跟我自己也比较像。咱们走在街头,你能一下指出哪个人是诗人、哪个人写诗吗?好像很难。但是诗人身上的确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那种内省的气质,甚至是见花落泪的那样一种东西。有这样一种气质的人,活得才更加充实、真切、优雅、高贵。狄金森的诗,“没有任何伤口和血迹,却在意义隐居的深处留下记忆”。其实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承受了很多,苦和幽怨,很多是你看不到的,有时候恰恰是在看不到血迹的时候,你的心才最难过。这些都能在狄金森的文字当中一点点地体现。另外她写战场,狄金森写战场也跟其他人不同,她是一个女性的角度,她写那些战场的战士:“他们雪片般地落下,他们流星般落下,像一朵玫瑰的花瓣纷纷落下。当风的手指突然间穿划过六月初夏。”这个战场就写得让人感觉特别与众不同,没有战场上那种厮杀的、血迹斑斑的场面,而写那些人像雪片一样,流星一样,玫瑰花瓣一样,都落下了。“当风的手指突然间穿划过六月初夏”,这个句子你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她是对死亡、对生命特别有感觉的一个人。尤其是她对死亡的感觉,对幽微之处的这种敏感,我觉得好像很少有诗人像狄金森这样,感受得那么深入、那么强烈。在白朗宁夫人、狄金森之后,第三个影响我的就是索德格朗。索德格朗对生命的感觉是很强烈的,最近我在读她的《我必须徒步穿越太阳系》,她的思维跨越是很大的。刚才你说辛波斯卡,辛波斯卡我也很喜欢,她的《一见钟情》等许多诗写得都非常棒。有意思的是,辛波斯卡出生于1923年,索德格朗去世于1923年。基本上辛波斯卡算是二十世纪的诗人,索德格朗主要还算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是东欧、一个是北欧。你还提到聂鲁达。我最早是从父亲的书架上读到聂鲁达的诗,当时还读了惠特曼,我都挺喜欢。聂鲁达写给他爱人的那些情诗特别美,去年上海诗歌之夜我还朗诵了他的《I Like For You To Be Still》,他对爱的书写特别具体,是灵魂肉体一起喜欢,特别坦率、真实,特别强烈的一种感觉。但是跟聂鲁达相比,我好像更倾向于里尔克。为什么喜欢里尔克呢?因为他的气质类型跟狄金森近似,看似很柔弱,但是写出来很有力,而且他的诗歌确实是带有难度的一种写作。里尔克也属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诗人,1875年到1926年,跟索德格朗基本上同时代。索德格朗1892年到1923年,31岁,里尔克活到了51岁。他的《杜伊诺哀歌》对我影响非常大,我有段时间每次出差都带着《杜伊诺哀歌》的节选本。第一句就是“如果我叫喊,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听到我”。第一句就把我震了,“即使他们之中有一位突然把我拥到他胸前,我也将在他那更强大的存在的力量中消失。”……这些句子感觉都是天外来客。里尔克的一生跌宕坎坷,基本上居无定所。但是他写出这么有难度的诗歌来,现在你要让我写,我确实是写不出这样的东西。“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听到我”,这些句子好像很难再得。这首诗他写了十年,写完《杜伊诺哀歌》之后身体越来越差,好像是精力全都用在这上面了。其他像《沉重的时刻》那些,当然也都不错,但是我觉得《杜伊诺哀歌》确实是他创作的顶峰,甚至也是德语诗歌的一个顶峰。此外我也喜欢艾略特,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我都非常喜欢,我的许多文章当中都引用过他的诗。
梳理一下,我喜欢的诗人好像大多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他们多数都生活于十九世纪。欧美的文学可能在我们当时的阅读当中也是比较重头的,这些东西当然会丝丝缕缕地进入到诗句当中去。俄罗斯文学也读得很多,但在诗歌写作层面,对我的影响好像倒不是很大。我喜欢的还是那种优雅当中又有内省的东西,以及那种从微观出发的对生命本身的观照。
李壮:爱情主题在您的诗歌写作中似乎格外引人注目。与之相关的是时间主题:爱情与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爱的感觉在瞬间的爆发、在漫长时间中的延续,对时间体验的扭曲,甚至是对时间的虚构,不同的关联方式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而时间体验的极端形态便是“生死”。这一主题也是您在诗歌中经常触及到的。能否简单谈一谈这几个主题?
何向阳:大家都说我在写爱情,其实要说爱情是否针对于谁,他是一个具体的人吗?我也很难回答。前年在海口知与行书局签售诗集的时候,主持人孔见也提出来说,你这个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倾诉对象?我说好像有也没有,具体与抽象之间吧。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爱情诗都写给谁了呢?好像也很难说出一个具体。但是真没有吗?也不是。我很同意你说的这种抽象的感觉,他是一个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就是说诗里的“他”其实是一个内化的“我”——其实对方,这个爱人,“你”,其实就是另一个“我”。我赋予了他很多品质,对他倾诉,给他我的爱,在这个世界和我的内心当中给他一个位置,他就是内化的另一个我,是穿越时空无处不在的一种东西。这其实就是一种自问,对他者之问,其实也是对自我之问。我会想到我看过的一些电影,比如《薇诺妮卡的双重生活》。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一个我,跟这个我一起存在着。但是在不同的时空当中,这两个人从来没见过面。这个人心痛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会有感应。一个人陷入爱情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心里也会充满欢喜。我诗里的那个“他”或者“你”也可以是我不认识的一个“我”,他可能是一个男性,也可能是一个女性,当然在我的诗中,他被书写为一个男性。我一直咏叹着他、歌赞着他、追寻着他,一直想去触摸到他。因为相距遥远,或者是有某些阻隔,我们始终是在一个“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状态,但这个伊人始终是存在的。一个很美的意象吧,这种爱情不是一种对具体异性的爱,它是爱本身。具体的爱当然也很美,它能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但这种非具体的爱我觉得仍然是难以代替的。在诗里,我给他赋予了很多我没有的品质、我缺乏的性格,在他身上寄寓了很多情感,这其实是比真实的我更美的一个“我”。所谓爱情,其实是我在对方身上爱着一个理想化的自己。当然也可能起初有些诗里面,也是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比如说中学时候曾暗恋的老师、大学时候曾暗恋的对象。但是慢慢地,他就从这些具体的人当中抽象出来了,抽象出来一种特别理想的偶像化的存在,他不会让我失望,也不会让我失恋,他就是一个不存在的爱人,但确实又一直活在内心当中。我是活在对他寻找和相遇的期待当中,活在这样一个诗的世界里面、一种自我编织的美好梦境当中。很美。我觉得我写的可能更多是这样的一种爱情。
至于生死,从2013年一直到现在,对生死写得越来越多。那年在八大处,大家都爬山去了,我自己坐在灵光寺的台阶上,想轮回问题。去年春天去青岛,我们把母亲的骨灰撒在了麦岛近处的一处海峡,就是她当时指过的一个地方。我在八大处的台阶上就想到她,想到轮回,想到她和我之间的关系。《古寺》这首诗后来发在《作家》。以前生活是完整的,经历了亲人的死亡后,对于生死的思考就多了。
李壮:您的诗中往往会有一个“自我”的形象出现。不仅如此,频繁出现的“你”在我看来,似乎也可算作另一个内化的“我”。这种自我意识对您的诗歌写作来说,意味着什么?
何向阳:我的自我意识还是蛮强的。一个诗人,其实是要通过对自我形象的塑造来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我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写过一篇影响比较大的论文,叫《不对位的人与“人”》,就是写知识分子形象。中国文学为什么有史以来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形象?或者有,也不如现实中的知识分子那么有亮光,为什么?你看俄罗斯的文学当中,有一个很强烈的、多少代人都在建立的一个知识分子形象。哪怕是流亡,在苦水当中、在盐水当中、在血水当中反复折腾,最后还是能够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在呼唤中产生出来。我就想到我们文学书写中的这种“不对位”。鲁迅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但是这种形象在文学当中很少出现;小说中有没有一个虚拟的知识分子形象跟鲁迅相对位?没有。鲁迅本人也没有,鲁迅本人写过《在酒楼上》《孤独者》,但鲁迅本人最有名的、影响最大的,还是《阿Q正传》。他在世界文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流氓无产者的形象,是身在农村但已经不在土地上的流亡者的形象。中国不乏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但却是缺少一个特定的知识分子形象,当时我也在呼唤这种形象。我们文学中的诗人形象好像一直不够强大,甚至不仅不够强大,而是常常作为被欺凌的对象。西方的作品当中写诗人,不是把他作为一种挖苦的对象、被同情的对象、被取笑的对象,而是一种比较高贵的、能够承担的一个形象。但是我们好像常常拿诗人的弱点开玩笑。所以我一直想通过诗歌建立一种不一样的自我形象。这种形象当然不可能承担起一个时代的或者一个民族的宏大叙事,但是我觉得,她哪怕能够承担起忠贞的爱情,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形象。当然我们也看到,同时代的一些诗人,他们其实也在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形象体系,比如欧阳江河等人。这种形象,可能确实是要通过诗人一生的写作才能建立起来。我们现在谈里尔克,其实他是有一个自我形象在里头的。谈狄金森,狄金森也有她的一个形象,她对生死、对爱,都有她自己的明确的一种价值取向,能够用她的文字拼贴、结构一个她个人的形象出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通过自己对心灵的历练,去完成“自我”这样一种形象的建构。这也是我期待能够达到的诗歌最高境界。其实,谈及诗所聚合的形象,又能改变多少,那个通过文字传达或塑造的“样子”,不过是成就了万丈红尘中的初心,“一切刚开始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