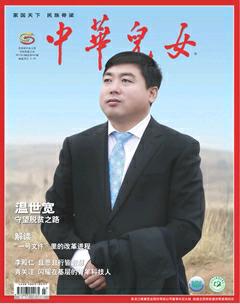辛德勇甘当匠人的学人
李肖含
辛德勇说自己并没有什么宏大的追求,只是想纯正地做人,真诚地对待学术。很多人追求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他却研究具体的问题,甘于平凡,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匠人
去年以来,辛德勇的名字出现在新闻中,几乎都少不了一个关键词:汉武帝。
2015年10月,他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制造汉武帝》,提出了传统的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源于《资治通鉴》的历史建构的观点,引来不少争论。半年多后,该书再次印刷。在严肃的学术出版物中,有这样的表现,实在少见。
两个月前,他的另一本学术专著《海昏侯刘贺》由三联书店出版。书中对海昏侯刘贺及其背后的时代进行了详细分析,而其分析的起点仍然离不开晚年的汉武帝。
“《制造汉武帝》已经正式出版了一年多,外界的争论我也看到了,非常欢迎不同的声音。”辛德勇一只手搭在沙发的靠背上,一只手端起茶杯,淡淡地说。
这里是1月6日上午的北京。雾霾仍未散去,辛德勇拉开窗帘,淡淡的光线透进来。屋子不算小,但并没有太多的家具。大部分的空间被书架占去,就连客厅的地上也堆着不少的书。定睛一看,有的竟是极为罕见的古籍。
“对我而言,历史学首先是史料学,”辛德勇说,“《制造汉武帝》一书中的细微之处或有疏漏,但我认为,书中的结论并不需要做任何修正。”
被“制造”的汉武帝?
辛德勇口中所说的“争论”,涉及到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著名问题——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其晚年有没有偃武修文的政策转变?
传统的观点认为:武帝早年征伐四方、开疆拓土,却也耗费了国力,以致民不聊生。及至晚年,武帝“幡然悔悟”,停止了对外的征伐,下诏“罪己”,使西汉的统治转危为安,并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1930年代,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指出汉武帝晚年的“轮台之诏”,使骚然不宁的民心“复归于汉室,处于动摇状态的西汉王朝幸而保全。”
其后,中国学者唐长孺同样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到了1980年代,北京大学教授田余庆发表《论轮台诏》一文,评述汉武帝一生行事,更系统地指出,武帝在其去世的前两年,大幅度转变了政治取向。而《资治通鉴》中的相关记载,正是“汉武帝‘罪己的开端”。
经过几代学者的阐发,这些观点几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定论,并获得了高度赞誉。但辛德勇却发现了其中的漏洞:“为什么北宋《资治通鉴》中所载的‘罪己诏在《史记》、《汉书》、《盐铁论》等成书于汉代的史籍中并不见记载?”“如果武帝晚年已经从‘尚功轉向‘守文,为什么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还要对当时的政策进行猛烈的抨击?”
由此“追查”开来,辛德勇发现:正是由于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采用了“语多诞妄”的《汉武故事》等材料,才使人产生了汉武帝晚年从“尚功”转向“守文”的印象。
换句话说,是司马光人为地建构了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而北宋以降,据《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得出类似结论的研究,也自然是站不住脚的了。
辛德勇将自己的研究写成论文,但辗转多家刊物,一直也没有能够发表。2014年底,《清华大学学报》的主编偶然听说此稿,马上索去,并以最快的速度一字不删地全文刊出。其后,三联书店又将该文单独出版。
此论一出,立即在学界和社会上引来众多争论。誉之者谓其目光如炬,论证严密;毁之者谓其推论过度,厚诬古人。
“上海一家报纸上的书评说我‘制造了司马光,哈哈,但文中并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证据。”辛德勇说,“近来已经发表的反驳我的学术论文,也没能对我在文章中提出的疑问给出合理的解释。”
“我无意博取他人的认同,更无意评判前人的研究。其实,我只是从一个很土鳖的问题出发,用很土鳖的方法,做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史料辨析而已。”
史念海说,这个学生我要了
中等身材,肌肉健硕,一身利落的装扮。57岁的辛德勇,看起来并不像一个“典型”的历史学者。
“我出生在内蒙古东部,少年时代做过伐木工人,一直到现在还有冬泳的习惯。”辛德勇笑着说,“你看,我这体格可能比许多大学教授要强壮得多。”
1977年夏,刚刚高中毕业的辛德勇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林场做了一名伐木工人。
那时候,山上的林场条件特别差。“大雪封山时,半个月才送一次给养。只好用冻白菜做菜,就玉米面饼子。”现在再讲起这些,他笑呵呵的。
但也有难得的休闲时刻:“每天干完活儿,大家一起睡‘地火龙——东北地区林区采伐作业时特用的一种火炕,有这么长。”辛德勇张开双臂,笑着比划着,“外面冷风呼呼的,我就点着灯,趴在被窝里看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书。”
不久后,辛德勇返城,曾进入内蒙古海拉尔市的一所中做代课教员,当临时工。当年冬天,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他立即决定报名应试。结果考入了哈尔滨师范学院地理系。
“‘文革十年,大学没有招生,结果七七级入学考试时,很多省份都误把地理系当成了文科。进校后知道是理科,当时就懵了。”辛德勇说,“我本来一心想上中文系,但现在看来,当年的阴差阳错,却使我接受了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这让我受益无穷。”
那个年头,大学里不许转系,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他便悄悄地跑到其他系里听课。无奈战线拉得太长,只好折衷妥协,选择了历史地理这个专业方向——既将就了原本的专业,又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对文史的爱好。
大二时,辛德勇便开始给国内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些老前辈写信求教。第一封信,他就写给了被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开山祖师之一的史念海先生。没想到的是,不久后,他竟收到了史先生的亲笔回信!
这让他备受鼓舞。此后,他一直与史念海先生保持着书信往来。“两年下来,竟有十几通之多。先生几乎每次都会亲笔回信,解答我的问题。”
大学毕业前夕,系里的一位老师要到陕西开会,辛德勇便托他带上自己的毕业论文向史念海先生当面请教。史念海先生看完论文后,高兴地对这位老师说:“这篇论文写得很好,这个学生,我要了。”
1982年春,辛德勇顺理成章地来到古城西安,投到史念海先生门下,攻读历史地理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大师注视下成长
初入师门,由于缺乏专业基础,辛德勇一时颇觉迷茫。史念海先生便让他从练习写读书札记入手。
考虑到东北是自己的家乡,辛德勇便选择以东北地区为对象,连续写了几周的札记。由于历史地理学以区域为研究对象,专门选择某地进行研究,正如普通的历史学者治断代史,未尝不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
但史念海先生在看过他几篇内容相近的札记之后,对他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年轻人想要在学术上有所作为,一定要放宽自己的眼界。如果画地为牢,即使毕生只从事某一区域的研究,也不大可能取得有深度的成果。”
还有一次,在讨论一个汉唐地理问题时,辛德勇引用了后出的清朝史料。结果,史念海在他的札记上郑重地加上批语:“使用第一手史料,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这是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写读书札记的方法,看似笨拙,其实渊源有自——清代的朴学家,常随时写录自己的读书心得。“后来,我才领悟到,这其实是老师锻炼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方法。”
而为了让自己的学生有良好的目录学基础,史念海又专门让他跟随黄永年读书。“黄先生每天工作多长时间,我们就要持续读书多长时间。”
“黄先生熟悉各种史料,却特别强调花大力研读基本史料,而不是刻意去找寻生僻新鲜乃至怪异离奇的其他史料。大家都知道黄先生曾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点提出许多不同的看法。其实,这就是缘于他在陈先生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更用心地细读两《唐书》、《册府元龟》等这样的一些基本史料。”
因为与黄永年先生意气相投,交往也更多,辛德勇自认是其私淑弟子,但又不敢以“黄门弟子”自居。有一次,他对黄永年先生说,自己不敢打着黄先生弟子的旗号出去“招摇撞骗”。结果,黄永年先生生气了:“辛德勇,你就是我的学生。我认你这个弟子,你居然不认我这个老师?”
“黄先生有真学问,更有真性情,哈哈,”辛德勇说,“有次先生知道我在北大开了版本学的课程,就故意开玩笑说,辛德勇,连你这样的人都登台讲授版本学啦!”“但更多的时候是鼓励:古籍版本的‘妖法,我看你也已经修炼成了。有了什么想法,要赶紧写出来发表。”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中华儿女》:《制造汉武帝》发表以后,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您之前想到过吗?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一书,源自我2014年底发表的一篇论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书中的一些观点,可能与传统的看法不大一样,因而引起了一些争论,这是很正常的。在论文发表之前,我曾把它打印出来送给一些同事和朋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后来,我把它投给几家学术杂志,但迁延了一年多的时间,也没有能够发表。2014年底,《清华大学学报》的主编仲伟民先生偶然听说此稿,马上索去,并以最快的速度一字不删不改地全文刊出。随后,三联书店又把它单独出版,印了一万多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中华儿女》:挑战权威的说法,是有一定风险的。
辛德勇:其實,我并不是想故意地挑战权威。对前人的研究,我也一直满怀着敬意。我无意博取他人的认同,更无意评判前人的研究。我只是从一个很土鳖的问题出发,用很土鳖的方法,做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的史料辨析而已。可能它与传统的观点不大一致,但你要实事求是。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做学问要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立论不妨大胆,但是否符合实际,要拿出扎扎实实的证据来。
《中华儿女》:我注意到了媒体上对您的一些批评。有的批评说,不是司马光“制造”了汉武帝,而是您“制造”了司马光。对此,您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辛德勇:你说的这些文章,我也看到了。本来,我打算写一个东西出来回应一下的,但是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也缺乏对我文章的全面的、冷静的分析,并没有多少讨论的价值。很多人以为我反对司马光,其实不是的。我非常希望他们能静下心来,认真地读一读《制造汉武帝》这本书,然后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严肃的学术文章。
其实,我的文章发表以后,已经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论文,对我的观点进行批评。但是,遗憾的是,他们也没有对我提出的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历史学的研究,涉及到价值判断,几乎言人人殊。但历史学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所有论述最要命的基础,仍然是史实的认定。在这一点上,我不认为它与自然科学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制造汉武帝》一书中有没有疏漏?我想,细微之处或有疏漏,这个我会在该书再版的时候进行修订。但我对书中的结论不做任何修正。
做个匠人,别太蹩脚就行了
《中华儿女》:我们知道,黄永年先生当年也曾针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提出过不同的观点,而黄先生的老师顾颉刚先生,更是“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您是否也在有意无意间继承了这种传统?
辛德勇:坦白地说,鼓励学生与老师商榷、讨论问题,确实是顾门的传统。当年跟着黄永年先生读书时,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说法。黄先生做研究,特别强调对基本史料的掌握,而反对刻意找寻生僻的其他史料。黄先生曾说过,他最敬重的学者就是陈寅恪先生。但是,对陈先生的有些研究,他有自己不同的看法。黄先生晚年不止一次向我讲:陈寅恪先生的有些研究太粗了,基本的史料没看,就作出了结论。当年他年轻时曾写信向陈先生讨教,陈先生还回了信,表示欢迎。事实上,这些讨论或商榷,并无损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我写作《制造汉武帝》这本书,绝不是要刻意地去翻什么案,也不是要否定前人的研究。前辈学者们的优秀研究成果自有其历史地位,自有其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所有研究,都能够终结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我认为他们的结论正确与否,一定要通过史料的检验。通过严谨的史料比较与考辨,往往可以看到其间的罅漏。《制造汉武帝》出版了以后,有人认为我在翻田余庆先生的案。其实,他们不知道,更早之前,我还对谭其骧先生在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某些重要结论提出过否定的看法,譬如关于东汉以后黄河的长期安流问题。后来,谭先生的弟子曾对我说,你的质疑是合理的,结论也是正确的。
《中华儿女》:曾有海外的一些学者认为,陈寅恪先生的某些研究,比如他写作《柳如是别传》,事实上是他晚年的“心史”。您怎么看?
辛德勇:陈寅恪先生是史学大家,同时有很强的贵族气息。他对学术有着很高的追求。田余庆先生对学术也有很高的追求。但我认为,正是他们有时跳过诸多具体的细节而去做宏大的追求,反而妨碍了他们某些研究的深度。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与我们不同,但其中的某些疏失仍是不可接受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指出来。每个人都会有缺陷,对于他们,我们不要神化,也不要过分地回避,那样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至于《柳如是别传》,我没有读过,不能发表看法。
《中华儿女》:开宗立派,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是许多学者的追求。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您有着什么样的自我期许?
辛德勇:我学术基础很差,懂的东西很少,欠缺很多基本知识,所以,并没有什么宏大的追求,只是想纯正地做人,真诚地对待学术。很多人追求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我却研究具体的问题,甘于平凡。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匠人,尽量做得好一点,不太蹩脚就行。对于我来说,学术研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与错,要交给学术史。至于学者是不是要追求开宗立派,我认为,这要看时代的条件是否足以让你开宗立派,还有你是否真的有那个能力和够那个分量去开宗立派。否则,硬是要建立某种体系,如同揪着自己的头发想要升天,实际恐怕很难做到。
责任编辑 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