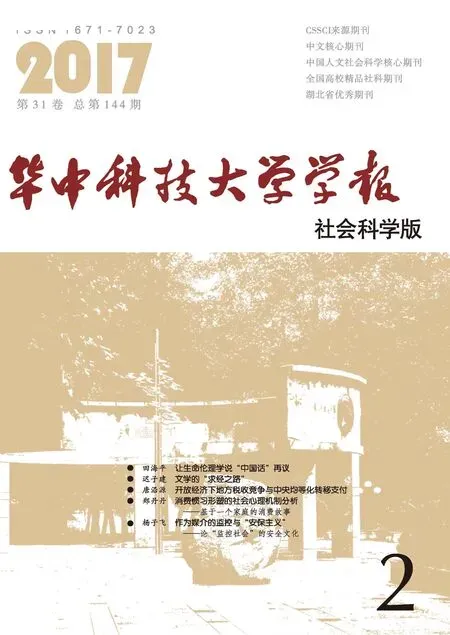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再议
田海平,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再议
田海平,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生命伦理的探究方式,凸显了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基本价值诉求,即中华卫生文明的“道-德”价值图式,其可表述为:传承中华文明之“道”,彰显中华卫生之“德”。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在话语体系构建上,需要以两个重要的突破为前提:一是推进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拓展”;二是展开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这反映在当今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构建及其研究进路上,也表现为破解“应用论-建构论”对峙的难题。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必须瞩目于“应用论-建构论”之间隐含着的关联性方面而非分歧性方面,在相对宽广的历史视域中界定中国生命伦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方向。
生命伦理学;中国话;认知旨趣拓展;问题域还原
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总是会被打上鲜明的时代性标记和本土化(或民族性)印记,因而呈现为一种众说纷纭的样态。当今天人们讨论“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堕胎的道德性”以及与“安乐死”、“克隆人”等有关的生命伦理论题时,或者探讨儒家生命伦理学的重构和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的建构时,又或者更为一般性地论证生命伦理学应遵循何种道德原则时,必然遭遇一种“元问题”层面的诘难:即,这些表面上互不相关的话语,意味着什么?这就涉及对“话语体系”、“语境”进行分析和澄清。此时,我们有必要问:我们到底要让生命伦理学“如何说话”及“说什么话”?
在这一问题向度,这里所要言说的生命伦理学的语言或话语,既需要面向全球化时代诸文明难题,又要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课题,尤其需要面向当今日新月异的卫生健康领域的伟大变革,以及生物医学、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棘手的伦理道德难题。为此,本文再次强调指出,我们仍然有必要重提并澄清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近年来,笔者注意到,生命伦理学的原则主义进路和“应用伦理学范式”在“话语体系构建”方面陷入了一种普遍主义“焦虑”之中,同时也激发了一种文化特殊主义(通常以“建构生命伦理学”的样式出现)的“纠偏”的尝试,因而呈现为一种“应用论-建构论”之争的态势。其突出的征候之一,就是把西方普遍主义的理论话语引以为原则论证或应用性探究的学术话语资源,进而产生了我们提到的“生命伦理学如何说‘中国话’”的问题。笔者在《道德与文明》(2015年第6期)、《吉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0期)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及其‘形态学’视角”、“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问题和挑战”、“生命伦理学如何说‘中国话’”等论文,从不同的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这些论文。本文“名”为对这一问题“再议”,是继“生命伦理学如何说‘中国话’”(《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0期)一文后重提该问题,实际上是将前此讨论中提出的观点尽可能地以一种“总结”的形式进行简明扼要地概述,以更好地就教于学界,推进该问题的探讨。
一、文明之“道”与卫生之“德”
生命伦理的探究方式,凸显了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基本价值诉求。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彰显中华卫生文明的“道-德”价值图式。概而言之,此价值诉求可表述为:传承中华文明之“道”,彰显中华卫生之“德”。
我们总是在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提出并面对生命伦理学问题。因此,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在文化、历史层面,必然涉及一种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产出”的动机和前提反思。略而言之,这里存在一个根本之诉求,即透过生命伦理的话语方式来表达吾人之“如何安身、何以立命”的文化政治学或生命政治学意义上的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我们需要从一种文化进路上,特别是从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上,思考生命伦理学的语境前提或历史前提。一旦我们从这一方面进入生命伦理学问题,就会赞同恩格尔哈特做出的如下判断,他说,“这样的生命伦理学的语言是与俗世的程序生命伦理学的语言截然不同的……这样的背景下,道德是一个真理,它超然于圣人的体验,并牢牢地与历史嵌合。”*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谈到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出现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与“俗世生命伦理学”之间的两歧,特别是它们在话语方式上的异质性分裂。这一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亦有比较鲜明的表现。引文参见:(美)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孙慕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8页。借助这种看问题的视角,我们不难发现:在“与历史嵌合”的“道德真理”的向度内,生命伦理学的价值图式在中国语境中的现实展现,它既不同于西方传统基督教背景下的生命伦理学,又不同于西方现代自由主义背景下的生命伦理学。它要求我们从一种文化历史的语境视域进行“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的历史还原,以反思生命伦理学的文化根本和精神命脉。
另一方面,虽然不同文化类型或文明体系在其文化历史语境中都开出了“医治受伤之心灵(或灵魂)”的“灵丹妙药”*例如,恩格尔哈特指明,传统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根本旨趣,“并不局限于考量善、正当、德行。福音书的语言并不是善、正当或德行的语言。尽管我们参与的不仅限于病痛、顽疾与健康护理,还参与罪恶和道德的毁坏;因此,传统基督教生命伦理学首先要关心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去追求圣洁之地,应该如何去追求天主之国。”[1]396,但“身体与心灵”的辩证法表明,从“灵魂转向”到“身体转向”,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不论是基督教文明体系还是儒家文明体系)在其现代化的文明进程中都会经历的道德形态过程。这并不是说,现代性不需要照料灵魂或者不致力于灵魂的拯救,而是说它把“身体问题”置于一种优先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与身体问题相关联的现代医疗卫生及保健的专业化发展和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各种生命医学伦理的挑战。在这个层面,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就是要搁置具体道德内容上或具体道德立场上的众声喧哗的争议,将探究的重点聚焦于一种程序合理性的共识,以寻求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则。当然,达成共识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有多少宗教,有多少关于道德、正义和公平的理解,就可能存在多少种对生命伦理学的俗世的理解。这导致的效应是:对于医疗资源分配问题,我们既无权威理论和恰当说明,也没有被普遍接受或公认的论证;对于堕胎、保健分配、安乐死也无法达成普遍一致的公认的主张。“……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良善生活和正当行为,没有一个富于内容(content-full)的、普遍接受的界定。关于如何着手解决这一困难,并建立一个规范的富于内容的伦理学(content-full ethics)和与之相适应的生命伦理学,也没有一致意见。”[1]68生命伦理学在具体内容上产生的歧见和异质性话语,带来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共识坍塌”的危机。在这个问题向度,生命伦理的价值图式在道德世界观上的体现,要求我们从形式合理化视域或程序正当性视域进行“问题域”的逻辑还原,以思考生命伦理如何应对或求解普遍原则之论证及其应用的难题。
当然,今天高新生命技术(包括基因技术)、纳米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深远的伦理挑战和法律难题。高新生命技术的发展遵循“支配对敬畏的绝对胜利”。它不仅仅构成了现代人之“生存”无法摆脱的“座架”,还支配着从身体到心灵、道德和情感(例如在脑技术或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中所展现的那样)的领域。高新生命科技通过对基因、信息、细胞(或神经)进行操纵,发展出一种全面技术统治。在这个层面,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必然在关涉人性之本质、人格之尊严、人类自主性之内涵等实质伦理问题的理论诠释、实践治理和难题求解等论题,进而强调从实践智慧和实践理性视阈进行认知旨趣的实践还原,以探究具体情境中伦理难题的求解之道。
以上三方面涉及生命伦理的思考方式或探究方式在文化取向、原则取向、问题取向(或难题取向)上的分殊及其话语方式的异质性分布。不难看到,它同时也特别地凸显了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基本的价值目的之诉求。
一方面,就文化根源而论,我们当然不能脱离中华传统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家园。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就是要让生命伦理学传承中华文明之“道”。
毫无疑问,我们总是从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中产生“生命伦理”的思考方式和话语方式。中国传统的哲学和文化(包括宗教、艺术、政治、法律等方面),是由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历史性伦理实存及其文化价值核心产生独具特色的理论话语和生命道德智慧,进而对卫生文明、生命政治、身体保健、医德规范、生死问题等创构了一套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生命伦理的精神资源。这是西方生命伦理学不能完全理解、也无法全面、准确地呈现“生命”和“伦理”以及“生命-伦理”内在关联的体系。我们必须面对或正视我们自己的生命伦理学的文化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方面,描述中华文明体系中“生命”和“伦理”如何结合成为一种伟大文明进程的“生命伦理”之“道”。
另一方面,就道德现实而论,我们不能脱离人口意义的医疗卫生和保健的现实生活世界。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就是让生命伦理学关注当下中国生命伦理的医疗卫生现实,以彰显中华“卫生”之“德”。
不可否认,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构建不能脱离中国语境的“卫生”之“德”或保健之现实。“卫生”一词在汉语语境中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日常用语,它的原义有“护卫生命”之义。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要面向当代中国语境,讲述中国医疗实践和卫生保健的故事,探究和谐医患关系的建构途径,解决中国医疗民生问题,求解人口健康和医疗公正的伦理难题。其重点应放在其现实层面的“保健”、“卫生”之“德”的关注上。在当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变革和卫生健康革命的全面展开及医疗技术进步的宏阔背景下,重构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话语。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卫生美德论述只有转化为一种现代性道德话语,融汇进“现代医生-医院体系”的道德形态之中,并在精神实质方面完成现代性转换,才具有普遍性并焕发生命活力。因此,在中国语境的现实性维度,我们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和文化融合的趋势,引入“和而不同”的伟大智慧,汇聚全人类的良知和智慧,只有这样,才能让说“中国话”的生命伦理学呈现为一种具有普遍的世界性意义的中华文明之“道”和中华卫生之“德”。
二、“认知旨趣拓展”与“问题域还原”
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在话语体系的构建上,需要以两个重要的突破为前提:一是推进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拓展”;二是展开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
(一)推进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拓展”
这里所说的“认知旨趣拓展”,是指从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视角出发拓展生命伦理学的知识谱系、话语形态和思想类型,目的是要摆脱过于“西化”的应用伦理学范式对生命伦理学的那种“窄化”的理解。这是从认知旨趣层面寻求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解范式进行突破,以利于进一步揭示并阐扬生命伦理学的(不同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性内涵和中国道德形态之特质[2]51-65。
就一般意义而论,“认知旨趣”在生命伦理学领域似乎预设了一个“提出问题(或难题)-解决问题”的“技术路线”。然而,与专门具体的科学领域的认知旨趣不同,生命伦理学是一个自身充满矛盾的领域,以至于它甚至都不能清楚、明白地表明:如何界定可靠的生命伦理学的专业知识,以及如何鉴别确定不移的生命伦理学内容。这使得生命伦理学的专业领域及其专家系统并不严格,而仿佛是一种力图穷尽“跨界”之可能的“杂烩”。它往往根据提问者的提问而给出相应解答。这使得它所给出的答案总会牵扯众多的学科领域和一些长期存在的根本分歧。比如,生命伦理学家并不简单地告知由论证得来的知识——如“堕胎就是杀人(或杀害胎儿)”,他们(她们)还会指出,禁止堕胎的法律由于强迫妇女屈从于违背其意志的律令(不准她们堕胎)而违犯了其基本权利。于是,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由于充满了“事实-价值”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的道德框架的制约,且在不知不觉间,将“认知旨趣”从认知领域扩展到“价值域”或“道德域”。
这种“认知旨趣拓展”典型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取决于伦理学本身的发展,如果一种文化或文明体系中的人们不知道何种伦理和道德是指导其生活的准则,就不可能给出可靠的生命伦理学建议;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引发重大道德难题的生命伦理学问题,人们更希望通过认知旨趣从知识域向价值域的拓展,来引发异质性观点和见解的实质性对话和协商,从而推动医学层面的生命伦理进一步拓展其认知旨趣,以面向文化层面的生命伦理。
由此,“认知旨趣的拓展”负载着一个更为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就是以尽可能包容的思想姿态和尽可能促进合作的争辩性商谈的形式,去理解“文化他者”,并以这种方式促进文化生命伦理学层面上的自我理解。“认知旨趣的拓展在一些重大生命伦理议题上(例如,性行为的意义,生殖干预的正当性,稀缺保健资源的分配,器官移植的道德合理性,临终安慰和安乐死,等等)尽管难于达成共识,但是,由于它强调在跨文化条件下直面人类道德复杂性或道德多样性的现实,因而有利于从一种文化诊断或文化理解的意义上通过促进对话商谈和比照互勘而促进价值扩展。”[3]因此,生命伦理学在话语体系层面,要自觉地意识到它的文化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特性,反省其与特定人口形态、人伦形态和身体形态紧密相关的文化政治实践或生命政治实践。
就生命伦理探究的中国语境而言,中国人生活于其中的医疗生活史、疾病史、身体的历史和医疗制度的历史构成了中国生命伦理学建构的基本历史图景。这即是说,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拓展”要体现中国价值观的道德诠释的基本诉求。这从反面进一步表明,认知旨趣拓展并不回避西方启蒙现代性带来的挑战,但它在一种价值拓展的意义上要求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借鉴、引入、应用西方话语的各种尝试虽然会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但不能替代能够体现中国价值观的伦理话语体系和道德形态论述[2]51-65;而任何传统重述的尝试(或传统的重新发现)和语境回归的努力,必须有助于从一种原始生存经验和本源生命深度上寻绎文明之“道”,并具体地呈现为一种现实的卫生保健之“德”。
(二)展开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
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拓展”,在具体的方法学进路上,是指从文化传统的溯本还原和医疗生活史重构,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进行梳理,以从文化历史的进路、理论逻辑的进路和实践难题的进路拓展其知识谱系、话语语境和思想类型。因而,内含着一种“问题域还原”的方法学意识[4]。
当今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诸种论辩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前提性探究的工作,即在进入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之前对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进行还原和澄清,以避免生命伦理学的争论出现话语形态上的不可通约。事实上,由于忽略对生命伦理学的问题方式进行反思,人们很少关注“问题域”的构成。因而,很多时候争论各方并不清楚何以会争论不休,这使得生命伦理学论争经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不同学科背景或文化背景的学者们,在生命伦理学的诸论题上,似乎除了展示分歧之外便无所作为了*麦金太尔指证: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论证道德的诸种努力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除了展示分歧就似乎无所作为了,他称之为“双重困境”,即现代伦理学理论之困境和现代性道德之困境。我们看到,在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各种主题论争中,遭遇到类似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困境。。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的“问题域还原”的方法,就是主张面向不同学科之间、不同文化传统之间以一种对话形式和关联方式对构成生命伦理之问题的方式进行跨界沟通。其主要目标在于寻求形态学视角上的理解范式之转化,其基本进路就是:在理论、思想、话语的前提上通过问题域之“问”使人们获得面对道德分歧的引指。
“问题域还原”是对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以清理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或者“不构成问题的问题”。如,“人权”是否构成儒家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就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产生了对儒家生命伦理学进行“问题域还原”的重要课题。“问题域还原”的必要性在于,它通过对构成问题的语境条件进行前提批判,并由此进入生命伦理学跨学科条件和跨文化条件下的形态构成论域,进而在一种道德形态学视角下展开与人口健康、人伦关系和身体政治有关的道德维度。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域还原”的方法是一种切近于从道德形态学视角研究生命伦理学的进路。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它包括历史、逻辑和实践三个层面的“问题域还原”。从“历史还原”的视角看,西方话语体系无论以何种标签的“普世”形式面世,它都不能够全面、准确地呈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谱系和思想脉络,无法替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实践和语境回归。从“逻辑还原”的视角看,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逻辑(包括它所坚持的道德原则论证)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印记,它或多或少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谋划。原则主义进路的生命伦理学所标举的普遍主义价值承诺,在理论逻辑上隐蔽着某种西方中心论的陷阱,需要中国生命伦理学以逻辑还原的方法破除这种普遍主义的“迷雾”。从“实践还原”的视角看,生命伦理学必须应对由大数据、云计算、高新生命技术, 特别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所带来的生命伦理挑战,不能脱离自身的文化信念和价值基础去面对生命伦理学的棘手难题,而必须在问题域还原的基础上回答“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问题。
“认知旨趣拓展”和“问题域还原”表明,不同的“文化景观”和“问题方式”开启并面对极为不同的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和难题,这在“知识脉络”和“问题构型”上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形态的生命伦理学与具体问题(或难题)的生命伦理学之间的异质性断裂。于是,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就是要打破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一般”和“科学话语”(特别是与之相关联的“科学项目”)之“具体”之间所预设的一致性。二者之间的不一致所形成的张力,并不影响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的文化价值诉求。相反,它通过区分不同层次的“问题域”,使得生命伦理学在界划理论分析与难题治理的功能分域中,既保持对“文化景观”的图景构画或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在价值姿态上的诚实性,又保持对具体问题应对和伦理难题治理在道德敏感上的开放性。
三、破解“应用论-建构论”对峙的难题
当今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构建及其研究进路,受到两套相互对立的话语及范式之影响。第一种是“应用伦理学”,准确地说,就是“应用论”的生命伦理学范式。第二种是“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可以称之为“建构论”的生命伦理学范式。两者的差异非常鲜明,甚至可以说是两套全然不同的生命伦理学话语和范式,构成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中互不相容的“应用论-建构论”的难题。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必须从“认知旨趣拓展”和“问题域还原”寻找突破口,破解这一虽属“入门”然而却影响深远的难题。
从“应用论”观点看,它强调将某种被视为具有“普遍性”或“普遍主义特质”的道德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应用。应用论尤其偏重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被尊奉为具有普世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道德理论的应用。其用力之处不是理论上的创造性建构(它认为原有的理论已经足够了),而是将重心放在了理论的“应用”上。也就是说,这一研究范式在逻辑上是按照“理论-应用”的逻辑来安排先后秩序,只不过逻辑上居先的“理论”被当做毋庸置疑的前提,而逻辑上在后的“应用”才是重点所在。以这种方式,它旗帜鲜明地采取了一种理论的应用姿态,即把某种现存理论话语及其原则论证(通常是“西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话语”)指认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生命伦理学论述,从而把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任务界定为具有普遍性的生命伦理学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应用。
“建构论”则选取了另一套话语及研究理路。它致力于中国语境下生命伦理学的传统重构——或曰“传统的重新发现”。以此为进路,建构论话语主张“重构中国生命伦理学”。它的重要标志是通过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前提和精神资源进行提炼或深入挖掘,以推进一种“传统重构”或“传统的重新发现”。它的重点是“理论的建构”而不是“理论的应用”,即是说,它优先关注的是通过某种特色理论话语的建构来抗衡西方普遍主义的侵蚀,强调从传统的现代转化或当代重构的建构主义纲领出发,界定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和问题域构型。
“应用论-建构论”在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方式上的对峙,在宏观视野上带来了关于“中国生命伦理学”合法性问题的争议,在微观视野上进一步加深了生命伦理原则论辩的复杂性和歧异性。这不仅对“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方式来说是如此,在全球生命伦理学的各种竞争性理论和观点论争中亦同样呈现为大致相同或相似的理论格局。两套话语及其研究范式的分野或相互竞争,通常表现为文化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如基督教生命伦理学或儒家生命伦理学)与原则取向或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如俗世的或应用的生命伦理学)的相互对峙、难于让渡的困局。我们只要翻阅当代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的著作清单,就不难发现一个可资引证的事实:他在世俗人道主义的生命伦理学与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两翼上所从事的探索工作,明显地凸显了“文化-历史”向度与“问题-原则”向度之间存在一条泾渭分明、难以逾越的鸿沟。
不同“认知旨趣”和“问题域构型”的生命伦理学的不可通约及互不相容并非一无是处。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不难发现,它们亦有其毋庸置疑的积极意义,是中国生命伦理学展现其形态多样性的一种表征,更是其蓬勃生机的体现。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需要面对不同类型的生命伦理学的话语范式之间的相互交锋和论争。一方面,多样性论争有利于我们深化或拓展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论题和问题范围。另一方面,为人们扩展道德形态或文化形态的生命伦理学的认知旨趣及其问题域视阈提供了契机或参照,推动生命伦理学面向更为广阔的实践论域进行主题拓展。例如,进一步凸显和重视与人口健康和身体伦理有关的生命政治实践、大众医疗卫生和公共健康政策等重大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多种形态(而非单一形态)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异质性话语对峙,既有利于人们扩展道德形态或文化形态的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提供了契机,又有利于人们深化或拓展具体项目层面的生命伦理学论题和问题范围。前者是具有鲜明的文化意识形态印记的问题域类型。后者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面向实践或现实的可细化为具体科学化研究和原则论证。它们之间的对峙和冲突在表现形态上尽管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则可归类为两种典型的形态:一是与“信念”有关的精神形态,涉及传统的重新发现、文化历史语境的回溯或回归、宗教形而上学根基之探寻等实质伦理方面的有关论题;一是与“程序”有关的理性形态,涉及各种类型的现代性之建构、科学化之循证、世俗人道主义原则之论证等切近“形式伦理”方面的相关论题*此处使用了“切近‘实质伦理’”和“切近‘形式伦理’”的表述。用这种表述,目的是为了避免将“实质伦理”与“形式伦理”生硬地对立起来。我们倾向于将实质伦理与形式伦理的区别看做是两种不同的“趋向”,而“形式”与“实质”之间,实际上又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形态过程的组成要素。。
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既需要立足于中华卫生文明的生命伦理之“道”,推进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之“重新发现”,又需要立足于现代医疗技术和生命科技的迅疾发展,关注医疗技术实践在伦理形态视阈(特别是在技术形态和伦理形态的相互关联方面)的理性内涵和精神内涵的拓展趋向及其发展趋势。
让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需要瞩目于“应用论-建构论”之间隐含着的关联性方面而非分歧性方面。从道德形态过程看,“认知旨趣拓展”和“问题域还原”表明:“应用论-建构论”之间的关联,随着传统意义凸显和医疗技术实践的深入展开而变得愈来愈显著。建构论生命伦理学对文化信念的强调影响了应用论生命伦理学的形态。比彻姆和丘卓思合著的《生命医学伦理原则》从第4版开始接纳医学美德伦理学,可视为明证。同样,应用论生命伦理学对道德议程或道德原则的强调也影响了建构论生命伦理学的致思取向。这一趋势在相对宽广的历史视域中呈现为亟待深入挖掘的道德形态过程,并界定了中国生命伦理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方向。换一个角度,从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伦理难题及其应对看,生命伦理学的两种范式之争存在着对立面统一的可能。也就是说,在“应用论-建构论”的两歧论争中隐含着一种融合的趋势。它为生命伦理学说“中国话”创造了丰富生动的语境前提以及将技术形态与伦理形态融贯起来的形态互动的视阈,蕴含着破解“应用论-建构论”之争的新进路。
[1](美)祁斯特拉姆·恩格尔哈特:《基督教生命伦理学基础》,孙慕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2]田海平:《中国生命伦理学认知旨趣之拓展》,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3]田海平:《生命伦理学的“第三条道路”》,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11日第2版。
[4]田海平:《中国生命伦理学“问题域”还原》,载《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1期。
责任编辑 吴兰丽
Reconsideration on Letting Bioethics “Speak Chinese”
TIAN Hai-ping
(SchoolofPhilosophy/CollegeofPhilosophyandSociology,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consider on the discourse system demand that to let bioethics speak Chinese. Our inquiry way of Bioethics highlighted this basic value that can be expressed as Dao and De, namely, Dao (Way) that pass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De (Virtues) that show the merit of Chinese Heath-care. There are two premises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breaking in building this discourse system in order to let bioethics “speak Chinese”. One is the extension of epistemological tenor in Chinese Bioethics. The other is restoration of problem domain out of Chinese Bioethics. It should be showed that a puzzle of “Applied way Vs. Reconstructed way”. Letting bioethics speak Chinese should focus on their relationship and widen the vision to define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Bioethics.
bioethics; speak Chinese; extension of epistemological tenor; restoration of problem domain
田海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13&ZD066)
2016-12-30
B82-069
A
1671-7023(2017)02-0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