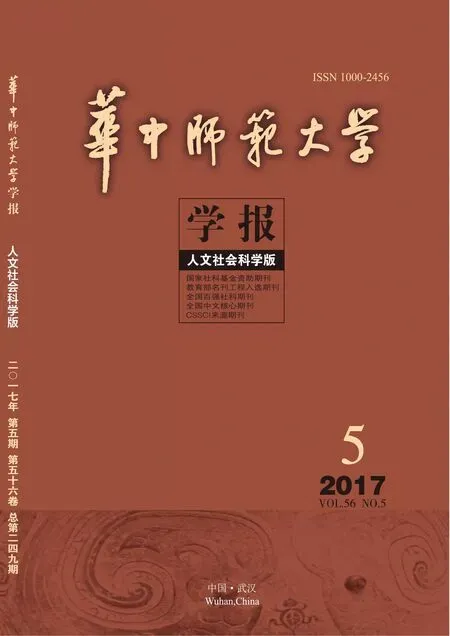中华文明胜利跨越五千年之象征性年份初探
周国林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华文明胜利跨越五千年之象征性年份初探
周国林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度讫无定说,以致学者间的表述差距较大。本文旨在对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度做出基本认定,并推测文明史跨越五千年的象征性年份。依据近百年以来考古学界的发掘与研究成果,从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出现、青铜器的铸造、国家的产生等标志,可以确定中华文明已有五千年左右的历史。文明起点之具体年份既难推定,姑且选取近似的中心点来推算中华文明跨越五千年的象征性年份。在中国轴心时代,孔子是一位继往开来的标志性人物,加之春秋战国之际铁器时代到来,经济、政治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古今变革的时间节点,故采用孔子为两个两千五百年之间近似的中心点较为合理。以孔子卒年推算,2021年为中华文明胜利跨越五千年的象征性年份。确立这一象征性年份,对学术研究、社会动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 五千年; 中心点; 孔子; 象征性年份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但是由自在的民族实体转变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却是在近代。1902年,梁启超在其名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论及先秦时期濒临东海的齐国的学术派别,有“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之语①,在学术界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他在“中华”内涵的说明中有云:“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②梁氏“中华民族”的用法,得到国人高度认同,对聚合全国民心、促进民族团结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他此处关于中华文明历史长度“四千余年”的推断,却时常见到不同的意见③。此举若干有代表性的说法为例。在《建国方略》中,革命家孙中山称赞中国人民:“聪明才智自古无匹,承五千年之文化,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尝为世界之雄矣。”④后来又在《三民主义》一书中说:“我们中国的民族也很古,从有稽考以来的历史讲,已经有四千多年;故推究我们的民族,自开始至今,至少必有五六千年。”⑤抗战期间,国学家钱穆说:“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举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从黄帝传说以来约得四千六百余年。”⑥到当代,史学家李学勤说:“我们的文明从炎帝、黄帝那个时代就开始了,而炎帝、黄帝那个时代距离今天,一般的理解就是将近五千年。所以我们说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和炎黄子孙这句话有着密切的关系。”⑦偶尔也说:“我们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着丰富的古史传说。”⑧哲学家汤一介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长达5000年历史文化的古老民族。”⑨此外他还用过其他概略性时间,“中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化根基”⑩、“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在五六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以上关于中华文明历史长度的看法不仅言人人殊,同一人的表述也不一致,除去发表时间上的间隔,出入仍然比较大,少者几百年,多者上千年。由于客观上没有一个“中华文明元年”存在,以上看法基本上用的是概数,难以评说孰是孰非。不过,各种看法之间的差距达到数百上千年,终归值得加以探讨,以避免不经意之间的差异性。概略地寻求中华文明的起点,确定一个中华文明胜利跨越五千年的象征性年份,使大家的文字表述由“四千多年”变换到“五千多年”时不至于悄无声息,是学术界早晚需要面对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意在先行提出刍荛之见,以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探索。
二、中华文明五千年左右的可靠性
欲确定中华文明胜利跨越五千年的象征性年份,必须对中华文明已经有五千年左右历史的事实加以确认。这是因为除了上列四千余年至五六千年的诸种看法外,其他学术领域还有更短和更长的推断。像文化学者易中天编写《易中天中华史》,讲的是“中华文明从二里头遗址算起,至今3700年历史亘古未断”;文学人类学学者叶舒宪主张运用四重证据法,“将八千年延续至今的玉文化作为华夏文明发生的一条主脉”;甘肃一些文物考古界人士根据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发掘情况认为,“中华民族有8000年文化史已毫无疑问,而传统所说的5000年中华文明史能否上推到8000年甚至上万年,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重要课题”。于是,中华文明为什么不是三四千年,也不是六千年以上,而恰恰是五千年左右?就需要科学证明了,说确切一点,是需要考古学的证明。近百年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以古史重建为己任,充当了中华文明起源探索的主力军。经过大量的科学发掘,结合传世文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已经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中国20世纪的考古学,起步于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此后,中国广袤的大地上陆续发现远古人类化石,并发掘了一批构成历史演进链条的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此基础上,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遍布中华大地的考古文化,已形成六大区系,各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分别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并陆续进入文明时期。而它们进入文明社会,是有衡量标准的。通常的看法,是将文字、铜器、城市或大型礼仪建筑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也有人依据恩格斯的定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或者从词源角度考察,认为“文明”即“国家”,将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认为文明起源与国家起源或可等同。这里不拟对这些衡量标准加以讨论,仅对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中华文明形成的显著标志略加考察,对中华文明形成后的时间长度得出基本的结论。
(一)文字的发明
19世纪,摩尔根、恩格斯将使用文字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文字的出现的确是人类惊天动地的大事,汉代的《淮南子·本经》称“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意思是人类发明文字后,各类信息由前代传到后代,由此地传到彼地,使从前在冥冥之中主宰人类命运的天地鬼神黯然失色,它们为天机泄露而痛哭。以文字为文明起源的标志,良有以也。19世纪末年,河南省安阳县殷墟卜骨从民间大量流出,激起众多学者研究甲骨文的热潮。加之20世纪前期15次科学发掘,巨量的甲骨文字成为古史研究的宝贵资料。这些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的文字,一下就将中国的信史由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向前推进了数百年,成为中华文明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由于殷墟文字已经十分成熟,形成了完整记录语言的文字体系,自然会勾起人们进一步探索的欲望:更早的文字在哪里?是什么样子?
可能是古文字在地下埋藏得太隐秘,加之发掘的偶然性,此后数十年总难见到甲骨文源头的面目。于是,人们转而从文字的起源文字画、刻画符号中去寻找头绪。西安半坡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村落遗址,出土陶器上有27种刻画符号。文字学家郭沫若、于省吾等人皆认为这就是文字起源阶段的简单文字,是甲骨文字的前身。虽然这个看法未获一致认同,但推动了相关理论的探讨,即刻画符号在何种条件下转化为文字。有的学者还以世界视野来考察刻画符号同文字的关系,说明符号是文字的先行者。
当然,理论不可能剪裁现实。文字学家臧克和在一部丛书总序中引述有关理论后禁不住感慨:“考古发掘以及人类学等材料的陆续发现,也越来越超乎人们的想象。”他随手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例是2004年山东省昌乐出土的100多块兽甲骨,刻有600多个符号,结构和布局上有规律可循,据有关专家鉴定为“4500年前的甲骨文字”。第二、三例是在宁夏、内蒙古发现的大规模绘有原始文字的岩画,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据分析很有可能改写中国文字史。类似的考古发现也不时见于报端。2005年,在安徽省蚌埠市小蚌埠镇双墩村发现7000年前遗址,其中有600多件刻画符号,为同时期国内外文化遗存所罕见。符号大都刻画在器底部位,内容包括日月、山川、动植物、房屋等写实类,狩猎、捕鱼、种植、养蚕等生产生活类,记事与记数类等,内涵广泛。刻画符号分为单体、复合、组合三种,不少符号反复出现具有明显的记事性质和一定的表义功能。从各地遗存刻画符号比较和文明形成的规律看,“双墩刻画符号是中国文字的重要源头之一,对于探索中国文字乃至人类文字起源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6年,考古学界又传出良渚先民5000多年前使用文字的信息。据报道,在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中,共有240余件器物发现了刻画符号。这些符号排列成序,不像其他单体刻画符号那样孤立地存在,而是可以成组连字成句。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原始文字,且是较为成熟、初具系统的文字,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报道中分析说:“当时的先民已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需要用某种方式来交流沟通,就会出现这类刻画符号。”以上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刻画符号分布广泛,表明殷墟成熟文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不难推测,距今6000年左右至距今3500年之间,是文字由产生到逐渐成熟的阶段。人类为殷墟卜辞等待了三千多年,更早的五千年左右的文字重现世间是必然的,只不过等待时间会更长而已。
(二)城市的出现
城市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是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1950年提出来的。此后学者们对城市在早期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视,特别强调城市人口要达到一定的规模。现在大家普遍认识到,“城市”是涉及整个人类社会进入到文明阶段后一切社会群体、社会关系集中的载体。
数十年的都市遗址发掘中,已经发现大量距今五千年左右的重要遗迹遗物。其中有影响者,1980年代考古学界权威性的描述包括: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淮阳“平粮台”;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带刻文陶器地点所在的处于最高发展阶段蛋壳陶、成组玉器集中范围内;山东寿光、益都间“边线王”城堡遗址也属同类遗存集中范围内;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遗址普遍存在的以玉琮、玉璧为主的成组玉器墓;辽宁朝阳喀左东山嘴的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建平、凌源间同一时期的“女神庙”和山头上“积石冢”;内蒙古乌盟凉城“老虎山”石砌古城等等。“这些遗址、遗物的发现地点范围北至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至黄河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
从1990年代至今,古城遗址续有发现,研究方面更有不少突破。其中最重要的当推陶寺遗址,将近40年的发掘终于带来了惊人的发现。2015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陶寺遗址是中国史前功能区划最完备的都城,由王宫、外郭城、下层贵族居住区等构成,兴建与使用的时代为距今4300-4100年。陶寺遗址的城垣可分早期和中期两个阶段的建筑,中期城址(约公元前2100-前2000年)在早期城址上扩建,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堪称当时东亚第一大都城。宫殿台基宽广宏大,其中建筑材料陶板残片是全世界目前发现最早的板瓦。在1740平方米的大型圆体夯土建筑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虽然对陶寺遗址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还存在一些分歧,但不容否定的是,通过陶寺的发掘和研究,尧都正走出传说时代,逐渐向信史转变。其次是陕西省神木县的石峁古城。2011-2012年,考古部门通过对石峁古城的调查和发掘,最终确认石峁古城是一座面积约400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晚期到夏朝早期的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是目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史前城址。随后几年的考古工作中,皇城台又发现了4300多年前结构复杂的大型建筑遗址。皇城台的底部有一条用石头砌出的通向内城和外城东门的主干道,进入皇城台之前有多重结构的瓮城,旁边还有大墩台和广场。如此大规模的古城是何人所建?到底是黄帝部族的邑居,还是尧的陪都,或者是上古西夏都邑?已经激起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学者们的浓厚兴趣。
此外还有其他文化遗址中的若干古城、聚落发掘。如上文提到过的甘肃大地湾遗址,大致可分为五个文化区,年代从距今8000年至距今5000年。在距今5000年的大型房屋建筑中,编号为F901的房址占地面积420平方米,有前厅、后室、左右侧室、门前棚廊等部分,主室面积达130平方米,这种具有对称观念的建筑布局,是中华文化特色的宫殿建筑的雏形,被誉为迄今为止同时代遗址中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最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宫殿式建筑”。又如湖北省天门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在2015-2016年的勘探发掘中,新发现的谭家岭古城为认识石家河古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印信台祭祀遗址是目前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这些古城和聚落遗址,距今年代都在4000年以上,发展阶段相衔接,在探索文明起源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国家的产生
考古发掘中,各地青铜器的出土非常多,如前举陶寺、石峁古城遗址中就时有所见,兹不具列。有人认为大量出土青铜器是中国特色,作为文明产生的标志代表性不强,实不尽然。各文明古国的产生,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考古学家张光直指出:“中国青铜时代这个概念与古代中国文明这个概念之间相合到几乎可以互换的程度。青铜器本身当然便是古代中国文明的突出的特征,而造成它们的特殊地位的因素,同时也正是导致那文明产生的同样的因素。”如果说文字和礼仪建筑主要反映的是先民们精神文化成果的话,青铜器以及城市则可以视作物质文化成果。它们的同时具备,起码表明其时已接近文明形成的临界点。当然,除了以上判别文明产生的标志,还要结合当时的阶级分化和公共权力的诞生等若干因素,来确定当时是否已经迈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不少考古学家花费了毕生心血。
通过对各地出土的大量文物条分缕析,苏秉琦在1985年的“晋文化研究会”上发表了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总体认识。在六大文化区系中,他格外看重中原和北方二系,并以出土图案为各自的代表,有“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等诗句。他说:“北方的红山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在各自第二次演化(聚变或裂变)出的两个支系,约当距今五六千年间在冀西北桑干河上游交错相会。这就是辽西新发现的红山文化坛庙冢产生的历史背景,而后者正是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系在大凌河上游互相撞击、聚变的产物。这也是我们从宏观角度对辽西新发现意义的认识。以上是对第一句‘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解释,也是提出中华5000年文明曙光论点的依据。”进入21世纪,“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学界首席专家李伯谦在阶段性成果结题后,又参与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接连发表重要论文。他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说:“文明的形成是指文明的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产生。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的龙山文化正处于这一阶段。在这一时期,多级聚落形成,区域中心纷纷涌现,有的当已率先进入文明社会。”后来,他又将考古学重建的古史体系与传统史学的中国古史体系对应起来,形成考古学视野下的三皇五帝时代。其中,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分别对应有巢氏、伏羲氏、燧人氏,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对应神农氏;而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对应炎帝、黄帝,社会形态已进入部落联盟、古国阶段即文明社会,距今5000年至4500年;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对应颛顼、帝喾、尧、舜、禹,社会形态为王国初期,距今4500年至4000年。苏秉琦、李伯谦俩人的看法,在考古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久前,王巍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领军人物得出结论:“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虚言”。这就是说,距今5000年前,当全国各地文明的火花如“满天星斗”闪烁之后,终于迎来文明的曙光,开始照耀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
三、以孔子为中华文明两个两千五百年之中心点的依据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左右的文明史既如上述,下一步就是如何推测中华文明跨越五千年的具体年份的问题了。如上文所说,中华文明的起始之年谁都无法确定,也无从确定究竟在哪一年跨越中华文明的第一个五千年,推测跨越的年份自然碰上了难题。那么,难题面前就真的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了吗?不一定。我们的设想是,既然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概数已经确定,似乎可以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即两个两千五百年,在前后皆接近2500年的时段寻找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最好同时兼具)作为近似的中心点,来求取胜利跨越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性年份,不失为权宜之计。
毫无疑问,中心点的选择是需要十分审慎的。列宁当年在确定帝国主义战争性质时,提出要分析所有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并说:“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该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然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同样的道理,选择中华五千年文明近似的中心点,不能只顾及某一方面,而应该是两个二千五百年之间那个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材料的总和”,才有客观性和说服力。较为符合这一条件者,我们认为是孔子。其理由有三点。
(一)孔子是中国轴心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半个多世纪以前,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轴心期理论,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他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经过漫长的史前、古代文明阶段,公元前800-200年期间的精神过程,标志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年是它的高峰期。这一阶段中,在中国,在印度,在西方几乎是同时产生了一批哲学家,他们探索根本性的问题,“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在雅斯贝尔斯提到的中国哲学家中,有孔子和老子,还有墨子、庄子和列子等人。很显然,这些人中影响最大的是孔子和老子。关于老子,雅斯贝尔斯把他归入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原创性形而上学家之中:老子以“道”统摄一切,道存在于世界之中;道与个体的人(生命的实践)、道与国家之统治(驾驭人类社会的实践)皆通过“无为”来起作用。老子的意义,是所说出者正是不可言说者,“老子所瞄准的目标乃是被悟性和目的掩盖起来的、处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根源”,使人们在看来总是相同的事物中,在根本处把握住特殊。不过,“老子缺乏与道之中的终极之虚静不同的、在时间之中不停运动着的、自我反省的开端;缺乏自我澄明、自我交往,无法驱除一再硬要出现的自我欺骗、隐蔽及颠倒。”关于孔子,雅斯贝尔斯认为他在人类进入轴心时代的关键时刻也在一心求道,孔子的根本思想,是“借对古代的复兴以实现对人类的救济”。由于孔子将目光更多地投向社会,雅斯贝尔斯将孔子与苏格拉底、佛陀、耶稣总共四人并列,称为人类历史上“思想范式的创造者”。雅斯贝尔斯的这些论述,对我们选取孔子为中国轴心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极具启迪意义。
《论语》一书中,记载了孔子一生求道、传道的经历。孔子之道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是为人类文明提供一个超越的精神支柱。为此,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于前人的业绩和文明成果敏以求之。尧舜是古代明君,孔子称赞:“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夏商周制度代有损益,孔子权衡利弊后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尤其是对制礼作乐的周公,自始至终倾心仰慕,魂牵梦萦,视作与自己所处时代最近的一位心心相印的圣人。正是对前代礼乐文化如饥似渴的充分吸收,孔子成为此前几千年文明最博大的承载者、最忠实的维护者。在社会陷入“礼崩乐坏”困境的时刻,“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于是他毅然担负起传承“斯文”的使命,对找回人类文明的深层意义怀抱坚强的信念。在周礼的基础上,孔子从深邃的人性和人类社群观念出发,建立起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在社会实践层面,“仁”始于君子之“爱人”,由家庭推及于人群,达之于天下,“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冀以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社会。
对于这种以“仁”为核心,其中包含礼义忠恕信、温良恭俭让等范畴的儒家之“道”,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将其与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相比较,认为是轴心时代的最高成就:“仁的观念在《论语》里居于最重要地位,引发出累累硕果,这是古代中国思想符号世界中的划时代事件。仁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意指超越生死的终极价值。”“孔子相信,人的本性可通过自我努力得以完善,这是对他所处时代非人化倾向的回答,引导他致力于由内及外地转化这个世界。孔子相信,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近在咫尺,对仁的渴望就是实现这一价值所必需的力量。”“儒家和利用天启神学或思辨哲学作资源的同时代人,走上了基本不同的两条道路。由于他们以人类文明的守护者自居,因此原则上就无法切断与政治、社会、历史的联系。结果,他们自己承担起吁求人民尤其是掌权者的真诚感情、正当理由、常识的任务,以求重新确立世界秩序。”美国现代最著名的外交家基辛格追溯中华文明史,提到儒家学说时写道:“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源自一位古代哲学家的教诲,后人称其为‘孔夫子’或‘孔子’。”“身处乱世,孔子提出的对策是施行正义的和谐社会之‘道’。孔子称,远古的黄金时代曾实现过这种正义与和谐。在信仰上,人类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拯救这一岌岌可危的合理秩序。信仰的目的不是启示或解脱,而是耐心地恢复已被遗忘的克己美德。”“孔子与一神论宗教的先知不同,他绝口不谈人类如何获得个人救赎。孔子主张通过个人修养获得国家的救赎。孔子思想着眼于现世,肯定的是一种社会守则,而不是来世的救赎。”孔子的这些历史性贡献,学术界的探讨相当充分,无须细述。
孔子立足于古代文明的创新,是中国轴心时代超越性的突破,引领了历史转折阶段的思想潮流。这使他的学说迅猛地传播开来,他本人也成为所在时代最令人崇敬的人物。仅仅过了一百多年,孟子就一再引述孔子的弟子之语,称颂“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再过两百多年,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又流连于孔子庙堂前,对孔子表达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般的顶礼膜拜:“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我们回头再看这位既不是帝王也不是神祇的人物,仍然时时处处感受到他的存在,希望从他的思想中得到新的启示,禁不住发自肺腑地尊之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这自然让人联想到恩格斯评价但丁的一段话:“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借用恩格斯的说法,孔子是中华文明第一个两千五百年的总结者,同时又是第二个两千五百年的引领者。以孔子为中华文明两个两千五百年之间近似的中心点,在思想文化领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二)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显著变化
相传孔子作《春秋》,书成而卒,历史便告别春秋时代,进入战国。在此前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就生产力而论,最大的标志是铁器时代的到来。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之初,主要生产工具是石器,后来是铜石并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春秋左传》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荀寅率领军队筑城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是冶铁使用在古籍中之首见。考古发掘中,自1957年在河南信阳县长台关1号楚墓发现春秋时期五件铁带钩之后,在湖南、江苏等地陆续出土春秋铁质工具。综合文献和冶金学研究成果,春秋时期的铁器使用还比较有限,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也同样有限。经过春秋300多年逐步发展和扩大的过程后,直到春秋战国之际,冶铁和铁器使用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故考古发掘的大量铁器,基本上是春秋晚期之后的遗物。像湖北省大冶县铜绿山古矿,这个时段的冶铁业就相当发达,获得了“中华第一冶”的美誉。战国特别是战国中期以后,铁器的使用完全普及。张光直在几十年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中国铁时代之始——亦即中国青铜时代之终——可以放置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虽然青铜礼器与若干青铜兵器的显著使用还要再继续好几百年之久。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在秦始皇下的统一,很可能便是中国铁时代开始的政治上与社会上的结果。”在他看来,青铜器、铁器明显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是不同时代的重要标志。
铁器登上历史舞台,特别是铁农具的运用,劳动效率大为提高。诚如恩格斯所说,“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加之牛耕的推广,农田水利事业的广泛开展,过去粗放的耒耜农业在战国时期发展成为深耕细作的精细农业。其结果是促进土地的大量开辟,生产能力的大幅度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包括金属铸币的广泛使用、城市的兴起、富商大贾的活跃。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仿佛被猛然激活了。
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主要经济领域的生产关系转变十分明显。春秋时期,井田制已经难以维持下去。公元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就是对井田制下助耕公田、“藉而不税”的突破。不久,又有楚国的“量入修赋”(前548)、郑国的“作丘赋”(前538),都是统治者被迫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的反映。土地和赋税制度的演变,使原来的宗族公社逐步分化瓦解,以私田为基础、以个体劳动为主要方式的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确立。战国时,各国统治者纷纷认识到,农民在公田上劳动积极性低,分地则加快进度,于是对土地制度进一步调整,普遍实行授田制。像魏国的李悝作尽地力之教,使一家五口耕地百亩;秦国商鞅变法,也是“废井田,开阡陌”,授地于民。这使原先各种家族的集体性质的劳动过渡为个体小农家庭的独自劳作,逐渐占据社会的主流。个体小农脱离原有的宗族组织,不再具有对各级宗法贵族的依附关系,也不再在各级贵族的“籍田”中无偿服劳役,而是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单位直接隶属于国家。其土地来自国家的授予,自然要向新主人纳税服役,但其身份却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不再是过去的“族众”,逐渐演变为新型国家组织下的编户齐民。当然,社会上也还存在一些失去土地的雇农,以替豪民耕地而谋生。生产关系上的这一变化影响至为深远,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经济结构。个体小农生产方式也从此成为其后历代的立国基础,绵延两千多年。
(三)孔子生活年代政治体制的急剧变革
孔子去世前后,政治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周平王迁都洛阳,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不断衰微,这对极力维护周朝礼制的孔子来说,难免心有戚戚焉。在国家治理方式上,孔子强调天子的尊崇地位,希望天子诸侯上下有序,减少战争,人民少受战乱之苦。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因此,他对天子失去礼乐征伐的发号施令权耿耿于怀。幸亏当时还有齐桓公等“春秋五霸”挟天子以令诸侯,保住天子的颜面,使局势不至于完全失控。孔子曾对齐桓公和辅佐者管仲大加赞扬:“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革,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然而到战国时期就不一样了,是“七雄”相争,没有实力争雄者则依违于其间。“雄”与“霸”的差别是不再打天子的旗号,各自奖励耕战,扩充实力,赤裸裸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七雄相争的结局,是在付出巨大的人财损伤代价后天下统一,建立秦王朝。按照一些考古学家的说法,是由王国进入帝国阶段了。如果说春秋是实行“天下共主”的王国体制开始出现松动的时期,战国则进入裂变时期,由量变到质变了。在帝国阶段中,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当然更有条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这未必不是孔子心中可以接受的更高层次的“天下有道”。只是王国与帝国之间横亘着一个战国时期,又要承受战争的苦痛,孔子也不可逆料。这大概是形势比人强的地方。
在由王国进入帝国的过程中,政治体制上一个巨大变动是分封制的解体与郡县制的建立。分封制下,“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形成同心圆性质的逐层负责的权力网络结构。战国时各国在兼并战争压力下,出于集权的需要,纷纷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由此形成垂直管理地方的郡县制。郡县长官不能世袭,既打破了从前的裂土分封模式,也有利于防止地方割据,维护国家的统一。即便是保留了封号或新授予封号的封君,也没有对土地和民众的治理权。与此相应,从前的宗法制度、基层社会管理方式,等等,都得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做出程度不同的调整。虽然人们习惯上称中国古代为宗法社会,但春秋战国时大有改变。西周乃至春秋早期,大多数诸侯国是方五十里、方七十里的规模,小国寡民,以宗法等级制为核心治理社会,是家国一体的结构。战国之后的宗法关系却仅限于社会的两极,即基层和王室,把它们联结起来的是上至宰辅、下至三老的官僚机构。“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中,通行的并不是宗法制原则,君臣关系、官民关系本质上并不是宗法关系”。也就是说,战国之后的宗法关系,已经是次生形态,政治功能削弱了。类似的制度性变动,战国时期还有不少。
将上述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综合起来看,当时的社会形态(或曰社会性质)明显处于演变之中。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还是封建社会内部由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或者是奴隶社会内部前后阶段的过渡,学术界尚存争议,恐怕短时间内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不过,大家无一不认同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看法:“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
总之,在中国社会进入轴心时代之际,“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成为引领文明演进方向的思想范式创造者。恰巧在这一时间节点上,中国进入铁器时代,经济大发展,政治大改革,国家格局变换,社会形态嬗替,使以孔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心点的理由更为充分。如此偶然巧值之事,岂天意乎?
四、中华文明胜利跨越五千年的象征性年份及其意义
依据上面的论述,确定中华文明胜利跨越五千年的象征性年份就只是简单的计算了。公元前479年,孔子在完成他伟大的历史使命后,走到生命的终点。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年份。如以该年为两个两千五百年之间的中心点的话,公元前剩余的479个年头加上公元后的2021年正好2500年。这也就是说,公元2021年是伟大的中华文明跨越五千年历程的象征性年份。如果这个象征性年份得到确认,意义不可小觑。
一是学术研究方面。将中华文明划分为前后两个二千五百年,有助于历史学界珍视考古学界的发掘与研究成果,充实和推进第一个两千五百年历史文化的研究。比如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目前基本上是从孔子讲起,这显然不是源头,要向前延伸,要从炎黄文化、从尧舜之道讲到孔孟之道。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完成后,该工程特别顾问宋健撰文评论说:“年代学对人类和世界的影响是潜在的、多方面的。无论哪个民族,人们总想知道他们的历史,了解祖先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前覆后鉴,知故创新。”我们采用两个两千五百年的划分法,就是希冀在年代学的勘定上有所推进,对先秦的历史文化追本溯源,完整地探寻祖先们的足迹,清晰地认识历史的走向和规律,从而达到前覆后鉴、知故创新的目的。此外,将中华文明划分为两个两千五百年,强调长时段的研究,这在目前重视细密化研究的背景下,有加强微观研究与宏观、中观研究相结合的意向。胸有全局,视野开阔,可以避免不少研究项目中的碎片化现象。
二是社会动员方面。按照《礼记·礼运》中的说法,中国在远古是“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随后进入小康时代。今人皆知,古代的“大同”是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小康”是阶级社会的初期,亦即中华文明的起点。巧合的是,就在中华文明毫不间断地走过五千年历程的时刻,中国又将全面建成现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社会变迁竟然是如此的神奇瑰伟,有如自然造化中的鬼斧神工!为了这个时刻的到来,中国人民不知经历了多少险阻甚至劫难,不知付出了多大艰辛乃至生命。因此,这个时刻值得中国人民自豪和惊喜,它应是全民族举杯庆贺的日子。在享受欢乐的同时,回望过往历程,反思成败得失,全面总结五千年的文明成就,深入探索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道路,认真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智慧,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也是庆贺的最佳方式。这对中国人民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满怀激情地迈进第二个五千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价值不可估量。
最后,引录“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注释
①②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第1页。
③梁启超本人也偶尔用“四千年”,如《戊戌政变记》文首有云:“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起,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而其附录一《改革起原》作:“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分别见《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第113页。盖有无“余”字,于文义无碍,初未措意也。
④张磊主编:《孙中山文粹》,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上册第274页。
⑤张磊主编:《孙中山文粹》,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下册第678页。
⑥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上册第1页。
⑦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⑧梁枢:《陶寺:帝尧时代的中国》,《光明日报》2013年12月9日第15版。
⑨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2页。
责任编辑东园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ymbolic Year of Inheriting Smoothly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Zhou Guolin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The time spa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not yet been defined until now, therefore the expressions among scholars are distinctly different.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make basic recognition for the time spa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o speculate the symbolic year of inheriting smoothly five thousand years’ civilization.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the recent 100 years,it regards the invention of the character, the emergence of the city, bronze cas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countries and so on as signs of human civilization,thus it determines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 five-thousand-year history. The starting specific point of civilization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so it chooses to use an approximate center point to mark the symbolic year of inheriting smoothly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ivilization. In the Axis Time,Confucius i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who continues with the past and opens up with the future. Meanwhile, the coming of Iron Age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earth-shaking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ields make this period as the time point of historical change.So it is reasonable to use Confucius as an approximate center point of the five thousand years. Finally,it thinks that 2021 would be the symbolic year of inheriting smoothly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ivilization based on Confucius’s death tim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ademic research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to establish this symbolic year.
Chinese civilization; five thousand years; center point; Confucius; the symbolic year
2017-03-0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荆楚全书》编纂”(10&zd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