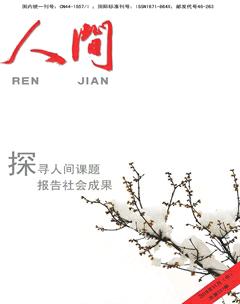论美国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重庆 404000)
摘要:美国对于非法言词证据认定主要依据宪法关于正当程序、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以及获得律师帮助权的相关规定。对于非任意性供述,除了要审查是否存在暴力、承诺、威胁等行为外,还要对案件的“总体情形”进行综合审查。我国在认定非法言词证据上,可对非法取证行为采取概括性规定;在具体案件审查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审查;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来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说理,为实践中认定非法言词证据提供详细具体的指导。
关键词: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总体情形;指导性案例
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77-01
一、美国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
美国非法言词证据的认定依据主要来源于宪法条文中关于正当程序、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获得律师辩护权的相关规定。凡是在侦查活动中,通过违反上述有关规定而取得的言词证据均予以排除①。
(一)违反正当程序、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而获取的言词证据。
无论是违反正当程序规定的“非任意性”(involuntary)、还是违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规定的“强迫”(compelled),美国最高法院已将二者概念合并使用,在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中,二者之间几乎不存在明显差别②,在实践中通常将违反上述规定的言词证据称之为“非任意性供述”。
对于非任意性供述的认定在实际案例中有以下几种常见行为:
1.对被讯问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包括不给被讯问人食物和水、或者不让其睡觉。另外,如果办案人员或者办案人员安排的线人对嫌疑人说,如果他不供述将会受到其他囚犯的攻击,而取得的供述也将予以排除。
2. 向被讯问人承诺轻罚或威胁重罚。在布拉姆案(Bram v. United States)④中,美国最高法院宣布“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承诺而获取的”供述都不是自愿的。如在莉娜姆案(Lynumn v. Illinois)⑤中,办案人员对被讯问人说,如果被讯问人不供述将会失去福利待遇并且将失去孩子监护权;但如果与警方合作,则警方将建议法院从宽处理并帮助其拿到孩子监护权。基于此,被讯问人供述了自己的行为。但最高法院排除了该供述。
但如为了换取供述,办案人员仅承诺会提请检察官注意嫌疑人给予的配合,基于此取得的供述,法院一般不会予以排除。
3. 欺骗被讯问人。在美国最高法院开始排除暴力和刑讯取得的供述后,美国警方开始更加注重其他讯问技术——尤其是欺骗。因为对于欺骗与侦查谋略的性质难以界定,这也导致法院对于仅仅依靠欺骗而获得的供述往往未予以排除。
除此之外,对被讯问人施加心理压力也是造成非任意性供述的行为之一。主要包括被讯问人遭受长时间秘密状态下的讯问(无法接触家庭成员、朋友、律师),使其意志崩溃。包括长时间不间断的讯问、转移讯问地点、变换讯问人员。
对于被讯问人的供述是否具有任意性,美国并未制定详细标准,法院需要对案件每一供述有关的“总体情形”进行综合审查,包括审查被讯问人与律师接触、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是否被剥夺⑥。因此,上述关于违反任意性供述规定的行为也仅做为参考,并非绝对标准。
(二)违反获得律师帮助、辩护的权利而获取的言词证据。
该权利要求被告自愿、明知且以明白的方式放弃,即必须表明该权利的放弃是被告有意识的以明白的方式放弃,且并不因为被告人没有主张而丧失——同时表明放弃的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
在威廉斯案(Brewer v. Williams)⑦中,在被带到爱荷华州首府得梅因接受谋杀指控路途中,威廉斯表示在见到得梅因的律师之前不会向警方供述自己的行为。警方也保证在路途中不会对威廉斯进行讯问。但一名警察却在路上对威廉斯发表了关于“基督教葬礼的话”。之后,威廉斯向警方进行了有罪供述。但在随后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联邦上述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均做出了对威廉斯有利的裁决。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威廉斯被剥夺了宪法规定的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威廉斯没有明确表明放弃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前提下,警方通过“基督教葬礼的讲话”故意获取威廉斯的归罪性言论。
二、非法言词证据适用毒树之果规则的情况
(一)实物证据。根据早期普通法规定,对于通过不可靠的供述而获取的可靠的实物证据是会被采纳的。但现在,排除证据的理由不光是证据不具有可靠性,更考虑该证据的获取行为是否侵犯了公民的其他權利。
(二)言词证据。对于根据非法言词证据而获取的证人证言,只要证明证人的身份迟早会被发现,该证人证言在最终必然发现原则下是认为可采信的。对于根据非法言词证据而获取的嫌疑人供述,一般而言也是适用毒树之果原则的。
三、对我国立法与实践的借鉴
(一)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依据为笼统的宪法规定。我国对于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行为采取列举法加兜底条款的方式进行规定,但列举无法穷尽所有的违法行为,且随着社会发展,列举也无法将新增的违法取证行为一一囊括其中;同时,兜底条款又使裁量权过于自由⑧。
(二)对具体案件的“总体情形”进行综合审查。在具体案件上,对于是否认定为非法言词证据,以宪法规定为前提,以案件具体情况为依据,对案件的“总体情形”进行综合把握判断,从而最终认定是否违反相关宪法规定、是否为非法言词证据。毕竟每个案件具体情况不一样,每个被讯问人的个人情况也不一样,讯问活动本身是否对其造成了影响从而导致其供述为“非任意性供述”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通过判例对具体案件审判提供参考。2010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强调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参照“指导性案例”。对此,可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指导性案例对具体的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详细的说理,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加明确的指导和认定标准。
注释:
①在美国,任何违反米兰达规则所取得的供述都不能采纳为证据。
②[美]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麦克尔斯著,吴宏耀译。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第四版)(第一卷·刑事侦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③499 U.S. 279 (1991).
④168 U.S.532 (1897).
⑤372 U.S.528 (1963).
⑥这一权利属于正当程序的要求,被包含在米兰达规则之内。
⑦430 U.S.387 (1977).
⑧马明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结构性困境[J].现代法学,2015(4):189。
作者简介:代金山(1988-),男,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侦查处干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