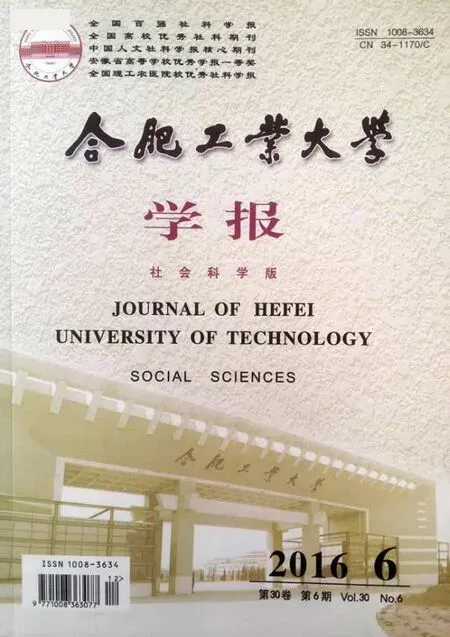驭情以共享:孟子家庭思想中的治国之道探微
——基于脑认知科学的尝试解读
章亮亮
(安徽大学 哲学系,合肥 230039)
驭情以共享:孟子家庭思想中的治国之道探微
——基于脑认知科学的尝试解读
章亮亮
(安徽大学 哲学系,合肥 230039)
现代新脑认知科学的研究证明了孟子以血缘判定情感亲疏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表明了非血缘性个体间的恻隐之情是建立在基本情感之上的复杂情绪,同时也为孟子积极推动以情感为重的家庭建设进而寻求治国之道的思想理念作出了自然科学层面的深入阐释:人类的情感左右着个体及群体的行为,共享行为生发于人类的通情能力,通情的道德抉择又受到群体所处特定情境的强力控制。塑造积极健康的大脑、遵循情感的优先性、创设良好的情境已经获得了脑认知科学的广泛认同,也为家国同构的传统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情绪构建;情感优先性;通情;情境
中国传统观点普遍认为,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建的最小群体单位,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将立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亲情视为家庭建立的基点,试图在以捍卫亲情、遵循伦常之仪的家庭建设道路中探索齐家以治国的方法。令人欣喜的是,现代脑认知科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已经从自然科学的立场上证实:情感、情境、通情在人类生活尤其是家庭乃至国家的永续发展方面具有决策性作用,由此出发,本文拟对孟子积极推动以情感为重的家庭建设进而寻求治国之道的思想理念作出进一步的合理性解释。
一、情绪的社会化构建:对血缘之情与恻隐之情的再探讨
孟子以血缘为基本标准确定情感关系的亲疏:其一,血缘关系之有无以分内外。其二,血缘关系之近远以分亲疏。先看第一点,孟子借兄弟阐发了因血缘关系的有无而产生的对同种情形的迥异看法:“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对此,赵歧的评论颇具意味:“此‘章指’言生之膝下,一体而分,喘息呼吸,气通于亲,当亲而疏,怨慕号天。”(《孟子注疏》)同一人面临“关弓而射之”的相同情形,“疏则言之和,故谈笑,亲则言之迫,故号泣”(《孟子正义》)正是缘于血缘上的天然分别。再看第二点,先秦儒家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划定了亲疏之界。“亲”的范围涵盖了父、母、叔、伯、子、孙、兄、弟等所有直系父辈母辈、旁系平辈关系。“尊”的对象地位更为尊贵,它突出特重父、祖父、曾祖、高祖四层直系父辈关系[1]。显而易见,“亲”与“尊”在全部的宗族关系中都凸显出对直系父系关系的尊崇,其本质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直系父系关系为主线,对宗族内部成员进行“子对父”“弟对兄”的尊上式剪裁,以此来彰显亲疏远近的分化脉络。
当然,孟子并未忽视非血缘性个体之间的情感关系,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恻隐之情。恻隐之情不同于“其颡有泚,睨而不视”流露出的骨肉亲情,对孺子的情感不会因为血缘的有无存在任何的厚薄之分。孟子认为,激发于“不忍人之心”的恻隐之情与“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的血缘之情并行不悖,二者皆为人之本然常情,只不过血缘之情乃常情之尊。但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人少,则慕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厚,逐渐呈现出“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的发展趋势,个中缘由就连孟子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人的情感倾向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变化?血缘之情的不足之处与合理性又在哪里?它与恻隐之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厘清上述问题,有必要借助脑认知科学的早期研究。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对认知的研究表明,情绪是社会化构建的产物,并借由社会、文化的交互性发展过程被人们感知、理解、命名。简言之,情绪不具备先天性指向,而来源于后天的经验习得。就情绪与情感的关系而言,情绪更具复杂性,它是由欲望、爱悦、憎恨、快乐、痛苦、惊恐六种原发性基本情感派生而出的[2]。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亲者之爱是人类幼年时期最基本的感情之一,在此后的发展阶段中,情感受不同心理预期和现实需求(知好色、有妻子、仕)的影响,逐渐向复杂情绪衍变,因而呈现出慕少艾、慕妻子、慕君的情感转向。这同时也验证了哈佛大学马丁·诺瓦克团队的研究成果: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人类彼此之间的行为选择取决于血缘关系[3]1057-1062。由此可以看出,基于特定血缘关系的情感纽带并非坚无可摧,而恻隐之情则更为普遍。“不忍人”是个体对主观感受、身体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后的结果,是“孺子将入于井”这一特定环境诱发下的复杂情绪的显现。于孟子而言,他仅仅注意到了“不忍人”这一情绪的强烈迸发,因为这是“一种我们几乎或根本无法控制的冲动。就像反射一样,它在一瞬间就抓住了我们”[4]54,却因时代所限无法知晓人类的复杂情绪是由后天的社会化构建所习得的,故从直观的亲缘性角度出发,将血缘作为判定情感亲疏的基本标准,而以“不忍人”作为非血缘性个体间的情感纽带。
至此可以发现,以恻隐之情为发端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是基于人类基本情感所构建的复杂情绪,爱其亲的血缘之情包含于“四端”之内,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并非人际之间情感亲疏的决定因素。但不可否认,从情绪的社会化构建角度看,血缘之于情感的纽带意义具有两大合理性。第一,人类在婴幼儿时期离不开成年人的照料,其突出表现是婴儿对外部世界的最初感知来自其与母亲的亲密互动,母亲的凝视、点头、挠痒痒等一系列行为是促成婴儿情感向复杂情绪构建的外部刺激。因此,与婴儿具有最直接血缘关系的母亲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婴儿最亲近的对象,同时也是婴儿早期情绪构建的第一推动者。第二,饱经漫长社会历史进程的浸润,追溯祖先已经凝结成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特有的情愫。“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国语·卷四·鲁语上》)周代伊始,宗族内部的祭祀、祭祖的观念就已经在社会领域形成,至春秋时期,这一观念在文化辐射与典籍熏陶的长期经验积累中已变得牢固而坚实[5],并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后继诸子特别是儒家的思想。确切地说,早在春秋时期,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始祖情愫已经凝固成华夏文明体系中的关键基石,“血浓于水”“炎黄子孙”的社会文化价值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孟子血缘之情的思想正是基于此种社会化进程所构建的。
二、情法汇通:情理之优先与法理之回应
血缘之情、恻隐之情揭示出孟子以“情感为中心”的人际交往法则,这种交往法则始建于家庭之中,尤以血缘之情为重。以此为据,面对桃应“瞽瞍杀人,则如之何”“舜不禁与”“舜如之何”一连串诘问,孟子作出了舜弃天下“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的应答。历代学人大都将这一问答笼统地归结为情与法、忠与孝的对立,事实上,问题远非如此简单。“窃负而逃”的实质就在于肯定情感的优先性,就目前学界的研究近况而言,对此观点的合理性解释仍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始终跳不出中国哲学的传统范畴。因此也就无法被以逻辑性、科学性、系统性见长的西方哲学所承认、接纳。站在现代自然科学的角度,以西方哲学较为严密的逻辑思维阐释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不仅可以为中国哲学扬名助威,更可以为当今社会情法关系的处理提供良好的理念。
根据神经生物学的实证分析,“情感神经科学”(Affective Neuroscience)的创始人雅克·潘克赛普将情感定义为大脑的“行为系统”,认为情感和行动总是协同并进,并在此过程中构成“情感行为系统”,这一研究揭示出孤立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引导具体行为的发生的,因为思想必须依托于情感才可以开启行动的闸门。针对人脑运行方式的研究同样支持潘克赛普的观点,即思想只有在被情感地管理和经验的情况下,行动才是可能的[6]40。换而言之,二者都打破了柏拉图理性控制情感起主导作用的学说。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人类无法单凭理性行动,神经哲学家约书亚·格林以情感动机论驳斥了康德的伦理学义务论,认为当人们自以为出于义务而行动时,实则是因情感的驱动,而非合理的思考。如果说情感动机论的提出暗含哲学家之间的个人博弈,那么,海蒂·M.瑞文则从神经医学层面为情感动机论提供了强大的实证支撑:那些因神经创伤而丧失其道德认知的情感作用、情感管理的人,同时也失去了做道德决定和根据这些决定进行行动的能力。简言之,情感是人脑中能动性的源泉。在道德决策和具体行动中,情感动机的程度或强度随着做决定过程中所在乎的东西而不同[7]394,典型性的表现是,当有害行为是非个人性时,这些行为就不能激起人们的情感反应,尽管这些行为有时是非常严重的。然而,当伤害是个人的、近在眼前的时候,它就触发了关于大量神经活动的“类似警报的情感反应”[6]43-46。与天下相比,舜“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集注》),降罪于父近在眼前,人伦之痛远胜于将天下让位于他人,故而在强烈的情感驱动下“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
由上可知,以“窃负而逃”为代表的“亲亲相隐”制度具有足够的合理性,但要使其顺利纳入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之中,彰显其积极意义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在更为极端的情况下,受情感驱动的行为必须受到强力制约。弗朗斯·德瓦尔认为,在涉及道德抉择的紧要关头,情感所起的作用超过了理性。人类的道德是牢固地建立在以拟他性同心为核心的社会情感的基础上的,因而我们有着不杀我们自己所属群体中成员的强烈禁忌,更会反对那种涉及亲手对他者造成伤害的道德决策[4]59,这恰好呼应了孟子“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的深刻体悟。朱熹更是一语道出了此类行径的严重后果:“其实与自害其亲无异也”(《孟子集注》)。这就将“瞽瞍杀人”的预设推向了更为极端的情况:若被杀之人为人之父、人之兄,则如之何?显然的状况是:如果他者的感受及相关的行动与我们的设想相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认为他者的感受与行动(亦杀其父、亦杀其兄)是正当的[4]101。这种报复的倾向正是在高度情感地驱动下产生的。
在此情况下,存在于家庭与家庭之间的不再是某一个家庭内部的立基于血缘之情的差等的爱,而是具有公共领域属性的同等的情,此时“亲亲而相隐”已经站在了维护受害者情感的对立面并可能成为不良后果的催化剂。从更大的范围看,这种公共领域最终可延伸至“国”的范畴,当行为危害到“国”的公共领域时,相隐不再获得情感,包括法律上的广泛认同*《唐律·名例篇》规定:“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法治的必要性得以凸显。孟子在捍卫情感优先性的同时,并未排斥法治的理念,而是为相隐划定了适用范围*至秦代,“亲亲相隐”开始发展为法律。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贼杀伤、盗它人为‘公室告’;子盗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不为‘公室告’”;“子告父母……,勿听。”。舜受命于天,肩负域民之责,其言行具有国的“公领域”属性;身为人子,理应奉“亲”“尊”之行,其言行又具有家的“私领域”属性。借由极端性的预设,孟子坚定地表明了立场:情感具有伦理上的优先性,以家立国正是对此种优先性的坚守,但应区分“公”“私”领域,不可偏私而废公。舜弃*《说文》中捐、弃二字转注,清人焦循以捐释弃,认为弃乃“不惜”之喻。舜并无卸责之过。天下而遵海滨,由“公领域”转向“私领域”是捍卫情感优先性的前提。以此来看,舜的行为并没有践踏法律,让位于天下既可以实现自身向家庭内部私属领域的转变,以满足顺于父母的情感需求,同时保证了公共领域不受私情的左右,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法治的权威性,对此焦循作了精微的评判:“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荣父,遗弃天下。虞舜之道,趋将如此,孟子之言,揆圣意也。”(《孟子注疏》)更要看到,法治的初衷包含将高度情感地驱动的报复倾向以合乎理性的方式进行疏导,是对公共领域的情感——通情——的坚决捍卫*“亲亲相隐”具有现实意义。研究表明,在刑事实体法、程序法中,亲亲相隐的“新型”性主要体现在扩大权利主体范围,拓宽免责领域,构建情法统一格局三个方面。。
三、情感地共享:齐家以治国的可行性论证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一个有机共同体,家庭是其中最小组成单位。促成人类社会实现共享式发展,进而构建有机共同体是现代家庭与国家建设的基本方向。人类能否实现共享式发展?新脑认知科学可以为这一问题找到答案。新的研究表明,人类大脑神经具有极其强大、因神经元的变化而引发的可塑性,虽然这种可塑性能够朝着积极、消极两个方向发展,但我们已经找到并证明了一种可以使人类回归道德轨道并勇往直前的方法:个体不是作为“原子”孤立地存在于身体的躯壳中。与之相反,个体可以超越自身,进而融入到诸如自身的关系、家庭、社会、文化和历史等领域,并被指派到这些领域中的特定位置。这种融入特定领域、超越了自身的自我使伦理成为可能,因为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以及自我与环境之间的界限被模糊[7]343,内在的自我与外部的世界彼此互相影响,自我和“他者”就处于一种共享的状态。这一研究成果强有力地证明了儒家特别是孟子“修身”思想的科学性。修身就是对自身的超越,是个体努力把自我放置于一个特定领域中并希冀与其实现共享式发展的实际行为。孟子将这一特定领域设置为与个体密切相关的最小、最直接的群体性组织——家庭,并赋予家庭社会化*家庭的社会化并非等同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前者强调在确保家庭完整性的前提下帮助个体实现预期社会化,后者则将家庭纳入社会的体系之中,迫使个体与家庭分离。的结构,倡导个体在家庭中规范对自我的定位,与家庭实现共享地发展,由此将这种发展推向国乃至于天下(国与国)的更大范围的群体性组织中。这就是儒家借由修身以达成齐家、治国、平天下共享式发展的逻辑依据。
此外,人类的进化也同样沿着共享式发展的轨道前进。在生物学进化论的框架内,物种之内或物种之间的群体对群体的竞争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群体间的互助与合作,即推动群体发展而非仅益于单一个体的行为、独立的道德价值是促成人类完成社会性进化的基本原则[3]1062。与神经可塑性的积极性影响类似,进化的原则表明实际的情况是,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如年龄性群体、目标性群体、种族性群体等互相接触而不被孤立,处于一个保护他们避免互相挑战的领域[7]151,家庭便是这一领域的起点,由此也就具备了社会化的形态,这自然是在具体的社会形态向着更高一级的国的转化实现之后,进而揭示出贯穿于以家立国理念背后的是符合人类进化原则的共享领域的生成与延续,家庭、社会、国家、天下亦或全球化是共享领域由初级到高级的表现形式。
还应当说明,人类的进化与神经的可塑性为什么能够朝着积极共享的一面发展呢?新脑认知科学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人类共享自我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这是一种神经元的集合,当个体作出具有特定目的的实际行为以及观察者看到另一个个体实施相似活动时,神经元集合被瞬间激发,紧随其后的是在大脑的“镜像系统”(Mirror System)中对此类行为由内而外地高度模拟,尽管并不一定表现出来,但足以证明:镜像神经元促使我们可以直接地理解有关于他人的目标和情感——这就是人类具有通情能力的主要原由*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神经机制是自映射。研究认为:人们相互交流和理解得越多,大脑活动的模仿就越多,他们也就更能够融合在一起。。由此回过头看,个体设法超越自身、遵循进化的法则,都需要借助于通情的推动,正如潘克赛普所指出的那样,神经可塑性是一种“能够用热烈的情感来浇灌‘冰冷’概念的古老的情感系统”[8]。这样的情感系统能够确保我们以家庭这一原初群体成员的身份,朝向共同的目标:齐家,进行多样却并非方式具体同一化的努力。家庭中的每个人成员对自身及家庭的群体性行为都应当负有责任,以营造并维护良好的家庭发展氛围,这是因为特定的情境反过来可以决定群体的行为,并且只有正面意义的情境可以促成共享的实现。
近年来,针对纳粹大屠杀的研究证实了一种观点:当涉及普遍的个体时,在毫无批判的情况下对既定情境程式化解释的接受是犯罪的症结所在,这其中又包含了对权威的消极服从,因而表面上正常的普通人往往会成为非道德行为的潜在追随者,虽然他自身并非是这种行为的制造者。这的确令人感到吃惊,但一个纳粹医生将犹太人比喻成人类身上坏死的阑尾*案例源于心理学分析学家罗伯特·罗伊·利夫顿对纳粹医生的研究。研究发现,战前那些一直在从事恰当工作的正常人最终都背离了他们的组织和职业而变成了屠杀者,其屠杀行为并非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源于对整个场景与权威的消极接受。的荒谬谎言已然取得了广泛的赞同。可以肯定的是,充当纳粹帮凶的普通人绝不会是无辜的,我们不能否认群体行为中的个人责任,亦如汉娜·阿伦特坚称的那样,集体导致的过错无法掩盖自身在集体中成员的身份,这种身份不同于随时可以解除的商业伙伴关系,因而负责是成立的[9],甚至必须针对个体没有做过的事情。非常明显,恶的情境可以改变甚至决定人的意志,导致了个体对群体事件中自身责任的否定,迫使通情与犯罪为伍。
为了在生命早期向着最好的方面塑造我们的大脑,创设良好的情境,实现人类共享式的发展,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敏锐地发现了:家庭这一共同体是个人借以同该共同体中其他成员建立毕生信赖之联系的那种感情的一个结果[10]。它赋予个体社会化成长的模拟空间,以通情构筑起持久的人际关系,以规范自我的定位达成对自身的超越,以携手齐家营造共享的氛围,最终使个体顺利地加入他们所属的群体性社会,而国家的持续稳定与健康发展就依赖于这样的活动。综上所述,基于本文对孟子家庭思想的探讨以及学界的最新研究,现代新脑科学的蓬勃发展已然将传统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平台,其意义与成果必将是显著而非凡的。
[1] 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159.
[2] 勒内·笛卡儿.心灵的感情[G]//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23.
[3] NOWAK M A, TARNITA C E, WILSON E O. The Evolution of Eusociality[J].Nature,2010(466):1057-1062,1062.
[4] 弗朗斯·德瓦尔,等.灵长目与哲学家:道德是怎样演化出来的[M].赵芊里,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3:54,59,101.
[5] 吾淳.中国哲学的起源——前诸子时期观念、概念、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成型的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537.
[6] GREENE J D. The Secret Joke of Kant' s Soul[G]//SINNOTT-ARMSTRONG W. Moral Psychology.Cambridge:MIT Press,2008:40,43-44.
[7] 海蒂·M.瑞文.超越自身的自我——一部另类的伦理学史、新脑科学和自由意志神话[M].韩秋红,刘金山,谢昌飞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94,343,151.
[8] PANKSEPP J, PANKSEPP J B. The Seven Sins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J].Evolution and Cognition, 2000,6(2):114.
[9] 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M].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54.
[10] 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32.
Sharing Affectively:Exploring Statecraft in Mencius's Family Thoughts: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Science of Brain Cognition
ZHANG Liangli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The study of modern science of brain cognition has proved that Mencius's idea that blood relation determines the emotional distances is quite rational. Human kindness among non-blood-related individuals is complex emotions derived from the basic human emotions. The rapid advancing of brain science explains Mencius's ideology which affirms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mil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bond 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family construction in statecraf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science: human emotions affect the behaviors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empathy triggers sharing behaviors; moral choice of empathy is under the powerful control of the fixed situation in which groups settle. Building healthy and active brains, following the rules of emotions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situation have been widely accepted in the science of brain cognition. It also provides a new direction of thinking for Family-Country Isomorphism,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governance.
emotion formation; priority of affection; empathy; situation
2017-09-06
安徽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研究项目(yfc100095)
章亮亮(1988-),男,安徽合肥人,硕士生。
B222.5
A
1008-3634(2017)06-0039-05
(责任编辑 刘 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