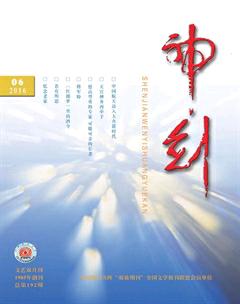从历史记忆的断裂处书写
郑润良
在当代文坛,安徽作家洪放应该算得上一个“异数”。1968年出生的洪放,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发表诗歌作品,90年代后开始散文创作。代表性作品有系列组诗《苍茫》,发于《诗刊》等五十多家报刊,曾获安徽省政府文学奖、首届鲁彦周文学奖提名奖等奖项。从2 007年起,洪放突然放弃了自己写得越来越顺手的散文,写起了小说,而且是从长篇写起。或许是彼时方兴未艾的官场小说热激发了他的灵感,他发掘自身多年的机关工作经验,写出了《秘书长》系列长篇小说、《秘书长》《挂职》《党校》《领导司机》《最后的驻京办》等官场小说。在洪放看来,“官场亦是世象之一部分,官员亦是人群之一部分,只是这一部分不为更多人所了解、熟知,或者说:这一部分现在发生了畸变、模糊、曲折和隐晦。关键是:不管什么题材,你必须得是文学,得是小说。文学性和对人性揭示的重要性,必须蕴含在作品之中”。(洪放创作谈《为人性的深井借一束光》)这些小说不仅获得了市场意义上的成功,而且由于作品有着作者自身丰厚的生活积淀及其扎实的写作功底,以及作者对官场生涯寄予的人文思考,使得这些作品获得了与通常的“官场小说”不一样的人文深度与品格。
在《菩萨蛮》《苏幕遮》等作品中,洪放事实上还是主要聚焦自己熟悉的官场生活。《失踪者》是洪放最新创作的中篇小说。这一次,作者没有将目光对准官场,而是移向了历史记忆的深处,移向历史记忆的断裂处,以文学语言书写20世纪30年代初鄂豫皖苏区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历史悲剧。是什么样的因由使得洪放选择了这一相对陌生的题材领域呢?这一题材的选择对他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事实上,1934年红军长征之前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各种势力、各种矛盾复杂纠结的时期,国民党内部左右派、中间派的对峙、割裂,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军队斗争时一方面要应对国民党的多次疯狂围剿,还得应对共产国际的僵硬指示、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位指挥,党内军内不同的声音以及人民军队初创时期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等等问题。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才发生了肃反运动以及肃反扩大化的悲剧。这种纠缠复杂的关系、尖锐的时代矛盾、悲剧性元素等等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广大的空间。可惜,因为种种原因,这一题材领域尚未得到很好挖掘。洪放选择了这一题材领域加以表现,无疑表现了他的睿智和勇气。
作者在题记中写道:“据有关资料介绍:红军时期,仅安徽省金寨县一地,就为中国革命牺牲近十万人。这里面,还不包括因各种原因失踪人员三万余人。这些失踪者,被隐没在红军史中,成为中国红军史上最难以释怀与疼痛的一笔。”这一题记为作品增添了一份无比凝重的力量。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弘扬、讴歌红军的长征精神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主旋律;但是,我们的文艺作品在表现1927年到1937.年红军的革命历史时,是否也应当看到在人民军队成长的初期阶段,这支军队所曾经经历的苦难、挫折与内耗、曲折以及在内耗、曲折中无辜逝去的英灵呢?迄今为止,关于20世纪30年代肃反运动,相关的学术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在文学创作领域,除了贺捷生《高耸入云的碑》等报告文学作品有所涉及之外,依然少有作品对此加以表现。
在对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事件进行文学书写的时候,首先对相关历史史实进行探究是非常必要的。关于鄂豫皖苏区肃反运动的起因,在现有的学术探讨中依然有争议的空间。大部分学者认为主要归因于张国焘等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学者姜义华的观点比较典型,“肃反锄奸,本是革命队伍内部一项正常而必要的工作。可是,在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时期,肃反却被用来对付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持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它使‘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推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一党内斗争的错误原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九三一年秋冬间鄂豫皖苏区所进行的‘肃反,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主持这场‘肃反的,是当时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事委员会鄂豫皖分会主席的张国焘。”(姜义华《论一九三一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另一些学者则对此观点有所商榷和补充,比如张永在《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新探》一文中指出,除了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沈泽民、陈昌浩等的“左倾”教条主义,鄂豫皖肃反发生原因至少应补充三点:一、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二、20世纪30年代初政治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容易诱发冤案;三、红四军干部在南下行动中对抗中央分局,违反了“党指挥枪”原则。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不是2500人,约有800人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被捕,其中小部分人被杀,另外有超过1500人作为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被驱逐出红军。中下级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不管这次肃反运动的正当性是否存在或是否充分,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悲剧则已成为公认的历史事实。对这一历史悲剧进行文学化的书写不仅是修复历史记忆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告慰那些在历史中无辜逝去的英灵的一种方式。那些失踪者的命运究竟如何?他们在生前经历了怎样的悲欢离合?洪放的《失踪者》力图通过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命运故事对此加以解读,让人们在八十多年后重温那段充满热血与忠诚、幽暗与惨烈的历史。
《失踪者》没有正面去描述被“肃反”者所遭受的种种悲剧,而是从悲剧的幸存者的角度进行书写。小说从女主人公丁小竹去驻在接善寺的保卫局送文件写起。丁小竹十八岁,从农会被转到保卫局后,负责通讯联络,具体事情就是负责传递保卫局内部往来文件。丁小竹和保卫局的叶局长之间的第一次对话就说明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情形。叶局长问丁小竹:“昨天晚上那个黄老根是不是叫了一晚上?”“是的。一直在骂。说他冤枉。”丁小竹说,“黄团长说他革命这么多年,一心想着打白匪,怎么忽然就成了AB团?他说他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过。”叶局长的回应是,“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AB团的。越是反动,越是顽固。丁小竹同志啊,斗争很复杂哪,很复杂!”这种荒谬的审判逻辑不尊重事实和证据,完全凭借上级精神和审判者的主观臆断,由此导致无数冤案的发生。事实上,正如后来许多学者指出的,政治保卫局这些干部的素质低下是肃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丁小竹之所以被信任,派到保卫局工作,是因为她出身贫农,没有文化,不识字,能够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指示。小说通过人物对话等提到,许多军队高级干部都被抓走并处决。相关史料也提到,一些师从班长以上的干部都被当作AB团、改组派、第三种势力抓起来。他们最好的出路是被遣送回乡,剩下的则被无情处死。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江子龙就面临这样的命運。丁小竹从叶局长手里接过的文件中已经下达了对他进行处决的命令。在江子龙下属丁三树的提醒下,丁小竹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不要参与江子龙的营救计划。作者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让我们接受了丁小竹的选择。江子龙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虎口之下取回丁小竹哥哥的头颅,让丁小竹的哥哥得以全尸埋葬,并做了丁小竹的“干哥哥”。这份情谊不亚于血缘关系,并且掺杂着青年男女之间的隐秘好感。在冰冷的组织命令和个人情感偏向之间,丁小竹最终选择相信自己的感觉。事实上,纵览现当代文学史,无论是张爱玲的《色戒》还是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丰乳肥臀》中的女性形象,女性似乎天然地与政治主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使得她们更相信日常生活、相信常识与伦理感觉,而不会轻易投入时代政治的风云中。丁小竹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似乎也确证了这一点。江子龙三人在逃脱后并没有改变自己革命者的本色,在敌我夹击的情况中,仍然试图以五支队独立分队的名义展开对白匪的斗争,说明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纯正的革命信仰和理想。在丁三树被白匪击毙、丁小竹失散的情况下,他一个人仍然坚持对敌斗争,让敌人心惊胆战。和丁小竹重逢后,他们在相濡以沫的生活中走到了一起,成为一对夫妻。最终,在白匪的包围中,他把怀孕的妻子藏了起来,自己壮烈牺牲。
小说通过江子龙、丁小竹的经历反映肃反扩大化的历史悲剧,虽然没有对处身悲剧中的历史人物的遭遇进行正面书写,但还是有着“一两拨千斤”的功效,让有心的读者通过这个故事感受当时的时代氛围,缅想历史中沉沦的英灵。
新时期以来,对红军历史功绩的正面书写在文学创作领域应该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对于红军所曾经遭受的挫折,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很多作家都止步不前了。正所谓,“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失败的历史同样需要我们去直面。书写失败的历史、失败的英雄同样具有总结历史经验、启示未来、凝聚正能量的作用。正如八十年代乔良的中篇小说《灵旗》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敢于直面并深刻书写湘江战役这一失败的战役中的历史人物及其心路历程。徐贲在其文章《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写道,“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如果以《灵旗》作为比较,洪放的《失踪者》在哲理的思考、人性深度的发掘、人物关系复杂性的揭示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这毕竟是当代小说家在这一题材领域做出的第一次开掘,其意义自然深远!
责任编辑/刘稀元